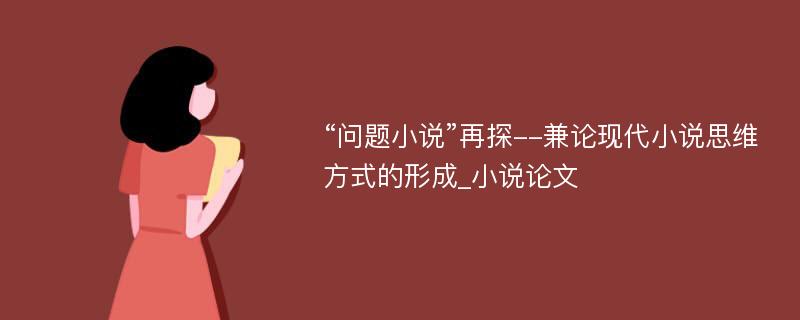
再探“问题小说”——兼论小说现代思维模式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思维模式论文,再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外延模糊的“问题小说”
当“问题小说”从个人的言语活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文学言语符号,就意味着这个偏正词组从此具有了指代一种文学创作现象的意义。那么,问题小说的定义是什么呢?
在已查到的、都有“问题小说”这一词条的6种文学词(辞)典[1]中,由于研究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认识不同,除了在小说题材是反映社会“问题”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以外,在其他方面都存在分歧。对于“问题小说”产生原因的理解,存在着“由易卜生的‘问题剧’演化而来”、“被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唤醒”、“人道主义新思潮的输入”、“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的不同说法,这源于研究者对其创作时间、所囊括作家作品的认识差异;对于“问题小说”的创作时间主要有四种意见:“‘五四’过后,二十年代初年形成的小说流派”、“新文学运动的前十年出现的”、“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后期”。时间的不确定引起对代表作家及作品的认识不一致:或者把《新潮》小说排除在外,或者把文研会“为人生”派十年间的创作都混入其中,甚至还有联系到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从而造成“问题小说”这一概念外延(即所包含的小说文本)的模糊。文本(量)的不确定,造成了对“问题小说”内涵(质)理解上的偏差。
对《新潮》小说和文研会作家作品的理解,是产生种种分歧的焦点。这二者是同“质”的么?能否一起构成“问题小说”的内涵?若异质,差别在哪?产生不同的原因是什么?若从创作思维特征分析《新潮》小说和1921年《小说月报》刊登的小说,则应该能看得更为清楚些。
一、旁观者·想象·再现——问题小说与近代小说思维模式
“问题小说”这一概念的提出,首推周作人。在1918年4 月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他评价了日本近代文学中“问题小说”的地位。又于1919年2月发表了《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明确提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2], 强调“以小说为闲书”的中国传统不可能产生“问题小说”,从而规定了“问题小说”的“近代性”本质,也就是小说文本中蕴涵的近代小说思维模式。
所谓近代小说思维模式,就是晚清以来,作者、批评者在小说观念上不再迷信传统“小说”的定义,但又囿于历史阶段的局限,不能形成完整的、有系统的现代小说思维模式,而呈现出一种比较模糊的小说创作思维状态,这可以从当时《海上花列传》等创作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论批评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新小说的功用在于“新民”,把小说提升到与传统散文、诗词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但达到的方法,却还是传统小说想象性再现事实的方法:“人之恒情……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3]
这里提出了小说的题材是真实(“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的,而非传统小说的“虚构”,要“摹写其情状”、“和盘托出”、“彻底发露之”,这样一种近代小说思维模式,蕴涵了这种思维模式的近代小说文本内部呈现出矛盾的特征,《新潮》小说亦不例外。
所谓《新潮》小说,指的是刊登在杂志《新潮》上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短篇小说。《新潮》杂志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团体新潮社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出版的一种宣传新文化、倡导文学革命的杂志,到1922年第三卷第二号结束时共发表小说26篇。创作者主要有汪敬熙、叶绍钧、杨振声、罗家伦、俞平伯、欧阳予倩等。
这些小说发表的刊号、篇名、作者如下:
第一卷第1号:《雪夜》、《谁使为之?》,汪敬熙
第一卷第2号:《一个勤学的学生》、《一课》,汪敬熙;《断手》,欧阳予倩
第一卷第3号:《渔家》,杨振声:《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这也是一个人》,叶绍钧
第一卷第4号:《一个兵的家》,杨振声;《花匠》,俞平伯;《怪我不是》,某君
第一卷第5号:《新婚前后七日记》,任銒;《春游》,叶绍钧;《洋债》,郭弼藩
第二卷第1号:《明天》,鲁迅;《砍柴的女儿》,K·S;《炉景》,俞平伯
第二卷第2号:《死与生》,汪敬熙;《一个好百姓》,杨钟健
第二卷第3号:《狗和褒章》,俞平伯
第二卷第4号:《两封回信》,叶绍钧
第二卷第5号:《伊和他》,叶绍钧;《贞女》,杨振声
第三卷第1号:《不快之感》,叶绍钧;《磨面的老王》,杨振声;《贵生和他的牛》,潘垂统
(按:尽管《新潮》杂志出版历时3年之久,在第三卷第1号的“目次”上,标有“民国九年出版”的字样,但根据1920年他们对于不能按月出杂志而做出的如下种种解释:(1)因国内事变太多……(4)出版迟延[4](P1076)),我们可以推断它们都是在1919—1920年间创作的。)
《新潮》小说的创作模式,基本可以代表当时在文学革命倡导下的小说创作状态。不论是根据傅斯年等人的回忆:当新潮社“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5](P201),还是根据杂志的销量,应该说,《新潮》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在《新潮》上发表的小说,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个期刊(《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少年中国》——笔者注)和社团”[6](P5),1920年5月出版的《新潮》上,也记载了对同期出版状况的评价:“五四以来,中国的新出版品,虽是骤然增加四百余种,但是最大多数是没有成熟的”[7](P859)。这些都说明了《新潮》小说创作具有新文学草创期小说的代表性。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从结构小说文本的语言方式能反映出作者的思维方式,因此,从《新潮》小说的文体特征可以反观出新文学提倡者的小说意识。
这些小说是胡适“横截面”理论的实践者和体现者。1918年5月刊载于《新青年》4卷5号上的《论短篇小说》,是新文学早期小说理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本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小说科所做的讲演。其中胡适提出了“横截面”理论,他针对“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现在的报纸杂志里面,凡是笔记杂纂,不成长篇的小说,都可叫做‘短篇小说’”,提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认为“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是指“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新潮》小说作家们奉该理论为圭臬,认为胡适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集中诸篇都是选择最精可为短篇范本的小说,后附胡先生所著论‘短篇小说’一文详说做短篇小说的方法,也是研究文学门径的人不可不读的文章”[8](P1077)。
既然是描写事实,而且是“生活”、“历史”、“变迁”的“纵截面”、“横截面”,摹仿阶段的作者们在小说叙述中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旁观者的视角,把用想象来再现事实作为目标。《新潮》小说的主要文本特征:描写、场面、社会,是作者此种小说创作思维的明证。
作者的学生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从旁观者的角度为劳动人民的贫苦打抱不平。《雪夜》、《断手》、《渔家》、《一个兵的家》、《洋债》、《死与生》、《一个好百姓》、《磨面的老王》就是以描写的方法再现穷人生活苦难,还有摹写封建制度下婚姻家庭悲剧的《是爱情还是苦痛》、《这也是一个人》、《新婚前后七日记》、《春游》、《明天》、《砍柴的女儿》、《炉景》、《狗和褒章》、《两封回信》、《贞女》,和讽刺教育的《一课》、《一个刻苦的学生》、《贵生和他的牛》。这些小说,展现的都是一个现在时的生活片断,没有时间空间上的重叠。其中蕴涵了“我(显或隐)—看—他(们)”的模式。叙述者是个站在圈子外的“人道主义”的旁观者,即使用第一人称(如《花匠》)叙述,也只是为了增强所述事件的真实性。《是爱情还是苦痛?》的结构是一个嵌套模式。小说的总框架是叙述者“我”—看—叔平,又嵌套了一个叔平的自述,但它没有反思和自我批判色彩,而是认为“我一生的幸福,前半是把家庭送掉的,后半是把‘人道主义’送掉的”,自己只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未能脱离“我—看—它(家庭、人道主义)”的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决定了想象在结构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想象,在《韩非子·解老》中解释为:“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这里的象,不仅是形象,更是一种印象。这些小说再现的只是一种印象,而不是思考,更别提对自我作批判性反思。这决定了这些小说不会有更深的思想深度。叶绍钧在1921年就已认识到这一点,“他人要我们讲些故事消闲……故其所表现每为事事物物之表面,而不能抉其内心”、“作者若有独特的精神,浓厚的感情,则不论若何平凡细微的事,乃至全无事实而唯有感想,都可以为真实的动人小说”[9],这也暗示了1921年以后的小说创作与《新潮》小说的不同所在。
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卷·导言》中评价这一时期创作的缺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一角,第二是观念化”,并且指出原因在于作者本身缺乏思想深度,“他对于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活的知识……缺少真正的透视和理解,他不能把他的材料好好地分析组织,试来一个大规模的全面表现。”“观念化”批评的是,创作者的“想象”思维;批评“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一角”,则意味着颠覆“再现”、导引出“表现”。
回异于古典小说的气质,和偶现的某种现代小说品格,犹如一层迷雾,遮蔽了《新潮》小说的近代性,模糊了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也增加了“问题小说”命名的难度。从发生、影响、作家作品、题材、结构方式、思维模式等多方面来明确“《新潮》小说”这一概念的内涵,才能理清“问题小说”与“《新潮》小说”的关系。因此,蕴含有近代小说思维模式的《新潮》小说属于“问题小说”,是勿庸置疑的。
二、亲历者·联想·表现——1921年《小说月报》创作中的现代思维模式
在以往文学研究中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对于“问题小说”与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小说关系的认识,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代表性的描述如下:
一、“‘问题小说’的兴盛是在五四以后二三年间……有的论著将‘问题小说’归属于‘人生派’或文学研究会一派,是与史实不符的。”(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二、“到1919年下半年……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更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高潮……只是‘五四’前后三四年间的一股小说‘题材热’。”(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三、“问题小说的初出固然是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1918年—1920年间,但……王统照等文学研究会会员的创作不可分离。”“问题小说的著名作品还有《买死的》(李渺世)……通常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但也有些作家试图找寻答案,以‘美’和‘爱’来弥合缺陷,净化人生。”(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引文一认为二者不同,引文二、三都认为文学研究会在1921年、1922年的创作应该是“问题小说”的主体。那么,1921年后以《小说月报》为会刊的文研会小说创作是否与其前的《新潮》小说具有同质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分析1921年12卷的《小说月报》入手。
根据《〈小说月报〉索引》“小说”类中篇名统计,1921年(第12卷)的《小说月报》被茅盾接编革新后,成为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园地,共发表57篇小说。这些小说隐含的创作思维机制与《新潮》小说有明显不同。
首先,是对“再现”思维的突破。在这一年的“创作”栏目中,没有一篇是以《新潮》小说用对话结构文章以求再现情景的方式进行创作的。与《新潮》小说的创作方法、审美特征如出一辙的仅有6篇文章:《幻呢真?》(直民)、 《完卵》(普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天石)、《人间地狱》(陶雪峰)、《救命呀》(缩飞)、《一个兵士底忏悔》(范鸿劬),都被辑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六号特辟的“特载”栏中。“特载”专栏之意,类似于今天的“特写”,而“创作”栏中的作品,才被看作是小说,区分出“特载”和“创作”两个栏目,说明编者评判小说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改变。第七号“创作讨论”专号登载的8 篇文章:《创作与哲学》、《创作的要素》、《社会背景与创作》、《创作的我见》、《怎样去创作》、《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创作的前途》,更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当时作者和读者对小说创作思维方面的要求。他们普遍认为之前的小说创作存在着“单摹外相”、“平凡和浅薄”的弊端。对创作者提出很多要求:“创作文学时必不可缺的,是观察的能力;两者偏一不可,表现的两个手段是分析和综合”[10],这要求小说中叙事者不能再以局外人作冷眼观,施舍一点廉价的同情,而是要以亲历者的身份表达感想,进行反思。尽管如同早期把自然主义混同于现实主义,他们此时也并不十分明晰想象与联想、再现和表现的差异,但强调创作要有个性:“组成创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个性的情感,这种绝不是万人一律的”,提出“思想是文学的本质”等,这些观点表明,《新潮》小说“想象地再现事实”的创作思维已经被要“表现”思想、情感的创作思维所替代。
其次,联想是小说“表现”思维实现的重要手段。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很多小说创作中,联想都是结构文章的主要方式。此时的新文学倡导者似乎也在有意无意间,用“同题征文”等形式培养、锻炼创作者的联想思维能力,从第九号开始选登的6篇“风雨之下”同题征文(注:6篇分别是第12卷第9号的高歌、王思玷2篇《风雨之下》,第11号上孙梦雷的《风雨之下》,和第12号杨之甫、俞文元、周志伊的3篇《风雨之下》。),就是为了考察创作者能由此题联想到什么内容。联想是由此及彼、连绵不断的思维过程,是现代散文创作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和组织结构最主要的方法。根据被联想在一起的二者间的关系,可分为相似联想(类比、接近)和对比联想、遥远性联想。运用在小说创作中,使文本呈现出描写渐有被主观化的叙述取代的趋势,冲淡了小说情节的叙事特征,叙事者的身份也从《新潮》小说事件外的旁观者,变为事件中浮想联翩、感慨万千的亲历者。正是由于在小说创作中引进了联想的思维方式,通过联想对想象的超越,从而实现了意象对形象的超越,为“五四”小说文本多重时空叠印造成的美学效果提供了可能。
冰心的《笑》(第1号)就是运用类比联想来结构全文的。 正是通过这些语句:“‘这笑容仿佛在那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这笑容又仿佛是那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把3幅画面中的笑连成1篇文章,来歌颂笑和爱。在庐隐女士的《红玫瑰》(第7号)中,类比联想起到的是引出故事的作用,“一个医生曾告诉我这是一种病——叫做‘男女性癫痫’。我想到这里,忽觉心里一动,他的一件故事不由得我不想起来了”,先提出小说主题,叙述的故事是这个观点的例证而已。荣鼎《儿时的恐怖》(第8号)运用的是联想另一种方式:接近联想,前后结构并不均匀,类比联想过渡句“忽又记起十一岁的一年,我……就遇见一个疯子,手和脚都带着铁链,——想是怕他暴动,才这样的设施——同将才的疯子差不多的样子”,是为了阐明疯子“疯”的原因和我怕疯子的原因。叶绍钧《苦菜》(第4号)中,先是描述福堂厌倦种田的故事,运用联想推理后归纳出一种现象“从‘种田的厌恶种田便致怠业’,推衍出‘作工或教书的厌恶作工或教书便致怠业’,更可归纳为一个公式:‘凡从事X的厌恶X,便致怠业’”,从而得出“X决无可厌恶的地方,可厌恶的乃是纠缠着X的附生物。去这附生物,才是治病除根的法子”的结论。
除相似联想外,对比联想也是这时小说创作常用的布局方式。比如伯颜的《幸事》(第6号),就是用东京对汽车撞人事件的处理,和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进行对比,来反衬中国穷苦人的不幸。文中把描写的几个场景连接起来的方式,是用过渡句“我眼所见的,耳所听见的,引起我心中一重过去的印象……我想到这里,心儿往下沉了,但残忍的思想又引我到别的一重印象上”、“……想到这里,心越发沉重了,不能再想了;——不幸!今天见的那个被电车撞伤的人,还算是运气的啊”来实现的。还有一种不用过渡句的对比联想,比如易家钺《命运》(第11号),用以前的优越生活和现在的落魄对比,来表现许舅妈这一类迷信命运的人的麻木,尽管表达上缺少明显的过渡语句和段落,但是内容结构采用的还是前后对比的联想方式。朱自清的《别》(第7号)用对比“反衬”的方法,先写“合”的不容易和在一起的幸福与快乐,来反衬不得不“别”的痛苦,后以具有总结性的议论“为一百元底缘故,他俩不得不暂时贱卖那爱底生活了”,表达出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为了突出思想,对比成为结构小说的一种重要方式,起到“反衬”的作用。
对意象深层意蕴塑造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遥远性联想。以上三种联想涉及的两者之间,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而遥远联想则是关系不太密切或者无关的事物间的联想。“遥远性联想是衡量思维是否具有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指标”[11](P175),用在小说创作中,把形象意象化了。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语),就是因为作者具有遥远性联想的思维方式。《荷瓣》(第1号)、《天亮了》(第8号)等,甚至是《死后二十日》,这看似虚构实则较为特殊的、有寓言意味的小说创作,遥远联想是其创作的主要构思方式。遥远联想和想象思维结合后,赋予思想以形象,从而达到暗喻象征的效果。尽管这种结合还不成熟,有牵强性和突兀感,但是它们暗示了现代小说的发展方向——对象征性的追寻。
用联想思维结构小说,为人物进行自我反思提供了多重空间,使现代小说蕴涵了“我看〈——〉我被(我)看”模式,正如陈平原所言“促进小说叙事时间转变的,主要是普通心理学研究和‘联想’”、“‘五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种自由联想的权力赋予小说人物时,小说的叙事时间不能不发生剧变”[12](PP57—58)。联想思维的运用,给1921年以后《小说月报》的小说创作染上强烈自我批判色彩。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一种自己批判自己的态度,是一种反对自身的反思趋向”[13](P9),以联想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小说思维模式,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思维模式。《新潮》小说与1921年以后文学研究会小说的不同本质由此可一目了然。
三、“散文化”——思维模式转变原因之一种
从《新潮》小说到《小说月报》1921年小说,短短几年时间里,小说文体形式发生了上述转变。究其原因,历来的研究者都归功为西方文学思潮和时代环境的背景,而现代散文发展对现代小说形成的影响却甚少被提及,从思维方式转变的角度考察,现代散文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议论性报刊散文训练了现代人的白话思维;二是“随感录”文体的影响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当然,二者也都烙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用文言创作的传统散文历来被用于阐释“微言大义”,传统的语言材料“文言”及相应的语法习惯,都是专为统治阶级垄断的。想打破少数统治者长期形成的知识或言论领域的集权式垄断,就要求作者表达出的思想不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服务,而是包括所有能识字读书的下层平民,其当务之急就是语言和表述方式的变革,用“白话”取代“文言”进行思维表达思想。现代传媒的发展、西方思想的传人为中国散文创作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契机。
这种变革早在1874年就已经开始了。从1874年到1885年,王韬所创办的被称为“中国人自办日报获得成功之最早一家”的《循环日报》,约发表了890篇政论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王韬手笔[14](PP156—157)。这种专为报刊撰写的政论文体,一般根据报纸版面需要而采用短小精悍的形式,明快而雄辩,既议论和陈述政见,又具有强烈的修辞感染效果。由于这些政论文时常被国内报刊转载(如仅《申报》就转载了近百篇),引发“仿效”浪潮,致使这种新文体如火种般渐渐燎原。虽然此时的语言文白夹杂,实际上开创了一种议论时政、传播不同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新现代政论文体,成为后来梁启超“新文体”实践的基础。从1874年到1919年,中国现代政论散文近45年的发展,到“五四”时期最早的几种进步期刊中,白话政论文已经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
更多的中国人通过阅读报刊中的“白话”政论文,被唤醒了主体意识,这些议论性报刊散文深刻地变革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属于思维方式的转变……获得了一种用以观察一切问题的新思维方式”[15](P112),新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于对“人”主体性的肯定,对自我的关注。强烈的自我表达需要,为突破传统小说思维模式中的“再现”功能观,为形成现代小说创作的“表现”观提供了可能。这是从文学观念上改变了小说作者的创作思维模式。
直接影响着“五四”小说文体形式的,是“随感录”。它从篇幅、结构等多方面对现代小说创作思维模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青年》创刊后,便有了批判孔学、号召思想革新的议论散文。这些文章多是阐发新思想,批判旧观念,介绍西方各类思潮的。当时既有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论文,也产生了一些篇幅短小、甚至仅三言两语、却颇有战斗力的短论,这些文章都是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特别是其中的短论,由于短,不能过多谈经论道,却可以在文字技巧上多下功夫,锻打锤炼,使其成为尖锐精巧的语言精品,后来形成一种“随感录”文体。
1918年4月,《新青年》杂志自第4卷第4期起,开辟了《随感录》专栏。 之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新生活》、《新社会》、《晨报副刊》等报刊杂志,也相继开辟了《随感录》专栏,推波助澜,这种文体盛极一时。甚至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刊的小品文期刊《人间世》也延续了这一传统,设置了“随感录”专栏(前12期)。
几家主要刊物刊登的数目如下:
《新青年》130余则(1918年至1921年1月)
《每周评论》250余则(1918年12月至1919年8月,仅存8个月)
《晨报副刊》900余则(1918年至1924年)
《民国日报·觉悟》1500余则(1919年至1925年)
这些作品,“大都是以‘随感录’为总题刊出的,如果把各个刊物的‘杂文’、‘杂谭’、‘杂感’、‘杂评’、‘乱谈’、‘浪漫谈’、‘随想’、‘小言’等栏目内刊发的作品统统加起来,其数目是相当惊人的”[16](P29)。
“随感录”的成功与小说创作的寂寞构成鲜明对比。“随感录”鲜明的“思想性”和“个性”特征,成为当时评价小说的标准。因此小说作者面对缺乏“思想性”、“个性”的指责,会自觉不自觉地借鉴“随感录”创作经验,就不难理解了。
“随感录”创作对小说创作思维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都对现实作出敏锐的反应:有的迸发着昂扬奔放的激情、燃烧着讽刺的火焰,如李大钊的《青春》、《今》、《新的!旧的!》、《新纪元》、《政客》、《宰猪场式的政治》等;有的则充满战斗精神,如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底误会》、《反抗舆论的勇气》等;还有“颇汪洋,而少含蓄”(鲁迅语)之钱玄同的“随感录”,和更具艺术性的刘半农“善夸张,富想象,好用反语,讽喻性强”的文章,都以针砭时弊为目的,是作者进行社会批评的武器。这种文体的创作浪潮,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得到回应,林语堂创刊《人间世》时,仍然设立了“随感录”一栏。它的敏锐性冲击着现代小说创作,使小说在题材上更关注现实。而不同作家表达风格的差异,也启发了早期小说创作的研究者,去纠正新潮小说存在的单一化、简单化倾向。其次,是这种随感形式中蕴含的联想思维,给小说创作带来生机。联想思维在文学创作中发生作用,是以知识积累和认识深化为前提的。它的哲学基础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观,它的实质是“联系”方法论的体现。随着人类对时空分离和时空重组认识的不断深入,它的重要性也越发显露出来。特别是在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摧毁了中国独立发展的可能,在这种大背景下,现代中国人被迫“睁眼看世界”,把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情况与中国现实相联系看待,也在不断强化联想思维。“随感录”对联想思维的成功应用,远早于在小说创作上的应用,可算是比较成熟的文体样式。很多小说家也都进行过散文创作,比如鲁迅,他的小说自《狂人日记》始,就已经显示了联想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散文创作与小说创作相得益彰。
现代散文创作对小说创作思维模式转换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现代散文创作对小说创作思维模式转变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散文化”,也是对以往从审美特征角度定义小说“散文化”的一个补充。正是由于小说创作思维上的“散文化”现象,才使得后来的很多现代小说会呈现出某些散文的审美特征,对这一文学现象评论界已有诸多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梳理《新潮》小说和1921年《小说月报》小说,“问题小说”的面貌似乎变得清晰。或许这样的一个定义,会被认为太过狭隘,简单的时间分段并不完全是区别文体的可靠依据,但从思维特征入手,也许更能贴近文学创作意义的真谛。从明晰“问题小说”引出对小说的文体现代性是什么、它如何形成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才是本论文的终极指向。毕竟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因此,任何一种小说文本形式中必然蕴涵着一定的思维模式。从思维角度来区分小说的时代特征,不敢说颠覆以往的框架结构,或许也能为现代小说研究开辟出另一片空间。
标签:小说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联想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新青年论文; 每周评论论文; 新潮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