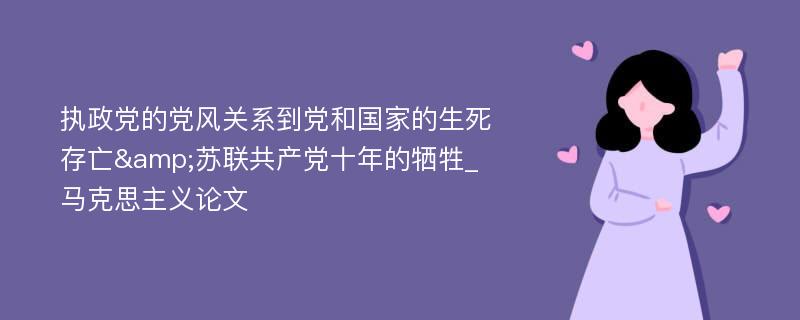
执政党的党风 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苏共亡党十年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死存亡论文,执政党论文,党风论文,党和国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世界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坚强战斗力的第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它同苏联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在艰难困苦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漫长的、曲折复杂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布尔什维克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模范行动建立起与苏联人民的血肉联系,并赢得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钦佩和尊敬。然而,经过七十多年的执政岁月,它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严重地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人们从失望到不满,最后,当它面临崩溃的时候,几乎是“不堪一击”,像颓危的大厦一样轰然而倒。这不能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然而,苏共党建传统模式中的一些问题和苏共在改革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苏共的前车之鉴,可以给我们党的建设事业提供诸多有益的教训和启发。
一、在党的建设中,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结合国情和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苏共以亡党的惨痛代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名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把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形式化;或是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基本内容,这两种错误在苏共党建的传统模式和苏共“革新”中都十分明显。
长期以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态度,使苏共的理论严重脱离国情和时代、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回答现实和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样,一方面使广大党员对理论学习变得淡漠、甚或厌倦,另一方面使党失去了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形成了守旧、保守的思维定势。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间,由于思想僵化,体制固化,而导致苏联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时期。
尽管在传统的党建模式下,“人们把自己的想法和感情都隐藏起来了”,但当改革大潮把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带来后,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那种党的统一就变得异常脆弱。党内信仰的分裂、思想的分化在公开性、多元性的旗帜下,开始了公开的论战。论战中,反对派咄咄逼人,苏共的理论则显得软弱无力。此时的苏共又靠牺牲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来维持党内各种势力的平衡,结果是徒劳无益。
二、在党的建设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建立起完善的民主集中机制。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党内民主问题上,苏共的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
首先,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应当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得以任何借口削弱和破坏这项原则,更不能随意取消它。改革时期,在苏共党内,一些人以种种借口,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存留提出异议,引起广泛争论。虽然在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中,仍可看到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它的一些重要原则却被削弱和取消了。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苏共开始不断吞食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破坏后的恶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破坏,致使党变成了争论不休的俱乐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被取消,使共产党按照民族门户各奔东西成为现实;党内允许派别存在,对苏共的分裂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其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正确贯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能把两者分裂开来,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结果形成个人专权、家长制、行政命令的体制,民主集中制被独裁者所利用,其本质被歪曲;而改革时期,又无限夸大民主,否定集中和纪律,导致混乱和分裂。这两种倾向都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应有的作用。
再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应建立起完善的民主集中机制,以确保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际运作中的有效性。在苏共党的建设中民主集中制作为指导党的活动的基本原则,其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是被公认和反复强调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模式,完备的集中机制一直在高效运转,而完善的民主机制则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以致改革伊始,要求民主的呼声成为苏共党内上下压倒一切的声音,并迅速遍及整个社会。苏共的民主措施原本是推动改革的手段,之后却成了葬送改革和苏共自身的利剑。这主要是因为高度集中的机制受到冲击,不能发挥作用,而完善的民主机制又不可能一蹴而就,结果导致整个党的机制的瘫痪。
三、在党的建设中,必须从严治党,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党的机体的健康。
苏共是一个一党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大党,随着执政时间的延伸和执政地位的“巩固”,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不是愈加紧密,而是不断疏远。从斯大林开始,长期以来,苏共对人民的思想、情绪和利益要求缺乏认真的考察和考虑,甚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扼制和压制。同时,党内的不良风气,诸如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理论脱离实际、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等等却日趋增长、泛滥。这样日积月累,人民对党的意见和积怨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以至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
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在苏共执政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取得巨大胜利以后,相当多的党员由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追求权力的升官发财者。二是权力特权化。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间,官员的特权有六种之多: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特供权(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特教权(高官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特卫权(为维护高级领导人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三是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四是权力商品化。即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很多官员通过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
在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还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权力的,接受人民的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苏共在整个执政时期,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权力的监督一直是单向的。任何时候党都是监督者,而不是被监督者。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把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改成人民监察机关,但又说明:“人民监察机关并不是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党的机关的工作由党内监察系统根据党章进行监督”。但是,党内监察系统在实际运作中,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却不可能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对由它选出的执行机关也没有监督;监督机制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更是无能为力。
苏共监督机制在某些重要环节上的低效或无效,使不受监督的权力日益膨胀,助长了党内的个人独裁和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使党的机体受到损害,最终使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在党的建设中,必须重视学风和理论建设,以保证党的思想和理论与时俱进。
苏共的瓦解,与理论研究的混乱、畴形、教条,与学风的败坏有很大关系。首先,苏共缺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去过基层考察。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赫鲁晓夫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勃烈日涅夫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其次,党的很多干部思想中明显有“守旧”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逐渐失去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当党面临改革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广大干部的思想就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倾向。在苏共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冀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再次,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性、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苏联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它既解释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世界。
五、在党的建设中,必须严格遵守任人唯贤,绝不能让旧的政治文化死灰复燃。
苏联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极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使机关官僚化和官僚特权化不断发展,而且给党的组织制度造成极大的危害。党内培植亲信、拉帮结伙、宗派倾乱、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权钱交易、卖官买官、瞒上欺下、弄虚作假、谎报政绩大肆涌现。这种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红色外衣包裹之下的旧时代的政治文化,是一个较之西方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更为腐朽僵化、更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勃烈日涅夫当政年代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勃氏的亲自带头下,权贵中授勋颁奖成风,各级官僚恬不知耻地为勋奖而钻营,求门拜户、自荐说项、勾结倾轧、讨价还价的现象层出不穷,随称号而来的奖金奖品格外丰厚。更为严重的是任人唯亲几乎成了那个时期遴选干部的通则。勃氏又起“表率作用”,儿子当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弟弟当上了中央的副部长,女婿官拜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氏还加恩于远房亲戚,以及亲戚的亲戚或亲戚的朋友,最后还忘不了自己的老伙伴、老朋友、老部下、老熟人。总书记如此,以下各级还能做到选贤与能吗?不仅如此,勃氏还无原则地维护亲属,对心腹、朋友、旧属的犯罪行为进行袒护包庇。另外,勃氏和他的亲属有送礼收礼的癖好。他出国访问或在国内巡视,总要带些礼品(当然是由专门机构筹办,从国库开支)赠送给主人,对方当然也礼尚往来。上行下效,用公款请客送礼之风,刮遍全苏每个角落,全社会弥漫污浊,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无所不有,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降。
苏联共产党倒下了,克里姆林宫易帜了,苏联没有了,其教训再一次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现在,我们的党风总的是好的,但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由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环境,物质诱惑的因素增多了;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许多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由于有的地方和部门治党不严、思想政治建设抓得不紧不力,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一些同志产生了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思想,一些同志的精神世界受到侵蚀,个别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现象: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这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和蔓延,严重侵蚀了党的健康肌体,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前事不亡,后事之师。全党上下务必朽索为御,精警惕励,认真端正党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