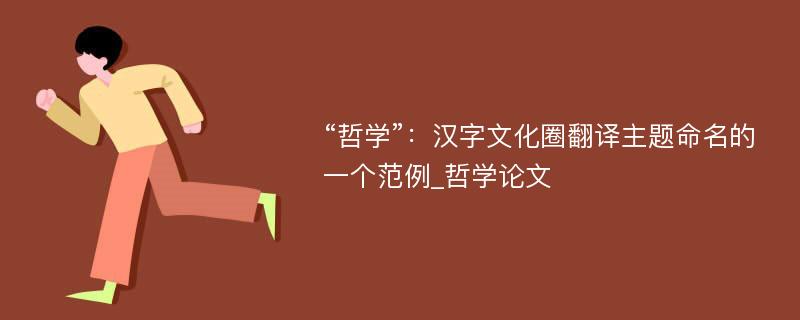
“哲学”: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目的论文,文化圈论文,范例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文化圈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西洋学科名目,较具范式意义和影响力的,是对译Philosophy的“哲学”一词。“哲学”的厘定,典型地展示了“中—西—日”三边文化互动过程中汉字新语的生成机制。
Philosophy的“爱智”义
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命题,诸如阴阳、道器、体用、心性等,直逼哲学堂奥。然而,汉字文化系统内,并无“哲学”一词,也无“哲学”学科的确立,较相接近的名称有“玄学”、“形上之道”、“理学”、“道学”等,但均不足以担当统括此一学科的总称。时至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学科意识渐趋明确,以研究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人生观、真理观为使命的学术突现出来,需要专门术语加以界定,于是,从西洋引入Philosophy一词便成为汉字文化圈诸国的共同诉求。
在西洋,Philosophy一词的形成过程,正是哲学学科的界定过程。英、德、法语的Philosophy皆源于希腊文Philosophia。Philo意为“爱”,Sophia意为“智”,合成义为“爱智”。在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之学,而智慧就是生活的艺术,它来源于神谕,人们热爱并追求它,这就是哲学。第一个使用“爱智之学”的,是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稍后,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宣称自己是“爱智者”,其弟子柏拉图(前427~前347)认为“哲学从惊奇开始”,并提出“哲学王”理念,展现“哲学”总领诸学的思想。概言之,自古希腊开始,欧洲即有“爱智”义的Philosophy一门学科的潜滋暗长,这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研讨百学之“理则”的学问,自古希腊到现代欧洲,有着一以贯之的学脉和范畴系统。
早期汉文西书中Philosophy的译名:音译“斐禄所费亚”,意译“学文”、“理学”、“性学”、“爱知学”
西语Philosophy传入汉字文化圈,是16世纪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欧洲耶稣会士进入德川时代的日本和明末清初的中国传教,随之带来西方学术文化,Philosophy为其中之一。自16、17世纪之交,日中两国开始对这一西洋术语作翻译尝试。日本文禄四年(1595)印行的天草版《拉葡日辞典》,将Philosophy译作“学文の好き”,意为“良好的学文之径”。“学文”采自《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文当为汉字文化圈最初对Philosophy的意译。
16、17世纪之交较高水平的Philosophy译名,出自中国的早期汉文西书。明天启三年(1623),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1582~1649)所著《西学凡》出版,介绍欧洲大学的学科设置,将其分为“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艾儒略对这六科都给定音译名称,其中理科为“斐禄所费亚”,并有“大斐禄之学”的名目。同书又将“斐禄所费亚之学”意译为“理学”。文称:
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藏于物中,如金在沙,如玉在璞,须陶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
艾儒略的另一著作——地理书《职方外纪》,其卷二《欧逻巴总说》介绍欧洲各国教育,谈到中学所设“理科”分为三家:“落日伽”(逻辑学)、“费西加”(物理学或自然哲学)、“默达费西加”(形而上学),三家“总名斐禄所费亚”。这就给Philosophia厘定了音译名“斐禄所费亚”和意译名“理学”、“理科”。
明天启四年(1624)出版的“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有“斐禄苏费亚(译言格物穷理之学)”的提法。次年,“高一志译校,毕拱辰删润”的《斐禄答汇》也将“斐禄”意译为“格物穷理”。
与艾儒略大体同期入华的耶稣会士傅泛际(1582~1653)与中国士人李之藻(1565~1630)1628年合译的《寰有诠》、1630年合译的《名理探》,将Philosophia音译为“斐禄琐费亚”,意译为“性学”和“爱知学”。“性学”一词出自《寰有诠》,该书称性学为“因性之学”,指根据自然探究天地万物之理、天地万物之源的学问,所谓“性学者,形性之学也”,这显然是从宋明理学的“心性”一词演化而来。
《名理探》创制的“爱知学”,更接近Philosophia本意。古汉语“知”“智”相通假,“爱知”即“爱智”。《名理探》称:
爱知学者,西云斐禄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
爱知学之本务,在通物物之性,性性之理……凡就所以然处,推寻确义,贯彻物理,皆为爱知学之属分。
《名理探》将Philosophia意译为“爱知学”,是贴切的,甚至比两百余年后日本思想家西周(1829~1897)的译词“哲学”更为完整地表达了Philosophia的意义。然而,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介的西洋哲学,在中国影响十分有限,《西学凡》、《寰有诠》、《名理探》等人文学著译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泥牛入海无消息”,其Philosophia的译语,如《西学凡》的“理学”、《灵言蠡勺》的“格物穷理之学”、《寰有诠》的“性学”、《名理探》的“爱知学”,鲜为人知,关于Philosophia的译名尝试并未在中国知识界留下多少印象。
直至19世纪中后叶,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译介西学时,哲学的译名与17世纪明清之际时译名大同小异。1877年出版的《格致汇编》载英国传教士慕维廉(1822~1900)撰《培根格致新法》,称哲学为“格学”或“学”。德国传教士花之安(1839~1899)撰《德国学校论略》,介绍德国大学学科,把哲学称之“智学”。至于清末的官私学校,尚未把哲学视为独立学科,哲学所涉及的论题混杂在“经学”的总名之下。
日本兰学书、洋学书的译名:究理、学文、物理学、性理论、理学、玄学
日本德川幕府中后期相继兴起的兰学和洋学,主要译介西洋自然科学,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宽政八年(1796)出版的稻村箭撰《波留麻和解》,将西洋的世界观学问译作“鸿儒”、“硕学的学修”、“究理”、“学文”。兰学家志筑忠雄(1760~1806)1801年译注《极西检夫尔著异人恐怖传》,创“穷理科”一词,以对译西洋哲学科。
天保十年(1839),洋学家渡边华山(1793~1841)的《外国事情》创“物理学”、“格智”二词,以译介西洋哲学。洋学家高野长英(1804~1850)在《闻见漫录》中,将Philosophy译作“学师”,取义“总体之学”、“至要之学”。安政二至五年(1855~1858),洋学家桂川甫周(1751~1809)编《和兰字汇》,用“理学”译西洋哲学。
类似的翻译还有:津田真道(1829~1903)文久元年(1861)的“性理论”;元治元年(1864)村上英俊(1811~1890)在《佛语明要》(此处“佛”为“佛兰西”省称,指法国)中的“天道之说”;庆应二年(1866)堀达之助等在《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的“理学”;明治元年(1868)《学舍制案》中的“玄学”;明治二年(1869)《舍密局开讲之说》中的“知识学”、“熟考知察学”、“考察学”;明治三年(1870)《大学规则二月》中的“性理学”等等。①
总之,在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关于Philosophia的译名,纷纭杂陈,莫衷一是。直至西周以“哲学”翻译,方获得规范、统一的译名。
西周、津田真道的厘定工作:从“性理论”、“希哲学”、“希贤”到“哲学”
日本学习西洋文化是从科技入手的,德川时代称之“艺术”(采自古汉语的“艺术”义,指技艺)。洋学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是典型表述。日本人对西洋“哲学”的发现,是幕末洋学机构“蕃书调所”(1856年创办)—“洋书调所”(1862年创办)—“开成所”(1863年创办)培育出的启蒙思想家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是西周与津田真道。西周等人对西学的认识,也是从科技层面入手的,庆应四年(1868)夏,西周在译作《万国公法》的卷头语中说:“方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国,火车俭地,汽船缩海,电机以通千里之信,新纸以广四海之闻”,对火车、汽船(轮船)、电机(电话)、新纸(报纸)等西洋物质文明成就发出由衷赞叹。西周等人的可贵处在于,对西学的关注并未停留在技艺领域,而是由西洋物质文明推究其精神文明,将研习的目标直指哲理层面。
津田真道于文久元年(1861)撰《性理论》一文,探讨哲学问题,“性理论”一词,相当于Philosophy。“性理”指心性与天理,借自宋明理学。西周还于1870年以“理性”译Reason。西周在《尚白札记》(1870)、《生性发蕴》(1873)等文中论及:“哲学家”探讨“百科学术”的“统一观念”。“哲学”是成体系的学问,追求“究极的原理”。哲学所论之“理”,包括生理与性理,心理与物理,为此征引《易》的易象、易数之理,《中庸》的中和之理,《说文》的治玉之义,包括脉理、条理、文理,进而与西洋哲学涉及的理性、原理相比拟。西周论哲学之理,有一种打通中西的气势,从而为“哲学”术语的译制奠定基础。关于Philosophy的译名,西周启用“希哲学”,是打通中西哲思的产物。西周在为津田《性理论》一文作跋时,使用“希哲学”一词:
西土之学,传之既百年余,至格物舍密,地理器械等诸学科,间有窥其室者,独至吾希哲学一科,则未见其人矣。遂使世人谓西人论气则备,论理未矣。独自我友天外如来始。今此论颇著其机轴,既有压夫西哲而轶之者,不知异日西游之后,将有何等大见识以发其蕴奥也。西鱼人妄评。
津田真道的论文和西周的跋语写于二人1862年赴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的前一年。西周跋语中的“希哲学”为“希求哲智之学”的简称,是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太极图说》中“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语中套用过来的。以“希哲学”或“希贤”对译Philosophy,颇有沟通东西方哲理的意蕴,也生动地显示出:近代日本思想家接受西洋哲理,以中国传统学术作依凭,用汉文古典词充作“格义”西学的工具,汉字固有语汇是译介西洋概念的得力中介。
作为通晓东西哲理的思想家,西周并未在西方哲学与东方学术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在《开题门》一文中指出:
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②
他既看到东西哲理“明天道”、“立人极”的一致性,也不把东洋的儒学与西洋的斐卤苏比(即哲学)混为一谈。他的学术工作的重心,是向东洋介绍西洋的斐卤苏比(哲学),从而成为一系列哲学术语的厘定者。西周充分利用自己对汉字文化和西语文化的通识,在“中—日—西”三方语文世界间游徙,完成了富于创意的沟通工作,而“哲学”一词的创制,便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
西周与津田真道留学荷兰莱顿大学,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更加深一层。返回日本后,西周在明治三年(1870)的东京讲学中开始使用“哲学”一词,该讲义的笔记多年以后,方由西周的学生永见裕整理出版,此即《百学连环》。《百学连环》称,Philosophy有“爱贤、希贤”之义,“亦可直译为希贤学”,又说:
凡事物皆有其统辖之理,万事必受其统辖。所以哲学是诸学的统辖,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正如国民之受辖于国王。③
古汉语没有“哲学”一词,“睿智”、“聪明”义的“哲”字却多次出现,《尚书》有“哲”字十八例(如《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等),《左传》有“哲”字五例(如《左传·文公五年》“并建圣哲”等),《诗经》中“哲”字十二例(如《诗经·小雅·鸿雁》“或哲或谋”等),《礼记》中“哲”字三例。中国古来常将有大智慧的人称“哲人”、“圣哲”,如《礼记·檀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左传·文公六年》:“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西周深悟此意,所创“哲学”一词是“睿智之学”的意思,虽然未能将Philosophy(爱智)的“爱”义突现出来,而“智慧之学”的意思则是一目了然的。1870年西周在书简《复某氏书》中出现“哲学的巨臂”④ 等语。而在公开书籍中首见“哲学”一词,是西周于明治七年(1874)出版的《百一新论》。该书“卷之下”论及学科分类,明确地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他在该书中说:
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⑤
并说哲学体现了“百教一致”的精神,物理、心理皆遵奉哲学的法则。⑥
山本觉马明治七年(1874)二月一日为《百一新论》作序,也多次出现“哲学”字样。其序文曰:
教之与政其理混淆,学者之惑数千年,于兹心理之与物理其学交错,世人之疑亦数千年。于兹我友西氏忧之,由哲学明政教所别,又晰道理之所歧,将辨世人之惑,著斯书名曰《百一新论》,取于百教一致之义也。……西氏于和汉西洋之书莫不讲究,……且能明哲学者,我邦未尝闻有其人也,故余请而刻之以公于世,识数言于卷首云。⑦
这里的“哲学”,取“百教一致之义”,也即“万事统辖之理”。
明治七年(1874)日本建立“东京开成学校”,明治十年(1877)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包括法、理、文、医四个学部,文学部内设“哲学科”。这是“哲学”一词在日本获得正式地位的开端。但“哲学”与相关词纷然并用,在日本延续了十余年。
西周于19世纪70年代使“哲学”一词面世,但并未立即受到社会及学者的认同。关于西洋世界观之学,另有种种译名,与“哲学”并用,如中村正直(1832~1891)明治四年(1871)译《自由之理》,使用“理学”;明治五年(1872)出版的《和英语林集成》,使用“学术”、“理”、“道理”、“道”;西周本人明治六年(1873)著《生性发蕴》,并用“哲学”、“理学”、“理论”;同年柴田昌吉等编《英和字汇》使用“物理”、“理论”、“理科”;福地源一郎(1841~1906)明治七年(1874)为《东京日日新闻》撰《社说》,使用“性理学”;儿岛彰二明治十年(1877)撰《民权问答》,使用“理学”;尺振八明治十三年(1880)译《斯氏教育论》,使用“理学”。
明治十四年(1881)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等据英国人Wiliam Fleming 1856年编的《哲学词典》,参考《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和佛学典籍,编译《哲学字汇》,界定“哲学”一词,并以“哲学”作书名,又收录西周创译的一系列哲学术语,如“演绎”、“归纳”等,“哲学”一词的影响力大增。但此后一段时间,仍然有西村茂树(1828~1902)的《日本道德学的种类》(1882)、中江笃介(即中江兆民,1847~1901)的《政理丛谈》第三号(1882)等书以“理学”译Philosophy。中江笃介明治十九年(1886)翻译《理学沿革史》、编著《理学勾玄》两部名著,仍赫然使用“理学”一词。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明治二十年(1887)发表《伦理教科书凡例案》,使用“哲学”一词,日本大学课程也用“哲学”名目。此后,“哲学”一词才在日本通行,成为规范术语。
黄遵宪、蔡元培、王国维等输入“哲学”名目
19世纪末叶,中国学界开始介绍西洋哲学,但当时尚未使用“哲学”一词,书刊上出现的是“理学”、“心智之学”、“思维之术”、“心理学”等驳杂的名词。严复(1854~1921)译著《天演论》,将Philosophy译为“天人会通论”,译著《穆勒名学》将Philosophers译为“智学家”。
“哲学”一词传入中国,大约开端于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年撰毕,1895年初刻)。该书的《学术志一·西学》,列举“东京大学校”的学科,“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其中“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⑧。黄氏撰定《日本国志》的1887年,正是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使用“哲学”一词的同一年,也是东京大学设“哲学科”后的第10年。但黄氏的《日本国志》延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方获刊印,故“哲学”一词在中国得以流传,已到19世纪末叶。
在《日本国志》刊印前的光绪十九年(1893),曾游历日本的黄庆澄(1863~1904)在《东游日记》中论及日本广设学会,其中提及“哲学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1873~1929)据日文资料,撰《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文中多次出现“哲学”一名。同年印行的《浙江潮》第4期,刊登署名公猛的《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一文,是中文报刊较早介绍“哲学”这一新概念的论文。该文对哲学下定义:
哲学二字,译西语之Philosophy而成,自语学上言之,则爱贤智之义也。毕达哥拉士所下之定义,以为哲学者,因爱智识而求智识之学也;亚里士多德亦以为求智识之学;而斯多噶学派以为穷道德之学;伊壁鸠鲁学派以为求幸福之学。
哲学之定义如此纷纷不一,虽然,希腊人哲学之定义,则以相当之法研究包举宇宙与根本智识之原理之学也,约言之,则哲学者,可称原理之学。
“原理之学”,即探求事物一般规律之学。此说颇能切中“哲学”的本质。
至20世纪初,以“哲学”命名的日文书籍大量译为中文出版,如井上圆了(1858~1919)著、罗伯雅翻译的《哲学要领》1902年印行;井上圆了著、王学来翻译的《哲学原理》1903年印行;藤井健次郎著、范迪吉翻译的《哲学泛论》1903年印行;井上圆了著、游学社翻译的《哲学微言》1903年印行。
清末影响较大的哲学译著是,德国科培尔在日本的讲演集、下田次郎记录并日译、蔡元培(1868~1940)中译的《哲学要领》(1903年印行),文曰:
哲学者,本于希腊语之费罗索费。费罗者,爱也,索费者,智也,合而言之,则爱智之义也。
认为“哲学”是“求知此原理及一切运动发现之公例”的“原理之科学”。
中国人自著的以“哲学”名书的著作,较早的是侯生编撰的《哲学概论》。1906年,上海广学会刊印冯葆瑛《哲学源流考识》,以“哲学”为全书关键词,并指出:“哲学一家遂为过渡时代转移之目的矣”,具有“唤醒国民之灵魂,持示教科之正轨”的作用。
总之,清民之际,日源词“哲学”逐渐取代中国原用的同类词“理学”、“玄学”、“性理学”、“形上学”,正式以学科名目被国人认可。其间王国维劳绩卓著。
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学涉文、史、哲,早年译介西洋哲学论著十余种,署名译著便有7种,其中日本桑木严翼(1874~1946)的《哲学概论》(海宁王国维译本,1902年刊于上海教育世界社出版的《哲学丛书初集》),直接涉及Philosophy译名“哲学”。《哲学概论》的“第二章哲学的定义”,王氏的译文为:
“哲学”之语,本译字而非本来之成语,人人知之。其原语谓之“斐洛苏非”或“斐洛苏非亚”……斐利亚译言“爱”,而苏非亚者,“智”之义也。故“斐洛苏非”,若以其语源译之,则可称为“爱智”。然其真义必非但爱智之义,而有究理探真之义者也。然而考其译语“哲学”之“哲”字,《尔雅·释言》曰:“哲,智也。”扬子《方言》亦曰:“哲,智也。”又如《书·舜典》所谓“哲,文明”,睿《说命》所谓“知之曰明哲”,皆与原语之“苏非亚”有所似者。……求之古来我国(按,日本)及支那所用之文字,如宋儒所谓“理学”,与其真义相近。然理学之语,今日用为自然科学之总纲,即总称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博物学等。故不关其意义之远,而袭用哲学之名称,或反有避误解之益欤?况哲学之语义反近于斐洛苏非之原义欤?⑨
王国维的这一译文,相当周全地论述了以哲学翻译斐洛苏非的过程及理由。
清末中国朝野尚不接受“哲学”一词,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上奏称:“盖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鹜广志荒之弊”,认为哲学使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故朝廷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从大学科目中取消哲学一门。有鉴于此,王国维1903年撰《哲学辨惑》一文,申述译名“哲学”与中国固有名词“理学”相通,委婉地规劝国人不必惊骇,诟病外来的“哲学”一名:
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观去岁南皮尚书(按,张之洞)之陈学务折,及管学大臣张尚书(按,张百熙)之复奏折:一虞哲学之有流弊,一以“名学”易“哲学”。于是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艾儒略《西学凡》有“斐洛苏非亚”之语,而未译其义。“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斐洛苏非亚”曰理学,而译曰“哲学”。我国人士骇于其名,遂以哲学为诟病,则名之不正之过也。⑩
王氏此议的主旨中肯,然关于日本译名的“理学”、“哲学”之辨有偏误:日本早在幕末即以“理学”意译Philosophy,至明治初,西周等以“哲学”意译Philosophy,方把“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总名。王氏认为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在先,这是千虑一失。
时过两年,王国维撰《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一文,更明确地强调新语输入的重要性: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11)
王氏同文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引进科技类术语,包括“哲学”在内的“形而上”新语的引入,对“文学”(指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至关紧要。当时朝廷讨厌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专列“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条,对“袭用外国名词谚语”的行为大张挞伐,声明“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针对此种保守之风,王氏充分肯定输入新名词的必要性,认为日本人创制的汉字译词,理当为中国人借用:
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12)
王国维不仅是译语“哲学”较早的推介者,而且也是理性地对待外来术语的倡导者。其哲人风范殊堪效法。
注释:
① 参见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日本讲谈社昭和五十二年版,第327~329页。
② 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1卷,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出版,第19页。
③ 《百学连环》,《西周全集》第4卷,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出版,第145~146页。
④ 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出版,第30页。
⑤ 《百一新论》,《西周全集》第1卷,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出版,第289页。
⑥⑦ 参见《明治启蒙思想集》,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出版,第23~24、3页。
⑧ 参见《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
⑨⑩ 转引自佛雏《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9、10页。
(11)(12)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期(1905年)。
标签:哲学论文; 汉字文化圈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明治时代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理学论文; 读书论文; 王国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