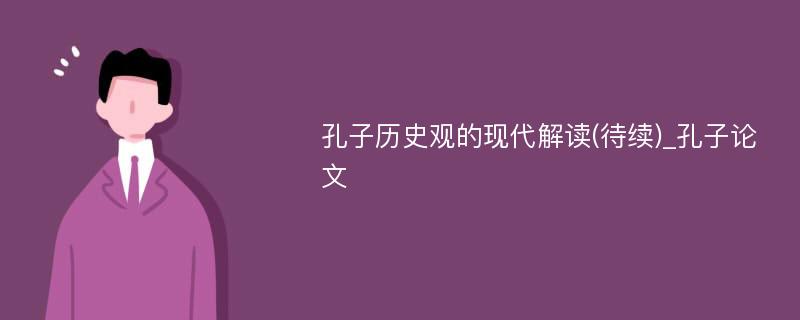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待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史学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是中国史学之父,正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85-425年)是希腊史学(从而也是近代西方史学)之父一样。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孔子不仅比希罗多德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学术思想上有更大的成就。希罗多德只是一个历史编纂学家,孔子并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所以孔子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史学理论,它在古代世界史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本文将在适当的场合,把孔子的史学理论和西方的史学理论作出比较观。
我们所说的史学理论,按照今天一般用法,指如下两个方面:一为历史编纂学理论(theory of historiogrpy);一为历史元理论(metatheory of history),即一般所说的历史哲学。意大利著名历史理论家克罗齐指出:“历史编纂学的理论……是历史编纂学所得到的关于它自己的意识”。①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主要见之于关于《春秋》的编撰学方面。孔子的历史哲学主要见之于他所编著的《易传》中。本文拟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以《春秋》为主专门论述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一部分以《易传》为主专门论述孔子的历史元理论。这里仅发表第一部分,下一部分另文发表。
在孔子死后差不多五个世纪,司马迁才第一次对孔子的史学理论作出全面的理解。在这五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的历史编纂学缓慢地发展着。司马迁以孔子的史学理论作为历史方法论,结合自黄帝以来的历史实际,写成《史记》一书,奠定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模式”(disciplinary paradigm)。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史”(normal history)二千年来都是在这个模式的指引下发展的。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时,这种模式才被打破。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历史编纂学家,所以只有他才能第一次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和解释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这是不足为奇的。令人奇怪的事是自司马迁以后直到今天,却不再有人全面而系统地阐明孔子的史学观念。本文的旨趣就在于:主要以司马迁的论述为参照,对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作出现代的再理解与系统的再解释;并且粗略地涉及一下,在司马迁以后,我国传统史学家和经学家只重视孔子的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全面的原因。他们所重视的就是孔子的史学观念中关于历史学的“训诲职能”(didactic function)这一个方面。
第一节 司马迁的“六经皆史说”—一“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历史方法论
汉初,司马氏世为史官,这个史学家族把儒家的经典《六经》(汉人习惯地称为《六艺》)作为孔子的历史方法论,并且作为他们司马氏治史的家法来传授。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世〔者〕: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并参照《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并表示他自己的学术意图就在这里。
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六经》,从而把《易传》与《春秋》和其余四经分开,并且郑重地作为“正”和“继”的对象,而对《诗》《书》《礼》《乐》四经则泛泛地称作“本……之际”。这是明显的区别对待。只要细读《史记》中的有关言论,我们就可看出司马迁把前二经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纲领或“预先假说”(pre-supposition);而把后四经作为历史资料的根据。分别引证和论述如下。我们先看司马迁就正于《易传》的是什么。他写道:“《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太史公自序》)。就《易》本身说,如汉代学者所指出,“易”有三种含义:“易简”、“变易”、“不易”。第一义所指的是方法论,第二和第三是有关本体论问题。而司马迁于本体论中仅取“变易”世界观(即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不断运动和生灭的体系),这正好作为历史研究的前提假说。因为摆在任何一个历史家面前的是人类社会已发生过的事,是前言往行,而它们只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们不断发生和消失。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看作在本质上是“不易”的,那就没有历史了。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的时代,当时的史官就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如公元前510年,晋国的史墨(史官名“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三代的后裔——引者注),于今为庶”(《左传·昭公32年》)。这位史官把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统一在他的历史意识中。孔子在《易传》中系统地叙述了变易的世界观,我们将专文讨论。司马迁继承《春秋》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可用他的如下说法来回答。他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可见,司马迁把《春秋》看作是一部历史编纂学的著作,其中包含了孔子的“史学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本文即将全面论述孔子的史学观念(史学观)。汉代学者常把《易》与《春秋》对举,认为前者谈“天道”(世界观),后者讲“人道”(历史观)。如班固所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律历志上》)。总之,司马迁所说的“正《易传》”和“继《春秋》”意味着以前者的“天道”(世界观)和后者的“人道”(历史观)作为他自己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基础,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出他自己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论纲领。
至于“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提法,不仅意味着司马迁把这四经看作历史资料,而且他认为孔子也是这样的。先就《书》(或称《书传》、《尚书》)言,它本身就是国家的档案,是历史资料,孔子可能是最早作这样看待的人。司马迁写道:“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引者注:“序”即编次整理,而不是作序文之“序”);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世家》)。在司马迁看来,孔子编次《书传》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自唐虞至秦缪的历史事件的年代学顺序去追迹三代之礼。再就《诗》言,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者〕,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同上书)。这就是说,孔子删《诗》的目的在于选存反映整个殷周的历史进程中的“礼义”(在先秦文献中“礼义”与“礼”这两个词在意义上没有区别,可以互用,如荀子在其《礼论》篇的第一段中就这样使用着)的诗篇。再就《礼》言,“礼”本来是三代的政治和教化的“典章”,其文献应当是很丰富的。然而,孔子之世,周室已衰微,“诸侯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已,去其篇籍”(班固语),故司马迁说:“《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儒林列传》)。但是〔我们在本文第二节第三段中将要说明〕三代之礼就是三代之史,所以司马迁特别重视孔子在三代之礼方面的研究:当《礼》作为史料“而其经不具”时,孔子则在《书》中“追迹三代之礼”,在《诗》中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以补充《礼》本身之不足征。最后,就《乐》看,它在史料学上是不重要的;“乐”是否有“经”都成问题。汉代的古文经学家认为《乐》本来有经,因秦火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乐”本来就无经,而附见于《诗》中。司马迁在儒学上是倾向今文经学的,所以他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四种庙堂音乐——引者)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世家》)。总之,司马迁的“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提法,显然是说,孔子本人就以这四经作为史料根据。
这样看来,司马迁所继承的孔子的历史方法论,其基本原则是把历史理论(正《易传》和继《春秋》,和历史资料(本《诗》《书》《礼》《乐》之际)统一起来,这一原则与当代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趋向相符合。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口号是“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而“年鉴派”史学则声称:“没有理论,就没有史学”。但从两派的历史编纂学的实践看,前一派的著作中隐含着宗教信念和政治偏见(如欧洲中心论)之类的理论。后一派不过要求在史料根据之上作出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态的各种理论解释。可见史料与理论的结合正是历史科学的常规。
我们顺便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司马迁把“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作为历史方法论来把握时,应当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六经皆史说”,虽然他没有提出这个命题。但是我国当代学者(包括台湾学者)一致认为六经皆史说起源于隋代王通的《文中子》一书,而无一人上溯到司马迁。②事实上司马迁不仅是六经皆史说的先驱者,而且对六经的历史学的意义的理解,远远超过了从王通到章学诚的理解。我国当代学者所以忽视了司马迁,显然由于没有把六经作为孔子的历史方法论来认识。至于王通以来的儒家学者的六经皆史说都是一隅之见,而没有掌握孔子的全面的史学观。例如,王通只把《书》、《诗》和《春秋》三经看成是“圣人述史”。王阳明认为“《春秋》为史……五经亦史”时,仅从表面看到每一种经涉及到一代的史实,如云:“《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等等(《传习录》第一卷“答徐爱问”)。李贽也是这样认为“六经皆史可也”,不过他能见到《易》“示人以史〔观〕之由来”(参看李贽:《焚书》第五卷”经史相为表里”)。章学诚所以被视为六经皆史说的权舆,因为他第一次给“六经皆史”以系统的理论陈述。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详论章氏的六经皆史说。仅就其大略而言,他提出了新的史学观念,即“史学所以经世”(其实是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派”最初提到的),从而把经学和史学统一起来。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又说:“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内篇一《经解上》)。可见,他所谓“经世”即“纲维天下”和“切合人事”,用我们的话说,即为现实政治服务。他既然认为史学所以经世,而六经都是经世的,所以六经皆史。于是,他进一步断定:“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浙东学术》)。显然,章氏的六经皆史说的理论根据仍然是自孟子以后的封建史学的一个传统观点:即“孔子成《春秋》”,以褒善贬恶为主旨“而乱臣贼子惧”。例如,王阳明在谈到六经皆史时就标出:“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这个传统所重视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史学的“训诲职能”,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最后归结为“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这个传统之形成,乃由于在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要求是:不论经学或史学都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经世”理论根据的要义就在于此。所以他认为三代以后的史学家“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史释》篇)。
司马迁是从历史方法论理解六经皆史的。所以他对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际的认识是全面的和客观的,从而是正确的。以下,我们以司马迁评价孔子《春秋》的言论作为线索,来理解和解释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
第二节 “《春秋》之义”——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系列
孟子第一次把孔子的《春秋》作为历史著作而揭示出史学的三个要素:“事”、“文”和“义”。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孔子的《春秋》与孔子以前的各国史籍,如晋之《乘》、鲁之《春秋》以及其他,是有所不同的;而这个不同就在于孔子赋予他的《春秋》以“义”。在孔子以前,各国的历史档案虽然各有专名,而一般称之为《春秋》,所以墨子除了泛称《百国春秋》外,还列举过《周春秋》、《齐春秋》、《燕春秋》,等等。它们所以被称为“春秋”者,顾名思义,它们都是年代记(chronicle)性质,如杜预所指出,“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孔子修《春秋》也采用了年代记的体例,但是它与“前孔子的“《春秋》已有所不同了。孟子认为这个不同之处就是孔子还给予了传统的编年记以“义”。什么是“义”?孟子没有解说,因此,孟子以后两千年来对孔子的”《春秋》之义”有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晋代《春秋》专家杜预所说的:“据归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春秋左传序》)或者如我国古代最大的史学理论家唐代刘知几所说:“《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通·忤时》)。我们认为褒贬惩劝只是孔子的“《春秋》之义”的一个方面,而不足以表明孔子的《春秋》与前孔子的《春秋》的根本差异。例如,楚庄王(公元前613-591年)请人教育太子时,申叔时建议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其心”(《国语·楚语上》)。由此可见,“明善恶,示训戒”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孔子继承了它。这个传统一直被中国正统史学所强调,但是,如我们所理解,它不足以尽孔子的“《春秋》之义”。那么,究竟什么是《春秋》之义?我们认为它就是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体系。章学诚是有见于此的。他说:“史之大源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从章氏所用的词汇看,他显然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不过,章学诚的提法是抽象的,司马迁则从孔子所涉及的夏、商和西周这三个朝代的史迹,具体地把《春秋》之义理解为孔子的历史编纂的“理论系列”或“研究纲领”(借用自当代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术语)。以下,我们把《史记》中有关论《春秋》之义的言论,归纳为三个层次;并且取材其他权威性的资料—一如孔子的《论语》、《礼记》中有关孔子的思想和言论的记载——作出我们的信而有征的诠释。
(一)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司马迁对《春秋》之“义”所作的最基本层次的理解,是把它理解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就孔子史学的对象而言,司马迁写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太史公自序》),又说:“《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土道备,人事洽”(《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三王之道”(简称“王道”),乃指夏、商、周三代盛世所实行的政治统治,就统治者而言为“王道”或“王事”,就被统治的人民大众言,为“人事之纪”或“人事”或“人纪”(如《书·伊训》中提到商汤上“肇修人纪”),王道与人事是一回事,都是指人类的“行事”是人的所作所为。这意味着孔子第一次把人的行事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孔子在《春秋》中虽然还记载了一些自然事件,如日月蚀、地震、下冰雹、长期不雨,等等,不过,它们是被认为与人的行事有感应关系而记载下来的。在西方史学史上,第一次把“人的事”(ta anthropma)而不是“神的事”(ta theia)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的人是希罗多德,而他比孔子迟生半个世纪。在近代西方,不管什么流派的史学都得承认,人类行事和经验是历史研究的起码对象。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谈到什么是史学对象时说“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虽然这个答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进一步问题,其中许多会引起争论,但不管对它们可能做出怎样的答案,这些答案都不会推翻如下命题:历史学是关于res gestae的科学”③如所周知,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一词都来源一个拉丁化的希腊词“historia”这个词在近代西方的使用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指“过去的事”(res gestae),一指“关于过去事件的叙述”(historia rerum gestarum,在古汉语中“史”这个词(除最早指“史官”外)一般仅指过去事件的陈述,如孟子所说的“其文则史”,或如汉代标准词典《说文》的解释,“史,记事者也”,至于过去事件本身,从来不称为“史”,而直接称为“事”“故事”“往事”或“前言往行”等等,这不仅是用语的习惯,而且反映了历史思维的倾向性,中国正统史学家几乎没有人把历史作为一个客观过程而作出总体的或宏观的研究,他们仅重视“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的史学训诲作用。所以叙事史成为中国正统史学的学科模式,并取得光辉的成就,如刘知几所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上”(《史通·叙事》)。但是,如我们在下下节将要说明的,孔子本人不仅认为史是记事的,并且把“一代之礼”作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研究。可惜后来的正统历史家没有沿着孔子所开拓出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至于现代汉语的“历史”一词也具有双重含义,显然是受翻译或介绍西方学术著作的影响。)
我们再看看司马迁所揭示出的孔子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认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方法仅指历史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而言。西方近代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史学是诉之于证据的科学,而不能掺入历史家的虚构或想象。所谓证据就是可靠的史料,它主要是历史文献,还有非文字的文物或遗址。孔子治史的名言是“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所说的“文献”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献”在意义上稍有不同。朱熹注《论语》:“文,典籍也;献,贤也”。这就是说,除了典籍外,还有正直的人(贤者),关于他们所见或所闻的报导。近代德国历史学大师兰克认为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原始档案和目击者的报导,这正与孔子所说的“文献”相同。司马迁非常重视孔子修《春秋》时对史料的搜集,他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归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这几句话如班固所理解就是:“〔孔子〕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汉书·艺文志》)。所谓“史记”(即史官所记载者)或“史记旧闻”指各诸候国的史官用编年形式记录下的国家大事,如《鲁春秋》、《楚春秋》等。西周是礼文最丰富的时代,如班固所说:“周监于一代,礼文尤具……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汉书·礼乐志》)。但是,周代自幽厉以来,周室衰微,史官失守,唯有鲁国因为是“周公之国”,所以“礼文备物,史官有法”,忠于史料根据的孔子,只有“兴于鲁”而编次《春秋》,即以鲁国所藏的史记归闻(《鲁春秋》)和史法(编年体)而编撰成《春秋》。东周学者要研究西周的政治史(“王道”)只能利用鲁国的档案资料。在孔子前不久,鲁昭公2年(前540年),晋派韩宣子使鲁,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2年》)。孔子自己也说:“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记·礼运》)。
后代学者甚至认为孔子已经有了“史料批判”的初步意识,晋代的《春秋》专家杜预指出,鲁国的“策书”(策”是竹简,策书即写在竹简上的史记旧闻)上的一些“记注多违旧章”所以“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春秋左氏传集解》序)。这就是说,孔子对鲁国史官在策书上所作的“记注”进行过考证。不过他不是考其是否合于事实,而是考其是否合于周公所制定的典礼,凡违背名教者则刊而正之。可见,杜预对孔子在史料考证方面的这种理解,仍然是从史学的褒贬劝惩作用出发的。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对孔子的史料批判方面的理解则比较客观些,也许正确些。就孔子修《春秋》的记事三原则,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来看,他说:“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乎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缺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日知录》卷四“所见异辞”条)。
(二)历史学的训诲职能
据司马迁的理解,“《春秋》之义”的第二层含义是史学的训诲职能。
有人问司马迁:“昔孔子为何而作《春秋》哉?”司马迁爰引孔子自己的如下两句话作回答:“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还引了董仲舒的如下说法:“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司马迁并用自己的话说:“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上均见《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把《春秋》看成一部历史著作,它以春秋时代的242年(从鲁隐公元年到哀公14年,即公元前722-481年)的行事为对象。司马迁是把《春秋》的“经”和《左传》看成一体的,他说:“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左丘明惧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刘知几明确指出,《春秋》的“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申左》),所以他所说的《春秋》,和司马迁一样,兼指经传而言。如云:“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莫不备载其事”(《二体》)。这样看来,司马迁把《春秋》(《左氏春秋》)看成是对242年的历史大事所作的叙述性的陈述(descriptive statement),但是孔子的史学的特征表现为:同时对事件作出评价性的陈述(evaluating statement),这就是杜预所说的“指行事以正褒贬”。这种价值判断甚至表现在造句和用词中,因而被称为“以一字为褒贬”,如司马迁所指出:“践土之会实〔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孔子世家》)。
班固说:“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这也就是说,孔子不用纯粹的理论陈述(或者说坏一点,不用教条形式)去表达他的政治和道德理想,而是用242年中的历史大事作为实例,进行褒贬劝戒的直观教学(object teaching)。但是,孔子认为事情真正是怎样,就如实地加以评价,绝不“强史以就我”,所以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宣二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孔子史学的训诲职能。司马迁非常严谨地用了“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提法来表达孔子史学的价值判断的客观性。所谓“善善”就是说,某某行事本来是善的,就恰如其本来地评价为善。如果某某行事本质上是恶的,就恰如其本来地“恶恶”。“贤贤贱不肖”也是这样。司马迁的这个提法比“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史通·曲笔》)的提法好得多,因为一掩一扬之际,就缩小或夸大了事件的真实性。所以班固称赞司马迁为“良史之才”时,也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传》)。司马迁把善善恶恶看成是《春秋》之义的一个方面,而司马迁以后的传统史学则认为《春秋》之义就是褒贬劝戒,这是本文试图辩明的一点。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从世界史学史的角度怎样评价孔子的“训诲史学”(didactic history)?
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揭孔教之缺点”的口号对孔子的训诲史学作出激烈批判的是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当梁启超发动以“新史学”代替“旧史学”的“史学革命”时,他所谓的“新史学”,就其方法论而言,主要是借鉴于西方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兰克式的史学——当时称之为“科学的史学”或“实证主义的史学”或“客观的史学”;他所谓的“旧史学”指以“经世”和垂训”为宗旨的中国的传统史学,他把这种史学的起源上溯到孔子。
19世纪西方的“科学史学”的大师兰克在他的处女作《拉丁日耳曼各民族史》(1924年)的序言中高举客观的、如实叙事的史学的旗帜来对抗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史学。他写道:“人们分派给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教导现在以有利于未来。本书不敢期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要求表明确实所发生过的事情(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已”。最后那半句德语(梁启超既雅且达地译为“使恰如其本来”)成为“科学史学”的座右铭,并且一直为西方史学界家喻户晓。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论述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史学革命”的意义,我们仅仅谈谈梁氏在批判旧史学时在方法论上的依据。他说:“夫史学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历史,是否事实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以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之,使恰如其本来。……故吾侪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些话完全是兰克所标榜的客观史学的旨趣。梁启超所说的“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或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正是兰克所要求的历史家在价值观念上要严守中立,不“判断过去和教导现在”,仅仅“恰如其本来”地据事直书。梁启超以兰克史学的模式为标准,批评我国旧史学“从不肯为历史而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的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同上引书)。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批判矛头是指向孔子史学的训诲职能,他把孔子视为中国旧史学的这种“恶习”的始作俑者。今天,我们检视梁氏的这种批评时,有理由断定它是片面之见和过激之言,因为第一,梁氏对他所持的批判武器(即兰克所标榜的为历史而历史的客观主义史学)作了片面的理解而不是全面地从西方史学史去理解;其次,梁氏对他的批判对象(孔子的史学观),也没有像司马迁那样作出全面的理解。以下,我们分别说明这两个方面。
第一,梁启超把兰克式的史学奉为客观的、科学的史学模式时,没有认识到兰克史学只是西方近代史坛上的一家之言。梁启超也没有认识到兰克所标榜的“纯客观的历史”即使兰克本人“事实上”(即在兰克的历史著作中)也并没有做到。20世经前期,西方不少历史家(如美国的“现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查理·比尔德以及其他史学家)从兰克著作中揭示出一条一条的宗教的、政治的、历史的偏见;他们并且论证了纯客观史学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些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多发表在梁启超去世以后。但是,仅就上述兰克的1824年的那本名著而言,如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史学史专家古奇所指出:“由于兰克把历史看作在伦和宗教方面给人以教训的实例,所以在他的笔下,意大利的可耻的道德败坏就是它遭遇厄运的原因”。④可见,兰克本人在其“使恰如其本来”的据事直书的前提要求下,也用历史行事的实例给人以教诲。这和孔子的史学观念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孔子也是在据事直书或“书法不隐”的前提下,才对历史行事作出道德判断的,我们在前面已论证过了。再者,如果梁氏所说的“强史以就我”的“恶习”乃指孔子在历史编纂学中只选择有利于他的道德判断的历史事实,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是恶习,而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的通例。因为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在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时,都必须以其“预先假说”为根据,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作出“历史的选择”。就西方史学史而言,自古迄今表现出历史选择的两大取向:一为因果关系的取向;另一个为价值判断的取向。如就古罗马的历史学家言,波里比乌(polybius)是取向于因果关系的,他探求某些史实的原因,以便应用于类似情况;他把不可预料的事件看作是次要的,或者以其不规律性(irregularity)而置之规律(rules)之外。在另一方面,如塔西陀(Tacitus)则是一位道德主义的(moralistic)史学家,他声称他的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搜集那些善恶昭彰的历史事实,为了“不使美德湮没无闻,而使后人对秽迹恶名有所畏惧(ne virtutes sileantur utque pravis dictis factisque ex posteritate et infamia metus sit)”⑤再就西方近代史学家的选择取向而言,一种倾向以受自然科学方法论影响的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家为代表,他们为了对历史作出因果关系或普遍规律性的解释而对历史事实作出选择,至于不利于这种解释的则视为偶然事件或不予重视。另一种倾向以19世纪末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学派为代表,该派从对象和方法上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是探索普遍规律的科学;后者,用李凯尔德的话说,是描述个别事件的、与价值相联系的科学。李凯尔德认为要把握“历史个性”就要“参照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个人的价值观念,而且是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本世纪不少的西方历史家都认为人类行为本身是价值取向的,是一种价值结构,所以历史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历史家的理论的或价值的负荷。我们在这里仅引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的说法为代表,他写道:“把人类看作有目的和动机的生物(而不仅仅看作是在事件进程中的因果关系的因子),在这种观点中必然包含着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或心理的评价。如果鼓吹历史家把这种评价压抑到最小限度,在我看来,那就是由于混淆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这是最近一百年来最大的和最有破坏性的谬误之一”。⑥以上我们说了这些题外话,用意在表明:波里化乌、兰克、伯林等等的史学观,和孔子的史学观一样,都是一家之言。梁启超对孔子的所谓“恶习”的评定完全是执着于兰克的一家之言,如果梁氏在批判孔子的史学观时,对西方史学的各流派理解得更全面些和更深刻些,他就会对孔子理解得恰如其份一些,而不会作出片面的,过激的诋评。梁氏本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后来接受了李凯尔德的史学观以后,就改变了他的一些重要史学观点。
第二,梁启超仅就为我国正统史学家对《春秋》之义的片面理解去理解孔子的史学观,而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全面地理解《春秋》之义。梁氏在其《论书法》一文中写道:“〔旧〕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虽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梁启超所以反对这种《春秋》书法,因为它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把历史事迹作为供吾目的的刍狗而已。但是,不管怎样评价我国传统的史学观,它本身只是孔子的《春秋》之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对它的全方位的理解。我们在下面将论述《春秋》之义的最重要的方面。(待续)(本文作者朱本源,陕西文史馆名誉馆员)
注释:
①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英译本1923年纽约版,第174页,英译文为:“……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are the consciousness that historiography acquires of itself。”
②我国当代学者一致认为“六经皆史说”最早见于隋代王通的《文中子》一书。请参看周予同、汤志钓的《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年);钱钟书的《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263-264页);何兆武等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北京外文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第408页);台湾余英时的《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一文(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第297-306页)。
③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④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1989年,第178页。
⑤关于波里比乌和塔西陀的史学观的叙述,转引自克罗齐上引书第197页。
⑥伯林:《历史的必然》,见梅耶霍夫(meyerhoff)编辑的《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文选),纽约1959年版,第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