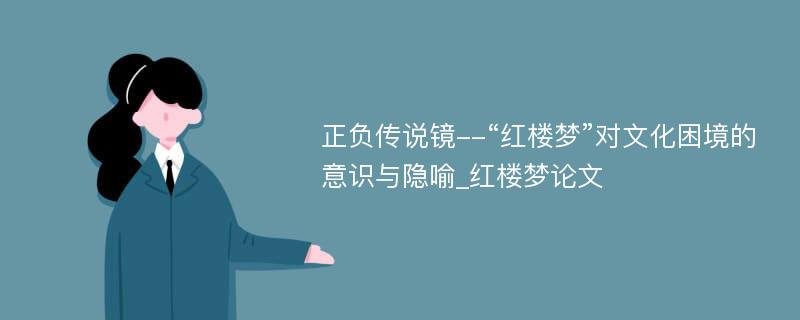
正反悖谬风月镜——《红楼梦》对一种文化困境的意识与隐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谬论文,红楼梦论文,正反论文,风月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风月宝鉴在《红楼梦》中实际上只在第十二回出现过一次,而就有“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第一回)即把它作为总领全书的题目,足见风月宝鉴在《红楼梦》中已大有深意。甲戌本“凡例”在谈及《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五个书名旨义时,有这样的话:“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①]那么作为《红楼梦》文本世界的风月宝鉴,其旨义果真只有这种道德说教意义上的“戒妄动风月之情”?对此,红学界并无人去深究,因为它并未引起红学研究者的重视。笔者却认为,《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富有另外更深的象征旨义,通过对它的解读,我们能从另一种角度把握到《红楼梦》深层文化底蕴所在。
在第十二回,当贾瑞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时,跛足道人送来了风月宝鉴:“我有个宝贝与你,你天天看时,此命可保矣。”并告之曰:这物“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跛足道人向贾瑞悬设了风月宝鉴的功效、看照对象以及看照方式。然而,跛足道人强调了照镜的方式:“只照他的背面”,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宝鉴还可能有另一种功效,而这种功效恰恰是否定“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的,如果只照正面,那么宝鉴非但失去解救之功效,反而会成为一种催命陷阱。既然风月宝鉴是“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曹雪芹又为何同时将另一种可能性功效即诱惑与催命功效维系于风月宝鉴呢?跛足道人明知风月宝鉴有可能成为一个死亡陷阱,他为何不将这种可能性明确地告知贾瑞呢?恰恰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实际上所要预设的两重悖谬:一是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构成相互否定而又同生一体的两极悖谬。当代儒夫妇火烧宝鉴时,镜内却说:“你们自己以假为真。”这表明宝鉴正面是假,反面是真。因而那种两极悖谬也就是真与假的两极悖谬。再者,风月宝鉴与看照者构成另一种悖谬。宝鉴与照者作为解救者与求救者,他们之间本应是能动与被动的关系,然而当跛足道人把宝鉴交与贾瑞时,实际上就是将主动权交与了受动者,作为能动解救者的宝鉴成了作为受动求救者手里的被照者。而求救者正由于他是求救者,故而他永远是无法掌握主动权的受动者,如果他能够成其为一个能动者,他就无需解救。风月宝鉴与看照者之间所构成的悖谬是:当人需要风月宝鉴来解救的时候,其实他已无可解救;当人无需解救的时候,也就无需风月宝鉴。
曹雪芹何以要通过风月宝鉴来预设那种二重悖谬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尚需对风月宝鉴镜像作进一步具体阐释。
宝鉴反面是骷髅,正面是纵欲,既然说反面是真、正面是假,那么,反面镜像的骷髅在何种意义上是真?而正面镜像的纵欲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假?这个真与假又如何能共生于宝鉴一身?
骷髅是死亡后的生命形态,而死亡对于人来说,永远具有普遍性,正由于此,骷髅的确构成人的本真形态,每个人终将都会成为骷髅的。而纵欲却是唯有肉体特殊而无有生命一般,正由于此,此肉体特殊实际上只能是抽象的生命特殊,因为它以皮肤滥淫形成对生命的否定。因此,相对于作为人之本真形态的骷髅来说,那种未死亡却正在走向死亡的皮肤滥淫,的确只能是无有生命意义的虚假现象。然而,作为人之本真形态的骷髅,却也同样无所谓生命的意义,因为骷髅是剥去了个体生命一切生之内容后的死亡形态,骷髅镜像就是直接对生命的否定,在这一点上,它同正面的纵欲镜像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这样地认为,风月宝鉴镜像,无论是正面的纵欲还是反面的骷髅,实际上取得的是同一种本质,只是表象形态的不同,这种本质就是死亡:骷髅是已经死亡的死亡形态;纵欲是走向死亡的死亡形态。前者是一种否定了一切生之内容后的普遍形态,因而是无生命的抽象的普遍;后者是唯生命肉体的个体特殊,因而是无普遍形式的抽象的特殊。风月宝鉴正反两面镜像其实都是抽象的非生命形态,抑或说都是生命之死亡形态。它们构成了相互否定而又互为因果的关系:骷髅否定一切生命特殊而唯有苍白而干枯的一般;纵欲则相反,唯有感官肉欲而否定一切普遍和一般。正由于骷髅要否定一切生之内容,故而有唯生命肉欲的感官放任;反过来,又正由于纵欲是无任何生命普遍形式的皮肤放任,故而有干枯的普遍形式的骷髅。
风月宝鉴镜像是由宝鉴与贾瑞所共同完成的。虽然《红楼梦》再没有写到其他“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看照宝鉴,但曹雪芹通过贾瑞的看照所预设的二重悖谬已经表明:风月宝鉴对于任何一个需要看照它而企望通过看照获得解救的人来说,无论是正面或反面,都只能构成看照者的死亡陷阱,抑或说,它永远成为一把插向看照者心脏的风月宝剑。诚然,风月宝鉴警世戒妄、济世保生之功效必需通过需要看照者的看照而实现,但那种功效对于看照者自身来说,却是永远构不成的。《红楼梦》中,虽然只有贾瑞一人看照过风月宝鉴,但并非只有他一人需要看照,但却只需贾瑞一个人的看照就足以看照出“红楼”世界中许多的需要看照者来。《红楼梦》正是通过贾瑞的看照,从而让人看到风月宝鉴正反两极悖谬的非生命形态,它们不仅是贾瑞自我生命病态的两极分离幻相,也是风月宝鉴照摄的“红楼”世界其他许多人的两极病态幻相。也就是说,风月宝鉴不仅是作为贾瑞需要看照的镜子而存在,更是《红楼梦》中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指涉。
我们可以把“红楼”闺阁以外的男女归结为两种类型群体:一类是以贾政为代表的包括贾政的幕僚、甄应嘉、甄宝玉乃至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林如海、王子腾等男性,以及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包括薛姨妈、邢夫人等女性组成的群体;一类是以薛蟠、贾琏、贾蓉、贾芸、贾环、孙绍祖等男性,以及以多姑娘、夏金桂、宝蟾、秋桐乃至赵姨娘等女性组成的群体。
对于前一类群体中的男性,《红楼梦》借贾宝玉之口称他们为“禄蠹”(第十九回)。他们如“《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左窃尧舜之词,右背孔孟之道’”(五十六回),是空谈心性却无能于世俗事务的粹然醇儒。如贾政,“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梁轻薄仕宦之流”(第三回),但他却既在贾府内族“不惯于事务,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来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兴等几人安插摆布”(第十六回),在仕途之中,又任李十儿等恶奴“做起威福,钩连内外一起哄着贾政办事,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第九十九回),他“案牍劳烦”却“迂腐古板”(第十七回),虽心性古仆忠厚,但却无论为臣为官为父为子都是一个无能废人。而这类男性群体却既代表了社会意识形态,又代表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他们是儒家文化在政治生活、家族生活及个人生活中的具体履践者。前一类群体中的女性则自觉自愿地以自我生命意义的丧失,从而构成前一类男性现实履践的一部分。“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②]从中可看到,父权文化的形成虽然其中有女性的参与,但她们却是工具性地参与,这种参与正是以女性生命的沦丧为代价,即如贾宝玉所言,她们实际上成为“死珠子”、“鱼眼睛”(第五十九回)式的苍白生命。前一类男女群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个体生命意识已被迂腐抽象的儒雅规范所消蚀,他们实际上已沦为被挤干了生命汁液的木乃伊,已经无法去感知自我生命、大自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机与活力。我们从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中即可看到贾政及其幕僚处水光山色之中却迂腐古板,只有贾宝玉流光溢彩;从王夫人等人恪守“班姑、蔡女之德”(第一回)的贤淑向善中即可看到她们“处膏梁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的无见无闻”(第四回),难怪贾宝玉刻骨铭心地诅咒古代圣贤:“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第一百十八回)说女孩子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则变成了死珠子,再老了竟是鱼眼睛了。这一类男女群体正是正统儒家文化精神的人格具象,也是其文化功能的体现者。不仅其自身的生命活力已遭泯灭,而且他们是在自觉地去对自我与他人的生命价值进行否定中体现儒家道统之非人性功能的,即如戴震所言的“以理杀人”[③]。贾政的所谓忠厚古朴造成的却是民不聊生、宝玉挨打;王夫人的贤淑从善酿成的却是金钏投井、晴雯夭折。这一类男女群体正是风月宝鉴上骷髅镜像的象征指涉。
如果说前一类男女群体是既定历史文化之所谓正果的话,那么后一类男女群体则是其反面之所谓恶果。这是另一类型的抽象生命。他们是“斗鸡走狗、问花评柳的一干游荡纨绔”(第七十五回)、“皮肤滥淫之蠢物”和一群“流荡女子”(第五回),唯声色货利是图而无文化规范可言,其个体生命成为一具纯粹形下之物,那是有如动物式的存在,他们是一群无有文化精神和生命形式的行尸走肉:贾琏偷鸡摸狗、孙绍祖淫虐无度、薛蟠玩女狎男、贾赦贾珍欺世盗名。他们则正是风月宝鉴上纵欲镜像的象征指涉。
“红楼”世界那两类男女群体,正构成同一历史文化形式下的两类非生命性的病态人格。前一类是一种纯粹抽象的文化人格形式,即抽象的儒雅规范的人格具象,这如同骷髅镜像,骷髅正是否定和抽去了一切生之感性内容后抽象而无用的普遍形式,它已非个人,亦非人,而是非生命的干枯形式。后一类,完全依肉体的感官冲动而存在,而完全否定一切对肉体感官的文化普遍规范。人受本能欲望的自然驱动而放任流荡,这如同风月宝鉴的纵欲镜像。这种人同样非个人,亦非人,而纯粹是一堆非人性的肉体。风月宝鉴所照出的正是“红楼”世界中那两类非生命性质的两极分离形态。
骷髅与纵欲镜像,直接指涉于“红楼”闺阁之外两类男女的两极形态,而我们所进一步要深究的是,那种无法整合的两极悖谬,其实正是明清之际文化哲学精神内在的重大悖谬,同时也是其时社会现实上人所面临的巨大生存困境。
其实,儒家文化在其始源的孔孟学说中,就已潜伏了拒斥人的生命感性的可能性,虽然孔子通过“三年之丧”、“孝悌”[④]把人欲、礼和仁较完善地统一为内在人格心性与外在行为方式之互动互摄的有机整体,孟子更把仁义礼智四端赋予先验色彩,从而把人的生命本能筛取和置换成道德本能,孔孟因而开启了整个中国古代儒学的伦理道德价值向度。但从孔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⑤]即可看到潜隐于其仁学的内在矛盾,即“好德”与“好色”在人之天性中的分离而难以整合的矛盾。虽然从孔子开始,儒学对“色”筑起的是坚固无比的道德理性堤坝,从而把它疏导到伦常渠道,但这却无法从根本上去消除“色”之盲动性质,漫长的儒学演进理路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儒学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性”到董仲舒的“天”到朱熹的“理”到王阳明的“心”,这似乎演示为一种逻辑循环,但其中却蕴含着哲学意识的运动与发展,而这种运动与发展过程也正是潜隐于孔子仁学中的固有矛盾逐渐显露而走向激化的过程,即从道德一元到道德理性与生命感性的二元分离。此二元分离,在个体人格心性上,使孔子“吾与点也”到理学“孔颜乐处”成为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苍白幻影;在社会政治上,使孟子的“不忍仁政”走到了“灭人欲”的宗法专制;在人的行为方式上,使孔子的以礼识仁走到了内圣与外王的背反。可以说,正是那种分离,使儒文化在社会意识形态、个体人格心性以及人的行为方式上全面地步入病入膏盲的明清时期,这便是从文化哲学到社会现实上全面演示的“理”与“欲”的巨大悖谬时期。宋明理学在“明天理去人欲”的逻辑过程中建立了拒斥感性生命的“理”本体规范,然而何为天理?“朱熹庞大体系的根本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观念公式:‘应当’(人世伦常)=必然(宇宙规律)”[⑥],即把几千年的儒雅规范高扬为必然律之绝对命令。这个既无视历史发展运动又无视个体生命感性的理本体走向破裂是必然的,因为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发展,古老的儒学伦理规范也必然日益沦为人的感性生命之异在,即沦为一种日益抽象而无有生气的苍白形式,正如戴震所言:“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⑦]
由此,出现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以及社会现实上的纵欲风高现象是自然而然的事。何必隐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⑧]李贽明确提出“夫私者,人之心也。”[⑨]戴震强调“好货好色,欲也,与百姓同之即理也。”[⑩]他们以强调另一极的“人欲”,从而对无视人的生命感性的理学构成反动。虽然他们对促进人的生命解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们本质上已遁入某种文化怪圈,即从“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性论变而为资本主义的自然人性论,走了一个圆圈,似乎回到张载、朱熹所要反对的地方。”(11)因为他们都未能也无法“建立任何可替代宋明理学的新的哲学系统。”(12)故而,他们滑向另一极端的非理性鼓噪带来的却是明清之际的靡然从风景象。
源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性论在生存现实上具体体现为一个极端;而源于王阳明心学直到李贽、戴震等人的自然人性论则在生存现实上具体体现为另一个极端,此文化精神内在的两极背反,构成社会现实上道德理性与生命感性的两极分离。《红楼梦》闺阁以外的两类男女群体之两极病态人格则正是那种两极分离的写照,他们也正是曹雪芹在风月宝鉴上所显示的骷髅与纵欲两极镜像的象征指涉。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恰好体现为明清之际儒家文化精神中“天理”与“人欲”的背反,体现为把那种背反具体化了的病态现实及其病态人格。天理与人欲的两极背反并非两种文化价值取向的背反,而是同一历史文化以两类病态形式体现出自身的自我否定性和无用性。因此,骷髅与纵欲两极镜像,无论是取正取反,它实际上无法构成正反价值取向的悖谬,而只能是同一本质的死亡,要么是已经死亡的骷髅,要么是走向死亡的纵欲,它们既是贾瑞在风月宝鉴上所看到的自我无以解救的两极病态,同时也是风月宝鉴所照摄到的明清之际病入膏盲的文化困境和现实困境。
《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的出世,不仅意味着曹雪芹对文化和现实中“理”与“欲”的两极困境的哲学意识,更意味着他要为消除那种困境而作出哲学努力。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当人根本上就无需风月宝鉴的时候,才会出现一种无需解救的文化和现实,才会出现一种健康而完好的生命人格。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进行一种文化逻辑的逆转,才能从根本上整合“理”与“欲”的分离,才是使人的肉体与精神获得完整复活。由是,相对于“理”与“欲”,《红楼梦》断然提出了“情”这个新的文化价值符号。“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第五回)这既是直接对人的生命存在所进行的追问,又是对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行直接的本体性追向。这其中蕴含着对整个古代文化的颠覆与否定,同时也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开启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向度。
于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出了另一种富有新的文化意义的现实——大观园闺阁世界。他以“使闺阁昭传”(第一回)的勇气和目的,以想象的方式展现了在“情”文化氛围中的另一番人文景象,这在第六回到第七十回甚至更长的章回里,占去了《红楼梦》的主要篇幅。《红楼梦》把闺阁世界从一种被历史文化压向边缘之暗处弘扬开来,因为曹雪芹充分认识到,正是那个严格受到正统儒雅文化规范所禁忌和禁锢的边缘世界,同时也就是遭到其尘染最少的一方净土。闺阁世界的少男少女充分遵从和顺应于自我的生命激情以及生命之间的相互吸引,这不仅使每个生命都真实而晶亮起来,也使各个生命之间的关系也真实而晶亮起来。并且曹雪芹有意把闺阁世界放置于水光山色的自然怀抱,从而直接地将它与大自然相联结相交融,让闺阁人在大自然的草木枯荣、季节更替中去充分感受生命、舒展生机。《红楼梦》甚至精心组织了一幕幕的生日宴会、节日庆典、游艺仪式、语言戏谑等场面与情境,从而在其中热情洋溢地绘制出一幅幅高潮迭起、多姿多彩的生命图案。曹雪芹的所有努力,要达成的是一个目的,即:把闺阁世界塑造成一种崭新的生存现实,把闺阁人塑造为一种崭新的文化人格。而这同风月宝鉴镜像所指涉的那种两极背反的病态生存现实及其病态人格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本质。曹雪芹所要弘扬的“情”,不在风月宝鉴所指涉的“理”与“欲”的两极悖谬之间,而在那种悖谬以外,它只存在于闺阁世界之中。因为“红楼”作者深深体认到,“理”与“欲”所构成的两极生存悖谬,已经无法孕育出人的个体生命之意义,也无法孕育出人的类属性之意义,而只有真“情”,才意味着人的意义。
这便是以贾宝玉为典型的情性化的生命人格。贾宝玉既非如贾琏、薛蟠等人那样,只是任由感官本能的放纵,即唯有肉体特殊而无有普遍精神,也非如贾政等人那样,只剩有干枯而苍白的人格精神而无有丰富的个体生命内容。在贾宝玉身上,个体性与普遍性、特殊性与一般性、生命感性与道德理性得到一种完整而健康的融合,从而完全消除了传统文化精神内在的“理”与“欲”的两极悖谬。贾宝玉以一种真情博爱的方式,结成与他人与世界的普遍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生命与生命、生命与世界的感性关系,也是生命与生命、生命与世界的精神关系。同样,以林黛玉为代表的大观园闺阁女子,既非如夏桂花、多姑娘之流那样唯声色货利是图、如行尸走肉一般;亦非如王夫人等人那样唯三纲五常是从、如槁木死灰一般。她们是一群秉“天地日月之精华”的闺阁精灵。她们身上洋溢着生命自然之盎然生机,活泼泼地充盈着生命的创造力,她们把闺阁世界创造为五彩缤纷的美的世界,使闺阁生活成为诗意的栖息。她们同贾宝玉一样,是一群富有崭新的文化人格的生命群体。
通过对风月宝鉴的深入解读,我们已能从另一种角度深刻把握到《红楼梦》的文化意蕴所在:风月宝鉴体现出“红楼”作者对中古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古社会现实中所固有的“理”与“欲”的两极悖谬的哲学意识;同时也意味着“红楼”作者试图以“情”这个新的文化价值形态去消除而整合那种两极悖谬的文化哲学努力。
“理”与“欲”、道德理性与生命感性的两极分离与悖谬,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依然面临着那种巨大的生存困境。所以,风月宝鉴不仅是高悬于“红楼”文本世界的一面宝鉴,而且,至今依然可以成其为高悬于人类头顶的一把宝“剑”。
注释:
①:见徐辑《从〈红楼梦〉数易其名得到的启示》载《求是学刊》,1985年第2期
②:《易·序卦》
③⑦:戴震《与某书》
④:《论语·阳货》、《论语·学而》
⑤:朱熹《论语集注卷五》
⑥ (11) (1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33、249、28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
⑧:《何心隐集》第4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⑨:《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⑩:《孟子字义疏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