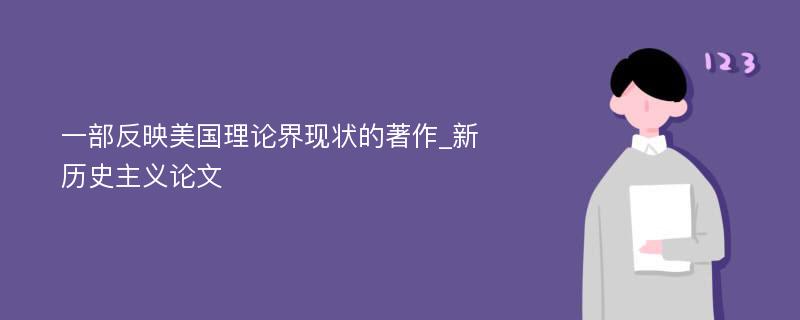
一部反映美国理论界现状的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界论文,美国论文,著作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要介绍的《近期美国理论中的压制和反抗》,集中揭示了美国理论界目前的一些论战,对美国当今流行的一些后现代理论持批评和审查态度,认为新近出现的非常时髦的新历史主义和阵容强大的解构主义之争,不过是几十年前发生过的旧历史主义和新批评主义之间老的争论的延续和发展。该书作者纽勒·科瑞格(Murray Krieger),现为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教授,是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也是美国批评和理论学派的先驱和创始人。他迄今已经发表十多部著作和几十篇论文。
本书首先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旧历史主义和新批评主义之争。旧历史主义萌芽于美国19世纪中期。当时的美国文学界兴起了一种要求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的呼声。在这批呼吁者看来,美国文学必须独立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文学,成为一种由美国本土生发出的和由美国社会之根营养出的东西。这些人把美国看做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把美国人看作是出生在美国的亚当,居住在一个新的天堂中,以其新颖性和纯真性区别于那个旧的和堕落的世界。这个新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它必须忠实于这个独特的国家命运,尽量不模仿英国文学传统中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不使这些形式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方式污染这个新世界。对这样一种使命的向往导致了一种社会历史批评观:它把美国文学当成一种能直接反映独特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东西,而很少顾及和关心其他地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文学中所具有的美学趣味和性质;它还极力强调对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研究,把注意焦点放在文学作者所在的社会历史环境上。
这种以牺牲审美关怀为代价的旧历史主义激发出一种反抗力量,这就是自30年代发展起来的把文学作为艺术和文学、提倡仔细阅读文学文本,欣赏文本本身的审美意味的“新批评主义”。这一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进入大学,成为大学文学系的主要力量和教学内容。很明显,新批评主义注重的东西,正是提倡研究美国文学特色的历史主义所忽视和抛弃的。新批评主义一旦立足,便致力于建立一种适用于解释一切文学(而不仅是美国的)的形式的或结构的原理。它把文学视为一种不受一般规则制约的特殊话语形式,因而需要一种特殊设计出来的分析技术,这种技术只能用于文学分析,而不能用于其他话语形式。相应地,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单纯是为了弄清文学文本同其作者和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而是集中于文学形式之内的各种相互关系的研究,因为只有这种关系和相互作用能解释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的巨大力量。
在1940年前后的大争论中,新批评主义指责旧历史主义沉溺于周围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而不加强自身的美学修养,成为不辨音和色的聋子和瞎子,对构成文学作品的那些美学性质毫无反应和知觉。反过来,旧历史主义者指责新批评主义者,说他们是无知的学者,不具有关于历史上各种思想和观念的点滴的历史知识,对各种典故一无所知,而这些都是解释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东西。
作者认为,目前发生在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之争,正是这一旧的争论的延续和发展。
目前出现的美国解构主义者继承了新批评主义的传统,但不满意新批评主义者将诗的话语同其他话语分离开来的主张。在新批评主义者看来,在诗的话语(包括小说、散文等)和常规话语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诗是对正常话语之常规功能的破坏,它必须扭曲正常话语的用词顺序,模糊其词语的含义,强调隐喻的使用和它的构成力量,迫使它再现常规语言不能再现的东西。反之,如果语言被用来表达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的意识和观念,就成为一种局限性很强的工具。而诗和文学的特权在于,它自身就含有对各种确定性观念的否定力量。阿纳尔德(Arnold)指出,诗作为一种言语系统,能抛开那种仅仅指涉和装载冷漠的知识的义务,破坏了那种由普遍的命题和真理组成的冷漠的知识世界,通过这种破坏,使我们有可能把握一个更丰富的世界,这个世界比天地间现有的东西更丰富,比理性哲学家们梦想的东西还要丰富得多。雷查兹(Richards)则认为,诗通过讽刺而产生一种平衡力量,这种力量总是产生出一种反向冲动去对抗我们的那种只在一个固定方向上行动的冲动。新批评主义者将诗和文学话语独立于其他话语的做法,受到后来兴起的解构主义的反对。这些解构主义者将自己的阅读扩大到文学之外的其他文本,而且在阅读时比新批评主义者更仔细。他们发现,即使那些典型的非文学文本,也可以运用阅读文学文本的方法阅读,从而在其中发现许多与它们表面想要表达的意义相悖的或与之完全不同的微妙意义。美国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尔·的·曼用这种方法阅读了英国大哲学家洛克的著作。在英国哲学史上,洛克的论证通常被认为说理最直接和最不具有模糊其词的特征。然而包尔在阅读时发现,这种文本同样要借助一系列的文学比喻和转喻,它们传达出的许多微妙含义与作者明显要说的东西相互矛盾。这一实例说明,任何文本,不管看上去如何专一和单纯,都能在其中发现与其原来的“纹理”相反的“反向纹理”。解构主义和新批评主义的不同在于,它关心的文本的范围超出了文学,把一切语言看成是为平等的和都能按照解构主义方法阅读的东西。而阅读的目的,就是寻找出任何文本的自我解构的倾向和性质。很明显,虽然解构主义者反对新批评主义者将文学单独列出来并赋予一种特权的做法,其对待文本的方法上,却与新批评主义有类似之处:二者都把文本视为反抗已有的和固定的思想观念的东西,都把文本本身视为一种反观念的过程。
与此同时,美国文坛上还出现了另一种思潮,即新历史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既反对旧历史主义,也反对解构主义。它抱怨解构主义,说它总是以一种非历史的神秘主义谈论语言的散播能力,对文本之间的语词游戏不设立任何界限,更无视其历史背景,从而陷入到文本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它攻击解构主义不过是形式主义的晚开花的花朵,无法使自己同政治现实联系起来。
但是,在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中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使它们与旧历史主义和新批评主义区分开来。按照旧历史主义,历史就是一系列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真实的事实,它是客观的,也是可以证实的,其本身不需要阐释,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文学文本就不同了,它是想象性的,也是有疑问的,因而需要阐释。而所谓阐释,就是用我们已经知道的去解释我们不太知道的。而这就意味着,可以用历史去解释文学文本,以解答文学文本中那些有疑问的问题。一句话,在旧历史主义看来,历史是事实,而不是话语。在大约二十年之前,这种情况改变了。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出现,历史也同其他一切话语形式一样,变成有疑问的。它不再被认为是纯粹的外部客观事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话语形式,只不过它是以叙事体写成,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对所谓的事实的解释。这意味着,历史也同其他一切话语形式一样,是有疑问的和不确定的,所不同的是它比其他话语形式更具有欺骗性。总之,历史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解释的文本,它与外部客观事实的关系不比其他文本更亲近,因而不具有解释比它真实性更小的其他文本的特权。对“历史”本身的这一认识,来自于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共同见识:对任何一种文本的阅读,都与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和非真实性无关。人们应该把整个所谓的知识世界看成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一个话语的世界,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文本。通过这种转变,新历史主义就摧毁了旧历史主义的基本假设,不再像旧历史主义者那样,把文化中的某一时刻看作是一种好像摆在那里等待我们去直接认识的、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一组事实,相反,它把那个想要将所有的种类的文本互相联系起来的读者看作是一个正在玩戏法的人,他把手里的许多个球同时抛在空气里,其中一个也许是文学,另外一个是历史或人文科学中的任何其他一个学科。在这所有的学科中,没有一个是优先的,也没有一个比其他所有的更稳定些。所有的文本都要同样地阅读,它们同样都是不稳定的和需要解释的语言片段,任何一个都没有优先权。就历史来说,它已经不是一种自明的事实,因而不能充当一种解释的代表,去解释其他不确定的和有疑问的文学文本。同样,文学也不应该将自己看作是一种与历史或其他任何话语形式不同的话语,因为所有的话语都不能再现现实。那么一个试图使自己的评论合乎历史的评论者该怎么办呢?通常情况下,他必须阅读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各类不同的文本,在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融合中,找到它们的共同元素——隐喻、叙事结构,即福科说的“话语结构”。新历史主义者通常是使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文本互相“阅读”,将所有这些文本视为同一种文化中的某一时刻的不同组成部分,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同一个“循环系统”中。但是,在详细审查了某一文化时刻的所有文本并找出它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结构后,新历史主义者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继续超越其话语,揭示出创造这一独特的话语结构的社会政治力量。在他们看来,这种从不同文本中展示出的话语结构,揭示出一种共同的比喻的和叙事的结构,其修辞功能是偏向某一种判断,保护社会中的某些分子和压制其他一些分子。换句话说,它揭示了某一历史时刻中社会结构中的力量的等级次序。包括种族的,阶级的和性别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创造了自己的话语,通过对这些话语结构的认识,就可以判断,是谁在对谁行使权力?谁在拒绝这种权力?这种拒绝付出了什么代价?话语的界限是如何确定的?是在为谁的利益服务?毫不奇怪,这种做法将新历史主义者引导到一个明显的政治方向上。在他们看来,在每一种历史时刻的每一种观念和意识,都在创造自己的语言,并通过自己的语言说出自己的话语,这些话语隐藏在文本中,等待捕捉读者。这就是说,新历史主义者必定是一些对一个社会中的真实的政治权力敏感的人,它们对话语的兴趣最终同权力挂上钩,这就暴露了,它不过是旧历史主义主张的一种延续。与美国早期的那种捍卫从美国本土滋生出的美国文学的论调相互呼应,虽然二者在方法上已经根本不同。
新历史主义者的上述做法和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解构主义者的批判。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新历史主义者也同旧历史主义者一样,最终在文本之外的真实历史关系和权力斗争中找到落脚点,认为文本受到真实的历史关系的控制,这就完全违背了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原则。作者认为,这种争论归根结底是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是关于文学是要反映思想观念还是拒绝反映思想观念之争。他认为,任何一个精明的读者都不会反对,语言会受到权力的控制和侵犯,即使那些解构主义者也得承认,语言结构中如果没有观念进入其中,语言就没有用处了。但是解构主义者的做法也是有意义的,他们有理由将诗歌和文学看作是运用它的要素去反抗流行观念的领域,只有这一领域才能通过其语言游戏,寻求从某一单调的倾向中解脱出来的自由。但不管怎样,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新批评主义早先追求的文学价值受到怀疑和解体。现在的多数具有影响的理论家都劝说人们去注意评价过程本身——即评价时涉及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过程本身或是我们评价时的那种奇特的行动本身。他们认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要评价和如何评价,而不是确定什么东西值得评价——什么东西真正地包含价值——因为后者的行动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帝国主义的企图——通过声称自己发现的那种狭隘的价值是普遍的和普遍适用的,而将自己的偏见强加到别人身上。
这种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强调产生的一个明显的后果,是人们对一种宽泛的文化理论的重视和注意,导致了对不同的话语之间的界限的解体,进而摧毁了大学中各个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科学学科之间的界限,从而使大学中各个学科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融合本身产生了一种“隐藏的大学”: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促使人们相互指导的机构,这里没有一种被认可的固定学科,没有固定的课程或教学日程,不同系科的教工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互相教育,从而使每一个人将自己和自己的学科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这一视野允许他们相互交织,从而走出自己的学科,不受其约束。学科之间界限的松动,人文科学范围的拓宽,使现在的大学具有一种值得主义和尊敬的特色,它促使人们对那些长期被视为神圣的和不成问题的东西提出了问题,从而大大激励了人类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