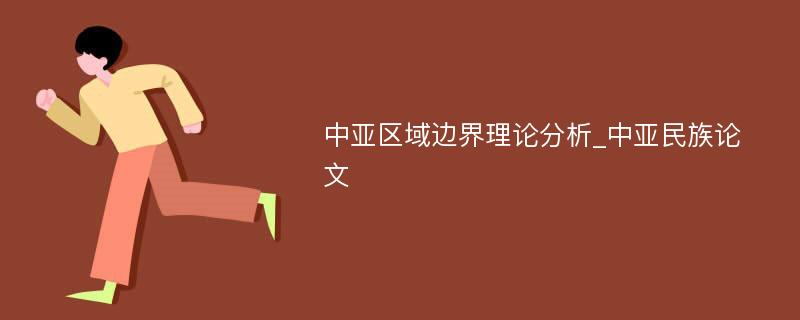
中亚地域界说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地域论文,界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中亚史,首先必须划定中亚地区的界线,明确中亚一词的范围,可是,目前研究中亚史的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却是众说纷纭,歧见丛生。本文拟作一次搜寻扫描,对各种界说试以排比诸说,校核质疑,谨呈之于前辈及学界同仁,乞望教正。
在学术界,影响较大提出较早的有德国著名学者洪堡。他认为中亚包括里海到兴安岭、阿尔泰山到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带。与之正成对照的是另一端的看法,认为中亚主要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这种说法也流传甚广。王治来教授在《中亚史》一书里中肯地评价说,前者失之太广,后者失之太窄。[(1)]他还指出:“在苏联,中亚一词专指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2)]下文中虽然没有进一步确指,但看来应该是指中亚全部的五国。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克瓦顿认为中亚从北到南分为冻土带、泰加森林、草原和沙漠4个地带,这4个地带“覆盖着从匈牙利到中国,从北极圈到波斯高原的广阔地区。”[(3)]这就比洪堡所指的范围更广。
在上一世纪的欧洲,人们已经感到“中亚”这个概念的不明确。德国的李希霍芬试图解决问题,提出中亚应该定义为亚洲内陆没有流入外洋的内陆水系分布的地域,也就是蒙古的大部、准噶尔、西藏北部、东西土耳其斯坦和阿富汗北部。此说虽然仍旧可划归“广阔归”,但已经是一种新的思路。它从水系流向来划界,对后来的内亚(内陆亚细亚)概念的产生是一种先导,也曾被一些学者广泛使用。日本就有学者认为李希霍芬的定义“最为清楚明了”[(4)]。可是,这种界定仅从自然条件出发,毫不考虑政区、民族、文化等因素,使得它在历史学中常常处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在日本,中亚学长期是一门显学。不过,日本学者对“中亚”的界说直到不久前还给人游离不定、徘徊摸索的感觉。就从权威的《史学杂志》每年刊载的研究动态综述来看,曾经题为“蒙古·中亚”的专栏在60年代初改成分为“满洲·蒙古·西伯利亚”、“中亚”、“西藏”3个栏目。1964年日本的“北亚史”和“中亚史”两个领域的专家首次联合召开“野尻湖最高会议”以后,1967年上述栏目又定为“北亚”、“中亚”和“西藏”,直至80年代。[(5)]
从那种过于宽泛的“中亚”区划中分出位于冻土带和泰加森林的“北亚”,这是有必要的。但是,他们所理解的“北亚”并非如此。被评价为反映80年代日本北亚史研究动向的护雅夫和神田信夫的新版《北亚史》,竟然前一部分叙述蒙古民族活动地区,后一部分叙述中国东北地区(“满洲”)。这种对“北亚”的理解,起码我国学术界就难以认同。与此同时,日本“中亚史”的研究对象又不时向东向南过分超越。
俄语文献中,情况也相当复杂。19世纪,俄国人使用的“中亚”词组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ъная Азия),一个才是后来常用的“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后者的“中”侧重于“中间”、“当中”的意思。在商务印书馆较新版本的《大俄汉词典》中,这两个词组都译为“中亚细亚”[(6)]。实际上,上述二者的含义有一定的差别。前者涵盖的地域有时要大出许多,特别是向东方展拓,近于洪堡说法之类,有时又与后者混用。前一词组到后来也逐渐少见。为了区别,似乎可以将前者译为“中央亚细亚”,后者译为“中亚”。《大俄汉词典》是在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的基础上增订编成的。[(7)]。而《俄汉大辞典》中正是将这两个词组分别译为“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细亚”的[(8)]。建议《大俄汉词典》重印再版时考虑作修订。
不过,问题的症结所在,倒还不是这两个词组的区别,而是后者自身的歧义。
分歧的核心在于19世纪的哈萨克是否应该属于中亚。的确,原苏联的一批涉及征服中亚史的著作曾经将中亚与哈萨克分开。[(9)]可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上一世纪的后半期到本世纪初,俄国的一些比较权威的代表著作就认为中亚包括哈萨克。例如捷连季耶夫的《征服中亚史》所附《中亚地图》就是这样的[(10)]。
《征服中亚史》的序言中先提到当时的中亚一般指3个汗国。但是随即便指出,这些汗国的疆域由于各游牧民族的归附而扩展。于是,在当时“中亚的概念就扩大了”,不仅只是指三汗国本土,也包括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生活的地区(沙俄时代称哈萨克人为吉尔吉斯人)[(11)]。此后,在这部书中也正是这样使用的。例如,谈到19世纪初连接从奥伦堡到西西伯利亚的各条要塞线(略近于现今哈萨克北部边地)的时候称此举是“封闭我国中亚边境”[(12)](句中的“我国”指俄国)
俄国人一般也都习惯类似用法。比如作曲家鲍罗丁的名作《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在俄罗斯可说是稍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的。它所描绘的大草原景观正是哈萨克斯坦北部的特征,这与三汗国本土的绿洲缀于沙漠间的那种地貌大不相同。
西方学者一度认为苏联学术界都是将哈萨克同中亚分列的。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著名史学家梁申科就曾经专门讨论过中亚的地理范围。他也指出中亚的“地理境界并不很明确”,但是认为其北方“越过西部西伯利亚草原和乌拉尔山的山麓。”最后的结论则是在“通常称为中亚细亚的历史地理的疆域内,我们便列入了5个苏维埃共和国。”[(13)]当然就包括哈萨克在内。
近年来中亚五国的说法更是在世界各国报刊上频频出现,成为约定俗成的通行用语,似乎还未见过“中亚各国与哈萨克”这样的组合。看来,五六十年代一些苏联学者对中亚的界说,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也只是一种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欧美的中亚学界大都不同意将哈萨克单列的做法。如,中亚史学家弗鲁姆金在他的《苏联中亚考古》前言中声明,与苏联用法不同,他所指的中亚包括哈萨克和西土耳其斯坦[(14)]。《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哈萨克共和国辞条中,也明显将哈萨克归入中亚,比如说它“象邻近的其他中亚共和国一样”等[(15)]。伦敦出版的魏勒尔的《苏联中亚现代史》则指出:“如果不是研究中亚古代史而是研究中亚现代史,将这5个共和国放在一起来研究,从它们种族的和文化的渊源来查,这样作是有道理的。”[(16)]
我国地理学界由于多方面的影响,对中亚一词也是众说纷纭。在这里,姑且分别归之为“四国说”、“四国半说”、“五国说”。
“中亚四个加盟共和国”的提法,可以举出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编写的《世界地理》为例[(17)]。这4国是指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不包括哈萨克。
“四国半说”一度影响颇大。70年代发行最广的一本世界地图册中就明确断言,中亚“包括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4个加盟共和国的全部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南部。”[(18)]
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常见的是“五国说”。但是由于仍然是其说不一,甚至发生一书两说。例如多校合编的《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中,先有“中亚的一些国家,如哈萨克、乌兹别克等”的讲述,几页后却又出现“哈萨克与中亚”这样的区域名称[(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各种传播媒介中,“中亚五国”的表述方法则越来越普遍地被采用。
面对歧见纷杂的“中亚”界定问题,项英杰教授在80年代初为贵州师大学报增刊《中亚史丛刊》确定办刊方针时就指出:“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以现今中亚5个共和国,即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塔吉克为主体。附带涉及其周邻的有历史上疆域盈缩关系的地区,如伊朗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西伯利亚西部、乌拉尔西部以及我国的新疆和西藏。”[(20)]事隔多年,再来回顾,对于这一提法的切实确当,慎重取舍,而又兼及主次,感受更为深刻。
科学分类有两个基本原则:相斥与穷尽。对中亚的定义如果范围过宽,就会导致与其他地区史、国别史专攻的领域重叠交叉,这违反相斥性原则。何况同时也会导致分散力量,对自己应该专务的辖区反而治理不力。如果范围过窄,就会违反穷尽性原则,发生不该出现的缺环。将270多万平方公里,约当于整个西欧面积的哈萨克地区排除在中亚之外,就是一大遗漏。
原苏联政府极力要将哈萨克从“中亚”地域中分离出去,自然是有它的考虑的。比如可以以此来强调哈萨克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可是,这种做法在学术上却造成了一种难于周圆的困境。其中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就是如果哈萨克斯坦不属于中亚地区,那么它到底应该划归哪一个地区呢?
显然,它不可能属于欧洲。因为乌拉尔山脉与乌拉尔河是公认的欧亚分界线,而哈萨克正位于这条界线东面的亚洲一侧。同时,也正因为此,哈萨克是亚洲各部分当中邻接东欧而偏于西面的地带,似不宜划入东亚。如果把它归入北亚也不合理,因为在地理特点和传统联系上,它同以冻土带和泰加森林为特色的西伯利亚地区是截然区分的。当然,更不可能将它归属于西亚或南亚。它们之间连邻接关系都不具备,中间还横隔着阿姆、锡尔河流域。假若不是完全取消“中亚”这一区划的话,哈萨克是根本不可能并入西亚或南亚的范畴的。
由于以上困难而在苏联和我国过去一些史地著作中出现的“哈萨克与中亚”的说法也难以成立。这样做虽然绕过了哈萨克归属于亚洲哪一部分的问题,但却将属于较低层次、较小范围的“哈萨克”同较高、较大的“中亚”这一概念并列。其毛病有如“奶牛与牛”、“地球与太阳系”这些奇怪提法一样的不相称。
总之,处于欧亚大陆中间十字路口上的哈萨克,难于归入东欧、北亚、东亚、西亚或南亚,也不应该单列。从地理区划,从历史联系,从宗教、民族、文化的共性,从一贯的经济联系上看,哈萨克都宜于归入中亚。
时至今日,可以说历史的发展为一个半世纪以来让人莫衷一是的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转机。各种说法的合理与否渐显明朗,国际间对此正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定义。各国学者之间缩小对中亚概念理解上的差距,甚至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种可能性也比往昔大为增加。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使中亚地域的界分既不遗漏缺损,又不重复交叉呢?
归结起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清概念。首先是以现今五国为主体。其次,根据所研究的时期的不同,附带涉及者也有适当伸缩。
对于中亚古代史,有时以阿姆、锡尔河流域为重点,有时又可作相应延伸。如治突厥史,后人所称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自然也应纳入视野。类似情况下,极富弹性的“内亚”、“中欧亚”等概念,也有一定作用。
又如哈萨克北部的少数地区属于西西伯利亚,而“北亚”几乎曾经与西伯利亚等同。这大概就是“四国半说”的来源之一。但是,这类用法太不方便,且越来越背离目前人们的习惯用法。至迟从19世纪直至最近,对于近现代史而言,无论从历史脉络、民族宗教,还是从地理条件、政区隶属等各个方面来权衡考虑,大体上还是以五国说较为稳妥。虽然历史学、地理学与一般报刊之间存在分歧,而且它们自身内部也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显然也在逐渐向五国说方向靠拢。
在涉及近代史领域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沙俄在侵占中亚领土的同时,也强占了我国西北的大片领土。这也是在研究和表述中必须加以重视,给予准确阐述的。
“中亚”这一词组所对应的地域怎样界定,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对于中亚近代史又是不可绕行的障碍。事实上,它已经导致某些关于沙俄征服中亚史的阐述刚刚切入问题就发生混乱。试看原苏联将哈萨克从中亚分离出去的那些历史著作,就常常是在论及这段历史的大框架时,以三汗国本土的征战为限,可是一接触到具体过程时还得先从哈萨克入手。由于类似思路的影响,我国的不少论著,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的“俄国征服中亚”辞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1)]。
注释:
(1)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2)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3) (美)克瓦顿《游牧帝国》,列斯特大学1979年版。所引中译文见《中亚史丛刊》第2期,第3页,蓝琪、马骏骐等译。
(4) (日)羽田明《西域史》,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译文见《中亚史丛刊》第5期,第2页,娄贵书译。
(5) 日本《史学杂志》第91编第5号,第244~256页;第92编第5号,第224~238页。
(6)(7)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73、2501页,前言。
(8) 刘泽荣主编《俄汉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88、1264页。
(9) 如(苏)雅库宁《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各民族,中亚归并于俄国》,原苏共中央高级党校讲义,俄文本,莫斯科1954年。书名就将哈萨克从中亚划出并置。
(10) (俄)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俄文本,1966年圣彼得堡,卷末地图。此图中译本未载。
(11)(12) 捷连季耶夫前揭书,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序第1页、92页。
(13) (苏)梁申科《南高加索与中亚细亚各部族的氏族的解体与各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出版《历史问题译丛》1954年第3辑,第95页。
(14) 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学》,中译本,新疆博物馆1981年,黄振华译,第7页。
(15)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本第15版,长编第10卷,第407~411页。
(16) (英)杰·魏勒尔《苏联中亚现代史》,中译本,《中亚史丛刊》第5期,1988年2月,第272页,向阳生译。
(17) 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世界地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06页。
(18) 《世界地图册》,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1972年,第3图“亚洲”所附说明。
(19) 西安外院、北京外交学院等编《世界政治经济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1、230页。
(20) 项英杰《中亚史丛刊第1期编后记》,《中亚史丛刊》第1期(1983年9月),第172页。
(2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1990年版,第1册,第268、269页。参见拙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俄国征服中亚”辞条考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29、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