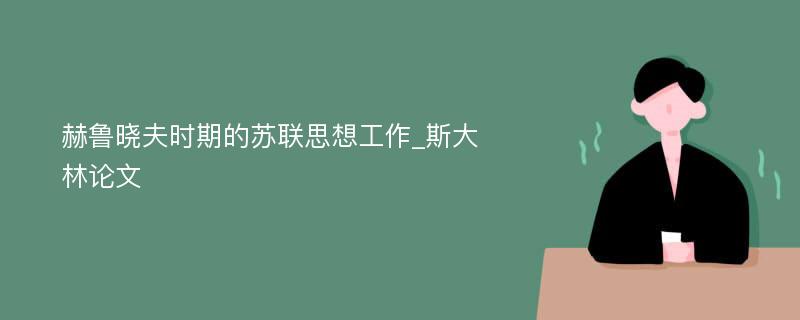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苏联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时期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7)02—0070—(06)
赫鲁晓夫时期被称之为“伟大的十年”(1953—1964年),整个时期特色非常鲜明,相对于斯大林时期的控制和高压政策,是“解冻”的时期。而“解冻”正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因此增色不少。相应地,“解冻”也成了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词和典型特征。
一、“解冻”的阶段性
以“解冻”的程度为度量,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所谓的“两松两紧”①。当然,所谓“四个阶段”的划分并不绝对,只是大体上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解冻”的出现。
“解冻”并不是始于苏共20大,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治、社会开始发生大的转折和变化。自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一文直接批判“个人崇拜”以后,苏联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1953年7月16日,《文学报》发表了社论,提倡文学作品的真实性。“这就是说,要真实地和大胆地,诚实地和无所畏惧地反映我们意气风发的,幸福的,同时又是复杂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斗争和矛盾,困难和障碍;就是说要多方面地,性格多样化地描写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1] (P13)1954年5月,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的第一部。用文学的方式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苏联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褒贬不一、就这篇小说发表了各种评论和意见,在苏联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共领导层对“解冻”这个提法也深有顾虑。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因为一方面我们已经容许在一定程度的放松,人民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在报上和文学作品中已开始有更多的言论自由。”[2] (P137)
但《解冻》的发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54年12月15—26日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苏共中央致大会的贺辞要求作家深入研究现实,“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积极干预生活”,同时对“粉饰现实”和“歪曲、诽谤现实”两种倾向进行了批评。[3] (P442-604)1955年5月7日,《文学报》发表专论,“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有时会碰到一些严重违背历史真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作用的学说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对战争初期的困难常常轻描淡写。”[4] (P34)在苏共20大召开之前,1955年12月《共产党人》第18期发表了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在1956年2月14—25日召开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在总报告中不满意苏联文艺的发展现状,批评文艺“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维埃现实”。[5] (P132)在苏共20大召开前后,苏联文艺界总体上就是强调“现实”,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做法与路线。
第二阶段:开始加强控制。
苏共20大召开一年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路线又产生了新的变化。1956年底、1957年初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开始肯定斯大林的某些功绩。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工作没有继续前几年的动向,采取的政策与方针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一年,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在肯定总的方向的前提下,强调了党性问题、原则问题。1957年3月9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认为该杂志“犯了具有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1957年5月14日苏联作协理事会第三次全会召开,大会主报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提出“个人崇拜对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战后年代,是无可怀疑的”,但同时又强调,不应夸大个人崇拜的有害影响。1957年8月28日,《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内容是赫鲁晓夫5月13日在苏共中央召集的作家会议上,5月19日在作家、美术家、作曲家招待会上,7月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三次讲话摘要汇编。赫鲁晓夫批评“在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中间,还有个别的人有时候丧失立场,离开了正确的道路。”[6] (P113)
第三阶段:再次“解冻”。
到了1958年,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大体上又回到了1957年以前的发展轨道。这个时期强调继续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开始出现人道主义思潮。1958年2月8日,在知识分子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希望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更为勇敢,更注意对生活、对人生的观察!”“下更大决心来面向现代生活”,“抓现代的重大问题”。1960年3月,《共产党人》第10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对人的社会主义关怀》,强调“人道主义、人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活动的主导原则之一”。这一年,苏共还出版了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取代了斯大林时期的《联共(布)党史教程》,成为苏共党史新的理论教材。同年7月17日,赫鲁晓夫接见科技界和文艺界代表讲话时认为苏共中央和知识界对“目标和任务的理解,现在有着完全的一致”。
1961年,苏共召开22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批判。1961年12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伊利切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批判斯大林在理论上所犯的错误。1962年1月30日—2月2日召开的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苏斯洛夫作了题为《苏共二十二大与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强调“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是发展理论思想的最重要的条件”。
第四阶段:执政末期的控制。
1962年,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以后,在苏联文坛掀起了一股“集中营文学”的浪潮。面对无数新的作品,对苏联历史的揭露与讽刺更加露骨、深刻,赫鲁晓夫执政集团重新开始实行紧缩政策,意识形态领域又出现控制的迹象。
1962年以来,格罗斯曼(Гросман)1960年写就的战争题材小说《生存与命运》一直不能发表。1962年7月23日,在同格罗斯曼进行谈话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指出,小说政治上是敌对性的,可能带来的危害比《日瓦格医生》还要大得多,“要出版的话,可能也得等2、300年”[7]。12月1日,在莫斯科参观美术展览和抽象派画展;12月17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伊利切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见苏联文艺工作者;12月24—26日,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召开青年作家、画家、作曲家、电影和戏剧工作者会议。赫鲁晓夫反复强调“有些同志不正确地理解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性质,有时候忘掉了我们的思想立场的不调和性和不妥协性。”伊利切夫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根据苏共新纲领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立场,“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帮助青年文艺工作者唱响自己嘹亮的歌声,帮助党和人民建设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同人民、同党正确地合唱。”[8] 1963年6月,苏共中央就“党的思想工作和当前任务”召开全会,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共处”。他认为“谁要是想置身于党的政策之外,否认意识形态中的党性,那就等于组成一个非党人士的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我们党。反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反对我们的现实。”赫鲁晓夫甚至计划就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专门召开全会,但由于中苏冲突日益激烈,中苏论战开始白热化。1963年8月7—16日苏共中央召开的全苏思想工作干部会议;同年11月,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开会讨论剧院“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和剧院演出的思想艺术性”。1964年1月29日,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又举行会议讨论苏联电影创作问题;2月15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苏共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5月15—16日,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一年多来,苏共中央多次召开重要会议,就意识形态工作做出了很多部署,总的思路就是要通过讲党性、讲原则,使“共产主义阵地得到巩固”。在具体的工作中,各种意识形态机构则是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各种不良的倾向,并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比如,1964年8月24日,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就判定国家新闻保密局扣押《新世界》上拟发表卡岳林(В.Каверин)的文章《白色的斑点》的结论成立。理由是“文章中包含有很多富有争议的、不正确的结论和评价。”[9] 比如说认为法捷耶夫撰写《青年近卫军》第二版时是昧着自己的良心和意愿的,等等。
总体上看,赫鲁晓夫时期还是以“解冻”为主,虽然在1957年和1962年以后两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控制,但总共只有不到3年的时间。这与斯大林时期和列宁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突出特点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重视不仅表现在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的表态,还在于经常性的会议讨论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实践行动。经常召开政治局主席团会议专题讨论意识形态工作,还曾就意识形态工作召开过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自己曾多次尝试要处理好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其主政期间曾多次与知识分子会面,并数次就意识形态工作发表自己个人的见解和观点。比如1957年5月13日举行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作家的见面会;同年5月19日又举行了同作家、雕塑家、作曲家、画家的见面会;1960年7月16日,接见了知识界代表;1962年12月17日会见了文艺工作者;1963年3月7—8日,会见文艺工作者,等等。
第二,在机构设置上,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党组织的结构进行了大的调整,但意识形态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削弱。1962年12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改组州、边疆区、自治共和国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作出了决议,规定在新成立的州、边疆区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里通常都要“设四个书记,一个主管思想部门,一个为党政监察主席,另两个则主管相应的工作部门。”[10] 1962年,将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科学和教育部、苏共中央文化部合并而成意识形态委员会。“苏共中央科学、高等教育和学校部,苏共中央俄联邦科学、学校和文化部于1962年12月20日取消,它们的职能被转到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和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工业党委意识形态部。”[11] 表面上看,这是对意识形态工作不重视的标志,因为是将三个独立的机构合并成一个新的机构,这个新机构履行以前三个部门的职能;实际上,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设置一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专门机构,集中进行工作。越是到执政后期,赫鲁晓夫越是想方设法加强意识形态工作。1963年4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意识形态工作专门通过决议,“组织改革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文化问题”[12]。
第三,意识形态工作从总体上为政治服务。无论是“解冻”还是控制,意识形态工作上所采取的一系列针对性措施都是为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服务。再仔细分析,“松”与“紧”,都与苏联国际国内政治密切相连,与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上需要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的时候,就是放松控制,苏联的创作知识分子就会随之创作出很多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对历史的反思与揭示来影响舆论、煽动民众的情绪,为政治上的进一步动作做好铺垫。比如在1956年苏共20大、1961年苏共22大召开之前,苏联文艺界都涌现出一批“重磅炸弹”式的文艺作品。而在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不利的苗头时,赫鲁晓夫则会适时强化控制,比如1957年波匈事件刚结束不久、赫鲁晓夫又面临所谓的“反党集团”,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论战时,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都普遍收紧。1962年,赫鲁晓夫之所以会同意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刊登反斯大林主义的作品被看作是化解内部政治矛盾积聚的一种手段。”[13]
第四,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与“解冻”相适应,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彻底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残酷镇压、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的极端做法,但碰到了难题,尤其是需要减缓“解冻”的步伐、扭转方向的时候,赫鲁晓夫同样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斯大林时期的某些色彩。“赫鲁晓夫本人未能从过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还在其治下就开始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新的压制。”[14] (P147)比如说在处理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格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上,同样使用了斯大林时期阶级斗争型的处理方式,组织各种作家、组织苏联社会各界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申讨与强烈谴责。再有就是通过行政手段、使用党的文件的形式对一些具体的工作进行裁决,1957年9月9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星火〉杂志内容的严重缺点》的决议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从总体上看,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是敢于承认历史上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一些错误,并及时修正。1958年5月28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对联共(布)1948年对上述歌剧的决议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是更加人性化。即使有对帕斯捷尔纳克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的威胁,但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改变了以前完全否决、甚至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的极端做法。还有一方面,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在赫鲁晓夫时期只是一个个案,对各种异己思想,赫鲁晓夫很少采取这样的方法,整体上还是以教育为主。对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说对撰写了反斯大林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1956年)的杜金采夫、对诗人叶甫图申科、对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等,尽管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并不喜欢其作品,但没有采取对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相对极端的政策,而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希望通过党性原则对他们进行改造。
第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赫鲁晓夫个人诸如“主观主义”、“唯意识论”的缺点尤其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与在苏共20大闭幕前夕作长达四个小时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秘密报告类似,赫鲁晓夫在一些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没有更多考虑工作的延续性,缺乏深思熟虑,也没有一种统筹的安排。他力排众议,不经过集体研究或者是不顾集体的研究而自作主张。比如在苏联社会引起巨大影响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作《焦尔金游地府》,就是赫鲁晓夫自行决定发表的。1962年,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某些主席团成员持保留态度,但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做出小说在《新世界》杂志上全文发表的决定。尤其是对文化艺术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虽然赫鲁晓夫承认自己“并不内行”,但还是经常在公开讲话中发表一些自己个人的看法,对一些作品及其作者发表一些评价。
三、赫鲁晓夫对“解冻”的矛盾心态
“控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时期长期担任苏共高级领导人,对禁锢与控制的弊端非常了解,也曾设想彻底放松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放开言论自由,但对此又顾虑重重。一方面,赫鲁晓夫认为“解冻”对打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从文学的角度入手,为他在政治上的大规模行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解冻”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局面难以控制。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不过没有点他的名。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能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利的发展。我们要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15] (P138)在某种程度上,赫鲁晓夫甚至对“解冻”抱有一种胆怯心理。他说,“当然,我们也要对艺术家放松控制,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有些胆怯。我国人民对我们所处的状况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你想抓痒处,但你的妈妈不让你抓’。”[16] (P138)所以,感觉“解冻”引起局势的变化难以驾驭时,赫鲁晓夫就要实行回收政策,开始加强控制。“两松两紧”,清楚地表明了赫鲁晓夫是在试探“解冻”需要把握的度。
基于上述疑虑,即使在“解冻”时期,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也不乏强有力的控制。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就是其中典型代表。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管理局主席团、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政治局和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管理局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参会的作家们一致通过决议,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7] 1958年10月29日召开的苏联共青团全会上,身为团第一书记的谢米恰斯内扬言要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让他成为真正的移民,让他到自己所谓的资本主义天堂去”[18]。在巨大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信,恳请“不要对我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19]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草案提出要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不过这个决议草案在1959年2月2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没有获得通过。在其他年份,就是在1956年召开苏共20大前后和1961年召开苏共22大前后,即使赫鲁晓夫深入、全面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解冻”成为主题词,苏共相关意识形态机构也时刻没有放松警惕,而是同样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对各种他们认为对苏联党和国家有害的作品和人物进行行政上的控制,很多优秀的作品被无情地封杀。比如苏共20大召开以后,1956年10月4日,苏联文化部向苏共中央报告,认为电影《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中》不适合放映,原因是“没有展现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战争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和重要转折点,影片中取而代之地变成了部分的、零散的情节。”[20] 再如,苏共22大召开前夕,1961年3月1日,苏共中央文化部同创作了《生存与命运》的作者格罗斯曼进行了谈话,对其告诫“今后作为文学家和公民的资格完全取决于他自己。”[21]
总体上看,赫鲁晓夫的“解冻”有一个前提和底线,那就是不触及到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统治地位。俄罗斯有学者认为,“解冻”只是一种表象,是一种虚幻。“在意识形态的宽容下,尽管一些杂志得以出版发行,尽管以前绝对禁止的话题变得‘半公开化’了,但总体上看,是一个虚幻的氛围,满是蒙蔽性的谎言和表面现象。”[22]
四、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的效果和影响
从列宁缔造一个全新的苏维埃制度,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成熟,确保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的统领地位一直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方法就是加强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在此以前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赫鲁晓夫所进行的“解冻”带有开拓的性质,产生了一些正面效果:
(一)总体上维护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虽然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有起伏变化,但总体上还是维护了马列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据俄罗斯学者研究,“大众传媒总体上还是处于党的宣传机构的直接领导之下,除了纯粹的官方观点和为‘所有群众’称赞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23] 在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系上,强调把同西方国家的缓和与意识形态斗争分开,“不能把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必须保持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而不是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24] (P204)
(二)新闻出版自由大为增加。一大批30年代大清洗中受害者恢复了名誉,报纸上开始触及过去属于“禁区”的问题,对工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重大问题,报纸上也逐步接触和揭露。
(三)解放了思想、繁荣了苏联文艺。与斯大林时期一潭死水不同,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呈现繁荣、多样化的特征。文艺界的全国代表大会频繁召开,第二次与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分别于1954年12月15—25日和1959年5月召开。第二次全苏作曲家代表会议于1957年召开;1958年2月28日—3月4日全苏电影工作者会议召开;1961年6月12—14日召开了全苏科学工作者会议;全苏史学家会议于1962年召开。平反了过去的一些冤假错案,给一些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最典型的就是1958年恢复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名誉与地位,并使其成为一名苏共党员。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决议,比如1954年9月《关于改进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措施》,11月《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中所犯的错误》的决议等等,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出了一批在苏联(俄罗斯)文艺界声名显赫的大师,比如说索尔仁尼琴、阿勃拉莫夫等等。出现了一批在读者中享有较高威望的新期刊,一些老的刊物也恢复了勃勃生机。电影、戏剧、音乐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也造成了相当多的负面影响,不仅在苏联产生了思想混乱,而且对国际共运界都产生了连锁反应,出现一些苏共领导难以预料的复杂局面。
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影响巨大。赫鲁晓夫提出的很多理论,比如说“两全”理论(全民党、全民国家),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三和理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等等理论和苏共赖以依存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勃列日涅夫时期总体上给予继承,或者说没有超过赫鲁晓夫时期的水平。
另一方面是对苏联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直接导致了“60年代人”现象。“60年代人”并不是指出生在60年代的人,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那些出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参加过卫国战争(大部分还攻入了德国),战后参加工作或进入大学学习,在斯大林时期成长起来并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部分人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同时又耳闻目睹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各种政治运动,参加卫国战争时又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赫鲁晓夫的“解冻”使他们的信念发生动摇,出现迷失和彷徨,继而产生怀疑与不满,甚至变成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者。被称之为“改革与新思维”之父的雅科夫列夫就是“60年代人”的典型代表,他便推出这样的结论:“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在于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25] (P131)
再有,就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分裂。赫鲁晓夫的“解冻”,虽然解放了思想,解除了斯大林模式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但也事实上在苏共内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中国党与苏联党大论战到最后关系完全破裂,西方国家共产党与苏共关系也出现裂缝,这些都与“解冻”不无关系。
总之,与斯大林时期相比,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在实践中有了很大的进步。苏联的氛围更加宽松、艺术文化生活更加繁荣。但同时,赫鲁晓夫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控制做法,行政措施仍然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手段。由于草率行事、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欠周全的考虑,给苏联带来了很难消除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1953—1956年间,为第一次松动,开始“解冻”;1957年开始加强控制;1958—1962年间,再次松动,再次出现“解冻”;1962年12月到1964年,又再次加强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