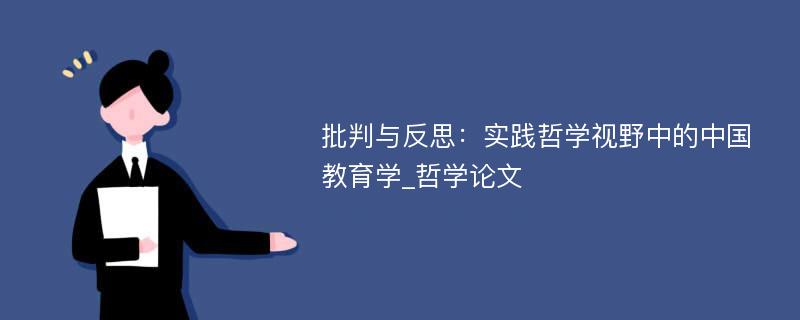
批判与反思:实践哲学视野中的中国教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教育学在诞生之初就与实践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教育学的康德,教育哲学的奠基人罗森克兰茨,“科学教育学”之父赫尔巴特,开创了教育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杜威,都明确地把实践哲学作为建构各自教育学的阿基米德支点。遗憾的是,日后的教育学却迷津于教育学的科学化而遗忘了这一传统。而忘掉了自身即是目的的教育实践亦即生命的实践,忘掉了以教育实践为目的和旨归教育学之源——实践哲学,很难想象不致今日迷惘的教育学和教育学的迷惘。然于今实践哲学的复兴和繁荣[1],又为教育学走出迷惘之境提供了阿里阿德涅之线。英国的卡尔教授,国内的进生宏教授都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和分析。不过,如果不能就实践哲学复兴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命运加以观照,并作一批判性的省思,那么,一般性的探讨实践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就值得怀疑。因此,为在实践哲学复兴背景中的当代中国教育学寻找新的价值坐标理应成为我们每一个热爱教育学的人的神圣使命。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并无学科化意义上的教育学,有的只是教育思想。中国教育学的出现,乃是中国文化承受西方乃至扶桑文化冲击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从学科角度讲,中国教育学一开始就因没有自己生发的土壤而不得不以学科的形式进行“移植”或“被教育学化”。[2](P202)时至今日,中国的教育学仍然行走在“被教育学化”的充满痛苦与艰辛求学之路上。因此西方教育学因遗忘实践而走入迷惘之境的现象和命运必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下中国教育学的现象和命运。那么,面对因遗忘实践而致的迷惘窘境,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即是中国教育学如要走出迷惘是否要走“被实践哲学化”的道路?否!因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特质即是人生实践。遗憾的是,面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急于想“现代化”的我们不加分别的把小孩连同洗澡水一块泼掉了。诚然,古之内圣难以开出现代之新外王,但新文化也不是脱离历史语境而突然出现的,否则就会出现如同说从宙斯脑袋中生出了的雅典娜,而这个宙斯又不存在一样的悖论。因此,中国的教育学要走出迷惘并且立于现实语境开口说中国话,就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回归、解读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和教育学思想。当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教育学思想不应也不可能被忽视,但在引进的同时也应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现实问题出发进行一番“再语境化”,由此才能真正避免他者的独白、主体的失语,真正改变“进口教育学”“千人一面”的窘状。新教育学的问世,也真正为期不远了。
一、以实践而不是以知识为内核的中国哲学
从词源学的角度讲,哲学,即Philosophy,源出于希腊语,意为爱智之学。但几乎与“哲学”这个词出现的同时,希腊人就把“智慧”与“普遍的知识”混淆在一起,从而西方人解释哲学为求知识的学问。而“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3](P488)亦可以说,与游离生活的西方知识论哲学相异,中国哲学不是为知而求知,以知为内核的;而是为人生行为而求知,以人生行为、人生在世的价值和意义为研究对象的实践论哲学。诚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可归结为四点:性之善恶,孟荀所讨论;仁义之内外,告孟所讨论;理欲关系,宋儒所讨论;知行分合,明儒所讨论。而中国先哲所以要关注讨论这些问题,是“以为各人自己修养人格或施行人格教育的应用,目的并不是离开了人生,翻腾这些理论当玩意儿。”[3](P489)而是关注人生实践,探究如何养成健全的人格。此可以《大学》与《论语》的“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己以安人”概括之;也可以荀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概括之。国学大师陈寅恪则以其深沉的历史眼光注意到:“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西泰也。但中国古人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其长处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短处是于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4](P17)这里,陈寅恪以更为简明精到的语言扼要指出了作为中国哲学特质的实践哲学之所指——政治学和实践伦理学以及实践哲学之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同时又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实践哲学因缺乏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等西方实践哲学所特有的“理论是最高的实践”“理性和它的对象是统一的”“对思想之思想”的命题和思想而有所短。罗光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后也认为,把握内在的生命实践成为有德之人是中国哲学的特质。如其所说,“中国古代哲学在《易经》和《书经》里,以‘人’为中心,人代表万有,连接天和地。人的价值在于心灵的生活,这种心灵的生活,综合天地万物的意义和价值。古希腊哲学,研究宇宙万物的本体,以静为研究的观点;中国古代哲学讲论人生,以动为研究的观点。由静的观点去研究,所以方法为逻辑的分析法;以动的观点去研究,所走的途径为实际的体验和言行合一的实践。儒家的哲学就在于发展成全的生命,而成一个成全的人。”[5](P23)这一切充分说明,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不是外在的知识,而是实践,进一步说,是自身即是目的实践活动,眼光向内,反求诸己,成就生命的实践活动。
从具体微观处着眼,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处处充盈着实践的精神。在古代先哲看来,宇宙和人生是一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创造洪流,人类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完成生命,开启智慧,通达自由的境界。而确定的知识只会割裂复杂、变动的世界,消解自由、健进的人生。故而,道德理论的核心不是对普遍道德规则的论证以及对道德规则的掌握,而是如何在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中通过切身的体究践履获致德性之知,培养有德之人。所以,如石元康先生所言,儒家所论述的道德,“不是以律则的形式出现。我们所碰到的,大部分是描述德性的字汇以及教人如何去做到道德实践的工夫”。《论语》和《孟子》中所提到的一些概念,例如:智、仁、勇、义、信、孝、恕,以及《中庸》中的诚,都不是规则性概念。这些概念是形容人的德性的概念。如果这些概念是规则的话,则我们应该可以替它们下定义,用一种很确定的理论语言,将它们的意思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每次当弟子问孔子什么是“仁”,什么是“孝”等概念的意思时,他总是因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说法。譬如樊迟问“仁”,孔子就说“爱人”,子张问“仁”,孔子就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刚、毅、木、讷近仁”。[6](P115-116)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不一而足。这表明,实践之知或德性之知不是写在书本上可以传授的死的知识规则,而是寓于复杂变动的生活中的活的智慧。人惟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且在现实的人生实践中启用自己的理智,对事情作出灵活具体的对待,才能真切地体察把握这种真知与德性。
其实,不仅儒家哲学是如此,在道家看来,“道”也由实践而来。就连淡泊宁静的老子也欣赏“上士闻道勤而行之”。[7]而庄子笔下的庖丁则以朴实的语言告诉我们,解牛的行为也是一种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而要达道成为游刃有余的“道庖”,靠的是长期切身实践中的不断亲证体悟,而不是对解牛之理的空谈冥想,静观默照。
有意思的是,为了解决如何在具体的情况下深切地体认善和实际追求善的问题,中国的先哲提出了一个与亚里士多德的“适我之中道”的概念相类似的“中行”“中庸”“中和”的概念,作为一种道德美德和根本的思维方式。如古人所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不可否认,对中和等概念的解释可谓丰富繁多,但根本之意是说,善不是实体性的,不能通过机械的推论得之;善是关系性的,它唯有在我对实践生活的全身心投入中,在对实践的条件、背景作出综合具体的分析思考中,才能呈现、展示自身。
对先哲的这种实践精神,可用以下两句诗总结概括之:“书册埋头何时了,不如抛却去寻春”;“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说到极端处即如陆九渊的“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不过,今人却远离了实践的智慧,滑向了知识的探求:美德即知识,德性之知即对道德原则的掌握,道德实践即道德原则的应用,从而犯了王阳明所批评的知行分离的弊病。
二、中国传统的“教育学”:实践之学
以上宏观与微观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是教人以“知如何行”(to know how to do),即如何修养或获得德性,养成健全的人格,而不是教人以纯粹求知(to do),对各种概念范畴的进行辨析和掌握,培养理念人。或者说,中国的哲学是为学与做人的同一,理论与德性的同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和探究如何成人做人的“教育学”(不是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学)生来就不分你我,二者都以“人生实践”为内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质言之,教育学虽为“学”,但本质上却是实践的,贴近生活的,教育即为学,学即为教育,因此不妨将中国古代的教育学称之为“实践教育学”。(石中英博士将其称为“人生教育学”,不过在我们看来,“实践教育学”的命名更为直接和贴切,因为人生是行动的人生、实践的人生)。原宪的“学以为人,教以为己”,“学而不行谓之病”;孔子的“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学而优则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等等都是其真实的写照。如严元章所言,“由人之初开始,教育与人生同步,并且与人生同归。因此,教育原来便是‘人生教育’,教育总该是‘人生教育’。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年代,教育离开人生就不对;离得越远就错得越多,错得越多就错得越大。”“历代的教育家大多数都是人生教育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中国古代教育学延续着一条“人生教育思想的路线”。[8](P289)
具体说来,在中国古代的教育文献中,一般都把教育学的本质归结为使人向善的实践,或者是反躬内向,反己体认的“为己”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学是一致的)。《孟子》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一语,《说文解字》释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段玉裁注:“育,不从子而从倒子者,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可以说“使之善”是中国教育(学)的“一贯之道”。由于德性是智慧,不可言谈:“道可道,非常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善不可能像知识那样可通过耳提面命式的传授获得,而只能靠自己在身体力行中仔细寻思与体认成就。因此本在传道的传统教育是强调人的自觉、主动、体悟等的无为之教、“无言之教”。故此《论语》篇说:“为仁由己,岂有人乎。”《学记》篇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孟子》篇说:“善以养人。”朱熹注:“养谓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朱熹晚年与学生讨论什么是教育与教学时说:“事事都用你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动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子语类》)又说:“读书要自家道理浃洽透彻。”杜元凯云:“优而柔之,使自得之;厌而袄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焕然冰释,恰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朱子语类》)“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加培养转深沉。”人格的感化与学问的培养的精神是一致的,立教在宽,使人向善,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所理解、实践的教育,所以《大学》的开篇会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何谓至善?“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是。[5](P171)
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后七十年。微观教育研究(如其所说的“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和宏观教育研究(如其所说的教育政治学)将进入教育学研究领域,成为教育学的重要课题。现在看来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其实,结合我们所述的实践哲学,这相当于指中国古代的内圣外王之学,亦是“实践之学”,所以实践哲学理应是重新解读原典和未来两种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之一。对此我们期望着。
三、问题与祈盼:让教育学说中国话
不管我们每一个热爱中国教育学的人的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并无近代西方学科化意义上的教育学,(石中英博士对中国“学”字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可参见其博士论文《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学也多数是舶来品。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如陈寅恪所言,因为我们的传统过于强调道德的教化,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学术的科学观;另一方面是因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教育近现代化,从根本上源于近代以来国势衰微,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打击的惨痛历史,由此而形成的激进主义的教育学思潮对传统的“矫枉过正”,使得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强烈的“西化立场”。因此,于我们而言,尽管“实践哲学”与“教育学”的内在亲缘关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古而有之,但由于缺乏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最高实践”,康德的“理论理性”,海德格尔的“操心”或“思”等为知而知的思想,以及因我们想急于脱困而致的数典忘祖,使得我们非但没能改造创生出康德与赫尔巴特式的“实践教育学”,反而沦落于靠进口谋生的窘迫之中。自然,于今西方教育学的迷惘同时也是所谓有名无实的中国教育学的迷惘。
面对一同处于迷惘之境的中西教育学,“我们”何去何从?“我们”该如何让中国的教育学真正说中国话?该如何“使欧美的教育学者以不懂中文为憾事”?
(一)对以传统自居,充当救世角色的批判
如果承认我们对西方的实践哲学因过于科学化而引致的教育学迷惘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注重生命的中国实践哲学和教育学思想可起到过于科学化的西方实践哲学和教育学走出迷惘的解毒剂的作用。也许国人常常津津乐道的,“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后发表的宣言中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道德智慧。”“行孔子之道的时代,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代,最令人神往的时代。”[5](P21-25)这样的话语是对上述论说的有力佐证。的确,伴随着20世纪之走向终结,欧洲列强的世界性控制已经被逐步打破,而全球性危机的出现则加速了一个霸权独白时代的终结,对话合作时代的开启(抑或实践时代的开启,因为如前所述,实践即是对话)犹如1993年《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中所宣告的,“世界一直在从数千年之久的‘独白时代’缓慢而有痛苦的走进‘对话时代’。仅仅在一百来年以前,每一种宗教,后来是意识形态——即每一种文化,还在倾向于十分肯定,只有自己才拥有完全的‘对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该如何生活的解释。’后来,通过从西方开始而最终在全世界日益扩展的一系列理解方面的革命——历史主义、实用主义、认知社会学、语言分析和诠释的认识革命论,先是单个思想家,而后甚至越来越多的中下层人士也开始意识到,关于事物意义的一切说明都具有有限性。”[9](P139-140)于是,面对有限,常常是眯缝着眼地,目光不清地,教育学开始从西方独白时代的相对黑暗中走出来,走进了对话的曙光之中。而实践哲学则为中西哲学和教育学的对话准备了前提,提供了可能。因为尽管中西哲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自有着一套独特的概念与范畴系统,但在行、实践的概念上却是双方共有的,因此以行、实践为核心展开的实践哲学是中西哲学真正的交切点(张汝伦,1995)。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认为东方学的时代已经开启,而以救世者的角色自居,企图为走入迷惘的西方教育学开出一剂救治的良方。殊不知,这种无视时代发展的救世心态只会让我们重染过去的“夜郎症”。毕竟,中国传统实践哲学和教育学思想得以产生和展开的语境,今天已不复存在,而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也经历了一段历史的发展。今天的西方是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基于自己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现实问题,有选择地汲取中国的实践智慧和教育智慧,不是饥不择食地“崇古”。对此,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明白,“西方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精神相悖”,而现在正在“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表达一种与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但又补充云,在“愈益接近两重文化的交汇点”,愈应“保留已证明已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10]即是说,尽管西方正在把目光转向代表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亦即实践伦理学,但其根本的立足点仍自我“岿然不动”,伦理审美感性系统在普里高津等西方人试图构建的“新天人合一论”中,只是三维中的一维。(另两维为科学之维和宗教之维)所以一当冷静的我们立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理应仔细体味并大声朗诵:“留恋过去而放弃眼前的奋斗,逃避现实而追恋‘埃及的肉锅’,永远是弱者的表现。强者的逻辑只能是探索,进取,超越。”(俞吾金)西方对中国实践智慧和教育智慧的择取之目的是超越过去,走向未来,不是复归于过去。由之,我们惟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以当下的教育实践为血肉文本,超越前人,才能真正参与、实现与西方实践哲学和教育学的平等对话,从而使欧美的教育学者真正以不通中文为恨。否则,拘泥于过去,死抱住古人不放,表面看来,我们的教育学的确是摆脱了西方教育学独白的束缚,然深入下去却发现,我们不自觉中又落入中国传统教育学独白的藩篱,与倡导开放、对话的全球化时代精神相悖。由此,“被教育学”化的窘境依然未变,中国的教育学仍不能真正昭著于世界。其实,就实践及实践哲学本身而言,创造、进取是其本然之意,没有创造也就没有实践和实践哲学,当然也就没有教育学。因此实践的主体抑或教育学的主体永远是当下的具有创造性的我们,而不是古人。换言之,是我们在写在说新教育学,不是古人借我们之手与口重写重说教育学。否则,我们写的越多,说的越多,本真的新教育学离我们就越远。
(二)对“客观”但非“同情”的教育学史的批判
要让教育学说中国话,惟有通过不断的行动和创造。然而,这并不是说要摈弃历史或传统的教育学。试问,如果没有前人辛勤地劳作,我们的新教育学之新又从何而来?我们活在历史中。但真正的历史与传统不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在我们之外的客观反思对象,真正的历史与传统是有我们参与的生命本身的历史。历史决定了我们,我们也在参与历史与历史的频繁应对中选择、保存和发展、创造了传统。由此,历史与传统的理解本质上即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或实践,不是无主体的客观记述。诚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所认为的,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对象,是这一个和那一个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现实性和历史理解的现实性。因此,我把所需的这种历史叫做‘影响史’。理解本质上是一个影响史的过程。”[11](P71)我们的教育之“思”亦在返回、沉入教育学史,与教育事件相照面并让其自身展示、言说的过程中,传达、理解,创造着教育学史。
通贯中西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提出的“了解同情说”亦即“中国式的解释学”,比上述“非客观的历史观”说的更为简洁明了:“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而“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造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5](P86-87)然理解历史,创造传统,不能仅仅局限于与本民族传统的神交契合,还须与外来文化相交相接,如此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修正自己。故而他又言: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是两千多年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教育交流史所昭示的真理。[5](P87)同时也只有从这种从本体论的“同情”“理解”之角度,而不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无我的“客观”“我思”之角度解读教育学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才能深切地体认陈元晖先生所说的新教育学之新在对传统的系统总结,在把教育思想还原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全面观照,而不在片言只语地引证。诚其所说:“新教育学应该是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著作,它不是‘进口教育学’,而是自己的2000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外国朋友或学者们的琢磨是不能忽视的,但忽视自己积累达2000年(以孔子的《论语》算起)之久的宝贵遗产,是不能编出新教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学理论遗产的继承,不是以引用古人的片言只语为标志,应该是一种系统的总结。当我看到某一本教科书中引用了几句中国古人的名言,来证实外国某一种理论时常有喧宾夺主之感。”[12](P94)
逝者如斯,屈指算来,陈元晖先生所说的这番话已过去整整10个年头了。期间,整天标榜“知道”的我们倒是出版了不少的“新教育学”,但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实现了陈先生之“最迫切的希望”即“能写出一本新教育学,在今后70年的头十年,即在本世纪之内,出版发行。不是教科书,而是学术性的著作”的迫切希望,我们不得而知。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传统的或历史的教育学研究只是对过去教育学知识的客观叙述和简单梳证,只是衬托我们“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外在粉饰,他们没有对古人之“同情”,他们眼里只有“知识”二字,然知识与同情不可同日而语,无同情便无真正的教育学史。如此这般,新教育学的产生似乎遥遥无期了,何时走出越说越迷惘的迷惘怪圈也成了一个未知数。
实践和实践哲学告诉我们:教育学对它们的疏略或遗忘或许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教育学遗忘了本体的实践和实践哲学也就造成了“人”的缺席,尤其是“治”教育学的个体的缺席,进而招致新教育学的难产与教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实践是一种关系,一种体现我为世界而生,世界因我而在的本质关系,我在世界中,不是旁观者,所以研究实践的实践哲学和教育学不是一种排斥了丰富的整全的我的抽象的、纯粹的“我思”,而是“我”在与生活世界的交往中表达“我”对其中的教育事情的体验和态度,亦即“我在”。如此,从实践哲学和教育学文本中我们所读到的不是“对象的人”“死的知识”,而是有血有肉的、本源性的、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人。孔子、苏格拉底的“话”不多且亘古久远,但却被世代承继,为世人诉说,就是因为透过他们的著作可发现这有他们这个人的存在。教育学是育人之学,更应有人在,有“我在”,无人无我无以成学。人们常说“教育学是人学”,这句话起码包含着三层意思,教育学是写人的,教育学是写给人看的(这里的人不仅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教育学是人写的。然而这最后一点却长期被许多教育研究者所忽视。实际上,写教育学之人的人格折射出他所写的教育学的广度与深度,决定着他的教育学能否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能否给人格以教化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约而言之,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学。正如实践哲学家费希特所说的,“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个人们可以随意放弃或接受的死用具,反之一个哲学体系因占有这个哲学体系的人的精神而充满生气。一个天性萎缩的或是由于精神的奴役、博学的奢侈与虚荣弄得萎缩了和歪曲了的性格,将永远不能把自己提高到观念论的程度”。[13](P5)明了了“文如其人”,学问是学者的人格,那么,如果写教育学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缺乏生命的活力,实践的态度,完整的心灵和对生活的深刻的体验的知性主体,很难想象他所写的教育学会是灌注着人的生命气息与性灵,震撼着人的心灵与濡化着人的人格的名副其实的育人学。反之,教育学便因有了教育学者的人格和德性而有了个性化的特色,具有德性自证的品格。这样的教育学理论,当然也就不同于一般教科书的那种形态,而成为一种具有内在价值,富有个性特色的创作。因此教育学要摆脱陈元晖先生所批评的“千人一面”“大同小异”的局面,要成为世界瞩目的新教育学,就必须具有知行合一,生命与学术合一的实践态度和境界:要教人做人,自己必先作一个人,不能自己眼光向外或躲入由教育学知识堆积而成的教育学阁楼,反要求读其书的人向内转,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约而言之,“知行合一”的学者出现之时,便是说中国话的新教育学诞生之时。
总之,不追问和反思教育学研究中“人的问题”,新教育学的产生必将遥遥无期。我们的时代呼唤大师,呼唤教育家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呼唤知行合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真学者的出现。
标签:哲学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教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新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