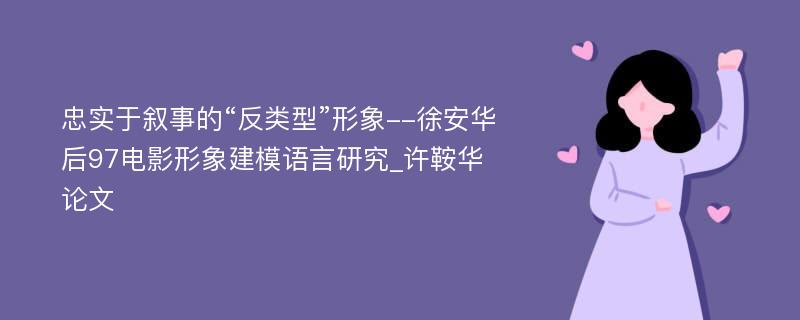
忠于叙事的“反类型化”影像——许鞍华“后九七”电影影像造型语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像论文,造型论文,类型论文,语言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回归十年之后,许鞍华导演作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推出,再次证实了给许鞍华电影影像风格贴上一个标签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难度来自于在许鞍华28年的电影导演生涯中,作品题材、类型各异,影像风格也丰富多元,涉及悬疑片、鬼怪喜剧片、犯罪惊悚片、武侠片、平民悲喜片、纪录片、社会政治/战争片等等。此外,这种独特、不媚俗、含蓄、质朴的影像语言,在香港商业电影制片体制下,在艺术/商业、作者/类型的矛盾对立中,艰难地取得平衡,探索出了不同于徐克、杜琪峰、王家卫等香港导演的独特表达风格,成为香港电影多元化表达和书写的重要一员。
在目前对许鞍华导演作品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对许鞍华作品的影像风格进行系统的分析,基本上停留在具体单个作品的视听语言分析上。一种普遍的共识是:把许鞍华电影的影像造型语言归结为“朴实无华”,“在她悠长的电影创作生涯里,尽管不乏规模宏大或耗费不菲的制作(两集《书剑恩仇录》、《倾城之恋》、《半生缘》、《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但很有趣的是,这些电影却差不多完全缺乏一般同类大制作的豪华瑰丽或闪烁生辉(《倾城之恋》勉强算是沾到一点边)”。① 对这种“朴实”影像的态度分为两大阵营:赞同者充分肯定许鞍华的创作诚意和不随波逐流的创作态度,对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给予了高度评价;反对者则“嗤之以鼻”,认为其作品游离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早期作品的商业艺术双丰收是因为恰逢香港电影新浪潮其时,新浪潮高潮之后,许鞍华的创作状态不够稳定,无法对剧本进行创造性改编,对一些题材的把握上呈现失控等。
对于许鞍华的电影影像语言的探讨和对其电影的研究一样,给予过高或过低的评价都会面对很多的质疑,这一方面是因为许鞍华分散、多元的创作路线并没有像徐克、杜琪峰或是刘伟强、王晶等人的作品那样,依托香港的武侠动作平台,有鲜明的影像风格化标记,虽然被誉为艺术导演,但是在整体的影像风格上并不如关锦鹏、王家卫等有着鲜明的风格特征,没有累积风格形成品牌,这也是许鞍华面临尴尬和困境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成功的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对许鞍华的影像风格必须进行动态、系列的梳理和分析,在不断变化的商业制作环境中进行考量,才更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用“质朴”、“现实主义色彩”和“写实主义风格”来概括许鞍华导演电影的影像风格显然有流于简单和片面之嫌,虽然每部作品都自成一格,但是如果从影像创作构思和风格完整性表达的角度出发,会发现许鞍华对影片影像风格独有的认知和贯穿的脉络。
从新浪潮发轫之初创造性地用现代电影语言讲述故事和表达剧中人的情绪,强调影片中的各种商业类型元素,到“后九七”反其道而行之,不刻意放大题材上的商业类型元素,强调用电影语言传递出导演的情绪、视点和观点,成就了许鞍华作品在香港众多商业片中独特的艺术气质。
许鞍华在后期的电影创作中,提供了人们传统或者惯性以外的另一种看事物的角度,也许正因为此,和她合作过的诸多著名摄影师如李屏宾(《上海假期》、《女人四十》、《半生缘》)和关本良(《男人四十》、《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都呈现出了与以前作品不同的风格特征。
商业类型元素+反类型化的影像表达策略,逐渐成为了许鞍华导演在创作当中自觉地去遵守和执行的艺术观念,是许鞍华在商业和艺术的钢丝上行走探索出来的一种特殊平衡状态:从表面上看是和目前商业电影强调的背道而驰,对观众的传统审美心理发出了挑战;实质上是让观众更加注意导演所流露出来的价值判断和观念表达,它使得商业电影类型的表达更加丰富和多元。
这种架构同时也使得许鞍华很难到达商业和艺术的两极,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思辨,但未必就不是许鞍华在30年的创作生涯中寻找到的最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也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样的评论:“许鞍华导演一向擅拍奇情故事,利用惊险刺激的题材,经常拍出佳句,直接处理文艺题材,反而暴露出许鞍华对含蓄、微妙、复杂的内心层面,未能把握。”②
商业类型片的“反类型化”的影像创作思维和风格,为我们辩证地理解商业类型片的影像风格和创作有着重要意义,在目前国内电影的“大片”和“作者电影”的两极格局下,那些不断迎合商业类型影像的创作思维和模式在接受着挑战,促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对许鞍华电影进行审视,寻找到影像的多元表达以及其和商业的平衡点。
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反类型化”影像语言分析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同时也是许鞍华50岁时推出的。对导演本人和研究者而言,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问世,也让我们看到了许鞍华导演在影像上更为清晰的追求。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融入了黑色幽默、悲剧、文艺、荒诞等诸多类型特征,导演让现代电影观众接受一个50岁女人的生活、恋情,同时接受导演希望给这部影片赋予的荒诞和思辨意味,这在目前的商业体制下,无异于一次巨大的冒险。
从该影片的整体风格上来看,对这样一个平民悲喜剧题材,没有采用像在90年代初期拍摄的同类型题材《女人四十》时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来建构影像,讲述平民市井小人物,反而追求一反写实基调,用一种反类型化的表现主义表达方式,营造了荒诞、充满拼贴感的影像空间,在当下众多现实题材的商业类型片中也是独树一帜。
这种“反类型化”的影像处理在色彩使用和超现实主义的镜头处理上尤为突出。由于影片的人物和整体叙事充满了拼贴感,在色彩和色调上如果不从整体的风格来把握,处理得过于细碎反而不容易帮助叙事和铺垫情绪。在影片中,上海和鞍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色调,上海是拼贴和年轻化的丰富色彩基调,鞍山则是纯粹和苍凉的色彩基调。从情绪段落而言,宽宽来到上海时,所有的人物身上都有着一种明亮而又温暖的光线,叙事充满喜剧色彩;姨妈发现宽宽失踪后,光线的风格随之改变成冷色调;宽宽找到后,姨妈送宽宽上火车,这种温暖的光影便又出现;姨妈认为自己上当,与潘知常感情破碎后,整体的色彩色调急转直下。
关于本片光线的创作意图和构思,笔者和该影片上海段落的摄影关本良先生做了沟通:关本良把影片的前半部分的灯光处理得比较柔和温暖,只是背景有些阴暗的部分,柔和的灯光会使姨妈不会显得很老,让观众忽视姨妈的年龄。在具体布光时用了比较多的柔光布和反射光,因为房子不算很大,柔光使人有一种平滑感,而背景又要有一些明暗的变化,使人和背景要分离出来,同时也不能让背景影响到人物。所以每次都要把打在人物脸上的光挡掉,再处理背景。到了后面随着剧情的发展,才使用了一些比较硬的光源,做出脸部的衰老和皱纹。
在色彩的细节方面,从姨妈一出场手里拿的和年龄不搭调的黄绿色的伞到房间里出现的粉色窗帘,甚至导演还用被宽宽打开电视机中的声音对这种色彩进行强调,“今年夏季的流行色调以黄色为主,至于粉红色……”;下雨天周润发打着的是一把粉红色的伞;两人唱戏时男女戏服的混穿,姨妈唱戏,潘知常照相时数码相机和古代戏服产生的间离感、杂糅感和虚幻感;姨妈穿着自己织的红色毛线泳衣游泳,被救的人说“怎么搞得,来例假还下水”的荒诞色彩;种种与姨妈年龄不匹配的颜色在摄影师关本良的画面中显得丰富而有趣味。
关于本片的色彩处理方面,关本良先生表示:在拍摄的时候已经有了后期色彩的想法在里面,现在采用数码拍摄,完全可以采用数码调光对局部甚至是某一个颜色进行处理,如影片一开始姨妈出现时打的那把绿色的伞,群众演员的服装色彩也很丰富,这是美术道具之前就准备好的服装和道具,但是在拍摄时,还是故意把姨妈和伞的颜色进行了处理,把伞的颜色跳出来,把别的颜色压下来。
在超现实主义的镜头处理上,影片中两次出现的圆月给所有人留下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回味空间,更是投射了许鞍华导演在所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似乎代表着“姨妈”的梦想,在灵魂深处给姨妈以安慰,又似乎代表了一种希望,照亮了姨妈的脸庞,还是代表了一种来来往往的轮回力量,让人向往,又映衬感伤。这个超现实主义的意象镜头把观众从剧情中拉出,充满了思辨的力量,画面语言充满了多义性和开放性,也使得影片形成了强烈的心理节奏。
其实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让我们想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虽然是一部写实风格的影片,但同样也采用了一些非常规的表现手法。在男主人公韩三明和女主人公沈红寻找爱人的过程中,天空中有飞碟划过,地面上的一座废旧的雕塑突然像火箭一样飞上天空。故事结尾处,苍凉的歌声中远处有人在三峡高处、两座高楼之间独走钢丝。有趣的是,这部片子的摄影师也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鞍山部分的摄影师余力为。在与笔者的沟通过程中,他表示:关于月亮的构思,原剧本里已经存在,但是许鞍华导演对这个镜头非常重视,她确定要一个特别大的月亮,而且要求摄影师在对月光的处理上要和现实中的月亮处理区别开来,余力为在灯光上加了滤色片,最后导演选中了一个略带粉色的光源感觉,为了方便光线的处理和控制,余力为和剧组成员在摄影棚中搭置了医院和鞍山家中的场景,利用人举着灯行进模拟了光线进入的感觉,同时利用黑旗遮放光线;为了方便特效的制作,在窗户后面放了一个蓝背景,方便后期进行扣像。
关于本片色彩的创作意图和构思,关本良先生表示他对于本片色彩的理解:最初跟许导讨论这部电影的画面风格时,许导提出了她心爱的西班牙导演艾慕度华(Pedro Almodovar,内地翻译为阿尔莫多瓦)的作品。“姨妈”跟艾氏早年的电影不约而同都是充满了黑色幽默,对现实的荒谬做出了讽刺,笑中有泪。艾氏的作品喜欢用强烈的甚至是夸张的色彩来衬托情绪的起落和立体的人性。我跟导演讨论过后,总觉得“姨妈”这部片所发生的地点是上海,而上海本身的色彩并没有很强烈,如果强要把这些色彩加到我们的布景上,可能反而会引起观众的不认同而难以投入,也对现实外景场地造成极大的限制。为了达到某种荒谬感又同时不离弃真实的环境,我们最后选取了以“不协调”这个方向来定位,不协调的颜色,不协调的背景。其实宏观地看,不协调就是当今中国大城市的普遍基调,到处都正拆毁与未建成之间,旧的来不及送走,新的还未完全追得上。就像姨妈这位曾经有理想有文化修养的过气知青,她与生活的环境和周遭的人伦格格不入、互不协调,这些不协调成为了她每天生活本身的种种笑话,笑话背后却是伤痕累累。“姨妈”电影画面上也刻意营造了这种不协调,跳跃的颜色出现在演员的衣饰乃至道具上,有时背景也突然会出现某些耀眼或杂乱的色块,各种新旧、贫富、整洁或市井杂乱的背景都随时出现在角色的生活后面。在混合光源的映照下,累积着他们每天的生活经历,每个有特质的个体最后被磨蚀殆尽,直至像姨妈回东北之后一片淡蓝和苍白。
从关本良的回复中可以旁证,许鞍华所设想的阿尔莫多瓦的影像风格其实就是对生活写实影像风格的一次反类型化处理,就如同阿尔莫多瓦对自己影片风格的分析:“我叙述的故事越是虚构或越是非理性,我就越争取使其更为贴近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像的非类型化处理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具有戏剧的张力,如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影像建构方式。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影像的缺陷更多地来自于叙事。由于时间限制,许鞍华不得不忍痛删去一些姨妈与宽宽、潘知常的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姨妈和上海这个大城市的沟通实在太少。如果姨妈生活中更多一点现代大都市的交融,姨妈与这个城市的隔离感和戏剧张力则会增加,各种元素共存的拼贴感和荒诞意味则会更加强烈。从视觉的直观感受上也是如此。姨妈的生活基本上没有留下大城市的烙印,因为不曾共舞过,所以很难理解城市表面的浮华对她的诱惑,而她欲望/理想的破灭的痛苦也缺乏了力量。这种既与现代生活共呼吸,又只能处在边缘的尴尬位置,是很难通过新旧建筑共存的城市空镜头来感知的。
二、从“新浪潮”到“后现代”
如果说,80至90年代导演为了取得更好的票房成绩,把心思都放在拍摄和延长壮观的场面,希望找到新鲜和惊人的东西,可以打动午夜场观众(首映效果的风向标),徐克、许鞍华等电影人对现代电影语言的建构开辟了香港电影的一片新天地,那么90年代后期,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旗手之一,许鞍华导演已经在香港电影传统镜头语言和影像风格上渐行渐远。
现代化的影像类型语言探索针对不同的商业类型,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电影语言,镜头、剪辑、场面调度依据一定的程式,迎合了大多数观众的心理,用直观、形象、生动的影像刺激观众,反映当下的主流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说,许鞍华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玉观音》、《幽灵人间》、《千言万语》、《半生缘》中影像造型语言的探索,就是对传统的类型化、模式化语言解构的过程,也是因此形成了许鞍华渐趋平实和厚重的影像语言风格。
1997年《半生缘》的推出,似乎是许鞍华在电影语言使用上的一个分水岭。之前1996年拍摄的有关电影行业题材的影片《阿金》,还在充分地调用各种商业类型的元素。在镜头语言的处理上,追求商业效果的追逐与打斗场面的设计,把剧组拍摄武侠片时的场面也处理成武侠片镜头语言,但是该片并没有把握好商业和艺术的平衡,许鞍华在商业类型上的强调,使得一个关注女性题材的影片,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男性气质,观众在打斗场面的刺激下,偏离了对女性的关注和思考。
相较而言,《半生缘》的素材可以拍成非常奇情曲折、紧张刺激而又感人肺腑的商业通俗传奇,但是导演和摄影打破了人们对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固有印象,特意选择在上海的冬天拍摄,几乎成为旧上海标志的色彩艳丽的旗袍消失不见。影片很少使用鲜艳饱和的色彩,人物的服装总是褐、灰为主的暗色系列。在祝鸿才强暴小姨子顾曼桢的这场戏中,摄影机缓缓上升,透过螺旋形楼梯的一根根栏杆,用全景镜头去俯拍站立于楼梯下方的顾曼璐,使她形似一只笼中鸟,祝鸿才对顾曼桢实施强暴的过程,并没有运用影像进行强调,只是远远地透过窗户看到两个搏斗的人影。前景画面风吹过树枝,树影晃动,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妙,也和影片中精心营造的一种冷漠的氛围和视点融为一体。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与《女人四十》相比较,在视听语言的反类型探索上风格化更趋明显。而同是鬼片的《幽灵人间》相较于许鞍华早期的作品《撞到正》、《疯劫》而言,也呈现了非常明显的反类型特征:《疯劫》和《撞到正》的成功,是许鞍华成功找到了类型元素之间的交叉点。《疯劫》里没有鬼,但许鞍华却成功地借鉴了恐怖悬疑片的类型,大量使用特写强调感官化的画面视觉,如双尸案的血腥和残暴、解剖尸体时刀子切腹的特写镜头等,让一场三角恋充满另一种极端神秘的气氛。《撞到正》则成功运用了喜剧片和鬼片的类型交叉,以乡野传统为依据,从一个粤剧戏班中展开,影像造型语言上成功强化了中国特有的戏剧元素和舞台效果,但是在运用上显得较为凌乱,红衣女鬼,问米婆,顽皮的丫鬟幽灵,最后的高潮戏“武松打虎”,奇特而逼真,虽然带着一点恐怖的鬼魅,但总体上还是洋溢着市井的生活和搞笑气息。虽然黄岳泰以拍摄动作片而闻名,但是《幽灵人间》在其内在气质上更像是一部艺术作品,那些我们认为可以制造恐怖的人物近景和特写多用俯拍和仰拍制造变形、冷色调、暗调子营造恐怖氛围,动态光源造成光影动荡,强调恐怖血腥氛围等传统手段,在这部作品中并没有过分的强调,整体影像精致,大部分色调以暖色调为主。
《千言万语》与《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相比,从整体风格的设计和具体镜头语言的使用,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虽然同时具备惊险、奇情的样式,同样投入了许鞍华对社会弱势群体/边缘人物生存状况与命运的关注和同情,但是《千言万语》以纪实风格的电影语言描绘了香港艇户居民、水上新娘和无证妈妈们的悲剧生活和命运,电视镜头画面在每次游行中的出现,与电影镜头的连贯组接,也为作品的表现增添了一份历史感和叙事张力,尤其是黑白照片的定格穿插,更是起到了情节的预示作用,在造型与美术上,创造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形式风格,具有思辨的力量。《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则注重惊险样式的类型片影像特性,注重造型/叙事上的兴奋点和对视觉/心理上的冲击力。《胡越的故事》既有激烈火爆的搏杀,又有细致感人的爱情,蛇团诡计、黑帮阴谋、逼良为娼、拐卖女人的内幕和异国情调,使本片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投奔怒海》在影像上同样也强调了这种商业类型,如特准介川这个外国人在滂沱的雨夜参观最残酷的“新经济区”,枪毙、血尸、自杀、爆炸、卖淫、儿童集体赤裸等画面,在摄影的镜头下显得触目惊心。
90年代中后期,许鞍华更加注重从商业类型和故事中发现和强调其人文价值和审美情趣,《玉观音》、《男人四十》、《半生缘》的镜头运用充满了这种反商业类型的特征。《玉观音》没有采用传统香港动作片中的多景别、多角度,而用大量特写镜头等语言来强调残酷、血腥、刺激的动作场面。当笔者就此段落的动作镜头设计和摄影师关本良沟通时,他回复说:这样拍是许鞍华导演的意图,因为她觉得以前所有的武打片的动作都是很清楚很利落的,虽然很好看,但并不是真实的打斗,导演希望拍出混乱一点的感觉,像一种纪录片的效果,摄影机处于抓到又抓不到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许鞍华导演是自觉地在创作中对传统的商业类型进行解构,也是对被香港特有的动作影像类型训练出来的观众观影经验的挑战。《男人四十》本来也可以处理成第三者的通俗剧,但是在许鞍华的处理下,加入了古诗词等中国文化的元素和长江的画面,使影片透露出一种特有的诗情和文化意蕴。
三、影像的“反类型化”策略
1、忠于故事和人物
在许鞍华导演的作品中,影像语言强调和固有的商业类型语言的不同,并不代表着过分强调影像造型语言的作用,这种“反类型化”的语言需要为叙事和人物服务,因此导演和摄影师对于人物的情感有着准确的理解和把握,通过精心捕捉画面的深度意义为人物和叙事“锦上添花”。
在与摄影师关本良先生的沟通过程中,他特别强调:之所以没有采用像阿尔莫多瓦作品中那种特别夸张的色彩,是他觉得上海本身的颜色没有西班牙的颜色那么饱和,如灯光和建筑物的颜色,没有西班牙那样丰富,而且《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人物的性格也没有那么夸张。
关于采用不协调这种风格的色彩设计,关本良先生强调:“不协调”会给人不讨好的感觉,因为这种和一般的艺术电影有分别,一般的追求和谐统一的氛围和色调,这种处理可能会给人感觉比较混乱。但是即便如此,在这种色彩的不协调风格的实现当中也不是没有原则的。整体上讲,开始的时候色调比较偏暖,因为当时的天气很热,没有空调。进入秋天和冬天,随着剧情的发展和姨妈心理情绪的变化,这种色调就会有相应的变化。在景别的使用上,很多时候使用中景,基本上是导演的意图,许鞍华认为这部戏不是一部在镜头上很夸张的电影,而是想让演员带这个戏,像阿尔莫多瓦早期的电影一样。
其实,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某些颜色的饱和度完全可以通过后期调色来进行适当的夸张和强调,但许鞍华小心翼翼地在观众对姨妈的认同和色彩的“隐喻”意义中寻找平衡,没有把色彩和影像凌驾于故事之上。这种忠实于故事的“反类型化”思维,隐藏在叙事背后的影像风格呈现,都值得引起思考。
2、隐藏的风格
许鞍华始终贯穿浓重的“家国情怀”,以悲悯情怀冷静观照世界、批判现实,其后期电影中的“反类型化”影像语言策略,其实是其创作宗旨的投射。从表面上似乎是把叙事者的作用减至最低程度:人物、背景和暗含的参照世界似乎在直接传播,而叙事者则被降至一种被动地进行观赏或记录的地位,实质上并不是刻意追求观众对某些故事特定情绪和氛围的强烈感受,而注重建立观众对导演观点的心理认同机制。
早期许鞍华的作品在视觉冲击力上被很多影评人所诟病,到了90年代中后期,她的表达手段更加含蓄和节制,“她注重拍摄前的准备工作,多于现场的临时发挥(曾几何时几乎是‘港产片’引以为傲的独家标记)、剧本结构、主题上的和视觉风格上的完整性(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多于个别场面或出境的设计和把玩”。③ 其作品多以场面调度为主,强调的是叙事上的简洁经济,而非先声夺人。很少使用特写镜头,不刻意强调视觉上的重音和冲击力。在一些情感的重场戏上,也避免过分刺激化和煽情化,力求冷静和细致。像《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姨妈与潘知常的黄昏恋、《半生缘》中顾曼桢被强暴的镜头处理等。
这种“反类型化”镜头设计隐藏在人物和叙事的背后,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化特征。而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如和她合作的黄岳泰、关本良和李屏宾,都深谙这种隐藏风格的道理。黄岳泰接受访问时曾说:“仔细想想,虽然我以拍动作片出名,但我获了那么多奖(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却都不是动作片,像《不夜城》、《幽灵人间》等等。我个人对电影的看法是,永远不强调个人风格。”而李屏宾对于怎样的摄影才是最佳摄影的答复是:“电影摄影并不一定要漂亮,最主要是能配合剧情,并加强剧情的张力,让你看得很舒服,你会完全感觉不到里面有什么摄影风格。让你看出很刻意的摄影风格就已经是失败了。”
3、画面的隐喻意义
许鞍华后期的电影作品中,擅长用空镜头和色彩来表达某种象征意义。《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坐出租车离开上海的那场戏,是许鞍华导演亲自设计的。夜幕下,姨妈乘坐的出租车汇入上海的车流,她悄悄地离开,就像车子汇入车流一样无声无息,而车子驶入上海的环形立交桥,又似乎如同姨妈从鞍山到上海再回到鞍山这样的人生隐喻。《千言万语》结尾处描述平民生活实景的长镜头,画面下方近四分之三的幅度上,是平民露天生活的场所,只有电线杆放射的微弱光芒。在画面的上端是高速公路,不断有汽车飞驰而过,现代化的生活距离他们既近又遥远,仿佛触手可及却又好像永远无法企及,许鞍华利用这个空镜头对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投去深情的一瞥。很多时候许鞍华用空镜头刻意回避在传统商业片中强调的紧张情境,选用一种含蓄的处理方法。在《男人四十》中,空镜头与中国古诗词相结合,传递出了一种特别的中国意境和诗情。
许鞍华还善于用色彩传达情感和隐喻意义,《男人四十》中张学友所饰演的男主角家中和办公室的色彩如同个人的情感世界,非常的单调,但是林嘉欣饰演的女学生身上总是穿着粉红色等色彩鲜艳的衣服。《千言万语》的结尾,人们在雨夜祭奠民主运动人士,无数烛光被虔诚地点燃,映红了整个路面,而雨伞和人们的身后,却依旧是暗蓝色的泥泞,意寓着人生的道路依然充满艰难。
四、结语
许鞍华题材的商业类型特征和“反类型化”影像处理的策略,在巨大的商业压力下,在电影中出现了或多或少举棋不定、艺术和商业两边都不靠的妥协。有影评人说《千言万语》是“拒绝好好讲故事,关心底层大众,充满草根风味,却不以普通大众为观众对象”;《玉观音》中动作打斗场景的设计也被一些人误认为“许鞍华处理这种电影类型的陌生”。《幽灵人间》虽然作为近年来香港最卖座的灵异惊悚片,造就了许鞍华继《投奔怒海》之后的商业成功,但《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并没有理想的票房,从某种角度而言,也证明了许鞍华这种策略的商业困境。在近来一些国产大片带来电影视觉消费的环境下,年轻人快餐式的电影消费观念和思维模式给许鞍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成为许鞍华电影特色和风格的对细节镜头的重视大于对戏剧高潮的经营;含蓄表达情感,在关键处点到为止,很少给观众情绪宣泄的时刻,是否适应内地观众的观影心理,不仅是许鞍华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在新的时期,所有电影工作者着力研究的新课题。许鞍华和内地合作拍摄的《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两部影片的票房不力,也深刻地反映了香港电影人在回归之后,融入内地电影产业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如何把握内地观众的审美需求,适应内地市场的运行规律,满足内地观众的审美要求,需要对这种“反类型化”的影像语言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探索出一条电影多元化发展之路。
注释:
①舒琪《许鞍华与她的电影》,http://www.yingxiang.org/shukei/index.php? paged=3 shukei。
②石琪《香港电影新浪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52页。
③同①。
标签:许鞍华论文; 电影论文; 疯劫论文;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论文; 电影类型论文; 胡越的故事论文; 玉观音论文; 半生缘论文; 男人四十论文; 千言万语论文; 投奔怒海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恐怖电影论文; 犯罪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