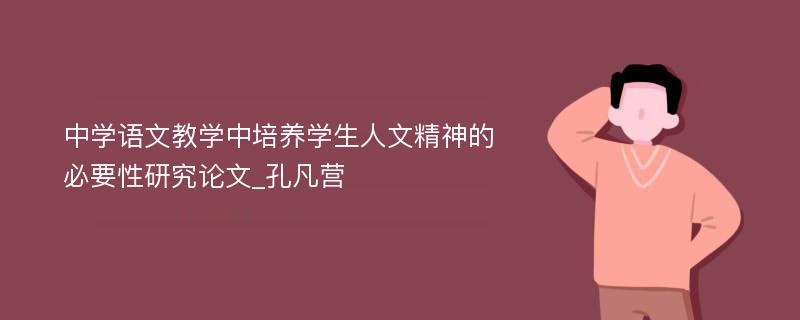
孔凡营 山东省平邑县第一中学文化路校区 273300
中图分类号:G633.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1672-6715(2018)12-105-02
近几年,国内中学语文教育屡遭诟詈,不少专家学者从指导思想到方式方法都对其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这一五十年代承袭苏联模式建立的教育体系终于面临崩溃的命运了。然而大厦将倾,痛心疾首也好,釜底抽薪也好,忌的是头脑发热,轻率发议。因为我们还要建立一套崭新的体系。在一片指责声中,有不少人认为中学语文教育最大的缺陷就是脱离时代,生活在象牙塔内,陈腐保守,不思进取,所以语文教育改革首先要从紧贴时代入手,反映最新的时代浪潮。
这是一种非常要命的误解。回顾这五十年,中学语文教育从来就不曾脱离过时代主流。相反,它的教材配备、教学设计、思想指导等甚至反映出了时代风口浪尖上的每一个微妙的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时代主流的正确性。五十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前四十年的泛精神时代和后十年的泛物质时代。泛精神的标志就是意识形态化,一切从政治出发;而泛物质,评论家郑敏有很好的阐释:“我们被告知,火车已到了‘后现代’一站。……后现代的特点是唯科技,唯财富,唯效率,唯享受。最终一‘唯’是最终的目的。……一个年轻人会高傲地告诉你人生是享受,至富者是俊杰,清寒是耻辱无能,一位中年人会委婉地宣传下海的重大意义,一位老年人会容忍地承认这是时代精神。”⑴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时代潮流,表现了民族心理的浮躁和人文精神的匮乏。而中学语文教育跟风的结果就是前四十年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而后十年则不断强化语文的工具属性,以应试为主要目的将语文教学等同技能培训。
功利地看待语文教育,语文教育便失去了它的精神内核。摩罗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序中曾经沉痛地说:“我觉得当下人们最明显的一个精神特征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依恃。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们在精神上一点依赖都没有。没有依赖也就是无赖。”⑵这一评价当然包括中学生群体,学了十多年的语文,我们却很少能在这批未来主人翁身上发现他们对世界、社会、人本身深刻的思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有着惊人相似的两面:一面是沉浸在学校一隅,为了分数名次而奋力拼争,一面是浮动于灰色心情中,为了简单浅薄的小情小感而悲欣交加。同样是十六七岁,当代学生明显缺少了五四时期的青年们深刻的理性、跳跃的激情以及宏大的气魄。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想象将来的成人世界如何的刻板和鸡零狗碎。这才是五十年中学语文教育的致命之处。也就是说,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学语文教育从来未曾独立过。长期以来它就是一个附庸,一个紧跟极端潮流的可怜小厮。我们的教育界一直都未明白中学语文教育必须要有专属自己的精神特质,而不是什么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或形而下的技能技术。
这种精神特质便是人文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自93年上海文学批评家王晓明等人开始人文精神大讨论起⑶,这一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humanism)的词语便不断被定义着。教育界亦有人撰文论述,但或语焉不详或界限太广。我以为人文精神必须是立足于人本身的一种思考,且带有终极意义。那种把国家民族政权都一股脑儿放进去的做法只能导致人文精神这一概念的消解。李政涛曾提出“有灵魂的教育”,他将之解释为: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类永恒的终极价值:智慧、美、真、公正、自由、希望和爱,以及建立与此有关的信仰,真正的教育理应成为负载人类终极关怀的有信仰的教育,它的使命是给予并塑造学生的终极价值,使他们成为有灵魂有信仰的人,而不只是热爱学习和具有特长的准职业者。⑷蔡元培先生亦曰:“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即认为人必须超出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即从小我成为本体世界之大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和人格的发展与完善。⑸这些都是对人文精神的较好阐述。
从根子上把握人的一些基本精神,我们的语文教育才会真诚、纯粹,我们的学生才会学会彻底地思考一些东西。人类一些美好的本性才不致迷失在时代的逆流中。很难想象,一个从小接受人类良知教育的人会轻易地迫害无辜或迷失于物欲世界。语文教育更应是美好记忆的传输,它的核心便是人文精神。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早在五四时期便已明确提出的需求,我们五十年的语文教育却没有多大反映;相反,倒是文革以及近几年的物欲潮流从另一意义提醒我们人文精神缺失的严重后果。站在这一个世纪的台阶上,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中国的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意识到:该是呼唤人文精神复归的时候了。语文教育工作者尤其要带着忧患意识身体力行。
2000年秋季在全国推广的语文新教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文学作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量的加大对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与相应的审美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长久以来,语文课本被等同于政治普及读物,学生得不到美的享受,自然不感兴趣。而新教材强调选文的作品属性,淡化其应用性、政策阐释性。像全套书中文学作品约占60%,其中高二全是文学作品。第三册甚至一口气选录了32首古今中外的诗歌。学生第一次正式有了文学欣赏的权利,而教师也第一次正式有了从文学角度讲解课文的权利。”⑹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了解析人文精神的最好途径。
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人文精神的最佳载体。它的形象性使它可以摆脱理论传输的僵硬,教师完全可以把人文精神当作一种感受甚至下意识逐次渗透给学生。如《将进酒》,何必硬要剖析什么是豪放,什么是主题,教师充满激情的一读,学生们就能感觉到人类自由精神的高蹈不顾。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齐声诵读声中,低眉顺眼,胁肩谄笑的人格障碍定将烟消云散。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又使其意味深长。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雷雨》中周朴园或许令人憎恶,或许也令人同情,人性的压抑、扭曲、张扬、蜕变在这一形象上纠葛纷扰,所以又何必定型为一个类别呢。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一面是天使,一面是撒旦,善恶交织,也许这才是人性的复杂之处。文学作品还是美的标本。“智慧、真、公正、自由、希望和爱”不是概念性的东西,十几岁的孩子从来都拒绝接受居高临下的干瘪的教条灌输,我们也无法忍受一个把《西厢记》讲成封建礼教反抗史的教师。“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美的让人心神俱醉。什么是爱,什么是绝望和希望,我们的学生只有在美的境界中才能最真切地感受到。如此等等。在作品的时代,语文教育者才有更多展示人类伟大精神的机会。所以,尽管新教材的编选者止步于文学属性,并未将人文精神作为最高宗旨提出,但有心的语文教育者还是要心怀感激,牢牢把握这一新变,以人文鼓吹者的姿态积极地介入新教材的教学中。
如何利用新教材强化文学性的趋势传递人文意识呢?这牵涉到人文精神的传承问题。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精神是西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的概念,是中国近现代打开国门吸纳自由思想的结果。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人文精神?新教材中国古典作品的比重提醒我们必须对此引起注意。虽然我们可以用西式的人文精神解析中式文学(这也是近年国内古典文学批评界相当流行的一种手法),但有些东西如老庄所谓“虚静”,孔孟所谓“浩然之气”这些中国特有的概念以西式方法解释,就有隔靴搔痒之弊了。
我的意见是只要符合上文提出的反映人类终极关怀的原则,我们就可以把它归入人文精神的行列。中国古代文化包含了经世致用和精神修养两方面内容。前者也即儒家所谓的“外王”。“儒家强调文艺的政教功能,强调文艺的功利目的,从而给文艺以很高的地位,甚至把它和礼、刑、政相提并论,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⑺,这是政治史的内容,有些学者将之与国家民族的兴亡联系起来,亦归入人文精神,就有些勉强了。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我以为,“精神修养”这一内容才具有我们所谓的人文意义。《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庄子•逍遥游》:“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五灯会元卷一•佛祖》:“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在人的精神心性方面,儒道禅三家都寻求自我的提高,所不同的只是,儒家追求人格的完满,道家追求人格的自由,而禅宗则讲究人格的消解,在顿悟中达到个人与宇宙的交融。应该说,这三家学说综合影响了古代文人的人格形成,他们在精神上并不只是儒家的嫡系,而往往出入儒学,游乎道禅。
这样的认识对应至中学语文教学,我们便有了广阔的话语背景和充足的文化底气。如上《前赤壁赋》末一段:“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盛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我们就不会把它简单地批判为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相反,它里面有庄子“齐物论”的影子,苏轼相当聪明地利用道家思想自我消解了人生焦虑感,达到了平和圆融的境界。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这种出入世俗的人生态度对于事务缠身忧心忡忡的现代人来说是否有所启发呢。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庄玄禅正是在这个一定意义上可以陶治、培育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境界。它可以教人们去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适,与活泼流动盎然生意的大自然打成一片,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活的意趣。它可以替代宗教来作为心灵创伤、生活苦难的某种慰安和抚慰。”⑻我想,当代中学生精神上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关奋斗拼搏的激励,过分追求,也是人格病态的一种表现。自我调和,自我平衡,这在剑拔弩张的竞争时代里更为可贵。缓释现代焦虑,提高生存质量,这就是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功用。
如果说中国古典人文精神是个体的,自我的,那么基于西方人本主义的现代人文精神则是群体的,他性的。因为它观照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戳,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尔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⑼所以,现代人文精神追求的不是“自了”,而是从自我需求出发的群体生存质量的提高。这种需求已经超越了中国古典人文精神模糊社会的模糊理念的层次,而成为了一种权利,并上升至规则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现代人文精神支配的社会人人都可以要求提高生存的质量,并请求制度的维护。
我的最大感触是,人类文明不可能在一节语文课内传授给学生,但我们的教师却可以通过激发自身的文化底蕴尽可能多地传递,跬步之功,其莫大焉。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⑾,讲的是心对物的能动作用。而我们的语文教师在登文章之山,观作品之海时,亦可以以胸中所积指点江山,导引百川,纵横捭阖间,全方位地向学生展示人类精神财富,而人文精神也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清代诗论家叶燮认为诗人必须具备“才、胆、识、力”这四项素质,其中“识为体,而才为用”,“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⑿,这是对创作者的要求,但对于语文教师——文学作品的鉴赏者来说也同样适用。从纷繁复杂的作品中理出人类精神的普遍规律,并作出深刻评价,没有超越常人的识见力无异于天方夜谭。《屈原列传》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三闾大夫怀沙自沉的结局。很多教师都从屈原该不该自杀这一角度导引学生分析其人格构成。但如果我们能联系整部文学史观察,就会发现选择自戕之路以了愁怨的中国古代文人少之又少。历史上除了屈原、李贽、徐渭等有限的几个,大部分文人即使再潦倒再困厄,也都会存活下去。什么原因呢?我想应该是儒道互补的文化心态(前文已经论述)调和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使其降至不威胁个体生存的程度。而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以来,“诗人之死”却成为了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线。顾城、海子、戈麦、昌耀纷纷以主动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语境中,理性、心性、理想、真理之类的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消隐,代之而起的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变或游戏规则的彻底解体:消解、平面、颠覆、边缘……人们曾经依持‘理性’、‘启蒙’而张扬‘人道主义’,而如今,在‘后乌托邦’的场景中,反理性、反启蒙、反人道主义者终于迎来了‘理性的终结’和‘人的终结’(福柯语)。于是‘物道主义’正在取代‘人道主义’”,“当诗不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灵魂的唤醒,或诗背离了直面苦难并拒绝苦难,而只以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柔甜的耳畔私语或无所追求的粗野放纵”时,当“在物质的消费主义怂恿中,在精神彻底搁浅时”,诗人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自杀行为。⒀这样深入思索后,我们就可观察到正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文化心态。当今中国知识界是否还能用宠辱不惊的传统文化心态解决现代困惑?我们的民族在迷惘中该走向何方?显然,这是一个比屈原该不该自杀更能让学生获益良多的问题,也许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的学生也正迷失在时代的多义性里。很多时候,语文教师扮演的应该是一个带领学生步入人文精神深处的向导的角色,而他最大的倚靠,便是卓越识见。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风格,或激情或稳健或纵横驰骋或一脉延伸,多姿多彩,符合艺术个性化的特征。而只要将人文精神成功地传递给学生,那么它就是成功的授课艺术。当然,授课艺术是人文精神传递的保证,在这最后一环上,我们不可大意,还需有一定的原则。如在新教材的文学作品处理上,我们始终要将之作动态的处理。也就是说,教材中的每一篇作品在课堂教学进行过程中不是单一绝对的,而是开放的体系,需要大量的课外材料的补充。新教材提出的课题教育模式就体现了这一精神。教师可根据所上课文确立一个课题,如上文所举《包身工》个案就是先确立有关人的生存权利的课题;然后以此作为一个点导引出其他有关课题的材料,把问题做深做透,真正让学生有高屋建瓴的感觉。另外,授课艺术还包括思辩原则、讨论原则、不确定原则等,这些将专文阐述,此处囿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如何让中学语文教育中失落已久的人文精神复归,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在观念杂出、变革纷仍的现代社会里保证我们的青少年人格精神的完善健康,这是关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试从人文精神的原则内涵以及教师的素质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粗浅之论,权作引玉之用。真心希望我们语文界更多的专家学者一齐来出谋划策,使人文精神的复归早日成为现实。
注释
[1]郑敏:《诗与后现代》,《文艺争鸣》1993年3期,9页。
[2]孔庆东、摩罗、余杰等:《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代序),《审视中学语文教育》,13页,汕头大学出版社。
[3]参见《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编,文汇出版社。
[4]李政涛:《没有灵魂的教育》,《方法》1998年12期。
[5]转引自《人文精神寻踪》,高瑞泉、袁进、张汝伦、李天纲,《读书》1994年4期
论文作者:孔凡营
论文发表刊物:《基础教育课程》2018年12月2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2/26
标签:人文精神论文; 精神论文; 这一论文; 语文教育论文; 人类论文; 文学作品论文; 时代论文; 《基础教育课程》2018年12月24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