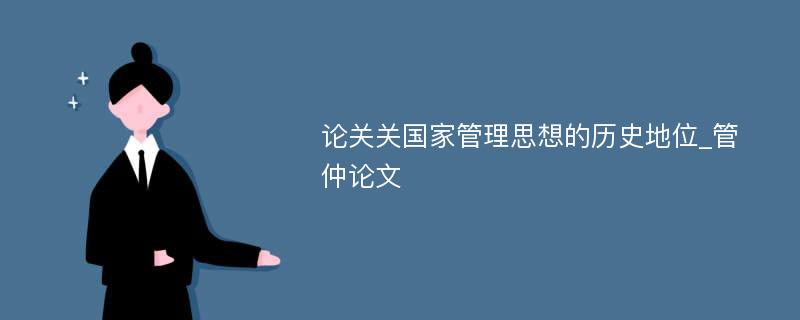
《管子》国家管理思想的历史地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思想论文,地位论文,国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一般认为从礼治开始,经过法治,然后到汉代有了比较成熟的“德主刑辅”这样一个过程。汉代的“德主刑辅”影响是深远的。而事实上,春秋初期的管仲提出并实践的礼法并重,是从礼治到法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更是“德主刑辅”的基本源头。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私有制,有了国家,相应地产生了国家管理问题。而对于国家的管理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先人们曾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用于国家管理的政治工具是“礼”。“礼”最初是被用来祈福祛灾的,在商代的时候,人们在鬼神面前还表现得诚惶诚恐。到了周代,人们忽然发现了鬼神并不是万能的,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鬼神是左右不了的,在人类社会当中,人的力量不可忽视。于是,人们把用来祈祷鬼神降福祛灾的“礼”借了过来,赋予了极其丰富的伦理内容,运用到国家管理方面。在宗法统治的社会条件下,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取得的成效是令人满意的。由于礼治强调严格的等级性和浓郁的教化性,所以,从社会道德的伦理教化方面来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礼治只能用于原始的宗法统治环境。因此,在早期的国家礼治时代,礼的内容极其丰富,礼的主体就是一个伦理问题,人的社会行为差不多都要用礼来衡量,所谓“制礼作乐”是当时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西周时期的“制礼作乐”,大约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家“立法”。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整个社会进入了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礼崩乐块”已经成为社会现实,“制礼作乐”很难继续成为国家管理的主体。但是,春秋时期还没有人把礼治置之度外,春秋五霸个个都在情愿或不情愿地高举着维护周天子统治地位的旗帜。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追求的“霸”就是周天子之臣,天下诸侯之长。到了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的序幕一拉开,礼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周天子的意志成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幌子,周王朝的宗法秩序乱了。礼治不行了,用什么办法来代替呢?这是战国时期诸子学派百家争鸣的焦点。[1]这一时期出现的齐国稷下学宫里的学者们几乎都在为这一问题积极探索。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观点,比如,儒家主张“仁政”,认为“仁者无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法令为治之本”;道有甚至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等等。最后的结果是,法家胜利了,秦孝公运用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秦王赢政随后采用韩非的法治理论,统一了中国。但是,韩非的法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刑罚意义上的治国理论,苛刑严法虽然奏效迅速,由于忽视了人的思想管理,把人当作了工具,因此,持久力不长,秦王朝很快就灭亡了。
汉代的帝王们认真总结和借鉴了先人们的探索成果,在汉武帝时期初步确立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管理体系,这就是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德主刑辅”。从此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国古代的国家管理思想在大的思路上没有出现新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从礼治到法治,再到德主刑辅,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演化过程。对于礼治的选择,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即使对于鬼神的信仰也是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演化来的。战国后期对于刑罚意义上的法治的选择,同样也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韩非的话说:“儒者以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则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秦国选择法治的办法统一中国,实际上是“快刀斩乱麻”。显然,礼治也好,法治也好,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都是偏于一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国家机器复杂程度的提高,对于国家的管理都很难有普遍的使用价值。汉代的“德主刑辅”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普遍使用价值,仔细分析一下,显然也不是简单的总结利用,其源头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源头的所有是明确的,这就是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提出的礼、法并重。明代赵用贤在《管子书序》中这样说:“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周公之法,实际上指的是礼治之法;管仲对周公之法的变革,《管子》书中的记载叫做“修旧法”,实际上就是在尊重原有礼治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崭新的法治管理体系。而且,这套法治管理体系当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就属于原来的礼治范畴。[2]对于这一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管仲在国家管理过程中提出并实践了礼、法并重的思想。现代的学者们一般认为,《管子》书中保存了管仲关于国家管理思想的精华,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管仲这一思想的基本轮廓。
首先,《管子》非常注重对于礼治的加强。重视礼治是当时国家管理的传统观念,《管子》对此进行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在《牧民》篇中,他把礼、义、廉、耻比做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在首位,义、廉、耻同样也属于今天的道德范畴。在《管子》当中,礼是人的社会行为的规范和标准。但在国家管理过程中推行礼治必须要有坚强的经济后盾,“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的基本生存生活条件失去了保障,礼同样是没有办法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他把礼用作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标准,一方面对于维护齐国内部的社会秩序本来就是题中之意;另一方面,当时齐国的治国目标是称霸,这就必须要在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中强调一个秩序问题,否则,就难以实现称霸诸侯,拱卫王室的基本目标。齐国不仅自己要强化礼治问题,而且在天下诸侯当中还要带头推行礼治,《左传·僖公七年》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于是“齐侯修礼于诸侯”。由此,结合齐国称霸诸侯过程中的实践来看,齐国对礼的重视和加强,正是源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需要。
其次,《管子》特别重视法。《管子》中对于法的认识是空前的。比如,关于法的定义。《七法》篇说:“尺寸也,绳墨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七臣七主》篇又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禁藏》篇中又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就是治民一众的规范,从另一个角度说,法也就是人的社会行为的准则,是固定化了的程式和仪表。关于法的来源,《管子》认为,法是人的权力行为的产物,《任法》篇中说:“生法者君也。”君主有权,权力行为就会产生法。关于法的特征,《管子》认为法是至高无上的,《任法》篇中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法又具有强制规范性,《禁藏》篇中说得非常形象:“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填,冶之于金也。”法具有客观统一性,“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禁藏》)。法是一种强制性的工具,《禁藏》篇中说:“法者,……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七臣七主》篇又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从理论上讲,《管子》对于法的认识,已经和现在人们的认识基本一致了。虽然对于法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但对于法的认识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的,在先秦诸子当中是绝无仅有的。[3]
第三,强调对法与礼的协调运用。长期以来,学者们习惯把《管子》放在古代法家的行列里。事实上,《管子》是礼、法并重的主张者,在正常的国家管理过程中,法与礼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是具有强制性的,礼则只能通过社会公众舆论的力量来落实。法的作用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收到明显的成效,但如果只是强调法制的力量,忽视社会道德的作用,容易出现的结果是“刑罚繁而意不恐”,“杀戮众而心不服”(《牧民》)。如果国家的道德体系建设跟不上,国便很难成其为国,正如《权修》篇所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禁也,小礼不禁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
《管子》中的这些思想,主要来源于书中的基本哲学观点,以及他从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建立起来的比较坚定的人本观念。
第一,《管子》从意念上抛弃了意志之天,确立了自然之天的观念。认为天同地一样,是一种自然存在,“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形势》)。天也没有感情,“如地如天,何私何亲?”(《牧民》)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也,莫之能损益也。”(《乘马》)认为天有一定的自然规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管子》提出了天有则、有常、有节、有理的观点,“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形势解》)。春秋以前的天,是至高无上的,可以赏善惩恶决定人的命运,天是有意志的。《管子》从理论上对于意志之天的抛弃,从而肯定了人在把握自身过程中的作用。[4]
第二,《管子》在先秦诸子当中最早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观点。[15]《霸言》篇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对于人的管理已经与国家的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国家管理理念当中,鬼神的位置已经不是十分显眼了,并且在《牧民》篇中明确提出了“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的观点,这里的“分”,就是管理的意思,不怕无财,怕的是没有人来管理。这实际上强调的就是一个人本问题。
第三,《管子》对于人的管理提出了规范与引导相结合的观点。在《权修》篇中明确提出了“治人如治水潦”的观点。人类最早关于治水的经验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堵水是惟一的办法。后来大禹的出现,才有了疏导与堵挡相结合的治水办法。《管子》提出“治人如治水潦”,道理非常浅显,就是说,对于人的管理,一方面要进行积极的引导,另一方面要进行强制性的规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牧民》篇中才提出了著名的“刑罚不足以服人意,杀戮不足以服人心”的观点。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理论指导下,我们在《管子》书中可以见到许多关于如何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论述。
《管子》之所以能够在朴素的唯物辩证观基础上提出礼、法并重问题,关键还在于管仲本身是治国活动的直接实践者,他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治国的实践活动,这与后来的儒家、道家等的代表性论述都有所不同,在他们那里,尽管见地非常深刻,但书生意气,理论认识有余,实践经验不足。因此,《管子》的礼、法并重不仅在理论上是至高的,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问题历来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书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管仲的思想。[6]《管子》书中对于礼、法并重的观点和论述,一般被认为是管仲思想的篇目中都可以见到,而管仲所处的时代,正好是春秋初期,也就是礼欲崩而乐未坏的时候。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秦国采用法治措施治理国家则更为久远。但在《韩非子·五蠹》篇中就有了“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有之”的记载,这说明《管子》书在战国末期仍然十分流行。到汉代初期,仍然广为流传,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详哉其言之也。”汉武帝时期吸收和借鉴历史的经验,确立“德主刑辅”的国家管理办法,受到《管子》的影响应当是十分正常的。按照这样的推论,春秋初期管仲提出的礼法并重理论,应当是汉代“德主刑辅”的国家管理思想的基本源头。
那么,为什么《管子》的国家管理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当中没有被得到足够的重视呢?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是一个致命因素。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主张苛刑严法的秦王朝灭亡了,“法”治失败了。在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楚汉战争以后,汉王朝建立了。从此以后,中国历代的封建社会仍然沿用的是不同形式的宗法统治。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只不过是从奴隶制社会条件下的宗法统治过渡到了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宗法统治。《管子》的礼、法并重思想也是在宗法统治条件下产生的,如果真正按照这一理论实践下去,当时齐国的宗法统治环境也会土崩瓦解。《管子》所倡导的治国理论,并不能够适应后来的封建社会的需要,因为管仲所倡导的国家管理理论,不可能适应诸侯纷争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就是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倍受尊崇的孔子,对于管仲也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但他又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仔细分析,孔子对管仲肯定与否定的都是相对孤立的个体行为,对于管仲的治国方法如何,孔子没有说法——恐怕他也实在无法评价什么。这样来看,《管子》所提出的礼、法并重,就是中国整个宗法统治社会条件下关于国家管理的第一个不和谐音符。
当然,《管子》所强调的礼、法并重与汉代“德主刑辅”不是同一个概念,《管子》所强调的礼主要是一种道德行为规范,法则主要是一种强制性规范措施,法的概念使用也不完全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难区别于刑罚意义上的法治,[7]要害的问题在于他把礼与法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与以前的礼治时代也不同,与后来秦代的法治时代不同,与汉代的“德主刑辅”更不一样。由此,我们的基本看法是,《管子》的礼、法并重正是当时齐国能够首霸春秋的根本政治原因,也是其人本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既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法家的胜利提供了依据,更为汉代“德主刑辅”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古代国家管理史的发展链条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链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