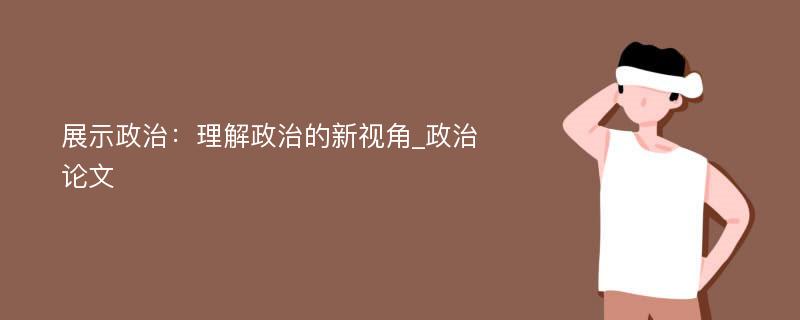
展示政治:理解政治的一种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16)02-085-(8) 如今,越来越多的展示发生在我们周围,“展示”正在成为现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然而,国内对展示的研究基本上还局限在艺术领域进行的展示设计研究,尚没有将其纳入政治学的视野。国外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展示的角度尝试探讨了展示政治,然而笔者认为展示政治不仅仅存在于博物馆等文化展览领域,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社会展示当中,可以说展示政治是无处不在的。 一、展示政治的提出 展示,英文为display,源于拉丁语的名词displico和动词displicare,主流观点普遍认为展示的概念是对展览概念的扩展和延伸。[2]“展示”的含义丰富多样,就“展”字而言,具有打开、展开和扩展等含义,而“示”字则具有能动和被动的深层含义。因此,一般认为,“展示”具有清楚地摆出或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意思[3]。展示可以视为一种壮观的陈列、展出,以其范围、细节、美观、丰富的程度等引人注目,具有广告、宣传的性质[4]。对个人而言,展示就是向大众展示自己的风貌和气质;对团体、企业而言,是对外界宣传自身,让公众了解其理念、主张、成就等[5]。展示具有阐述、解释和宣传、夸耀两种基本作用。展示的阐述作用是将隐藏或掩盖的某种观点或事物的意义主动地显示出来,传达给展示对象[6]。 相对于引人注目的展示设计而言,展示政治(politics of display)尚躲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冷清角落里,国内目前还鲜有研究,而国外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艺文展览方面对其进行探讨,研究的视域较为狭窄。 其中,国外从博物馆的公共展示入手进行政治解读的最多。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对博物馆的分析中引入了“展览政治”的概念,他从解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与权力框架入手,对博物馆与文化建构、殖民地景观几个层面展开文化政治分析,认为博物馆占有和展出物品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考量,展览物按照现有的话语系统加以结合与组构,并最后得出结论:“展览的政治意味着各博物馆让特定的文化被看见”[7];其他学者在对博物馆的分析中虽然也使用展示政治(politics of display)的概念,然而在具体的论述中也交叉使用展览(exhibit)这个词汇。Sharon Macdonald认为,所谓展览就是“对眼睛说”(speak to eyes)。他的展示政治分析理论基础就是把博物馆视为一个公共展示背景或者传播媒介(media),这个公共展示的媒介中涉及权力的展示,展示中隐含着权力分配,比如谁有权赋予特定的展示编码,在展览的组构之中有哪些程序、利益团体和谈判参与等。简言之,展览中经常包含文化、社会、政治意蕴(political implication)。比如17、18世纪的博物馆,主要作为一个科学研究服务中心,当时还没有对公众开放,它的参观者主要是一些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获得知识权威的贵族;19世纪的博物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博物馆已经对公众开放,并被设想为是国家认同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和象征;1960年开始的博物馆,由于一系列的族裔民族主义和环境运动等政治运动影响,原来作为“工业遗产”标志的科技博物馆发展为“生态博物馆”,这个时期的展览还包括了一种民主化的尝试,展览试图缩小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差距[8]。总之,当代博物馆已经发生转向,从简单地告诉公众他们所需要知道的知识和历史,到回应公众的需要的趋势转变,并有意识地嵌入一定的话语和权力关系。展览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强化,博物馆的展览鼓励与参观者的“对话”(dialogue),这在某种意义上源于当代政治互动的回应性(political resonances of interaction)[9]。 国际博览会也是一个重要的展示政治研究对象,它关涉国家的展示(nation on display)。Penelope Harvey认为,文化与技术是展示的载体,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展示是国家对昂贵的展示进行赞助的动机,大国都试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展自己的实力。因此,在国际博览会中,明显的竞争导致各国不同的展示风格,而且这种展示的重心已经不在于展示本身,既不是展示的物品,也不是展示的过程,而是人们想要和追求的模拟效果(effects of simulation)[10]。Sabrina Norlander Ellasson论述了18世纪罗马展览馆中肖像画与展览政治。他表示肖像画中角色的社会展示根据不同精英的个性而变化,而这主要取决于精英们希望外在地、形象地表现他们的社会地位[11]。 除了博物馆、展览馆这些具有强烈展览性质的载体所蕴含的政治寓意之外,展示政治还包括围绕着公共展示对象(主要是公共艺术)所引发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这种对公共艺术引发的不同公共意见中,政治体现在公民、学者、社团、政府相互之间的博弈和协商处理。这种政治往往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政治色彩,比如女权主义政治等。Michele H.Bogart论述曼哈顿的一个被称为“市民美德”的城市雕塑,由于雕塑的男主人公像使得很多妇女认为她们的性别被贬低了(demean to their sex),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争论[12]。 展示政治不仅有政府组织主导的,还有民间自发进行的。Ken Arnold认为,展览政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process of persuasion),展览体现了有关机构和组织的观点,他们通过展览来传播他们的声音,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他描述了一个医学研究所进行的一个医学史中所呈现的生育展览,其中的展览内容包括一些具有西方文化政治色彩的标语,比如“只有健康的种子才允许播种”(Only healthy seed must be sown)、“女人: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Women:your body belongs to you)等。这种政治的话题在展览中变得越来越有争议,以至于有人表示在女人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候关于谁来控制生育具有这么大的争议性[13]。 如果我们把“展示”理解为思想对话的物质表达(表现),那么展示不仅仅是反映社会历史运动的镜像,同时它也能动性地形构历史过程。不同的展示策略,可以让艺术史进行叙事重构。为了实现集体认同,德国发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传授新国家历史的公众理念的媒介,即通过艺术展示的方式进行形象表述和规训教育[14]。甚至可以说,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展示政治”建构出来的。 一言以蔽之,西方的展示政治研究多是在“展览”的意义展开的政治分析,从展示的载体而言,主要围绕着博物馆、博览会、公共艺术品等文化的公共展示而展开讨论。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下展示则是对展览的延伸,比展览具有更广泛的范围。另外就政治的传播和渗透而言,它也不局限在博物馆等浓重展览性质的展示载体、形式上面,而是扩散到各种展示的场域。因此,本文讨论的展示政治,并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文化展示的范围之内,而是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存在。所谓展示政治,简言之就是展示场域中的政治,也即公共展示之中蕴含的政治意蕴。 二、展示政治的多样面孔 在艺术层面的展示中,空间、色彩、声光等媒介都是展示设计要素。展示往往是经过装饰的,而政治时常也需要进行包装,因此展示政治往往具有多种面孔。 从展示的载体或者途径而言,展示政治具有多种寄身空间。展示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一般会通过各种标志性的符号进行表现。而符号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来说可分为两大类,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后者可进一步分为建筑符号、仪式符号、标语符号等[15]。展示政治可以借助各种符号进行展示和表征,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文本、建筑、仪式、标语等系列符号。 在文本层面,展示政治时常隐身在公共政策之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个部分,其中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的总体目的是美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等级,“放大国家形象”[16]。其实不仅仅是在文化政策领域,在其他政策中也都可能蕴含展示的色彩。比如我国诸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在表述中都会提到“服务型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从政策执行和落实的实践进行反观,会发现一些政策的展示或宣示意义远远大过其实际作用。“宣布的政策未必会有效实施,当政策的目的可能不会实现或准备不实现时,政策本身就不具有其实质功能,它只不过是某种观念、诉求的象征性表达而已”[17]。另外,从文本的角度,展示政治还可以体现在权力的诗篇之中。比如,14世纪的叙事诗《内加拉克尔塔嘎噶玛》,将印度尼西亚治国之术中王位的神圣以诗文修辞的方式形象表述:“满者伯夷的王城是太阳与月亮,无与伦比;众多以树丛环绕的采邑是日月周匝的光晕:……群岛中其他众多的岛屿是周环的王国、藩属,齐驱于陛下的跟前。”[18] 政治还会经常化身在建筑的展示当中。建筑与空间紧密相连,它既可以是一种政治载体,也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叙事方法,一种政治象征符号。空间呈现出连贯和“可读”的一组象征和信息,成为会说话的环境(talking environment)[19]。通过真实世界和表征世界的结合,物质世界变成了信息与概念,而不只是一个物体[20]。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将建筑视为是个人和社会行为的物质背景,它其实是一种社会行为[21]。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各地的财政局、国土局比民政局、林业局等办公建筑大楼富丽堂皇和气派得多,这在某种意义即是一种部门权力的彰显。另外,在每个政府机关的建筑内部结构之中,办公室最豪华肯定是部门的一把手,这种建筑空间往往折射出权力的构成格局。 仪式通过各种庄严肃穆的程序以及各种符号的装点,在经过一番公开的、集体的公共活动之后,以群情振奋的“狂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开的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展示政治载体。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地更新其自身的和统一体的情感[22],集中展现一种象征意涵。2015年5月9日,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同以往5月9日的红场阅兵式一样,它是对俄罗斯卫国战争的纪念。然而今年的红场阅兵与以往略有不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今年的阅兵式将成为俄罗斯现代历史上最为盛大的阅兵式。除了展示强大的军力之外,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的特殊背景下,胜利日阅兵式可以展示信心,鼓舞俄罗斯国内士气,争取在与西方的对峙中不落下风[23]。 标语,是指“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24],往往标示于公共场合,加之其简单明了,朗朗上口,非常符合展示“引人注目”的特性。标语形式简洁,具有良好的传播功能,因此生活中到处可以看见各种标语口号。以计生为例,宣传生育文化类的标语“晚婚晚育铺平致富路,少生优生盛开幸福花”、“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配套的计生奖励政策标语“奖励600元,幸福度晚年”;与小康社会联系的计生标语“计划生育搞得好,小康生活来得早”等等随处可见。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政府的很多中心工作都会配以大量的标语口号进行宣传,因此反过来看,很多标语之中其实蕴含了丰富的政治信息。 从展示的主体而言,不仅有国家、政府层面的展示,展示政治还存在于各种民间行为之中。政治往往被认为是有权者的游戏,相应的上层的展示政治容易引起注意,然而随着新媒体的日新月异,底层政治也越来越具有展示色彩。基层民众往往借助行为艺术,通过网络的传播来武装“弱者的武器”,从而上演一次次花样不断翻新的表演政治①。比如,2011年2月,一段由化州市同庆圩村民历时3个月自导、自拍完成的视频《同庆的故事》在网上广为传播[25]。视频中有几个典型的“展示”要素非常博人眼球:一排农民蹲在地上,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子,在地上画圈,意为“画饼充饥”;一张凳子上摆着3双碗筷,一个碗里装满泥土,一个碗里装满沙子,一个碗里装满石头,意味无地可耕后的“吃泥土”;失地村民高举饭盆,期望“天上掉饼”……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表演式抗争”[26],认为在当下社会转型期,这种艺术化的政治生活,这种严肃政治环境下的活泼政治景观越来越多,比如法官穿法袍上访、给官员送负面锦旗或带刺皮球、现代版开封府申冤等[27]。以上案例正是民间利用行为“艺术”进行的展示政治,它通过把一些权利受到侵害的现实用艺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进行戏剧化的展示,利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引发的感想让人瞬间留下深刻的印象。利用展示“广而告之”的效果,借用强大的社会舆论来倒逼当地政府纠正违法行为。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此类民间的展示政治将会越来越多。 从展示的策略而言,展示既有明示,明确地表达;也有暗示,含蓄地表达。展示政治除了一些国庆阅兵等直观地展示国力和权力之外,很多场合是一种隐喻性的展示。因为现代社会中,政治的表达往往是含蓄的、柔性的,它会借助各种符号进行表征。“隐喻不仅简化了复杂的政治,更重要的是包装了无形的政治,给予抽象问题以生命力”[28]。统治的艺术也是掩饰的艺术,甚至是欺骗的艺术[29],因此,很多我们日常所见到的“真实”可能仅仅是一种“包装真实”(packaged authentic)的镜像而已[30]。就像拉康与齐泽克所分析的,大写的真实状态(the Real),完全被一个符号的、话语的意识形态机制所任意操纵改写,形成了一个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现实”,而真实状态本身,则始终是空白的、沉默的[31]。要想真正了解展示政治,还必须在“台前”的展示形式之外,深入解剖“幕后”的政治内涵。 三、展示政治的多重内涵 以上是从展示的角度呈现了展示政治的多样面孔,接下来从政治的角度来揭示展示政治的多重内涵。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可以说政治一直伴随着人类生活,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则导致了政治的多重内涵。 首先,展示之中可以蕴含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权力关系只有通过定期的、经常的展示才能够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各国都会定期进行大型的阅兵仪式,这种阅兵式就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展示。它通过三军仪仗队和各种尖端武器设备的公开展示,让国内外充分了解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强制性权力,从而以一种潜在的武力威慑来维持既有权力格局的再生产。前述的建筑规模以及建筑结构的展示也蕴含了一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同时日常生活中开会及饭桌上的座次安排也不断地展示着既有权力关系的再生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可以说是研究展示权力的鼻祖,尽管他并没有直接提出展示政治的概念。福柯从公共景观式的惩罚消失现象入手,探讨了其背后刑罚的变迁以及微观权力变化的政治现象。他直言:“我们不能把公开处决仅仅理解为一种司法仪式。它也是一种政治仪式。即使是在小案件中,它也是属于展示权力的仪式”[32]。 其次,展示之中可以蕴含权利表达或者利益诉求。民主和宪法制度的确立明确了公民的权利,同时也规定和限制了政府权力。出版和言论自由给了公民针对公共议题进行讨论和批判的权利[33],然而在中国当下的实际中,底层的声音依然相当微弱,难以影响决策。因此,民间便产生了表演式抗争,通过艺术化的渲染,公共舆论的“围观”,来放大自己权利表达的声音。在政府层面,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提拔主要是由上级党政机关的意志决定的,而上级考察又以政绩为中心,因此各地政府领导都喜欢大上项目,建一些标志性的工程或建筑,即平时我们所说的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这种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展示,它是当地政府“政绩”的彰显,以这种标志性的、引人注目的展示来向上级政府“诉说”其政绩。 再次,展示之中可以蕴含政府形象的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可以增加政府的信任度和提升政府的影响力,它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政府形象的塑造。发展中国家经常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改善或者提升政府形象。比如当下中国国内的反腐,通过党政军各层面轰轰烈烈的反腐及密集的曝光频率,来重塑党政清正廉洁的形象。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可以说该通知就是一种形象塑造层面的展示政治。通知表示:“近期一些地区和部门又出现了违规修建楼堂馆所的现象,损害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形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强调各级党政机关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从中可以看到,党和政府期望展示的是一种“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党和政府形象。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通过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措施,来展示和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再其次,展示之中可以蕴含文化的规训。任何政治统治都离不开相应意识形态的包装和维护,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并不是纯粹空洞的东西,它有指向性,它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34]。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规训。到处可见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标语、横幅、电子屏幕等等,就是通过一种无处不在的展示来吸引公民的注意,并在日常的关注中潜移默化地实现文化规训。福柯提议,最好不要从大群体或单一性集团的意义上,不要从阶级或国家这样宏观政治的意义上来认识权力,而是从存在于社会各处的权力关系网络的微观政治意义上来认识权力。权力不仅在工厂,也在学校、监狱、医院和所有其他的组织中[35]。伴随着“微观政治”转向,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规训的展示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致。 最后,展示之中可以蕴含统治合法性的渗透。展示政治背后体现的可以是政治的任何基本要素,比如权力、权利、意识形态等等,然而就其深层次而言,自上而下层面的展示主要是为了实现统治合法性的渗透。比如,前面所述的以权利为包装的“服务型政府”形象的展示,其背后蕴含的则是政治认同和统治合法性的渗透。随着民主和法治观念的普及,统治越来越需要包装,治理也越来越需要艺术化的“治理术”对民众进行无形的“规训”。所谓治理术,就是使人将治理误认为是维护他们的自由,通过自由来显示治理,或者更简洁地说,通过自由进行治理。福柯认为:“对人的治理,首先应当考虑的不再是人的恶习,而是人的自由,考虑他们想做什么,考虑他们的利益是什么,考虑他们之所想,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这种新式的软性文化政治所蕴含的规训,恰恰是展示政治的核心。可以说展示政治就是一种新式的治理术,而这种治理术的核心其实就是实现合法性的无形灌输。 展示政治是借助一系列符号进行传播的,而正如皮尔斯所言:“只有将符号放置于具体的交际和指称背景中,我们才能把握它们的意义……也就是说,符号意义是需要在具体的意指过程中形成的”[36]。同样地,对展示政治的理解也只有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时空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其背后的表征意义。面对不同的展示对象,展示政治会有不同的传递内涵。不同的展示载体,也可以体现不同的展示政治。即便是同一展示载体,相同的展示对象,由于展示时空的不同,其所蕴含的政治意蕴也可能不尽相同。比如以各地的博物馆展示为例,在2008年之前,它们更多的是展示当地的文化遗产、地方认同。而在2008年《文物局发布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通知》执行后,原来收费的博物馆变成免费参观的地方,因此它在原来展示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展示政府重视国民文化权益、塑造服务型政府形象的政治意蕴。 现实是个万花筒,不同的组装会产生无穷的新花样。展示政治就是现实中的万花筒,展示具有多种面孔,政治具有多重内涵,二者的不同组合会产生无数的存在形式,以上对展示政治的介绍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四、展示政治的“解码” 展示政治,通过引人注目的公共展示,意在传递和灌输一种有目的性的、有选择性的政治理念或者塑造某种公众形象,是一种暗含特定政治目的“编码”。展示政治经过主观的、有选择的“编码”,在传达到受众并被受众接受之间,还需要经过受众的自行“解码”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解读”并不是简单的从文本中读取意义,而是读者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与文本进行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同意和附和,可能会产生协商或张力[37]。换言之,不同的受众,因其知识、地位、背景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其解码后所得到的信息未必一致。同时,同样的受众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经过不同的经历之后对同一展示的政治解读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展示政治在编码的时候具有特定的意指,“编码”了确定性和目的性,但“解码”后的展示效果可能是不确定的。所以,展示政治不完全是一个单向的“编码”的过程,不能只是一厢情愿地、单边主义地宣传和展览,它还必须从受众的角度考虑和研究“解码”,必须根据社会实际和受众的“需求”制定正确的策略,唯此才能减少“解码”后展示政治中的非控制因素。 展览,是以相对专业的方式陈列出来供观众“看”,它的功能主要就是提供“被看”,以“被看”的方式“诉说”或者传播信息。信息有其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属性,即直接存在的依附性。信息作为意义和符号,必须依附或嵌入在一定的载体上才能呈现。展示,不仅包含了信息的传播,还包括了信息传播的载体本身,而这个展示载体本身往往也具有实用价值。比如文化中的建筑,既有“展览”中被看的一面,同时也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场地,在被看之外,还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跟单纯的展览(博物馆)不尽相同。相应的,展示政治是嵌入或者依附在某种公共展示载体之中进行自我实现的,因此展示政治的预期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示载体本身的质量是否过硬,它的实际价值与宣传价值是否接近一致。因为很多公共展示除了“展示”意义之外,本身也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比如农家书屋,一方面它展示了政府重视农民的文化权益,并意图借此塑造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形象。但同时,农家书屋本身除了象征的展示意义之外,还具有自身的提供阅读、传递知识的自身功能。农家书屋的展示政治目的是否可以实现预期的“编码”,还需要依赖于农家书屋本身的实际价值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就目前的实际而言,农家书屋基本上沦为了一种摆设,只见屋不见人,仅仅剩下了象征性的存在意义。舍弃了展示载体本身的实用价值,而片面地追求展示意义,最终结果无异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展示政治只有实现了展示载体自身的功能与展示意义的相统一,展示政治的“解码”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编码”。 ①国内的表演政治主要在底层,而国外对表演政治的关注主要在上层,与名人文化(celebrity culture)有诸多相似之处。随着网络、电视等现代媒体的兴起,政治领导人经常要曝光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言行经常是公开的,他们经常像名人一样被置于放大镜下被观看(seen in magnifying mirror),于是管理公众人物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政治的核心,“表演政治”(performative politics)逐渐兴起。参见:Melvan Elteren(2013),Celebrity Culture,Performative Politics,and the Spectacle of "Democracy" in America[J].Urban History,36(4):263-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