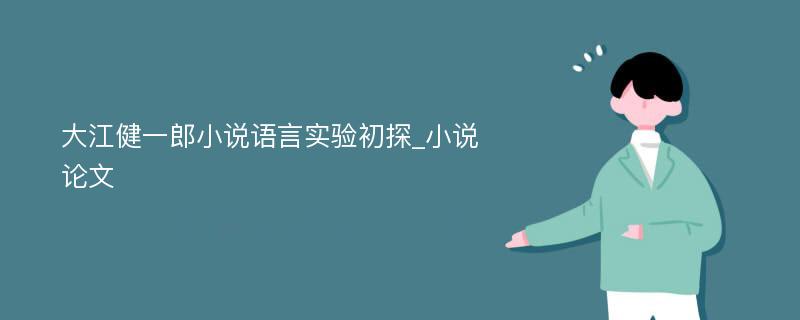
大江健三郎小说语言实验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探微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09)03-0043-06
一、引言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实践者。在日本当代文坛上,似乎没有人像大江那样对小说的文体和叙事产生如此大的兴趣。从初期翻译式文体、比喻、引用式文体的实验到打破文学体裁形式之间的界线的跨文体写作,在小说写什么和怎么写上,他的每一次实验,都具有重要的文体革新意义。可以说,大江在小说文体、叙事上的探索、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日本当代小说的文体、叙事形态。
二、表意的焦虑——大江健三郎的文体探索
在日本,大江文学似乎被贴上了“晦涩难懂”的标签。在文学随笔《“说后想”与“写后想”》中,大江这样写道:“即便是我,也非常渴望自己的小说被上百万人阅读。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我也会不惜一切去努力的。但是,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文体来表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我是那种仅仅创造出表现自己的文体,就用去了大半个人生的小说家。”[1]265不难看出,大江在文学的“写什么”和“怎样写”上,似乎对“怎样写”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他认为自己是“仅仅创造出表现自己的文体,就用去了大半个人生的小说家”,表现了他重视文学创作的个性、把形式创新放在首位的先锋姿态。
语言一直是小说文体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作家个人风格的有力体现。小说文体是整个小说文本率先呈现给读者的第一存在。在创作初期,大江重视语言破格,晦涩难懂的翻译式文体受到了很多作家、评论家的关注。比如,大江的短篇小说《他人的脚》中,“僕は、この姿勢のままで何十年か生きるんだ、そして死ぬ、と僕はいった。僕の掌に、銃を押しつける奴はいないさ。戦争は、フットボールをできる青年たちの仕事だ。”“便器にまたがったまま、紅潮した顏をむりに振りかぇって学生がいった。”两句在格助词的使用上就存在有别于传统日语之处。很多评论家、作家一时还接受不了这种对传统日语的强暴行为,谷崎润一郎甚至不客气地指出:“要是我的话,我会将之改为‘戦争は、フッ卜ボールが’、将‘紅潮した顏を’改为‘紅潮した顏で’或‘紅潮した顏をむりに振りむけて’”[2]51。
实际上,这些格助词使用上的“错误”反映了作家对待语言特别是对待文体的态度。语言破格仅仅是大江初期小说文体特色的一个方面,它带给读者一种异质感。从总体来看,小说的语言、文体中的异质元素给当时文坛带来的冲击似乎更大。那么,作为小说家,大江是如何认识小说语言的呢?
在《小说的语言》[3]一文中,大江这样写道:“作为小说家,我的实际工作方式就是将语言写出来,反复修改,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审视小说语言与自身的关系。这也从反面证明小说家没有专门的语言、专业思考体系。也就是说,小说创作没有任何线索和法则,即没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应该具有的关于工作的基本道路。小说家的工作从意识活动来看,就是在白纸上书写语言。”[3]20-21大江认为小说创作没有“关于工作的基本道路”,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基准的问题。对大江来说,文体不存在一定的基准,这也是大江对传统文体大胆突破的思想根源。大江的文体策略,总的来说就是在词语、句子、篇章的不同的层面上,改变常规化的表达,使作品标新立异。在大江抛弃传统日语文体的简洁明快、故意写得晦涩难懂这一写作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他对传统进行突围的焦虑和冲动。
莲实重彦认为,虽然大江的文体被称为“翻译腔”,但是,无论将其翻译为何种语言都是有难度的。“当然,这种文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修正的,稍微改变一下思考方式,我认为或许就可以用更为容易理解的语言来重新讲述。那些批判大江至今仍执著于这种文体的人或许想借此来表达其他的内容。或者是与其他内容比起来,毋宁说他们仅仅被一种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所束缚,不由自主做出‘翻译腔’这样的评价的吧。”[4]28
在莲实重彦看来,对大江文学作出“翻译腔”这一消极评价的人,内心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文体范式。这种文体范式就是以“小说之神”志贺直哉为代表的简洁明快的传统日语文体。大江初期小说中的独特的破格、具有超长修饰语的西欧句式的应用以及新奇的比喻,打破了习惯传统日语表达的读者的文体期待视野,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异质感。
对于大江文体“翻译腔”的批评,音乐家武满徹在《眼睛背后的黑暗》中指出:“我不知道与‘翻译腔’对应的恰当的词是什么。但是,如果存在完全顺应国语的文体的话,在处理不断变化、生成的语言这一小说创作行为中,给既定的言语空间带来异质透视的大江的语言操作就是正当的了。这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事实,音乐史上最初出现的长三度的不协调音,对现在我们的听觉来说就是最美的声音。”[5]9
武满徹用音乐史的例子试图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包括文学)都不存在一个永远恒定的基准,大江对文体的认识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的确,从翻译式文体的历史来看,明治时期的文人创造的所谓口语体的文体的功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洋式的措辞。新的时代要求新的艺术形式。战后,《太阳的季节》(1955)的石原慎太郎、《恐慌》(1957)的开高健、大江他们这一代年轻作家以清新而又富有个性的文体描绘出了战后青年的精神状态,给战后文学带来质的转换的事实就是明证。“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6]1通过大江的文体,我们可以看到其文本背后的文化领域,可以观察作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战后是一个作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迅速分化,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的分歧逐渐趋于表面化、公开化的时代。作家不同的文化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审美选择。大江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继承者,民主主义思想也必然反映在其小说形式中。
井口时男认为,大江健三郎的“民主主义”,就是承认与作为“异物”的他人共存的思想。这不仅仅反映在他的社会思想或政治思想上,也反映在他的语言思想上。“大江健三郎的文体并不是为了将‘异物’排除或者同化,而是为了竭尽所能地突出‘异物’。我们将之称为‘恶文’的话,大江的‘恶文’就是对战后文学家野间宏、椎名麟三的那种为导入观念、意识这些‘异物’而不自然地扭曲变形的‘恶文’最为正统的继承……这一思想,对以‘物哀’这一美学理念为范式的日语来说就是异物。他的文体,就是使刺入日语中的异物凸现出来,促使读者觉醒,以认识到‘异物’必须通过经常交流才能得以存续。”[7]160-161的确,语言的生命在于交流,思想的火花在于碰撞。民主主义思想反映在小说文体上就是承认“异物”的存在。在大江看来,所谓的纯粹的、恒定的日语文体是不存在的。只有在不断与他人的交流中,才能建构自己独特的语言世界。
在《读书人》中,大江这样写道:“我不是极其自然地进行小说创作的那种类型,不是天生具有漂亮文体而因此写作的人。我总是首先读外国小说、论文,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那种文体很有趣,接下来就考虑创造具有这种感觉的日语句子。特别是每次读外国诗,我都那样想。因此,经过痛苦的探索,我创造出了自己的文体。”[8]70-71
由此可见,大江新的文体的创造是和他的大量阅读分不开的。在阅读母语文学和外语文学的过程中,他的思维不断在外语和日语之间穿行。这样,他就不断体验到语言的往复、感受性的往复、知识的往复。读书方式的变化,也改变了大江自己的文体。不断选择新的阅读对象,集中阅读选定的作家、诗人和思想家,就不可能不受到自己阅读对象的影响。阅读是一个与他人交流的过程。在试图理解他人语言的过程中,大江也找到了自己新的语言感觉。可以说,大江采用将阅读(他人语言的接受)直接转化为写作(自己语言的创造)这样的创作方法。
这种倾向,在以奥登和布莱克的诗句为内核的《告诉我们在疯狂中活下去的路》(1969)中就初露端倪。《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开始,大江有意识地引用的麦尔康·劳里的文本。之后,在《新人啊,醒来吧》(1983)中引用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在《给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中引用但丁的《神曲》、在《人生的亲戚》(1989)中引用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再见了,我的书》(2006)中引用艾略特、《美丽的安娜贝尔·李毛骨悚然而逝》(2007)对爱伦·波的引用等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大江在写小说的同时,大量阅读诗歌、散文、戏剧等其他领域的人类优秀的成果,这使他深深认识到现代艺术门类之间的互通性,也使他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实现文体的开放与整合成为可能。
文体越界是指在一个创作文本中包容了两种或多种文体形式。文体越界增加了大江文学表现的思想因素、文化因素,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更具创造性、想象性的广阔思维空间。除他人的文本外,大江健三郎的小说还内在地融合、涉及了他不同时期创作的其他小说文本。大江小说的文体越界,在文本内部创造了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锋,表现了一种主体思想的内在不确定性。从创作主体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的角度来看,大江的文体越界,表现了主体对现实、对文化的积极再创造、再思考。可以说,大江对传统文体的话语方式、艺术规范进行反叛的自觉,源于他强烈的表达自我的焦虑。这种强烈的诉求,使他在消解甚至颠覆传统文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超越自我。
三、叙事的冒险——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叙事策略
一般说来,艺术形式转换的深层原因在于时代精神的嬗变。新的时代精神呼唤新的艺术形式。对小说创作来说,这就要求作家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创新意识的自觉。小说叙事模式的变迁也是如此。大江在叙事上的探索是具有突破性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对家族历史追溯的多元视角所表露出来的新历史主义倾向;《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1976)独特的双重叙事视角所造成的滑稽的艺术效果;《二百年的孩子》(2003)科幻小说叙事手法的运用所产生的时空交叉的艺术魅力,都体现了大江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表现了他在小说叙事方面大胆、不懈的追求。
在与赛义德的对谈中,大江这样说道:“到目前为止,我对自己的小说并不满意,因为我没有把握说在叙事上具有了自己的风格。我对日本的宏大叙事、主叙事一直有抵触。但说到与此对抗的反叙事,我还没有创造出来。特别是作为最后的作品(指《燃烧的绿树》——笔者注),超越时间和空间,把很多不同的事物聚拢在一起的构思倒是有了,但是找不到叙事方式。毋宁说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反叙事这样的东西。”[9]30-31
大江所提及的“宏大叙事”,是指叙述者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处理宏大的社会题材,对历史试图提供一种全知的权威解释的叙事。由于宏大叙事为西方思想界所构建的理性主义神话(如世界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同一性、普遍性等)的合法性寻找合理的解释,长期以来,宏大叙事不断遭到质疑,解构中心、关注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了时代的主流。大江文学拒绝宏大叙事的历史、时代、社会大叙事,表现出刻意强化“日常性”和“生活化”的倾向。特别是80年代发表的《新人啊,醒来吧》《听“雨树”的女人们》等一系列小说都具有这种倾向,以至于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大江对私小说传统的回归。从小说创作来看,大江对宏大叙事的“抵触”也仅仅存在于宏大叙事对人类生活普遍性和统一性过分强调,对个体性、差异性、多元性较为忽视这一方面。大江文学强烈的文化意识、紧迫的现实使命感以及对文学的诉求,虽然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史诗视野,但也追求以小见大,进行着形而上的关于人生意义、信仰、理想等的思考,体现着宏大叙事精神。可以说,正是这种精神,使大江以个人经历为背景的小说最终超越了传统的私小说,而没有陷入私小说视野狭窄的泥潭。
按照传统的文学经验,一部(篇)小说的故事无论是直接叙述还是间接叙述,基本上叙述者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是靠单一视点完成的。从大江的小说创作来看,他似乎更倾向于把不同的视点结合在一起来讲述。这种多重视点使小说的故事往往处于一种有意味的含混状态,也使小说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增强。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江试图摆脱传统小说叙事的时空限制,努力使小说结构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多隐喻主题的决心。《万延元年的football》题目本身就表明小说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万延元年的暴动和安保运动为背景的这部小说,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场面的描述。但是,大江在叙事角度上却采用了个人的视角切入,以蜜三郎眼睛的观察以及他对万延元年农民暴动来龙去脉的追溯展现了一个宏大丰富的艺术世界。在鹰四和蜜三郎个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挫折和人生救赎,更有时代的投影和人类的生存状况。由于受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传统小说在结构形式上显著特征就是以时间的自然流动为表现形态,对观照对象作直线性的描述。《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种个人叙事视角的运用,在小说情节结构上突破了单线发展、平铺直叙,在同一叙述平面上增添多条叙述线索,构成多条线索交错并行的结构。正是大江在叙事上将过去交织进现在,才把“发生在两条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推向悲剧的顶峰。”[10]344
《二百年的孩子》描写了1984年暑假,主人公兄妹三人借助“做梦人”的时间装置,在睡梦中进行时空穿梭的故事。在祖母遗画和当地传说的指引下,他们先后去了120前的元治元年(公元1864年)的峡谷村庄、103年前的美国、庆应三年关押农民起义领袖铭助的狱中、80年后(2064年)的县政府以及与其相对抗的“鼯根据地”。借助于科幻小说中常用的时间机器,二百年的历史就在同一空间(峡谷村庄)得以真实再现。我们看到,科幻手法的运用不仅没有冲淡作品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映,而且强化了艺术观照的空间感和层次感。对于科幻小说来说,这样的题材、内容和切入视角并不新鲜,但该作品在叙事结构上却匠心独具。它突破了以往情节化叙事的思维定式,巧妙地将流动的时间结构和舒展的空间交叉,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时空观念属于人类生存体验范畴,只有确立时空界域,人类才得以在历史演进和空间位移中把握自身存在,体验现实人生。《二百年的孩子》这部小说,首先确立了一个叙事起点“现在”,然后追溯到过去。接下来再经由“现在”,到达遥远的将来。最后又重新回到叙事起点“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全部交融于叙述过程中,“现在”成了在整个时空之流中往返运动的参照系。这种独特的时空观念,构成对线性时间观和历史空间观的有力消解。霍士富在《九十年代以降的大江健三郎》中明确指出了《二百年的孩子》这种时空交叉的叙事效果。“时间的空间化具有使抽象的存在得以生动再现的表达效果。视觉化的空间和时间的融合,可以将既具有个人性、又具有时代性的历史传承得以透彻把握。历史时间的哲学把过去、现在、未来置于历史长河中而不是分割开来加以理解、解释。”[11]243当然,这样的叙事策略是和大江的表达主题密切相关的。叙事形式本身表现了大江重视当下的时间观念。大江将希望寄托于现在,认为可以像在河流的中游建水库改变下游的状况一样来改变未来。他立足于现在,在历史回顾和未来展望中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索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对过去的描写,就是追溯历史,使来自历史的启示更好地服务于当下;对未来的展示,就是在当下敲响警钟,努力改变未来。
叙事上的每一次对传统的突破,都伴随着能否被读者接受的风险。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同时代的游戏》可以说是大江迄今为止形式实验走得最远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大江将长篇小说文体与书信的内在形式功能做了恰到好处的结合。《同时代的游戏》中的“我”,是这部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共同体“村庄=国家=小宇宙”历史的书写者。叙述者通过给妹妹的六封信,完成了对共同体历史的书写。在此,书信的个人性、隐私性解构了历史的严肃性、厚重性。整部小说都是“我”漫长的独白和倾诉。对妹妹的呼唤“妹妹啊”一句,在文本段落开头多次出现,其目的就是唤起收信人——妹妹的共感,在历史与当下的叙述中来回穿梭,增加了小说中共同体历史叙事的私人性质。
一般说来,虽然故事在如何讲述上也有正叙、倒叙、插叙之别,但从总体上来说,小说文本还是遵循着一种历时结构。叙事本身的总体特征、小说的文本顺序也就理所当然地决定了阅读顺序,读者必须遵循这一顺序对文本进行解码,才能顺利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同时代的游戏》的六封信虽然有先后顺序,但是每封信的内容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每封信中几乎都存在相似的表述(比如对“破坏人”创建“村庄=国家=小宇宙”过程的描写等),无论从哪一封信读起都似乎是可能的。这样,小说由于其共时结构形成了罗兰·巴特在《S/Z》中称之为“可写性文本”的文本。它不同于传统的那种把读者当成被动的消费者的“可读性文本”。读者获得了一定的阅读自由,可以对六封信顺序重新编码,在阅读中主动介入,对文本进行再创作,从而体现小说题目本身所标明的“游戏”本质。
《同时代的游戏》以书信作为小说的表现方式,是为了表现山谷村庄世界的多重存在方式,为被宏大叙事忽视的存在立传。小说叙述的“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历史,有别于传统小说的历史书写,它不是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再现,不再以“正史”笔法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而是通过书信讲述历史,消解了传统话语对人、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定位,把人和历史由单一性还原为生活本真状态的多元性、复杂性,从而完成了对宏大叙事的反动。
我们看到,大江的叙事实验是对作家创新能力的挑战。每一次叙事实验对作家来说都是带有危险性的,最明显的就是对读者期待视野的打破有可能会导致的作品的可读性问题以及小说文本的过度开放可能使读者无所适从等。为了杜绝形式实验走到最后变成自我复制,除了追求叙事技巧上的新奇之外,大江一直站在时代思潮的前沿,博览群书,时时保持思想、内容上的先锋性。这也是大江能够不断超越自我,叙事方式越发多样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结语
语言一直是小说文体和叙事的基本组成因素,也是作家个性的有力体现。大江小说创作的焦虑和不安,并非来自文学创作题材本身,而是对表现在语言定势和言说方式中的知识危机与意识形态驯化的焦虑。在此,我们不难理解大江在《小说的方法》(1978)、《为了新的文学》(1988)中对俄罗斯形式主义所提倡的“陌生化”手法情有独钟的深层原因。大江从俄罗斯形式主义那里学到的“陌生化”手法,就是“加大感知的难度,拉长感知过程的晦涩难懂的形式的技法”[12]33。正是不遵循“地道的日语”,故意将其改造为“拙劣的日语”“晦涩难懂的日语”这一语言策略上,我们看到了大江小说创造的契机。大江以“陌生化”为武器,通过不断的形式探索,试图突破自动化的语言、言说的定式对文学家和读者的独裁。文体和叙事实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力关系的体现,大江的文体和叙事的实验可以说是对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权力秩序的挑战。大江对小说形式孜孜不倦的探索,体现了他主张文学多元化、个性化的艺术追求。
标签:小说论文; 大江论文; 宏大叙事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同时代的游戏论文; 文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