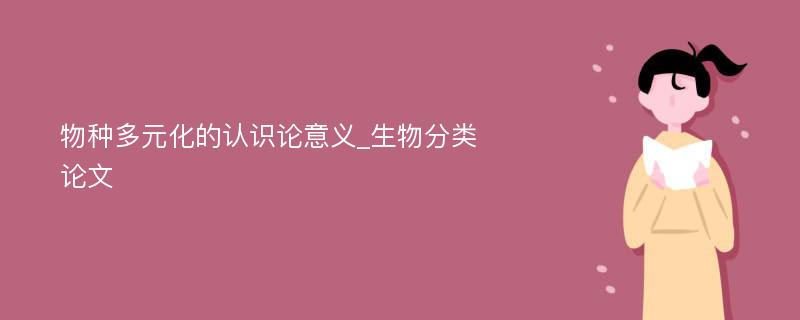
物种多元论的认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元论论文,认识论论文,物种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0)10—0017—07
导言
近二十多年来,主张物种多元论(Species Pluralism)的哲学家和生物学家多起来。各种多元论观点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尽管在拒绝物种一元论(Species Monism)方面是一致的。凯切尔(P.Kitcher,1984)主张的物种多元论是一种多元实在论,主张不同的物种概念对生物界的划分是同等实在的。斯丹佛(P.Stanford,1995)、艾瑞舍夫斯基(M.Ereshefsky,1992、1998)等的多元论是反实在论的,或者主张物种单元不具有特殊的实在性,或者主张物种阶元没有理论意义。物种多元论在其论证中总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接受多个合法的物种概念时,应当如何协调这些物种概念理论意义之间的关系?斯丹佛和艾瑞舍夫斯基看到了这个困难,于是否认物种概念的理论意义。可是,这与生物学家的实际工作不一致,物种概念在进化论、生态学、形态学中具有不能替代的理论意义。
物种多元论的失误主要在于对物种阶元与物种单元的区分不明确,以至提出了一些伪问题。物种(species)作为分类学的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意义:物种阶元(category)和物种单元(taxon)。生物分类学(taxonomy)在对各种类型的生物进行鉴别和命名的同时,总是要假定一个等级系统,或者是自然系统,或者是人为系统。现在,生物学通常采用的是7个等级的阶层系统:界(Kingdom)、门(Phylum)、纲(Class)、目(Order)、科(Family)、属(Genus)、种(Species)、亚种(Subspecies)。物种阶元就是这个阶层系统最基本的一级。建立一种阶层系统,就是假定某种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或者是亲缘关系的远近,或者是本质特征的相似程度。理解了物种阶元的生物学意义,就要用适当的分类单元来列示物种阶元。于是,还要有一个物种单元的概念。作为分类单元的物种,是指一个真实的群体,是具体的动物学对象或植物学对象。一种分类学,总是要根据一个分类单元所具有的特征,把一个类群(group)归于某个阶元。根据迈尔(E.Mayr)的意见,可以把阶元与单元的关系概括为:(1)一个分类单元是一个具体的动物学对象或植物学对象,一个分类阶元则是阶层系统中的一个级或阶层;(2)物种单元是物种阶元的成员。把哪些分类单元列为物种,这取决于所采用的物种阶元定义;(3)关于物种单元,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个体的变异体划入适当的物种类群,划定不同单元问的界限;(4)物种单元中,各成员之间有自然聚集性质,因而物种单元具有时空上的同一性和连续性。
生物学家正在使用的不同物种(阶元)概念,都依据了达尔文的共同由来学说,各种各样的物种划分标准都要服从亲缘关系的分析。现有生物学研究还不能提供把形态学、生态学特征还原为亲缘关系的性质,但这不意味着生物学家没有这样的假定。因此,定义物种的不同途径同样合法,只是现有生物学知识不完备的表现。物种阶元的异质性或多元论,毕竟是认识论的;而物种单元的多样性,则是生物学的事实。本文在评论凯切尔的多元实在论时论证了上述观点。
集合还是个体?
1984年,凯切尔提出了一种叫做“物种多元实在论(pluralistic realism)”的观点,由下面4个命题构成:
(1)物种可以被看成是生物的集合(set),物种及其成员的关系就是“集合一成员”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set-membership)。
(2)物种是那样一种集合,其中的生物由复杂的,生物学上有意义的关系关联起来。有许多这种生物学关系可以用于划分物种单元,但没有哪一种能够回答所有生物学家的所有问题。也就是说,物种阶元是异质的。
(3)物种阶元的异质性是由于存在两种主要的划分物种单元的方法:一是结构相似性,二是系统发育上的联系,而且每种方法都有许多合法的变化。这就支持了物种单元的多元论,因为结构相似性和系统发育联系所给出的要求可以为不同的分类学单位所满足。
(4)物种单元的多元论不仅与物种实在论相容,而且还提供了理顺有关“物种是自然界中的真实实体”的各种观点的途径[1]。
凯切尔对命题(1)的论证,主要体现在对霍尔(D.Hull)等人的“物种是个体”命题的反驳上。他认为,物种的本质论和个体论都是不能接受的,承认物种是集合与否认这些集合的成员具有共同性质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凯切尔的反驳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完全翻译谬误。凯切尔把霍尔的论证归结为一个刻板的模式:“物种是进化的。集合是非时间性实体,因而集合不能进化。所以,物种不是集合。”凯切尔认为,这个论证中存在一个“不完全翻译谬误”(fallacy of incomplete translation),即,集合并不能等同于非时间性实体,进化实体也不能等同于时空连续性实体。按照凯切尔,物种进化就是性质(基因的或者基因加表现型的)的频率分布在不同阶段的改变,一个物种产生了几个世袭种(descendant species)意味着这些世袭种的奠基群体包含着来自祖先种奠基群体的生物个体。在这里,物种被假定为由一个奠基者群体及其后裔构成的集合,这与霍尔的物种定义有着相同外延。凯切尔要表达的意思是:把物种定义为这样的集合,更有利于表述物种的进化行为。
第二,对于作为个体物种的描述,也可以是定律。按照霍尔,如果物种是时空上不受限制的类,则物种就是可以按照定律运行的事物,从而,“所有天鹅是白色的”这样的概括就是真正的自然定律,只要它是真的;如果“物种X具有性质Y”这个陈述是自然定律,它就不能被允许有例外;这个陈述是有例外的,物种不是可以按照科学定律运行的事物,即不是时空上不受限定的类;不存在具体物种的定律,所以物种是时空上受限制的个体[2]。凯切尔承认“所有天鹅是白色的”这样的概括不是真正的自然定律,但认为霍尔的说明是不正确的。在凯切尔看来,“所有天鹅是白色的”之所以不是自然定律,就在于这个陈述是关于进化的偶然结果的,而不在于它有例外。所以,“所有天鹅是白色的”本来就不是定律似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凯切尔认为关于单个物种的定律是可能的。他分析道,令S是一个物种,P是一种性质,在下列情况下,“所有S是P”这个陈述就可以作为定律似陈述:(1)由于缺少性质P而使得s产生了不能正常发育的合子,(2)缺少P就不能产生正常的配子,(3)引入P能导致S的一个物种形成事件。“我认为,这些定律与‘DNA分子链包含相同数目腺嘌呤和胸腺嘧啶分子’这样的低层定律有同样的地位”[3]。
第三,存在非历史联系的物种。凯切尔对物种个体论的第三个批评针对霍尔下面的论证:如果物种是类,则物种是历史不连续的;不存在历史不连续的物种;物种不是类[4]。凯切尔要举出非历史联系物种的实例来反驳这个论证。他举出的例子是关于单性蜥蜴起源的。早在1976年,帕克尔(E.D.Parker)等人就报道了北美单性鞭尾蜥的存在。随后,一些生物学家利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技术以及电镜观察等方法证明:鞭尾蜥属中单性的棋斑鞭尾蜥(Cnemidophorus tesselatus)是两性的虎斑鞭尾蜥(C.tigris)与另一种两性鞭尾蜥(C.septemvittatus)杂交的后代。此外,单性的新墨西哥鞭尾蜥(Cnemidophorus neomez icanus)也是虎斑鞭尾蜥(C.tigris)与素色鞭尾蜥(C.minornatus)的杂交后代。这些研究结果还表明:1)单性种群是两性种群的杂交后代;2)一般单性种群都较年轻。凯切尔指出,棋斑鞭尾蜥也许是历史连续的,但按照历史不连续性更容易解释这个单性种的起源。他说到了两种体现非历史联系性起源的可能途径:第一,起源于母系种的边缘种群,即在某一时间来自不同的繁殖群亲代杂交产生了孤雌繁殖系,并一直延续下来;第二,所有棋斑鞭尾蜥的初始群体都被消灭,母系种的偶然杂交使得单性种重新繁衍起来。凯切尔的结论是:所有物种是历史联系的,这不是必然的,甚至也不是真的。
凯切尔对“物种是集合”命题的论证其实只是对霍尔有关“物种是个体”论证的反驳。从逻辑上说,即使霍尔的论证不成立,也不能证明物种就是集合。在上述的三个反驳中,第一和第二个属于论证方法问题,中立于“物种是集合”与“物种是个体”。只有第三个反驳才是有利于“物种是集合”论题的,但凯切尔只用了一个反例,而没有正面的论证。况且,这个反例能说明的问题也是值得怀疑的。“历史联系”(historically connected)这个概念是凯切尔加在霍尔头上的,用于表达霍尔这样的意思:物种具有历史唯一性,一个物种只能起源于更原始的物种。凯切尔把霍尔的这个意思改造为历史联系的定义:一个生物的集合是历史联系的,仅当属于该集合的任何生物或者是该集合中初始群体的成员,或者是该集合成员的直接世系。一个棋斑鞭尾蜥群体起源于两个不同繁殖群的杂交,这有两种情况:两个繁殖群属于同一个物种,从而这个棋斑鞭尾蜥群体就是一个物种(由两个繁殖群构成)的直接世系,这与凯切尔的历史联系定义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这两个繁殖群不属于同一个物种,则这个棋斑鞭尾蜥群体仍然是由两个不同繁殖群构成的集合成员的直接世系,也符合凯切尔对于历史联系的定义。在棋斑鞭尾蜥的初始群体被消灭后,母系种的偶然杂交还能产生出类似的单性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的单性种与棋斑鞭尾蜥的初始群体之间存在着跨种差别,就不能把新的单性种看做是棋斑鞭尾蜥,这时,并没有违背物种起源于物种的原则——这个原则用霍尔的话说就是:马总是由马所生。如果新的单性种与棋斑鞭尾蜥的初始群体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这违背了霍尔的马生马原则,但不违反历史联系的定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新单性种仍然是母系种的直接世系。我们还可以把话题放开一些。马和驴的后代是骡子,骡子没有生育能力。马和驴符合生物学种的定义,而骡子就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同样,两个不同的两性蜥蜴种的杂交产生出单性蜥蜴,这个单性蜥蜴也可以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种,因为骡子和单性蜥蜴都可以被看作是在生殖方面有缺陷的,只不过骡子不能繁育后代,而单性蜥蜴由两性变成了单性。既然棋斑鞭尾蜥不是独立的物种,凯切尔用它来作为物种的历史联系性的反例就不恰当了。
被作为物种的生物集合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方法,这容易使人想到物种的多元性。尽管物种集合论与个体论中立于物种的多元论和一元论,但物种是集合的假定更容易与物种多元论协调起来。也许,凯切尔主张物种集合论的目的正在于为多元论准备有利条件。
物种阶元还是物种单元?
物种究竟是集合还是个体,这本来是由物种阶元的定义给定的,不能把不同的物种阶元定义纳入到同一个理论假定之下。物种阶元的一个定义,意味着一个关于自然秩序的理论。我们不能想象这种情况:在同一个自然秩序的理论中,同一个概念同时指称两种相互矛盾的性质。接受了一个物种阶元的定义,也就等于对物种究竟是个体还是集合的问题给出了唯一的答案。关于物种单元,它是由划分类群的方法定义的。例如,我们可以用生殖隔离的方法把一个两性生物的繁殖群定义为一个物种单元;也可以根据结构的相似性(特别是遗传结构的相似性)把一个类群看做是物种单元;还可以按照系统发育的关系把一个单系作为一个物种单元,等等。对于同一个类群,如果按照不同的划分方法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比如结构相似的一群生物在系统发育上不能被作为一个物种),那就说明这两种划分方法还没有被统一到一个物种阶元的定义中。对于相应的理论假定来说,这种划分方法是不完善的。比如,我们可能怀疑某种辨别结构相似性的方法不够可靠。
凯切尔的物种多元论,究竟是物种单元的多元论还是物种阶元的多元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凯切尔的正式说法是:物种阶元是异质的或多样的(heterogeneous),物种单元是多元的。在命题(2)和(3)中,凯切尔是根据物种单元划分方法以及生物学兴趣的多样性给出上述两个结论的。
按照命题(2),物种这个集合中的成员之间是由生物学上有趣的(biologically interesting)关系联系起来的,用于划分物种单元的这些生物学关系有多种,但没有哪一种能够回答所有生物学家的所有问题。生物学种概念强调了生殖隔离的标准,可以适合于许多物种单元的划分。例如,按蚊属的各个姊妹种之间在形态上是相似的,但在繁殖上是隔离的。但是,生物学种概念在古生物学中就遇到了尴尬,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手段来判断已经绝灭的各类型之间是否在生殖上彼此隔离。这时,进化谱系上的物种相继关系主要是利用形态学材料来给出的。不仅如此,生物学种概念几乎不能应用于无性繁殖的生物。基于这样的事实,凯切尔说:“生物学种概念给出了自然界多样性的一种模式。虽然把生物划分为繁殖上隔离的群体在理论上是重要的,但这不是生物多样性唯一重要的模式”[5]。
凯切尔的命题(3)指出,物种阶元是多样的,而每一种物种概念都可能是合法的并为不同的分类单元划分所满足。他坚持这一命题的理由是:生物学家使用物种阶元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生物学家要达到的目的不同,所使用的物种概念也不同。生物学家究竟要用物种概念达到哪些目的呢?详细的数目是不能给出的,但可以把生物学家的诸多研究区分为两类:结构的和历史的。同样,物种作为集合的概念也可以区分为两类:物种的结构概念和物种的历史概念。凯切尔强调,这两种解释模式没有哪一个是更基本的。
通过分析凯切尔的命题(2)和(3)可以看出,凯切尔的物种多元论不仅是物种单元的多元论,还是物种阶元的多元论。存在于自然界的生物类群(group)本来就是遵循不同的自然秩序形成的,如一个孟德尔繁殖群、一个生态群等。能够作为物种的自然类群,就是一个物种单元。因此,物种单元的多元性是容易理解的。但是,物种阶元的多元性就很费解。一个物种阶元的定义,总是对应于一个或一组理论假定,规定了自然类群作为物种的标准。选择了一种理论假定,也就确定了一个物种阶元的定义。在同一个理论下,不能有多个物种阶元的定义,至少不能有逻辑上不相容的物种阶元定义。可是,凯切尔在论证物种阶元异质性时似乎就是要指出生物学中现存的物种阶元定义是同样合法的。他的这个论证大致有三个步骤:现有的生物学研究兴趣是多样的且没有哪一个是更基本的,不同的生物学兴趣对应着不同的物种单元划分,多样的物种单元划分对应着多样的物种阶元。这个“三部曲”式的论证,每一步都是成问题的。
首先,生物学研究兴趣是多样的,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基本的生物学理论假定。早在1961年,迈尔就提出了两种生物学的划分:研究远因(ultimate causation)的进化生物学和研究近因(proximate causation)的功能生物学。“近因控制着个体(及其器官)对环境的直接因素的反应,而远因则负责每个种的每个个体所赋有的信息的特殊DNA密码的进化”[6]。受此启发,凯切尔也区分了两种生物学研究:结构解释和历史解释。结构解释的目标是找到这些性状的共同基底结构和机制;而历史解释则是要找到不同类型的共同祖种,并通过每个类型在系统发育谱系中与祖种亲缘关系的远近来解释各种性状的分布。他认为,“这两种解释模式没有哪一个是更基本的”,因为“对具体生物的研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有些是结构的,有些是历史的,对这些问题的结构回答会产生新的历史问题,而历史的回答也会引起新的结构问题”[7]。两种生物学研究兴趣的确是不可偏废的,但这只是在两种生物学研究兴趣基于同样的理论假定时才出现的情况。事实上,今天的生物学家,不论他们关心的是分类学、生态学还是进化论,每当他们使用物种概念时,大都接受了达尔文的共同由来学说,也大都相信物种来自物种。即使是数值分类学,也要在鉴定物种时考虑亲缘关系。当基于物种不变假定的结构解释与基于共同由来假定的历史解释相矛盾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可以预期这种选择是有利于共同由来假定的。凯切尔说不同的解释模式同等合法,只是表明现有的生物学研究并不完备。
第二,生物学研究兴趣未必与特定的物种单元划分一一对应。凯切尔结合下面的例子来论证生物学研究兴趣与物种单元划分的对应关系。微生物学家在研究病毒时,首先是从形态学和生理学的性状来区分不同的病毒,如蛋白质壳的组成与形状、在不同寄主中复制的能力等。接下来就产生了诸如“为什么这个病毒的蛋白质壳有如此形状”以及“为什么能够在这种寄主中复制”等需要解释的问题。于是,微生物学家转向研究病毒的遗传组成,用共同的基因组来解释一种病毒具有的某些共同性状。在这种解释中,我们需要从遗传结构上划分病毒的类型,而且,无论遗传物质上的差别是否对应着表现性状的差异,都把遗传物质的差别看作是真实的。历史解释面对的问题是多样性,多样性可以是形态、行为、生态或者是遗传结构方面的。这些性状可能是不稳定的,但对这些性状分布的解释把我们引向系统发育研究,根据与共同祖种的远近来区分不同的物种。凯切尔认为,两种生物学研究的主要类型,产生两种不同的生物分类系统。凯切尔没有在此止步,又要把每个生物学研究主要类型进一步细分。他区分了物种结构概念的三种定义途径:具有共同的基因,具有共同的染色体结构,具有共同的发育程序(developmental program)。关于物种的历史概念,凯切尔根据系统发育分支原则和连续性原则,从观察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生殖隔离、生态学的特征、形态学特征,给出了6个定义途径。
在上述的论证中,凯切尔的失误是明显的:混淆物种单元的鉴别手段与物种概念的理论意义,进而把生物学的研究兴趣唯一地挂靠在一种鉴别手段上。物种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对一种自然秩序的承诺。在基于共同由来假定的物种进化理论中,物种是进化的单位,处于进化树上的特定位置,亲缘关系是物种概念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定义亲缘关系远近要依据生物的可观察特征,例如形态结构特征、生态行为特征、生殖隔离等。物种概念的理论意义并没有因为观察特征不同而有变化。现代生物学文献中的生物学种、生态学种、进化种、形态学种等概念,是与物种单元的鉴别途径相联系的,但不意味着这些概念的提出者遵循不同的理论假定。亨尼希(W.Hennig)在定义与祖种关系的远近时,不能不用到各种观察特征,并不限于某一种鉴别方法。所以,我的结论与凯切尔的不同:同一个生物学研究兴趣可以对应着多种不同的物种鉴别方法,不同的生物学研究兴趣也未必意味着不同的物种概念。
第三,物种单元的多元性不一定意味着物种阶元的多元性。按照凯切尔的说法,“不同的研究要求不同的物种概念,……生物学研究的每一个主要类型又可以细分为最好通过采纳新的物种阶元观点来指导的探究”[8]。凯切尔先说不同的研究要求不同的物种概念,这时的“物种”其实是物种单元;凯切尔又说细分的研究类型需要新的物种阶元。这明显是把阶元与单元的概念混同在一起了。凯切尔关于物种阶元是多元的这一结论,正是建立在对阶元与单元不加区分地使用的基础上的。一个生物学家在对两性生殖生物的单元划分中可能使用生殖隔离标准,同时又在对无性生殖生物的单元划分中使用结构相似性标准。但是,这不表明该生物学家的物种阶元观点发生改变了。通过上一段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物种单元的多元性一定不意味着物种阶元的多元性”的结论了,这里不再赘述。
物种多元论与实在论是否相容?
按照凯切尔的命题(4),多元论与实在论不冲突。他指出,“物种实在论独立于物种作为个体的观点”。凯切尔的论证有两点。第一,“如果物种实在论被看作是关于物种独立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判断,任何接受关于集合的温和实在论的人都能接受物种实在论。生物存在,生物的集合也存在。作为物种的生物集合存在独立于人的认识。所以,物种实在论是无意义真的。”第二,物种的实在论定义所要求的自然界客观结构与物种多元论是相容的。“多元实在论所依赖的观念是: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们在进行不同解释目标的生物学研究时可以是客观上正确的,进而不同生物学领域的自然图景可以把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交互分类(cross-classify)。”[9]由于凯切尔对物种单元与阶元不加区分,他的多元实在论就可能是物种阶元的,也可能是物种单示的。在物种阶元的意义上,多元论与实在论不能相容;在物种单元的意义上,多元论可以与实在论相容,但多元实在论的命题过于平庸,因为物种单元是一个可观察实体,对于它我们不提出是否实在的问题。
凯切尔的多元实在论,在物种阶元的意义上存在这样的问题:主观兴趣的多样性与客观的自然图景单一性不能相容。一种交互分类就是对单一自然图景的承诺,承诺一种自然界的结构体现了实在论,而按照主观“范式”选择观察视角才能保证多元论的结论,但这又背离了单一宇宙结构的承诺。在凯切尔那里,多元论与实在论好像是被硬拉到一起的。
按照凯切尔的物种阶元多元论,容易走向反实在论的结论。艾瑞舍夫斯基(M.Ereshefsky)的消除主义多元论(eliminativism pluralism)就是这样形成的。按照这种观点,物种多元性反映了世界的真实性质,而不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状况;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物种阶元的存在;物种概念的多元性不在于我们对于物种概念的定义来自不能相容的科学目的,而在于各种分类单元之间没有统一的特征。消除主义多元论从反实在论的立场否认物种阶元概念所指称的单元的真实存在,进而否认物种阶元在理论上的有用性。艾瑞舍夫斯基认为,他的消除主义多元论“避免了因用不同词项指称不同类型单元引起的歧义,同时又通过要求各种分类方案的内在统一而保持了一致性”[10]。
艾瑞舍夫斯基强调,“物种的反实在论只是反对物种阶元的存在”,而不否认被称作“物种”的单元的真实性,因为“物种阶元不存在并不意味着被称作‘物种’的单元是人为的”。这样,“在一个理想的理性决定的世界里,消除‘物种’一词将是最佳选择”[11]。我们可以把艾瑞舍夫斯基从多元论到反实在论的论证线索总结如下:
(1)一元或多元的争论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
(2)被称作“物种”的单元是真实的分类群体,
(3)物种单元是多元的,即物种单元有不同的类型,
(4)各个类型的物种单元之间没有共同的性质,
所以,
(5)没有一个物种阶元概念能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物种单元。
(6)物种阶元概念在理论上没有作用。
命题(1)只是对讨论角度的规定,命题(2)和(3)也是被生物学家广泛接受的,因而这三个命题一般不会引起争论。但从命题(4)开始,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而这又是得出(5)和(6)最重要的理由。艾瑞舍夫斯基给出了三类物种单元,认为它们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生物学过程。由于这三种生物学过程是不能被统一起来的,且三类物种单元之间没有共同的性质,所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物种阶元能够适用于三类物种单元。生物学家对于物种概念的理解情况并不像艾瑞舍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只是按照自己的研究目的来定义统一的物种阶元,而是要用一个统一的物种阶元概念整合不同的物种单元。正如霍尔所说,“自达尔文以后,许多系统学家就反对把进化的基本单位等同于分类的基本单位了”[12]。无论是系统学家还是进化生物学家,都要求物种阶元的可应用性,也都要求相应的物种单元的可识别性。这样,他们采取的策略通常是简化物种阶元的定义性质。尽管不同类型的物种单元之间很少共同的可识别性质,但找到作为进化基本单位的共同性质还是可能的。数值性状分类学家的目的就是企图给出可以操作的方案,把性状的相似性程度与作为进化基本单位的要求关联起来。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说,任何具有重大差别的实体之间,只要我们把它们定义为同类过程的载体,就存在共同的本质,就有可能用同一个词项来指称这种共同的本质。这样,从命题(4)到命题(5)的论证是不合理的。
艾瑞舍夫斯基把命题(6)看作是命题(5)的必然推论:物种单元的多样性意味着统一的物种本体论阶元是不存在的。所谓统一的物种阶元,无非是不同物种单元的共同定义特征或者共同本质。就现有的生物学来说,追求统一的物种阶元是为了建立统一的进化论。这时,一个物种阶元的定义就是一个一般进化模型的前提假定,而物种阶元的定义特征决定了与该概念相对应的进化模型的可应用性。进化模型在经验上的恰当性,显然受到了物种阶元定义的影响。如果进化模型要求的物种阶元不能与其他理论模型要求的物种阶元相一致,这只是说明了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不说明物种阶元在理论上没有作用。
斯丹佛((P.Stanford)也有类似的论证。凯切尔认为,一个合法的生物学研究兴趣所要求的物种概念必定是实在的。斯丹佛指出,一项研究是否在生物学上有趣,因而相应的物种概念是否合法,这只能根据当时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目标来评价,因而具有历史相对性。“这样,相同的物种划分在一段时间是生物学上有趣的,而在另外的时间就不是。物种概念变化了,但在物理状况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物种,并不依随于物理状况。……凯切尔的物种依随在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心灵状态上,因而缺乏真实客体必须具有的性质”[13]。
艾瑞舍夫斯基和斯丹佛指出物种阶元的多元论与实在论不能相容,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而得出物种阶元是非实在的结论就过于草率。在一个理论中(比如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物种阶元是对各个类型的物种单元共同性质的承诺。是否找到了这种共同性质,这是生物学研究的水平问题,不能作为物种阶元是否实在的证据,因为这不排除未来生物学进步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种共同性质。
结语
凯切尔的多元实在论观点,映射出了理论生物学的不完备性。一方面,生命科学还不能告诉我们关于生命的确切定义,不能给出关于生命世界的完整理论图景,而这些正是完美的物种阶元定义所必须的;另一方面,一个统一的物种概念有赖于各种生物学研究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模式,但这个条件现在只能部分地达到。现有的物种概念都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物种单元,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
实际上,凯切尔的多元实在论与他的解释统一论也不能完全相容。按照凯切尔,科学解释的目的在于确定一个论证集合,它能使我们所接受的语句集合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也就是确定唯一的解释库E(K)。一个论证集的统一程度或统一力的大小取决于该论证集的结论集的大小和论证形式的严格性。解释就是一次次地用尽可能少且尽可能严格的论证形式推导出尽可能多的关于不同现象的描述[14]。如果假定唯一的宇宙结构,物种多元论就违背了凯切尔的解释原则;如果假定多元的宇宙结构,物种多元论可以与凯切尔的解释原则相容,但要放弃实在论的承诺。
收稿日期:2010-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