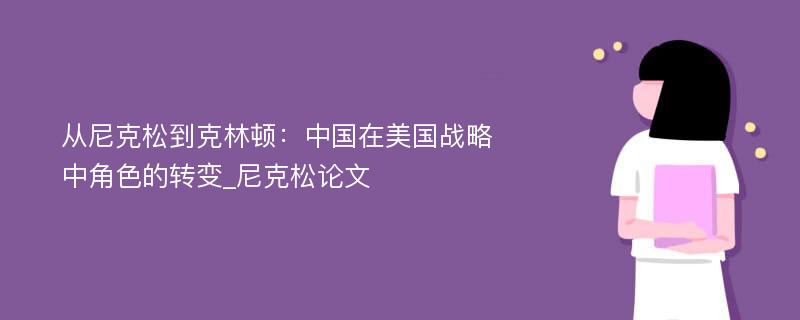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角色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克松论文,克林顿论文,中国论文,角色论文,在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以来,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考察中美关系的变迁,而把重点放在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其战略中的位置。本文试图证明以下几个命题:(1)中美两国间大期望导致大失望, 更实际地认识两国关系反而更有利两国关系的发展;(2 )冷战时期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始终以它国威胁为前提,而冷战后的中国终于以自己的经济成绩显示其在美国战略中的价值;(3)与命题二相联系,70~80年代, 中国对美国存在经济与安全双重需求,而美国对中国主要是安全需求,今天,双方对对方的需求均是双重的。
一、从尼克松到卡特:战略三角中的中国
到60 年代后期, 中美双方均渴求缓和。 在反帝反修的斗争中,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9年中苏边境战争,使中国认识到最直接的威胁来自苏联,而不是美国。因此,中国寻求与美国缓和以减轻两边对抗的压力。不仅如此,中国期望与美国联合共同对付苏联。
就美国而言,面对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尼克松政府迫切需要体面地摆脱东南亚泥潭。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认识到无力同时执行“两个半战争”的战略,即同时与苏联、中国和越南作战;与中国的缓和使美国的战略变成“一个半战争”。(注:1970年2月8日,尼克松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外交政策报告》中,公开宣布从“两个半战争”战略转向“一个半战争”战略。)尼克松和基辛格期望美国削减其在东南亚驻军后,中国能在亚洲起稳定作用。
虽然与中国的缓和是美国全球战略重新调整的一部分,但其直接目标是利用中苏分裂和中美缓和,来赢得对苏联战略性武器限制谈判,以及在越南问题和其它双边或多边问题上的外交优势。苏联也担心中美联合,因而也急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样在1972年2月和5月,尼克松总统戏剧性地访问了北京和莫斯科,分别签署了《上海公报》和《苏美战略武器限制协议》(SALTI)。
这样,中美出现了分歧。美国期望利用与中国的新关系而居对苏联谈判的优势,而中国则期望把美国纳入反苏联联盟并因此削弱尼克松—基辛格致力以求的苏美缓和。如果苏美缓和得以推进,中国的安全就会受到更大的威胁,中美关系也可能恶化。
到福特政府时期,具体地说是1974—1975年,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看待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作用问题发生了争论,即是否与中国建立军事联系。(注:Michael Pillsbury, "US- China Military Ties? "Foreign Policy(Fall 1975).No.20.)此时已是国务卿的基辛格仍然以地缘政治来处理中美苏三角关系。基辛格设计的中美联合的目的是增加苏联的疑虑使美国在美苏关系中处于心理上的优势。因此,任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都必须志在维持和加强美国对苏联的杠杠。与此同时,基辛格又担心,与中国的军事联系有可能刺激苏联对美国更加强硬的路线,促使苏联采取更富进攻性的国际行为,因而会损害整体缓和关系。
国防部从军事而不是外交角度看待三角关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认为,美苏缓和既没有使苏联放慢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发展,也未能使苏联领导人改变长期的霸权目标。美国的全球军事平衡优势来自中苏分裂,而中美缓和更加强了美国在全球,尤其是在东亚的军事地位。作为一个战略盟友,中国有巨大的潜力去束缚苏联的军事能力和资源,使苏联难以全力与西方搞军备竞赛。国防部相信,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比苏美缓和更加重要。
基辛格的战略还受到其它国内势力及中国的挑战。1974年12月国会通过的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严重削弱了基辛格的战略,该修正案把美苏贸易与苏联的移民政策联系起来,促使苏联废除了苏美1972年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苏联在中东和安哥拉的行动也使人怀疑基辛格缓和战略的可信度。苏美关系紧张起来。
基辛格也受到中国方面的批评。中国认为基辛格的缓和战略是绥靖主义,怀疑能否依靠中美联合而抗击苏联。中国要求他履行《上海公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在这种背景下,1975年12月基辛格和福特总统一道访华,批准美国在西安建立一个生产F-4鬼怪式战机发动机的工厂。(注:西方盟国间建立的“协调委员会”(CoCom)专门控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让技术。 美国可以通过该委员会而封杀中英之间的军事交往。)为了稳定毛泽东去世后的中美关系,1976年10月12日,基辛格又促使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向中国出售两台最先进的具有军事用途的计算机(Control DataCyber 72)。10月15日,基辛格在中国局势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对世界均势至关重要,不允许受到外界的威胁。
至卡特1977年1月就任总统时, 卡特和国务卿万斯的优先目标仍然是延续基辛格的与苏联缓和政策,由于中东问题、巴拿马运河问题都是美国要倾力解决的难题,中美关系远远靠后。和基辛格当初一样,万斯不希望中美的军事联系损害苏美关系。(注:[美]万斯:《困难与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郭靖安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然而,当卡特的人权外交遭到苏联的拒绝后,卡特才开始打“中国牌”。
其实,“中国牌”一开始就是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和中央情报局所主张的。(注:[美]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应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年。)以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对苏强硬派主张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比如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或允许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这一主张因国务院的阻挠而暂时搁浅。
1977年,NSC的研究报告《总统评估备忘录(10)》完成。 该报告的结论是,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将下降,美国将居优势地位。这是由于苏联面临接班人问题,资金和劳动力短缺,农业欠收;而中苏分裂更加剧了苏联的困难。面对这一结论,国务院和NSC 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万斯和其他鼓吹缓和的官员认为苏联的脆弱恰恰会使其对缓和感兴趣。而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的脆弱为美国削弱其实力提供了机会。但是,后一主张直到1978年春天才占上风。
1978年,苏联和古巴联合军事干预埃塞俄比亚,美苏关系恶化,卡特总统才不得不采取布热津斯基的对苏强硬并发展与华军事关系的建议。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决定向中国转让军民两用技术, 允许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1978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加快了美国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步伐,国务院的方案流产。12月底,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至1980年底,中美发展成准军事盟国,中国允许美国在中苏边境建立装置以监视苏联的核试验。
但是,应该看到, 正常化建立在对付共同的敌人的基础上, 整个70年代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是赖于美国自身的困难及美国面对的强大的外部威胁。而当美国认为自己更强大更安全时,它对中国就会重新定位。
二、里根政府:重新评估中国的作用
里根热衷于反对共产主义,因而在总统竞选中就攻击《上海公报》,声称要恢复美台关系;作为当选总统,又邀请台湾代表参加他的就职仪式(后又收回邀请);在他就任第一年里,拟出售先进战机给台湾。但是,里根毕竟是现实主义者,他不但没有放弃传统的遏制苏联战略,反而决定放弃缓和,以更强硬的政策压垮苏联。因此,里根仍然奉行三角战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1982年的《8.17公报》中承诺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不会增加,并逐渐减少售台武器。
但是,随着基辛格的门徒黑格国务卿在1982年夏天的离任,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继任,里根政府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作用。(注:详细内容刊载于《远东经济评论》,1983年4月21日。 )从杜鲁门总统的政策顾问乔治·凯南到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都是欧洲中心论者,一直以战略安全或权力平衡来思考世界,在这种框架下,中国是亚洲战略的首要目标。
来自加州的里根及其助手的背景与前任有了根本性变化。在国务院,一直从事金融和商业活动的舒尔茨把经济实力、工业基础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看作集体安全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在日本长期生活过。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Pawl Wolfowitz也是位日本问题专家。在国防部,温伯格的亚洲防务政策设计师Richard Armitage是位东南亚问题专家。在NSC,负责东亚事务的Gaston Sigur是位日本问题专家。 从微观个体行动角度看,这些关键决策人员的观念,尤其是共同的背景当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政策倾向。
1983年初,舒尔茨召集亚洲问题专家在华盛顿举办一系列研讨会,评估美国的亚洲政策, 尤其是中国政策。 评估的结果反映在舒尔茨1983年3月15日在旧金山世界事务理事会的讲话中, 即降低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强调日本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新评估其美国政策。由于美国对1979年中国自卫还击战的暖昧态度,尤其是里根的挑衅性言辞,使中国的“一条线”政策转变为1982年的独立自主政策。
里根政府为何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中国呢?除了上面提及的决策者因素外,至少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由于中国已公开声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开与苏联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国似乎不大可能与美国进一步合作对付苏联,而美国的苏联政策比过去更强硬;
第二,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正致力于现代化和内部发展,不可能把精力放在外部,尤其是东亚事务上,因而不能配合美国的亚洲战略;
第三,由于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而苏联正面临一系列国内外困难,美国对抗苏联的能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大大提高了;
第四,美国的盟国多年来第一次与华盛顿空前密切地合作对付苏联的威胁,日本的中曾根康弘,西欧的撒切尔夫人和科尔,都是里根的忠实盟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大大减少;何况,即使没有美国的推动,中国也会自然地抗击苏联的威胁;
第五,日本及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更关注通向东亚、印度洋和海湾的海空交通安全,一旦受到苏联的攻击,他们会比中国更积极地配合美国的反应。
美国中国政策变化意味着什么?从胡娜事件、台湾在亚洲发展银行的成员资格及其它问题上看,美国对中国都持更强硬态度:里根政府声称,无论中国采取何种报复措施,即使降级外交关系,美国都不会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里根政府及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抱有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现代化,由此必然要求良好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技术和资金回报。这样,里根时期中美间实质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1984年访华期间,里根总统决定向中国出售核燃料和核设施,转让核技术;次年,中美签署了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定。这是美国首次与社会主义国家签署这样的协议,也是美国第一次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签署这样的协议。
里根政府降低了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却取得更具实际意义的进展,为什么?第一,中国开始以增加的经济变化吸引美国的注意力;第二,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都本着更实际的目光看待对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缩小,而此前的中美关系是大希望导致大失望。
三、布什: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总统
布什任期内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特别时期,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触动了美国人的根本价值观,而苏联解体抽调了中美关系过去赖于发展的基石。中美政策一时成为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总统与国会对抗的导火线。
争论和对抗的根本原因来自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布什是在尼克松—基辛格时代开始其外交生涯的,深受尼克松—基辛格的实力政治原则的影响,布什曾任第一届驻华联络处主任。而布什的一些高级官员,如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都曾是基辛格的助手。现实主义的原则是:伦理应该让位于国家利益,秩序重于理想,战略利益重于意识形态差异。
布什的外交政策典型地反映了这些原则。布什把中国当作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战略伙伴,是平衡苏联衰落和日本上升的关键因素。布什担心孤立中国会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或危险的后果。
现实主义在本质上与美国民主传统不一致。布什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受到两股意识形态力量的挑战:自由人权活动分子和保守的反共分子。在冷战时期,自由人权活动分子还不构成障碍,但在1989年之后,他们与保守的反共分子一道,形成反华合力,并通过国会传媒而释放能量,向布什总统施加压力。1990年秋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对布什对华政策的赞成与反对比例是5:2,而民意领袖对布什政策的态度是5:1。(注:Washington Post,5 Oct.1990.)
看来,布什在与国会的斗争中,处于舆论的劣势。另外,国会反对布什的对华政策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虽然两党多数议员均反对布什的温和政策,但是民主党议员更想借机来抵消共和党总统比较成功的外交政策。而一些来自西海岸华裔美国人聚居区的议员,亦借机同情“民运”而赢得选民的拥护。有些议员坚持更强硬地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则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州的工业受到来自中国产品的压力,例如赫尔姆斯参议员就来自纺织工业相对集中的北卡莱罗纳州。
总统与国会的冲突的焦点是制裁、中国留学生的法律身份以及最惠国待遇问题。布什总统极力以“国家利益需要”来化解国会要求的严厉制裁;以行政令而非国会要求的立法形式解决中国留学生法律地位问题;游说共和党议员,动员利益集团而且在中国最惠国待遇(MFN )问题上取得全面胜利。这不仅是因为MFN是中美全面关系的基础, 而且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参与已越来越多。仅1990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60亿美元,丧失中国市场就意味着西海岸飞机制造工人、中西部农业工人和东北部高技术区工人失去工作。在后面我们将看到,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卷入越深,中国对美国就越重要。
布什为何不余遗力地捍卫他的对华政策?和以前的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不同的是,作为总统,布什亲自负责和过问具体的对华政策,这是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没有过的现象。就任总统不久,布什就访问中国,表明总统对中美关系间的各种问题的重视。北京政治风波后,布什控制了行政部门中国政策的制定,亲自过问有关武器销售和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颇有集权化倾向。他还专门就中国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解释他的对华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同寻常的。布什曾多次向国会表明,他很了解中国,要全面负责对华政策的制定,要享有制定对华政策的灵活性。应该说,这种意愿和决心在与国会的冲突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评价布什总统的这种行为时,有人这样说,“驱使布什政府反对(国会)的动力不是他们渴望所谓的灵活性,而是源于这样的事实,总统本人视自己为中国事务部主任,比华盛顿特区中的其他任何人都要了解中国——更不用说国会了。若被国会束缚而不能决定对华政策,这将不仅是对总统尊严的冒犯,也是对这位前驻华大使尊严的冒犯。”(注:Thomas L.Friendman,"The Politics of Punishing China",NewYork Times,3 Sept.1989.Sect.4,3.)这种评论至少部分地道出了布什总统“亲华”的根源。
四、克林顿:经济至上主义者
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其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是,第一,冷战后处于战略大调整中的美国在以下5种大战略上徘徊:新孤立主义, 选择性接触,集体安全,遏制和主导权;(注:Posen and Ross,"Competing U.S.Grand Strategies",in Robert J.Lieber( ed) ,Eagle
Adrift: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An Imprint of Addison Wesley Longman,Inc,1997).)第二, 克林顿总统本人把绝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国内经济,较少过问外交政策;第三,上述两点的结合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美国战略为“漂泊之鹰”,没有明确的航向。
美国外交的这种特征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摇摆不定。美国一方面不停地制造麻烦:封杀中国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制造“银河号”事件,搞人权反华提案,阻挠中国入关,最后允许李登辉访美使中美关系跌入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另一方面,美国又在朝鲜半岛、柬埔寨等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还企图把中国纳入涉及中国主权的地区多边机制。因此,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的全面涵义是在接触中遏制中国。
“全面接触”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徘徊后的必然选择。冷战结束意味着美国是苏美争霸战的胜利者,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无疑最有利于美国。为了维持这种格局,美国只能追求主导权。1997年5 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个大标题是:“为了安全,更加繁荣的明天,今天必须领导世界。”(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May,1997.)
有了这种定位,美国所要做的就是努力维持现状,阻止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的出现。1992年国防部制定的《防御计划指南》说得明白,打败苏联以后,“现在我们的战略必须集中于排除任何未来的全球性竞争者的出现。”美国“必须建立和保卫这样一个新秩序,它能扼制那些最有可能成为竞争者的国家不要渴望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必须“负有责任地忠告那些错误的国家,其行为不仅威胁着我们的利益,也威胁着我们的盟友或朋友的利益,同时还有可能严重地扰乱国际关系。”(注:这一战略文件被有意地透露给《纽约时报》。参见“五角大楼计划摘要:防止新对手的出现。”New York Times,March 8,1992.)为此,国防部制定的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是“不接受任何敌对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对亚太地区的政治或经济控制,防止任何这样的集团主导亚太地区的丰富资源、巨额财富和先进技术。”(注:美国国防部:United States Security S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Washington D.C.February,1995.)可见,既然要充当霸主,就要阻止挑战者。那么谁会成为这一战略的挑战者的候选人?
根据一些美国人的判断,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就是中国。要成为挑战者候选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是综合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地位。在目前的几个大国中,俄国将会花相当长的时间完成其政治和经济的阵痛转变。欧洲的统一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政治上是不完全的;另外,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似乎都不可能成为挑战者,德国仍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致力于由统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日本将仍然是一个经济大国。经过剔除,中国似乎成了最合适的候选人。美国主导权的倡导者,兰德公司的资源研究员Khalilzad写道, 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全球性对手的候选人”。(注:参见Zalmay Khalizad,《从遏制到全球领导权:美国和冷战后的世界》,第30页,加州、兰德公司,1995。)一方面,中国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发展着,其经济实力不多久可望超过日本、并且在下一个世纪的20年内将会和美国一样强大。同时,中国正在加快其军事现代化建设。尽管中国在政治上仍面临改革,但在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注:参见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中国的崛起”,载《外交事务》, Vo172,No.5 (1993年11-12月),PP.59-74.)这样,在美国主导权的鼓吹者看来,美国主导权长期战略的最迫切的问题是防止中国霸权的出现,因为中国将有能力主导欧亚大陆。(注:Posen and Ross,"Competing U. S.Grand Strategies",P.120;Michael O'Hanlon,Defenese
Planningfor the late 1990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5).)不管中国是否能成为“霸权”国家,是否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主导权,冷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忧虑恰恰从另一方面告诉人们,冷战后的中国比以前更加重要,不能不慎重对待。而中国地位的加强又是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
这里无需一般地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至少,中国经济对中美关系是积极的。虽然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但美国对华贸易已为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不可小视的贡献。如何来理解这一判断?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总量的一半来自出口的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美国出口的重要市场。1991年和1992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分别增加15.2%和13.7%,而同期对发达国家的增长仅为2.6 %和1.8%。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已占对发达国家出口总量的3/5,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总量是对发达国家出口增加额的若干倍。例如,1992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额为200亿美元, 而对发达国家的增长额为46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1991~1992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54%,1993年增长21.5%。仅1992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20%,是向发达国家出口增长率的10倍。(注:上述数字参见Nicholas Lardy,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117.)1996年, 美国成为除香港之外的头号对华投资国。 (注:The U.S.- ChinaBusiness Counci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March 5,1997.)
面对这样的经济前景,经济至上的克林顿总统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采取了比前任更积极的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冷战时期不同,推动经济繁荣和保障安全、推动民主成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or A New Century.May,1997.)
由此可以相信,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已由冷战时期单纯的安全需求变成了冷战结束后的安全与经济双重需求,因此,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实际地位已大大提高。30年来的中美关系证明了这样一点:一个国家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它宣称什么,而在于它拥有什么。
标签:尼克松论文; 军事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苏联总统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里根论文; 上海公报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