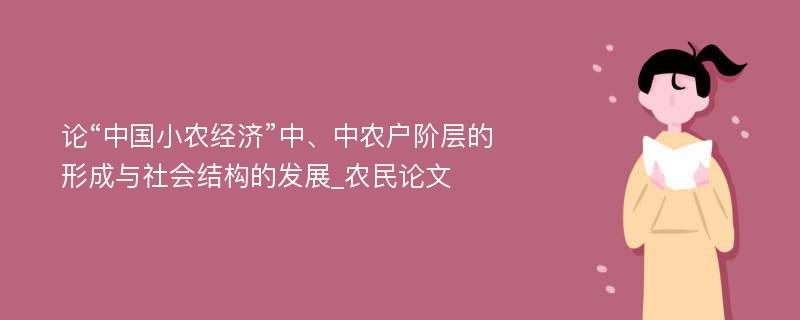
笔谈: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中农阶层与发展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经济论文,笔谈论文,中农论文,阶层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目的是依据农村阶层结构对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性质作出判断。按照历史比较的方法,笔者把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定性为“中度分化的发展型”,其比较的对象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高度分化的贫农经济”和土改之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度均质化的小农经济”。
笔者认为当前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到达了打破“高度均质化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中度分化的发展型”社会结构的阶段。在农业经济领域,发展指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农业劳动的单位报酬递增,克服内卷化的状态。显然发展型社会结构不仅指涉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指涉社会结构本身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发展指的是社会学上通常所指的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过程意味着系统从环境中摄入更多资源提高系统内部的资源分配总量、意味着系统内部各部分互相调适,形成善治秩序。
目前的从阶层角度所考察的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一般采用职业分层方法,学术界持有激烈的批评意见,原因在于农民家庭经济不是像现代工业社会中高度专业化分工那样,农民家庭经济整体上是兼业型的。按照贺雪峰等学者的研究,农户家庭经济的主流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职业分层的方法的另一缺点是无法对阶层之间的关系内容做出分析,因此无法从阶层结构变迁中观察到农村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变迁的逻辑,也就是阶层分析不具有学术解释意义,因此成为孤立的类型学分析。
本文意图克服学术界脱离农村家庭经济性质和孤立的阶层类型分析的弊病,决定通过对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各阶层的分析来达到对农村家庭经济性质的概念化理解和对农村阶层关系所构成的农村社会结构性质的理解。
当前农村各阶层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高度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实在过于庞大,总体上劳动力融入城市化速度又很缓慢,因此大量的农民往返在城乡之间。在城郊农村形成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在中西部大多数地区,则形成离土又离乡的就业模式。
为了彻底打破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循环,新中国成立之后决定走一条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限制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国家通过这一体制为工业化提供大量农业剩余,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内向积累式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限制农民流动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动,农民获得了大量在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从而为农户家庭经济的兼业化提供可能。这一趋势到2000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时达到高潮。
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具有双向的性质。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则表明农民家庭并没有放弃在农村的居所和土地。由于城市非正规就业具有风险性,农村土地上的稳定收入就成为农民家庭经济能够抗击风险的重要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农民选择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的原因。支撑这一双向的农民流动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改革以来的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均分承包的家庭承包制。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农户虽然只拥有“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块土地,然而可以保障基本的温饱水平,能够为农户家庭提供国家无法大规模普惠式供给的社会保障。这是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三农学者反复论证的一个道理。
综上,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高度发展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支撑下,农村社会发生了阶层分化。这一阶层分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经过近20年积累到90年代末,已经达到一个不同于均质化社会结构的阶段,同时由于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农村不可能出现像解放前的高度分化,即处于中度分化。
按照与土地的不同关系,可以把农民分为以下五个基本阶层,分别是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在乡兼业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以及农村贫弱阶层。半工半耕阶层也就是传统上所述的兼业农户,从90年代末以来占据农村家庭经济构成的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土地自发流转,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纯农业户有机会扩大规模成为一个适度规模的主体,从而有可能依靠耕种土地获得不低于兼业的收入。这就是当前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结构因子,我们将之称为“中农”或者“新中农”、“中坚农民”。随着城市化扩张,可以预期能够脱离土地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他们的土地主要流转到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那里,形成种植20~50亩土地的中农阶层。
在中国农村于是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图景:主流阶层是半工半耕阶层,表现为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中老年在家里种地;一部分农民摸爬滚打融入城市,还有一部分正在努力融入城市,他们是脱离土地阶层中的进城户和半进城户;一部分农民在农村劳动分工发展中寻找到就业机会,土地逐渐成为一项无足轻重的兼业,成为在乡兼业户;最后是普通农业经营者由于流入土地而成为中农阶层;此外,还有少数农民则由于因病致贫或其他原因沦为贫弱阶层。
这一社会结构的各阶层之间关系的中心内容就是城市化背景下的阶层之间发生的土地自发流转。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均分承包的小农经营格局下,土地不允许买卖,这保障了阶层之间关系的非竞争性,流出土地的阶层与流入土地的阶层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关系,而是存在人情意义的互动关系。流出土地的阶层将土地放入亲戚朋友那里暂时耕种,在返乡时随时收回。流入土地的阶层获得土地的大部分生产收益,适当对流出农户进行租金补偿或者不补偿。土地制度的理性安排承包地遏制了小农理性的不足,支撑了良性的阶层互动关系。
以上阐述了当前农村社会的阶层构成,指出半工半耕阶层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和由于土地流转而形成新的结构因子——新中农阶层。本节将充分阐述包含这一阶层的农村社会结构的性质。主流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若存在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那么社会结构就会相对稳定,变迁就会有序,因为中间阶层充当缓冲期和润滑剂功能,维护结构的稳定,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在农村发现的中农阶层是否能够充当这个稳定器和润滑剂呢?中农阶层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本文认为新中农这个社会结构新的因子,既能够维护结构本身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构成,又能够推进结构本身的发展性变迁。
1.农村社会秩序的守护者
谁是农村社会秩序的受益者,谁就是农村社会秩序的守护者。中农阶层对基本的土地制度、基层组织建设、公共品供给的政策最为支持,因为他们的主要利益关系在农村,主要社会关系在农村。脱离土地的阶层与农村长期脱离利益关系,希望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就可以变现,但是这会侵犯到在村耕种土地农民阶层的利益,包括半工半农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和贫弱阶层的利益。在乡兼业阶层对土地利益比较不敏感,他们既可以耕种少量土地获得口粮,又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其主要利益关系在于兼业,因此他们对村庄公益事业缺乏积极性,他们是在农村中的非农化阶层。半工半耕在城乡之间摇摆,受益于农村社会秩序稳定,因为农村是他们最后的退路,然而由于只有中老年人留守在家里,他们缺乏像中农阶层维护公共利益、参与村庄交往和村庄治理的能力。贫弱阶层是村庄中需要照顾的阶层。
农村社会结构一边联结着城市,城市是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始动力,一边还立足于农村小农体系和其上的伦理道德、政治体系。中农阶层长期在乡村中,耕种20~50亩的土地,获得中等水平的收入,过着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乡村生活,中农阶层爱护这种秩序,具有保守性。其表现是对政府主导的资本下乡的排斥,中农本身是中农与资本相互冲突时被发现的。他们希望能够扩大规模,依靠口头约定、低租金、灵活性的土地自发流转,坚决反对资本下乡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在农村中构成中坚力量,在村庄中积极构建熟人社会中的关系,对农民流动、村庄边界开放和市场经济侵蚀后形成冷冰冰的人际关系进行润滑。他们是村庄弱势群体的守护者,比如对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照顾;他们沟通着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与各阶层之间建立合作的而不是竞争性的关系;他们大量进入基层组织体系,填补村治精英流失的力量,遏制基层权力的真空。
2.农村社会发展的接力
把农村看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则城市就属于农村的环境,系统从环境中摄入资源,系统内部形成分配资源的机制。农村社会秩序稳定是农村社会结构发展的基础性前提,农村社会结构发展依靠阶层互动过程中农村从环境中摄入的资源量变大,经验上表现为农村土地资源越来越能够实现自发集中,农村社会秩序在城市化和市场冲击下能够依靠中农阶层崛起的力量得以保障。
依据我们的预测,在城市化发展主导未来20年的背景下,脱离土地的阶层农户数量越来越大,土地自发流转的量越来越大,这样承接土地资源的中农阶层越来越壮大,最终整个社会结构向中农化的结构变迁。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中有10%左右的中农阶层,这个阶层还在继续扩大。在湖北钟祥曙光村调研时发现在大规模外出务工潮的推动下,出现了约15%的中农阶层,脱离土地的阶层达到50%。由于我国城市化还处于中期阶段,未来20年还处于加速时期,到城市化基本完成的时期,我国农村还留下目前人口的一半和劳动力的一半,那么农村主流的阶层就不再是今日的半工半耕阶层,而是中农阶层,他们劳均耕种20亩土地,一个家庭平均耕种40亩土地,就可以不再兼业专心种地。
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外在推力是城市化,城市化通过阶层互动过程中的资源交换来完成对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中农无疑是阶层互动和资源交换的中心,中农阶层是城市化这一外在推力的阶层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承接着城市化间接输入的资源,是村庄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这里区分两种资源交换机制是必要的:一是从城市向农村输入的资源,主要是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以劳动力换来的非农收入,这个非农收入足以让其脱离土地接着放弃土地,土地廉价地释放出来,向其他阶层集中;二是农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资源交换机制,这一机制表现为土地灵活性地向中农阶层集中形成适度规模。城市向脱离土地阶层输入的资源,间接地促进了中农从农村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量,从而总体上增加了农村资源的摄入量,这个增加的过程是各阶层形成有序互动情况下取得的。在没有资本下乡打破这种阶层互动关系的情境下,系统内部依靠这种阶层互动关系规则形成整合。
改革要让社会各阶层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中农阶层的崛起作为一个新事物,表明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的性质是发展型的。中农阶层与农村各阶层之间不是利益的竞争关系,而是共同从外界摄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城市愈加发展、吸纳的劳动力越多,那么中农越来越发展,农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愈高。未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一个发展型的以中农阶层为主体的结构。这个阶层是中国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基础,也是乡村在城市化背景下实现内在发展动力的社会基础力量。因此新中农现象值得关注。
标签:农民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小农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农村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