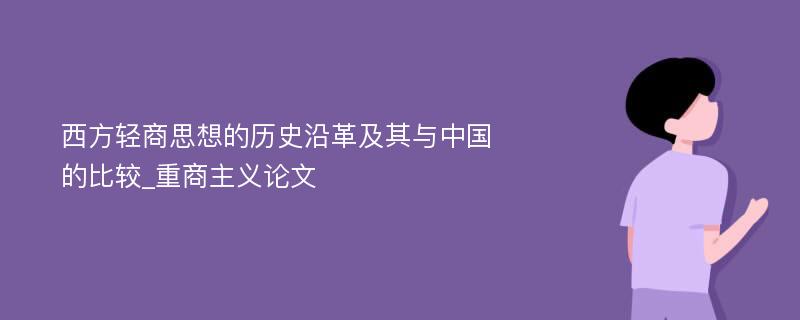
西方轻商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与中国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轻商思想在西方学界不是一个被经常讨论的课题,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来自营销学界,专注于西方社会的“轻营销(prejudice against marketing)”问题[1-4],缺少对西方轻商思想的整体考察。国内学界关于中国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的研究成果颇丰[5-8],但对西方相关问题的关注不多,一些研究虽然涉及了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的轻商思想[9]37-55[10-11],但很少开展专门而系统的讨论。尤其是重商主义时代以后,很多学者认为西方不存在轻商思想,因而对此缺少关注。但本文发现,重商主义并不“重商”。本文对西方轻商思想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整体考察,并将其划分为古希腊罗马的轻商观念、中世纪西欧的轻商思想及其弱化、重商主义时代的轻商观念和重商主义之后的轻商思想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学者对中国轻商思想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中西方的轻商思想进行了比较,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启示。
一、古希腊罗马的轻商观念
西方的轻商思想同经济思想一样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认为商人属于最愚昧无知和微不足道的人,还责难“贸易使纯净的风俗腐败”[12]14。这种轻商思想在他的学生柏拉图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在规划其理想国的蓝图时,非常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的重要性。他在《理想国》中说:“只要每个人……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13]60。但专业化同时带来了交易的困难,“我们是如何彼此交换个人所制造的东西呢?……这种需要产生了一批店老板。那些常住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我们叫他店老板,或者小商人。那些往来于城邦之间做买卖的人,我们称为大商人”[13]61-62。可见,柏拉图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解释了商人存在的必要性。但他同时认为:“这(商业)是些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的”[13]62。在《法篇》第十一卷中,柏拉图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柏拉图认为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行业,因而建议由奴隶或外国人来经商,反对本国公民从事本行业,他说:“如果有公民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卑贱的商业,那么他要为玷污高贵的血统而受到审判”[14]686。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商人弱小、唯利是图和卑贱,从而将其贬斥到社会的最底层。从柏拉图对商人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他对定价、促销、广告等营销行为的看法,他说:“在市场上无论出售什么货物,不能给同一样东西制定两种价格……卖方不能为了促销而赠送,也不能用誓言来保证货物的质量。违反这条法规,任何不小于三十岁的在场公民都可以法律的名义痛打发誓的人”[14]683。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继承了柏拉图对商人的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了商人的剥削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农业、牧业、渔业和狩猎是值得称道的致富方式,它们“顺乎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事属必需,这是可以称道的”[15]31。对于经商,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他说:“(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5]31。他还否定了商人的公民资格,认为:“城邦……不能以从事贱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15]66。商人获取财富的方式只有靠剥削,使他人蒙受损失,因此,市场交换行为也就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不能产生新的财富。这种观念自亚里士多德以后长期存在,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专注于形式效用(form utility),而很少注意到交换效用(exchange utility)或占有效用(possession utility)的存在[1]5。古希腊先哲对待商人的态度逐渐形成了一种轻商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不仅深深渗透在西方主流学术思潮中,甚至对马克思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公元前323)率领他的大军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的马其顿帝国,为希腊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崛起的罗马帝国也成为希腊文明的载体,使希腊文化产生了更加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古希腊哲人的轻商思想也随着希腊文化的传播而得以流传,并统治着人们对商业的认识。跟上述希腊哲人一致,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认为零售商和各类小商贩都是卑贱的、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话就捞不到好处”[16]312。在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中,商业活动往往与偷盗行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商人比盗贼更为恶劣。因此,罗马的商业活动都由最下等的人从事,尤其是伴随战争而来的战利品贸易。这些战利品掌握在罗马上层人士手中,成为天然的商品,但这些商品的经营全部由奴隶和外来人完成[9]15。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他们(罗马人)的气质、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军事教育、他们的政体,使他们远离了贸易”[12]59。
二、中世纪西欧的轻商思想及其弱化
罗马帝国逐渐衰落后,轻商的文化传统依然源远流长。在西罗马灭亡后的中世纪(Middle Ages,约公元5~15世纪),轻商思想在西欧社会统治着人们对商业的认识,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成为商业或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17]46。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其对商业的态度与古希腊罗马并无二致,只是更具有神学色彩。在教会看来,商人难以取悦于上帝,他们的逐利行为是一种罪孽,对于拯救灵魂是危险的[18]79。在这种宗教教规的笼罩下,商业被认为是下等人从事的职业,尤其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13世纪以后,人们对商业的认识有所转变[2]131,基督教的轻商观念似乎开始动摇。宗教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提出了诸多理由为商业利润辩护,如对物品的改进、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之间的价值差额、承担的风险等。阿奎纳实际上指出了运输、仓储、风险等重要的流通功能,并承认商业可以创造部分效用。尽管如此,阿奎纳实质上依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轻商思想。因为在他看来,尽管贸易是必要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通过贸易来发财致富却是罪恶的,商人的货币只是一种便利交换的工具,不应当产生利润,即G-G'是一种无耻的行为。可见,托马斯依然坚持认为商业活动本身有“某种卑鄙的东西”[19]147,因而轻商传统也深深扎根在他的思想中。从根本上讲,阿奎纳尽管已经承认商业承担的重要功能,但未能阐释占有效用这个观念,依然将直接的市场交易视为一种零和游戏[20]。另外,由于运输、仓储等也可以被视为生产过程的延续,因而对这些功能的承认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商业的偏见,如马克思在解释商业的剥削本质时,就将这些功能视为生产功能,而非流通或营销功能[1]5。
中世纪的轻商观念也与人们对财富的认识有关,即认为只有土地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特点是国土的层层分封,将国家分割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封建领地经济或封建庄园。在这种封建制度下,从领主到农奴的每一个层级都依附于土地,唯有土地被视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因此,脱离于土地的商业活动被普遍认为是卑贱的,自然留给了那些外来人(如犹太人)或失去土地的流浪者。
层层分封尽管创造了一个个封闭的封建领地经济,但同时也导致各个封建领地彼此隔阂,形成了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这为游离在封建领地经济之外的商品经济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商人起初可能是从农村的市集中产生的,也可能是从君主的仆从中分化出来的[21]27-29,但商人真正能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出现取决于西欧松散的社会结构和众多失去土地的流浪者和冒险者。①封建庄园之外的流浪者没有土地,只能筚路蓝缕开辟远程贸易通道,穿梭在社会的夹缝中,靠从事商业活动谋生。由于没有固定的寓所,他们也被称为流浪商人或经商的游民[9]130[18]78。毕竟,任何一个领地或庄园都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而且容易受到远方新奇货物的吸引,尤其是领主们对奢侈品的渴求成为流浪商人的天然市场。11世纪前后,西欧人口开始急剧增加,进而使更多的人从封建庄园中游离出来,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浪者[9]117。这些流浪者都首选商业作为谋生之道,并迎来了中世纪商业的繁荣。②商人队伍在壮大的过程中,也在寻求安身立命之地,他们选择了那些交通便利,又能保证货物和钱财安全的地方,即城镇和城堡[18]87。经过商人的不断经营和改造,城镇和城堡演变为城市,带来中世纪城市经济的兴起,③而城市作为一种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制度结构必然会削弱封建领地制度。至此,商人阶层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不仅拥有自由和谋生之道,而且拥有了立足之地,发展成为除教士和贵族之外第三特权阶级,即市民阶级。他们享有商业特许权和城市自治权,这对封建庄园内的农奴非常具有诱惑力,因而成为瓦解封建领主经济的重要力量。但商业特许权和城市自治同时也渗透着封建势力的因素。商业特许权尽管保护了部分商人的利益,但其目的是将商业限制在封建权力可控的范围之内,因而限制了商业的自由发展[22]。城市自治及其行会制度同样也限制了商业的自由发展,阻碍了市场范围的扩大[23]。行会制度是中世纪城市经济的特点,在其产生之初有助于保护城市商业,但同时给市民施加了一种封建式的身份限制[24]318。行会成员被禁止任何的促销活动,如对顾客的劝说行为、惠赠行为、广告等都被认为是不诚实的,并将得到惩罚[3]53。当然,对于教会和封建贵族而言,商业复兴是不幸的,即使非常富有的商人在他们看来也是卑贱的[18]97。
在商业的复兴和市民阶级的壮大过程中,我们看到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也看到了两种思想观念的对立。这表明城市经济的壮大已足以对封建领主经济构成挑战,而商人阶层的兴起也正在改变人们的财富观,对宗教神学构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下也酝酿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后者实现了西欧社会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认为不应该把财富视为罪恶,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唤,在各自的职业中追求与获取财富,此为上帝所允许并加以支持的[25]。因此,商人的逐利行为已经不再被认为有违上帝了。随之兴起重商主义使商人得到了更尊贵的地位。但重商主义依然将商业视为一种零和游戏,重视国际贸易而非国内贸易,强调通过贸易顺差来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重商主义所关心的是国家财富的增长问题,其产生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
三、民族国家的形成与重商主义时代的轻商观念
中世纪西欧在对国土层层分封的同时,也导致了权力和政府的分割,因而国家成了“一个松懈的领土集合体”[26]324。集合体中的每个领主对自己的领地都有独立的统治权,摆脱了对国王的依赖,甚至使国王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摆设。每个封建领地的居民都与外界隔离,与其他领地的居民“没有共同的命运,没有共同的国家,他们并不成为一个人民整体”[27]79。因此,“国家”也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对领主而言,“国家”可有可无,任何领主都可以带领手下造反[26]302[28]7-9。而且,在每个松散的集合体之上是统治着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会,在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中,欧洲各国都臣服于罗马教廷,失去了各自的民族独立性。可见,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普遍缺乏民族或国家意识的时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政权统一的国家,所谓国家或民族也都是一些地理概念而已。“‘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波西米亚’等等主要是一些地理概念,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波西米亚人’等等也主要表示他出生在哪一块土地上,而很少带有民族区分的意义”[28]9。这种分割的封建领地制度在11~15世纪达到鼎盛,但该时期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兴起又成为瓦解这种制度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商品经济的不断渗透和城市经济的兴起,改变了封建领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况,并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商人,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给教会和教皇的宗教神权造成重创,为民族国家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支持。一方面,中世纪的城市制度显然是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商人和市民都要遭受封建领主和教会的限制,而王权也因封建割据势力和教皇的制约而形同虚设,因此,市民与国王有共同的利益,成为对抗封建领主势力和教皇的天然结盟[29]448。国王以此为契机,依靠壮大起来的城市力量击垮了封建贵族和教皇,实现了中央集权,做到了国家的统一[24]317。国王或君主成了国家主权的象征,真正意义的“国家”也随之产生了。另一方面,西欧卷入了争夺控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贸易路线的争斗之中,战争频发,费用之剧增令人惊愕30]140。当然,战争也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此背景下,建立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政治组织实体,已是大势所趋。
民族国家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尽管学界对民族国家的定义莫衷一是,但可以看出,这个概念生来就具有极其浓重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并发展成为重商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31]27。民族主义决定了民族国家的好战和侵略性,因此“侵略或所谓‘防务’就成了政策的重点”[19]231。为此,国家必须储备足够的贵金属为战争和防御做准备,因为在当时缺少能够迅速积聚资金的手段或方法[32]。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社会根源,西方有学者认为“重商主义时代就是从急需提供从事近代初期这一伟大民族斗争所需中诞生的”[30]166。民族国家成立后,爱国主义高涨,国家的发展成为重大课题,这在当时看来,需要众多的金银货币来刺激投资和就业[20]90。但一个国家金银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必须通过对外掠夺或对外贸易增加本国贵金属货币的数量,显然,后者是最佳选择,即通过商品出口换回金银,这就是重商主义的历史起源。重商主义极其重视金属货币,强调通过贸易顺差增加自身的金银数量。后来的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大师都认为重商主义把货币当做唯一的财富,并进行了严酷的批判,如穆勒直言重商主义的这种认识“引导欧洲的政策走上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道路”[33]14。但这种批判过于偏颇[19]549,如上所述,重商主义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无论是对于战争和防御的需要还是刺激国内经济的需要,贵金属都是最重要的财富。因此,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贸易顺差将会增加国家的财富,而贸易逆差将会减少国家的财富,贸易双方必然有得有失。由此,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再次附体,即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收益即另一方之损失”[19]548。正是秉持了这种观点,重商主义对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merchants)表示尊敬和爱戴,而对国内零售商或中间商人(middlemen)④则表示蔑视[2]131[20]90,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内贸易不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任何净收益。正如托马斯·孟在其被誉为重商主义圣经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所指出的:“倘使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交换(国内贸易),国家是不能由此增加财富的,因为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倘使我们是与外人交换的,那么我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34]51。显然,在重商主义看来,国内商业是不能创造财富的。不仅如此,重商主义者还认为,消费也会导致国家财富的减少,尤其斥责对进口奢侈品的消费,因而节俭也成为重商主义普遍遵循的一个信条[32]274。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消费的广告、促销等营销行为也是会被排斥的。这似乎是从亚里士多德经由中世纪的行会制度遗留下来的。总之,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上文得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即重商主义在“重商”的同时,依然继承了轻商的文化传统。实际上,重商主义重视的是国际贸易,同时轻视国内贸易,因为他们将贸易视为一种零和游戏。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本质,对内无比忠诚,对外又无比残忍,为了让自己国家更加富裕,高度赞扬通过贸易这种“邪恶”的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西欧的民族国家开展了全世界范围的掠夺和奴役运动。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我国就成为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受害者。⑤
四、重商主义之后的轻商思想
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西欧各国都通过政府的强制干预追求贸易顺差,这在当时确实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到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批判重商主义的弊端,宣传自由贸易思想,如威廉·配第(1623~1687)、达德利·诺斯(1641~1691)、大卫·休谟(1711~1776)等。他们对贸易的认识开始有所转变,如休谟(1741)在批判重商主义时指出:“将所有的贸易国都视为自己的对手,总以为其他国家的繁荣必定会使本国受到损失。和这种充满敌意的狭隘观点相反,我敢断定,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及财富的增长一般来说不仅对所有邻国的商业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没有损害,反而会有所帮助”[35]107。这表明休谟没有将贸易视为零和游戏。18世纪以后,市场交易增加财富或创造价值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36],人们逐渐克服了将商业视为零和游戏的偏见。然而,也正是从18世纪开始,经济学研究的重心逐渐偏离了贸易,而是在重农主义的引领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传统,进而使商业研究又被边缘化了。
这一转变萌芽于配第,他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的著名论断[37]71,马克思因此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强调土地和劳动的同时也继承了轻商传统,他在评价商人时说:“这些人本来就得不到社会的好评……他们除了充当促进国家的血液和营养液(即工业及工业的产品)循环的静脉和动脉之外,本身什么也不生产”[37]28。魁奈领导的重农学派跟随配第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农业)生产领域,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他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即从事农业劳动的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从事工商业的不生产阶级。可见,魁奈也表达了一种轻商观念,认为工商业是不生产的。⑥在魁奈的自然秩序中,商业活动或商品流通过程可以无阻碍的完成,因而无须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在魁奈的自然秩序和经济表中,流通过程都被抽象掉了。魁奈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因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很少看到专门针对具体商品流通过程的研究。
五、中西方轻商思想的比较
有趣的是,魁奈对农工商的认识与中国的“重农轻工商”思想颇为相似。他还以树根和枝叶之间的关系来形容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完全可从中国古代的“农本工商末”思想中找到蓝本[38]。魁奈所处的时代正是18世纪中国文化在法国广泛传播的时期,法国人极为崇尚中国的商品和文化,掀起了“中国热”。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也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强烈冲击,并以儒学为思想武器向宗教神学发起进攻。魁奈是启蒙思想家中杰出的一位,也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尤其崇尚孔子,他所著《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对中国进行了全盘的赞扬和肯定,并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由此可见,魁奈的轻商思想也有可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轻商思想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圣人。从儒家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看,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等儒学圣人虽然承认商业存在的必要性,但却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7]43。他们只认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合理性,而对商业持有一种贬低态度。这一点与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是基本一致的。战国时期,轻商思想经李悝、商鞅、荀子等的倡导和强化,由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系统地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和“强本抑末”的理论[6]24-25。秦汉时期,轻商思想已经被诉诸治国政策中,秦始皇首次将重本抑末作为诏令公布,把商人视同罪犯;汉高祖发布贱商令,商人不准穿好衣服,不准乘马骑车,不准占有土地等[8]21。“秦汉之后,儒法合流,儒家提供了伦理依据,法家提供了政治经验,重农抑商成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从桑弘羊的盐铁官营、平准策,到王安石的‘青苗’、‘均输’诸法,再到明太祖、康熙帝的禁海、禁矿诸令,都严重抑制着商业的发展”[7]44。总之,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相互促进,合二为一,成为阻碍我国商业发展的桎梏。
西欧社会将轻商思想诉诸国策中的情形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显然也是存在的,如前文提及的古罗马法律体系中,把商人同盗贼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恶劣。罗马实施的抑商政策在帝国后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釜底抽薪式的榨干商人的钱财,导致商人陷入贫困境地;另一方面颁布了许多抑商的法律政策,导致商人阶层的萎缩甚至消失[9]19-21。但在西罗马灭亡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表现出与中国古代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是层层分封,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封建领地,为了维护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每个领主会严格限制商业的发展,但他们的掌控范围只能局限在自己的庄园或领地之内,这就给领地之外的流浪商人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西欧的商业复兴和商人阶层的兴起主要得益于那些不受封建领主限制的流浪商人。因此,西欧封建庄园经济的瓦解是由外向内开展的。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自上而下森严而不可分割的等级体系,与西欧社会的松散结构形成鲜明对比,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和统一体,这是中国在西方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中国古代森严的封建等级体系中没有商人发展壮大的空间,因而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商人阶层,商人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封建特权。西欧社会在商人阶层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新式的经济制度,即城市经济,其主体是市民阶级,也被称为除教士和贵族之外第三特权阶级。这是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必经阶段,而中国由于缺少有力的商人阶层而没有形成类似的城市经济制度。因此,当18、19世纪西方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中国依然固守于封建王权。在森严的封建制度下,中国的轻商传统自然是顽固不化的,而西欧的轻商思想则随着商人阶层的壮大而逐渐削弱。当然,西欧社会并没有彻底摆脱轻商观念的束缚,重商主义者依然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重商主义之后形成的经济学传统始终没有将国内贸易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传统的始作俑者是魁奈,在他的经济学框架中,贸易或商品流通过程被认为是自动完成的,因而无需做专门研究。魁奈认为商品流通可以自动完成的这一预设来自他的自然秩序和自由贸易主义思想,因此他坚决支持商业自由放任的发展。也就是说,魁奈认为商业不创造价值的同时,却又支持任其自由发展。可见,轻视商业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其自由发展[5]54。而封建社会的中国把这种思想落实到了国策之中,不仅思想上轻商,而且实践上抑商和贱商。尽管不排除魁奈的轻商思想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魁奈轻商而任其自由发展的思想与中国轻商而又抑商的思想是不同的[40]。
六、小结与启示
轻商观念在西欧社会是长期存在的,从古希腊哲人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商业都被认为是卑贱的,并演变为一种轻商文化。但中世纪松散的社会结构为这种卑微职业创造了无限的发展空间,使之成为后起之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壮大,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最终导致了西欧社会的转型。尽管如此,轻商文化并没有被彻底瓦解。贸易乃“零和游戏”这一从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观念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成了重商主义的治国方略,认为海外贸易可以为国家致富,而国内贸易却徒劳无功。这种偏见可能是欧洲学界不重视国内贸易研究的一个原因。
中国由于森严的封建等级体系,没有形成类似西欧的独立商人阶层,轻商文化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落实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国策中。商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是中国落后于西欧社会的最直接原因,而商业发展滞后是由更加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导致的。当然,制度差异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例如,从独特的地理条件来看,⑦“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迥异的关键”[21]37。古希腊城邦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24]66,而“地中海已卓然成为联结生产力颇不相同的各国的一条公路”[21]37。因此,欧洲很早就产生了广泛开展海外贸易的传统。其实,中世纪的流浪商人多从事国际贸易或远程贸易,并由此从外向内瓦解了封建制度。
不同于欧洲,古代中国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不能发展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中国的地缘优势是地大物博,本可以在同一政权的统治下建立国内的统一市场,大力发展国内贸易。但遗憾的是,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完全压制了国内贸易或商业的发展。同样是地大物博的美国自建国之日起就没有轻商思想的包袱,而其19世纪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国内贸易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轻商思想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但国内市场分割的现状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尤其是加入WTO后,国际贸易一直是主角,而国内贸易一直是配角。这一战略导向是需要转变的。
注释:
①中国古代不缺少类似前两类的商人,但中国的封建制度不同于西欧的层层分封,前者在整体上是一个森严而紧密的等级体系,而非松散的社会结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能使商人壮大的发展空间,使商人难以从政府的权力中独立出来并形成强有力的商人阶层(一些著名的商帮可能都是依附于政府的,因而注定不能基业长青)。
②当然,中世纪商业的繁荣还要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生产力的提升带来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动摇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使人们不再盲从宗教神学,而转向更世俗的理性思考。这就在经济和思想观念两个方面促使更多的人从事经商。
③中世纪的城镇或城堡对于重视土地财富的封建领主和贵族而言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被废弃的。但成为商人的立足之地后,这些旧城就立刻展现了新的生命活力。随着商人在旧城的聚集,超出其容纳能力,很多商人就在旧城外围建立新的商业基地,这样,新的商业基地与旧城相互融合,城市就诞生了。
④“中间商(middleman)”这个术语在西方有一种被贬低的含义,表示平庸而没有两边重要[1]6。
⑤欧洲盛行重商主义的同时,中国正以茶叶和陶瓷等商品闻名于世,欧洲国家对中国商品的狂热导致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大量的贵金属货币流入中国,中国甚至被称为“欧洲货币之墓”。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这直接导致了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为了扭转这种局势,西方国家想到了充满邪恶的鸦片贸易。
⑥这是学界对魁奈的普遍认识,但也有学者认为魁奈后期转变了这种看法,承认工商业也是生产的[39]161-162。
⑦希克斯说:“欧洲城邦是地中海的恩赐……它有许许多多孤立的小块区域,冷僻的角落、岛屿、海岬和溪谷,这些在同样的条件下一向是容易防御的。亚洲就没有完全类似这样的条件”[21]37。
标签:重商主义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古希腊论文; 中世纪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