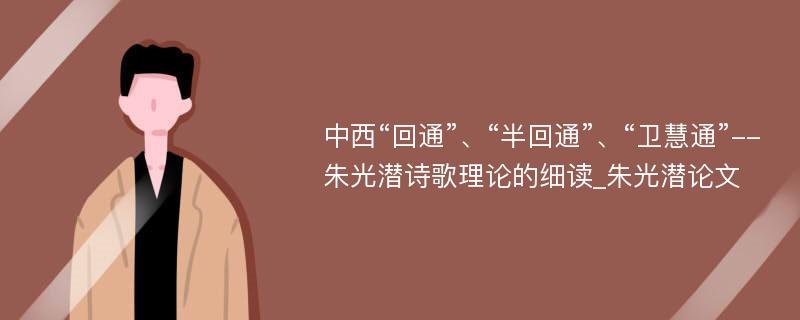
中西“汇通”、“半汇通”及“未汇通”——朱光潜《诗论》的方法论细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通论文,方法论论文,中西论文,诗论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0-0120-09
一
朱光潜晚年回眸其一生美学建树,有两段话颇堪玩味。一是坦承“研究美学主要是解放前的事,无论从质看还是从量看,解放前的著作都较重要”①;二是在1949年前的著述中,最令其“敝帚自珍”的②,“还是这本《诗论》”③。可见《诗论》在朱光潜心头的分量之沉。
朱光潜如此珍视《诗论》的理由是:“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立见解。”细想亦对,无论朱光潜在1949年前作为审美心理学家(代表作是《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还是1949年后作为美学史家(代表作是《西方美学史》上下卷),其特点,皆是在远离故土的思辨天际构筑“纯概念”城堡。唯独撰《诗论》,近乎魂兮归来,重新亲近秦楼汉月,“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④在其学涯另辟一条“中西汇通”之路。
“中西汇通”,作为“比较文学”方法,旨在寻觅中西文学元素之间的比对关系。所谓比对,是指经交互比照而证明彼此间有对应。此对应样式有二:“血缘”型与“非血缘”型。“血缘”一词在此属借代,它喻指国别文学元素之间曾有过的“影响”与“被影响”事实,那是做“影响”比较的法国学派所重视的。做“平行”比较的美国学派则着意“非血缘”现象。当叶维廉倡言“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⑤,这也恰巧合乎其美籍华裔的学者名分及学科背景。这就是说,两种文学谱系全然可在异质语境独自演化,但各自未必不含某种“文学所以为文学”的普世“共相”。这一普世“共相”之存在,可以说为“中西汇通”者在深层次掘出颇具价值的,既跨文化、跨国度,却又为中西文学所“共同的美学据点”⑥,提供了可能。
然“可能”还不是“现实”。“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转为“现实”,这不仅取决于勤奋,还往往受制于才情、睿智甚至天分。这就是说,无论是欲觅普世“共相”,还是精湛地诠释国粹特色,关键看怎样操练“汇通”。“汇通”一词,实可拆成“汇”、“通”二字。若将“汇”释为国别文学元素的“并置”或“碰撞”,“通”则可释为彼此间“比对”关系之成立。于是,很显然,“汇”与“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律,“汇”并不无条件地导向“通”。其必要前提是能否精准地回答:我所做的那个“比较文学”目的是什么?其有效与否,当取决于“比对”,而“比对”之前提,则取决于明白“我是谁?我到底要什么?”这是评判“比对”有否意义之基准,这也是生死攸关之法则。做“比较文学”,就其方法论而言,道理归一。
二
明乎此,就能弄清《诗论》究竟何处成功及其成功秘诀。《诗论》秘诀首先在于:作者明智地将主攻方向定为,用近代西学来阐明古汉诗的国粹特色是音律之美。其实质,是为他立论“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⑦,夯实学理基础。
朱光潜一眼认准古汉诗异质于西方诗的美学特征是在“音律”,这很内行。这不是说西方诗无音律,而是说古汉诗律,经齐梁至唐,已臻化境:抑扬顿挫的音调,鲜明的节奏,前呼后应的谐和韵脚,及其词语、句式的对仗等,使诗兴的传递极富“声入心通”的音乐感。诗律的内核是声律。可以说,汉语四声语音所蕴藉的音乐潜质,通过平仄相异的声调交互所形成的丰繁格式,已焕发到极致。近体律诗所以蔚然而成中国文学的辉煌星座,音形兼美的诗律可谓居功至伟。这是西方诗所无可企及的。
古汉诗律(音律)精妙绝伦,这是事实。古今诗人不乏将诗律玩得炉火纯青者,却很少有人用学理去系统解析诗律为何能“声人心通”,这也是事实。从欧阳修《六一诗话》到王国维《人间词话》,连绵千年未做成的事,到朱光潜撰《诗论》,首战告捷,功莫大焉。
《诗论》重在对古汉诗律(音律)做“中西汇通”。这从书的述学布局便可见出。全书十三章,除末章“陶渊明”属附骥之尾,其余十二章,有八章直接或间接有涉音律,占全书三分之二。在有涉音律的八章中,又用整整五章专论古汉诗律,依次“论声”,“论顿”,“论韵”,论“赋对于诗的影响”,论“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之后”。
朱光潜确乎有能耐对古汉诗作“中西汇通”。“中西汇通”在这儿,实是“比较文学”的别称。诗学不是诗话。诗学作为概念系统,其“任务就在替关于诗的事实寻出理由”⑧,即对“诗何以为诗”给出逻辑建构,以阐明诗作为事实为何能以如此样式存在。这就规避了传统诗话常见的偶感式或随笔体,“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却难免“零乱琐碎,不成系统”。⑨朱光潜在草拟《诗论》纲要前,已在英、法、德留学八年(1925-1933),现代学术的严格规训,足以让他担当此责。诚然,更重要的是,在草拟《诗论》前,朱光潜已撰《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二书,他所看到的西方诗暨诗学等“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⑩,这就为他做好古汉诗律的“中西汇通”,铺设了厚实的台阶。
三
在朱光潜看来,包括古汉诗在内的诗律的核心是音乐性节奏,它是一切音响(含语音)在单位时间的有序停顿与起伏所造成的延绵性听觉美感。这既是诗从原始图腾、祭祀歌舞的混沌母腹带来的、不曾被岁月抹去的胎记,也是朱光潜认同诗、乐、舞原初“同源”的美学标记。(11)当《诗论》第一章“诗的起源”,特标明“《诗经》的‘颂’原训‘舞容’”,以及“《风》、《雅》、《颂》以音别”,(12)其动机亦在说明古汉诗律的根是节奏,而源头也可上溯到原始歌舞。只是“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意义方面发展”(13)罢了。中西诗律,莫一例外。
国人对古汉诗律的审美体认,若落到具体个人,也大体是从对“节奏”的身心感应起步的。这从先秦孔记诗教到清末桐城私塾“正蒙”(14),一脉相承。诗卷在握,一唱三叹,继而摆首晃脑,诗篇声“谐”便顺耳,不顺则“拗”。这里试从“节奏的谐与拗”楔入(15),来见证朱光潜对古汉诗律的“中西汇通”之成功。
传统诗教大多是从经验出发,以为谨遵声调“平仄”模型便“谐”,否则即“拗”。这当然不是诗学。学术要尊重经验与事实,然更须追问它“为何如是”。这便导致学术与经验在面对同一事实时,后者觉得无话可说,前者却可说一整套,且合情理。
为何吟诗能“声入心通”?为何诗韵“谐”便顺耳,否则便“拗”?朱光潜是用谷鲁斯“内模仿”理论来解说的。日常经验很熟悉人能“外模仿”,比如“看见山时我们不知不觉地挺胸昂首;看见杨柳轻盈摇荡时,我们也不知不觉轻松舒畅起来”(16)。这转移到听觉系统,便是:“听一曲低而柔缓的调子,心力与筋肉也随之作一种低而柔缓的话动。”(17)什么叫“声入心通”?似乎这就是。
但这是低层次的“声入心通”。还有高层次“声入心通”,这就亟需用“内模仿”说来解释。“内模仿”说之要害在于:它强调人“把模仿冲动加以精神化”(18),即把动作性“外模仿”积淀为心理模型内存于心,且以此为尺度来自动制约内在感应及审美感受。朱光潜正是在此意义上用“内模仿”说的。他说:“诗与音乐的节奏常有一种‘模型’(pattern),在变化中有整齐,流动生展却常回旋到出发点,所以我们说它有规律。这‘模型’印到心里也就形成了一种心理的模型,我们不知不觉地准备着照这个模型去适应,去花费心力,去调节注意力的张弛与筋肉的伸缩。”(19)
以此来看“谐与拗”,也就茅塞顿开。无非是内化为心理图式的音律模型,已自动预设了吟者或听众的听觉定势,这就像听“京戏或鼓书,如果演奏者艺术完美,我们便觉得每字音的长短、高低、疾徐都恰到好处,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如果某句落去一板或是某板出乎情理地高一点或低一点,我们的全身筋肉就猛然感到一种不愉快的震撼”。这就意味着,当你“听见的音调与筋肉所打的板眼相合,与注意力的松紧调剂,与所准备的适应方法没有差讹,我们便觉得‘谐’,否则便觉得‘拗’”。 (20)这都是谷鲁斯的“内模仿”在起作用。
所谓“内模仿”,在此拟可解读为“模仿内”,即只有当外部对象演绎得合乎主体所内置的现存图式时,主体才会认同或赞赏。于是,“内模仿”之发生,与其说是源于主体对外部对象的观赏,毋宁说是主体欲借外部对象来印证内在图式的存在价值。由此再来体会“谐与拗”的顺耳与否,此“耳”也绝非指与生俱来的、纯生理性听觉器官,而分明是青年马克思所说的“音乐的耳朵”了。
用谷鲁斯的“内模仿”说来解析“谐与拗”,无疑是《诗论》之成功。此成功,不仅是指朱光潜将历代诗话未说清的事说明白了,它更是指在浩如烟海的近代西学中觅得谷鲁斯来深层次地纾解“谐与拗”,真可谓“对症下药”。“对症”,是指朱光潜别具慧眼,确认了“内模仿”说跟“谐与拗”有“比对”关系;“下药”,也就是“内模仿”说所蕴涵的理论能量作为方法,恰好契合了“谐与拗”这一对象的诗学期待。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中西汇通”:在作为方法的西学与作为对象的中国问题之间,未见阻隔,倒呈交融。这儿既未见王国维曾告诫的西学新名词“滥用”(21),也没预演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所流行的生吞活剥西学之怪现象。实不容易。
四
时下做“中西汇通”者,常有此患:即当他把某西学奉为方法,来诠释中国经验及问题时,并不先慎重地考量彼此“比对”关系在何种水平及程度上可能成立,便仓促地将前者视作“模子”,硬套在后者上。结果,你说不清那个“比较文学”,到底是旨在阐明中国现象而引用西学呢?还是不惮扭曲乃至肢解中国对象,来反证西学的高明?……相比之下,《诗论》绝无自我矮化的“西崽相”。当朱光潜经香港,再从爱丁堡游学伦敦及柏林,簇拥而来的全是近现代西学,然朱光潜既不激进排外,亦不盲目崇洋,他是常怀一颗平常心,视中西学术皆为天下公器,有一份材料,一份真实的心得,就说一份话。比如朱光潜以古汉诗为证,判莱辛“诗画异质”说有误,便是范例。这是《诗论》“中西汇通”成功之三。
莱辛《拉奥孔》是西方美学经典,“他在欧洲是第一个人看出艺术与媒介(如形色之于图画,语言之于文学)的重要关联”,从而终结了“诗画同质说的笼统含混”;从此,“艺术在理论上才有明显的分野”。(22)此即莱辛的“诗画异质”说。
其实,“诗画同质”抑或“诗画异质”,皆不宜作绝对之论,全看你从什么视角楔入来谈。世上从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任何理论皆在其所预设的语境内才被判为有效。若着眼于诗、画皆属艺术,而艺术全赖于“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从此出,画也从此出”(23),这无疑是“诗画同质”。这是用克罗齐“直觉”说看艺术时的观点。但基于同一情趣丰盈的内心意象,到了诗人或画家的笔下,会被诉诸不同媒介,“就是对于诗画兼长者,可用画表现的不必都能用诗表现,可用诗表现的也不必都能用画表现”(24)。毕竟画所诉诸的线条与色彩可直接吸引观众的眼球,而诗所诉诸的语符只能通过再造想象,间接地在读者心里唤起符合文字所描绘的图景。从这一角度楔入,莱辛说“诗画异质”,亦不无理由。
莱辛《拉奥孔》之迷人,还在于作者将“拉奥孔”这尊雕像,置于罗马诗人维吉尔《伊尼特》所呈示的史诗语境去作比较,使其“诗画异质”说尤显例证丰富,雄辩动人:“据史诗,拉奥孔在被捆时放声号叫;在雕像中他的面孔只表现一种轻微的叹息,具有希腊艺术所特有的恬静与肃穆。为什么雕像的作者不表现诗人所描写的号啕呢?希腊人在诗中并不怕表现苦痛,而在造形艺术中却永远避免痛感所产生的面孔筋肉挛曲的丑状。”(25)究其因,无非史诗是用文字描写号啕,而文字是非直观的,它只在时间中流逝,故不会像雕塑那般在空间直观地去定格“很难看的狞恶的挛曲”,(26)造成“视觉污染”。
若莱辛讲“诗画异质”,讲到这儿,见好就收,就没事了。但莱辛想追求理论的“彻底”,由此推导如下结论:“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相并立的事物叫做‘物体’(body),因此,物体和它们的看得见的属性是图画的特殊题材。全体或部分在时间上相承续的事物叫做‘动作’(action),因此,动作是诗的特殊题材。”(27)简言之,“画只宜于描写静物,诗只宜于叙述动作”(28)。这就把话说绝对了。真理因多走半步,而成谬误。
朱光潜一下便道出莱辛的破绽:“艺术受媒介的限制,固无可讳言。但是艺术最大的成功往往在征服媒介的困难。”(29)这更无可讳言。因为“画家用形色而能产生语言声音的效果,诗人用语言声音而能产生形色的效果,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只略读杜工部、苏东坡诸人题画的诗,就可以知道画家对于他们仿佛是在讲故事。我们只略读陶、谢、王、韦诸工于写景的诗人的诗集,就可以知道诗里有比画里更精致的图画”(30)。
更有意思的是,莱辛不是断言诗不宜像画那般在空间“历数事物形象”吗?(31)朱光潜随手便从国粹宝典拈来一组清词丽句,皆取“写物赋”这一技法,其实质是“意象叠加”,然乍看皆似在空间并列“物体”:比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贺铸的“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32)在这些古汉诗面前,莱辛公式之“不甚精确”(33),已无须赘言。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用古汉诗(中国经验)去针砭莱辛(西学)之欠缺,这本是“中西汇通”的分内事,但不多见,朱光潜有此示范,对国人启迪不浅。“西学东渐”这一背景,并未强求国人应以西学为坐标来规范中国经验,而仅仅激励国人可在远比传统遥深的理论视野来拓展眼界。西学即使有精粹值得国人虚怀师承,弟子也未必事事皆不如师。“教学相长”,当是“中西汇通”之常态。然不知从何时起,国人似更愿将西学视作解析中国经验之方法,却忘了西学之不完善,也会在中国经验面前露馅。朱光潜所以能揭莱辛的短,是因为莱辛本有其短,对此,朱光潜瞄得极准。他说,立论“诗画异质”之莱辛“虽是新风气的开导者”(34),但其艺术理念,仍沿袭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老调子:“艺术即模仿”。亚里士多德《诗学》曾言:“模仿的对象是动作”;于是莱辛说:“诗只适宜于叙述动作”。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立论背景是古希腊戏剧与史诗,故强调“动作”,无可厚非;但“近代诗日向抒情写景两方面发展”(35),莱辛再对“诗画异质”作绝对机械之切割,也就未免落伍。
五
一首古汉诗(无论长调,还是小令),作为文本在读者眼前缓缓展开,若作逻辑剖析,总有三个层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语符—语音”层;其次是“语象造型”层,最后是“整体意蕴”层。这与国故所言“技、艺、道”三分法大体暗合。“语符—语音”直接关涉诗的媒介和形式,朱光潜所重视的“音律的谐与拗”、“语言节奏与音乐节奏”、“诗画同质抑或诗画异质”诸现象,皆是“技”层次所衍生的。“语象造型”属于“艺”层次,在《诗论》那儿,重点是落在“意象与情趣的契合”(36)。“整体意蕴”则接近“道”层次,若此诗确实传递出王国维所标举的精神高度,“力争第一义”即“境界”的话。(37)
笔者在前文已论证朱光潜在“技”层面做诗的“中西汇通”,实绩斐然。现在深入到“艺”层面,看看《诗论》面对“意象与情趣”一案时,“中西汇通”得怎样。
“意象与情趣”,顾名思义,旨在探幽“意象与情趣”之间的诗学关联。此关联应是有机的,互逆的,既可从“意象”汲得“情趣”,亦可追思“情趣”如何演绎为“意象”。当然,也可让“意象”、“情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诗论》所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下简称“情趣”)一章即此,作者是撇开“意象”,从文化学角度楔入,单对“情趣”作“中西汇通”。
从国别文化谱系高度来俯瞰中西诗的“情趣”差异,这就像远离大地的高空航拍,其效果不外是宏观写意,浑涵印象。大色块,粗线条,有大局观,厚重感,可为嗣后的微观个案探幽提供概观性参照,然终究不宜替代文本细读,从经典性“意象”汲得“情趣”。事实上,“情趣”的功夫是落在“题材”层面,“其中最重要者有(一)人伦(二)自然(三)宗教和哲学几种”。(38)朱光潜毕竟负笈欧洲八年,14岁前在桐城于国故有“童子功”,故无论耳闻目染,还是漫卷诗书,都让他有底气对中西诗的情趣比较,给出有味道且聪明的评述。
比如言及“人伦”题材,他指出“男女恋爱”在古汉诗所占份额及分量,远不如“友朋交谊”来得重,究实质,是因为“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39)这不是说古汉诗“不能深于情”,而是“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40)
又如在“自然”题材,古汉诗与西方诗相比,“一个以委婉、微妙简隽胜,一个以直率、深刻铺陈胜”(41)。“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这当然只就其大概说。西方未尝没有柔性美的诗,中国也未尝没有刚性美的诗,但西方诗的柔和中国诗的刚都不是它们的本色特长。”(42)
未了,作者表示:“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诗所能及,但是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43)原因呢?朱光潜直指“民族性”。他眼中的“民族性”,颇接近鲁迅的“国民性”,但未将其视作宗法礼教的牺牲品,而是归咎为华夏民族“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内化所致:(44)
就民族性说,中国人颇类似古罗马人,处处都脚踏实地走,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所以就哲学说,伦理的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就文学说,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而凭虚结构的作品则寥若晨星。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45)
朱光潜所概述的民族文化谱系,一旦内化为历代诗人的精神襟怀,便累积成中西诗在“情趣”方面的巨大落差。“情趣”结论如下:
哲学思想平易,所以无法在冲突中寻出调和,不能造成一个可以寄托心灵的理想世界。宗教情操淡薄,所以缺乏“坚持的努力”,苟安于现世而无心在理想世界求寄托,求安慰。屈原、阮籍、李白诸人在中国诗人中是比较能抬头向高远处张望的,他们都曾经向中国诗人所不常去的境界去探险,但是民族性的累太重,他们刚飞到半天空就落下地。所以在西方诗人心中的另一世界的渴求能产生《天国》,《失乐园》、《浮士德》诸杰作,而在中国诗人心中的另一世界的渴求只能产生《远游》、《咏怀诗》、《游仙诗》和《古风》一些简单零碎的短诗。(40)
中国诗达到幽美的境界而没有达到伟大的境界,也正由于此。(41)
朱光潜在七十年前对古汉诗“情趣”所作的郑重评判,至今尤作黄钟雷鸣。然鉴于述学样式,这终究是从宏观文化学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从微观诗学,即通过对经典性“意象”系列的细深勘探来坐实的。故“情趣”的若干语段写得愈激越,愈抑扬顿挫(这并非朱的述学本色),就愈让人不敢轻易采信。这就像覆盖地球的卫星导航定位,它给出的信息再有价值,最后仍得靠你脚踏实地去验证。这就是说,背靠文化学的“情趣”对古汉诗的“中西汇通”,其实做了“一半”。“这一半”很重要,但不是更重要。好在“情趣”仅属《诗论》之“附”,更重要的“另一半”,尚有待朱光潜以其正版《诗论》来做实做深。
六
现在可以来说说“半汇通”了。
所以置“半汇通”这一概念,是为了谨防“比较文学”尤其是“平行比较”,被平庸化乃至庸俗化。“平行比较”不是将国别文学元素作机械“并置”或“碰撞”。这充其量是“汇”,还不是“通”。以此为坐标,再看朱光潜对中西诗的“情趣”比较,笔者有理由说:即使从文化学所推导的、因受制于国故的“思想平易与宗教淡薄”,古汉诗只能“幽美”而无法“伟大”,其在逻辑上是顺的;但也务必明白,上述一切仍属文化学之“假说”,它本身还得靠诗学来“圆说”。故曰“半汇通”。
诗学对古汉诗“情趣”之圆说,只有一条路:让“情趣”回到与“意象”的共生框架里去。用朱光潜的语式,这叫重觅“意象与情趣的契合”。(42)
一首诗,若在艺术上还称得上是“诗”,“意象与情趣的契合”,当是其“必要条件”。这就决定了诗之“情趣”,犹如融水之乳,体匿味存,与“意象”须臾不分。解析古汉诗尤其如此。一个在现代学术语境长成的专家,要能体认历代诗人凝冻在文言音律中的“情趣”,除了破译“意象”,别无他途。这是所有古汉诗研究者的基本功。朱光潜亦无例外。
面对“意象与情趣的契合”一案,朱光潜也尝试着“中西汇通”。有的做得较实,有的未必。当他译介克罗齐关于“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的说法,且将克氏“意象”转述为诗境之“景”,进而提出,包括古汉诗在内的“诗的境界是情景的契合”(43),粗看不错。它让人联想王国维曾言:“一切景语皆情语。”(44)鉴于“情景相生”之诗境本属艺术创造,故“景是各人性格和情趣的返照。情趣不同则景象虽似而实不同”(45)。比如陶潜的“悠然见南山”,当有别于李白的“惟有敬亭山”,亦有别于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更不是姜白石的“数峰清苦”。简言之,“每人所见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创造的”(46)。这一切,都颇好。好就好在:既开掘了克罗齐“意象”说与古汉诗景语造型的“汇通”渠道,又印证了古汉诗(田园题材)“意象与情趣”之间的静态对应。
所以注明“静态对应”,因为这是从鉴赏论角度所确认的“意象与情趣的契合”。这是一个已明摆在眼前的事实。然这一“契合”事实又从何处而来?这就亟需从创作论角度,去追溯诗人“情趣”是如何演化出“意象”的?这么一来,“意象与情趣的契合”之述学,就“静态对应”型转而为“动态演化”型。
也正是在这节骨眼上,可让朱光潜展示其名家风范的时候,读者发现:他失语了。在应该可说许多话的地方,他没说什么,却又“王顾左右而言他”。问题出在他所“任举二短诗”上:一曰崔颢《长干曲》;一曰王维《鹿柴》。(53)他说不出如上两诗“意象”究竟是从何“情趣”演化所致。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相问,或恐是同乡。”崔颢诗区区二十字,写活了一个漂泊他乡的船女,在异地向异性探寻乡音时,心头泛起的那份微妙的悸动。前三句是“妾”的主动提问(行为层),后一句则在时态上同步并置“妾”提问时的瞬间心跳(心理层)。这是另种纯心理(而非地理)水平的“近乡情更怯”。且不论此诗句法的深层结构几近预演了乔伊斯“意识流”技巧,笔者只想说,若析出此诗“意象”的“情趣”所系,没准还真能让此个案来参证朱光潜的所谓“民族性”,确实从精神深层制约着古汉诗只能“幽美”,无法“伟大”呢!
着眼于题材类型,将崔颢诗概述为“他乡遇故知”,似无大错。“他乡遇故知”,为何能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和“久旱逢甘霖”,列为举国认同的“人生四大快事”?说到底,这是植根于内陆型中古农业文明所孕育的宗法文化想象所致。若曰“洞房花烛夜”可为宗族子嗣香火,“金榜题名时”是在光宗耀祖,“久旱逢甘霖”是因农耕受制于风水气象;那么,“他乡遇故知”则是“安土重迁”的游子格外渴望乡音的温润,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也。不难揣摩,正是活在崔颢心底的那份情系现世一人伦的“民族性”,驱使他将“妾”这一“意象”抒写得那般精致、细深、灵动且立体。这儿没有“伟大”,却真有诱人微醺的“幽美”。
本来,这番话应由朱光潜在七十年前说的,可惜他没说,反倒祭出克罗齐“直觉”说,将崔颢诗、王维诗泛泛地概括为“都是从混整的悠久而流动的人生世相中摄取来的一刹那”,因“艺术灌注了生命给它,它便成为终古”。(54)且不说王维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表现孤独者徒闻空谷足音,却未睹人影,那种既亲近又渺茫的心理境况,与崔颢诗的意蕴指向差别甚大,又怎能将两者捆绑一团?人们只须问:因“这两首诗都俨然是戏景,是画境”(55),故值得赞美,那么,流芳千年的古汉诗,哪首又不“俨然是戏景,是画境”?若每首古汉诗皆是,那么,朱对崔颢诗、王维诗说的好话,说了也白说。因为他只从审美心理学角度抽象地、形式地交代,诗作为“意象与情趣的契合”在落笔前,皆像“戏景”、“画境”在脑海闪现;(56)唯独未从诗学角度说清“情趣”在诗人心中,是如何具体地、有内涵地生成鲜活的“意象”。于是,他所请出的克罗齐“直觉”说,与崔颢诗、王维诗之间,也就不存在“比对”关系。它们不过是在《诗论》的同一章节或同一页面作机械“并置”或“碰撞”,却永远谈不拢。这叫“汇而未通”。
用克罗齐“直觉”说,无法阐明古汉诗如何让“情趣”生成“意象”。就症状而言,这是“专业不对口”:即“直觉”说的真正贡献在于,它是现代西学最早确认诗人在将“意象”诉诸笔墨前,他已在心里“见”到了它。诗人用心眼“见”到的“意象”实是即将分娩的胎儿,并非胎儿在母腹的发育进程。然考察古汉诗如何让“情趣”生成“意象”,重点正在其“进程”性。这就是说,“直觉”说作为方法所具备的阐释能量,与它所面对的、古汉诗“情趣”如何生成“意象”这一对象之间,没有“比对”关系。故“直觉”说不是真能阐释后者的“方法”,后者也不是能被“直觉”说所阐明的“对象”。
方法论上的这一“专业不对口”,症结仍在于作者未看清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谁?它到底要什么?《诗论》所以能在“技”层面,成功地阐明古汉诗的若干形式问题,是因为找准了西学“方法”与国故“对象”之间的“比对”关系,做到了“中西汇通”;相反,它所以未能在“艺”层面同样成功地阐明古汉诗“情趣”对“意象”的动态演化,是因为未找准西学“方法”与国故“对象”之间的“比对”关系,故只能流连于“半汇通”。
七
朱光潜因找不着“方法”与“对象”的“比对”关系,而铸成其“中西汇通”打折扣乃至无效,并非偶然。他在建构克罗齐“情趣—意象”说与王国维“境界”说之间的“共相”通道时,同样看走了眼。
《诗论》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这一标题已预示一切。作者所以把王国维“境界”和克氏“情趣与意象”径直相连,大约是基于如下预判:即王国维“境界”与宗白华“艺境”实属同义词,或是对同一概念的类似命名。
宗白华“艺境”全称为“艺术意境”,出自其刊于1943年的一篇论文《论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由于“艺术意境”含“意境”一词,而后者曾被王国维用作对“境界”概念的另一命名,故学界大多视这对术语指归为一,忽略了彼此间的细微转义。(57)宗白华亦然。(58)然要害尚不在此。要害在于:当宗白华信手拈来“意境—境界”这对因《人间词话》而流行的术语时,既没注明出处,也不在王国维语境内演绎这对词语,而是注入了自己的理解。他是仅仅借这二词来作自己的概念。
于是,识者发现,宗白华笔下的“艺术意境”,也确乎与克罗齐“情趣—意象”说,属异曲同工。当宗白华说,“艺术境界”就是“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体化”;(59)且进而概括:“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60)这近乎是克罗齐“情趣—意象”说的现代汉语版。
宗白华与朱光潜的最大区别是:当宗白华借“意境—境界”这对词语瓶子来灌自己的诗学心得时,他不曾说王国维也有此意,故他一点也没错;相反朱光潜明明是与宗白华所见略同,却申明这同时也是“王静安标举‘境界’二字”之意(61),这就未免失真。
朱光潜阐释其“诗的境界”,理据大体有三:
A.“一种境界是否能成为诗的境界”,全靠“见”的程度;而“诗的‘见’必为‘直觉’(intuition)”(62)。故“一个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完整的形象,就还不成为诗的境界”(63)。
B.“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64)
C.“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着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干,在有限中寓无限。”(65)
综上所述,可谓A讲朱氏“境界”发生的心理前提是“直觉”,这当与克罗齐接轨了;B讲朱氏“境界”的诗艺构成不离“情”、“景”二字,这几乎在复述克罗齐;C触及朱氏“境界”的传世意蕴,即诗为何能对历代读者起道德影响。就方法论角度讲,A、B是从审美心理学楔入“直觉”和“情—景”,这是朱光潜在1933年前很娴熟的视角;C则稍带文化价值论的眼光,惜语焉不详。这里所以作此概括,是为了针对性地重温王国维“境界”,看看它与朱氏“境界”到底是否一回事。
大凡真正读通《人间词话》者不难认同,推动王国维建构包括“境界”说在内的“人本—艺术美学”的第一内驱力,当源自其青春期,想以艺术创造暨欣赏来超越个体忧生之心灵苦痛。这一思辨基点落到“境界”说,也就转为王国维衡定诗词有否“境界”的诗学尺度在于:看其作品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诗人对宇宙人生的遥深体悟。其间,从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到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再到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王国维依次铺设了“境界”自“趣→性→魂”逐级递升的诗学模型,“境界”也就由此分大小,却“不以是而分优劣”,(66)即皆美。简言之,“境界”在青年王国维那儿,首先指向诗艺之“内美”(67),“美”在诗人能从宇宙角度领悟人生真谛,且由此判其精神高度,以此来比照朱氏理据A,可鉴王国维是将其“境界”置于文化价值论框架来透视的,而不曾放到审美心理学水平去探究“境界”与克罗齐“直觉”有何牵连。
接着比照朱氏理据B。《人间词话》对“情—景”关系曾有论及,但王国维似未将“情—景”交融视作“境界”构成的本体性特征。比如王国维激赏牛峤之“甘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顾复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等,皆“专作情语而绝妙者”,(68)无疑是上“境界”的,但又确是有“情”而无“景”。故王国维“境界”说与克罗齐“情趣—意象”说也大体无涉。
诚然,王国维还有“意境”说,称“文学主事,其内足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69)若有人在此愿将王国维之“意”比对克罗齐之“情”,王国维之“境”比对克罗齐之“景”,不算牵强,然在逻辑上,这已不是拿王国维“境界”说,而是拿其“意境”说,来与克罗齐作“中西汇通”了。
再来比照朱氏理据C。正是在这个朱光潜说不了几句话的地方,王国维能说好多。简约地讲,也有三点。一是天才之作能臻“境界”,旨在其“内美”关乎人生感悟之深邃。二是此“内美”之操作,在于“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内”,乃诗人在日常境遇中所积累的人生体验(素材)。“入乎其内”,就是将曾牵动诗人衷肠的、毛茸茸的素材体验再三,“故有生气”。“出乎其外”,即诗人若想写出杰作,还得不拘泥于素材原型,要将此放到终极关怀层面作审美关照,“故有高致”。美成词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堪称一流,为何在王国维心中仍比“至情至性”的苏、辛低一档次?因为他“能入而不能出”(70)。或曰“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71)。“意”者,“境界”所系也。三是“独能洞见”与“独有千古”。在王国维看来,“天才”虽也像普通人不时痛感人生缺陷,但普通人的神经太粗,“虽有大疑大患,不足以撄其心”,“天才”则悟性太高,“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于是就活得特苦,特累,偏偏“人世有限之快乐其不足慰藉彼也明矣”,最后“不得不反而求诸自己”(72)——王国维所称道的稼轩正是这样,他虽负雄才,然生不逢时,一腔忠愤,无处可泄,便索性将其悲抑一寄于词,倒也“俊伟幽咽,独有千古”。(73)若借朱光潜的话说,此亦近乎“在刹那中见终古”了。
然此“终古”或“千古”诗境,在朱光潜那儿,只作想象式远眺。但在王国维那儿,却是筑了诗学台阶,一步步拾级而上,直取峰巅的。这已进入诗的“道”层次。朱光潜撰《诗论》,还不曾有此眼界,他擅长诗的“技”层次,偶尔亦玩诗的“艺”层次。在这“道”层次,他已说不上克罗齐还有否对应性遗产,可拿来与王国维“境界”说作“中西汇通”了。
记得王国维在百年前曾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者,而西学能兴者。”(74)做“中西汇通”的比较文学界,恐更应将此铭刻于心。
注释:
①②朱光潜致陈望衡函,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46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③《诗论·后记》,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3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④《诗论·后记》,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31页。
⑤⑥温儒敏、李细尧编:《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第20、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⑦《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12页。
⑧⑨⑩《诗论·抗战版序》,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3、4页。
(11)(12)(13)(15)(16)(17)(19)(20)《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3、15、16、126、126、125、125、127页。
(14)朱光潜自6-14岁随父读书,其父执教私塾,恪守传统学馆套式。
(18)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18章第3节“谷鲁斯”,第6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1)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11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22)(23)(24)(25)(26)(27)(28)(29)(30)(31)(32)(33)《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46-147、137、137-138、140、140、141、141、150、150、151、151-152、150页。
(34)(35)(36)(38)(39)(40)(41)(42)(43)(44)(45)《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47、147、153、74、75、76、77、77、79、78、79页。
(37)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71页。
(46)(47)(48)(49)(51)(52)《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83、86、53、54-55、55、55页。
(50)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85页。
(53)(54)(55)(56)《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9-50、50、50、50页。
(57)参见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6-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8)(59)(60)宗白华:《美学散步》,第59、59、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1)(62)(63)(64)(65)《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50、51、52、54、50页。
(66)(67)(68)《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50、383、373页。
(69)(70)(71)(72)(73)(74)《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97、367、357、71、361、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