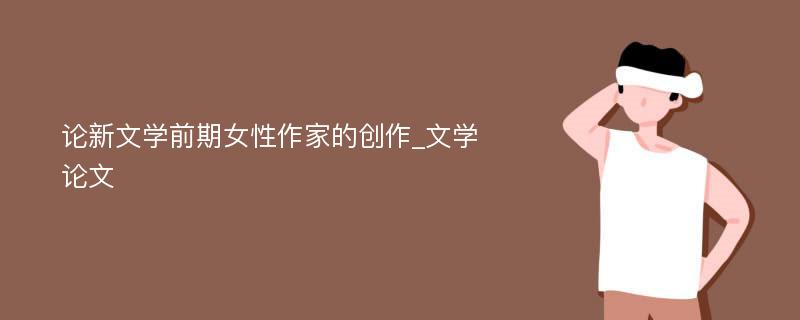
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创作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初期论文,作家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新文学初期女性文学的崛起、女性作家创作的特质及其差异性的横向思考与多向审视,简要地勾画出了五四以来女性文学创作产生、流变的轨迹,探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
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舞文弄墨似乎已成了男人的专利。能在深闺发出“凄凄惨惨戚戚”的低回之音的女才子,寥若晨星。封建礼教压抑着女性个性才智的正常发展,形成她们迥异于男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的心理特征和个性差异。古代文学史上所谓“闺阁文学”,充其量不过是男性文学的附属品。
或许正是这几千年的压抑沉寂,使得在新文学之初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现更具有了一种拨雾看花的美感效应。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林徽音……这一连串名噪一时的名字,被赫然写在新文学史的首页上,她们的作品虽然仍抹不去历史的深深烙印及初创期的稚嫩,但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尘烟的涤荡,那清新热烈的生命气息,激越跳动的青春脉搏却仍清晰如故。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尽管以各自独具个性的创作在新文学园地中各领风骚,然而共同的时代氛围,相似的身份地位,大体一致的文学和人生追求,又使她们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
本文试图通过对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和女性作家创作的异同及对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的创作进行一番横向思考与审视,并结合对现当代女性文学现象的分析,纵向探讨女性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跨入现代化行列的“过渡时代”①,五四运动又是在欧美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很自然地成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胡适的《贞操问题》和吴虞的《女权评议》等文章,都将妇女解放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讨论,并纳入当时思想解放、文化革命的主流。他们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女妇女运动的学说和著作。此外,一些妇女刊物,如《女界钟》、《新妇女》、《妇女声》等也应运而生。许多报纸纷纷开设“妇女问题”专栏,往集论文,展开讨论。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后,几乎当时所有的小说家都写过取材于妇女问题的小说。妇女解放气候的酝酿,使得一些被封建文化、伦理道德压抑的知识女性脱颖而出。正如冰心所说:“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洗礼,使她们走出深闺,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为进一步登上文坛作了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的历史契机,没有妇女解放运动促使知识妇女的觉醒,没有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就没有女性文学的崛起。
当然,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还有其自身的原因。她们大都是名门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或是不满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要求个性解放而离家出走的“娜拉”;或是远涉重洋,接受异域文化熏陶归来的新女性。也正是由于女作家们自身的努力,使女性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她们既共同打破了传统闺阁文学的狭小圈子,走到了时代思潮的前列,表现出刚刚挣脱羁绊与束缚的解脱意识,同时又带有难以泯灭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在二者冲突中由破到立的思想演讲的复杂性;加上女作家艺术素质的参差不均,在其创作上则体现出一种共同的文学土壤上奇葩纷呈的多彩局面,呈现出来自不同艺术视野的或深或浅的艺术开掘。
二
纵观五四女作家的创作,问题小说可以说是她们笔锋的共置点。从大的角度,可以将这些创作题材概括为两大类:一是爱情婚姻题材小说的创作,二是在爱的哲学的观照下人生问题的艺术反映。当然,爱情也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然而在五四女性作家的心理天平上,重于一切的不是由母爱、童心自然构筑的真善美的世界,便是纯洁美丽而忧伤的男欢女爱的爱情砝码。对于爱情题材的着力关注已使这类爱情小说在人生的横断面上获得了较为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内涵,她们用一连串优美委婉的爱的音符和旋律,或大胆,或谨慎,或热烈,或隐蔽地吟唱着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爱情描写体现了中国现代女性从爱的觉醒到爱的渴望,再到性的苦闷、爱的冲突的心理发展进程。在创作中则表现为从轻视低级的肉欲泛滥、崇尚高尚纯洁的精神恋爱到追求灵肉一致的现代爱情的一种逐层深入提高的发展轨迹。她们勇敢地在创作中发出了爱的呼唤。大胆直言的冯沅君的《隔绝》抒写了“第一次上最甜蜜的爱的功课的一夜”③的白薇,借琳丽之口表达了对性爱的强烈奔放的渴望。甚至连冰心这位“静如止水,穆如秋风”的女性也在她的《疯人笔记》中描绘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传达了新的性爱信息。
然而,不同于同时代不少男性作家如郁达夫、张资平等对于那种赤裸裸的情欲苦闷、性行为以及狎妓、纵欲、近亲通奸的描写,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男女性爱,极少触及两性肉体关系,对低级的肉欲泛滥,她们采取轻视甚至是鄙视的态度。在冯沅君的创作中有一种值得深思的“话语空缺”现象,常常出现一些删节号代替一些表示性关系的词语,如“夫妻、结婚、离婚”等等。每行文至此,就表现出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语态。在《旋行》中写到同行男女虽然开了两个房间,但男的那间“简直是作样子的”,“好象我们就是……,其实,除了法律同……的关系,我们……”④破译删节号的钥匙便是女作家心目中神秘纯洁的精神恋爱。在五四女作家眼中,只要顺应爱欲本身要求,便是合理的,值得赞美的,而违背这种爱欲,即使名分相合,也是罪恶。在庐隐的《父亲》里,父亲对庶母合法的欺骗和占有,显得丑陋可鄙,而儿子对庶母的爱情则如墓地上的玫瑰一样纯洁美丽。在现实中并非合理的“理”的压抑阻挠下,“情”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男女之间或同性之间的超越于情欲发泄需要之上的高尚纯洁的精神恋爱。精神的相通,心灵的交融又恰与放荡无耻的肉欲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五四女性作家还写到了少女之间的同性恋。同性恋在社会意义、价值取向上的地位我们姑且不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同性恋描写,亦是五四时期女性性爱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这种同性之间的爱恋只要是合乎爱欲要求的真实表现,便同样是合理的,美好的。庐隐《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与沅清之所以发生同性恋,是基于青年女子对于某种特殊情感的迫切要求:“人类生活,若缺乏情感的点缀,便要常泛于干枯的境地了”⑤。而此种情感,在异性那里却难以得到,“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⑥。生理、心理的需要不能在常态下得到满足,便会以病态甚至变态的方式寻求发泄,所以同性恋现象的实质是肯定性爱的意义。同性之间并不可能达到一种全身心的交合,因此,究其实质也只是精神恋爱的另一种形式。然而,真正圆满的爱情不仅是精神上的亲近,爱情同时也应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的使人能够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相互倾慕与交往之情”⑦。那种飘忽抽象的精神恋爱是一种残缺的爱,并不能满足爱的理想的真实实现;同时,这种心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往往与世欲社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往往会受到来自社会和个人的重重阻挠。“同性的恋爱,终究不被社会的人认可,我希望你还是早些觉悟吧!”⑧丽石在痛苦寂寞的心灵失落中身体消耗殆尽。陈衡哲在《洛绮思的问题》写到了瓦德教授与洛绮思、马昆与西克夫人之间不求诸肉欲结合的相爱,然而,只追求精神默契的苦恋既不能消除洛绮思事业成功之后的寂寞,也无法排遣西克夫人守寡后晚景的凄凉。性与欲的困惑与冲突,在新文学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被升华为对灵肉和谐一致的真正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从而使作品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白薇开始正面呼唤爱情:“人性最深妙的美,好象只存在两性之间”⑨。苏雪林笔下的杜醒秋经历了人间的波折“万念俱灰”,皈依宗教,但最终还是同未婚夫和好结婚,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棘心》)。即便是庐隐笔下那个对一切都冷漠的露沙在与梓青经历了一段精神恋爱的反反复复之后,也要寻求一种与爱人比翼双飞的真正和谐美满的幸福,而到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表现出更加狂烈、更为大胆的“灵肉一致”的性爱意识,她“把握到现代人心中的苦闷”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灵肉一致”的饥渴呼唤。然而,软弱无力的苇弟,庸俗不堪的凌吉士,使得现代女作家们不得不对这海市蜃楼般的爱情理想说声“再见”《再见》(凌叔华)五四女作家那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极富浪漫色彩的爱的罗曼史至《莎菲女士的日记》就画上了句号,面对她们的是吃喝住穿、养家活口的琐屑而又现实的人生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新文学初期女作家爱情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情爱生活领域。寻求爱情的自由解放是女性反封建斗争的第一步,她们往往“能够把题材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亲情、性爱以及由此滋生的关于个人情智上的困扰推而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11)。女性文学中性爱意识的觉醒同对旧制度的揭露批判和对一切违背人性的事物的挞伐是结合在一起的。
三
前文提到,五四时期是一个觉醒与苦闷、追求与迷惘、激动与感伤、抗争与颓唐互相交织的过渡时代。面对山河破碎、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青年们“不能寻得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便常感到人生之无意义和无价值,于是想寻找一个信仰,以使发生倾斜的心灵获得平衡”(12)。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们在寻求真爱、追求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同时,也在参与和履行着改造社会的责任与使命。她们既不同于共产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也不是遁入空门、皈依宗教抑或放浪形骸、游戏人间,而是以母爱作为净化心灵的清泉,在无邪的童心世界中寻求慰藉,歌颂世外桃源的自然美,开出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爱的哲学这一救世药方。她们寻觅到的“真理,就是一个‘爱’字!”(13)“让世界充满爱!”这既是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共同的人生理想,也是在爱情婚姻题材之外又一个永恒的创作主题。
母爱,是冰心诗集《繁星》、《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贯穿始终的思想与情感红线。在苏雪林的笔下,“慈母的一片真挚爱心细细写刻在每件衣服的褶缝里”,石评梅则吟唱出“母怀是我们永久倚凭的柱梁”(14),母爱作为人们回避冷酷黑暗现实的避难所,作为拯救世界的药剂,被新文学初期的女作家施用于现实人生。白薇的《苏斐》,试图用爱去平息恨,凭借爱的哲学使冲突得到解决。在冰心的《超人》中,母爱的神奇力量促使了冷心肠的青年何彬的思想转变。然而,母爱的力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庐隐的《余泪》中那结束女教师生命的一枪宣告了爱的哲学的破产。
童心永驻可以说是五四女作家们的一个共同点,晶莹剔透的童心世界始终是女作家们最真的追求。冰心说:“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可爱的》)绿漪在《给儿子的通信》、《小儿银翅蝴蝶的故事》中,用活泼跳动的童心的眼光观察自然界的事物和生灵。陈衡哲的寓言体作品《西风》和《小雨点》中的西风和小雨点便是一种童心的象征物,《孟哥哥》等小说则以天真烂漫之心观察大千世界。从儿童心理、口吻来描写成人世界,那排除了一切世俗平庸的超凡脱俗的纯洁也体现了一种童贞美。凌叔华的《小歌儿俩》刻画了一些儿童形象,写出了孩子们的纯真无邪,反衬了现实社会的丑恶、龌龊。
在沉重现实的压抑下,女作家们循着母爱与童心之间扯不断的血缘纽带,将自己的理想、天性、愿望都艺术地投射到童心世界中。和母爱、童心一样,女作家笔下的自然仍然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象镜子般照射出现实的黑暗、丑陋,寄托着女作家们对于美好理想的追求。
新文学初期的女性作家在五四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和男性作家一样,担负着作为人,作为作家所承担的反映社会,改造社会的神圣职责,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向腐朽的社会制度。她们多侧面地鞭笞旧社会,批判自我,希望以爱的哲学为基础建立一个新世界、新自我。尽管爱的哲学有点罗曼蒂克色彩,有些模糊,但它毕竟是对传统的决绝与分裂,是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一支独具特色的文学力量。
四
五四女性作家或来自豪门巨族,或来自乡野穷巷,发出的或是海外归来女性的呼喊,或是一群迥异于男性文学创作的壮丽合唱。在女性性别共性特征之下又显示了各具匠心的独特追求。
(一)对女性个体性别特征的强调
这首先表现为女性作家对女性主人公形象的热切关注。从作品数量上来看,庐隐的作品中有十分之八写女性;冯沅君的作品更是百分之百地塑造女性主人公;陈衡哲的集子《小雨点》也有十分之六写女性;冰心的作品更是多从现实出发,表现女性的愿望、情操、命运,阐释对妇女人格独立的看法。女作家们写女子的母爱、情爱,写女学生的学习生活,写贫女不幸的半生,以各自独特的感受理解描写女子。这种对性别特征的强调尤其表现在婚恋题材小说的创作中。
其次是作品中所具有的强烈而又细腻的感情色彩。文学离不开情感,女性在这方面更具得天独厚的天赋。作品多用第一人称,把自己的情感娓娓融入作品,使人感到亲切自然。女性作家们运用适合表现她们的经历、情感、心理感受的语言形式,表达缠绵的感情波动。作品较少客观描写,多主观抒情。女性作家们常常创造出一种具有浓郁感情色彩的抒情气氛来表达五四青年女性潜隐意绪的流动和缠绵感情的波动。
第三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是一种自传体,创作上多采用书信体或日记体,显示了女作家浓重的女性主体意识。郁达夫曾说过,“文学作品无非是作家的自叙传”,女性角色的特质,使女性作家往往更擅长写自己,这也是与自我情感抒发的方便联系在一起的。
(二)在个性化追求下的艺术挖掘呈现出一种发散型特点
五四时期是个力倡个性追求的历史时期,基于女性角色独特的文学视角,女性作家在女性文学这面共擎的大旗下,显示出色彩纷呈的个性创作特色,显示了各自赏心悦目的艺术视焦点及艺术挖掘点。
首先,题材选择,各施其长。陈衡哲采用寓言体形式创作了《西风》、《小雨点》、《运河与扬子江》等一系列象征性题材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用母爱、童贞、自然来对抗黑暗现实的文学和人生追求的理想,即便是涉及到妇女解放问题的写实性作品,如《巫峡里的一个女子》等,陈衡哲也并不直接揭示现实生活的严酷性,而是通过远离人群的一对男女的遭遇来作曲折的表现。陈衡哲多采用一种超现实的方式来反映现实,以悲天悯人的态度,以拯救众生的博大胸怀,在象征世界里描绘爱的理想天国,将人道主义与造命思想相结合,礼赞“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造命精神”,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冯沅君在题材选择上进行了着力追求,“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矛盾,展示给读者,她的创作不象冰心笔下“爱的哲学”的空洞说教,也不象庐隐那样如孤雁哀鸣,而是表现“拔心不死”的热烈追求与激烈反抗。冯沅君笔下的爱情故事本是要表现五四主流意识形态的完美性与崇高性,然而却恰恰由此暴露了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脆弱性、不完满性,尤其是暴露了它所遮蔽的女性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对作家个人而言,也可以说是时代意识洪流将冯沅君推上文坛,传统重负与学者生活方式又将她拉回书斋。凌叔华则闹中取静,选取了封建家庭影壁屏风后的生活内幕,向人们讲述五四妇女之外的闺门故事,表现这些温婉女性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人际遭遇,以叙写转型期中国妇女生存处境和心路历程的个性特色立于女作家之林。颇具眼光和忧患意识的凌叔华没有慷慨歌颂妇女解放的先锋们如何挣脱旧家庭的束缚获得自由和解放,而总是着眼于人物的现存状况,即脱离家庭获得初步解放之后,该往何处去?遗憾的是凌叔华对女性主人公面临无路可走的尴尬困窘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答案,而更多的只是对人物先天的精神弱质进行了发掘。与其他女作家偏于向外索取和认同不同,当五四文坛为作家们构筑的自由女性形象陶醉时,凌叔华开始对女性自身意识本位进行注目和审视,虽然这种审视不够深入,比较模糊,也没有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已使新文学的女性形象群雕更富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穿透性,也更富有真实感。
其次,艺术情调和风格追求同中有异。
女性,本身就是一种较具浪漫色彩的性别类型,而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的创作又往往集中在婚姻、爱情、人生追求这些共同母题上,作品中主人公内心思绪的流动,慷慨激昂的感情独白或者大段深入的内心白描,无不使作品烙上了鲜明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由于女作家们大都具有较为深厚的古典文学艺术功底,因而在其创作中浪漫主义色彩又无一例外地浸染了古典诗词的艺术情调。
然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女作家的创作亦是如此。
陈衡哲的寓言体小说呈现出一种空灵晶莹的单纯美,没有大波大澜的起伏情节,采用一种纯白描的手法抒写人物纯净、透明的性格和灵魂;冰心的作品是诗、小说、散文三位一体的创作,她的爱的母题的创作正如熠熠闪光的繁星下一泓温柔的春水慰藉改造着人生;冯沅君、庐隐则以其直露热烈的情感之火、心灵的激烈燃烧,震荡灼人的心扉;凌叔华的作品则象平静的涓涓细流、清澈的泉水将温情与爱心倾注在名门闺秀和中产阶级女性身上。
五
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具有拓荒意义的创作成就不可抹杀,但其创作局限也不容回避,这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时代、历史、社会造成了女作家笔下悲剧性的女性群体
在封建社会,妇女的一切都得维系在男人身上,旧中国的传统女性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永远扮演着琐碎、辛苦、卑微的主妇角色。当五四强劲东风吹起时,妇女们未死的心开始复苏,女性传统意识开始变动。然而女性陈旧落后的深层历史积淀绝不是一两次时代浪潮所能洗刷干净的,“五四”激进的反封建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飘浮在主流意识形态表层的理性觉悟,尚未内化到心理深层中去而真正成为她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她们表面上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馈赠,骨子里积淀的仍旧是陈旧的封建意识,当二者相遇时,就会出现一种异常尴尬的嫁接现象,因而结出的果也是畸形的。冯沅君笔下的爱情与母爱冲突时,就只能发现二者不可得兼的无可奈何的感叹,只有用母爱包容一切。在凌叔华笔下的小刘的激进时代先锋的表象下掩盖的是内质不堪一击的虚弱,在结婚之后,因耽溺于家庭琐事而变得面目全非。同时,这也是一种女性性别的悲剧,女性没有作为“人”的意识,没有作为人的独立性,没有人格独立的前提,侈谈爱情、婚姻、自由、解放、平等全是徒劳。在整个社会尚处于一片混沌时,为数尚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几声呐喊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女性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的觉醒与更新同步进行时,女性的解放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二)女作家自身的局限使她们停留于“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初诊阶段
相对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女作家视野比较狭窄,对现实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青年(尤其是女性)的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思考的表面化在女作家的作品中表现为对妇女命运及悲剧根源剖析的脆弱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作品主人公大多是为人性解放、人格独立进行过勇敢斗争并获得了妇女解放和为人的最初权利的妇女先锋,她们的婚姻也都是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旗帜下缔结的,然而婚后却变得无聊而又无奈,至于造成悲剧命运根源何在?作者没有给出答案。
女性作家创作中这种缺憾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由于五四时期接受运用西方个性解放的理论缺少自身坚实的经济基础,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契合也仅限于表层而并未触动民族文化意识的深层,而对于社会深层意识的改造则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女性意识的改造也不例外。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个性解放思想,在中国短短几十年间得到消化融贯,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这里涉及到获得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时代新女性面临的出路问题,实现自由恋爱与幸福家庭的必要生存条件--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没有在女作家的创作中提及。对于婚恋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女作家们大多采取了一种回避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至于女性深层意识的觉醒,对女性被压抑的个性意识的恢复与弘扬,对妇女所处非人地位的经济物质反抗的反映,只是在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即罗淑的《生人妻》、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中才重笔推出,至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标志着现代女性文学觉醒的最初阶段基本形成。新文学初期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只停留于浅表层的外在觉醒,而没能深入到自审阶段的内部觉醒。
六
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群及其作品的出现,在中国新文学园地上无疑有着开荒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她们的探索与尝试,就没有新时期女性文学蔚为大观的繁荣局面。
纵观五四以后70多年来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小说的演进流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30至60年代时期、近十年来的新时期。女性文学在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种由内--外--内的螺旋形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当一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渐趋成熟,愈来愈向深入发展之时,女作家们往往在文学大潮中固执地滑向自己的轨道,呈现出一种内转现象。
第一阶段女作家的创作以其独具女性特征的阴柔之美,关注女性自身的解放,自身的命运,营构出一个独具魅力的女性化的艺术世界。
到了第二阶段,萧红、罗淑等则是既带有对女性文学传统的顺应与继承,又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和社会的烙印,其作品也和男作家的作品渐趋一致,呈现出一种向外扩展和异化的特色。
经过文革十年沉寂,到了第三阶段,女性作家长期压抑的情感,长期禁锢的女性天地得以打开表现、带有较强的女性主体意识,关注妇女特殊问题和心态的作品,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的《北极光》。新时期女性文学以其纤细、柔美的女性色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女性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又回到女性文学自身,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女性毕竟是女性,违背常态强化女性心理是一种违背人的天性的病态,往往会使创作误入歧途。女性文学的归宿在于女性文学本身,这一点在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独具风采和魅力的艺术创作中可以找到明证。
责任校对 丁勇望 丁一 注释:
①陈衡哲《说过渡时代》《衡哲散文选》开明书店,1938年12月初版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文艺研究》1979.1
③④《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⑥⑧庐隐《海滨故人·归雁》
⑦基里尔·瓦西列夫《情爱论》
⑨白薇《琳丽》
⑩钱谦吾《丁玲》见《中国现代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8月
(11)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
(12)苏雪林(绿漪)《棘心》北新书局,1929年5月
(13)冰心《自由--真理--服务》,《燕京大学学刊》1921年2卷1、2合刊
(14)石评梅《母亲》《涛雨集》北京书局1932年
标签:文学论文; 作家论文; 小说论文; 艺术论文; 莎菲女士的日记论文; 读书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冰心论文; 凌叔华论文; 冯沅君论文; 小雨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