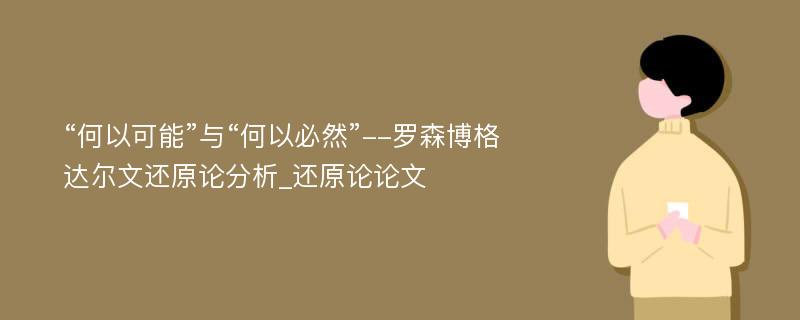
“如何可能”与“为何必然”——对罗森伯格的达尔文式还原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论文,伯格论文,罗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5)08-0020-05 无论是在生物学领域还是在生物学哲学领域,关于还原论的讨论都是近几十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布里甘特(Ingo Brigandt)和洛夫(Alan Love)对生物学中的三种还原论进行了区分:(1)本体论还原,即每一个特定的生物系统(如有机体)都只不过是由分子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2)方法论还原,即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研究生物系统最有成果,生物学实验研究旨在发现分子与生化层面的原因;(3)认识论还原,即关于某一科学领域的较高层次的知识,通常可以还原为另一组更基础层次的知识[1]。 时至今日,本体论还原,也称物理主义①或唯物主义,已经被绝大多数哲学家和生物学家所接受。可能只剩一部分宗教人士仍会诉诸“活力论”或“智能设计”。然而,方法论还原与认识论还原在生物学哲学中仍广受争议。 美国遗传学家与进化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曾有过一句名言:“如果不考虑进化,生物学中的一切都将难以理解。”这句话后来也被称为“杜布赞斯基格言”。很多反还原论者会利用“杜布赞斯基格言”来反驳还原论:如果生物学中的一切都是自然选择运作的结果且自然选择是一个无法还原为物理科学的过程,那么生物学中的一切都将无法完全还原为物理科学,因为至少存在着一些不可还原的余项[2]16。 在当今科学世界,生物学通常可以区分为两类:功能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功能生物学主要研究功能类描述之下的各种现象,如器官、细胞、基因等,而分子生物学则主要研究某些有机大分子。绝大多数还原论的分子生物学家希望把功能生物学还原为分子生物学,而很多功能生物学家则会诉诸20世纪最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之一、现代生物学哲学的奠基人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以及他对于“近因说明”与“终极说明”的二分[3]。例如,要说明为什么向日葵的生长总是朝向太阳,有些生物学家可能会分析向日葵中植物生长激素的浓度分布,这是一个近因说明;然而,进化生物学家可能会从向日葵的进化历史来表明朝向太阳生长的优势,因为这样做会增大向日葵的适应度,而朝向其他方向生长的向日葵最终被自然选择淘汰了,这就是终极说明。 近因说明是要表明某些尚存的生物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而终极说明则要表明,它们为什么能够在进化历史中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涌现出来。很多功能生物学中的说明是终极说明,而分子生物学中的说明往往是近因说明。如果终极说明不能够还原为近因说明,那么功能生物学也不太可能被还原为分子生物学。 二、“如何可能”与“为何必然”:两种生物学说明 美国杜克大学的亚历山大·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教授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学哲学家之一。在《达尔文式还原论:或如何停止担忧并爱上分子生物学》一书中,他试图让读者相信,“天堂确实属于分子生物学家”,同时试图说服非分子生物学家,“在分子生物学家的天堂里,仍为他们保留了空间”[2]1-2。 在《达尔文式还原论》一书中,罗森伯格试图论证,在生物学哲学中,物理主义者必须是还原论者。为此,他提出了“如何可能(how-possible)说明”与“为何必然(why-necessary)说明”的重要二分。如何可能说明是通过列举已有的事实,表明某事如何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毕竟没有很好的理由来设想它不会发生;而为何必然说明则试图表明,被说明项必定会发生[2]43。 罗森伯格坚信这两种说明是不对称的:“一旦有了如何可能说明,继续追问为何必然说明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反之不然。”[2]43因此,为何必然说明应该比如何可能说明更加完备。 在生物学中,几乎所有的功能说明都是如何可能说明,而分子生物学却可以提供为何必然说明。因此,罗森伯格提出了他关于生物学说明的还原论:(1)每个功能性的终极说明都是如何可能说明;(2)在功能性的如何可能说明之下都有着基因的与生化的路径选择的过程;(3)还原把功能性的终极说明中纯粹如何可能的方案,转变成了一种包含于某种历史模式中的为何必然的近因说明[2]46。 必须承认,罗森伯格对如何可能说明与为何必然说明的二分还是很有洞见、颇有说服力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关于生物学说明的还原论问题。本文将提出以下反驳论证: 三、部分说明与说明概略 亨普尔(C.G.Hempel)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为自己的科学说明的覆盖律模型提出了三种变化形式:省略说明、部分说明和说明概略[4]。如果有些定律或初始条件太过明显或众所周知,我们可能会在科学说明中省略相关的定律或条件,这就是“省略说明”。例如,要说明为什么某支笔可以导电,我们只需要说这支笔是金属制成的就可以了,而其实完整的科学说明应该是以下形式: 所有金属都导电。(普遍定律) 这支笔是金属制成的。(初始条件) 因此,这支笔导电。(被说明项) 不过,“所有金属都导电”这一定律对我们来说太过熟悉了,没必要提及,因此在很多情形下,我们会在科学说明中无意识地省略这一定律。 部分说明是指,被说明项只是我们能够从说明项中推导出来的子集。例如对于地震,我们既无法给出完整的事后说明,也无法事先进行精确的预测,但如果我们能够说明或预测某个地区属于地震活跃地带,这仍然可以算是部分说明。 说明概略的情况则更加糟糕:我们既不知道说明项的很多细节,对于其中的律则机制也只是一知半解。然而,说明概略提供了说明的框架或方向,可以指引研究者去做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来补充说明项的相关内容。因此,说明概略也算是一种粗略的说明。 回到罗森伯格的生物学说明还原论,本文试图论证:虽然绝大多数如何可能的功能说明是部分说明,但是也有一些为何必然的分子说明可能只是说明概略。虽然很多分子说明确实比相关的功能说明更加完备,但并不总是如此。在哲学意义上,说明概略可能比部分说明更加粗略。既然说明概略并不比部分说明更加完备,那么功能说明与分子说明至少应该享有平等的认知地位。 在有些章节中,罗森伯格也含蓄地承认了有些为何必然说明可能是说明概略:“(虽然)细节很复杂,但是跟随这些细节会向我们表明,为何必然的近因说明能够兑现如何可能说明所允诺的条款,并且在原则上把终极说明还原为近因说明。”[2]49 罗森伯格可能认为,虽然在当今的生物学中,很多为何必然的近因说明还只是说明概略,但原则上它们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变得更完备。的确,分子生物学中的某些说明概略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变得完整,从而转化为部分说明甚至是完备的说明,但并非所有的说明概略都具备这种潜质。从长远来看,还有一部分也许只能永远地充当说明概略。在物理学中,一些非线性的混沌系统对于初始条件极为敏感,一个开始时微小的扰动也许会使最终的结果发生巨大的改变。考虑到这一点,当我们企图从对于部分的说明中推出对于整体的说明时,近似的存在可能会给这一推导过程带来巨大的困难。生物系统通常被认为比物理系统更加复杂,如果物理学中的可推导性都难以实现的话,那么生物学中的情形很可能会更加糟糕。所以,尽管分子生物学中的一些说明概略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某种前景和展望,但它们仍然不一定真得可以变成完备的说明。 从分子生物学到功能生物学是否具有可推导性以及可预测性,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讨论。 四、近似与可推导性 罗森伯格相信:“对于这一星球上的历史事件与模式,只要科学期望寻找更加完备的说明,以及更大的预测精确性,就需要奉行一种还原论的研究纲领。即生物学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满足于如何可能的终极说明——它必须寻求为何必然的近因说明,而且它必须是在大分子的相互作用中寻求这种说明。”[2]54 为何必然的近因说明往往提供更好的预测与更深的说明。然而,在生物学中是否总是如此呢?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总是能把终极说明还原为近因说明。美国科学哲学家内格尔(Ernest Nagel)提供了理论还原的两个条件:可推导性条件和可连接性条件[5]。因为生物学中功能术语(如基因)的结构多样性与多重可实现性,可连接性条件在生物学哲学中曾引发了很多反还原论的论证。但在这里,我们将聚焦于可推导性条件。 萨卡尔(Sahotra Sarkar)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与保护生物学家,现任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他总结了至少6种近似:(1)近似可能是明确的或隐含的。(2)近似可能是可修正的、在实践中不可修正的或原则上不可修正的。(3)近似的最大效果可能是可估算的、在实践中不可估算的或原则上不可估算的。(4)近似可能涉及到(a)只在数学上有根据的步骤;(b)只在F系统中有根据的步骤②;(c)二者兼具;(d)二者皆无。(5)近似可能是语境依赖的或语境无关的。(6)近似可能包括反事实假定,也可能不包括[6]。 罗森伯格对于从近因说明推导出终极说明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但即使是在物理学中,因为这些近似所带来的问题,从基础说明推导表层说明有时候也会失败[7]。考虑到生物系统所具有的更大的复杂性,在生物学中可推导性将更难实现。 至于预测的精确性,首先,即使在很多分子机制没有被发现之前,功能生物学就有可能提供有效的预测。例如,早在发现光合作用的分子机制的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如何合理地灌溉植物了。 其次,相对于分子生物学而言,功能生物学中的有些说明至少可以提供相同的、甚至是更好的预测。美国生物学哲学家鲁斯(Michael Ruse)曾经提到过一位剑桥的生物学家尼古拉斯·戴维斯(Nicholas Davies)的工作[8]。戴维斯是一名研究林岩鹨(一种体型似麻雀的鸟类)的专家,他所研究的这种鸟类拥有非常复杂的交配方式:有时是一夫一妻制,有时是一夫多妻制,有时是一妻多夫制,还有的时候是群交。通过研究这些不同交配方式的目的或者作用,戴维斯可以很准确地指出某种交配方式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然而,要从分子生物学中推导出这些精确预测可能会非常困难。 五、功能生物学中在为何必然说明中的贡献 虽然罗森伯格坚持认为为何必然说明只能由分子生物学提供,但生物学中的很多为何必然说明实际上是由功能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共同给出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一些生物学说明,它们并不能由分子生物学单独完成。 以脑科学中的研究为例。在这一学科的早期阶段,为了解释大脑的功能,科学家把大脑区分为不同的模块,并认为每一个模块掌管着大脑的某一种功能。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科学家发现,大脑的很多高级功能(例如记忆、注意力和决策等)是通过某种跨越多个模块的神经网络结构来实现的。人类的大脑中大约有一百亿个神经元,其中每个神经元都与其它某些神经元形成特定的联系[9]。分子生物学家在说明神经元内或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机制等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认为,是众多神经元之间的复杂联系造就了大脑的许多高级功能。因此,要完整地说明那些大脑中的高级功能的运作机制,还必须要对该功能所涉及的神经网络中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方式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而这正是目前神经解剖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现代的神经解剖学中大量使用了分子生物学的工具和方法,但总体上来说,神经解剖学仍属于功能生物学的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生物学说明通常会涉及到生物系统中的多个层次,因此很少是一步完成的。分子生物学本身所获取的大量数据并不会必然带来对于宏观现象的有效模型或者说明[10]。在这种情况下,功能生物学在一些为何必然说明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上述现象也进一步说明,在当今生物学的发展中,功能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之间并非界限分明;相反,它们之间相互借鉴、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生物学中越来越多的科学说明将由两者共同完成。 六、反还原论:从“强版本”走向“弱版本” 即使一定要把还原论与反还原论划分为两大阵营,它们各自也应该可以有程度之分。罗森伯格提供了还原论的一种强版本,即“消去主义”(Eliminativism):所有生物学都是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不仅提供说明项,而且发现所有有待说明的事实[2]26。即使在罗森柏格看来,绝大多数哲学家与生物学家也会拒斥这种还原论。 罗森伯格显然认为,自己的还原论研究纲领是弱版本的还原论:生物学说明需要通过分子生物学中更为基础的说明,才能变得完备、得以更正、更加精确或者深入……生物学家应该寻找这样的大分子说明[2]26。 然而,罗森伯格有些地方对还原论的解释还是比较强的:“还原论是这样的命题:生物学理论以及使用它们的说明需要建基于分子生物学,最终是物理科学,因为只有如此,生物学的理论与说明才能提高、更正、加强、更加精确与充分、完备等”[2]4。 在罗森伯格看来,反还原论包括以下正面陈述:(1)在功能生物学的层面有概括总结;(2)这些概括总结具有说明能力;(3)在功能生物学之外再无进一步的概括总结,可以说明功能生物学的概括总结;(4)在功能生物学之外再无进一步的概括总结,可以比功能生物学的说明提供更好、更完备或更完整的说明[2]33。 然而,反还原论者必须坚持以上的四项正面陈述吗?既然罗森伯格可以拒斥强版本的还原论而提倡弱版本的还原论,我们是否也可以拒斥强版本的反还原论,转而为一种弱版本的反还原论辩护呢?与上述罗森伯格眼中的强版本的反还原论相比,弱版本的反还原论也有类似的四项陈述,但略有不同:(1)在功能生物学的层面有概括总结;(2)这些概括总结具有说明能力;(3)分子生物学可以使得功能生物学获得提升、更加深入;(4)功能生物学也有可能反过来使分子生物学受益。 自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他们的DNA双螺旋模型以来[11],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生物学分支的发展都从分子生物学的工具、方法和相关成果中受益良多。因此,“弱版本”的反还原论者们并不排斥分子生物学本身,他们所要强调是的:分子生物学本身是存在局限性的,还原论不应该被当作是生物学中唯一的或者是最为有效的研究纲领。 对于这一点,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的兴起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很多(如果不是所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同‘细胞是生命的最小单位’这一论述。尽管分子构成了生命系统,但分子本身却没有生命。不管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之间的分界线有多窄,它们之间毕竟存在着一个质的飞跃。”[12]系统生物学更加关注细胞和分子之间的关系。通过分子生物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学家之间的共同努力,系统生物学利用构建的模型来对分子生物学中收集的大量数据进行整合与重组,以期待找到一条理解生命机制的新途径[10]。 在《达尔文式还原论》一书中,罗森伯格提出了“如何可能”与“为何必然”这两种生物学说明的区分。笔者能够接受这种区分,也赞同生物学中的功能说明主要是如何可能说明,而分子生物学中的说明主要是为何必然说明。然而,本文试图论证,虽然绝大多数如何可能的功能说明是部分说明,但是有一些为何必然的分子说明可能也只是说明概略。因此,至少在哲学意义上,功能说明与分子说明应该享有平等的认识论地位。 因为近似的问题,要想从分子生物学中推导出功能生物学的所有概括总结,恐怕不太可能。因此,虽然分子生物学很多时候确实加深了功能说明或者增大了预测的精确性,但并非总是如此。另外,很多为何必然的生物学说明实际上是由功能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共同提供的,所以至少在某些为何必然的说明中,功能生物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罗森伯格一直在鼓励我们“停止担忧并爱上分子生物学”,但是另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哲学家杜普雷(J.Dupré)却提醒我们:爱很容易使人变得盲目,对于分子生物学而言,以赞赏的态度去接受它也许会更好[13]。而笔者则想进一步表明:虽然分子生物学很容易因其巨大的科学成就而引发人们的热爱,但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它自身的局限性而停止对分子生物学的担忧。 最后,即使罗森伯格对强版本的反还原论提出了很好的批评,弱版本的反还原论仍有可能成立。功能生物学当然应该向分子生物学好好学习,但是分子生物学就不需要从功能生物学或博物学的研究中获取良好的教益吗?对于罗森伯格的还原论研究纲领而言,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①罗森伯格在《达尔文式还原论》一书中对“物理主义”的定义是:从物质、物的实体和物理对象,一直到夸克,宇宙中只存在一种东西、实体或者事情。参见该书第2页。这与本体论还原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②萨卡尔认为,一种成功的还原应该要从另一个不同的(并且通常是更加基础的)领域中汲取说明要素。在这个更加基础(fundamental)的领域中所运行的那些规则就被总称为“F规则”,而“在F系统中有根据”指的是在F规则的基础上有充分依据,或者说符合F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