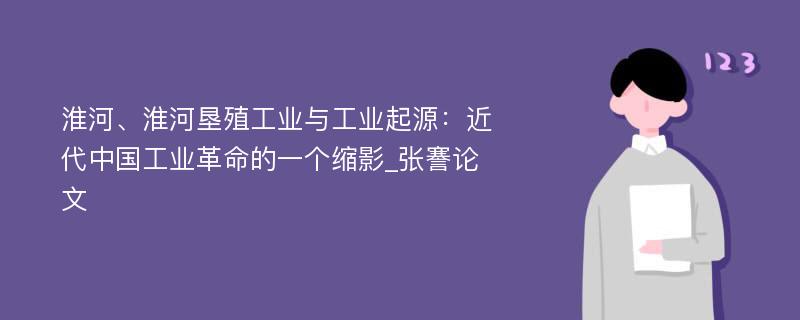
两淮垦殖业及工业的发端: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端论文,工业革命论文,缩影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5;K8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04)03-0102-08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尚未列举出在一个地区的成体系的形态较完整的工业革命的成例。其实,这样的成例就在苏北平原上。这就是从南通发端而延伸至苏北相当大区域的包含圈地垦殖在内的工业革命运动。苏北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或称淮南或两淮。苏北垦殖,又称棉垦、盐垦或垦牧。棉垦,是因垦区广植棉花而得名;盐垦,是因垦区多在原先的产盐区而得名;垦牧,是因曾经在发展植棉业的同时还尝试过发展养羊业而获称。近代苏北垦殖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封建农业,而是一场大规模的泛工业化的革命活动。1993年以前,对苏北垦殖的研究尚少,且受过去的思维方式与时代背景的制约较多。姚恩荣和邹迎曦同志曾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个总结:“当时人们认识的偏差和偏见毕竟难免,问题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有一些学者囿于旧说,惑于成见,攻击盐垦公司的某些‘不法’行为,把盐垦公司视同旧式地主而加以‘历史批判’。这显然是不公道的。”[1](P.652)此后有关的研究增多。除了章开沅教授(另曾与其学生田彤博士合作过)、常宗虎博士、林刚研究员等在各自的专著中有章节性的陈论外,直接以淮南垦牧为主题的论文,去除重复发表的,已达二十余篇;而其中一些文章的主题基本相同。学者们分别对淮南苏北垦牧的经过、农作方式,雇农承地的“崇划制”,其自身的商品生产、内部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棉种改良,区内教育,衰落原因及其与金融、与盐政改革、与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关系,与移民等等作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但迄今尚未把苏北垦牧作为工业革命体系中的现象与问题来给予探讨。苏北的圈地运动实际上与从南通等地延伸而来的工业运动一起,构成了一个在中国绝无仅有的体系完整的工业革命的模版。对近代史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的探索、对人类文化学的研究都深具价值。
近代苏北之南通的发展历程与在清末以前约开和自开的九十多个开埠城市的发展历程大不一样。南通是走的一条以工业革命推动区域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在中国近代社会史上有其唯一性,在中国的工业革命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2]。
一、两淮地区的近代工业化和垦殖运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謇联络了上海和南通的商人商议筹银创设大型的大生纱厂于苏北的南通州。以后除续建的几大纱厂外,南通及邻近的苏北地区还先后创立了电厂、广生油厂、大兴机器磨面厂、复兴面厂、大达碾米公司、大隆皂厂、翰墨林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颐生酿造公司、资生冶厂股份有限公司、大聪电话有限公司、皋明电厂、通明电气公司、通燧火柴公司、苏工染厂、大陆制铁公司、通源码头、通靖码头、大生轮船公司、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大达趸步公司、大中公行、大达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泽生外港水利公司、通海达通航业转运有限公司、惠通公栈、大储堆栈打包公司等等。工业企业已伸展至纺织、机器制造、冶炼、电气、垦牧、盐业、食品加工业、火柴、制皂、印刷、公用、金融、交通、航贸、养殖等十多个较大的领域。从清末至民初,从南通发端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导的工业革命快速兴起了。通过向苏北的工业性与资本主义农业性、商业性的扩展,苏北的相当大的区域也较快地进入了泛工业化运动之中。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在苏北惊人相似地重现了。这就是资本集团率先在苏北、主要是在苏北近海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具体的启动者是以张謇为首的工业家。在苏北圈地的目的是扩张植棉地。张謇坦陈:“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以纺织根本在棉,谋扩张植棉。”[3](P.299)张謇在自撰年谱中也记:“厂纱畅销,然棉以输出多而贵,……乃拟营垦牧公司。”[4](P.862)光绪二十六年,汤寿潜、张謇、李审之、何嗣焜、郑孝胥、罗振玉、孔驯等七人联名呈文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得允准设立垦牧公司,除拟收“江海旷地”外,又“查苏、狼两营兵田,原数共三万八千四百十九亩九分九厘六毫,……拟请赐檄两镇查明未圩地数,按公司集股章程,每亩规银二两二钱二分二厘二毫零,由两营备齐一例入股,照数收地。”[5]两江总督刘坤一欣然同意,批示:“查此案,前准函送议章、图说。当以设立公司,举办垦牧,增课惠民,天利公溥。际此时艰财匮,有此自然之利,岂容听其废。”[6]张謇、汤寿潜等招股后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在江北的吕四场近海的草荡地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圈地建场。《通海垦牧公司章程启》谓:“江北并海,自海门至赣榆十许州县,积百有余年荒废不治之旷土,何翅数万顷。今即通海中一隅,仿泰西公司集赀堤之,俾垦与牧。”[7](P.58)通海垦牧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的农牧业公司。张謇称:“中国之有垦牧公司,创举也。”公司初集股资30万两,圈地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七亩三分四厘二毫,经过砌河堤、造桥梁、筑道路、建水闸、埋涵洞、开垗沟等等工程及招徕垦种,实际治理出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一亩五分三厘六毫可植田地。其中的一千一百十一亩为植草养羊以取毛的牧场。十年后,虽因牧场被大水漂没,羊群损失惨重而获毛甚微;但通海垦牧公司的已治理好的田地中的八万多亩地开始产棉,而向南通的大生纺织企业输送了大批工业原料,大生纺织企业和垦牧公司皆大获其利。通海垦牧公司以后平均年产棉花三万六千担。这第一次圈地垦殖的成功激起了千层回应,终于掀起了苏北的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1914年,钱新之、李亦卿、张敬礼、章静轩等又合股在南通县三余区创办了大有晋盐垦公司,圈地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一亩九分三厘,后实际垦植十七万六千八百三十二亩。全公司平均年产棉花八万担。1916年6月,张詧等在掘港场创办大豫盐垦公司,原定集资本150万元,发行3千股。圈地四十八万亩,后因实得股金不足而实际垦植十三万亩,平均每亩产棉50斤。非南通张氏集团的资本也迅速地投入了圈地植棉的高潮中。如冯国璋于1917年创立了华成垦殖公司。1918年,冯国璋去北京任代理总统,就请张謇来主持公司事务;公司在阜宁境内购买土地,其后虽然因资本短缺,只提供了经治理的植棉之地二十万亩,但所圈所购的民荡民田竞曾多达七十五万亩。岑春煊、朱庆澜、张佩严等于1919年立泰和公司,在盐城的伍佑地区圈地,曾实际圈地六十万亩,但限于财力等,而放弃了大片草荡地,但仍自留了十七万亩地。浙江财阀陈仪于1922年在东台县西团创立裕华公司,先后投入资本五百万元,圈地至五十万亩,后实际治成了二十七万亩。甚至南通大学也按捺不住,而于1920年筹资四十六万元,在阜宁县圈地十万亩,而开垦了其中的三万五千亩供植棉之用。1915年张謇派张孝若的英文老师雅大摩思往澳大利亚购种羊却人款羊皆不见了,加上养羊成本过高,故牧业不足称说,垦区主要是植棉。
总计从清末至1922年,苏北农村先后涌现了45个垦殖类公司,至1935年,先后创立的垦殖类公司的数量已达77个。其中拥田万亩以上的公司有40余个。拥田十万亩以上的大公司有18个,而1917年由周扶九、张詧等人创办的大丰公司竟圈地112万亩,实占地85万亩(注:据胡焕庸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费范九的《南通盐垦始末》、《大丰县文史资料》第七册和第九册《盐垦史专辑》、张謇的《垦牧乡志》、邱云章的《通海垦牧四十年》以及一批旧档等等统计。)。苏北垦区南起长江北边的今海门市和通州市境内,向北直至灌河南边的今连云港市境内的陈家港地区,覆盖沿海或近海地区的广袤平原。垦殖区内总共有多少田亩,由于彼此间的兼并买卖和部分资料的佚散等,难以准确统计。胡焕庸撰《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记谓:“记自此涟水之陈家港起,南至南通之吕四;西以范堤为界,东迄于海,全部面积约一万一千方公里,合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五千亩。其中已垦八百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亩,占全面积百分之四十九;未垦八百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亩,占全面积百分之五十一。”[8](P.185)刘厚生写《张謇传记》,曾引冯奎义于1949年写的《苏北棉垦事业之报告》,此报告称:“苏北棉垦区,域辽阔,……垦区又可分为淮南、淮北两部分,以废黄河为界,淮北的地方略高。淮南部分,南部和北部的地势高,西部和东部稍低。全区面积一七,三八三方公里,合二六,七四○,五○○亩。”[9](P.261)这一地亩数,应包括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控制区内推动开垦的新地在内。今人有不同的统计数字,即使同一学者,也可能因新见一些资料而改变自己原先的所计数据。如姚恩荣等前谓:“整个淮南各公司总面积362万余亩”,后谓:“上表54家公司不完全统计实有土地面积470,4318亩。”[10](P.95)加上资料多已不全的另外二十多家公司的土地,笔者估计苏北近八十家垦殖公司的土地总数在600万亩左右,这应是接近事实的实际占有地的总数,而不包括圈而未占的土地。
“今各盐垦公司地主要农产为棉,棉为纺织工业之原,棉产丰则利必。”[11]各公司所治之棉花田在冬季则种麦豆,以供公司员工的食粮。李积新早在1931年时编过《各公司历年棉花产量表》,仅收录了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这七家垦殖公司在1924年前的棉产数。1920年是丰收年,七公司共产棉两万八千三百七十二担。此后因苏北大水灾而减产,至1923年起才大增产。苏北垦殖公司有几十家,故李积新的棉产表反映不全[12]。据《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引中华棉业统计会资料的统计,1930年至1934年间,江苏长江以北的新旧垦区的棉田已占江苏省棉田面积的二分之一,占了全国棉田面积的八分之一;“棉产之比例亦大略如是。”[8](P.260)1930年,江苏省长江以北棉区产棉四百六十万二千六百五十四担。垦牧区历年为纺织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棉花。英国的圈地主要是为了养羊以为毛纺业提供原料,苏北的圈地主要是为了植棉以为棉纺业提供原料。西方和东方的工业运动通过圈地来为大工业提供生产原料的功用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苏北恰巧有大批的人烟稀少的草荡地、盐田、兵田、庙田、坡地、滩涂地、沙地、公地、杂地、泽洼地等可供南通的工业革命去圈去占,其中所含的耕地较少。而人口稠密的英国没有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得不更多地圈占耕地。
二、两淮垦殖运动中的冲突与整合
与英国早期的圈地运动相比,苏北的圈地运动比较缓和。但抗拒圈地的人也不少。通州知州汪树堂称有五千户不服,说动了江苏藩台也关注这一事态。“是时汪知州仍四布谣言,江宁藩台为其所动,对人言有五千户不服。”[13](P.464)但张謇却轻描淡写这一情况,惟恐清政府出面干预。南通的新兴的工商士绅们后来设法抓住了汪树堂的某些把柄,向都察院呈控他,让御史参奏,终至于在汪树堂公开反对圈地后的一年内就把他撤职赶走了事。其后的继任知州王勖臧是唯唯喏喏之人,未有能力阻挡张謇等人的作为。因此,圈地运动的其他抗拒者就是土地所在的原住民了。
在被圈土地上的居民主要是盐户和农户。苏北盐业衰落和积弊已久,张謇等人趁清政府在庚子赔款后被迫推行“新政”之机,在一开始就已请得清政府批准“废灶兴垦”。因此得以大规模地收并盐田荡地。除灶户外,农户则多为佃农、自耕农和小地主。圈地者与被圈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资方组织了武装专事镇压。张謇声称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均因地滨江海,枭匪出没靡常,自集工商练团为卫”,请得南洋大臣批准,通过地亚士洋行,向德国购买了毛瑟枪200支,子弹20万发。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甫成立,张謇就令成立民团。由两江讲武堂毕业的龚伯厚和南京陆军师范学堂毕业的江导岷、章亮元、洪杰等率领训练,以大生纱厂武装的名义呈请得苏松太兵备道的批准而领购了枪支弹药。辛亥革命后,工商团和民团多次合并改组并扩充,先后有通泰海启实业特务警卫队,或实业保安队、实业警察等等多种称呼。张謇请震旦学院出面通过意大利义丰银行订购了“毛瑟枪一百二十杆,连刀在内,并子药一万颗”。由色哥利亚号船装运来华[14]。这支武装的宗旨就是捍卫圈地运动,维护治安和镇压任何反抗。这支实业武装所分驻和捍卫的地域几乎为整个苏北垦殖区。辛亥革命后它由江苏省民政厅直辖,由各地县政府监督,但其自身维持和活动的经费则由苏北的各垦殖公司分摊,因而实际上只接受垦殖公司资方的调遣。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支实业武装的官兵总数已达987人。
苏北圈地运动多是低价强购土地。沈友良有对1917年大赉垦牧公司在东台县圈地情况的回忆:“公司围田时,一经划界,围进的田以一半价收买,划垗后再卖给田主。当时公司时强迫收买。不卖就拆房子。”[15](P.281)成田尚且如此,至于圈购的取草烧盐的草荡就更是价格低廉。过去沿海每副盐灶均拥有草荡地或沙荡地,资方收购时常以25亩为单元。姚恩荣和邹迎曦两同志提到:“以每二十五亩给价一百千文~三百五十千文不等。通济公司1919年10月收买何垛场灶民夏余林新淤荡地二十亩另三分九厘,共付八十七千五百六十文。”[16](P.106)1917年,冯国璋初创了华成盐垦公司,唯当年7月即去了北京当代理总统,遂把公司委托张謇经营。张謇接手后用心为之筹算。今尚存张謇当年就此而拟给两淮盐运使的报告的底稿,此报告称:“统拟购足六十万亩为公司假定之范围,以二十万亩留煎,以四十万亩施垦,使盐与垦无相妨之害,有相济之功。分年进行,按序规划。预计关于盐事者,如疏运筑圩,开沟移筅一切之用;关于垦事者,如筑堤开河,建造涵洞工程一切之用;统约需款一百余万元。兹拟遵有限公司例集股一百二十五万元。”连建设费用摊进去,每亩地也仅两元[17]。冯国璋已是代理国家大总统,圈买的地自然是低价,而且“土质之优,居通泰各场冠”,付的地价竟然比通济公司付的低地价还要低。先实地考察,再测量绘图圈地,再报请政府同意收垦,再凭批文压价收地归公司,已是当时各公司通行的做法。顾金林也回忆:“大赉公司围田是带强制性的。光滩、无主田,包括有主田,均每亩给二三百铜板。凡围到的,田主非卖不可。”[18](P.282)
在冲突中,圈地的一方动用武力来镇压反抗是常事。1913年张詧等在创办大有晋盐垦公司后不久,被占滩地的盐民曾与资方发生激烈冲突,发生了“火烧公司”和杀死资方办事者的“暴乱”事件。几乎一生从事垦牧的顾毓章先生记述:“大有晋盐垦公司,为张謇之兄张詧所创办,南起范公堤,北至遥望港,西与石港接壤,东南接吕四场。东与东北临海。原为余东、余中、余西三场及金陵公荡,面积约三十三万多亩。……开办时,盐民与公司有矛盾,烧了公司办事处,杀了职员黄贡三和李安甫。”[19](P.91)另一亲历者姜伯涵也回忆:“大有晋公司开始建时,要把盐民赶走。盐民恨公司,就放火烧了公司办事处,杀死了职员黄贡三、李安甫。周寄愚幸亏长工背着他,得以逃脱。这就是著名的‘火烧公司’事件。被火烧的公司地点在贡安,离三余二里路。经火烧后,总公司才搬到三余来。……大有晋曾两度镇压过群众:一次是对盐民,实际上除头头外,被杀者还有好几个群众。第二次是在民国19年,红十四军在附近活动,几十名实业警察去打湾头镇。”[20](P.191-192)姜伯涵提到的周寄愚是大有晋垦牧公司的经理,黄贡三实为王贡三。李安甫,姓名李思危,字安甫。此事爆发在1914年5月下旬。李思危被“抗法”的“啸众”砍伤十余处后被投入火中活活烧死。火烧大有晋公司的盐民领袖唐八斤、朱兆贤后来逃到上海,被捉拿回来后,与其它被捕者一样被枪决在余东镇。张謇自己也有记:“民国三年五月,余中大有晋公司来匪数十名,焚毁屋舍,刃毙司事王姓、李姓二人。”[21]海门移民读“黄”、“王”时音同,故此处误作王姓。民国三年大豫盐垦公司在如东圈地时曾将当地人用以割草养牛的海滩公地圈去,致发生当地人和圈地方的冲突。公司派实业警察来镇压和守地,在当地建兵营常驻。因此兵营故,此地至今还被称作“兵房”。张宪文撰文记:“1914年,南通张謇借口垦荒,企图将唐某荡田一百六十亩贱价归并,并出动清乡营兵捕杀唐兄等人,然后把土地霸占过来。”[22](P.302)1917年4月,苏北发生了大广和华丰两垦殖公司的原住民聚众焚掠公司的事件,张謇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六年四月,栟角场大广公司又发生聚众焚屋掠财之案。丰场华丰公司系向财部偿领该场之四总公荡组织而成者,同时亦发生莠民焚掠之案;灶头孙姓为匪,击毙。其聚众至数十百人,敢于纵火杀人,不得不谓之匪。”[21]结果是:“因角斜莠民乘机蠢动,致劳旌派队弹压。”[23]张謇请得驻扬州的孙传芳部的省防军张旅长派了兵才消弭。今存的未有年份,仅署“五月十五日”的张謇的一份手稿上有记:“乃顷据大贲公司函报,忽有乡民张忠全集众复将□土坝坛筑,阻碍交通,并捣毁乡公所屋物;似此扰害公安,不法已极。拟请电饬东台县迅予严拿滋事之首犯到案惩办,一面仍请派委前徐委员剋日前往调解,根据前案办理,以息争端,而安垦业。”[24]1919年秋冬,草堰场的灶民反抗大丰公司的废盐拆灶低价收地,而发生了火烧卢家集的暴动。自觉出路渺茫的灶民三百余人在徐爱兰、张广和的带领下拔去计划开筑的卯酉河沿岸插列的作为占地标志的一批脚把,放火烧掉了开河工程办事处和民工的工棚群。在今盐城县境内新兴场的北七灶灶民爆发过反抗大纲公司占地、东台县安丰场的灶民爆发过反抗泰源公司占地的斗争。上海银行资本扶持的商记垦团在海门圈地,及1919年泰和盐垦公司在伍佑场筑堤圈盐田,为防止原住灶民的反抗,公司都特派武装警察80人荷枪实弹地至现场守护。大佑公司于1927年在盐城县插旗圈地时,当地的妇女们曾在陈汉初的号召下一起持器抗拒公司所派来的强行圈地的兵丁。
由于当时苏北的本地农民不善植棉,为了保证棉花的产量,所以资本家拨出巨款招募苏中的海门地区的擅长植棉的农民移民苏北;移民人数有十多万、二十多万、三十多万等多种估计。这样,在不少地区又产生了新移民和失地的原住民间的矛盾。在北方的阜宁地区,圈地的资方和从苏中去植棉的移民们还不得不携手联防,配备鸣警器械和武器,甚至制造各类土炮,轰击不断来犯的当地“土匪”,以保卫产棉区。苏北圈地运动导致的失去土地的人民的暴动另有数起,这里不多作介绍。另外,在垦牧运动的后期,一些人已真正沦为靠掠夺、绑票为生的土匪了。
以张謇兄弟等为代表的圈地资方在圈地时为解决当地民众的生计问题,通常采用两类解决办法。
一是在强行低价收购了所围之盐田荡地等后,让失业的盐民租得垦牧公司的一些农田以自己耕种植棉或转租,凭自己的劳动或收取转租金来维持生计。通常是失地的每户灶民视被圈地的多少而可租得二十五亩至五十亩不等的已属垦牧公司的并经粗治的地。开头两或三年,垦牧公司不向他们收租,以示优恤。张謇谓:“为贫民计,以垦代盐,资其生者也。謇兄弟预焉。方谋凡脱于盐者,户各授二十五亩令佃。”[25](P.406)大丰公司则租给每户灶民五十亩初治地以植棉,头三年免收其代租的棉花。但苏北人不善植棉,往往因此而造成亏损。因此,一部分灶民不得不继续煎熬海盐并私销,垦牧公司要圈收草荡沙地,他们自然会竭力反对。
第二个办法是对不愿种田的,每户给二百元,任其自去。“不欲得地而他图者,户给银币二百。”给资遣散迁去[25](P.406)。
无论是那一种方法,都有小部分人营田失败或将钱用空而沦为乞丐或土匪的。“各公司领田之佃,多半是穷户,其种田资本非出于告贷,即系鬻产做会。……往者有人效海门下沙粮户盘剥佃户之风,有放春盘、秋盘之事(春豆秋棉未成熟,先作至低之价),穷佃户但知济目前之急,罔知后患。”[26]张謇特此训令:“今年各公司同人中,若再有此等捉狭盘剥之事,令贷资之佃,只还原本;一面辞歇!”[26]以解雇放贷者相警告。资方的基本对策是尽力避免与原住民发生直接的强烈冲突。张兆炎先生记:“民国三年(1914年)盐商宋勉旃,其人吸鸦片,腐化堕落。偕子镕青,瞒着灶民将北七灶、四移煎大片土地偷偷卖给清末状元张謇(南通唐家闸人,号季直,人称四先生)为首的大纲公司。宋氏得地价一百万元,不久花销殆尽。大纲公司以主人身分通令灶民限期迁出,并强调连租坟都要一起迁走,以便招佃兴垦,或者让灶民永远做公司佃农(时称永佃)。灶民不让,纷纷起来反抗。张謇等要与宋勉旃毁约,追回地价,可宋氏无力偿款,大纲公司只好凭地契与灶民争衡。”[27](P.31)可知张謇等曾宁愿放弃收地而避免与本地人的大范围的对抗。且后来还让步,将花钱买的土地的三分之二给灶民自己分配,大纲公司只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地面。成田或银币的补偿毕竟成了更多的人藉之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个机会。张兆炎承认:“北七灶、四移煎的灶民在张謇等人废灶兴垦的影响下,逐步弃灶垦田为农,生活较前略好。”[27](P.37)由于资本集团明智地采取了对原住民的体恤政策,所以总的来说,苏北圈地运动的开展,才能比较平和。在苏北垦牧区,最终没有酿成如英国自1607年起的连绵不绝的大规模的反圈地暴动,没有发生像英国资产阶级领袖克伦威尔那样的对反抗民众的血腥镇压。
三、两淮垦殖运动与社会改造
苏北的资本集团的垦牧性农业公司内部保留了较普遍的小农经济形式,如分田到户、散地承租、崇划制等等,所以有学者否认南通资本集团的垦牧性农业公司中有足够高的资本主义成分(注:主要可参江苏省科学院江苏史纲课题组撰《江苏史纲·近代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常宗虎撰《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又参见王奇生撰《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年。);但无可置疑的则正是所有这些垦牧公司与农场构成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中的不可或缺的环链。苏北垦牧是南通的工业化运动所引起的。正是苏北垦牧为大工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南通等各地的工业资本与利润被大量投入垦殖区,甚至于苏北十多家垦殖类公司的创办人或领袖本身就是由南通大生工业集团的领袖兼任。林刚等都列有一张张氏家族及大生纱厂与南通系各盐垦公司的领导层和组织关系的表,可参看[28]。南通和淮南,也就是苏北已结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以我南通论,自治之本在实业,实业范围浸遍淮南。……淮南各县,凡我实业所及范围内之地,与南通无异。”[11]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也促使了苏北的近代农业、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农村的近代化,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改造了社会。即张謇所谓的:“垦牧为地方实业之一端,亦即为地方自治之一部。”[29](P.325)垦殖区的棉业生产,尤其是良种棉生产从无到有,产量大幅度增加。科学的农事实验场创立。近代水陆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形成。水利建设在广大地域进行,沟渠遍布。重要水利设施如遥望港九孔大闸、蒿枝港七孔合中大闸等等还都请外国专家指导设计建设,规格和质量都很高。据胡焕庸先生在其《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收集的资料可知,仅大丰公司,就在垦区修堤321公里,涵闸35座、建桥梁690座、汽车道450公里,挖河道12600公里。棉花的初加工业、工业化的制盐业和少量的现代轻工业企业等兴起,使用机纱的手工织布业以及染整业也从南通向垦区延伸,整个棉区的工商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杜渺同志记当时:“南通张姓经办的轧花厂规模最大,拥有轧花车40部,35马力柴油机1台,在当时的阜宁县境内也属佼佼者。民族资本家戴尧吉开办了通洋恒新碾米厂,这是射阳境内出现的第一家用机械加工的米厂。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射阳县境内共有工场、作坊共893家,规模都较小,基本都开在各垦殖公司所在地。”[30](P.697)分布在苏北其它地区的植棉区的工商业发展的情况大致与之相近。
在各垦牧公司所统领的农村地区,约25个新的大小镇市被从无到有地创建了起来,如今日启东市境内的海复镇,如东县的兵房镇,通州市的三余镇,大丰县的大中集、裕华镇、通商镇、南阳镇、新丰镇,射阳县的合兴镇、八大家镇、大兴镇、通兴镇、三区镇、千秋镇、闸口镇等等即是。公司机构、学校、钱庄、银行的分理所或储蓄所、邮政所、商店、药店、诊所甚至医院、合作社、花行、轧花厂、碾米厂、油厂、铁匠店、客栈、码头、车行、市场、仓房等等俱备,而皆为当时一地的商贸重镇。一些棉区集镇还架通了电话。海复镇还建立了发电厂和电灯厂。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因垦牧而起的“海复新镇街衢宽广,市廛整齐,地当通道,行人麕集,百货杂陈,贸易交通。以观昔年走五六里或十余里之村市,求腥蔬而或不得者,其利便何如也。”[31](P.310)大中集和合兴镇(后称合德镇)后来还发展成了大丰县和射阳县的首府。
由工商资产阶级掌控的垦牧区的近代政权也建立起来了。清末时,通海垦牧公司规划在该公司成立一年之后应兴办三件要事,一是设立自治公所。“遵照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之规则,建立自治分所,设区裁判,以理公司界内及毗连地方之民事。并办警察,以保公共之治安。”[32](P.351)二是建置小学。规划每16平方里建一座小学(注:因各垦区的学童密度及各项条件都不同,在具体建校时,并不依此标准行事。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詧张謇对于各盐垦公司之通告》的手稿对此有说明。)。三是开股东大会。新式的政权、教育和近代企业制度等在苏北的大地上从无到有,使社会的组织和面貌有了改善。尽管在苏北的圈地植棉的事业始终遭遇着资金匮乏、天灾、战乱、部分原住民的抗拒或破坏、经营失措等数不尽数的困难,这一历时几十年的运动已是长江北三角洲工业革命不可缺失的重要内容,客观上对支持大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的衔接也起了积极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基本上是外来的、移植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结果,与过去手工业的发展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不存在一个明显的、源于内部因素的‘工业革命’”[33]。我认为此种观点可能是因没有掌握充分的史实和新的认识角度而作出的,因而不敢苟同。
实际情况是:苏北圈地运动尽其所能地协调了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关系,苏北圈地运动所支持的工业革命没有像英国的工业革命那样摧毁了传统的手工纺织业,而是较好地处理了与传统手工业的关系。
江苏的棉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而发达,如其中的通海地区自明末起植棉织布,至清代时已几乎是家家妇女或纺或织,村村有机杼之声。所织土布滑软而结实,远销东北与南洋,名声较著。机器纺织厂的创办不仅没有立刻摧毁传统的手工织布业,造成无数传统的家庭织业的破产和造成旧新经济的激烈冲突;相反,竟奇迹般地与当地的旧式手工业相衔接。如南通大机器工业所生产的机纱大量销往周围地区的农村与集镇,取代手纺纱而成了新一代土布的原料。由于机纱土布的质量远胜于手纺纱土布的质量,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畅销于苏北和东三省等地区。而原先手工纺纱的妇女们则改摇线纺纱为织布,反而获利更多。因此,在近代苏北顺利地完成了纺织业的大机器生产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的衔接,有效地减弱了现代工业对旧式手工业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新旧经济的猛烈碰撞所造成的社会大震荡,避免了英国式圈地运动的血腥过程的重视。
然而这种同行业内的旧手工业和大工业在一地衔接互补而又并驾齐驱的现象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也未必能很好地发生在全国各地和所有的行业内。而且,在长江北三角洲的这种携手共进的情况是有条件的。严中平先生据前人资料估计:近代一名机纺工人的出纱约当于一名手纺工人的出纱的八十倍。但一名铁轮机机织工人的出布仅约当于一名老式普通布机机织工人出布的四倍[34](P.267)。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大机器工业若织布,其利润将远低于纺纱,因而大机器工业宁愿纺纱。这也就是为什么手工业的纺纱成本大大高于机纱成本,而宁愿织布的原因。一旦这种不可能长期不变的相对平衡被打破,比如新的自动织布机问世并广被采用,机器织布的效率大增,那么,苏北的这种建立在一定的偶然性上的大机器工业和旧手工业的成功交接、平安相处的良好关系就会被打破,并迅速转化为势力悬殊、你死我活的残酷拼搏。
庆幸的是,在苏北的工业化的环链内,这样的平衡只是到了约1922年时才开始被打破。这使得苏北的包含垦殖运动在内的工业革命能得到较长的时间来固化它已取得的成果。
苏北的圈地垦殖运动实是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缩影,其形态的独特、自身体系的完整、史实与资料的丰瀚,在中国仅此可见。其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的现代化命题的研究等等,有极高的标本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