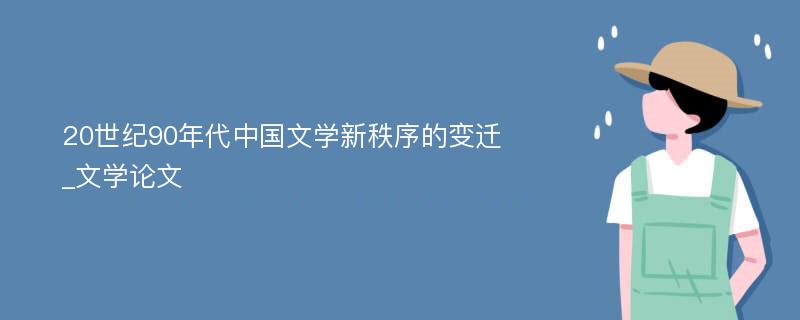
变动着的90年代中国文学新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新秩序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有人问我,90年代以来最有潜力的作家作品是哪些,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那些新生代作家作品。如果有人要继续问,新生代中哪些作家作品最值得我们注意,我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可以看看陈染的作品,看看虹影的作品,看看卫慧的作品。我这样推崇新生代作家作品,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可能是一种个人的偏爱,90年代不是还有很多作家作品么?单单上海就有王安忆、陈村、王小鹰、孙甘露等,至于全国范围来说,更是有许多值得推荐的优秀作家作品。你能说韩少功、张承志等不重要,你能说贾平凹、阿城不重要?的确,这些作家作品都重要,但在我看来,这些80年代过来的作家作品其基本风格已经定型,作品是写得越来越老到了,但无论如何仅仅是一种风格、一种方式和一种审美价值而已,并且这一切是确定的了。我所感兴趣的是那些还处在成长状态的东西。假如有朝一日有人问起,90年代中国文学除了那些80年代过来的作家作品之外,是否还有新的作家新的作品产生,或者说,除了那些80年代形成的审美方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审美方式存在呢?正是着眼于这样的思考,我注意到那些正在成长之中的新生代作家作品。
一
事实上,新生代作家的提法是一种非常含糊的概括方式,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提法。作家就是作家,每一个时期都会产生代表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并不见得所有后来的作家都应该称为后什么作家或新什么作家。我怀疑这个概念很可能是一些编杂志的人为标新立异而策划出来的。但从区别于50年代成长起来的右派作家和以老三届为主的知青作家的审美方式着眼,我理解新生代作家意味着一种不同于80年代延续下来的文学审美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些新的文学审美方式和表达方式集中在90年代新出现的一些作家作品之中,而这些作家就其个人背景而言,大都出生于60年代或更迟些时候。新生代作家与这些80年代的作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新生代作家的群体认同感很弱,他们不像80年代那些初登文坛的作家,群体意识很强。所以,从文学现象上看,80年代出道的作家常常喜欢谈代沟,讲他们与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作家之间人生经历的不同,以及与后来的新生代作家之间的代沟,这种前后代沟审美的立足点,就是作为群体存在的80年代的社会意识。当然,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喜欢张扬个性,强调自我。作品的主人翁总是处在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中。如,张承志《北方的河》中那个不堪城市生活重负的男主人公,只有到贫瘠的荒山野外去恢复自我的认同感,否则,他就无法生活下去。张欣辛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中那位将生活竞争视为如老虎吃人的主人公“孟加拉虎”,对自我的失落简直负有深深的恐惧感,生怕在社会生活中惨遭淘汰。这些80年代作家作品所表现的自我,事实上是镶嵌在社会背景上的,或者说,这样的自我主要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代码。所以,80年代所产生的那些最具个人风格的写作,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等,与90年代那些新生代作家作品相比,前者的社会关怀色彩显然是非常强烈的,汪曾祺和阿城在表现个人的意趣的同时,总是尽可能地与嘈杂的现实生活相对照,而这种对照本身蕴含着作家对现实的无言批判。正是由于80年代的文学作品普遍具有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因此,80年代产生的一些作品很容易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作家地位的确立和作品影响的产生,几乎都基于这种普遍的社会认同。相比之下,9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对80年代作家热衷的社会问题很少有兴趣,他们大都处在自言自语的写作之中,就他们中较为突出的作家作品而言,都表现出明显的心理症状,譬如,陈染的中短篇小说和虹影的中短篇小说,都沉陷于自恋的幽闭状态。我们读她们的作品,最大的快感并非在于从中得到当今社会的生活信息,而是感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理体验和心理潜能释放的快乐。尽管她们的作品一再被一些批评家冠之以女性主义或是女权主义,但我想,对于这两位作家的真实写作状态而言,是不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能够寻找到独立地展示自己的感受方式和自己想象生活的方式。新生代作家都关注自己个人的生活和生活感受,在创作上寻找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匹配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他们中有人在试笔阶段还曾模仿过80年代的种种表达方式的话,那么,一连串的失败教训提醒他们,如此写出来的作品,写得再好也只不过是80年代作品的翻版,更何况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根本就没有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进入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之中,新生代作家倒是创造了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空间。在卫慧的《欲望手枪》、《硬汉不跳舞》中,虽然没有表现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仅仅是展示了现代都市中一些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日常生活,但我们发现这样的小说也很有意思,至少它不比那些表现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差。而且,写作这样的作品,其严肃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执著于社会问题的写作。不错,新生代作家所提供的文学视域确实不是很开阔,但谁也不会否认这是90年代生活的一角。而且,新生代作家在作品中所显示的良好艺术感觉,是那种真正的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它不像80年代过来的一些作家是为了将某种已经写滥的经验变一种花样来制作,新生代作家所选择的文学方式与其感受生活的经验方式之间几乎很少有缝隙。他们的作品让人耳目一新,并不在于这些作家对小说形式有什么刻意的追求,而是他们经验生活的方式就是这样,他们心目中所想象生活的方式也是这样。虹影的《康乃馨俱乐部》,故事是虚构的,但所展示的生活感受却是非常现实的。我读这样的作品,常常会想起那个在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就读的不起眼的文学青年所感受到的心理重压。如果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爱好或对生活的憧憬,他/她是不会大老远地从内地来到上海或是北京,而到了这些地方,才发觉文学离他们的梦想又很远,这正如作品所说的“一句诗这么描绘插入中文系三年级的作家:世界是一幢网状的大楼左右颠动,他们附在上面,像猫头鹰的眼睛。”的确,在大学这个特殊的天地中,这些文学青年是一些附着物,就像青藤那样,需要一棵树或一栋房子作为他们的支撑点,以供他们生存。那些正牌的大学校园诗人往往就是作为树和房子介入他们的生活的。在《康乃馨俱乐部》中校园诗人古恒,进入“我”的世界,使得作为文学青年的“我”能够出入大学的咖啡屋,能够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区租借房子,与古恒共享同居的神秘体验。但在心理上这些文学青年并没有赢得正牌大学生们的尊重,如果不是“我”后来加入白领女子俱乐部中,如果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子,古恒大概永远也不会来找“我”。而事实上“我”的确是一无所有,甚至连奋斗的方向都没有。这种生活状况与文学青年原来的梦想之间有着多大的落差啊。这种生活体验,这种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我相信虹影在上海在北京的日子里是深有体会。事后回味所感受到的屈辱与愤懑,无疑是她文学写作的潜在动力。她想象着对男性的阉割,想象着女性行使权力的快感。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她的个人经验,也成为她独特的文学体验。新生代作家作品中类似虹影这样的文学体验并不在少数,这种体验,与80年代作家的个人经验非常不同,如果说,80年代作家作品所呈示的是一种社会阅历的话,那么,90年代新生代作家所呈现的主要是一种个人成长的经验。这种经验从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来说,可能显得太稚嫩、太个人化了,但对于90年代一步步走向文坛的新生代作家而言,确实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体验。至少我们难于否认,这是一个值得文学表现的潜在空间。
二
凡是认真读过新生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家,只要他不带偏见,我想都会承认新生代作家作品写得大都很认真,其认真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时下颇为走俏的一些80年代过来的作家作品。的确,对新生代作家而言,他们还没有资本作矫情状,他们是以一种本真的姿态投身于文学。所以,读他们的作品,我常常感受到作家投身其中的情感燃烧和陷于痛苦难以自拔的体验。不妨以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与卫慧的《欲望手枪》作一对照吧。两部作品都写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在现代都市的生活遭遇,但基于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作品表达的方式就完全不同。王安忆写了一个叫阿三的女画家,先是爱上了一个美国人比尔,后比尔回国,中断了关系,阿三又爱上了德国人马丁,在马丁与之断绝了关系之后,阿三的生活整个没有了方向,她只能靠在宾馆的大堂中搭识外国人来排遣自己的生活,直至最后被当作妓女抓进监狱。应该说《我爱比尔》是王安忆小说美学的痕迹。这种痕迹最集中地体现在作家创作时,对人物关系的处理,往往侧重于社会生活内容,是从社会生活的变动关系中来捕捉人物身上的变化。如,阿三这个形象,我们读后常常会产生一种同情和怜悯,这种同情和怜悯相当程度来自于作家所设置的社会视角。作家是以一种社会批判的眼光在审视着阿三这个人物,时时做出道德评判。这样的写作,当然可以成为一种有深度的文学写作方式。而相比之下,卫慧的《欲望手枪》表现了另一种生活感受。这部作品写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的个人经历。她在名牌大学读书,喜爱写作,毕业后给一位局长做秘书,因不喜欢这种工作,辞职专事写作。她的生活靠母亲接济,但她与母亲没有情感上的联系。父母早已离婚,哥哥与母亲远在南方,父亲独自在上海,整日酗酒,终于患肝病病逝。孤独的女孩独自经历着生活,她遇到过很多男人,但都不能解除她内心的痛苦。这部作品写得很沉痛,但没有80年代小说美学所体现的那种道德感和社会批判眼光。这当然不是说,卫慧这部作品真的没有道德感,而是说作者在小说表现上更注重个人的内心感受,她是要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在她的小说写作中,故事的叙述与小说形式的选择,全都是围绕这种感受的传递进行的。这样的写作,在美学风格上有着80年代作家不曾有过的创意,在表现人物时,作家不是在社会舞台上来搜寻人物活动的踪迹,而是表现个人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事件和心理成熟过程。作品所展示的人物和事件,不再是一种故事和技巧,而是作家个人经验的真正展示,可以说,新生代作家很少像80年代过来的作家那样动不动就会喜欢谈小说叙述问题,对新生代作家而言,感觉和经验本身都已经非常饱满,他们急于要把这种不同于爸爸妈妈阿姨哥哥姐姐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传递出来,而用不着为叙述什么而犯愁。所以,他们的作品用不着刻意讲求技巧,而是直接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冲击现存的各种文学叙述方式,靠这些鲜活的生活感受本身就足以吸引读者的注意。
确实,面对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能说这是又一种文学表达方式,而且这样的作品是80年代过来的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不是有许多人批评新生代作家作品全是欲望的展示吗?事实上,80年代的作家对欲望的展示并不少,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三恋”等等,全都是赤裸裸的欲望的展示,而与之相比,90年代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很少依据细节的描写来展示个人欲望,他们对性爱的细节描写毫无兴趣,他们更多的是将个人欲望作为作品人物宣泄情感的一种主要方式。看过陈染的《私人生活》、虹影的《康乃馨俱乐部》、卫慧的《欲望手枪》,不管读者是不是能接受和理解作品人物的生活态度,但我想许多人会承认新生代作家在作品中提供并建立了一种新的感觉方式。换句话说,对欲望的表达不是就欲望本身而展开,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欲望感官的享受之中,而是青春少年遭遇的生活特别富有刺激性,他们对外界的每一种生活都充满新奇,甚至对被人们视为是堕落的生活也一样。有什么理由在未经历一种生活之前就先要学着别人的腔调判定这种生活是堕落的呢?如果说,像陈染、虹影、卫慧、朱文等人的作品所展示的生活要被视为是一种堕落的话,那么,什么是不堕落的生活呢?那些成功人士的体面生活是不是就意味着合理或道德呢?事实上,纠缠在这样的问题上做没完没了的讨论,这本身就是远离新一代作家作品的一种指手画脚行为。对新生代作家而言,有什么比小说传递感觉,并让这种感觉像电流那样触及每一位读者的目光来得更重要呢?80年代的美学信条是思想、思想、再思想,深刻、深刻、再深刻,那么,90年代的新生代小说信条就是感觉、感觉、反复感觉,体验、体验、更多地体验。这样的小说构想方式当然不是说90年代新生代的作品没有思考,而是新生代作品的呈示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假如读新生代作家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让一些过来人感到不能接受的话,那么,类似于虹影的《十八劫》这样的作品应该是过来人所能接受的吧。但即便是这样的作品,我想与80年代延续过来的小说方式也是相距甚远。这部作品同样是写苦难,但它不像80年代的小说那样是一种控诉式的,而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陈诉,陈诉苦难在一个女孩内心造成的巨大恐惧。如果说,这样的小说能够感染人,吸引你继续产生阅读的需求的话,那么,应该承认90年代新生代作家作品是有自己的创意,它开启了一条不同于80年代小说构想模式的小说表达方式。
三
事实上,新生代作家作品才刚刚浮出水面,才刚刚被社会注意,他们的艺术感觉并不比现今人们所谈论的所有80年代以来的作家差,他们的写作勤奋程度也不比今天所有作家弱,如果今天还是一个《伤痕》时代、《班主任》时代,那么,凭新生代作家已有的作品早就应该获得社会的承认了,但时运不佳,偏偏90年代人们无暇再像80年代那样全民关注文学了,即便是文学圈内,人们也已不像80年代后期哄抬年轻的先锋作家作品那样来对待新生代作家作品了,所以,新生代作家作品是孤寂的,他们享受不到来自真正行家的赏识,他们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中艰难地寻找生存。特别是那些新生代作家的个人生存环境,的确并不像他们的小说所展示的那样轻松,咖啡馆、高级酒吧、宾馆、迪迪舞厅和休闲度假村,大概只是他们想象中表达90年代生活的一种意象吧,就像80年代作家喜欢用神秘的小屋、艺术沙龙和会议室来表达紧张的精神状况一样。假如因为他们笔下的这种生活意象而遭致人们的菲薄,我以为这是非常悲哀的。当然,为了引起社会对新生代作家作品的重视,90年代的文学杂志也采取了策划的手段,除了冠之以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以区别于80年代过来的作家作品之外,还通过出专辑的做法隆重推出这些作家作品。这更遭致许多批评家的批评。但排除策划的商业因素之外,我以为人们对新生代作家作品的知晓也正是通过这种颇带广告意味的宣传途径而获得的,至少这些被文坛冷落的年轻作家作品有了受人关注的机会。假如要等着那些文学编辑自然发掘新生代作家的作品,那么,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才会被社会注意。从这一意义上讲,应该宽容地接受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文学更替的方式方法,只要有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出来,有新的作家作品产生,就没有必要以以往的文学演进经验来苛求今天的文学演变方式。面对变化的世界,谁有权说我所认定的方式是唯一合理的呢?如果有人愿意用广告的方式来推出一批新作家新作品,而事实上这些作家作品真的一点也不比现在文坛上那些作家作品差,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死死揪住所谓的宣传方式并因此否认这些好不容易才冒出来的新生代作家作品呢?
新生代作家对自己的创作至今也没有非常自信的把握。所以,在众多的争议声中,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本身的确面临考验,在各种富有诱惑的批评话语面前,新生代作家能不能将自己良好的艺术感觉充分地展现出来,从80年代确立的文学表达方式中真正独立出来,而不是依照现有的各种批评话语来图解自己的感受,这是新生代作家未来写作能否持久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注意到像陈染、虹影这样的作家,在新近的创作中有一种认同现有批评阐释的趋势,她们或认同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解释,或以更现实的写实形式(如,虹影的《十八劫》)写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这样的写作或许可以避免许多责难,但就文学的想象方式而言,这是一个并不太值得乐观的信号。在文学史上,我注意到许多有创意的作家就是在放弃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想象方式,回归到所谓的现实题材之后而遭致自己艺术天才的毁灭性灾难。历史上如30年代的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施蛰存,先前用包括意识流手法在内的方式反映都市的生活,写得极有特色,而后来一旦随俗大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不仅没有写出好的作品,甚至连原有的水平都无法保持。而80年代的先锋作家中,像余华后来写《活着》这样的作品,虽然目前批评家中不乏叫好之声,但长远来看,这样的作品是否真是最能代表先锋派和余华个人文学想象的方式,实在是非常难说。因此,对新生代作家而言,现在没有必要为自己被打入“另类”而愤愤不平,重要的是要使自己保持在“另类”的体验状态,并以文学的形式展示这种经验,否则,很有可能使自己独有的文学感受方式淹没在现有批评的陈词滥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