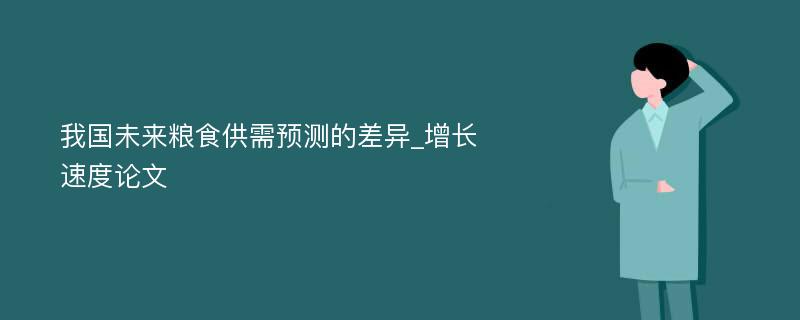
中国未来粮食供求预测的差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论文,差别论文,未来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国民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而且这种快速的增长势头在近期还将继续保持下去。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国未来的食品供给与需求将产生两个重要影响:第一,对于食品的需求,尤其是像肉类和奶制品等畜产品及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加工品的需求,将会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第二,农业比较利益的持续下降以及劳动力、土地和水等资源不断地流出农业部门将会使未来的粮食增产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为此,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预测模型对中国未来的粮食供求状况进行预测并以此来确定它对世界粮食市场的潜在影响。在这些预测中较为流行的有:布朗(Brown)、罗斯格兰特(Rosegrant )、 黄季焜等,美国农业部、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OECF)以及世界银行所作的经济模型。这些模型的预测结果已经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过,本文将以最近发表的结果为准。比如,布朗的预测结果来自1995年出版的《谁来养活中国——对一个小小星球的警钟》。 罗斯格兰特和黄季焜等人的预测分别出自1995年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发表的题为“2020年全球粮食预测:投资的作用”和题为“21世纪中国的粮食经济:供给、需求和贸易”的报告。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采用CPPA模型对未来中国的粮食供求状况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发表于题为“2005年国际农业的长期预测”的报告中(No.9612,1996年8月)。 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的预测模型选自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的发展协助研究所作的一项研究,该项研究的成果发表在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的题为“中国粮食供需平衡的前景及农业发展政策”(1995年)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预测由唐纳德·米歇尔(Donald
Mitchell )和美林达·英格科(Merlinda Ingco)在1993年作出并发表在《世界粮食展望》中。
上述各种模型的预测结果大都表明中国将继续增加粮食进口,但对于到底增加多少却说法不一。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三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这一差别:模型结构、宏观经济假定以及模型所使用的供给和需求参数。本文的目的就是比较建立在这三个因素基础上的上述各种模型并指出它们对预测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二、对中国粮食供给、需求和贸易状况的预测
在比较不同预测模型的结果以前,我们必须对模型进行两项重要调整以使各模型的预测结果建立在同一可比较的基础上:
1.关于粮食的定义,不同预测模型所使用的粮食定义存在着一定差别。美国农业部定义的粮食包括小麦、大米(不是稻谷)、玉米、高粱、小米、大麦和燕麦。布朗、黄季焜等人和世界银行采用了这种粮食定义。罗斯格兰特等人采用了联合国粮食组织(FAO )的粮食定义方法,这里粮食包括未碾磨的稻谷、小麦、玉米和其它粗粮,但将稻谷按65%的出米率折成大米。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则采用了中国的粮食定义:稻谷指未经碾磨的稻谷,同时它不仅包括美国农业部定义的全部粮食还包括马铃薯(与粮食的转换率为5:1)、大豆、 豆类和其它诸如荞麦的粮食。为了对各种预测模型的结果作出正确的比较,我们采用了较为普遍的美国农业部的粮食定义方法。因此,各模型中的粮食数量均根据这种粮食定义方法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罗斯格兰特等人的模型中,粮食数量均以1.06282为系数进行了上调〔1〕。相反,根据与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的差异(1990-1995年间), 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模型中的粮食数量以0.76为系数进行了下调。
2.对每个模型的预测期进行调整。对于中国粮食供给、需求和贸易情况,布朗预测到2030年,罗斯格兰特等人和黄季焜等人预测到2020年,世界银行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到2010年,美国农业部到2005年。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对于粮食产量的预测。布朗预测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为2.72亿吨,下降20%。按照模型的线性趋势对2020年和2030年的数据进行推算后,世界银行、罗斯格兰特和黄季焜等人预测中国的粮食产量将继续以年均1.7%-1.8%的速度增长,2010 年可达4.5-4.8亿吨,2020年为5.4-5.7亿吨,2030年达6.4-6.6亿吨。尽管这三个模型的宏观经济假定和模型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但它们的预测结果是非常相近的。美国农业部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的预测结果处于上述两种结果之间。 美国农业部预测中国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 %,2005年产量可达3.82亿吨,2030年为5亿吨。 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预测的中国粮食产量增长速度为年均0.44%,慢于美国农业部的结果,因此2010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89亿吨,2030年达4.14亿吨。仅比现在粮食的产量高出10%-17%〔2〕。
对于中国粮食需求量预测的差别,无论是在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在绝对水平方面,与粮食产量预测的差别比较而言都要小得多。其中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预测的需求增长量最大,在它的模型中,中国粮食需求量将从现在的3.75亿吨增加到2010年的4.92亿吨,2030年可达8.06亿吨,年平均增长速度在2.4%以上。与此不同, 美国农业部认为中国粮食需求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因此2005年粮食需求量将达到4.14亿吨,2030年为5.79亿吨。布朗关于粮食需求量的预测较为保守,仅略高于美国农业部的结果。布朗预测2030年中国粮食的人均消费量为 400公斤。罗斯格兰特、黄季焜等人和世界银行的预测结果仍然很接近,由6.8亿吨至7.17亿吨不等,相差不到6%〔3〕。
粮食进口预测的差别主要来自产量预测的差距。布朗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预计中国的粮食缺口到2010年将达到1 亿吨以上(占到总消费量的20%-30%),2030年还会增加到将近4 亿吨(几乎占到粮食总需求量的50%)。布朗关于大量进口的预测很显然是源于他对中国粮食产量的悲观估计,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的预测结果则是由它对产量的低估和需求量的高估所共同决定的。罗斯格兰特、黄季焜等人、美国农业部和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粮食进口的估计较为谨慎,且非常接近。他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只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4000-5000万吨的粮食,占国内需求量的5%-13%。
三、宏观经济假定
宏观经济假定在决定各国粮食产量和消费水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口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不仅是各经济模型中所使用的宏观经济假定,同时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宏观经济假定。
除了日本海外合作基金会的预测模型之外,各模型对于人口增长的假定大致是相同的。日本海外合作基金会假定1990—2000年间人口增长速度为每年1.46%,2000—2010年为1.22%。布朗预计2017年和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和16亿。也就是说,从1994年到2017年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017年到2030年为0.5%。罗斯格兰特等人在模型中同样采用了1%的年均人口增长速度。在黄季焜、 美国农业部和世界银行的模型中截止到2000年都采用了1%的年均人口增长速度, 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则使用了小于1%的增长速度。
与人口增长速度假定的情况不同,各个模型对于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假定存在着较大差异。一方面,黄季焜等人预计今后中国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仅为3%—3.5%,这一水平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增长速度还要慢。另一方面,日本海外合作基金会假定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继续保持1984—1993年的水平,即每年人均收入增长8.1%。 对于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假定,罗斯格兰特、美国农业部和世界银行大体是一致的,认为其年均增长幅度在6%—8%之间。
四、模型参数
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是每个经济模型都采用的重要参数,同时也是解释预测结果差距的重要参数。这里主要是指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对于供给弹性的比较,我们则通过比较单产和面积的增长率的预测结果而作出。除了黄季焜等人的模型外,文中提到的其它模型都将种植面积和单产作为描述供给的因素。
在所有预测模型中,尤其是用作粮食预测的模型中,粮食的需求收入弹性都相当小,有些还是负值。大部分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供食用的粮食被认为是低档商品。而饲料用粮的需求弹性和用作其它消费的粮食的需求弹性较大,如日本海外合作基金会的模型中假定饲料粮的需求弹性为0.346-0.907,粮食加工品的需求弹性为0.446-0.771。这显示了随着经济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粮食消费偏好的变化趋势。
各个模型对于种植面积和单产增长率的估计同样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一方面,布朗认为中国粮食的种植面积到2030年将比1995年减少近一半,相当于平均每年减少1.58%。考虑到他对中国粮食单产增长前景的悲观态度,平均每年1.1 %的单产增长率的预测结果就显得相对高了一些。这一增长率是根据他预测出的2030年4.8 千万公顷的粮食播种面积和2.72亿吨的粮食产量计算得出的。也就是说,2030年中国的粮食单产将达到每公顷5.7吨,比1990年的3.7吨提高了54%。
日本海外合作基金会同样对中国未来的粮食播种面积持悲观态度。它预计1993—2000年间中国粮食的播种面积将以每年0.62%的速度递减,2000—2005年的递减速度为0.51%,2005—2010年为0.58%。这样,粮食播种面积的大幅度减少就抵消了单产高速增长的预测结果(1990-2000年单产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5%)。 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模型中,对于粮食单产增长率的估计在2000年以后逐渐减少,2000—2005年年增长率为1.4%,2005—2010年仅为0.84%。
与上述观点不同,世界银行预测1990—2000年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仅以年均0.3%的速度递减,这之后则将保持不变。同样, 美国农业部假定在1990—2000年间,中国播种面积的递减速度为每年0.18 %,2000—2010年的递减速度将更为缓慢。对于粮食单产的变化,世界银行假定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每年1.9%和1.7%。美国农业部的预测分别为1.45%和1.42%。
罗斯格兰特等人的模型对于播种面积变化的预测是最为乐观的,尽管不同产品的变化幅度会有所不同,但模型认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播种面积将会稍有增加(1990—2000年的增长速度为0.27%,2000—2010年为0.03 %)。其中,玉米和小麦的增幅最大,稻谷有所下降。 然而,他们预测粮食单产的增长速度却较为缓慢,1990—2020年的增长速度仅为1.3%。与面积变化的情况相同,在单产变化中, 依旧是小麦和玉米的增长速度快于其它粮食品种。
五、模型结构
1、布朗模型。布朗的预测主要建立在对人口增长、 人均需求量及产量的特殊假定之上,而非建立在具体的供给与需求模型之上。在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台湾、韩国和香港)的经验之后,布朗认为中国90年代中期的情况类似于60年代初期的日本。
由于布朗没有作出一个结构性模型,因此在他的预测中,我们很难找到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例如,在他的模型中,需求过度而供给不足所带来的价格上涨并不引起生产者、消费者、研究机构和政府的反应。
2、世界银行的经济预测模型。 世界银行的预测模型是一个非地域、部分均衡的净贸易模型。这个模型共涉及24个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其余的国家则被分作9个地区。模型所研究的粮食品种包括小麦、 稻谷和粗粮。每个独立的模型是对某一品种与其它品种以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各品种之间的联系进行预测。
每一国家或地区的产量是由收获面积和单产的估计方程所决定。其中,收获面积的确定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总面积由包括上一年种粮收入、总库存和时间趋势三个变量的方程预测得出,然后再通过回归方程确定三种粮食作物的面积,其所包括的变量有:各种作物面积在总面积中的比例、各替代作物的相对收入和时间趋势。单产预测方程的变量有:前一期的作物价格、化肥价格、高产品种在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和时间趋势。
此模型中,粮食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的需求方程是不同的。对于粮食净进口国,粮食的人均进口量由收入、价格及其它诸如国内供给量等一些变量决定的方程所确定。总需求由剩余的产量、净进口量和库存量加总得出。无论是粮食净进口国还是净出口国其期末库存均是由消费量和价格来决定。粮食净出口国消费量的决定方程所包括的变量有:人口、收入和价格。此后就可以根据国内剩余的供给量、需求量和库存来确定粮食的净出口量。这个模型还同时解决了世界市场价格的决定问题,即净进口与净出口相等时的价格作为粮食的世界市场价格。
世界银行模型最突出的一个弱点是它仅仅包括三种作物,因此它很难用来确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之间的关系。
3、罗斯格兰特等人的IMPACT模型〔4〕。IMPACT模型是由罗斯格兰特、索姆比拉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佩雷斯(Perez)建立的。对于这个模型需要作以下几点说明:(1 )这是一个主要涉及农业部门的部分均衡模型;(2)是一个涉及35个国家和地区、17 种产品的全球性经济模型;(3)是一个非地域的经济模型;(4)是一个具有合成性质的经济模型,因为模型中所使用的弹性都引用了其它研究的成果。这个模型尽管主要针对农产品进行研究,但同时还建立了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增长之间的联系。该模型通过使用一系列供给和需求弹性,以及建立一系列线性和非线性方程来对生产和消费方程进行模拟。部门经济增长乘数在模型中被用来确定收入变化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效果。模型中一个典型的国家或地区的分模型不仅包括对每种商品的供给、需求方程,还包括联系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平衡方程。这个模型还通过世界市场上商品贸易的价格建立了国家间和商品品种间的联系。
但是,这个模型仍旧存在着弱点,即对于畜产品生产的分析相对较薄弱。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尤其应该抓住畜产品生产中技术和结构的变革对于粮食供给的影响进行分析。
4、黄季焜等人的中国粮食模型。与IMPACT模型、 世界银行模型、美国农业部的CPPA模型不同,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黄季焜等人的模型是针对中国状况建立的模型, 它是建立更为具体的模型的一种尝试。这个模型主要包括稻谷、其它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供给模型,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对于稻谷、粮食、肉类及其它6 种畜产品的需求模型。对于世界市场上实际价格的预测则来自IMPACT模型的结果。该模型除了涉及到价格和收入变量外,还增加了诸如灌溉设施的改善、科技研究与推广以及环境退化等一系列结构与政策变量。
与世界银行的模型相同,此模型涉及的产品品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仅仅是建立在一个国家和一个部门(作物生产部门)的基础之上,因此该模型对于其它部门及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于中国粮食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效果的分析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5、美国农业部的CPPA模型。美国农业部的CPPA 模型是一个涉及农业部门的多品种、多国家的部分均衡预测模型。它主要用来对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需求和贸易状况进行动态的、理论上前后一致的按年度进行的长期预测。象其它模型一样,由于模型中使用的参数和弹性大都来自其它研究的成果,该模型也属于合成性质的模型。CPPA模型的基本结构是世界市场价格及宏观经济变量为外生变量,而政策、价格和收入则属于内生变量。此外,这个模型还可以与其它国家的模型连接并建立起一个用以分析世界农业状况的综合性模型。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模型,CPPA模型在市场开放的前提下,确定了各国间各种农产品的世界市场均衡价格。该模型涉及的产品范围较为广泛,既包括初级产品又包括加工品。
CPPA模型中的中国模型对于中国农业部门的描述是本文所提到的各模型中最为具体的一个。另外它还将中国粮食的供给情况划分为6 个地区(东北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南方地区)来加以进一步的分析。
6、OECF模型。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模型是一个多品种、 多地区(省份)和单一国家的预测模型。它对于供给与需求的预测是分别进行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贸易状况的预测。模型假定价格对于粮食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不产生影响,同时,供给的预测结果来自对于单产和耕地面积变化的估测。其中每种作物耕地面积的估测是建立在下述两个假设之上的:(1 )凡是播种面积在过去10 年间稳定增长的作物的面积在1993年后将保持1993年的水平;(2)播种面积在过去10 年间不断减少的作物的面积在以后的年份中将以相同的速度递减。对于单产增长幅度的预测主要是建立在1984-1993年10年间增长速度的基础之上, 但是单产的增加要以现阶段中国或世界其它国家单产的最高水平为限。
很显然,模型中大部分预测结果主要是基于过去的趋势,而政策的改变、技术的变革以及价格对供给、需求的影响都被忽略了。
六、结论:为什么各模型的预测结果存在差距?
这种预测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分析者判断的影响,但是我们很难说它对预测结果的差距影响到底有多大。然而,很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前几部分中对模型在三个方面的差异来解释预测结果为何存在着差别。通过对模型的宏观假定、参数及结构所作的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各模型的结果均显示中国将继续保持主要粮食进口国的地位。进口的品种是小麦,其次是玉米及其它饲料用粮。这反映出随着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中国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们的粮食消费偏好将由大米转向小麦及畜产品。
2.所有模型对于粮食需求水平的预测结果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关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幅度的假定基本一致,加之粮食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对较小,因此就粮食需求的预测而言,各模型的结果基本上是相同的。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模型预测的中国粮食需求增长幅度最大,这主要是由于它假定的中国人口增长率最高。
3.在粮食供求的预测中,粮食的供给通常是最难预测的。由于建模者对于将来技术变革及其它引起播种面积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的估计不同,使得各模型关于粮食产量的预测结果存在很大差距,本文比较的所有模型在预测粮食产量时主要依赖于专家的判断特别是对将来技术革新的判断。布朗及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模型预测的粮食产量最低。罗斯格兰特、黄季焜等人和世界银行对于耕地面积增长速度和单产提高幅度的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他们预测出的粮食产量值也是非常接近的。
4.由于大部分模型都是在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基础上来预测其净贸易量的,因此同粮食供给的预测一样,各模型对于粮食净进口量的预测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基于对中国今后粮食低产出和高需求的预测,布朗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预测的粮食进口量都是相当大的。其它模型对于2030年粮食净贸易量的预测处于4000万吨到8000万吨之间。
5.布朗认为中国可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今后将有一半转为工业和城市用地,同时单产的提高并不能补偿土地面积的锐减。这种对于中国粮食生产的悲观论调导致了他预测的中国粮食产量最低。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模型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使在70年代末期进行的体制与政策改革的积极效果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中国的谷物生产在1986-1995年还继续保持2%的年增长率。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较高的生产率增长幅度还会进一步得到提高。由于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被低估了30%〔5〕, 使得中国的单产水平并没有达到以前报道的那样高。随着价格机制正面效应的发挥,中国粮食的单产水平还会有所提高。价格机制不仅对生产者发挥作用,同时也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尤其是中国经济正处在迅速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今后的粮食供给将逐渐趋紧,政府自然会通过增加对农业科研与推广和其它公共设施的投资来提高粮食的单产水平。随着科学信息、及其它研究成果在中国研究人员和国外研究人员及国际农业研究中心间的交流手段不断完善,中国谷物和畜产品的生产率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布朗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的模型不仅忽略了价格机制的作用,还忽略了研究机构及政府对粮食高价格的反应。这两个模型的结果只是描述了在其它所有因素都不能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的情况下最黯淡的中国粮食供需前景。因此,我们不必对这些预测结果产生过多的焦虑,尤其是在制订和评价实现粮食的供需平衡产生影响的政策方面。
6.其余的模型,尽管采用的计量方法、 宏观假定和参数不同以及涉及的品种和国家不尽一致,但得出的2030年中国粮食的生产、需求和贸易状况却是非常一致的。这似乎显示了这些经过很好描述的经济模型的力度,因为他们准确地抓住了各部门及要素对经济环境变化所作的反应。尽管这些模型的结构已经很复杂了,但大部分模型依旧忽略了一些可对中国粮食经济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和因素。这些因素会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七、今后的研究
本文不仅为回答为什么对中国未来粮食供求的预测存在差距提供了初步框架,而且还指明了今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方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更加准确地把握各国复杂的农业市场状况以及政府的政策变化。并且在建立研究中国农业部门状况的经济预测模型时,注意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的政策变化。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 )认为中国存在的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政策问题。尽管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政府在指导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仍旧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很好地理解政府对于新的经济环境的反应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对今后的粮食供需趋势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新政策与体制改革对农业生产和营销效率的影响,可以由它们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促进要素投入产出关系的调整的能力反映出来。
2、与非农业的联系。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迅速转轨时期, 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正在逐步下降,水、劳动力、土地及其它资源也正在迅速地由农业部门转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模型中没有一个考虑到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农业投入减少对粮食供给和需求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产生的影响。 在今后的模型研究中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从全球的粮食经济来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今后供求状况的影响。作为一个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粮食进口或出口的一个微小变化都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段志煌〔(Tuan),1994〕。这一潜在的影响效果将有助于中国及其它国家的领导人制订发展战略以防止国内及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
4、畜产品生产的技术及结构变革带来的影响。 畜产品生产部门应该引起现有各模型制作者的更多注意。在大多数模型中并没有涉及畜产品的生产部门。在那些涉及畜产品的模型中,它的结构也被简化了。畜产品生产结构的迅速变化(由庭院经济转为商品生产)将会对今后中国的食品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技术与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肉料比的合理发展将会节约大量的饲料用粮。
(译者:中国农业大学 刘庆华)
注释:
〔1〕这些差异很有可能是由所使用的稻谷转换率不同造成的。
〔2〕联合国粮食组织(FAO)的预测结果是:2000年中国粮食产量可达3.98亿吨。辛普森(Simpson )认为在经济停滞和腾飞两种情况下,200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分别为3:7亿吨和3.78亿吨,2010年为4.21 亿吨和4.28亿吨,2025年为4.37和4.67 亿吨。 粮食及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预计2005年中国粮食产量为3.86亿吨。 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OECF)则估计200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在收入正常增长的情况下可达4.32亿吨,在收入高速增长情况下达4.41亿吨。
〔3〕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2000年粮食需求量为4.15亿吨,粮食及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的结果是2005年达到4.1亿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认为2000年粮食需求量在收入正常增长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分别为4.61亿吨和4.89亿吨, 他们采用的稻谷转换率为0.7。
〔4〕农业产品与贸易的政策分析模型。
〔5〕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耕地面积为0.96亿公顷, 而国家土地局近期公布的数据则为1.24亿公顷(柯炳生,1996)。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耕地面积进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