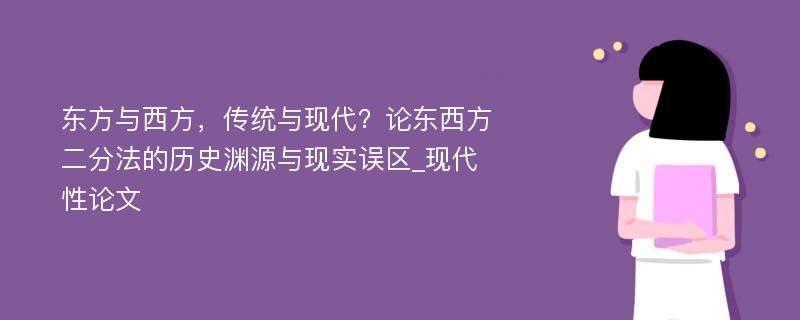
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论“东西方”两分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分法论文,东西方论文,误区论文,现实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下的中国,“西方”一词像幽灵一样徘徊于各个领域。政治上充斥着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提防,学术上则将诸多中国文化之外的研究领域都标上西方的标签,诸如“西方文明”、“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哲学史”、“西方经济学”、“西方史学史”等等,与此对应的则有“中国文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学”、“中国史学史”等等。“东西方”的划分,将我们的思维方式格式化了,以至于抛开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或术语,我们已经很难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学术思想了。姑且不论“西方”一词的政治含义是否准确,单就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似乎自晚清以来就从未彻底走出误区①。时值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重新审视困扰中国人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西学”话题,检索中西划分的前世今生,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笼统地划分中学、西学所犯的一个简单错误就是将不同时期的文明成果混淆到一起。不仅中国很多学者表现出这一倾向,在一部分欧美学者中也存在这种思维定势,将欧洲传统与现代文明整合一处,似乎西方文明天生就是现代文明,他们论著中的中西文明对比经常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段,如将前现代中国与现代英国或法国加以比较,以强化后者的文化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或许是一种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本能反应,当下中国有关西方化与现代化的话语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就是认同欧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整合,将一切现代化的成果统统归之于西方文明。这样就使得我们对“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历史上突飞猛进的发展成果存在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接受,而不管是全面接受还是部分接受,都可能被定性为西化;另一种是排斥,更多表现为态度上的对立和语言上的不服气,看到的都是现代文明的弊端,将现代社会的一切乱象皆归咎于西方文明发展的恶果。而抵制现代文明的一贯方式就是回归传统和倡导本土认同。所谓本土认同,除了对传统文化的眷恋,更多的可能还是对于话语权的争夺。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混淆让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起步就打上屈从的烙印。对很多非西方人来说,似乎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要跟西方人平起平坐,他们只能以本土文化的面目出现,不然就难以摆脱自身“追随者”甚至“被征服者”的身份。而要以本土文化的面目出现,他们就把人类近代文明进步的一切成果都拱手让人了,留给自己的,除了回归传统文化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换言之,把理性思维方式在内的一切现代文明归功于西方,就会窒息自身的发展活力,堵塞自己在现代世界的发展道路。 严格意义上说,所谓西方文明、欧洲文明、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等等,所指都应该是现代文明出现之前局限于某一地理空间的区域文明。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现代文明,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也就是人类历史真正步入世界史阶段之后,经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融合而形成的。在欧洲的纵向变化,则是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和社会变革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将这一历史性转折称为“人类历史必然经历的‘断裂’(discontinuities)”②。吉登斯并未否认“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延续”,但却认为过去三四世纪“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③。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一个世纪欧美学者在寻求现代性的欧洲渊源方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触角遍及地理环境、矿产资源、财产观念、契约文化、宗教伦理等各个领域,以此来争取欧洲对现代性的专利权。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证明,在现代化的大势下,任何传统文明都不能孤立地原汁原味地存在。然而,为什么不少学者在谈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或者中国文明时,还要采用一种纵向思维,不加区分地拉通整个前现代与现代的历史,而去认可某种孤立的、单一的、纯粹的、独特的文明形态呢?原因在于,现代性在向人类昭示了一种全新的空间观念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新的时间观念,那就是具有线性特征的进化史观。杜赞奇将其追溯到黑格尔《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将以理性为目标的精神发展的历史抽象化、进步化了,而这一发现“为马克思主义、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继承”,在过去两个世纪主导着人类的历史观④。吉登斯提出识别“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分离出来的断裂”的三个要素,即现代化变迁的速度、范围和现代制度的某些固有特性,这些特性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截然区分开来⑤。 然而,要清楚认识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以及东西方划分的误区,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是不够的,还需回放历史变迁的场景,探索“东西方”概念出现的历史渊源,辨析造成这一思维定势的心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跳出近代欧洲知识精英主导的现代话语模式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线性历史观,重新认识和建构人类文明史和“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世界史。 一、东西方划分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上看,东西方的划分既有地理上的原因又有文化和政治上的原因。欧洲“东西方”概念的建立始于罗马帝国时期。那时存在于东地中海地区的是高度城市化的文化,以希腊语为他们的共同语言,更为乡村化的西方则是以拉丁语为共同语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天主教影响下的西部和中部欧洲与拜占庭希腊文化和东正教影响下的东部渐行渐远,形成不同的文化认同。随着公元7世纪伊斯兰帝国的崛起,古代的东西方形成长期对立之势。“在这一重大而影响深远的转变中,形成了欧洲的认同,被阿尔卑斯山隔开的南北欧合而形成中世纪基督教欧洲”⑥。与此同时,他们对那些在地理上位居其东部的民族、文化或者国家则以东方相称。从古代的波斯帝国,到中世纪后期的土耳其帝国,再到“地理大发现”前后的印度和中国,都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众多历史资料显示,“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心目中东方的范围一再得到扩大,从中东延伸到远东;随着其自身认同与价值取向的联系日渐紧密,对东方的认识也逐步形成浓厚的文化偏见。20世纪中后期的冷战再一次改变了东西方的划分,“西方”的概念不仅包括了原来作为欧洲殖民地的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还经常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等亚洲国家包括在内。 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的绪论中专门对美国人的东方观与欧洲人的东方观进行了辨析。根据他的观察,对美国人而言,“所谓‘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而法国人和英国人——还有德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尽管没有法国人和英国人那么明显——则与美国人不同,他们有着我称之为‘东方学’(Orientalism)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⑦。这种他者形象一旦形成,便逐步超出了地理范畴,成了欧洲人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立物。 中国历史上对“西方”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始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明朝中期。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欧洲对中国的介绍,还是中国对欧洲的听闻,大多是通过偶然穿行于两地之间的商人、军人、旅者的道听途说,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马可·波罗游记》,以至于多数欧洲人不能分辨赛里斯、契丹、蛮子国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中国。有学者总结说:“欧洲人这种模糊、错误的地理概念,直到16世纪才由西班牙奥斯丁会士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第一次在文字上指正,到17世纪才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Ricci Mathew,1552~1610)最终确证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⑧也就是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与欧洲彼此的认识是模糊而支离破碎的。 毫无疑问,早期欧洲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相互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6世纪以来基督教传教士的信息传播,也正是在这种传播中,形成了欧洲知识界更为系统化的东方观,从而也形成了中国人将开始于欧洲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误解。中国媒体对欧洲诸国较为系统的介绍部分归功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的蔡尔康合作翻译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的《泰西新史揽要》(英文原名为The Nineteenth Century,即《19世纪》)⑨。从中英文书名的转译中即可以看到,麦肯齐讨论的“19世纪”应该是欧洲的现代史,而到了中国人眼中就成了“泰西新史”。对于对欧洲传统所知甚少的中国人而言,新旧已经无关紧要,关键词成了“泰西”。经过这样的转换,“19世纪”的历史,就成了“泰西史”或者“西方史”了。由于传教士的作用,中国对欧洲的了解一开始就超越了直观的认识,完成了一种新的知识建构和生产。正因为如此,当大批欧洲船只出现于中国的东海岸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被中国人按过去的方位习惯叫做“东夷”,而是沿用了李提摩太的“泰西”称谓⑩。 东西方的划分,开始或许是受到地理方位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划分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含义。从早期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到晚近的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人,无不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经常会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东方社会。及至20世纪50年代卡尔·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出版,通过对自然环境和所谓“治水社会”等因素的分析,更将东方国家与专制制度绑在了一起。为了证明他的推断,魏特夫无视至少可上溯到罗马帝国后期的东西方划分,而将之归因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观察到的“近东、印度和中国文明所具有的制度共性”,并认为这些共性“既没有存在于古典时代的欧洲,也没有存在于中世纪和现代的欧洲”,因此欧洲的思想家们称之为“东方”或“亚细亚”社会(11)。的确,16、17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在观察中国、印度等国的文明形态时,自然会更感兴趣于那些不同于其自身文明的特征。然而,这种标签化的做法最终让他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进而强化了他们对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偏见,淡化了他们对中国、印度等国历史上早已出现的“现代国家元素”的认识和探索。而后来的欧洲人,包括前面提到的我们熟知的一些思想家,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叠加新的内容,建构起所谓的“东方主义”,一个与欧洲或者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他者形象。令人不安的是,刻意强化东西方划分的不仅有立足于“欧洲中心论”的欧美各国的思想家们,也包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处境深感忧虑的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学者们,如果说现代民族主义在欧洲是一种现代化的自然生成,而对于中国等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则更多是一种对外来入侵和压迫的反应,关于东西方划分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 二、围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论争 除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到来后引起的局部的(如历法方面)东西文化之争,以及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期间在应对西方冲击时出现的“体用之争”,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有关东西方文化的讨论至少有五次。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文献集对前四次大论战作了总结,用他的话说:“这四次大论战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1915~1927年),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1933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新论战(30年代至40年代),关于中国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20年代至40年代)。”(12)如果再算上他在编写此书时所经历的80年代后期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20世纪出现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论争应该有五次之多。 根据罗荣渠的总结,在“五四”前后长达十余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声音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在其《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的成见。他指出:“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来谋人类对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罗荣渠认为这篇文章是西化论者在这场大论战中的代表作。他评论说:“从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重新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13) 第二种声音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这位晚清以来中国最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曾经敞开胸怀拥抱所谓西方文明。然而当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个文明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个正在经历成长的痛苦的欧洲。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在高速发展阶段暴露出各种社会问题。用罗荣渠的话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被沾满了血污,于是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在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金子马治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在这些新思潮的激荡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一个大转折。曾经讴歌过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方文明的幻想破灭了。”(14)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提出“中西互补”论。罗荣渠认为,“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论,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反现代化思潮。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15)。 第三种是梁漱溟所代表的本土派。在其出版于1921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接受并发挥了梁启超的新观点,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罗荣渠对此评论说:“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反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16) 与以上三种观点相比,蔡元培的兼容东西方文化传统,追求真学问的思想也许更为理性。他比较东西方价值观的相似之处,如将“自由”比作“义”、“平等”比作“恕”、“博爱”比作“仁”的思路,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倡导“世界公民”的策略,不啻为一种打破文化界限追求真理的理性之举。他试图冲破文化自恋与文化自卑的双重误区,建议将东西方文化平等地置于一池(common pool)而筛取各自的理性成分。遗憾的是,这一要求东西两方均放弃自我追求普适的见解却被带有“西方中心论”偏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瑟夫·莱文森看作是对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的抚慰(17)。 显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中还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西化”与“现代化”的区别。中国人之所以将现代化误认为是“西化”,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开始就是以“西化”的面目出现的,而且在最初出现时就给中国人在心理上种上了被动、屈从的情结。大部分中国人只是到19世纪中期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并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之后,才开始认识已经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的欧美国家,所接触到的现代的物质、精神文化无不打上西方的烙印。因此,在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辩与交锋中,无论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政治家们,都很难摆脱对西方亦步亦趋充当小学生的弱势情结。知识分子如梁启超、梁漱溟等在认识到欧洲文明的诸多优越之处时,不是心悦诚服地虚心学习,而是寻找各种借口为不得已的“承受”取得心理平衡,其表现形式就是梁启超的“中西互补”说与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政治人物当以孙中山为代表。罗荣渠写道:“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他得风气之先,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他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结合,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18)无论器物、制度还是文化,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们都希望能够采取“最直捷之途径”以超越欧美,惟其如此方能一雪前耻。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之后,知识分子又重拾古今中西话题。除了罗荣渠在北大领导的现代化研究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学者如甘阳围绕中西古今之争提出的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观点,尤其是他对固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分界的质疑,现在读来都不为过时(19)。跳出线性史观,重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断裂,是这一时期新生代学者在广泛接触欧美最新研究成果之后获得的思想突破。 三、是否存在中国的现代性——对“多元现代性”的反思 20世纪后半期有关现代化的讨论在中国大陆之外从来没有停歇过,其中以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的“中国的现代性”理论最具代表性。金先生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至少可推至20世纪60年代《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问世。在这部著作中,金耀基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并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成绩之所以不理想,“乃是由于中国的本土运动中具有反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两股势力。这两股势力削弱、抵消了现代化的力量”(20)。显然,金耀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出路时萦绕于心的还是既要“现代化”又要保持“中国文化”这一难题。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金先生还对中国的现代化成绩忧心忡忡,那么到2004年他的另一部力作《中国的现代转向》初版时心情就大为改观了,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不仅有了台湾等亚洲“四小龙”步上现代化的先例,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让一批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学者顿时有了底气。而90年代问世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让金先生的“多元现代性”理论找到了知音,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金先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观点,即建立在“多元文明”框架下的“中国的现代性”。他注意到,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非西方人因现代化之增加,不但没有被“西化”淹没,反而增加了对本土化的认同。如果说美国右翼学者亨廷顿是以一种忧虑的眼光去看待本土化趋势,金先生则对此充满乐观。 尽管金耀基认同诺贝尔文学得主、墨西哥诗人帕兹的话,认为现代化是“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21),但却并不赞同欧美学者提出的忽视文化特征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即认为“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社会在步上工业化之路后,不论起点如何不同,最终必然越来越走向近似的工业体系以及相关的社会与文化形式”(22)。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也不能是摆脱历史的运动。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进行的。一切现代化的社会,不论是西方的或东方的,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等,但同样的,任何现代化的社会也必然具有特殊的性格。英、美、德、法都是现代化的社会,但就我所知所见,他们都有各别的风格与面貌,即使东方今日现代化的日本,也复如此。各现代化社会之所以同中有异,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各别的人种、语言使然,而是他们的历史文化使然。”(23)可以看出,金先生的思维完全为线性史观所主导,而对吉登斯提醒的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无所觉察。为了描绘“中国的现代化”蓝图,他分析了台湾和香港现代化之后的传统元素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并据以相信中国人能够建立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文明秩序(24)。金先生所说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个性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过分强化个性支流而抹煞共性主流显然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如果因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了某些传统文化因素就可以称作“中国的现代性”,那么金先生上文所称“风格与面貌”各异的英、美、德、法的现代性是否也各有归属,可以分别被称为“英国的现代性”、“美国的现代性”、“德国的现代性”、“法国的现代性”呢?如果都可以这样认定,那么金先生力图论证的“中国的现代性”还有多大意义呢? 金先生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那无法抹平的“西方化”伤痕。我们从金耀基的论证思路可以看出,尽管他试图摆脱“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运动的几个面向”(即保守主义、全盘西化和中西合璧)(25),用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却始终对“西方化”如鲠在喉。他坦言:“在东亚,人们总是说他们追求的是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但从某种程度上看,东亚现代化很难逃出西方化的如来佛手心。”(26)金先生的意思是,不管我们怎么标榜自身的现代化,都还是西方化。原因在于,“现代性首先是在西方实现的,最早的现代性是西方的现代性”(27)。仅仅因为西方首先开始了现代化,就把后来的所有现代化实践都称作西方化,同样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诚如前文提及的何兆武先生的比喻,如果我们不能因为希腊人发明了几何学就把几何学称为希腊学,也就不能把欧洲人开始的现代学术认定为欧学或者西学。我们不能因为汽车最先是在美国发明的就把任何国家生产的汽车都叫做美国汽车:一辆新款奔驰与当年初创的福特汽车相比,虽然制造的基本原理一致,但结构、功能不知复杂了多少倍,这些补充成分包含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发明家和制造商的智慧,谁还能把它称作美国汽车?汽车的设计与制造经历了一个一国首创、不同国家不断改进的过程,固然不能将其归于最先拿到专利的个人或者国家,由不同国家知识精英在不同时段参与的启蒙思想,自然也不能归于哪个国家哪个区域所有;现代学术也经历了欧洲肇始、全球贡献的漫长发展历程,不能不顾后期汇入的众多河流而只认其欧洲源头。 金耀基的“中国的现代性”观点也在部分欧美学者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和认可。曾经长期在台湾中研院任职的沙培德指出:“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是全球和国内环境急速变化的产物。同时,恰恰是由于对启蒙的追求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并受其影响,一种特殊的中国现代性呈现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性因而存在于众多具有相似行为模式的群体中,并为这些群体所追求。他们具有共同的行为习惯、处事规则、话语和制度。”(28)沙培德将“中国现代性”理解为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地方化现代性,与金耀基的文化论已经产生了距离。 沙培德试图回到现代性的本义去梳理普世的与地方的现代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学术界的解释有很多,但还没有提供一个全面、权威的定义。沙培德跳过众多说法,提出两条他比较认可的定义:一个是他称之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自我形象中的与过去不同的感觉,一些与早期文明形式的根本断裂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重要的。这一觉察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后无论是以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形式都只能被扩大化。两种与这一新感觉广泛联系在一起而又彼此关联的特征是世俗与理性”(29)。第一种特征比较明确,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文化祛魅。而(工具的、形式的、官僚化的)理性,在沙培德看来,自韦伯以来一直与现代性的核心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从韦伯转向福柯,一个看来十分自然的转移,我们就能看出‘理性’在现代是如何通过权力机构的形式得以扩散的。先进的民族国家获得了空前的强制力和通向财富的途径,作为一种殖民势力,它维持或者协调着一个广阔的网络,一个通过官僚形式组织起来的管理者、军队、农场、工厂和学校网络。不仅如此,通过创造出公民和殖民地属民,它发展出一套将价值与纪律内化于个人的手段。”(30)鉴于此,沙培德写道:“事实上,中国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理性化过程,包括管理、消费文化的到来,产业工程和处心积虑地对‘新’的展示。”(31)显然,沙培德在谈及中国的现代性时关注的是中国自20世纪初期以来理性化的经验。与金耀基强调传统文化给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留下的烙印不同,沙培德强调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现代化因日常生活的影响而产生的地方化或者地方经验,但这种区域特征或地方经验不能改变或者背离现代性的共同特征,否则也就不成其为现代性了。 四、全人类共同的现代化进程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获得突破性发展。跨越封闭体系的方式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包括军事征服、商业往来和以宗教传播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交流。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碰撞与同化,都对文明发展起到刺激和促进作用。欧洲早期文明的发展同样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各种方式的接触与交流。有研究者指出,希腊文明是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地中海上相遇而形成的再生文明。从文化上讲,远古的希腊原本是周边不同民族的殖民地,希腊社会事实上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社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在这里聚合交流,才创造出早期的灿烂文明。这段历史发生在公元前14、15世纪,与摩西“出埃及记”中记录的移民流散时间大致相当。又有记载说:公元7、8世纪阿拉伯人对原属波斯帝国的中亚、北非、南欧等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的征服,使他们掌握了比一千年前的希腊人所拥有的更为丰富的知识。欧亚大陆的文明史告诉我们,文明正是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交流、传递中获得改进和发展的。 在其对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历史冲突的研究中,俄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伊利亚·盖杜克(Ilya V.Gaiduk)认为,要计量欧洲与阿拉伯世界在几个世纪的冲突与交流中彼此施加的影响是困难的,“很难判断是欧洲还是伊斯兰输出了最有影响的思想。从穆斯林世界输出到欧洲的数字与零的概念,推动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发展。没有这些欧洲人就不能实现其科技飞跃,更不用说称霸世界了。而民主、自由的理念,通过拿破仑的埃及远征被带到了伊斯兰,并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激发了社会改革”(32)。美国人马克·格莱汉的著作《伊斯兰怎样创建现代世界》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伊斯兰文明对现代化的贡献。这位与马丁·雅克一样的业余历史学家通过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证明,伊斯兰文明才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接力手。他指出,“在中世纪的欧洲,任何从罗马时代传承下来的医学知识几乎都被遗忘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医院根本不存在”。公元805年在巴格达建立的比玛丽斯坦才是第一家现代化医院(33)。 早期的文明接触与知识传播也许与现代化运动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却足以说明接触与交流是文明进步最为重要的契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文明进步是从长时段、整体历史的角度着眼的,因为短期、局部的文明接触,尤其是前现代军事征服带来的文明接触,常常会造成一个时期局部地区文明的断裂和倒退。穆斯林世界输出的不仅仅是阿拉伯数字,还有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文化专制主义;蒙元对中原征服的直接后果是唐宋以来该地区臻于成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破坏和中断。即便如此,我们从全人类的整体历史中还是可以看到文明接触的积极作用,而这种接触的现代意义,在“地理大发现”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之后得到了全面展示。 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无论是早年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中心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接触对彼此产生的影响(“冲击—反应”模式只看到单向的影响)。近年来部分美国学者对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亚文明的海上接触作出一些新的探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客观地观察在现代文明曙光中亚洲人和欧洲人相互交织的身影。在对其主编的《中国与航海时期的欧洲》一书的介绍中,小约翰·E.威尔斯(John E.Wills,Jr.)强调了欧洲船队进入印度洋之际亚洲各国在这片水域已经建立的繁荣的海上贸易。他指出: 根本的变化是从“欧洲扩张”视角转向“亚洲航海史”视角,前者将欧洲最终对长途海上贸易的控制看作是欧洲人进入印度洋之后不可避免的、可以一蹴而就的结果,而后者将亚洲的统治者、商人、航海家看作这一时期亚洲航海格局形成中积极有效的参与者。今天,亚洲航海史的研究非常本土化了,根植于亚洲各个区域的历史记载,也经常包括亚洲学者的成果。它将许多重要的航海发展看作“交互作用的呈现”,是亚洲各文明特色与欧洲闯入者特色相互影响的结果,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在于亚洲的生产能力和成熟的商业网络,如果将我们的分析划分为“欧洲冲击”和“亚洲反应”是讲不通的。(34) 沙培德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也认为,“20世纪初期将现代等同于西方的想法简单地忽视了推动现代化的全球过程”。他补充说:“近来的很多研究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和政府形式源自殖民体系,甚至更为确切地说是早期全球贸易体系。”(35)学者们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贸易和欧洲殖民体系建立等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全球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参与其中的世界现代化的酝酿过程,对于我们解构欧洲话语主导的世界现代史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名噪一时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新全球秩序的诞生》一书中,记者出身的马丁·雅克(Martin Jacues)从他自己定位的西方视角,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崛起的前景。尽管在严肃的史学家眼中,雅克的断言未免有些虚妄,但他以外行人的眼光的确看到了一些往往为专业史家所忽略的现象。从雅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与在欧美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的观察:15世纪的明代中国,无论是皇帝还是文人,其思维和言辞均离不开过去,远则三代,近则唐、宋,再不就是“国初”、“太祖”;中国人理想的社会是孔子之前的三代,而欧美人的理想社会则是旧约《圣经》中的古代以色列。一直到17世纪新大陆开辟以后,英国的清教徒们还期望到那里去建立一个干净纯洁的上帝之城。雅克在其书中指出: 直到18世纪后半叶,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去的形式被感知的。与之相应,未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清晰的观念,而是被当作对过去的重复或者重建。在一个大部分人生活在陆地,变化极其缓慢的世界,这是可以理解的。物质环境与日常生活孕育出一种哲学和宗教,重建并且敬仰过去。在日常生活和艺术、文学中受到重视的价值是那些经验、年龄、智慧、等级与传统。变化只有在不危及宝贵的属于过去的观念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和认可。即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人生活中的两支奇葩,也如它们的名称所示,是以过去的形式引导的,尽管它们所包含的事实上更多是关于未来的、新颖的。……从18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现代的到来,人们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改变。现在的人不再生活在过去,而是越来越朝向未来。(36) 沙培德在提到有的学者将现代与传统分离时,引用了安东尼·吉登斯的讨论,指出“现代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形式上区别于所有传统秩序”(37)。显然,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欧洲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岂止是欧洲传统社会,甚至与美国的传统社会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南方奴隶制被废除以前,美国的拥奴派倡导的“符合自然差别的和谐社会”,就是要维护白人奴隶主对黑人的长期压迫和剥削。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是将社会和谐与稳定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与传统基督教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不能说基督教符合现代精神,而儒家文化是中国特色。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都经历了从传统的不平等社会向现代平等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并非一帆风顺,也非一蹴而就,常常要克服巨大阻力和抵抗。北美殖民地诞生之初就是按照不平等的社会蓝图设计的,即使经历了启蒙运动洗礼,“美国革命”教育、《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中对诸多权利观念的宣传和普及,美国还是将违犯人权、平等观念的南方奴隶制度保留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现代思想的最基本内核是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正是“地理大发现”后文明碰撞、交流、比较、融合的结果。当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偶然性交流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代。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欧洲人已经了解到中国以江南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水路贸易网络、精细的劳动分工和庞大的工业品市场等等,这些现象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才出现于欧洲(38)。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强调:“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39) 近年来中国国内一些有影响的研究已经揭示了“中国观”对启蒙时代欧洲新思想的激励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帝制时期的官僚体系及其选拔和管理方式给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提供了现代政治制度设计的有益参考。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40)卢梭也在《论政治经济学》中颂扬中国的行政和司法,盛赞中国皇帝的民本思想(41)。也许他们通过传教士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并非全都准确,但不能否认这些信息给他们带来的思想刺激和知识冲击。 然而,启蒙时代之后的一批欧洲现代学者,包括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等著名思想家在内,在回顾欧洲现代化转型时,已经受到线性史观的左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追溯到希腊、罗马时期的民主、共和政治,并没有给“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文明交流与碰撞以足够的关注。当代部分学者为了让这种文化承传看上去更为合理,宁愿从过去被打上“黑暗时代”烙印的中世纪去寻找现代萌芽的蛛丝马迹,也不愿正视“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文明交融之功。当然,也有一些史学家早就关注到东西方交流对于近代西方崛起的决定作用:“即使在交流微弱的时期,是欧洲,而非亚洲,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42)中世纪欧洲的封闭与孤立显然制约了其思想文化发展,如果知识精英天天思考的是一个针眼中可以穿过几个天使,怎么能够产生惊世骇俗的科技发现?或许是为了突出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某些联系,有人举出牛顿科学实验的宗教动机作为佐证。即便如此,又如何解释这些掺杂了宗教动机的科学探索为什么只出现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欧洲,而在此之前却是数百年的黑暗与沉寂?众多史实证明,以“地理大发现”为分水岭的欧洲扩张及其所带来的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爆炸,才是欧洲人在现代思想与科学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关键。 即使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的东方学,也是西欧文明与其他文明接触、碰撞的结晶。用萨义德的话说:“东方是欧洲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43)另有学者的发现呼应了萨义德的判断,认为东方学作为一种科学,对于路易十四时代的知识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商人和传教士对于东方各国的见闻记录,成为法国科学进步的动力:“观察对于信息的证实与采用起着关键作用,不仅对卡尔波特(Colbert)如此,而且对全欧洲的科学家们的证据收集都是这样。”(44)近代早期法国著名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1529~1596)在其一系列著作,尤其是《共和国六书》中,对奥斯曼为核心的东方专制政权进行了分析评论,将奥斯曼帝国以及其他古老和近代的王国作为法国的镜鉴来分析何为理想的政府。虽然孟德斯鸠的比较政府理论最为著名,让·博丹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要比孟德斯鸠早了一个半世纪(45)。 在谈及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刺激推动了思想与科技进步的时候,人们总是想到正面的文化制度对负面的文化制度的推动作用,而忽视后者对前者的刺激作用。与让·博丹相似的是,孟德斯鸠也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宫廷中的负面经验作为其论述的依据。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这位法国著名汉学家,虽然终生未曾到过中国,但却出版了非常翔实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1735)。根据杜赫德的描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专门谈到“中国奢靡的严重后果”。尽管杜赫德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靠别人的转述,而对于孟德斯鸠来说,这些有关中国的描述更是道听途说,但我们不能不佩服其政治眼光的敏锐。他眼里的东方君主“将他们自己关在宫廷里,其精神变得懦弱,其寿命短暂,皇族凋零,强人崛起,宦官专权,只把孩童置于皇帝宝座;宫廷变成帝国的敌人……皇帝被篡权者弑杀”(46)。在《法的精神》与《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都把帝制中国和波斯帝国当作探索宫廷权力的反面教材加以引用。通过商人和旅行家口中传播的东方,“不仅是专制与奢侈的场所,而且是色情堕落的集聚地”。根据图夫茨大学教授麦克卡伯的观察:“这些被天主教视为罪孽的东西先是被认为来自‘他者’(例如,波斯人),然后很快反映到法国内部新的政治‘他者’身上,他们就是可恶的贵族阶层。在很多激进的政治描述中,宫廷贵族都是穿着东方马甲的。”(47)在这里,东方学或者东方主义从反面激发了欧洲现代思想巨匠们的创作灵感,也许不能说东方的某些专制文化对现代思想有什么贡献,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交流之功是不能抹煞的。正是基于对文明交流作用的观察,麦克卡伯得出其具有关键意义的判断:“17世纪支持法国帝国梦想的不是军事入侵,而是狂热的传教士、旅行家和收藏家们。商业裁判、贸易协议、科学观察和收藏都是早期帝国主义的工具。有一个庞大的信息网,其成员通过旅行、绘图、描述和收藏来了解这个世界。在路易的思想中,皈依是与科学努力密切相关的,很多传教士都是科学家。天主教、科学和商业传教使团之间并无矛盾之处;传教士并非不关心法国的商业利益或者法国外交。事实上,他们都是其最好的工具。在人文学科与新兴的科学之间没有界限,虚构的分野得到合理的质疑。在科学学会的初创阶段包含着东方主义。”(48) 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有关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同样可以证明,首先发生在欧洲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地理大发现”后出现的文明接触、碰撞与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早期学者,如魏源、严复等,所关注的主要是欧洲先进思想的介绍,那么民国初年以来的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陈垣、张星烺、向达、冯承钧、方豪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为中西交通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史料,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后新一批史学工作者从视角选择到研究方法又多有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于2000年的吴梦雪、曾丽雅合著的《明代欧洲汉学史》。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作者对明代欧洲汉学形成过程中的一批重要著作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从中反映了“地理大发现”之后,通过欧洲传教士的作用,中国文化对于启蒙时代初曙阶段的欧洲现代思想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可低估的借鉴和启迪作用。而张国刚、吴莉苇合著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则让我们更为全面地看到了中国文化对启蒙时代的欧洲,尤其是欧洲思想家们广泛而深刻的影响(49)。 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之前,在“地理大发现”中起了先锋作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人、军人和传教士们就已经开始从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接触中了解中国。这个时期最早的一部著作是皮雷斯完稿于1515年的《东方诸国记》,其中对中国的介绍“多半依赖于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信息”,尽管仍停留于表面,但较之于马可·波罗时代近乎传说的描述更为准确可信(50)。而其后陆续出现的佩雷拉(Galiote Pereira)的《中国见闻录》、科鲁兹(Gaspar da Cruz)的《中国情况记》、巴罗斯(Joao de Barros,1496~1570)的《每十年史》、以及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568)的《大中华帝国史》,则将介绍对象专注于中国的文化制度和风土人情,让欧洲人对中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尤其是门氏的《大中华帝国史》,“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林林总总,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向欧洲作了那个世纪最为完整的介绍,从而构成了西方早期‘中学’的基调,为欧洲汉学的形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51)。 如果说早期有关中国的介绍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的话,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晚明至清初的来华传教士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则是居功至伟。诚如吴、曾二位学者所言:“将中国文化有系统、大范围、深层次、多方面地介绍到欧洲,非耶稣会士莫属。”(52)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播的科学与文化知识在明清中国只能引起少数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他们传递回欧洲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却吸引了较多知识精英的兴趣。其实,直到18世纪末,欧洲知识界和政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印象还是“积极正面的,甚至是激情狂热的”。萧邦齐(R.Keith Schoppa)对当时欧洲人的“中国热”描述道:“中国事物变成欧洲旋风。欧洲人复制了中国的壁纸、室内装饰和家具;凡尔赛和伦敦的精英房主们建造了内有亭阁的中国园林。欧洲的保皇派和启蒙派哲学家们都充满激情地讨论着政府的中国模式,开明或仁慈的专制主义”。(53) 毫无疑问,来自中国的事物和信息在一段时期对欧洲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冲击,至于何种信息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是难以准确估量的。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是否因其热衷中国文化而从《易经》中受到启发也许是个谜案,至少伏尔泰对儒家文化、科举制度、文官制度的评价说明这些中国文化元素在他的大脑中引起了反应。可以断言,正是“地理大发现”之后通过大批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东方知识,激发了欧洲人的“头脑风暴”(brainstorm),为后来启蒙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盲目追随部分启蒙思想家们的“欧洲中心论”思维模式,将“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在现代化上的领先地位看作自希腊、罗马以来的文化基因所致,显然忽视了文明之间交流、碰撞所产生的驱动作用;而过分强调中国历史上的“理性主义元素”,动辄以中国历史上有过某种元素来排斥和抵制现代化潮流,就会陷入“传统文化自恋症”而自我封闭,其结果必然是重复历史上被动挨打的局面。 五、传统、现代与后现代 中国学者对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认知明显受到欧美学术潮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以“文明进步”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杂糅着迷信、宗教复兴和尚古论的新传统主义在世界很多地区得以崛起。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54),学术关注点由对普世文明规则的追求转向对具体文化传统与经验的理解,“边缘”、“非西方”、“非主流”、“亚文化”、“失去的声音”和“被遮蔽的真相”成为学术界力图挖掘以矫正历时数百年的“西方中心论”话语的热点。左翼批判在攻克了“西方中心”之后开始将目标指向其他各种中心和主流,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清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得以崛起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基调被严重质疑,甚至传统社会中的女子缠足陋习也在学者们的重新审视中获得同情的理解。这种思潮也波及开放不久的中国学术界,80年代的文化讨论,除了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五四”以来传统与现代的攻守,还受到海外带有民主化倾向的左翼思想的影响。正如甘阳当时的观察: 从目前看来,海内外的许多论者似乎都持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所谓“反‘反传统’”的态度或倾向。这种倾向认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把“现代化”与“西化”不恰当地等同了起来,以一种全盘否定的“反传统”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因此在客观上“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造成了所谓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带”。因此,今日的任务显然是应努力去弥补这种断裂,以“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55) 甘阳认为这种对传统的眷恋和对“断裂”的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文学中的寻根意识”自有“一番辛酸苦辣在内”(56)。把“传统”或“文化传统”看作“已经定型的过去”就造成“唯恐中国人变成不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不成其为中国文化的种种心理”(57)。甘阳指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58)国外学者也有类似论述,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看起来或者声称古老的‘传统’经常源自晚近,并且有时是被发明的”。“‘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指的是一系列实践活动,而控制这些实践活动的通常是一些被心照不宣地接受的规则、礼仪,或者象征性特征,它们通过不断重复来反复灌输某种价值和行为方式,从而自动延伸着过去。”这样我们在“不断变化、创新的现代世界”中会看到一些“构建不变而一致的社会生活成分的努力”(59)。换言之,传统经常表现为嵌入变化、创新的现代世界的某些“不变”成分,它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现代化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是基于理性原则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文化制度的不断探索,是在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下,人类对于各种现代实践活动的调适、批判与纠正。为了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扰,人类经常需要诉诸传统文明中的智慧,既包括欧美社会中的基督教福音改革,也包括中国儒、释、道思想中的仁爱观、正义观、善恶观以及对自然界的敬畏与尊重。当欧洲早期的殖民活动在非洲和中南美洲大肆荼毒生灵时,被现代性排斥的基督教传教士尾随而来,通过开办学校、医院以及慈善机构,缓解了殖民主义给本土居民造成的痛苦;当奴隶贸易横行大西洋时,是罗马教廷首先提出尖锐的批评,发出废止的号召;当19世纪后期美国急速发展的工业化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垄断、腐败和环境污染时,是基督教福音派推动了改善社会关系的进步运动。历史证明,被现代科学主义轻视、排斥的很多属于传统文化的宗教、伦理、文化、风俗,经常会在现代化的刚性诉求中起到缓冲作用,慰藉着人们脆弱的心灵。 当然,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现象的批评并非总是需要诉诸传统,19世纪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曾引起马克思等欧洲知识分子的广泛担忧,并因此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形成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为严厉的批判和对现代化选择的最为积极的探索。20世纪以来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对现代化进程中某些极端现象的批判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反思和批判在更为广泛的层面展开,形成所谓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是19世纪以来全球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批判的继续;后现代实际上并未超越现代,只是通过另一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调适着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 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些试图修正现代性的理论、行动常常会因为矫枉过正而造成出乎意料的后果。过去几十年获得发展的文化多元化、本土化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少福音,反而鼓励了宗教和文化中的极端势力和偏执情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作为现代化副产品而崛起的民族国家之间的隔阂与界限。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早在19世纪就被马克思主义所摒弃,在人类面临愈来愈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权践踏等等)的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人类争取福祉的障碍了。亨廷顿等欧美学者清楚地看到了文明冲突带来的危险,但却因其头脑中东西方划分的思维定势,只会从其文化本位出发探索文明出路,其胸襟和视野使之难以为人类文明指引未来的发展方向。 相比之下,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可能更有预见性。他认为,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以及为追求狭隘国家利益而带来的冲突和灭亡。而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只有具有“天下主义”传统的中国才能担当此任(60)。汤因比在20世纪80年代的预言不免会让一部分中国学者感到振奋,岂止是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自然观、佛家的慈悲关怀,都可以成为医治现代病的良药。然而,如果因此而让中国思想界抛弃现代化的努力而回归传统,则必然陷国家未来于危险之中。如果中国真要担当起拯救世界的大任,首先要做的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实现充分的现代性,不仅经济上要成为全球的支柱,而且制度、文化上能够取信于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领导作用的英国和仍在发挥领导作用的美国可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镜鉴:他们无一例外地首先抢占了文明的制高点——作为现代启蒙思想策源地的英国曾经是人类最先进思想的泉源,而美国自开国以来一直追求制度、文化上的高标准,以民主、自由等所谓“美国信条”吸引着全球的精英络绎不绝地汇聚而来,形成持之不懈的软实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的文化、政治精英中不乏种族主义者和文化优越论者,但其治国理念很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干预,无论是对内对外,尚未见到哪届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宣扬清教文化或者其他基督教思想。因为他们清楚,与现代理念相比,任何对传统文化的宣传都带有狭隘性、排他性,不会产生持久的文化吸引力。只有站在现代文明的制高点,才能引领文明走向,引领现代世界。 金耀基在其书中引用了“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an)1991年的一本书,名为《第一次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其中写道:“要建立一个全球社会,没有一种共同,或能包容多种文化的价值观作为基础是很难想象的。只有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上人类才能共同面对挑战,也才会有道德力量去因应世界的变化。”金耀基评论说:“事实上,在中西方的价值观念里,有一些已经变成‘世界价值’了。罗马俱乐部讲得很清楚,除非人类能够包容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性或多元性,否则全球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61)与其说是建立一种“包容多种文化的价值观”这样一个难以完成的使命,不如说是建设一种优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惟其如此,方能形成文化凝聚力与吸引力。而在这方面,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入江昭提出的“全球一体化”应该是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和努力争取的。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入江昭先生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未来世界大势。他说:“我想人们就是这么看待历史的。18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都有了巨大发展,西方的崛起意味着欧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其他地区对这种影响的回应。我认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种看法是没有问题的……到1990年代左右,我的想法变了。现在我觉得,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彼此相连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崛起,也是共同崛起,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有着持续的、反复的交流。我现在的世界观是,人与文化都在持续的接触与交流中,因此不应再以东西方,或者中国与西方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世界,而应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这是我过去二十年一直强调的一件事。”(62)如果说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取径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和“大同思想”或可成为当代中国推动“全球共同体”的文化基础,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开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践又为这个国家探索进步、理性的现代化道路积累了经验。在全人类都面临着气候、环境、资源等共同问题的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能够在引领世界先进文化、推动全球一体化发展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总之,东西方的划分只是由于某些时期出现的特定历史现象造成的思维定势,既与长时段的文明发展规律相悖,也不足以用来观察和定位当今世界。中外学术研究的诸多发现已经证明,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其承载了“地理大发现”后井喷式的文明交流成果;而美国在19世纪后期的崛起更多依赖于内战前后大批移民带来的文化融合。这让英美在人类共同参与的现代化进程中先后处于领导地位,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归功于它们,或者所谓西方。换言之,现代文明是“地理大发现”之后首先出现于西欧和北欧进而扩大到全世界的一种文明形式,它不仅区分于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和亚洲文明,同样也区分于传统的欧洲文明。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是历史上“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不仅缺乏可靠的历史根据,也在现实生活中造成思维上的混乱和误导。 注释: ①何兆武先生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学’本身无所谓中和西。几何学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它在埃及出现,在希腊形成体系,就是欧几里得几何,我们学的就是欧氏几何,但我们不能说几何学就是希腊学。”何先生还举出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请金岳霖为其《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金岳霖却对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国哲学”感到没有把握。何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学’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是没有中西之分。”参见何兆武:《中西文化与全球化》,《现代大学周刊》2014年7月23日。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4页。 ④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17~18. ⑤[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5~6页。 ⑥Gerard Delanty,Inventing Europe:Idea,Identity,Reality(London:Macmillan Press,1995),26. ⑦[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 ⑧吴梦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⑨该书先是于1894年3月到1895年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单行本,据称对清末启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王晓静:《试析〈泰西新史揽要〉的内容及影响》,百度文库。 ⑩萧邦齐谈及中国人和欧洲人最初的彼此印象时,曾奇怪中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还将英国大使称作夷酋,却没有将在东海岸出现的英国人称为“东夷”。见R.Keith Schuppa,East Asia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1700 Present(New Jersey,Upper Saddle River:Pearson Education Inc.,2008),37. (11)Karl 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York:Vintage Books,1982),1. (12)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13)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6页。 (14)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7页。 (15)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8页。 (16)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8~9页。 (17)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 (18)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12页。 (19)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5页。 (20)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89页。 (21)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22)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第121页。 (2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21页。 (24)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第159页。 (25)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3页。 (26)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第126页。 (27)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第126页。 (28)Peter Zarrow,"Introduction:New Discourses and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China," in Zarrow,ed.,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1900~1940(New York:Peter Lang,2006),21. (29)Peter Zarrow,"Introduction,"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18. (30)Peter Zarrow,"Introduction,"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19. (31)Peter Zarrow,"Introduction,"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19. (32)Ilya V.Gaiduk,The Great Confrontation:Europe and Islam Through the Centuries (Chicago:Ivan R.Dee,2003),158~159. (33)格莱汉认为:“如果基督教君主们继续他们对希腊、罗马学问的支持,情况也许会不同。但是,一百年间发生的两件相关的事情决定了欧洲五百年的医学空白。第一件是489年拜占庭皇帝关闭了埃德萨的希波克拉底医学院(Edessa’s School of Hippocratic Medicine),然后就轮到柏拉图亲自建立的雅典学院(Academy of Athens),因为其教师中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所从事的神秘的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探索,威胁到了东正教的权威。查士丁尼皇帝在529年将该学院关闭。”Mark Graham,How Islam Created The Modern World(Maryland:Amana Publications,2006),51~52. (34)John E.Wills,Jr.ed.China and Maritime Europe,1500~1800:Trade,Settlement,Diplomacy,and Miss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9. (35)Zarrow提到的研究包括:Immanuel Waller 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New York:Verso,1994); Andre Gunder Fru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见Peter Zarrow,"Introduction,"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20n. (36)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9),19. (37)Peter Zarrow,"Introduction,"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18. (38)John Merson,The Great Genius That Was China:East and Wes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New York:The Overlook Press,1990),56. (39)[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40)转引自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41)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第229~230页。 (42)Helen G.Matthew,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3),13. (43)[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2页。 (44)Ina Baghdiantz McCabe,Orientalism in Early Modern France:Eurasian Trade,Exoticism,and the Ancien Rgime(New York:Berg,2008),113. (45)Ina Baghdiantz McCabe,Orientalism in Early Modern France,58. (46)Ina Baghdiantz McCabe,Orientalism in Early Modern France,275~276. (47)Ina Baghdiantz McCabe,Orientalism in Early Modern France,279. (48)Ina Baghdiantz McCabe,Orientalism in Early Modern France,102. (49)张、吴的研究更为系统和全面,案例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阿尔让、伏尔泰等以中国的宗教宽容批评法国人的宗教排斥,以及伏尔泰对孔子道德观促成的社会和谐的推崇等等。详见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第216-254页。 (50)吴梦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51)吴梦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第12~13页。 (52)吴梦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第32页。 (53)R.Keith Schuppa,East Asia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1700-Present,38. (54)按照福山的解释,第三波民主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达到高潮,进入21世纪后开始退潮。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3~7页。 (55)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47页。 (56)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47页。 (57)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48页。 (58)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53页。 (59)Eric Hobsbawm,"Introduction:Inventing Traditions,"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2. (60)[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61)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第166页。 (62)陈越:《入江昭:昨日和今日的世界》,《东方历史评论》日本专刊,2014年9月18日。标签:现代性论文; 西方文明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