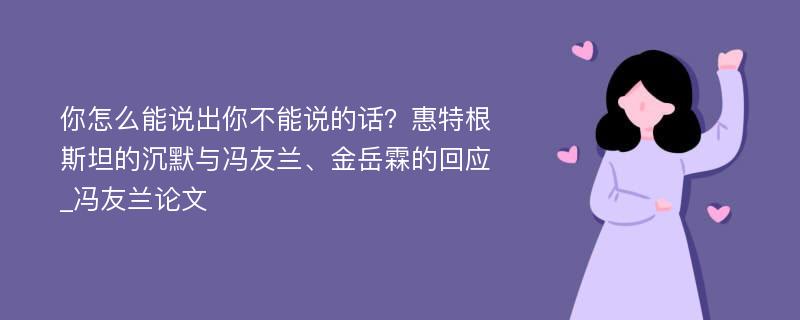
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和冯友兰、金岳霖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沉默论文,东西论文,金岳霖论文,冯友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逻辑哲学论》传入中国以来,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绍述研究不可谓少,但真正能立足民族的哲学传统和自己的哲学立场作出创造性回应的却属凤毛麟角,冯友兰、金岳霖紧扣《逻辑哲学论》一书的主旨,对“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为这种创造性回应的典范。
§1 维特根斯坦:可说的和不可说的
在《逻辑哲学论》的自序中,维特根斯坦开宗明义地说:“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因此,本书的目的是为思想划定界限,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限:因为要能为思想划定界限,我们就要能想到界限的两边。(这样,我们就要想那不能想的东西)因此,这种界限只能在语言中划分,而在界限那一边,就纯属无意义之列。”(《逻辑哲学论》,英译本,伦敦1961年版,第3 页)一句话,划清“可说的”和“不可说的”、“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之间的界限,是该书的主旨。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说”和“意义”等概念都有特定的含义,研究者必须严格遵循其特定的用字法,才不致于因望文生义而产生思想的混乱。他所谓“说”、“言说”、“语言”就是指命题,“命题的总和即是语言”。(《逻辑哲学论》,4.001,以下引该书正文只注序号)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象,语言和世界之间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具有结构上的同一性,所以命题能够描述事实。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值条件,“为了能说‘P’为真(或假),我必须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我说‘P’为真,这就是说我必须确定这命题的意义。”(4.063)按此意义规定,事实命题和逻辑命题(重言式和矛盾式)就有不同的逻辑地位。前者意义充分而后者缺乏意义,虽然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它们全无意义。(参见4.461和4.4611)总之,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说”就是用“命题”说,而“真命题之总和即是全部自然科学”,(4.11)所以, 也就是科学地说,强调了语言(实在的图象)的描述功能,与此相关,用真值条件来界定意义概念,注重的是语言的认知意义、理论意义。
按此,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事实(它的总和是世界、实在)是可说的,自然科学的领域是有意义的,那么,什么是不可说而必须对之保持沉默的呢?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讨论了不少不可说但能显示的东西。首先,是逻辑形式。“命题能表述整个实在,但它们不能表述它们为了能表述实在而必须和实在共有的东西——即逻辑形式。”(4.12)逻辑形式虽是“说”的前提,但本身不可说, 而只能在“说”中得以显示。其次,形而上学的主体,或哲学的自我。“自我乃由‘世界是我的世界’而进入哲学,哲学的自我并不是人,并不是人的身体或心理学所论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它是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部分。”(5.641)因为哲学的自我或形而上学的主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不能用命题来描述,“唯我论之所意谓是完全对的,只是它不可说,而是显示其自己。”(5.62)再次,世界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的、美学的和宗教的东西。“世界的意义必伏于世界之外。……世界里边,是没有价值的。”(6.41)由于“世界与人生是一回事”(5.621),所以,人生的意义、价值也必然落在世界之外,按此,以人的价值为核心而展开的伦理学、美学和宗教之属于不可说之列也就不难理解了,“很清楚,伦理学是不能谈论的。伦理学是超验的。(伦理学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6.421)“世界如何对于更高的东西是完全不相干的。神并不显示于世界中。”(6.432)最后,神秘的东西。“世界上的事物是如何的这一点并不神秘,神秘的是它那样存在着。”(6.44)“从永久方面看世界, 即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有限的整体来看。对世界之为一有限的整体的感觉乃是神秘的东西。”(6.45)对世界作为一有限整体那样存在的神秘感觉是不可说的,“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6.522)
至此,维特根斯坦划清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的界限,问题是,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何者是更为重要的呢?在为了出版《逻辑哲学论》而给出版商V.费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著作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恩格尔曼:《维特根斯坦书信集》,转引自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 页)没有写的东西比写在这里的东西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不可说而必须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比起可用命题说清楚的东西更重要。在1929年所作的一次关于伦理学的演讲中,维特根斯坦说:“对我来讲,事实并不重要”。他指出:“人类有一个向语言界限碰撞的倾向。……我的整个倾向以及我相信所有想写或谈及伦理或宗教的人的倾向都是在向语言的界限碰撞。这种对我们界限的碰撞是完全、绝对的无望。伦理学,因它想谈及人生的最终目的,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不能是科学。它所说的一点都不增加我们的知识。但它是人类心灵的倾向的一个档案。我个人不免深深地尊敬它而绝不敢嘲笑的。”(《伦理学讲演》,载《哲学评论》,第74期,1965年)对事实的贬抑,对人类向语言界限的冲撞的超越倾向的敬意,表明维特根斯坦在可说的东西和不可说的东西比的较中,将权重安置在后者之上。
§2 冯友兰:负的方法
要充分理解冯友兰对维特根斯坦“沉默说”的回应的价值和意义,必须了解《逻辑哲学论》研究史上的一些基本事实,这要从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说起。
对“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划界和取舍,使维特根斯坦和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显示了根本性的分歧。恩格尔曼在他所编的《维特根斯坦书信集》中附有一篇对维特根斯坦的回忆,其中精辟地指出,维特根斯坦“与实证主义者有很为重要的共同之处:他和他们一样在我们能够说的和我们必须对之沉默的东西之间划定的界限。不同之处在于实证主义者没有什么要对之沉默的东西。实证主义认为我们能说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所有要紧的东西——这一点是它的本质。而维特根斯坦则狂热地相信,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生活中所有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维特根斯坦书信集》,转引自《当代分析哲学》第214页)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可说的”是指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不可说的”则大致相当于广义的形而上学。因此,上述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之间的一致和分歧在有关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了批评,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和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参见4.003,6.53)另一方面, 如上所述,他又将“不可说”的广义形而上学领域的东西奉若神明。这里有没有矛盾?什么才是维特根斯坦关于形而上学的真正想法?我们认为,矛盾是不存在的,维特根斯坦的真正意图是要维护形而上学,他之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只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不恰当地袭取了科学的表达方式——命题,由于这一表达方式和形而上学的本性有所乖离,致使传统形而上学陷于无意义的境地。在他看来,真正的形而上学是非命题式的,沉默才是形而上学的唯一合法的存在形式。相对于可以清楚地言说的科学而言,不可说的形而上学是更为宝贵的。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有意义的命题有两类,即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而形而上学的陈述既非分析命题,亦非综合命题,所以形而上学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当然,作为保留,逻辑实证主义在否认形而上学的认知意义、理论意义的同时,还是承认了形而上学的表达人生总态度的作用,具有情感的或诱导的意义,能产生强烈的心理效应。但是在他们看来,表达人生态度的恰当形式是艺术,而不是形而上学。总之,形而上学有理论的兴趣,却不在科学领域中发挥这种爱好,想表达人生态度,又不能满足艺术的要求,“倒是混淆了这两个方面,创造出一种对知识既无贡献、对人生态度的表现又不相宜的结构”。(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见洪谦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5页)因此,抛弃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他们的心中没有一丝遗憾。
所以,虽然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都指出了形而上学没有(理论)意义,但维特根斯坦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真正的即“不可说的”形而上学,而逻辑实证主义则没有对形而上学作这样的区分,只想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将形而上学一古脑儿地加以清除。
但是在《逻辑哲学论》的研究史上,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上述分歧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抹煞了。因为在这期间,逻辑实证主义几乎垄断了对《逻辑哲学论》的解释权,他们不是忽视便是贬低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说的东西的兴趣,而将他解释成一个激烈反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者,他们重视他关于可说的东西的论述,认为他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其语言和逻辑方面的创造性思想。直到六十年代,在西方哲学界才出现了一种力图摆脱逻辑实证主义对维特根斯坦的解释的新倾向。如K.T.Fann(范光棣)在其编辑的《维特根斯坦其人及其哲学》(1967)中收集了不少维特根斯坦维护形而上学的资料,两年之后(1969年),在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中,他详细论证了维特根斯坦是个抢救形而上学的人的观点。上引恩格尔曼关于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一致和分歧的精辟论述是附在1968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书信集》一书中发表的。在这一方向的研究中,内斯的《四位当代哲学家: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萨特尔》(1965)和范波森的《维特根斯坦:他的哲学导论》(1970)也颇为引人注目。差不多与此同时,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开始了自我反省,卡尔纳普在1963年出版的思想自述中坦陈:“以前当我在小组中研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时,曾错误地以为,他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必定和我们很相近。我对维特根斯坦著作中有关神秘主义事物的论述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感情和思想与我相去甚远。”(《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 第41页)从这以后,西方哲学界开始注意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区别,开始重视维特根斯坦关于不可说的东西的思想。
西方学术界在六十年代才获得的上述结论,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一语道破。1933年,冯友兰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剑桥有过一次趣味相投的会面,当时,冯友兰就感到维特根斯坦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问题感兴趣。(参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四十年代, 在《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1943)及作为此文的扩充之一的《新知言》(1946)中,冯友兰阐明了他对《逻辑哲学论》的基本看法。虽然冯友兰直接讨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篇幅不大,却言简意赅,文约意丰。按笔者的梳理,大致有这样三层意思:
①划清了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界限。他说:“在西洋现代哲学家中,维替根斯坦虽是维也纳学派的宗师,但他与其他底维也纳学派中底人大有不同。他虽也要‘取消’形上学,但照我们的看法,他实则是以我们所谓形上学的负底方法讲形上学。”(《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如上所述, 和维也纳学派要求彻底消除形而上学不同,维特根斯坦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目的是为维护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学,用冯友兰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用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冯友兰认为:有两种讲形而上学的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是用逻辑分析法讲形而上学,负的方法是讲形而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即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表显,即是讲形上学”。(同上书,第173页)
②用禅宗哲学来阐明维特根斯坦的沉默说。冯友兰认为,负的方法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渊源流长,道家就用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佛家又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教结合,产生了禅宗,他把禅宗哲学称为静默的哲学。在《新知言》论禅宗的方法的一章中,在引述了《逻辑哲学论》的最后结论“对于人们不能说者,人必须静默”之后,冯友兰说:“照我们的看法,这种静默,是如上引慧忠国师的静默。他们都是于静默中,‘立义境’”。(同上,第263页)慧忠是禅宗大师, 曾“与紫璘供奉论议。既升座,供奉曰:‘请师立义,某甲破’。师曰:‘立义竟’。供奉曰:‘是什么义’。曰:‘果然不见,非公境界’,便下座。”(《传灯录》卷五)冯友兰认为,维特根斯坦和慧忠国师都是用静默的方法来表显(显示而非言说)第一义。
③指出《逻辑哲学论》采用了诗意的表达法。在冯友兰看起来,哲学家表达思想既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方式,也可用名言隽语的方式,他称前者为散文的方式,称后者为诗的方式。散文的方式言穷意尽,诗的方式言有尽而意无穷,富于暗示性,读者可得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冯友兰说:“维替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是用名言隽语的方式写出来底。它是用诗底方式表达意思,……他所说底是富于暗示底。”(同上书,第269页)冯友兰认为,维特根斯坦用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这一点,就是《逻辑哲学论》所暗示的。
冯友兰之所以能较早地指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区别和他的哲学先见有关,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无疑是最重要的哲学门类,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只适用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与真正的形而上学是无干的。立足于这样的哲学观,他就不难看清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浓厚兴趣,而不会人云亦云地将维特根斯坦实证主义化。而冯友兰对维特根斯坦的“沉默”有同情,则除了哲学观的因素外,还和他置身其间的哲学传统有关,在他那里,传统道家和佛家的智慧与维特根斯坦的“沉默”相互交通,达到了新的视界融合——负的方法。
§3 金岳霖:本然陈述
金岳霖在讨论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时,虽然没有点维特根斯坦的名,但是他对问题的提法却与维特根斯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作为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本然陈述的理论,更是明确针对维特根斯坦的沉默说而发的。
《逻辑哲学论》说:“为了解逻辑所需的‘经验’并不是某物如何如何,乃是某物存在。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经验。逻辑是先于一切经验的——即先于某物之为如何的。逻辑是先于‘如何’的而不是先于‘是何’的。”(5.552)“世界上的事物是如何的这一点并不神秘,神秘的是它那样存在。”(6.44)在这两段话里, 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关于世界的三个重要方面:1、“如何”(How),2、“是何”(What),3、“那样”(That)。经验(常识和科学)解决的是“如何”(How)的问题,拥有经验也就意味着拥有关于世界的逻辑图象。逻辑要解决的是“是何”(What)的问题,这里,“是何”(What)意味着逻辑空间结构可能性的总和。对于世界“那样”(That)存在的神秘感觉是属于广义形而上学的领域,它不是逻辑而先于逻辑,它不是经验而先于经验。
在《势至原则》中,金岳霖认为,“现在这世界”有“这样”和“这个”的区别。“这样”强调的是现在这世界的抽象的方面,“这个”强调的是现在这世界的具体的方面,也可以说,前者侧重的是现在这世界的本质,后者侧重的是现在这世界的存在。显然,金岳霖的“这样的世界”相当于维特根斯坦的世界的“如何”(Hwo),他的“这个世界”相当于维特根斯坦的世界“那样”(That)存在。
《势至原则》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何以有现在这个世界”?用英文讲就是Why is such actualization? 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问题呢?金岳霖说:“这问题就小的范围着想,就是问我何以坐在这间房子里,这张纸何以摆在这桌子上,桌子何以有这颜色,洋火何以歪歪地摆在这一包烟上,……详细地说,虽几千万言不为功,但是简单地说问题仍是何以有这个世界。”(《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不难看出,在此, 疑问由世界的独一无二的存在特性而起,金岳霖把它表述为对“这个”(This)的惊异,维特根斯坦则称之为对“那样”(That)的神秘感觉。
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世界那样存在的神秘感觉非命题——无论是意义充足的事实命题,还是意义缺乏的逻辑命题——所能把握。金岳霖也认为,对于“何以有现在这个世界”这个问题,命题不能为答案的工具。“何以有这个世界的问题也就是此势何以至的问题”。(同上书,第336页)因为势何以至问的不是必然的理, 所以逻辑命题不能为此问题的答案。“此势之所以至不决于已往的势,所以特殊命题(无论数目若何的多)不能为此问题的答案。此势之所以至也不决于固然的理,所以普遍的命题也不能为此问题的答案。”(同上书,第339页)总之, 决定“这个世界”的“这”(This)的因素不是命题所能表示的。
至此,维特根斯坦和金岳霖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对待不可说的东西的问题上,两者显示了原则性的分歧。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的那样存在不是命题所能把握的,因此关于它所说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它是神秘的东西,是不可言说而只能显示的,所以应当保持沉默。金岳霖则认为,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即所谓名言所不能达的阶段,但“治哲学者的要求就是因为感觉这些名言所不能达的东西,而要说些命题所不能表示的思想”。(同上书,第340 页)“虽在一方面我们认为这类话为无意义,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有意义,则在一方面说不得的话在另一方面仍然要说。”(同上书,第341 页)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①显然,金岳霖不同意维特根斯坦的沉默说,而要说些命题所不能达的思想。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②金岳霖试图突破维特根斯坦狭隘的意义观。如上所述,维特根斯坦用真值条件来界定命题的意义,事实上只注重了语言的认知意义、理论意义,按此,只有命题才有意义。金岳霖则认为,非命题的言说虽无命题式的认知意义、理论意义,因此,对于命题而言,说不得,但可有其他种类的意义,所以,仍然可说。虽然金岳霖没有在此基础上构造一种新的意义理论,但是他的上述想法却有助于人们从维特根斯坦的狭隘的意义观中解放出来,事实上,金岳霖没有做的工作由维特根斯坦自己完成了,后期维特根斯坦扬弃了早期的意义观,认为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语言有不同的意义,提出了更具开放性的意义即用法的新的意义理论。
但是,在积极的意义上,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这一问题中的两个“说”字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用命题说”,后者指“非命题或超命题地说”。金岳霖认为,对于何以有现在这个世界或势何以至这个问题,“命题既不能为答案的工具,我们只能用别的工具。而别的工具之中有本然陈述。”(同上书,第350 页)拈出本然陈述来对非命题所能达的东西加以言说,这就是金岳霖对维特根斯坦沉默说的回应。
那么,什么是本然陈述,金岳霖从三方面刻划了它和命题的区别。首先,从来源说,本然陈述是积极地总经验之成的话。命题“是分开来说的思想,它总有取舍,有取舍,才能积极。可是有取舍,就不能总经验之大成。本然陈述则不然,它积极而又总经验之大成。它无所取,亦无所舍”。(同上书,第345页)其次,从对象说, 本然陈述表示元理。金岳霖认为,有不同种类的理。逻辑命题表示必然的理,普遍命题表示固然的理,先验命题表示本然的非元理,本然陈述表示本然的元理。最后,从结构上说,本然陈述无逻辑上的主宾词而只有文法上的主宾词。任何陈述都有文法上的主宾词,因此,从文法上说,没有可说不可说的问题发生,只有从逻辑上去追究,才有可说不可说的问题。命题之为命题关键在于其逻辑上的主宾结构,“命题的逻辑主词总是表示个体,其逻辑宾词总表示共相或可能。命题之所表示总在名言范围之内。”(同上书,第341页)本然陈述表示超名言之域的东西, 因此无命题式的逻辑上的主宾词结构。
以上的讨论难免抽象,试举例说明之。金岳霖认为,以“能”为文法主词的陈述就是本然陈述。如若引用共相方面的无量的抽象法和殊相方面的无量的变更法于任一个体,便得一非共非殊的底子,即能。它不是知识的对象,对它也不能构成命题,但可以有本然陈述,如“能是潜能(Potentiality)”,“能是实质(Substantiality)”,“能是活动(Activity)”,等等。有了这样的本然陈述,我们就可以对“何以有这个世界或势何以至”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势何以至就是‘能’何以即出即入。我们的答案是‘能’的即出即入,是‘能’的纯活动。……我现在坐在这房子里,这样的坐法,……连同许许多多的这这那那的形形色色,我可以用一言以蔽之:‘这都是能的纯活动’。言简而意无穷。它实在是超名理之所不能尽而总其大成。 ”(同上书, 第350页)
如何理解金岳霖“本然陈述”的理论意义?
如上所述,维特根斯坦的“沉默”立基于其狭隘的意义观(即以真值条件为本质规定,只承认言说的理论意义)。逻辑实证论发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提出意义证实说,在此基础上力图彻底清除形而上学,但作为让步还是承认了形而上学的情感意义。虽然这一承认在逻辑实证主义都那里没有太多的积极成份(形而上学不是表达人生态度的合宜形式),但它毕竟透露了这样的消息:在理论意义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意义,在科学地说即用命题说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言说。如果我们不再执守维特根斯坦式的狭隘的意义观,那么,在本文讨论问题的范围内,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三种言说方式:描述(description)、表达(expression)、规定(prescription)。描述地说即命题,以实在世界的事实和条理为对象,属科学领域,具理论意义。表达地说以主体情志为对象,属文学艺术的领域,具情感意义。规定地说属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领域,一方面,它力求达到对宇宙大全的真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它又饱含着对人性自由的热忱。金岳霖的本然陈述就是“规定地说”的一种形式。哲学不是科学,“能是活动”这样的本然陈述当然没有命题式的理论意义,但作为积极地总经验之大成而得的话,它还是显示了哲学的理论思维的特征。哲学不是艺术,但“能是活动”作为所有个体变动的总宗旨,以“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的理想境界为归趋,其中蕴藏有丰富的哲意的情感。一句话,对于科学时代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因拘执狭隘的意义观而缄默不语,而可以开放的意义观的指引下,像金岳霖那样积极地进行规定地言说。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和“不可说的东西如何能说”的问题相应的是言意之辩,即言、意能否把握道的问题,所以,冯、金在这方面的探讨可视为传统言意之辩的延续,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由于《逻辑哲学论》的刺激,传统的言意之辩在冯、金那里已经获得了现代的形式和内容。从形式上说,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他们的“可说”、“不可说”的概念都建立在现代形式逻辑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从内容上说,言意之辩不再停留在一般意义的言象意道的关系问题上,而是具体落实为在科学昌明的现时代,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问题的这种提法昭示了清晰的时代内涵。
冯、金对维特根斯坦“沉默”的回应不仅赋予了中国传统的言意之辩以崭新的时代意蕴,而且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无论是在《逻辑哲学论》的研究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冯友兰对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差异的敏锐揭示,还是具有普遍理论价值的金岳霖对本然陈述的深刻探讨,都是中国哲学家对世界哲学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哲学宝库中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总之,作为创造性回应的典范,冯、金的探讨,为我们如何富有成效地开展中西哲学的交流指示了方向。
标签:冯友兰论文; 金岳霖论文; 逻辑哲学论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逻辑实证主义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