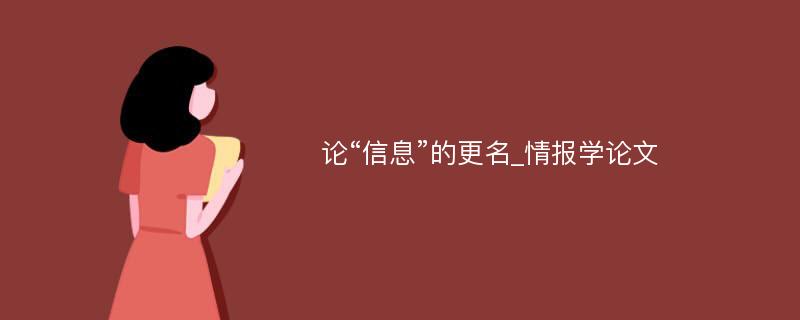
“情报”改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关于“情报”是否改名以及改什么名,议论纷纷。笔者认为,这一“情报”改名问题,值得重视。因为一个名词术语,如果作为一门学科一个关键性的概念,绝不是随便确定的,而是科学研究的结晶。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实体的真理就是概念。”孔子论政说“必也正名乎。”正名,就是重视概念的作用,他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认为:“名虽虚乎,却有实用而著实效,治国化俗,资以为利。”搞学问,搞科研,对名词术语,也应作如是观。试想,“情报”之名若废,“情报学”将焉存?所以关于“情报”改名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学情报学“命运”的大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讨论,还应深入进行,但不宜拖得太久,建议在一、两年内,由比较权威的机关主持召开有各界代表参加的讨论会,对此作出决断,以便人们统一使用规范术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交流。
1 “情报”改名观点简介
笔者对近年来,有关“情报”改名的观点疏理一下,大致有如下六种观点:
(1)主张把“情报”改为“信息”。1992年9月召开的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作出正式决定,将“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其主要理由是:①避免人们把“科技信息”和“科技情报”误解为两个不同的事业而搞重复建设,浪费人力、物力、财务;②“情报”概念的外延比“信息”小,会束缚科技信息事业的发展;③沿用“情报”概念,易与“谍报”混同,造成误解,尤其是在外事活动中产生诸多不便。
(2)主张将“情报”与“信息”合称“情报信息”。 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主办的《科技情报工作》1993年起改名为《科技情报信息》,是一典型例子。其主要理由是:①本着“大情报观”,既利于拓展原科技“情报”概念的内涵,又不致于延伸到“信息”概念的漫无边际,它着眼于“情报性的信息”的“有限目标”;②“情报”不改不行,但改为“信息”又不妥,所以,他们认为将“情报”改为“情报信息”,这在感情上也易于被科技情报界接受。
(3)主张将“情报”改为“信息管理”。如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等许多院校,都将“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信息管理”学系。其主要理由是:信息是普遍存在的,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如科技信息、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军事信息、文献信息等等,但各类信息管理过程,如生产、搜集、加工、存贮、检索、流通、消费等,在本质上却是共同的。而图书情报工作的本质,就是对信息的管理或属于信息管理范畴(当然,还有社会教育上的理由,如改名可以吸引考生报考等)。
(4)主张将“情报”改为“信息咨询”。其理由是, 改为“信息”内涵太宽,科技“情报”工作的社会功能在于辅助决策,提供给有关领导和研究人员参考咨询。所以改为“信息咨询”较为适当。
(5)主张将“情报”改为“资讯”。 其理由是港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华人地区已经流行此术语,可以借用,以便交流。
(6)认为不必把“情报”改为“信息”, 或认为不改也“无所谓”,可以沿用“情报”这个术语。其主要理由是:①科技“情报”或图书文献“情报”这个行业客观存在,与本义面向通讯行业的“信息”、“信息工程”有不同的内涵;②实践上,我国高校里所设的图书情报学系(专业)、科技系统所设的科技情报部门已颇具规模,“既成事实”,何必改换招牌、惹来许多麻烦?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以及不少刊物,如《图书情报知识》、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会刊《情报资料工作》、北京市科技情报所、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系等主办的《情报理论与实践》等至今仍沿用原名。
在以上各种观点之中,尽管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和矛盾,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对“情报”涵义的重视。情报改名与否,以及改什么名,其关键就在于对“情报”涵义作怎样的理解。
2 “情报”的涵义
本章开头就指出过,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很值得作科学研究的。80年代前后,对“情报”这一概念的讨论,就曾经是中国图书情报界的“热点”之一。
1991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周文骏教授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辞典》对“情报”的解释,可以说是中国图书情报界对“情报”涵义经过长期讨论所取得的比较一致的理解:
情报(information),习惯上指“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 由此发展为“推动用户当前事业的信息选择、传递,”即将情报看作一种活动,有一定的对象要求,需要一定的手段和过程,涉及多因素,如信息、传递、选择等。
在周先生主编的词典里,我们可以饶有趣味地看到对同一英文单词information但中文作为“信息”一词涵义的解释:
信息(information)从科学的观点看, 信息是物质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关系属性,是物质存在方式及其运动规律、特点的外在表现;从通讯的角度考虑,可认为是生物体或具有一定功能的机器通过感觉器官或相应的设备同外界交换内容的总称。信息的含义,是信息科学、情报学等学科中广泛讨论的问题。一般认为,信息是客观世界内同物质、能源并列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
比较一下这两个词条,尽管在英文里是同一单词,但在中文里,“情报”显然并不等同于“信息”。其主要表现在:(1 )作为图书情报界的“情报”,是信息,但只是信息的一部分,是“用户当前事业的信息”;(2)它不只是信息,还包括“信息的选择和传递”, 即“情报”应看作是一种“有一定对象要求、需要一定的手段和过程、涉及信息、选择、传递等因素的活动”。
从逻辑角度讲,中文把英文中的Information 作“情报”与“信息”这样的区分,在“情报学”意义上的解释,是把“情报”看作是“信息”的下位类概念。我认为是更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客观实在”,是力图“名副其实”的表现,“情报学”确实有不同于“信息论”或“信息工程”的内容,而是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一个成果。这样的区分,是不盲目“拿来”而是力求消化外来科学文化知识的洋为中用”可贵表现。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图书情报界又要将“情报”改名呢?
3 “情报”为什么要改名?
其关键原因,是由于选择“情报”这个名词来表达上述涵义时,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是中文词汇本身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所形成的两部著名词典《辞源》与《辞海》对“情报”本义的权威性解释,在中国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中,早已形成了“思维定势”。1915年初版的《辞源》和1939年初版的《辞海》对“情报”的解释基本相同。《辞源》的解释:——“军事集种种报告,并预先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辞海》的解释是:——“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它们都是从“军事”、“战时”以及占“敌方”有关来解释“情报”的。
“情报”之所以运用于中国图书情报界,首先是从科技界开始的。那时是50年代初,共和国建设初期,据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副秘书长、国防科技情报学会秘书长霍忠文先生介绍,当时我国科技方面的领导出身于战争年代,对战争中情报的重要性深有体会,所以对科技方面要求做好“情报”工作。后来,就把英文Information of science译名定为“科技情报”而沿用开来。这在《辞海》1965年修订版“情报”条得到反映:它在重申“情报”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后,加上了:“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导,如:科学技术情报。”(但不知何故,《辞源》1980年修订版却将原来初版有的“情报”条目删去了,待考。)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情报”一词又从我国科技情报界广泛应用到图书馆学界,并形成为图书馆学主要概念之一。图书情报界对这个名词用了十年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和交流,人们发现,它尽管通用于我国大陆图书情报界,但非图书情报界人士以及广大民众,特别是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却很难接受“情报”这一概念,已形成了思维定势:人们习惯的“情报”这一名词,它必定与“军事”、“战时”、“敌对状况”以及“秘密”等涵义相关。且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家喻户晓的概念经常见于报刊、电视、广播,人们一提“情报”,便自然联想起“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敌特”、“机密”之类的意思。所以,“科技情报界”和“图书情报界”讨论得很热的“情报”概念,并没有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名词术语,其涵义也常常造成误解,以为“情报工作人员”是在从事什么“秘密工作。”这确实影响了科技界、图书馆学界的正常交流和给外事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十多年使用“情报”的实践表明,这一“名”与其涵义之“实”是不相符合的。便有了要求科技情报界、图书情报界将“情报”改名的强烈呼声。
1992年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将“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开始,可以说,“情报”的改名是大势所趋。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使用的“情报”之名本来就源于科技界,而现在科技界都改名了,这就根本上动摇了使用“情报”的基础。
那么,“情报”改为什么名称适当呢?
4 “情报”改为什么名称好?
让我们先来简要分析一下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几种方案:
(1)“情报”改名“信息”——中文的“情报”与“信息”, 它们在逻辑上是上下位类的关系,上位类“外延大而内涵小”,信息在外延上包括“情报”,所以,把“情报””改称“信息”,在不少场合是可以兼容的,这也是“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中似乎没有带来什么不便的原因。但是试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改称“图书馆学信息学”,这就失去了上述“情报”所包括的“选择、传递”等活动过程的涵义了。如果说图书情报界所谓“情报”即是信息,那么也主要是指图书文献方面的信息,而“情报”改为“信息”,原来的“情报学”却不能顺理成章地改为“信息学”,因为,已有的“信息论”或“信息科学”,并不是原来“情报学”所能涵盖的。这将造成极大的矛盾。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情报”改为“信息”,信息是不能完全取代“情报”的。
(2 )“情报”改称“情报信息”——这不但是一个概念表达繁复的问题,而且也仍然存在“情报”这一名词所容易误解的弊端。
(3)“情报”改为“信息管理”——从高校招生角度看, 这样改是有相当效果的,但从图书馆学专业角度看,这将整个改变了图书馆学的原本独立的学科地位及其教学内容。也许,这是图书馆学的“命该如此”。信息科学的发展确实导致了科学体系上的“重新分类”。把图书情报学院(系)改为信息管理学系是否合理,本文对此暂且不论。然而从概念本身来说,“信息管理”是一个有偏正关系的复合概念,是“信息”的“管理,其概念的重心是在“管理”。尽管信息管理可以解释成具有“选择”、“传递”的情报涵义,但“情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传递”的信息或“选择”的信息,其概念重心是在信息之上。所以“信息管理”同样不能作为“情报”的替用词。
(4 )“情报”改为“信息咨询”——这反映了“情报”一定的活动内容,但仍然有含意过宽之嫌,因为“信息”的外延比“情报”宽。
(5 )“情报”改为“资讯”——“资讯”是港台地区使用的术语。此术语来历及涵义,据顾敏先生《现代图书馆学探讨》一书介绍如下:
70年代,(台湾)当时的资料处理界、数学界、电脑界、图书馆界以及各方面学术界人士纷纷提出各种看法,要创造一个新词汇能够完全代表英文中Information这个单词的全部含义的中文名词, 又能将分散于“资料”、信息”、“情报”等各名词的含义聚合起来,以建立一个完整的概念。1978年7月28日至29 日在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台湾大学联合召开的研讨会上,终于产生了“资讯”这个中文新名词。就这个名词的字面而言,资讯是由“资料”和“讯息”所组成的。但进一步推演起来,“资”取自于“资料”和“资源”的“资”字,“讯”取自于“讯息”和“电讯”的“讯”字。令“资”、“讯”二字所组成的这个词汇,代表一个统合性的概念。……基本上,资讯的定义和界论是由“资料”、“资源”、“讯息”和“电讯”这四块基石所砌成的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应当说,就“情报”与资讯”这两个中文字面所反映的涵义看,“资讯”比“情报”更为丰富,且不易误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把“情报”改称“资讯”呢?如果没有更恰当的名词,那当然无妨。就象对英文Computer,大陆译“电子计算机”,港台译为“电脑”,现在大陆也同样通用“电脑”。我们不必有门户之见,只要译得传神,谁翻译的都无妨。
问题就在于“资讯”对于我们在上面曾经表述过的图书情报界的“情报”的涵义,就字面上说,还反映得不够传神。“资讯”定名于1978年,那时“信息”还没有普遍使用,而80年代,则成了“信息时代”,它与大陆现今极其广泛使用的“信息”就挂不上钩,多少欠缺了信息的内涵,引不起对“信息”的丰富联想。因此,在大陆即使非图书馆界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也都宁愿用“信息”而不大愿使用“资讯”,没有如用“电脑”代替“电子计算机”那样自然的感觉。
6.至于图书情报界沿用“情报”,认为不必改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肯定过去十多年来“情报学”研究的成果,确实不能轻易放弃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还没有能够替代“情报”的恰当术语使然。但是,改名毕竟是大势所趋,这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使它改得好一些。
5 建议“情报”改名“资信”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图书情报界使用的“情报”术语应该改名,但迄今改名的各种方案尚不理想。
在这里,笔者不揣浅陋,提一个建议,是否可以把“情报”改为“资信”?
就字面讲,它可以表示为“资料信息”、“资源信息”或“信息资源”的压缩形式,这正是图书情报界“情报”的最本质的涵义。它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经过“选择”、整理,有序的、可供“传递”的“资料信息”,用户所需的“资源信息”或“信息资源”。
“资信”也可与“信息资询”相通,“信息资询”也是“资信工作”题中应有之义。
“资信”也包含了“资讯”所表达的内容。在现代,“通讯”与“通信”、“电讯”与“电信”已没有多大区别,而用“信”代“讯”,不仅可直接与“信息”挂钩,而且还可以有资料的“信用”、“可靠性”方面的联想。因此,“资信”有其广泛应用的社会远景,也可能成为海峡两岸通用的术语。
另外,就图书馆学界而言,把“情报”改名为“资信”,同时把“情报学”改为“资信学”也比较顺理成章。至于把“情报研究”、“情报中心”、“情报工作”等,改名为“资信研究”、“资信中心”、“资信工作”,则比较恰如其份,也比较自然。
“情报”改名,虽然只涉及使用中文的地方,但对中国图书情报界、科技情报界影响很大。它不仅直接涉及到所有有关院校机构的刊物更名,也涉及有关教科书的重写。不仅如此,它对今后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图书馆抛开了“情报”这个多少令人敬畏的面具,是否可以用“资信”或更恰当的“正名”开发自己巨大的潜能和广大的市场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而且,我认为,现代图书馆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资信图书馆学”。
(收稿日期:1995-0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