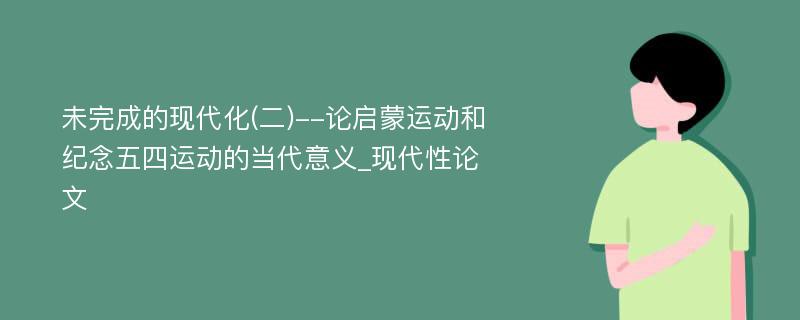
未完成的现代性(中)——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未完成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篇 回答对于启蒙的几种质疑
倘若不仅把启蒙视为发生于十八世纪西欧奠定现代性基础的思想运动,而且视为一种从西方向全球扩张之脱离传统进入现代的思想动力,一个不同地域文化难以避免的“西方化”过程,那么,像康德那样把启蒙解释为一个“通过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获致成熟性”⑨的普遍教育和训练计划,或者泛指把人类从迷信、恐惧中解放出来和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⑩,乃至如“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奠基者普遍具有的信念:脱离蒙昧、走向文明的中西文化融汇的脱胎换骨过程,以及树立民主、科学、法治的权威的文化革命,现在看来,仍未能曲尽其全部内容。启蒙的问题,正如福柯所言,“标示近代哲学没有能力解决但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问题在深思之中进入了思想史”(11),不论其发生于何时何地,亦不论其答案之是与否,在其所思所行中难免特征与现代性的纠葛,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对峙,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对于启蒙问题的个性解答。
在九十年代中国思想中,追问启蒙的意义可能是最严重的主题之一,国外有关思想资源如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后现代理论、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的引进被戏称为最具颠覆性的“外资”引进项目。这些多来自当代西方的思想展现了一幅迥异于“五四”思想先驱和八十年代启蒙主义思潮的现代性“末日”图景:韦伯通过揭示理性的分裂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难以通约和相互敌对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批判了现代性的根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把法西斯纳粹制度的起源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在历史领域反省哲学问题,把启蒙的辩证法呈示为一个理性、主体日渐神话化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理性变为非理性、启蒙走向蒙昧;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解构政治学用来揭示启蒙计划背后的权力关系尤为适宜,以“反现代”为宗指的“后现化”理论(如利奥塔德)则从质疑启蒙叙事入手质疑一切现代知识形式及其法则,现代性危机被明确为知识的合法性危机;而激进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更直言启蒙的文化侵略内含,启蒙计划被逻辑地理解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确认,启蒙知识分子成为其文化控制的工具和通道,重建本土文化的价值和尊严则近乎必然的选择。在这一图景中,诸如理性、主体、知识、进步等观念不再是启蒙殿堂巍然耸立的柱石,而作为现代化不良后果的原因频频受到拷问,启蒙及其问题与现代性建立以来“各种社会变化的成分、各型政治制度、各种知识形式、各种把知识与行为加以理性化的计划,以及各种技术突变”(12)的难题之间处于一种夹缠不清的状态,被撤去了界标和柱石的现代性不再是具有诱惑性的知识前景,而成为可资争论的思想遗产。中国“后现代”言论和“新国学”运动追问启蒙的意义,其知识、社会、文化依据主要即由它所提供。这种对启蒙的质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纠葛可解析为四个问题,即理性—主体神话的破灭、启蒙设计中的知识—权力关系、文化等级与进步的观念及交流沟通与文化归属之间的悖论,分别关涉启蒙的资源、方法、实践、作用等内容,有待我们围绕这四个方面就启蒙的意义作出辨析。
理性—主体神话的破灭 我们知道,在知识、道德、美学、历史、自然等领域确立人的主体性以对抗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宗教迷信。是启蒙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人的主体性又主要是指理性的主体性。理性不仅能够自立权威,确立知识、伦理、法律、科学等法则,提供人对抗上帝的资源和掌握自然的命运,而且能够掌握自身的命运,使人类历史走向一个正义、自由、平等、进步的和谐终端——“理性千年福祉王国”。尽管这一过于乐观的设计曾一路遭受质疑启蒙精神的如尼采、克尔凯郭尔、施蒂纳等鲁迅所谓“新神思宗”和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两面夹攻,战争、灾害、暴政等天灾人祸也为启蒙以来的历史作了相反的注释,但它“作为一种将真理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拉上直接关系的事业”(13),其内含的创造激情、人道魅力和知识远景仍能加固对自己的信仰,尤其当它从一件欧洲社会事件演变为一个“将整个人类都卷入”的复杂历史过程时,情况更是这样:在“五四”版和八十年代版的中国现代性拷贝中,理性及基于理性的主体,无疑居于价值的中心,一切现代知识形式及其法则都被奉为思想和学术圭臬,复杂的文化和社会转型问题在“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整体论逻辑中被组织成为一项严密的合理化工程。
把对启蒙的批判置换为对理性—主体的质疑、中国当代思想最早援引的是如尼采一类强调生命直觉、感性立场的非理性主义的意志主体性理论,如八十年代后期刘晓波和李泽厚的论争,就具有尼采和康德的不同思想背景,但由于指涉对象的不同,这类批判虽能深入文化的根本,直面人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内部精神生活的问题,却无法汇入其关于社会和文化合理性基础的沟通和建构实践,仅仅从身心分裂的角度质疑理性,把人的物化设定为主体的死亡,并不具有说服力。由于源各有自,其以意志主体性替代理性主体性的救赎现代文化的方案,实在是启蒙的修正和补充而非颠覆。理性—主体的观念从思想到具备真正的历史内容,当然有赖于启蒙以来各种知识、社会、文化的实践,它根植于它的程度,必将其具体存在化为一种深刻的历史诘问,而产生能够真正撼动其根基的力量。我以为,源自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传统的马克思、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等将主体社会化的思想庶几近之,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启蒙的逻辑质问启蒙,以理性的力量锤炼理性,以对主体的信仰宣判主体的消亡,使启蒙自身的问题逃无可逃,也使其对启蒙意义的追问更加显得严重。
声称“对现代性仍然深信不疑”(14)的他们是从追踪纳粹制度的精神缘起进入对启蒙的批判的,其思想和结论深刻地影响了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反省现代性的言论。把纳粹制度及各种极权形式、由科学工具化所造成的技术与社会的脱离现象、思想商品化、蒙蔽理性之光的文化工业等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病症作为启蒙的结果,以考察“这种思想的概念,以及这种思想错综交织在其中的社会的具体的历史形式、机制”(15),令人感触其内在的锋芒。它被展示为一个启蒙精神自我摧毁——理性成为神话、主体沦为个体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启蒙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一种使人类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的追求,它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理性作为“用主体的设想来解释自然界”(16)的神话的解毒剂出现;另一方面,理性又借助各种知识形式把主体的暴力施加到自然界身上,“以他们与行使权力的对象的异化,换来了自己权力的增大”(17),成为一种新式神话。科学与对象的关系、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被类同于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这样,科学和逻辑的意义都成了问题。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统治形式还随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日益渗入人类社会,理性的统一性和形式逻辑的简约在社会领域演化为极权主义的恐怖,而启蒙最工具性的形式——文化工业的出现则带来更大的问题:操纵技术的权力(一种主体性方式)日益为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让步,批量生产远离真实的伪知识、伪文化产品,对它们的不断消费导致批判能力的丧失和陷入新的愚昧,理性的普遍主体被分割为无数互不相干、无个性、物化的个体,启蒙的精神沦为欺骗群众、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个性和自由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极权形式。
启蒙最终被自身的逻辑和机制所摧毁,理性呈现为非理性,主体的统一性遭受分割和宰制,零散为碎片,“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18),这就是理性—主体神话破灭后的现实。应该说,这种基于启蒙逻辑的批判,及其注重思想与历史实践、现实状况的因果关系的考察具有一种致命的力量,但如果广义地把它也理解为启蒙思想的成果,启蒙的精神就不能说完全被自己摧毁了或必然被摧毁,其贡献和问题的尖锐性都来自将启蒙的思想与实践、崇高的动机与最恶劣的后果并置之“以果责因”的决定论方法:它把启蒙的问题揭示得深入而准确,却有赖于把其最坏的实践当成全部实践的误认。在其意识中,现代性的基础、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与法西斯主义制度的基础被完全混同了,似乎启蒙的逻辑及机制驱使自身从条条大路通向罗马——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必然性。其实,尽管纳粹制度与启蒙精神不无某种联系,可视其为启蒙实践中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形式,但毕意还存在与启蒙精神联系更紧密、更符合启蒙设计的其他政治、社会和文化形式。况且,既然启蒙是现代文明的共同基础,纳粹之为纳粹的原因就不可能在于共性,而必须到启蒙思想以外的个性文化中寻找。事实上,纳粹的意识形态与启蒙思想并不一致,倒是利用了质疑启蒙的如尼采一类的反理性的意志主体性理论及反动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等资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69年再版《启蒙辩证法》时曾含蓄地说他们当时(1940-1944年)未“非常准确地估计到向有秩序世界的过渡”,启蒙之“全面协调一致的发展过程被打断了,但并非断绝了”(19),默认其夸大了纳粹精神的普遍性。其中所谓“有秩序世界”,我理解就是接近于启蒙精神的世界。另外,纳粹制度及其他极权制度的逐渐消亡也可反证启蒙精神并未自我摧毁,而是处于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新陈代谢过程之中(20)。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真正遗产并非对于启蒙的辩证法的揭示,而在于对现代性的发达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尤其是对于工具化的理性形式——技术文明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制约机制及其束缚、分离主体的趋向的分析,以及对于启蒙实践中的知识的生产不单是理性的意识而是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发现,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后来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构成了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理论的经典问题,并引发新一轮对整个现代制度进行追问的需求,像福柯针对西方知识—思想史的批判解构理论,就充满源自它和尼采这两种不同思想路数的灵感。在福柯那里,类似霍氏和阿氏那种对于主体、本质、整体性、规律等整套理性主义传统的信仰没有了,相反却质疑构成主体的规则和条件,追寻隐伏于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主体和真理位于复杂的生产和意指关系之中,植根于笛卡尔和康德的普遍主体之理性的运作早已让位于对欲望、禁令、惩罚等不同主体形式的探讨,法兰克福式理性—主体神话的破灭主题经由阿尔都塞被倒置组织为对现代文明制度的批判:围绕所谓知识之轴、权力之轴、伦理之轴,福柯试图通过反抗使个体变为主体的权力形式——现代国家。“通过反抗这种强加于我们头上好几个世纪的个体性,来推动新的主体性形式的产生。”(21)福柯的主体—知识—权力理论无疑是把我们导入“后现代”理论视野的最佳途径,也使启蒙的问题更富于研究的意味。
启蒙设计中的知识—权力关系尽管八十年代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仿佛在追求一种西方业已实现的现代性,福柯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制度的批判与九十年代中国的追随者对于“五四”以来至八十年代建立的现代性基础的挖掘仍然非常不同,其差异极类似福柯自己与所谓“反思想家”的关系:“他们基于人类主体是由能指的任意运作而构成的空洞愿望这一非历史理论,把严肃性彻底打入冷宫并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毫不留情地进行冷嘲热讽”(22)。中国的追随者是在把九十年代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中心缺失等走向资本主义的不适与西方理性—主体神话破灭后的“合法性”危机混为一谈的基础上同福柯的思想进行汇通的。他们把当代精英文化地位的衰落、主体与历史的迷失及由此而来的“中心化”价值解体的文化情境归因于启蒙地位——据于社会和文化中心的价值、符号系统的创造者和阐释者——的失落,并把这一时刻描绘为“一个混乱如巴赫金意义上的文化狂欢节”(23):启蒙的话语,“那些教化式的呼喊有如老式唱机发出的声音”;而理想主义的姿态,也因不合时宜成为“堂·吉诃德式的狂舞”。不过,其中一些比较认真的思考,则能够套用福柯的主体—知识—权力理论,揭示启蒙设计中内含的知识—权力关系,把有关启蒙的质疑推向深入。
一般而言,启蒙的问题广义地涉及三个方面:人、知识、社会,福柯的思想虽不是专对启蒙而来,但其问题却深深植根于启蒙以来的主体性、知识、社会机构的实践之中,甚至更远(24)。对于人的问题,福柯重在考察把人变成主体的不同客观化方式,把主体性拆解为处于生产、意指和权力关系中的元素组合;对于知识的问题,福柯通过判明由知识、权力、语言三方面因素合成的“话语形成”,瓦解启蒙以来在主体观念支配下的认知传统,把真理的规范相对化、条件化;对于社会的问题,福柯特别关注合理化实践建立的机构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监狱制度及监控技术的历史考察,理清了其中知识—机构—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并把它发展为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质疑。对他而言,把个体化技术同整体化程序结合于同一政治结构中的现代国家形式,无异于对社会的全景监控,其中既充满科技进步和理性统治的内容,又意味着自由的失落和非人性的恐怖。福柯曾把启蒙理解为“就是修正意志、权威及理性运用之间的原有关系”(25),其对于整个现代文明制度的批判,也可视为对启蒙的全面质疑,一种对发达的现代性之中合理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拷问。
福柯之“知识的政体(regime dusavoir)”的概念包含着丰富的意思。对于启蒙而言,既然知识的意志就是理性的意志,那么理性的统治必然表现为合理化的进程。这一发生于人、知识和社会领域的合理化运动围绕某种主体化形式而进行:人的合理化是助人摆脱不成熟状态并“影响人性构成因素的变迁”(26);知识的合理化是使之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社会的合理化则必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一种福柯高度警戒的权力形式。为了理顺这一进程中意志、权威、理性运用之间的原有关系,康德在《答何谓启蒙》中的经典答疑可谓旨在确立启蒙内部之主体化机制的审慎而艰苦的努力。对于康德来说,人成为主体已囊括了关涉启蒙的大部分问题:在应该运用理性的领域和时刻敢于运用理性去求知;经由理性的批判——界定理性运用的合法性程序——确立各种权威;能够正确区分私人的理性运用和公共的理性运用的不同,即作为社会个体和作为普遍主体的不同理性运用方式。消除了意志、权威和理性运用之间的失衡,并建立起保证其比例协调的机制,不仅意味着主体化的完成和臻于成熟之境,而且是合理化的完成和获致自由的标志。但福柯并不认为康德这一强调合理化进程和主体化进程的统一的答案构成了启蒙的充分描述,对他来说,它始终未能圆满地解决一个问题,即“理性的运用如何获致它所需要的公共形式,以及在个体尽量谨慎服从的同时,如何能在光天化日下发挥求知的勇气”(27)。福柯根本不能相信存在一个超脱于各种私人目的的、中性的、不受权力关系牵制的“批判主体”的知识源泉,不经过“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话语生产就能使理性获致其公共形式,即使在启蒙思想为客观、公正、纯粹的知识生产领域也是如此。因此,所谓“知识的政体”可视为一个有别于启蒙之理性知识论的知识政治学的分析领域,其中能够洞穿启蒙设计中的知识—权力关系之秘密的关键正在于对知识—权力关系的重新认识。
福柯认为,应该重新考察那种基于启蒙原理的知识论预设,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超越它的命令、要求和利益知识才能发展。其实知识的生产过程同其他社会过程一样充满权力的角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正好与之相反:
我们应该承认,权力产生知识(而且,权力鼓励知识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使用知识也并不只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一个与权力关系有关或无关的某个认识主体的基础上,相反的,认识主体、认识对象以及认识模态应该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含义及其历史变化所产生的许多效果。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的,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28)
对于启蒙而言,“知识的政体”中知识—权力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主体化进程和合理化进程同样是统一的,但福柯显然承担着发达现代性的后果而来,经由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启蒙的辩证”过程的演示,他已洞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性为工具理性消损殆尽,人只能沦为整个社会机器的孤立的、物化的个体零件的现象,尤其是阿尔都塞把主体揭示为一种意识形态赋予的“自我中心”的幻觉:“大写主体(Subject)的主观意识,反过来恰恰是它被意识形态主宰的现实,即小写subject,意为‘受支配或被征服者’”(29),使源远流长的“主体化”和“合理化”命题的含义发生了倒转:“主体化”不再意指不成熟的个体脱离蒙昧成为独立自主、不迷信权威、独特的主体,而获致自由的本质;“合理化”也不再被视为指涉人类幸福、进步、秩序的中性技术手段,而是共同促成一种“使个体变成主体”或“使个体屈从并处于隶属地位的权力形式”(30)。这种权力形式广涉人、知识、社会的统治,其核心在于融汇了一种源自基督教机构的权力技术——牧师权力(pastoral power)。
这种权力技术也就是启蒙的权力技术。在福柯眼中,以“拯救”为目的、乐于为群体生活和理想献身、关怀个体、包含一种良心的知识和指导它的能力的“牧师权力”是现代一系列权力形式诸如国家、家庭权力、医学权力、精神病学权力、教育权力和雇佣者权力等的原型,它虽然是一种历史现象,但伴随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发生,“这种几个世纪(一千多年来)一直同一确定的宗教机构联在一起的牧师型权力,突然散播到整个社会机体,并获得大量机构的支持”(31)。这一历史变革虽不能完全归因于启蒙,但福柯对它稍作归纳后就提到康德的《答何谓启蒙》一文显然是意味深长的。就启蒙内含的目的能力、沟通关系、权力关系即前述意志、理性运用、权威之间的关系而论,康德并不特别强调其关涉启蒙者和启蒙对象双方的权力的运作,而是基于对沟通中介——理性运用的公共形式的纯洁性的自信,侧重目的能力(摆脱不成熟)和沟通实践(理性交流和不迷信权威)的完成。但呈现为主体化和合理化进程的启蒙既无法摆脱这种权力关系,也不能任凭它对于目的能力和沟通关系的扭曲和篡改而没有自觉。福柯清楚地区分了这一进程中目的能力、沟通关系和权力关系之间的纠结。就康德及一般启蒙者所重的沟通关系而论,“沟通总是某种作用于他人的方法。而意义要素的产生和流通无论是作为目的或作为后果,总会在权力范围内有所反映,但后者不单单是前者的一个方面”(32)。他认为,我们不能混淆权力关系、沟通关系和目的的能力,虽然哈柏玛斯也曾区分支配、沟通和最终行动,但这并非意指存在三个不同领域,即“一方面是有关事物、完善的技术、运作和转化现实的领域,另一方面是有关符征、沟通、相互性和意义产生的领域,最后是有关强制手段之支配、不平等和一些人作用于另一些人的领域”(33),而是意指三种不同的关系:它们相互渗透、利用,并以此为手段达到某种目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总的均衡,而是随时随地变换或形成其合目的的相互关系模式。像启蒙及类似的教育权力,就相对注重“能力的调节、沟通的来源和权力关系构成协调一致的系统”,其能力—沟通—权力关系的设定始终可按照一定的需求而互相调节。正是在此基础上,某种称为管制或监控的纪律被历史地建构起来。
由于权力的本质并非“共识的表现”,而是管制和支配,在某种程度上,它对于启蒙——诚如利奥塔德所言,“按照理性的双方可以达成一致意见这一观念来判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陈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导致共识的规律便能够成立:这就是启蒙叙事”(34)——便天然地包含一种颠覆的力量,尤其当它把知识内含的权力也包括在内且不与其他权力进行区别时,便必然陷入控制和解放的悖论:启蒙即反启蒙,控制即解放,受监管即自由等等。我想关键仍然在于管制或监控的纪律的确立方式:是突出权力关系、沟通关系还是目的能力,是否顾及三者的均衡或协调,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知识的政体”或社会中,福柯所反抗的“主体性的屈从性”倘若意指某种权力网络的制约,或者知识的对象化,那么其对于主从关系的斗争便注定是“无政府主义的”,很难期望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由于福柯始终把自己作为在历史上受到启蒙并为启蒙所限的生命来分析,重在探讨所谓“必然事物在当代的限制”(contemporary limits of the necessary),对于启蒙以来建立的知识论传统的另一方面——同宗教权力施诸知识领域的暴政的不懈反抗则难免会遭受忽视,当今或许只有仍时受“史前权力”骚扰的第三世界能够感受启蒙的知识论原则的生命力和建设性。事实上,为福柯所揭发的启蒙的知识论基础同样充满对权力的对抗,无论强调理性运用的公共形式之纯洁,还是真理意志的中正光大,还是什么客观、独立、中立的种种说法,都是一种为抵御权力关系的扭曲以维护其话语意志的努力。我们知道,存在各种各样的知识:真理、假说、信仰、故事……现代科学和哲学曾确立过形形色色的验收标准,亦有人以科学和意识形态、事实与价值、真理与形而上学、真伪命题区分等范畴分析这一知识学的混沌和矛盾,康德关于科学、艺术、道德(宗教)的三分法是现代知识的经典分类;其不同类属内含的权力关系绝对是不同的,像福柯那样把科学、伪科学、前科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统统视为相同的话语群,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其对知识—权力的诘问已把问题逼到了绝境,因为任何知识都要与对象发生一种关系,即通过对象化的方式达到对于对象的控制,但它正确与否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权力效果”,只有正确的知识才会产生正当而持久的权力。当然福柯并不期待一个不存在权力关系的领域或社会,对他而言,揭示人、知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支配关系或权力结构,展现并激发自由意志不屈不挠的反抗,或许真是天赋于斯人的“内在于所有社会存在的永恒的政治任务”。
(待续)
注释:
⑨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引文参酌其他译本,文字略有不同。
⑩参见M·霍克海默、T·阿多诺合著《启蒙辩证法》中译本序,重
庆出版社1990年版,该译本常有误译,并非佳本。
(11)(12)(13)(25)(26)(27)M·福柯《论何谓启蒙》,中译文见台北《思想》(联经思想集刊①),“福柯”台湾惯译为“傅柯”,今从大陆通例改之,后面不再一一注明。
(14)(15)(18)(19)《启蒙辩证法》导言,第1、3、1页。
(16)(17)《启蒙的概念》,《启蒙辩证法》第4、7页。
(20)国内外学界常有人把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出现纳粹制度和斯大林极权模式视为现代性的失败,如瑞士汉斯·昆《神学:走向“后现代”之路》(《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64页,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现代的大厦至少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已从根基上摧毁”,这种看法混淆了思想的必然性和历史的“结局”,简单地把历史的直接等同于逻辑的,值得注意。
(21)福柯《主体与权力》,见《傅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阐释学》跋,H.L.德雷福斯与P.拉比诺著,钱俊译,台湾佳冠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277页。
(22)德福雷斯、拉比诺《何谓成熟?论哈伯玛斯和傅柯答“何谓启蒙?”之争》,同上第359页。
(23)陈晓明《“精英”与“大众”殊途同归的当代潮流》,《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
(24)在《主体与权力》中,福柯曾写道:“即使启蒙运动在我们的历史和政治技术的发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仍觉得如果想要弄清为什么我们会掉入我们自己的历史的陷阱,我们还应考虑更遥远的历程”。
(28)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26页,刘北成、杨远婴译。
(29)赵一凡《福柯的话语理论》,《读书》1994年第5期。
(30)见《主体与权力》,《傅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阐释学》第272页。福柯曾这样解释“主体”一词的意思:“通过控制和依赖主从于(subject to )别人,和通过良知和自我认识束缚于自己的个性。两种含义都意指一种使个体屈从并处于隶属地位的权力形式。”这显然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
(31)见《主体与权力》,《傅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阐释学》第276页。福柯曾这样解释“主体”一词的意思:“通过控制和依赖主从于(subject to )别人,和通过良知和自我认识束缚于自己的个性。两种含义都意指一种使个体屈从并处于隶属地位的权力形式。”这显然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
(32) 见《主体与权力》,《傅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阐释学》第278页。福柯曾这样解释“主体”一词的意思:“通过控制和依赖主从于(subject to )别人,和通过良知和自我认识束缚于自己的个性。两种含义都意指一种使个体屈从并处于隶属地位的权力形式。”这显然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
(33) 见《主体与权力》,《傅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阐释学》第278页。福柯曾这样解释“主体”一词的意思:“通过控制和依赖主从于(subject to )别人,和通过良知和自我认识束缚于自己的个性。两种含义都意指一种使个体屈从并处于隶属地位的权力形式。”这显然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
(34)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25页。
标签:现代性论文; 康德论文; 福柯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主体性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