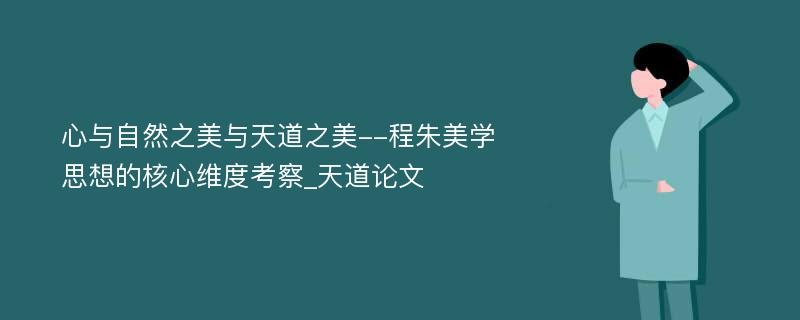
心性和谐之美与天道和谐之美——考察程朱学派美学思想的核心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美论文,和谐论文,维度论文,心性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宋是我国文化思想的繁盛期,其间以对后世影响深巨的理学为最盛。前理学时候,宋儒倡言“道统”,但还是执着于现实层面的,即以孔孟的仁义道德来教化社会。至学际天人、学至圣人的理学人物,则发展到超现实层面,即以伦理道德抽象而成的“天理”、圣道来统摄一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道学(理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程朱学派(二程、朱熹、邵雍、真德秀、魏了翁等),其用力所在,不再满足于将仁义道德仅仅视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是与无限的自然律动相融合,使之成为宇宙人心的根本,从而“明吾心之全体大用”,达到与天、理、圣等一的高明纯净的乌托邦境界。其心性和谐、天道和谐的美学思想体现的正是对这种超验境界的体悟。
一、心性和谐之美
程朱的心性和谐之美,侧重不在个体与社会大群的关系,而是“向内转”。“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应“唯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同上卷十)。朱熹也认为:“只理会自家身己是本,其他都是间物事”(《朱子语类》卷一三0),“大抵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 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答项平文》)所以,程朱一派的心性和谐是人内心之和谐,“学以至圣人”就是改造“人心”而至圣人境的和谐。程颢《定性书》云: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程氏文集》卷二)人心达到“定”,就可以内外两忘、澄然无事。这正是程朱心性和谐之美的旨归。人心要达此境,就得革尽人欲。“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一三),“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才是“至善”(见《大学》“在止于至善”朱子注)。人心至如此,也就“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而无咎也”(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三)。
程朱理学人物涵养性情、心性和谐的至善至乐境界,是与持敬主静相连的。被理学人物视为开山祖的周敦颐认为,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通书》第二十章)。其《太极图说》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障)立人极焉。”此说为程朱等所发挥,尽管他们为了防止弟子后学因“静”而入释氏之说,“不用静字,只用敬字”(《二程遗书》卷十八),但敬、静实属大同小异,无本质之别。朱熹《答张敬夫书》云:“敬字功夫,通贯动静,而以静为本”。(《朱子语类》卷十二)又云:“程先生说敬字,只是谓我有一个明底物事在这里,把个‘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字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同上)后来的真德秀解释二程“主一谓静”时说:“静时能静,则无思虑纷纭之患,动时能静,则无举措烦挠之患,如此则本心常存而不失。”(《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程朱学派持敬主静,强调“主一无适”,由不敢轻为、不敢妄为而至无欲无为、顺乎自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二程遗书》卷十八),甚至“只有所向便是欲”,“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理”。(《朱元学案·伊川学案上》)大公而无情,持敬而无欲,无所为而然,唯务性情所求的心性和谐就在其中。
可以看出,程朱一辈之心性和谐,不象传统儒家那样在“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在“人心与物”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合的“理(自然)与欲(有所向,有所为)”的关系。传统儒家的“诚”“敬”“仁”都被改造为其所用。程颢《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二程遗书》卷二上)又云:“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宋元学案》卷十三)心性和谐之美,实是人心与天地万物归一的太虚大乐,其关键是无欲无为,虚静自然。这从对天道和谐之美的论述中更可见出。
二、天道和谐之美
天道和谐之美是心性和谐之美的归结。程朱人物讲“至圣之学”,可分为互渗互补的两途:涵养性情和格物致知。涵养性情从人的心性出发,格物致知是“即物而穷其理”,以至“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涵养性情是为了物我两忘的无欲之境,格物致知是克尽人欲、明天下万物事理而顺之,与之无二。可见两途莫不是汇合在“心归于物”、“人走向天”的澄然无我之至乐的。朱熹谈天命与人的关系说:“命,谓天之付与,所谓天令之谓命也。有以气言者,厚薄清浊之禀不同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性……二者皆天所付与,故皆曰命”。(《朱子语类》卷六十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向天的依附,以天令为是。真德秀也说:“盈乎天地之间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则具此理,是所谓则也。……则者,准则之谓,一定而不可易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则者,天实为之,人但循其则尔。”(《大学衍义》卷五)人作为“物”归于天道,心性和谐之美与天道和谐之美的融合统一,魏了翁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夫人生于两间,而与天地同体,出乎百世之下,而与圣贤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说反而求之,寡欲以养其心,养心以极于无欲,则是心之运,明通公薄,岂有一毫之私间之哉!”(《魏鹤山集》卷四十四《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
程朱天道和谐之美是人顺乎自然天则,与天地同体无二。这种境界的获得,要做到“以物观物”。“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邵雍《观物外篇》)程颐也说:“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二程遗书》卷十五)以物观物就是要做到圣人那样,“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程颐《定性书》)性公而明和持敬主静一样,并不是叫人心如槁枯之木,而是与物理天道同体又同用。程颐《易传·易序》云:“散之在物,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太极,无极也(道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学际天人求天道和谐,就是要顺乎阴阳变化的太极又合乎无极之“一”,也就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顺应自然宇宙的律动运转,无适而无不适。这也就是说“心当如明鉴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鉴明水止,其体虽静,而可以鉴物,是静中涵动,体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真西山集》卷十八《讲筵卷子》)联系程颐的“至仁”境界,“无将迎无内外”、动静皆“定”的“圣人之常”,联系朱熹氏天人统一的理之极至——“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的“太极”(《太极图说解》),天道和谐之美的究竟也就更加明了。其至美之和谐,是以天为本。顺乎阴阳,自然而然,顺物无情,无为而无不为。
可见,程朱学派讲尊天、顺天,“听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顺时而动,不敢用其私心”(《答或人》,《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讲无欲、穷理,并不是对生命的否定,而是追求澄明自如、万物与我为一的天道之乐,体味永恒的造化之妙。
三、形上之美
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可看出程朱学派的美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形上之美。正如梁启超所言:“考其(理学)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1 〕传统儒家关乎世间人情的“仁”“礼”“诚”“理”等社会伦理范畴被改造成一种宇宙永恒法则。伦理规范被抽象成超验的实体化的“天理”“天道”“学圣”成了一种宇宙无限情怀的获取与体认,人具有了与“天”一样包涵遍覆的自然本性,不再累于情、滞于物,不再有物我内外之别。〔2 〕“夫天大无外,造化发育,皆在其间,自无内外之别。人有是形,而为形所梏,故有内外生焉。内外一生,则物自物,己自己,与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则安有物、我之异,内、外之别哉?”(《程氏经说》卷八《中庸解》)天人本无二,只有超越人之“形”,不为形所梏,超越感性的人的存在,才能达到人的本性之德,也即“天”之性。朱熹也直接述说了这种对尘世的超越情怀,“看得道理熟后,只除了这道理是真实法外,见世间万物颠倒迷妄,耽嗜恋着,无一不是戏剧,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书云: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耳”。(《朱子语类》卷八)既然世间万物为不堪入眼的“戏剧”,那么“真实”的只有超世间、超时空而无古今的“天理”“道”了。只有“理”(天道)才是个“洁净空阔底世界”。(《朱子语类》卷一)
心性和谐,是内在超越,以实体化的“理”来约制、压抑甚或取消人的世间情欲。持敬主静,由“定”而“仁”,至喜怒不系乎心的圣人境,就是把人心加以“提纯”,达到无情无欲,从而物我不分,内外无别。这种内省和谐是心的物化。天道和谐,是外向投归。学际天人,是顺应超验的天理、天则,以求和天同体同用,超越人“形”和人“情”的桎梏,在无极而太极的宇宙律动中,投归无臭无声的“理”世界。这种和谐也是人向外在客体的投归。所以,不论是心性和谐还是天道和谐,其实则一,都是主体的客体化;不管是道德内化、向内求“善”,还是格物致和、向外求“真”,都是以扼制人的感性活力为手段,最终使人成为“自在”的人。程朱学派无我而大我的自由和谐只能是一种非主体性的和谐。超感的“理”是人主观意念的投影,心性和谐与天道和谐、唯心与向天化合为生命还原的投归意识,主体也就消解在物理、天则中了。应该承认,程朱等人对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具有着强烈的体认,这种焦灼体认转化为对有限性、时间性的否定和超越。但其超越却走向了人的反面,剥离、否定人的主体性,其心性和谐、天道和谐的自由体验注定只能是一种异化的体验:人的世界被封闭自足的自在世界代替;人的主体性自由在对实体理性、宇宙法则的冥会中,在空间吸纳时间的永恒宁静中,冷却凝固了。
所以,程朱以形上为真为美的美学思想,体现出的不再是对人的世间存在的关切,而是消解主体、无我而大我的至真自然之乐,是对永恒、绝对、无限的形上乌托邦的体认。恰如邵雍诗中所吟,“虽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间”。(《安兮吟》)而在传统儒家,“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其所求是世间人伦的和谐之美。程朱则把这种偏重功能论的思想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3〕,专注于超验的性理之学、太极之道, 贬抑事功和诗文,而追求淡然无极的形上和谐之美。其“圣人”与老庄的“真人”、其“理”世界与释老的虚极自然境界,有着抹不开的亲和力。无怪乎清人颜元认为,“静,敬二字,正假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工夫”(《朱子语类评》),“宋儒,谓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存学编》卷一,《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今人周予同也说:“吾人如谓无佛学即无宋学者,决非虚诞之论。宋学之所号召者曰儒学,而其所以号召者实为佛学;要言之,宋学者,儒表佛里之学而已”,“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这与“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的传统儒学是大不相同的。〔4 〕如果说传统儒家的美学思想是以行(实)为先,游于艺而成于乐,旨在文质彬彬的人世间(其最玄亦不过“吾与点也”),那么,程朱诸氏则是以知为先,无欲存理,归于自然而然、澄然无情、形上之真的无限宇宙情怀。这种自然之旨与周孔名教之义是迥异的。
四、诗文精神与和平气象
对程朱学派的美学思想,有的人拘囿于程朱等的片言只语,以偏概全,只看到程朱们手中的“旧瓶”而未尝其瓶内的“新酒”,以致难明其美学思想的核旨,只有明晓了程朱学派和谐之美的核心维度,我们才能认清其诗论、文论的真面貌,以及其静观山水、品味花草所得的“和平气象”。
程朱一派的诗文精神,要之为二:不以诗文为先、不以诗文为能;为诗为文要自然而然,不可强为。他们主张学要“使人求于内”,而“以文为主”就是“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程颐《定性书》)。在他们心目中,文章之学、训诂之学都是离真失正,而“欲趋道,舍儒之学不可”(《二程遗书》卷十八),“不求诸内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伊川文集》卷四《颜子所好何学论》)。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认为“不求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得第二义了”(《清邃阁论诗》),所以,不能以文为先。“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是倒学了”。(《二程遗书》卷十八)同时,更不可以文为能、以文为美。他们认为,“今之学者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使心不宁静”(朱熹《答朱泽之》),心不静则溺于情而害于道、害于心性和谐、天道和谐了。词章利禄是与程朱们“洁净”的理世界不相容的。魏了翁同样反对以文为是、为美,“言根于有德而辞所以立诚,后之人稍涉文艺则沾沾自喜,玩心于华藻,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是,而本之则无,终于小技而已矣”(《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程朱等论诗论文其要在自然而然为诗为文。也就是邵康节所说“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答傅饮之》),亦是朱熹所吟“余事不妨闲戏弄,尧夫非是爱吟诗”(《首尾吟》)。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一是学至“高明纯一之地”,于诗固不学而能之(朱熹《答杨时卿》)。故“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观物”的诗也就不会溺于情、累于物我之两别了(邵雍《伊川击壤集序》)。另一方面,“文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朱子语类》卷八)。这“腔子”实为“理”、天道的化身。要合“腔”,须“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朱熹《答巩仲至书》)。这就是要求人“平淡自摄”,为诗文、为文方能真味发溢。程朱传人王柏道出了他们为诗、为人的标则,“朱文公独爱韦苏州诗,以其无声色臭味为近道”,“自《三百篇》以来,独平淡闲雅者为难得,夫平淡闲雅者岂学之所能至哉!惟无欲者能之,非无欲之诗难得也,正以无欲之人难得耳”。(《鲁斋集》卷九)不以文为先为能,就是要专内专一,不溺于情、累于物,讲持敬主静以达无欲的功夫;自然为诗文、不强为诗文,就是要“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无为而无不为,自然而然。程朱学派的诗文精神,不正是其心性和谐之美、天道和谐之美的流溢么?
从根本上说,天道和谐之美是超越感性形式、感性现象的。因为“理义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二程粹言》卷一,洁净空阔、澄然归一的“理”世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凡看文字,非只是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二程遗书》卷二十二)。所谓“圣贤气象”,也即圣人境界,是个体的人与天地同游、投归无限宇宙的大化体验,是“理”和天道和谐在人和万物中透出的意味。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云:“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吕祖谦云:“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宋元学案》卷十四)。这是从得道者的言行德貌和鸣道之文中观气象。而“气象”不仅在人、文中可观(圣贤气象),更在对皆存“理”的山水草木的静态品味中(和平气象)。这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的记载便可看出:
“……明道(程颢)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乙编卷三)
“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望花随柳之乐。学道而至于乐方是真有所得。大概于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丙编卷二)正如邵雍所言:“物物皆有至理。吾侪观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见《易学辨惑》)对这般境界,真德秀“养心”之境可作阐释:“方其外物不接,内欲弗萌,灵襟湛然,奚虑奚营?当是时也,气象何如哉?温然而仁,天地之春;肃然而义,天地之秋;收敛而凝,与元气俱贞;洋奂而休,与和气同游。则诗与文有不足言者矣。”(《跋豫章黄量诗卷》)超然闲适,虚淡清静,无喜无忧,与天地为一,与和气同游,其和谐之至美真是无可复加了。程朱一派沉浸其中的大而化一的形上之美中,是没有多少现世人间色彩的。至于它和陆、王美学思想,尤其是和老庄、禅宗的美学思想的相通甚或相同之处,相信读者能从拙文论述中看出一、二,此不再费言。〔5〕
程朱学派形上的本体论色彩的美学思想,假定了自然客观物的优先权,用先验论的方法对人加以自然化、物化的处理。贯穿其中的主线是“心”(人)向物化的客体理性(天理及其现实载体“圣人”)的投归,其至美之境就是心与客体理性的接触与契合。而这种客体理性也即天理,是“善”的先验化和自然化的产物。“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朱熹《四书集注》)美善混同、以善代美,是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心性和谐与天道和谐,体现的正是超越个体有限性的永恒的善——天理。这不仅与他们为儒门争一统的弘道精神相背,且是超社会人性、世间人生的。它是作为有限个体的人对梏己之“形”的超越,是无我而归真,向无限的宇宙自然的澄怀。然而,主体消解并向客体流失却是程朱一派获得其至美的代价。这是悖论还是必然?或许,朱熹晚年(62岁时)的自述是再恰当不过的注脚了:
“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有什么物事。某思量得几乎成病,到如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是的,那壁后究竟是何物?
注释:
〔1〕《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93页。
〔2〕此处可借用马克思论黑格尔的一段话做参照。 “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见《马恩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3〕重世务、 切实用的清儒视“本体”二字亦为程朱的禅旨体现,如陈确所言,“‘本体’二字,不见经传,此宋儒从佛氏脱胎来者”。见《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6页。)
〔4〕《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14页。
〔5〕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 ”(《鲒埼亭文集外编》)宋儒与释老的因缘关系, 自宋至今学界多有论述,可参阅今人姜广辉著《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