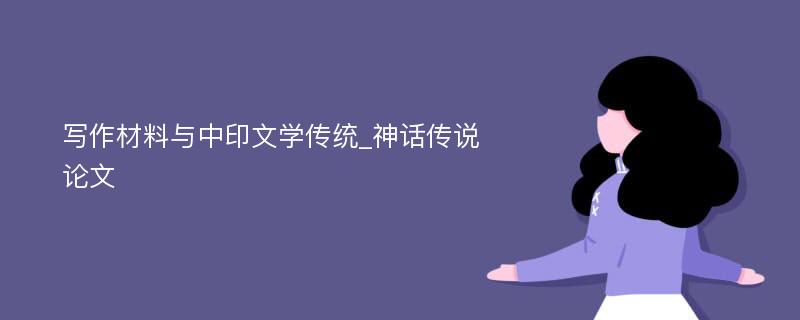
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印论文,传统论文,材料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都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两国古代文学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文学形态的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在形成这种差异的诸多因素中,书写材料的不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印度古代通行的书写材料是桦树皮(bhūrja)和贝叶(pattra 或patra,音译贝多罗)。贝叶是多罗树(tāla,即棕榈树)的树叶。这种树叶既阔又长,质地厚实,印度古人将它们裁成统一的长条形,用竹签或铁笔在上面刻写,然后在字迹上涂上颜料。贝叶上打有洞眼,可以用绳串连。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提及多罗树,称“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889页。)但是, 桦树皮和贝叶这两种书写材料都不宜长期保存,因此,印度古代始终保持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方式,书写一般用作记诵的辅助手段。
印度现存最古老的四部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就是通过严格的吟诵方式传承的。唐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就明确提到印度婆罗门“所尊典诰,有四薜陁书(即四吠陀书)”,“咸悉口相传颂,而不书之于纸叶”。(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205页。 )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的文献除了这四部吠陀外,还有各种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而在整个吠陀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文字书写的知识。因此,印度古代文字起源不明。印度现存最早的书写文字见于阿育王(公元前三世纪)石刻铭文,主要使用婆罗谜(Brāhmī)和佉卢(Kharosttthī)两种字体。婆罗谜字体自左至右书写,一般认为属于印度本土字体;佉卢字体自右至左书写,源于西亚的阿拉米字体。后来的印度本土文字绝大多数使用婆罗谜字体及其变种。
四部吠陀是为了适应祭祀需要而汇编成集的,主要是颂神诗、祈祷诗和咒语诗。它们是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的圣典。在人类上古时代,宗教和神话在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正常情况。
在吠陀时代末期,出现与婆罗门教相抗衡的沙门思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佛教也采用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这从现存佛经中的常用语“如是我闻”(evam mayā srutam)便可见出。 东晋法显在《佛国记》中记载道:“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而中天竺“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
印度吠陀时代是部落社会。吠陀时代末期,约公元前六世纪初,印度的部落大部分过渡到国家。此后,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为列国纷争和帝国统一的时代。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产生于这一时期。在印度古代,《摩诃婆罗多》被称作“历史”(itihāsa),《罗摩衍那》被称作“最初的诗”(ādikāvya)。我们现在按照世界通行的术语,称它们为史诗(epic)。史诗是以诗(韵文)的形式和诗(神话)的思维记叙民族的历史。希腊两大史诗是如此,印度两大史诗也是如此。
在印度两大史诗的形成过程中,宫廷歌手苏多(sūta )起了重要作用。适应列国争霸的社会需要,宫廷歌手不断编制英雄颂歌,在宫廷中和节日集会上吟唱,或者陪随帝王出征,在征战间隙吟唱。这些英雄颂歌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传播,经过历代宫廷歌手加工扩充,最终形成史诗。其内容或者围绕一个英雄人物,如《罗摩衍那》(即《罗摩传》);或者围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摩诃婆罗多》(即《婆罗多族大战记》)。而以英雄传说为核心,又汇入各种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在《摩诃婆罗多》中,还汇入各种政治、伦理、律法和哲学等内容,而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罗摩衍那》的最后定型约在公元二世纪,现存抄本约有两万四千颂;《摩诃婆罗多》约在公元四世纪定型,现存抄本约有十万颂。也就是说,印度两大史诗的篇幅总量相当于希腊两大史诗的十倍。
在印度古代,与两大史诗同时产生和发展的另一类作品是往世书(Purāna,或译古事记),主要记叙创世神话以及天神、 仙人和帝王的谱系。往世书也是韵文体,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传播,定型时间晚于两大史诗。现存大小往世书各十八部。仅十八部大往世书的篇幅总量就达四十万颂。史诗和往世书,加上吠陀颂诗、梵书和森林书,还有佛教文献和耆那教文献,印度古代文献中的神话传说资料之浩瀚,令人叹为观止。
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文字产生较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方式,也产生了丰富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史诗。近二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飞猛进,最引人注目的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发掘和整理。《格萨尔》和蒙族的《江格尔》以及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的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估计诗行可达百万行”。(注:王沂暖《关于藏族〈格萨尔王传〉的部数和行数》,载《格萨尔学集成》第2册,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285页。)也就是说,这部史诗的篇幅相当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五倍之多,堪称世界史诗宝库中一大奇观。当然,《格萨尔》直至近代和现代还处在创造性的发展中,是一部“活史诗”,与严格意义上的古代史诗是有所区别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对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史诗的深入研究,必将大大丰富世界史诗理论。
印度两大史诗和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都是口耳相传的创作和传播方式结出的硕果。那么,中国汉族为什么没有产生这样的史诗呢?我们也可以从汉文化的传播媒介和方式这个角度切入,加以探讨。
中国的夏商周时代类似印度的吠陀时代,而春秋战国时代类似印度的列国纷争和帝国统一时代。中国现存的最早文字是殷墟甲骨文,年代早至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但甲骨文肯定还不是中国的最早文字,因为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汉代学者总结的汉字构造原则“六书”(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和假借)均已具备。这说明汉字起源的时间还要大大提前,有待考古发掘证实。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钟鼎文)之后的汉字字体由秦汉的小篆和隶书,发展成汉魏以后的楷书。
中国在西汉发明造纸术。在纸张用作书写材料之前,汉字的书写材料是龟甲(主要是腹甲壳)、兽骨(主要是牛胛骨)、青铜器、竹、木和帛等。其中用于抄写书籍的材料主要是竹、木和帛。这些书写材料都宜于长期保存。直至本世纪70年代,我国还从汉墓中发掘出用竹简和缣帛书写的大量文献。而在印度,上古乃至中古时代的桦树皮和贝叶抄本已荡然无存。例如《摩诃婆罗多》,现存最古的抄本也属于16世纪。
纸张发明于西汉,而普遍用作书写材料始于魏晋。西晋傅咸曾作《纸赋》曰:“既作契以代结绳兮,又造纸以当策。”荀勖在《穆天子传叙》中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而东晋桓玄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据考古发现,现存最早的纸写本有西晋的佛经残卷和《三国志》残卷。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这样,除了抄写之外,书籍又可以以印刷的方式传播。而雕版作为印刷工具,纸张作为印刷材料,也有利于文献的保存。佛经梵语原典在印度本土基本失传,而在中国保存了卷帙浩繁的汉译佛典,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中国的纸张至迟在七世纪末已经传入印度,但造纸术的传入还要晚一些,纸写的抄本出现在11世纪以后。(注:参阅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尽管出现了纸写的抄本,更为流行的还是贝叶抄本和桦树皮抄本。至于印刷术传入印度,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了。
印度古代始终缺乏既实用又宜于长期保存的书写材料,因而一直保持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承方式。这就决定了印度古代口头文学创作——神话传说、史诗和民间故事——的异常发达。而中国古代早已具备既实用又宜于长期保存的书写材料,因而一向重视以书写文字为依据的文化传承方式。从古代“仓颉造字”的神话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文字的崇拜:“仓颉制字,洩太极之秘”(《文脈》),“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绎史》),“于是而天地之蕴尽矣。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路史》)。而中国古人重视书写文字,促成中国史学起源较早。
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明商代就有记叙“殷革夏命”的历史典籍。据《礼记·玉藻》记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说明周代有专职记事和记言的史官。《尚书》还只是关于尧舜至春秋的史料汇编。孔子讲授的《春秋》和司马迁编撰的《史记》则开创了中国史书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两种体例。司马迁编史注重利用文献和实地考察。 《史记》中明确的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在此之前的周、商和夏的帝王世系有世无年。然而,《殷本纪》中的帝王世系早已为殷墟甲骨史料证实。据此,现在人们推断《夏本纪》中的帝王世系也可能是信史,因为当时司马迁编撰《夏本纪》也是有史料依据的。如果将来能由考古证实,那么中国的历史编年还能推前一千多年。
中国历代史官仿照《史记》的体例,为后人留下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浩瀚的历史文献。这与印度古人为后人留下两大史诗和大小各十八部往世书形成鲜明对照。印度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印度古代史(12世纪以前)的“主要特点是缺乏任何正规的历史纪年”。直至12世纪迦尔诃纳(Kalhana)编撰的克什米尔地方史《王河》, 才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注:马宗达(R.C.Majumdar)主编《吠陀时代》,伦敦,1952年,第47、49页。)因此,我们阅读印度古代文学史,会发现印度古代作家和作品的年代大多是推测性的,倘若能确定在哪个世纪,就算万幸,不敢奢望像中国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编年大多精确到年份。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势必抑止神话传说的发展。从中国古籍《山海经》、《楚辞》和《淮南子》等可以看出,中国上古神话原本也是绚丽多采的,各种神话母题大体具备,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零星片断地记载在各种古书中。一般认为,儒家“六经”(易、书、诗、礼、乐和春秋)是由孔子整理编定的。孔子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人物,重视文献证据:“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也是一位现实感极强的人物,“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他也不断然否定鬼神世界,而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因此,在孔子编订的“六经”中,保存的神话传说资料自然十分有限。
孔子这种重人事而轻鬼神的态度也是有所本的。《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孔子直接秉承殷周时代先人从神话向现实转化的思维精神。而史学的成熟显然对这种转化起了促进作用。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史学观念。他在《史记》中也采入一些神话传说,但坚持“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也就是依据“六经”梳理神话传说。《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中指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薦绅先生难言之。”因此,他“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大宛列传》“太史公曰”中又指出:“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也就注定史诗难以产生。与印度文化史类比,中国的周代和春秋战国是应该产生史诗的时代。但自殷周以来,有史官制度,“有册有典”,促成诗(神话思维和虚构想象)与史的分离。孟子有“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之说,这里的“诗”不能理解为《诗经》,而应理解为诗和史浑然不分的史前诗或史前史。这样,孟子此说也可以理解为神话传说的消亡和史学的兴起。
古希腊两大史诗大约成型于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史学诞生在两大史诗之后,以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为标志。这部《历史》主要记叙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注:转引自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页。)同时代稍后的修昔底德撰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史学规范更严谨,书中没有“奇闻轶事”,“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注:转引自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页。)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则在《诗学》中对诗和史的区别作了理论概括:“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注: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诗”包括史诗,但不限于史诗。
《诗经》雅诗中有不少诗篇记叙从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以及宣王征伐四夷而中兴的传说和史迹,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六月》、《采芑》、《常武》、《出车》和《江汉》等,原本是英雄史诗的绝好素材,但终究没有发展成史诗。同样,屈原的《天问》也是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的绝好素材,但在汉文化背景中,已经失去发展成史诗的机会,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标志着中国神话传说时代的结束。
神话传说同史诗的生命依靠口头创作和传诵维系。一旦受到文字记载的历史束缚,相关的神话传说和史诗也就失去发展的活力。当然,神话传说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神话传说的灭亡。一是原有的神话传说能通过文字记录保存下来,二是神话传说作为文化活动的一个支流还会顽强地生存和发展,三是神话传说作为素材和创作手法不断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运用。
文字记录与神话传说和史诗的本性相违背。印度史诗和往世书在口头创作和传诵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印度史诗和往世书都采用韵文体,也是出于方便记诵的需要。而中国古人容易依赖书面文字传承,上古时代最重要的神话传说集《山海经》采用的就是散文体。五部儒家原典除《诗经》外,《周易》、《尚书》、《仪礼》和《春秋》都是散文体。在古代印度,不仅史诗和往世书采用韵文体,许多民间故事集,甚至各类学术理论著作也采用韵文体或韵散杂糅体。而古代中国尽管也是诗歌大国,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和元曲源远流长,但宏观地看,文献总量中仍然是散文体占据绝对优势。
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史诗,从文学形式继承发展的角度看,造成中国古代缺乏长篇叙事诗。印度文学从史诗时期进入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后,出现“大诗”(mahākāvya,即叙事诗), 大多取材于史诗和往世书中的题材。印度古人把史诗《罗摩衍那》称作“最初的诗”,实际上是说明“大诗”直接导源于史诗。但“大诗”不能称作“史诗”,因为它们是诗人独立创作的诗歌艺术作品。檀丁(七世纪)在《诗镜》中对“大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了理论概括:“大诗”分成若干章,故事取材于传说或真实事件,主角是勇敢高尚的人物,诗中应该描写风景、爱情、战斗和主角的胜利,讲究修辞和韵律,等等。同时,在七世纪产生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散文体长篇叙事文学作品——檀丁的《十王子传》和波那的《迦丹波利》。这种古代长篇小说体裁的出现,在世界文学史上算是相当早的。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它们在题材上继承了民间故事文学的世俗性,在叙事方式上继承了两大史诗和民间故事集的框架式叙事结构,在语言修辞艺术上继承了“大诗”的风格。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充分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教文献具有明显的印度文学传统特色。汉译佛经《佛所行赞》(北凉昙无谶译)、《普曜经》(西晋法护译)和《方广大庄严经》(唐地婆诃罗译)这样的长篇叙事文学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许多佛经中还包含有大量用作譬喻的印度民间故事。印度佛教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宣教,因而佛经文体大多是通俗的,采用韵文体或韵散杂糅体。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有过佛经翻译文体文和质或者说文言和白话的讨论。中国古人早就明白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区别,所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或者,“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都体现这种区别。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可以说是书面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典籍都是用文言写的,文体趋向简约文雅。中国佛教高僧习惯于中国典籍的文化,经过长期的佛经翻译实践,才渐渐认识到佛经原典本身大多是用白话文体撰写的。这样,也就不必忌讳用白话文体翻译佛经。(注:参阅拙文《佛经翻译文质论》,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大量的禅宗语录也都采用白话文体。显然,汉译佛经促进了中国古代白话文(近代汉语)的发展。
同时,纸张作为书写和印刷材料得到普及,也有利于白话文献的保存和传播,为白话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追究中国上古时代汉语文体简约文雅的原因,字体书写繁难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书写材料的限制,简牍嫌重,缣帛嫌贵。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衡石量书”(《秦始皇本纪》),也就是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简牍文书。汉武帝时,东方朔“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滑稽列传》)因此,《后汉书》为蔡伦立传,指出“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宦者列传》)而佛教传入中国,恰好赶上中国纸张逐渐普及的时期。
在唐代出现的变文是一种韵散杂糅的民间说唱文学体裁,主要用于讲述佛经故事,宣传佛教教义。这种韵散杂糅的文体就是采用佛经的叙事方式。由唐代变文发展成宋元话本,由宋元话本发展成明清长篇小说。明清长篇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乃至近代章回体长篇小说中,保持着在散文叙述中夹杂一些诗词歌赋,也就是保留着唐文变文韵散杂糅的原始特征。
佛经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体形式,佛经中的印度神话观念激发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想象力,业报轮回思想也给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主题和情节烙上深深的印记。没有佛教传入中国,不可能出现像《西游记》这样的神话小说。即使是描写中国世俗生活的小说,《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是三十六员天罡星和七十二员地煞星下凡,死后回归原来的星宿;《说岳全传》中岳飞是天上大鹏金翅明王下凡托胎投生;《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仙石和仙草下凡;《金瓶梅》中西门庆死后转生为孝哥;《醒世姻缘传》中晁源转生为狄希陈,仙狐转生为薛素姐,计氏转生为童寄姐,珍哥转生为小珍珠,这些全都体现化身下凡和轮回转生的印度神话观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有心搜集,可以写成一部专门著作。但国内研究佛教和中国文学关系的学者,似乎迄今在这方面还没有下够功夫。
标签:神话传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史记论文; 汉朝论文; 中印论文; 山海经论文; 尚书论文; 格萨尔论文; 史诗论文; 佛经论文; 佛教论文; 罗摩衍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