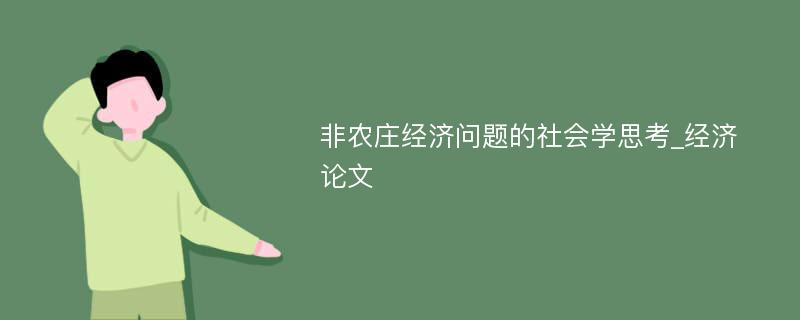
非农化村庄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村庄论文,经济问题论文,非农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农化村庄经济是我国农村城镇化过程的自然结果,这一经济的形成发展对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改变整个城乡格局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非农化村庄经济是农村改革开放成果的结晶。然而,由于非农化村庄经济是在传统农业村落的基础上急剧分化出来的,缺乏足够的规范性与整合性,因而又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其一,缺乏社会整合性是非农化村庄经济内在素质中存在的共同性问题。
非农化村庄经济是市场化取向的社会变迁条件下非农产业进村并借助村庄资源的推动与转化形成的,虽然这种经济的内容已经非乡土化了,但由于它直接根植于乡土文化背景之中,且这种背景对产生于其中的经济的塑造又是全面而深入的,致使非农化村庄经济呈现出难以摆脱的缺乏社会整合性的乡土本色。
封闭性的村庄利益共同体格局是非农化村庄经济缺乏社会整合性的根本。非农化村庄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尤其在非农化村庄经济的形成之初,土地的非农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土地非农化转化出的资金、物业或收益在村庄共同体的经济中一般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此,土地的重要性相应地会引申出土地权的重要性,而土地权的重要性又会相应地引申出分享村庄经济利益与土地权的密切相关性。事实上,非农化村庄中利益封闭格局就与拥有土地权主体的封闭性构成直接相关。在村庄里,土地权往往是由地缘、血缘、姻缘关系而天然规定与获得的,在村庄利益与资源的分配上,土地权大于其他任何身份权,如单纯的资金投入权、技术投入权等等。是否拥有土地权如同一道巨大的鸿沟把村庄中的人口一分为二,这种区别不仅反映在村庄与土地相关的收益分配上,而且还反映在村庄收益与福利的所有领域,包括村庄工程的承包权、就业优先权、子女入园入学优先权等等方面。在村域里,因土地权而派生出的各种特权甚至还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这种扩张趋势反映在村籍制度的日趋完善上。非农化村庄中存在一个普遍性的事实是,非农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村籍制度往往越完善。其实,村籍制度本质上就是村庄权益的保护性机制,通过这一机制,村庄将其资源截流在村庄里面不致外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村籍制度只不过是土地权封闭性的派生物,但它一旦形成却又成为强化村庄利益封闭性格局的催化剂,成为村域特权无限扩张的机制性保证。
村庄利益的封闭性格局以及村籍制度的强化对于村庄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会带来多方面的制约,并且这些制约还是所有村庄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根源。首先,村庄利益的封闭性格局制约了村庄内外人力资源的正常社会流动。村籍制度这道墙把村庄内外成员截然区别开使得与利益强烈相关的“一村二制”往往造成外边的进不来,里边的不愿出去的情形。非农化村庄中,一般都存在大量的外来人口,其数量往往超出本村人口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当中不乏村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优秀人才,但他们被视为村庄共同体的外人而无法纳入村制中,更没法公平地享受到村庄经济发展的利益。与此相反,对于具有村籍身份的人而言,由于利益分享的驱动而不愿意向外流动,有的甚至以放弃接受更多教育的机会为代价来达到滞留村庄的目的。可见,村庄利益封闭性是正常社会流动实现的障碍。其次,村庄利益封闭格局制约了村庄内外各种社会资源的正常流动与交换。有的学者指出,尽管非农化村庄的利益分享边界是固化与封闭的,但其经济边界则是开放的,利益边界的封闭性并不影响其经济边界的开放性。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因为几乎在所有的非农化村庄中,利益分享边界与经济格局的边界相比,前者非常清晰,而后者则相对模糊化。但如果从更深入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有内在矛盾的,其现实依据也不够充分。应该说,利益分享的封闭性必然会影响到经济格局的开放性程度,村庄单位化趋向就是经济内倾型发展的体现,这点将在后面详细论及。再则,封闭性利益格局所强化的村庄内聚力会引发类似地方保护主义性质的村庄保护主义倾向。村庄利益与资源的排他性独享在村民的心理认同上无疑会营造出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还会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附近社区时得到进一步强化。一般非农化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的确高于周边地区,现实的反差再加上现实的利益独享而派生出来的村庄保护主义情结就不难理解了。只是这种情结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发展常常是牵制性的,因为它往往成为演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最佳依据。可见,村庄利益的封闭性从根本上阻断了村庄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整体格局的良好整合,从而使村庄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之间存在一个断裂面。
作为封闭性利益分享格局的直接延伸便是村庄单位化现象,而村庄单位化倾向也是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缺乏社会整合性的重要体现。从村庄单位化的起源看,应当说,村庄单位化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因上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村庄单位化是粗放型城镇化的自然结果,是自发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因为村庄的非农化是与社会大背景中的城镇化格局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在区域中的功能是逐步建立并不断调整的,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用地结构、基础设施等等与之配套,村庄利益结构也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才会合理化。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城镇化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许多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是在缺乏长远与总体布局的前提下推进的,这种情形下的村庄构建只能是一种缺乏外部空间合理化支持的构建,因而也只能是村庄封闭取向的构建视野。即使在一些被认为“有序”的城镇化中,由于这种“有序”缺乏大格局中有序的支持,背后包含的同样是无序的因素与问题,如有的地区的城镇化是以村为单位进行规划设计的,在每个村域内建立起工业开发区、农田保护区、居民住宅区。不难设想,重复投资、产业同构、缺乏规模效益便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样的,在村社区组织构建中,结构同构、功能雷同、村办社会也成为难以避免的问题。其次,从内因上看,如前所述,村庄往往是一个资源独享的共同体,由于土地权的封闭性而派生出利益分配上的封闭性,且这种封闭性在村域内部具有向多层面扩张的趋势,这就使得非农化村庄不管产业结构如何分化、其功能如何复杂化都会朝向完善内部分配与再分配体系而努力,即村庄社会资源会通过内部的分配与再分配来转化与调节。还有,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村办社会是村庄共同体理念的一种实现,因为,非农化村庄是长期聚村而居、从事传统农业劳作的共同体延续而来,其根深蒂固的均贫富与自给自足的小而全观念会在新条件下作为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与行为取向而作用于社区构建,村办社会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观念与行为定势的影响。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村庄单位化倾向在村庄非农化初期便初显迹象,随非农化程度提高、经济实力壮大,村庄单位化趋向越明显,一些发达村庄的村办机构从生产到生活一应俱全,且还具相当的规模与水平。在此,如果把村庄当成一个整体来观察,存在于这一整体内部的分配与再分配机制使得其自身资源往往只用于其内在循环,由此而实现着村落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对于把村落纳入社会大市场、大分工的客观要求是相背离的,因为村庄的这种单位化现象实际上在生产着一种不利于实现与整体社会整合的内在结构。
无论是村庄利益封闭性格局还是村庄单位化倾向都会程度不同地从不同侧面强化村庄传统特殊主义倾向的人际关系,从而使村庄人际关系在其社会经济扩展中难以实现充分的整合。在充满乡土本色的村落社区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地缘、血缘、亲缘、拟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家庭家族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人们之间的互动交往大多是熟人之间的全面人际关系的互动,具有浓厚的情感性与个体性色彩,因而不难理解,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的思想习惯与行为模式都贯穿着因人而异的特殊主义原则精神。但随着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随着村庄产业结构的彻底转变,按理说会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社会关系的性质,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家族组织化方式,因为村庄的非农化与市场化是同时进行的,并会带来与之相应的利益性社会关系的普及,为了实现利益的扩张与追求效率,需要与之相应的是理性化的科层化组织管理方式的普及。但在非农化村庄中,传统的社会关系与组织化方式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抬头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村庄的非农化伴随着利益规模的急剧扩张,需要相应的社会关系与组织化方式去整合与联结,以便利益的分配与再实现。而在非农化村庄中,一方面是传统力量很强大,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性的力量相对弱小,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借助于传统的社会关系与组织化方式去实现利益的扩展与效率的增长便成为新条件下至少是比较理性化的选择,尤其是非农化村庄经济发展的初期。这就是为什么家庭性家族性企业公司与非农化村庄经济同时成长的主要原因。的确,在非农化村庄中,个体私营企业几乎都是家族性的,即使是集体企业与整个村社区组织的管理都带有极强的家族性色彩或称之为拟家族化倾向。其次,封闭性利益分享与单位化倾向都在实际中起到了强化特定传统人际关系的效果,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使人际互动关系更加固定化与封闭化,从而使原本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更得以在业缘、利缘关系的基础上得到维系与巩固。传统社会关系、家庭家族性、拟家族性组织化方式的凸现,对非农化村庄经济的持续发展总的来说是具有一定制约性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扩张越来越依赖于遵循一整套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包含普遍主义精神的规则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非农化村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社会关系与组织化方式的调整。
其二,非农化村庄“物化”经济存在的问题。
在非农化村庄经济面临的问题中,就这种经济的内在素质及结构而言,存在着缺乏社会整合性的特征,但就这种经济的“物化”形态而言,则隐含着诸多自然城镇化过程中的失范现象,并成为制约非农化村庄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目前的非农化村庄中,其“物化”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第一,非农化村庄缺乏整体规划中的合理化支持,因而,形成非合理化分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推动,主要是村庄在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利益差异的驱动下、以市场为导向而采取的集体性或个体性行动的过程。在其中,由于村庄的非农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的非农转化使用过程,因而土地权在非农化中至关重要。而我国土地政策中,虽然规定了土地集体所有,但只有行政村组织才具有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初审权。正是这个初审权使行政村在村庄非农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使得农村非农化往往是以行政村为单元展开,由此而使得一些发达地区形成遍地开花式的非农化村庄格局,造成一系列相关的资源浪费与破坏,如土地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第二,非农化村庄内部由于缺乏有效管理与合理规划而存在的不合理布局及相关问题。这是从非农化村庄内部的情况来看,由于行政村掌握相当的土地非农转化权,而这种权力往往与巨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稍微约束不力,再加上村庄保护主义势力的作用,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违章建筑、不规范建筑。以广州市为例,全市存在139条城中村, 每条城中村都有大量的出租屋,出租屋带来的高收益正是大量违章建筑的源头,而这种出租屋经济一旦形成市场,相关的后遗症极大。广州城中村改造难就以出租屋的改造为甚。第三,在非农化村庄中,虽然产业结构与人口就业结构已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但村庄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往往仍是沿用原来的一套,这包括较缺乏环境卫生习惯与公共道德意识等等,使得村庄中的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往往成为非农化村庄中的一大景观,当然这其中还有村庄管理不力的因素。总之,非农化村庄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经完成了向城镇的转变,但要完成本质上的城镇化尚需要一个过程,“物化”经济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印证了这一过程的漫长性。
其三,非农化村庄中的非正式经济及问题。
非农化村庄经济区别于其它经济形式的独特性之一便是这种经济往往包含更多的非主流经济成份或称之为非正式经济成份。
非农化村庄中,由于非城非乡或亦城亦乡的特征很突出,城乡要素的共聚,派生出许多消极现象与问题,非正式经济在一些非农化村庄中大量存在便与此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在城市区域内,一般都有较配套与规范的城市管理体制在监控着城市的社会经济运转,难以有非正式经济的良好生存空间。而非农化村庄中,非正式经济往往能够在那里找到相当适宜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为,首先,非农化村庄一般地理位置较好,交通便利,又邻近消费大市场,而非正式经济基本上都是民间自发产生的,以获取最大的市场效益为目标,正是这些便利因素为非正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其次,非农化村庄中,传统的社会关系都比较强,地缘、血缘、亲缘关系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容易形成严密的保护网,从而大大降低了利益获取的风险性,使得非正式经济本身的高利润与高风险较容易在非农化村庄中找到发展机会。第三,就整体素质而言,非农村庄居民处以较低层次,因为他们刚刚由农民转变而来,长期受旧观念与氛围的塑造,面对城乡一体化与现代文明的冲击,往往缺乏适应性而变得急功近利。第四,非农化村庄中,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应的村庄管理一般都处于受主客观制约的相当滞后状态。以广州城中村为例,许多村子已被纳入城市规划范围,且土地已被大部分征用,有的村也已由村委会转制为居委会,但在管理上却仍沿袭与城市不同的农村管理体制与运行格局。正是管理上这一致命缺陷的存在,再加上前述的三个因素,非农化村庄往往成为非正式经济生存发展的温床,诸多被城市管理所排斥的事物纷纷转移到这些村庄中寻找扩展空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非正式经济存在的巨大利益,不仅村庄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经济发展中起着保护性作用,而且一些行政组织往往还起着实际的纵容甚至是保护作用,形成强大的利益内聚共同体。
一些村庄中大量未经许可的私人出租屋、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地下工厂、无证无照经营、与黄赌毒相关的黑色市场等等。广州城中村的私人出租屋中居住着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就在从事着与非正式经济相关的职业。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村庄中非正式经济存在的严重性。实际上任何村庄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地位的提升都必须依赖于人文品味与正式经济的推动,否则这种发展只能是畸形的。
其四,非农化村庄经济中的产权后遗症问题。
产权是任何一种经济形式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影响其现存格局与未来走向的关键,而在非农化村庄经济中,其产权现状则存在不容乐观的问题。
非农化村社中,属个体或私营经济范畴的一般不存在突出产权问题,真正存在问题的是村集体经济这一领域。对外而言,村集体经济的产权也是清晰的,但对内而言,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却是模糊的,即使已经对村经济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村庄,其集体股部份从经济学意义上看,产权也被判明是不清晰的。
起初,这种模糊化产权经济的形成是建立在其产生所依赖的村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首先,村庄经济的直接背景是村庄社会生活共同体,长期的共同体生活既磨合着个人意志的从众性,又塑造着群体意志的合理性。村庄历史的积淀再加上解放后几十年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观念遗产的共同作用,村庄非农化中的集体再合作很容易成为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并非不理性的选择。其次,这种产权选择所依赖的信任结构的特定性还会带来效率的提升。非农化村庄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主要还是传统性的,即使利益关系也是在传统关系的化解中得以维持与巩固的,而建立在传统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信任结构在村域共同体内可以实现彼此的理解与信赖,因而,人们可以接受与采取产权内部模糊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并达到促进村庄经济发展的目的。
然而,随着村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传统社会关系与信任结构的改变,村庄经济的产权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因为村庄的非农化标志着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转型,随之迟早会引发工具合理性社会关系的深入与普及,并会改变建立在熟人圈内人际关系约束基础上的信任结构,从而产生出以组织有效性与制度有效性约束的信任结构,相应地就需要产权构成的明晰化为前提。但目前的非农化村庄集体经济则显示出传统社会关系与信任结构变迁中产权转变的滞后性,致使在城市国企中出现过的问题又在村庄经济中重现。这些问题包括:首先是“搭便车”心理而引发的低效率。集体经济实体中产权与收益的实际“外在性”挫伤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效率的提升。其次是缺乏有效制约的信任结构而引发的村有资产流失及腐败现象。市场化导致的个人理性化行为取向的强化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集体经济很有可能成为村庄经济领导者攫取个人利益的对象,滋生出腐败现象。可见,产权问题是村庄经济进一步发展无法绕开的问题,因而产权改革是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五,非农化村庄经济滋生出的食利阶层问题。
非农化村庄经济中相当比重来自于土地非农化而直接或间接产生出的收益,或者直接表现为征地款,或者转化为出租物业,或者转化为股份分红,当中的收益往往相当可观,形成一批靠此为生而不事任何职业的食利阶层,这是非农化村庄经济中较为独特而突出的问题。食利阶层的存在带给非农化村庄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影响是多层面的。个人层面上看容易消磨人的上进心与积极进取心态,形成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的消极意识与行为倾向。社会层面上看则会给社会造成反面的示范效应,腐蚀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观,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其六,非农化村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非农化村庄经济既是在市场导向下,同时又是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受市场导向形成的个体和私营经济一般不存在管理体制中的普遍性问题,但在强大行政力量直接作用下形成的集体经济则管理体制问题突出,企业的管理者与党政领导者往往合二为一,党政企业不分家造成企业管理的种种问题。如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管理中的浓厚家长制作风,管理者素质所限造成的专业化管理水平不高,行政干预太多造成的企业自主性不足,等等,许多国企中政企不分的问题又在村庄经济中重演。
综上所述,非农化村庄经济作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独特经济现象固然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但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很突出,既有深层次上与乡土文化背景和传统社会关系相关的问题,又有与现实层面上的利益分享相关的问题,既有自然城镇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又有村庄非农化中人为构建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非农化村庄的发展都是滞后性的,都值得引起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