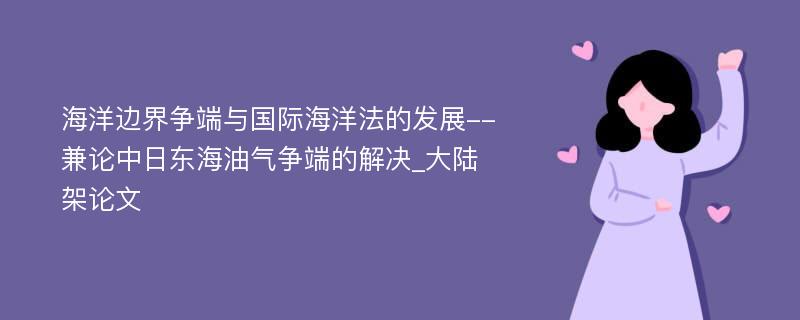
论海洋边界争端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兼谈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端论文,海洋法论文,边界论文,中日论文,海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6)06—0039—10
自2004年5月以来,日益严重的中日东海油气争端,不仅仅是简单的油气资源之争,它涉及历史、边界、政治和国际形势等诸多因素[1]。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解决也不是简单的资源争夺问题和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问题,更多的涉及海洋边界的划分和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与完善。研究国际社会关于海洋边界争端的实践,既有利于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解决,也有助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
一、海洋边界争端的国际司法实践
国际社会关于海洋法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我们重点考察和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国家海洋边界争端的司法与准司法判决,来探讨国际海洋法关于海洋边界的有关规定及其发展与完善问题。
(一)瑞典—挪威北海大陆架案
1909年瑞典与挪威之间的Grisbadarna划界案,可能是现代最先进行海洋边界争端仲裁判断的案例,而且北海大陆架也无疑是有关讨论海洋边界最重要的案例。1982年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深受此判决的影响。最后法院判决包含如下内容:
1.关于海岸线的走向。法院不止强调海岸线的一般方向,并且特别指出沿岸任何特殊或不寻常的地形,也都在大陆架划界中产生影响。法院并且说:“在海岸线凹入或凸出处……如果等距方法被运用,则海岸线愈不规则,划界地区离海岸愈遥远,最后的划界结果也就愈不合理。”
2.关于大陆架的地质状况。法院进一步检视上述的一些条件,以决定海岸线上若干地形是否应该影响大陆架的划界,毕竟大陆架是因承认实际地形上的状况而形成的概念。因此,法院说;“大陆架与沿海国相连接……是一项事实,而检视大陆架之地质结构是有裨益的……”
3.关于天然资源问题。这是国际法院在考察划界时另一项特别注重的有关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所重视的天然资源只是那些“已然被知悉”或“已可知悉”的天然资源。法院解释说,考察此“事实因素”旨在避免大陆架边界跨越某一个单独矿区时,相邻或相向国在未经司法裁判前,抢先开采或浪费开采天然资源。此衡平考察也显示出1909年瑞典与挪威之Grisbadarna案的影响力。当时常设仲裁法院一方面承认瑞典对Grisbadarna碥滩有历史性的权利,但同时也承认了一个确定的国际法原则,即对“一个已经存在并且长期存在的事物状况,应当尽可能减少改变”。
4.关于比例分配或海岸的相对长度问题。国际法院所作的此一考察,如今已成为各相邻国家在测试海洋划界结果是否“衡平”时的一项重要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坚持必须纳入考察的是,“邻接沿海国的大陆架面积与依其海岸线一般方向测量出的海岸长度之间……于一合理程度内的比例分配……”在这里必须被丈量而采用比较的是海岸的“宽度”,而非其曲折海岸线的实际“长度”。德国学者塞缪耳·普芬道夫应该是第一个主张比例分配应基于海岸线一般方向之宽度而确定的学者。他认为,一旦此点被确定,两个相邻国家才能划定一条与海岸线一般方向垂直的线,以寻求平等的海域划分。
5.关于“自然延伸”或“不侵占”问题,法院指出,自然延伸系指海岸国之“海岸前端”向海的持续延伸,这是“大陆架与海岸国家”之间的实质相连关系。法院声明,“陆地支配海洋的原则是被适用的,因此必须仔细检查那些大陆架有待决定的国家的海岸线的地理形状”。事实上“自然延伸”一词,最早被用来指示大陆架向深海延伸的最后尽头。虽然我们无法决定国际法庭是否的确将“自然延伸”当作决定大陆架划界的“决定性”因素,但无疑,“地理意义上的自然延伸”,或如1982年缅因湾案美国律师所谓的“海岸前端延伸”,已然成为大陆架划界时一项基本而重要的因素[2]。目前世界各国似乎都同意,在大陆架划界时,任何国家的自然延伸部分都不应该侵占另一国家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部分。
6.关于重叠部分的平等划分或联合开采。法院同时也指出,如果在应用于述诸划界原则时产生重叠区域时,当事国应该协议解决之,否则当事国即应“判断划分”或“联合开采”此区域内的天然资源。[3]
(二)英—法大陆架仲裁案
为了公正断案,仲裁法院依据争执双方均为大陆架公约的参加国,一开始就认定1958年大陆架公约在本案中可以被适用。法院并进一步认定,等距离原则在本案具有拘束力。但是它进一步定义公约第六条所包含的“等距离这一特殊情况规则”为:在欠缺协议时,大陆架划界必须基于公平原则。法院指出:“混合等距离这一特殊情况规则在事实上表现了一个一般规范,亦即当协议失败时,国家之间在同一大陆架上划定的界限应该基于公平原则而产生。”[4] 由于法院将“等距方法”与“特殊情况方法”视为一个划界模式中的两个平等的部分,事实上等于将“特殊情况方法”确定为1958年公约各缔约国以第三方裁判方式划定大陆架时应适用的规则,法院然后考察了本案中下列各项重要因素:
1.关于自然延伸的地质条件。仲裁法院试图进一步决定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所提出的“相关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法院显然试图降低自然延伸原则的角色。它指出,自然延伸原则不应该被忽略,但也不应被视为绝对的原则。适用此一原则时,应同时考察其他法律与衡平上的相关因素。法院特别降低了地质或地文意义上的自然延伸原则的地位。英国方面辩称,赫得深海以及赫得深海褶皱区应可构成英、法之间大陆架的一部分天然界限。但是法院发现英国曾经在它与挪威间划定大陆架界限时,同意忽略挪威海沟(Norwegian Trough)的存在。而赫得深海区与赫得深海褶皱区在和挪威海沟相比较下,实在只是很轻微的地质结构上的褶皱地带。法院坚称,赫得深海—赫得深海褶皱区若被赋予划界上的重大意义,将与近年来整个大陆架划界的国家实属趋势相违背。换言之,只有重大的结构中断才能被认定为划界中的“特殊情况”事实。[5]
2.有关岛屿的位置。法院认为英属海峡岛位于海峡中线的法国一方,使得等距方法在本案中不能适用,因为它“破坏了此二海岸线大体均等国家间的地理平衡状况”。如果海峡岛在划界中被给予“完全效力”则原本可划归法国的大陆架部分将大大地缩小。法院宣称,“这一事实本身似于……就足以构成一个会引发不公平的情形,而必须寻求其他划界方法,来设法弥补此不公平。”
3.关于岛屿的性质。英国方面提出了许多与海峡岛屿性质相关的因素,其中包括地理因素(该群岛的面积约75平方英里)、人口学因素(人口约130000)、经济、政治组织以及法律地位。法院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划界相关。同样的,当法院考虑到大西洋部分的划界裁决时,乌寻及西里岛都是“有相当面积和人口的岛屿”,因而具有划界上的重大意义。乌寻(Ushant)及西里岛都构成大西洋部分划界上不可忽视的“自然地理因素”,这使得在该区内的大陆架划界时,不得不“重视其地理因素”。[6]
4.关于比例分配问题。仲裁法院表示,比例分配原则提供了一项标准,用以决定“位于等距界限上之特殊地理或地形物所造成的合理或不合理、衡平或不衡平的效果”。比例分配所使用的客观标准是划界国家所分配到的大陆架面积与各国海岸线长度的相对关系。如果海岸线长度的比与所获大陆架面积的比不能“大体”相同,比例分配就应受到怀疑。此时,当事国间即应寻找另一条界限,以获得较佳且较合理的比例。[7]
(三)冰岛—挪威大陆架和解案
该案和解委员会由冰岛与挪威两国协议于1980年8月16日成立。1981年5月委员会提出了和解建议报告,其中包括了下列主要内容:
1.关于划界地区的地质情况。委员会就简麦因海底山脊的地质与地文构造问题咨询有关专家后发现,此海底山脊为一窄薄、狭长之陆块,地质上早先是格陵兰的一部分,而不是冰岛或挪威的一部分。专家判定简麦因实际上是所谓“微大陆”,其形成时间较挪威所属的简麦因岛与冰岛都要早得多;后二者是最近的火山活动造成的。因此简麦因山脊并不构成挪威所属筒麦因岛或冰岛的地质上的自然延伸部分。
2.关于地文因素或海底具体形貌。委员会发现简麦因海底山脊的北端部分在地文学上可视为简麦因大陆架向南延伸的一部分。委员会的结论是:冰岛不能基于自然延伸的原则,而主张超越其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外缘的简麦因部分。因此,筒麦因海底山脊的北部应归于挪威所属的简麦因岛。[8]
(四)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
本案牵涉到两个相邻的地中海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问题。法院于1982年2月24日作如下判决。
1.关于自然延伸。法院特别指明了“自然延伸”所包含的地质和地理上的意义。法院认为地质意义下的自然延伸与划界应不相关,在大陆架中必须被考察的是大陆架当前的实际情况,正如同考察当前的海岸地理形状一样,必须考察当前的海底形貌,重要的是海底地质变化的结果,而非长久以前海底变化的本身[9]。至于地文学上的考察,法院指出,此类考察在两国自然延伸部分的划分过程中有着有限度的相关性。法院进一步指出,为了影响划界,上述地文上的特质必须造成“明显的海底变化或中断,以造成两个分离的自然延伸部分的明显分隔”。法院特别强调了“地理”意义下的自然延伸原则。它重申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的结论,指出“海底之专属权利应归属于沿海国”,此外,“一个国家的海岸与海岸外水底部分的相邻接关系,是此沿海国主张法律权利的基础”。国际法院认为当前的、重大的地文条件与地理因素是本案中必须被考察的重要因素。于是,法院做出最后结论:(1)突尼斯海岸位于突、利两国陆地边界终点以西,其海岸方向有着重大的改变,此点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因为,虽然此方向改变不足以使两国的相邻接海岸成为法律上的相对海岸,但是却足以大幅修改两国邻接海岸的位置。(2)由于法院已经拒绝适用等距方法,及利比亚所提出的由陆地边界向北直接划定的界线,法院不认为在本案中“切断效果”仍然是一个划界相关因素。(3)法院也提到地文学上的“的里波里褶皱区”。此褶皱区被突尼斯解释为盖伯斯海湾海底的连续部分。法院认为由于这一褶皱区大部分位于RasT Tajoura以外,也就是划界区域以外的地方,并且它并未“造成大陆架的中断”,因此不应该被认为是两国“自然延伸部分的分界”。[10]
2.关于岛屿的位置。法院考察了几个岛屿的位置问题后认为,在杰巴岛及其周边若干小岛或低潮高地的地区有着其他的考察因素(例如:历史渔权),其效力超过了这些小岛及高地存在的效力。不过,法院认为柯根纳岛以及四周的低潮高地是重大而必须被列入划界考察的因素。3.关于比例分配。如同北海大陆架案一样,法院也考察了比例分配的原则,不过法院在本案中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1)法院不同意突尼斯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内水”与“领海”面积不应该包括在比较海岸长度与大陆架面积时的计算范围内。国际法院指出:大陆架之法律意义并不包括内水与领海下的海底部分。但是当前的问题并不是定义问题,而是为寻求衡平而适用的比例分配问题。被划归一国的地区事实上是否位于领海或内水之下,并不妨碍沿海国享受其开发利用该区域内自然资源之主权权利;该国享受这些权利,并且在实际上更在该地区享有完整的主权。(2)法院强调,应该被丈量比较的是海岸的长度,而不是两国自行划定的直线基线的长度。但是法院仍然不得不选定若干在相关海岸线上突出之点,作为丈量该国海岸长度的基础。不过一方面法院选定了这些定点,另一方面它却从来没有说明作成这些选择的基础。法院实际上应用了海岸线片断直线的方法来丈量长度,却未曾说明为何要拒绝两国自行选定之直线基线的理由。法院系依据特定的经纬度来划定沿海的直线,其依据似乎只是为了“绘图上的便利”。
(五)美国—加拿大缅因湾海洋边界案
国际法院特别法庭于1984年10月12日作出的判决是海域划界研究上极其重要的文献。此裁判是第一项由国际法院作出、以一条单独的海洋边界同时划分两国的“渔业区”(类似新海洋法公约所指之“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裁判。这也是第一个由相关当事国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26条第二款与第31条,以及法院规则第17条第二款所组成之国际法院特别法庭作出的海洋划界裁判[11]。
该裁判之所以重要,部分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公平标准”。特别法庭指出,它所谓的“公平标准”,意指“由衡平取得之标准——无论它们被称为原则或标准”。特别法庭指出“……国际法所要求的,只是在每一个案中应该努力去寻求与具体事实情况最适当的标准或不同的标准平衡”。特别法庭所提出的这份公平标准的“不完整”因素包括:(1)陆地支配海洋;(2)在没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案例中,平等地分配邻国海域或海底的重叠区;(3)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国海岸的向海延伸不应侵占另一国迫近海岸的水域;(4)相关两邻国应尽量防止切断他国海岸的向海延伸部分;(5)在若干情况下,有时候最合理的划界结果,是依据两国在划界地区的海岸线比例,不公平地划定出来的[12]。
1.岛屿或其他地理特点的有限度考察。正如特别法庭所指出,这类地理特点有时被给予完全的效力,有时被给予一半的效力,有时则全无效力。”在本案中,位于缅因湾口封口线九海里处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小岛——海豹岛(加拿大属),被给予一半的效力;此举使得修正之后,中线位置的适用比例约为1.32∶1,而非1.38∶1。
2.关于比例分配。法庭认定,美国方面的海岸线长度,由鳕鱼角“肘部”测算至伊丽莎白角,再由此延伸至美加陆地国界的末端,总长约284海里。加拿大的海岸线,由美加陆地国界终点计算至新布伦斯威克处以下的海湾岸边水宽均不足12海里——然后由此跨过海湾计算至对岸斯科希亚半岛上的相对点,再由该定点计算至布莱尔岛,然后计算至黑貂角,总长约206海里。两国海岸前端的长度比例为1.38∶1。如上段所述,此比例后来因海豹岛被计入加国海岸,改变为1.32∶1。[13]
(六)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
国际法院于1985年6月3日作出判决,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在两个海岸完全相对的国家间,为大陆架划界的司法判决(在此案之前,国际法院所作各有关大陆架划界的裁判,均系与毗连国家有关)。该案重点考虑的因素主要有:
1.自然延伸与距离。法院引述其本身于1982年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判决中的话说:“一个明显的海底突变或中断”可以构成“两个相分隔之陆架或两个相分离之自然延伸的无可争议的区分界线”。然而,法院也指出,“依据这样的法理”,将不免“忽略了一项事实,亦即只有在划界区海底距岸不足二百海里之处,上述法理才给予地形或地质因素在划界中相当的地位,因为在此地区的权利归属原本即重视过去(地形或地质条件)的影响。”在本案中,两国相对海岸的距离不足四百海里。法院表示,“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是两个“在现代法制上相连接”的法律制度,正如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表现的那样。因此,在划定大陆架界线时,所应纳入考察的因素之一就是“该国沿海在法律上可被允许延伸的专属经济区(200海里)”。总而言之,法院表示,“当大陆边(continental margin)距岸不足二百海里时,自然延伸的部分定义根本就是由海岸计算的距离,而不论其海底与底土实际上的形态、性质如何;虽然自然延伸的真正意义已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成愈来愈复杂的司法概念了。”[14] 值得强调的是,法院为适用马耳他所提出之“距离标准”,而设定了两个限制条件:第一是只在距岸二百海里以内适用,第二是此标准并不超越“自然延伸”的原则,只是构成“自然延伸”的部分定义而已。法院虽然不曾深入说明,但是它明白地指出,“自然延伸与距离观念……并非相反,而是互补的,两者都是大陆架法律概念中的重要成分。”换言之,在超越二百海里以外之处,“自然延伸”仍然是一个包含了其他地理或地文因素在内的观念。
2.岛屿的存在。对于马耳他自行划定直线基线,并将该国主岛——南方一个无人居住的费而弗拉岛纳入基线内一事,法院并未表示意见。但是,法院指出,“各国自行划定之基线并不当然与为测算大陆架而选定之海岸线定点完全一致。”法院引述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中的意见,认定费而弗拉岛只是所谓的“小岛,岩块及不重要的海岸突出地”之一而已,不应被纳入测绘“暂时中线”之计算内。此暂时中线系法院运用其他因素考察寻求最终界线的基础线。
3.比例分配与海岸线的相对长度。法院测算了马耳他相关海岸的长度(由Rasil-Wardija到Dalimara Point),并用于与利比亚的海岸线长度相比较(法院认为只有利比亚介乎RasAJdir与RasZarrug两点间之海岸与本案划界区域相关)。两者之比例为24海里∶192.1海里,亦即大约1∶8。法院因此表示,依其意见,由于两国海岸线长度差距颇大,理当调整(暂时)中线,以使利比亚享有较大的大陆架。但法院认为,此调整不应凭借任何数学意见而形成。法院认为,调整的基础应该是整个划界区的“整体地理环境”。[15]
以上分析表明有关国家海洋边界争端的司法实践确立了和平解决国际海洋边界争端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规范发展成为普遍的国际准则。
二、中日在东海的划界争端问题
中国在东海面临同韩国和日本的划界问题,中国同日本的划界既涉及大陆海岸,也涉及台湾海岸,因此在东海的划界是一个涉及三国四方的复杂问题。中韩和中日划界大致以北纬30°线为界。中韩划界在中国大陆和韩国的济洲岛等岛屿之间进行。按海岸一般方向测算,中国海岸线长约600千米,韩国为80千米,比例为1∶0.12。中日划界同样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岛屿相向海岸之间进行。日本琉球群岛共包括50多个岛屿,总面积6815平方千米,人口近200万,面向东海一侧的海岸线总长度为415千米。而中国一侧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岸线长度为748千米,中日两国在划界海域的海岸线长度之比约为1.8∶1。
日本是一个传统主张按照中间线划界的国家,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属于“中间线”集团。日本1977年5月2日公布的《关于渔业水域的临时措施法》规定:“当日本的二百海里渔区界线超过中间线时,以中间线为渔区界线。与有关国家已签订渔业协定者,以协定中规定的线为界”。1996年6月14日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如果日本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的任何部分超过了从日本基线量起的中间线,则中间线(或日本同外国议定的其他线)将代替外部界限的那一部分”。在中日东海边界问题上,日本同样主张按照中间线划界,并采用无人居住的一些列岛为基点。其在1974年1月30日同韩国签订的《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中单方面将其划定的中日假想中间线作为开发区朝向中国一侧的界限,只留给中国140~180海里宽的大陆架。对此,中国多次表示强烈抗议,认为该协议侵害了中国对东海大陆架的权利,日本的划界“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不承认日本片面划定的海上中间线,相反,日本也不接受中国的大陆架理论。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海洋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海底资源的开发,新的“蓝色圈地运动”应运而生。于是,中国对东海石油的开发,引发了日方的恐惧。中国勘测东海石油,从70年代开始。随后,在浙江以东海域的东海大陆架盆地中部发现了被命名为“西湖凹陷”的大型储油地带。自1980年在东海首次钻探龙井一号井成功以来,中国已在“西湖凹陷”钻井30口,其中20口获高产工业油气流。经过这20多年的勘探,中国目前已在“西湖凹陷”,开发出了平湖、春晓、天外天、断桥、残雪、宝云亭、武云亭和孔雀亭等8个油气田。此外,还有玉泉、龙井、孤山等若干大型含油气构造。自2004年5月以来,日本国内对中国开采东海油气资源,特别是春晓油气田表示出“强烈关注”,认为中国侵占日本的海洋资源,并认为,储藏在东海海底的油气资源。按照他们所定的“中间线”方案,大部分石油都储藏在中间线日本一侧的海底;而中国方面抢先进行开采,会像吸管一样,不仅吸于中间线中国一侧储藏的石油,还会顺势把日本一侧储藏的资源也一并吸走,从而造成日本国家利益的损失。据此,日本媒体和部分人士要求日本官方尽快采取措施,与中国争抢这块“海底石油蛋糕”。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就中日东海油气争端与日方进行多次磋商,日本横蛮的要求中国提供春晓油气田的有关地质资料和数据,并允许日本企业在春晓油气田附近从事油气开发探测工作。从而使中日东海油气争端不断升级,严重威胁中日和平友好和亚洲的稳定。
中日东海油气争端从根本上说源于中日东海划界问题,而中日在东海的划界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钓鱼岛等岛屿的主权归属争端以及它们在划界中的效力问题;二是冲绳海槽在划界中的地位问题。两国1995年开始举行海洋划界磋商,共进行了8次非正式和18轮正式磋商,都未取得圆满结果。
(一)钓鱼岛等岛屿的划界效力问题
从地质上看,钓鱼岛等岛屿位于中国大陆架边缘,其西面和西南面的海水深度均在200米以内,且愈靠近大陆海水愈浅。而其东面与日本琉球群岛之间隔着深达6500米的琉球海沟。钓鱼岛位于诸岛屿中的西南,距离日本宫古岛西端90海里,距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102海里。全岛略作半圆形,面积4.319平方千米,海拔360米,为钓鱼岛等岛屿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者。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有关海洋划界的司法及仲裁实践来看,岛屿是海洋划界中最典型和最经常出现的特殊情况。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岛屿应被看成特定划界中的特殊情况以及应当如何确定特定岛屿的划界效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适应多数国家利益的统一标准。一般的实践是根据划界的具体情况分别给予岛屿全效力、部分效力或加以忽略。那么,应当给予钓鱼岛等岛屿何种效力才能确保中日海洋划界获得1982年《海洋法公约》所要求的“公平解决”呢?
尽管钓鱼岛等岛屿完全符合1982年公约第121条(1)规定的岛屿要件,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就有资格主张自身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因为并非所有“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都可以有自己的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该条第3款同时规定:那些“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岛屿只能被看作“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很清楚,区分岩礁和其他岛屿的标准是特定岛屿能否“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凡是不能满足上述标准的岛屿,就不得拥有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
应当看到,1982年公约关于岛屿制度的规定是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支持和反对岛屿同大陆领土享有同样海洋权利的两种对立主张斗争的结果。公约第121条的前两款反映了希腊、新西兰、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多岛国的主张,认为应当坚持1958年《大陆架公约》的立场,即所有岛屿,不论大小,都应与大陆领土享有同样的海洋权利。而第121条(3)则反映了土耳其、马耳他、罗马尼亚以及非洲等国家的意见,认为应当对岛屿加以分类,各类岛屿应享有不同的海洋权利。此外,同1958年公约相比,1982年公约对岛屿的海洋权利进行了限制,这与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扩展国家海域权利的整体趋势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在解释第121条(3)时,就必须“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既然该款的目的在于否定若干岛屿享有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权利,以作为对第2款的限制,那么对于第3款的解释就必须从严,以免使这项限制失去意义。就钓鱼岛等岛屿而言,只有钓鱼岛上有饮用水,但其面积只有4.319平方千米,且无人居住。这一事实表明,如不自外界输入相当资源,单靠钓鱼岛本身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似乎难于维持人类的长期居住。
就划界实践而言,岛屿的划界效力一般是通过权衡它对界线的影响程度与其自身重要性之间是否成比例来决定的。2001年国际法院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就是根据这一标准否定了巴林的雅里姆岛在北部地区的划界效力,认为它会“歪曲边界并导致不成比例的效果”。岛屿的自身重要性取决于岛屿的面积、人口、经济等因素,而它对界线的影响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岛屿的位置。岛屿距离本国海岸越近,等距离线越远,其对界线的影响程度就越小,因此对岛屿的面积和人口等因素的要求也就越低,其获得全效的概率就越大;相反,岛屿距离本国海岸越远,等距离线越近,其对界线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大。因此,对岛屿的面积和人口等因素的要求也就越高,而其获得效力的概率就越小。
允许像钓鱼岛等岛屿这样的面积小、无人居住的中区岛屿在划界中发挥效力,不但“将与近年来在大陆架问题上的国家实践的趋向背道而驰”,而且会“歪曲边界并导致不成比例的效果”。总而言之,公平的考虑是钓鱼岛等岛屿在中日海洋划界中不产生任何效力,而最多只能拥有12海里的领海。[16]
(二)冲绳海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东海大陆架划界而言,中国主张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而非日本岛屿的自然延伸,而公平的划界结果就是要实现自然延伸原则。因此,应当以冲绳海槽,而不是中间线作为中日两国大陆架边界。但日本认为冲绳海槽只是两国自然延伸之间的一个偶然凹陷,不足以中断两国大陆架的连续性,因此主张以中间线为界。这样,如何看待冲绳海槽的地位就成了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最关键和最困难的问题。同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影响着能否实现1982年公约第83条所要求的“公平解决”。
最早将“自然延伸”和大陆架法律制度联系起来的要算1945年《杜鲁门公告》。根据该公告,美国政府认为“毗连国家对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行使管辖权,是合理的、公正的”,因为“大陆架可以认为是沿海国家的陆地的延伸,因而自然地属于它”。尽管1958年《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定义的第1条中并未明确提及自然延伸,但1969年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将自然延伸这一概念正式地引入到大陆架的法律制度中,并将其作为沿海国对大陆架惟一的权利基础。1982年公约第76条第1款对大陆架的法律定义作了新的界定,在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的同时,规定“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百海里,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国际法院1982年在“突尼斯—利比亚案”中认为,就“距离在某些情况下是沿海国的权利基础而言,它摆脱了自然延伸是惟一的权利基础这项原则,”但“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是主要标准”。尽管国际法院1985年在“利比亚——马耳他案”中态度有所转变,认为“至少只要这些区域是位于从有关海岸量起200海里以内的,作为大陆架而提出的”,但强调“这并不表示自然延伸的概念已经为距离的概念所代替,它只意味着在大陆边没有扩展到从海岸量起200海里的地方,自然延伸……部分是由从海岸量起韵距离决定的,而与下面的海床和底是互为补充的,两者都仍然是大陆架法律概念中的基本要素”。[17]
尽管1982年公约第76条第10款规定,关于大陆架定义的规定“不妨害国家间大陆架界限的划定”,但国际法院1985年明确指出,海域的权利基础和划界问题“这两方面不仅有区别而且也互为补充是不言自明的。将被划界的大陆架的权利基础不可能同这一划界无关”。到目前为止,在由第三方参与解决的大陆架划界中,地质、地貌因素均未影响划界结果。然而,究其主要原因,正如仲裁法庭1985年在“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中所言,“为划界的目的,只有存在着大陆架的分离,对于自然延伸规则的引用才能是有效的”;而“如果大陆架被认为是连续的,那么根据现今国际法,人们便再不能有效地引用任何特征来支持其关于自然延伸原则并旨在为一个确定自然分界的划界提供依据的主张”。而这恰恰就是1977年、1982年、1985年“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和“利比亚——马耳他案”所遇到的情况。然而,国际法院的这一论断不应被理解为在今后的大陆架划界排除地质、地貌因素的相关性。前面已经指出,尽管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基础已经从惟一的自然延伸原则转变为自然延伸加距离标准,但自然延伸原则仍然是沿海国的权利基础之一。距离标准的出现使得那些以前由于存在自然延伸的中断而不需要划界的大陆架区域如今也出现权利的重叠了,即由距离标准和自然延伸所引发的权利重叠。这种划界同那些完全由距离标准所引发的权利重叠或共处单一大陆架的划界是不同的,因为它的“权利重叠区域”是一国自然延伸界限和另一国200海里界限之间的区域。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自然延伸的中断以及自然延伸的界限,当然需要考虑地质、地貌因素了。同时,在理解国际法院1985年的言论时也不应忘记,利比亚和马耳他海岸间的最大距离为183海里,因此,基于距离标准将使得整个海岸间的区域都成为“权利重叠区域”。实际上,1985年法院并没有把利比亚关于“断裂区”构成他和马耳他大陆架之间根本中断的主张置之不理;相反,它是在详细审查了有关的证据之后才拒绝利比亚的上述主张的。法院的理由是,尽管这些地质、地貌特征完全可以称为“中断”,但它们能否构成“根本中断”却还是有疑问的。
那么,冲绳海槽是否构成了中日之间自然延伸的中断呢?1969年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为了阐明自然延伸的概念,考察了挪威海槽。该海槽位于挪威南部和西南部海岸边缘,从斯卡格拉克海峡尽头起到北纬62°止,深235—650米;长约430海里,宽度从南部的30海里到北画的70海里。国际法院指出:“被该海槽同挪威海岸隔开的北海大陆架在任何自然意义上都不能认为,是邻接该国,或是其自然延伸”。尽管1965年英国和挪威在划界时没有考虑挪威海槽,而是按照中间线划分彼此间的大陆架边界,但那是英国为了避免无限期拖延开发油气资源而不得已做出的让步。据此推论,那些比挪威海槽更明显的地貌特征无疑应被视为中断了有关国家间的自然延伸。而且,国际法院当时是以相当肯定的语气提及挪威海槽的,因此该海槽不应被视为构成中断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即使某个地貌特征没有挪威海槽明显,也并不能得出该特征就不构成中断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判断某个地貌特征的性质是国际法律程序中经常运用的方法。例如,1977年仲裁法庭认为:“同北海深深的挪威海槽相比,只能将它们(赫德海渊——赫德渊断层区)看成是大陆架地理结构上的小断层”,因此不能影响“大陆架的基本完整性”。而1982年国际法院在否定突尼斯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海沟构成两国间“一条真正、自然的海底边界”的主张时指出:“像赫德海渊这一重要特征在1977年英法大陆架案中都没有被赋予这一意义”。因此可以说,只要冲绳海槽比挪威海槽的特征更加显著的话,就有理由得出冲绳海槽构成中日两国在东海自然延伸的界限这一结论。
冲绳海槽是自日本九州西经琉球群岛至我国台湾东北的弧形海槽,形同舟状。海槽北浅南深,北部最深894米、中部1188米,而南部深达2700米。海槽内水深1000米的海床超过总面积一半,水深逾2000米的海床也占五分之一左右,冲绳海槽隔着琉球海脊与琉球海沟平行,海脊的顶端冒出海面形成琉球。这清楚地显示出,冲绳海槽的特征比赫德海渊和马耳他海槽显著得多,比挪威海槽也更长、更宽和更深。此外,两者的地质构造情况也不尽相同。包括挪威海槽在内的整个北海下面都是大陆地壳,而冲绳海槽两侧地质构造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其西侧是一个稳定的大型沉降盆地,地壳厚度30千米以上,属于大陆地壳;其东侧琉球岛弧地壳运动异常活跃。冲绳海槽底部的地壳厚度为18.5~22千米,属于大陆地壳向海洋地壳过渡的构造带,并且陆壳特点少而洋壳特点多。这样看来,如果说挪威海槽中断了挪威海岸向北海的自然延伸的话,那么地质、地貌特征比它显著得多的冲绳海槽无疑构成了中国大陆领土和日本琉球群岛间自然延伸的界限。中日两国处于两个分离的大陆架,而非“共大陆架”的事实对两国间的大陆架划界具有重大影响。冲绳海槽的存在使等距离方法不适宜中日大陆架划界,因为等距离线只平分了两国海岸间的距离,而没有平分两国的“权利重叠区域”,即冲绳海槽轴线和日本200海里界限之间的区域。事实上,海岸中间线将位于“权利重叠区域”中线的中国一侧。这样,使用海岸中间线就不是对两国海岸向海扩展的权利给予平等限制,而是否定了中国有主张直到冲绳海槽的构成其领土自然延伸的全部大陆架的权利。因此,以等距离线为中日大陆架划界出发点是不符合国家平等原则和公平要求的。[18]
三、中国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原则和东海油气争端的解决
中国有漫长海岸线和重大海洋利益的沿海国家,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争端实践中,中国遵循国际法和有关的国际惯例,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形成了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一)公平原则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作为漫长海岸线和重大海洋利益的沿海国家,中国需要与周边若干国家划分海洋边界,这主要包括:在黄海面临与朝鲜和韩国的划界问题;在东海主要面临与日本的划界问题;在南海面临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等国的划界问题。其中除全部涉及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外,与朝鲜和越南还需要划分领海边界。
关于领海划界,1973年7月14日中国在《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中主张:“相邻或相向的沿海国,应本着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对等的原则,划定相互间的领海界线”。
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中国代表1973年3月在海底委员会发言时指出:“同处一个海域的邻近国家,应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合理划分它们之间的管辖范围”。同年在《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中也主张应由有关国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确定”。1978年4月25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在第七协商组发言时首次详细阐述了中国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立场。他指出:划界“应当由双方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照顾到一切有关情况,通过协商共同确定,以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等距离线只是划分海洋界限的一种方法,不应把它规定为必须采取的方法,更不应把这种方法规定为划界的原则。海洋划界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公平合理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采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的方法,能够达到公平合理的划界结果时,有关国家可以通过协议,加以使用”,但反对“在有关国家未达成划界协议前,单方面将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强加于另一方”。中国表示“基本上同意”1977年7月15日产生的《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关于划界条款的规定。该规定来源于1976年第四期会议上产生的《订正的单一协商案文》第71条和第65条第1款,即“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应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完成,适当时适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并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1980年8月25日中国在第九期后期会议全体会议上重申了上述主张,强调中间线或等距离线方法只有在符合公平原则的条件下才能采用,“公平原则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它不仅为许多重要国际文件所确认,而且也为一些有关海域划界的重要国际判例所肯定”[19]。1996年5月15日中国在批准《海洋法公约》时声明:“将与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通过协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划定各自海洋管辖权界限”。而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参照”公约的有关条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岸相邻或者相向国家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重叠的,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限”。
综上所述,可以将中国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公平立场简单归纳为:第一,协议划界,即划界应当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加以解决,反对单方面将自己的划界立场强加于对方;第二,公平原则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划界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考虑各种因素;第三,等距离方法只是一种划界方法,只有在能够达到公平结果时才能够被使用,而且必须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加以使用。[20]
(二)自然延伸原则
中国在划界问题上的立场同其在大陆架权利基本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在东海面临的划界问题密切相关。在大陆架权利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大陆架为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认为大陆架定义“是以自然延伸原则为基础的,这符合关于大陆架科学的地理和地质概念”。中国代表1973年3月20日在海底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表达了中国对自然延伸原则的支持:“从地理条件来看,临近沿海国家的浅海区域是这些国家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1973年中国在其提交的《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中指出:“根据大陆架为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沿海国可以在其领海或经济区以外,根据具体的地理条件,合理地确定在其专属管辖下的大陆架的范围,其最大限度可由各国共同商定”。关于公约第76条中自然延伸原则和距离标准的关系,1979年4月27 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在海洋法第八期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时强调:应当根据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确定一国大陆架的范围,而不是机械地以某种距离标准规定大陆架的范围。只有在不影响自然延伸原则的前提下,大陆架不足200海里的国家才可以扩展到200海里。1980年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在海洋法第九期会议后期会议上重申了上述主张。
(三)以和平方式创造性的解决中日东海油气争端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海洋领土争端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联合国宪章》把和平解决有关海洋划界争端规定为各缔约国应尽的义务,该和平方法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解、调解、仲裁、司法解决等[2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再次否定了在海洋事务中使用战争及其他非和平方法作为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方法的合法性。由于有关海洋划界的问题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在1982年正式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划界问题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界限,应在有关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而无论采用由双方自行谈判协商解决,还是由第三方协助或由国际法院判决,一般都要决定适用的国际法以及法律原则[22]。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国际法的渊源不仅包括一般的国际公约,还包括国际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及著名的国际司法判例。到目前为止,国家之间解决划界的大部分争端都采用有关国家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来加以解决,而采用谈判等方式不能解决的,一般就采用通过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的判决或裁决等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划界争端。
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争端问题上涉及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两类不同性质的区域,两国又分别坚持中间线原则和公平原则,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划界原则又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从海洋边界争端案例判决或裁决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是最基本的划界原则。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国际法,这些案例又可以作为今后国家之间海洋划界的依据之一。再从中日两国争议海域的实际来说,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如果严格按照自然延伸原则划定分界线,将延伸至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附近,这对日本来说将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太公平的。而如果按照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原则划界,一方面本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东海大陆架将会划归日本,对中国来说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由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界限的一致性,中国的大批渔船将会失去传统的作业渔场,对我国的海洋渔业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中国也将不会接受。因此,中日两国东海的最终界限应该是在中间线和按照自然延伸原则划界所得到的界限之间的一条折中的界限,这一结果应该是对双方来说最合理的。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实现、目前面临的周边形势、石油可持续供给战略等决定了目前局面下维持和平大局的重要性。上世纪我国政府有关领海权益的处理过程,充分表明了按照国际海洋法及有关专属经济区规定的前提下,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海洋边界争议应该是最符合当前国家整体利益的。[23]
具有良好油气资源前景的海洋区域无不受原始地质构造背景的控制,一种是原始大陆板块背景上或其边缘的断陷或称为衰亡裂谷盆地;另一种是被动大陆边缘的沉积三角洲盆地。日本目前正在东海大陆架上进行油气资源勘探,显示出与中方一搏的姿态,其位置位于日方鼓吹的所谓“中线”以东。日本政府的举动,很大成分上是在于造势东海主权的争夺,以迎合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对此,中国政府应该提出明确抗议和严正警告,以清晰表明整个东海大陆架属于中方所有,但同时仍然要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不宜激化争执,起码目前对中国而言不是争执应该升级的最佳时机。因此,出现争执和不同意见,只要从科学、睦邻友好和按国际法、国际通例互相协商的方法处理,应该可以取得合理的解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要加快培养一批具备石油地质专业知识的地缘政治研究人员和国际法专家,以理性的态度思考。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以国际法及有关案例为依据,不断深入地论述并捍卫东海大陆架及我国其他海域的权益。从战略高度研究、设计如何维护我国的各个大陆架以及诸如钓鱼岛、南海诸岛等的领海权益,以指导、配合国内各界诸如民间的“保钓”力量等。总之,要在不损失领海权益的前提下,注重维护中国“和平崛起”的良好环境。
收稿日期:2006—01—20
标签:大陆架论文; 海岸线论文;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论文; 中日东海问题论文; 中日钓鱼岛争端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中国钓鱼岛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法律论文; 岛屿论文; 地理论文; 地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