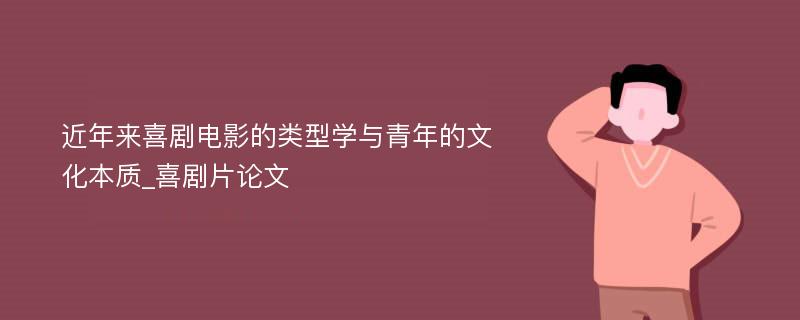
近年喜剧电影的类型化与青年文化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近年论文,喜剧电影论文,类型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在声势浩大的大片浪潮的挤压之下,以《疯狂的石头》为肇端,盈利模式与大片截然不同但同样的成功,使得中小成本影片尤其是小成本喜剧电影也形成了一个持久不衰的浪潮,颇为引人瞩目。
大致可以说,在当下与大片分庭抗礼的中小成本电影市场中,喜剧占了一多半。这堪称是一个小成本喜剧的时代,在大片拯救了中国电影的票房之后问题渐显(如今年的几部古装武侠大片大多以票房和口碑的双双落败而告终)的背景下,喜剧电影凭借着题材选择的亲民化、时尚化、偶像化,情节安排的喜剧化,内容的轻松,剧作、表演的灵活等优势在众多类型中脱颖而出。
但就中国电影史而言,喜剧电影一直并不繁盛。20世纪前半世纪有过“早期滑稽短片”、“软性电影”,“孤岛”时期和40年代末市民喜剧创作的高潮,也留下大量的喜剧电影经典,但大体而言,那种比较纯粹的,凸显纯粹娱乐功能的喜剧一直是没有成为主流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喜剧创作的禁忌和雷池日益增多,喜剧意识渐淡,“讽刺性喜剧”昙花一现,“歌颂性喜剧”、“轻喜剧”则蜻蜓点水而已。
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传统文化的渊源。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对文学艺术有着严苛的社会功能、伦理规范等方面的要求和禁忌。孔子不但自己“不语怪力乱神”,还以“文质彬彬”、“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偏不倚”之类的“中庸”之道来要求“君子”和文艺。而他对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原型性意义,其思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并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语)。而从近现代中国文艺思潮来看,以“焦虑”、“悲凉”为美学风格主潮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也不鼓励喜剧(也许,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太灾难深重了,中国人又怎么喜得起来?)。著名的“巴老茅”没有一个是喜剧作家(老舍略有一点京味幽默),张天翼等喜剧作家最后则从喜剧创作退居儿童文学创作了。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喜剧美学的流脉所幸在港台电影中有大量留存和超级发挥。不夸张地说,香港喜剧是“喜你没商量”!20世纪80年代,从逐渐进入内地的香港喜剧电影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了大陆轻喜剧之外的另类无厘头打闹喜剧的存在:“嬉笑怒骂”、“无厘头”、常常“俗不可耐”,更不刻意追求社会教化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港台电影文化影响的进入,美国电影影响的重启,喜剧创作的类型、风格越来越丰富多元了。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喜剧越来越受到欢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率先成熟的类型电影“贺岁片”即以喜剧为主体,而贺岁档电影票房则撑起了每年中国电影市场全年票房的几乎一多半。
一、近年中小成本喜剧电影的亚类型和发展态势
近年来,许多中小成本电影呈现出明显的喜剧化倾向,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类型性特征的中国特色的中小成本喜剧类型片。
在中小成本大喜剧概念下有几个亚类型较为突出,此即温情都市爱情喜剧、黑色幽默喜剧、戏说古装喜剧等。这三种小成本喜剧在叙事上均已形成了某种亚类型性的特点。
其一是温情都市爱情喜剧,风格温情而时尚,大多发生在都市,表现白领、职场生活,多为爱情题材的轻喜剧片,如《爱情呼叫转移》、《命运呼叫转移》、《窈窕绅士》、《夜,上海》、《全城热恋》、《全球热恋》、《非常完美》、《爱情36计》、《桃花运》、《爱情左右》、《游龙戏凤》,还有《女人不坏》、《第601个电话》、《完美爱情》、《杜拉拉升职记》及创造中国小成本电影票房新纪录的《失恋33天》等。
这类喜剧在叙事上一般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在此之前主人公则历尽各种艰辛去争取心目中的真爱。为了吸引眼球并且讲述多种爱情观,有些影片采取“糖葫芦”式结构,用一个人作为主线,穿插多段感情经历(如《爱情呼叫转移》);有的以追寻真爱为主线将不同状态下的“问题情侣”进行堆砌(如《全城热恋》,《全球热恋》等多段式叙事);有的将善意的戏谑与技巧的诙谐相融合来演绎当下都市男女的价值观、人生观、爱情观等等,用都市男女间啼笑皆非的纠葛来调侃爱情、婚姻以及人的各种欲望(如《非常完美》、《爱情36计》等)。这一类喜剧将镜头对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白领、金领阶层的青年人,以浪漫的轻喜剧化的故事表现当下都市、职场生活,影片虽为写实性日常生活但影像鲜光亮丽,风格时尚温情,表现出较好的视听效果,实际上超越了严酷的现实生活,折射了进入社会或即将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白领”、“金领”白日梦。
其二是黑色喜剧(平民喜剧)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斗牛》、《走着瞧》、《杀生》、《黄金大劫案》等。影片从始至终环环相扣,人物冲突激烈,情节起伏跌宕,加上导演对于节奏的掌控以及喜剧片特有的各种笑料包袱(如方言的运用,对现实的嘲讽等),严肃题材也借此表现,使得疯狂的背后有严肃和清醒,不乏现实指涉。《疯狂的石头》堪称代表也是始作俑者。影片以多线快速展开而天衣无缝的编剧,流畅的视听语言效果,地道的方言特色,精彩到位的表演、难得的“川味”黑色幽默,创造了2006年电影市场的奇迹,引领了一种亚类型电影的兴盛。
新世纪以来,“这种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①这些中小成本电影明显受到美国后现代风格电影、某些低成本独立制片电影、香港地区无厘头电影等的影响。在这些影片中我们不难看到似曾相识的,类似于盖·里奇、科恩兄弟、大卫·林奇的影片痕迹,更有来自更近的以周星驰喜剧为代表的“无厘头”香港喜剧片的影响。有论者称这一类影片为“受‘港味’影响的‘好看的电影’”:节奏快,噱头密集,反映了香港电影文化的“北进”。②
其三是戏说风格的古装喜剧,表演夸张、风格恶搞、娱乐性强、古装或古今混杂,如《刀剑笑》、《隋朝来客》、《十全九美》、《我的唐朝兄弟》、《大电影之数百亿》、《天下第二》、《大内密探灵灵狗》、《追影》、《疯狂的赛车》、《夜·店》、《气喘吁吁》、《熊猫大侠》、《倔强的萝卜》、《三枪拍案惊奇》等。
这类喜剧是对历史的娱乐化,是将历史游戏化、寓言化,满足了大众颠覆一切权威的文化心理,而古装只是为了逃避现实和嬉笑打闹的方便。影片中的各个朝代的历史背景往往不必具有历史真实性,而只是一个假定性情景,是一个可以忽略其具体性的历史真空。这类影片同样“港味”十足,往往采用每两分钟让观众笑一笑的叙事策略,将古装故事、现代人物表演、爱情元素、无厘头风格杂糅起来,创造了良好的票房市场。
上述小成本喜剧电影往往以快速变化的影像组成视听连续之流高强度、高饱和的能指符号,画面、音响的表意有时成为一种漂移、破碎、零乱、不固定的,非能指与所指约定俗成结合的表意方式,已经超越了索绪尔意义上语言符号的记号系统。它们在叙事上也呈现出某些共同特点,如结构多变灵活,或者是一条主线多条副线交错快速错综推动进行,叙事节奏快速。或是麻辣烫式的结构,内容稀薄、人物众多,反复叙述相近的故事;视听语言活泼,镜头转换快、细碎,剪辑轻快跳跃,明星客串多,迎合年轻的观影人群,或者说是平均年龄21.5岁的中国当下观影主力军。
从类型的角度看,此类小成本喜剧电影有着明显的类型杂糅的特点。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可以说是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是综合杂糅多种类型的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的出现。
二、电影中“青年性”的文化流变及其意识形态征候
近年中小成本喜剧电影繁盛是某种新的青年文化或青年性(Youthfulness)崛起的意识形态征候。
一般而言,在社会和文化结构中,青年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在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处于次要、从属、边缘性的地位。青年总是被认定为需要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被动者,他们缺乏青年人独立的话语表达,能够有效承载意识形态的文艺媒介不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青年意识形态,处于不被社会关注的状态。他们偏离中心而被视为异类,无法对社会构成大的影响和冲击,社会地位低下。
这种边缘化的文化境况培养了独特的青年文化,使得青年文化或青年性常常表现为激进、标新立异的姿态,崇尚感性感觉、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理想主义等,往往表现为与现存社会道德体制和规范的不和谐与紧张,甚至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危险性或至少是冷眼旁观、冷嘲热讽的不合作姿态。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伯杰认为的,“具有青年性的人们总是倾向于冲动、本能、精力旺盛、敢于探险和投机、轻松活泼;他们倾向于正直、坦率、引人注目、言语干脆(还没有养成掩饰的技巧和习惯);他们经常桀骜不驯、没有礼貌;他们好走极端,没有节制,不知道中庸之道;他们寻求行动,而不是寻求固定的规则;他们总是开玩笑;游戏的动机决定了他们的很多行为——他们总是倾向于把他们变成游戏,甚至是在看来最不合适的环境之下;他们缺少谨慎和明断,使自己陷于全部热情之中,带着强烈的性兴奋投入可能带来颤栗和激动的行动之中,不顾后果地去追逐”。
在中国电影(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艺术)的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电影的“成年人气息”过于浓重,“青年文化性”积弱。上半世纪的内忧外患、颠沛流离,下半世纪的政治紧张和意识形态重压,都是种种原因之一。有论者指出,“自50年代以来,占据绝对霸权地位的革命意识形态孵化出了独特的青春叙述方式,它将青春定义为个体为了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阶段。”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青春之歌》、《我们的田野》、《本命年》、《红衣少女》、《青春无悔》这些影片虽以青年人、青年心理、青年问题等为题材和观照点,具有一定程度的青春性,但相对来说,意识形态的浸淫或者往其他类型影片的倾斜,使得这些影片多了一份明朗的理想主义色彩,少了一份青春感伤、青春忧郁的私密性和真诚性。其青春叙述热情洋溢,个人成长史从属于国家的生成史,凸显为了至高无上的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主题。因而很自然地将个体叙述消融到国家、历史的大叙述之中,形成了共性大于个性的艺术特征。在此类电影话语中,个人成长的成年仪式与革命胜利的宏大话语完全缝合在一起,或者说,个人的成长是为了印证国家和革命的宏大叙事的不容置疑性。
新时期以来“第六代”导演的影片,是20世纪中国文艺中具有明显青年性的艺术现象。这种青年性有别于美国好莱坞经过国家意识形态洗礼矫饰的带有青春抚慰性的“青春片”(如《毕业生》、《无因的反抗》、《冒险的行当》、《美国派》等典型的美国青春类型片)。关于此类“青春片”,路易斯·贾内梯曾认为,由于当代美国电影观众的75%是年轻人,所以青春片直接迎合了年轻影迷的爱好;他认为青春片的类型电影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期喜剧”。美国学者埃·拉宾也认为,青春片的核心主题是“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既不是无能为力的儿童,又不是自立的成人,而是处于一种成长中的过渡状态”,它涉及“年轻人的生活脱离大社会中成人所关心的问题和责任的转移”。这也明显使得青春片标志着一种统一的消费行为,其中既包括每个时代对电影的消费,也包括对电影中所表现的时尚的消费。美国学者斯蒂芬尼·扎切莱克在论及《美国派》等“青春喜剧片”时认为“这些青春喜剧满足了青少年心想事成的实用主义心理。比如许多青春片以郊区为背景,可片中的少男少女们的穿着考究,他们的卧室布置得富丽堂皇,比他们实际生活的环境强之百倍”。④
早期的“第六代”电影因为多数为体制外的制作,所以顽强地保留了那种青春反抗性、意识形态异端性和边缘性色彩,虽然也不乏时尚化的外观,但还是发自真诚的表达个体的孤独、痛苦,绝少无忧无虑的喜剧性,从而成为转型期中国青年文化生成的典型例证。但随着他们逐渐被体制接纳,从“地下”走到“地上”,市场越来越成为他们影片生产所要考虑的要素,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青春电影表现出日益向青春消费发展的走向,青春反抗的色彩与精英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愈益淡薄,越来越走向世俗、庸常和时尚。
进入世纪之交,以“第六代”为肇始而扩展到包容量更大、范围更广的新生代创作群体的青春类型片反映了更为年轻的一代导演更为贴近时代、更为世俗化、更具商业意识的追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他们的生活也日益“去地方化”,他们的内心世界更为世俗化、日常生活化,原来在“第六代”早期创作中明显存在的意识形态对抗性趋于缓和(“去意识形态化”)。在作品中,青春仿佛变成一种对于以都市为核心背景的物质和文化消费的载体。影片往往风格清新,影像时尚,而且还玩弄叙事游戏,常有时尚题材与欲望主题的隐晦表达。正如论者指出,“青年导演们纷纷把目光朝向各种前卫的、另类的、流行的、反传统的、挑战世俗的生活方式、事件和人物,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来展现新时代日趋时尚化的生活”。⑤
如果用青春主题来概括20世纪后半世纪以来直到当下的中国部分青春电影或者说青年电影中青年文化的发展流变的话,不妨说,“青年文化性”大体走过了一条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残酷”再到“青春消费”的道路。
三、喜剧电影青年文化崛起的表征之一:告别“第六代”
当下中小成本喜剧电影具有鲜明的“青年文化性”,但又是一种有着独特的时代性特点的青年文化性。其定位有两个不同的对象可作参照: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第六代”导演(大体是60后)为代表的精英意识很强的青年文化性;二是以王朔的“顽主”形象系列为肇端,以冯小刚的冯氏喜剧为最终形态,先是平民化,现在则是颇具“中产阶级特征”的“中年喜剧”的文化性。
“第六代”电影的青年文化性常常表现为对现实、主流政治的疏远乃至“冷对抗”,他们的电影关注“灰色的人生”的边缘化生存,把镜头对准了一些个性独立、自我意识极强、自甘放逐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先锋艺术家、摇滚乐手,或是平民和社会边缘人(历史的缺席者、晚生代、社会体制外的个体生存者)。在他们冷漠幽僻的外表下也有着极度的内心焦虑,而这种焦虑是个体的、感性的、只属于自己的。
《北京杂种》、《周末情人》、《头发乱了》、《童年往事》、《牵牛花》、《危情少女》、《苏州河》、《月蚀》、《梦幻田园》等影片传达了“第六代”们动荡不安、迷离驳杂然而却真实感性、孤独痛苦的生存体验,在迷乱、困惑、无奈中隐含着希冀。一部分电影深入到潜意识、隐意识层面来探索当下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如《悬恋》、《邮差》、《冬春的日子》等。在一定程度上,“第六代”导演的影像具有浓烈的个体抒情的味道,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导演对主流、社会以及不可阻挡的商品、媚俗、“机械复制”时代的绝望抗争和自我的无望救赎。他们重归内心世界、个体心灵空间,甚至返回梦想与回忆的源头,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影像独白和精巧复杂的叙述结构、动态可感、梦幻迷离的影像语言,竭力营造出一片虚幻的影像天地,个体精神的乌托邦世界。所以“第六代”导演群体(包含“新纪录电影运动”的群体)实际上浸透着知识分子意识,他们活得沉重而焦虑,他们的作品与喜剧绝缘,精神上可以定位为自我意识觉醒的现代个体知识分子。
显而易见,小成本喜剧电影的青年性(大体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特征则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和世俗性,热衷游戏,“娱乐”狂欢,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好走极端,没有节制,不屑中庸之道,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更加迷醉于瞬时性的视听体验,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时下小成本喜剧电影的青年文化比较轻松地告别了“革命”,告别了“80年代”,告别了“个体主体性”,⑥告别了“第六代”,与这个时代做热烈拥抱状。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时代“长”出来的,天生属于这个时代。
四、喜剧电影青年文化崛起的表征之二:告别“中年喜剧”
新近青年喜剧与冯小刚“冯氏喜剧”明显不同。冯氏喜剧客观而言是王朔“顽主”类小说的延续或进一步的世俗化⑦和社会主流化,也可以从创作主体年龄身份的角度界定为“中年化”。冯小刚的电影如《一声叹息》、《不见不散》、《手机》等具有一种“中年特征”或中年气息,就像90年代诗歌创作界有一个“中年写作”的提法,⑧电影界也有一个或许可以称为“中年喜剧”的现象。引发中年人共鸣的《非诚勿扰》更仿佛是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冯小刚“廉颇老矣”!张颐武也曾称作为“顽主”一代的王朔老了!说实在话,冯氏喜剧其实并不很适合年轻人看。如《非诚勿扰》中的性隐喻语言,《一声叹息》、《手机》中的中年夫妇之间那种“左手牵右手”的感觉和婚姻危机、信任危机,《非诚勿扰》中喜欢怀旧、珍视友情的中年心态,充满苦涩无奈、苦中作乐的“离婚典礼”等,年轻人是根本无法理解其中三昧的。
我们不妨把当下青年喜剧与冯小刚贺岁喜剧电影做一粗略的比较。
其一,冯氏贺岁喜剧往往以语言幽默取胜,呈现为温情机智、幽默谐趣的轻喜剧风格。往往通过生活中耐人寻味的笑料演绎,表达对生活的思考,颇有中国独特的京味文化和平民气质,内涵并不肤浅。而现在的中小成本喜剧则主要转向动作、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夸张表现,更趋于视觉化。这两种喜剧风格的差异似乎有点像传统相声与小品的差别,相声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小品则是动手也动口。从春节文艺联欢晚会中相声逐渐衰落,小品大受欢迎的态势就可窥豹一斑,可见这种趋向具有时代性,并非无缘无故,突如其来。
其二,冯氏喜剧以北京为中心,以京味文化为背景,有一种“皇城根下的现代都市”的文化融合性,而现在的喜剧可以说港味大增,南方文化气息渐浓,现代大都市气息大增,好莱坞影响日重,这显然与香港导演大举北上,香港电影文化与内地电影文化融合有关,也与一个日益全球化时代年轻人审美消费情趣的全球化有关。从编创主体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80年代在以周星驰风格为代表的香港喜剧电影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导演开始长大成人,自己拍片了。
其三,冯氏喜剧是一种温情的社会心理喜剧,它与时代、社会比较贴近,常以当下热门话题折射现实,引发观众的宣泄或共鸣。现在的喜剧更趋于夸张的、表现性强的喜剧,甚至是恶搞、戏仿、颠覆、反讽的黑色幽默喜剧,滑稽的表情、夸张的肢体语言、搞笑化的嬉闹、非逻辑的剧情。很多时候,这些打闹、搞笑的片段甚至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为动作而动作,为搞笑而搞笑,肢体、面部表情之夸张几乎让人感觉又回到了默片时代的表演。而这些打闹搞笑,其功能主要是视觉性、娱乐性的。
与冯氏喜剧通过絮叨饶舌的对话语言折射社会文化心理不同,这些古装喜剧,或娱乐化的现实剧,与社会、现实发生的关系不是“现实主义”式的,顶多可以说是超现实式、假定性的、表现主义式的。他们早就不再坚持对社会的“物质现实的复原”式真实再现,而毋宁说更像是波德里亚所说的远离甚至虚拟现实的“类像”或“仿像”的制造者。
其四,冯氏喜剧在当时而言,投资上还是比较大的,至少是“中大成本”,相应电影语言是中规中矩,从容稳健的。而时下的喜剧电影基本上是小成本,与资金的紧张局促,与摄制器材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发展运用也有一定的关系,他们的电影语言更为活泼多变、破碎凌乱、杂糅拼贴、节奏短促,或都市生活的五光十色飘摇不定,或古今一体时空错乱“无厘头”,令人眼花缭乱。
不妨说,不仅“第六代”导演式的个体主体性时代已经过去,喜剧的冯小刚时代也已过去!在今天,不仅《我11》这样的带有顽强的“第六代”“遗风”的影片无法在今天的受众市场吸引眼球,冯小刚式温情的、社会心理性的、京味京腔的喜剧恐也不再能像当年那样吸引年轻一代了。以新的青年文化性为依托,青年喜剧电影正在登堂入室。
当下中小成本喜剧电影表现出来的这种青年文化性是与整个社会环境、新媒体、多媒体的媒体语境等密切相关的,电影,尤其是青年喜剧电影只是我们所能窥得的其中一斑而已。时下的青年喜剧电影,有着年轻人特有的草根性和娱乐狂欢精神。他们放纵想象力,放纵身体语言,既不像“第六代”导演那样沉湎与玩味个体的孤独愁怨,也不像冯小刚那样自矜自炫于在丰富的生活阅历基础上对生活的洞察与幽默,而是以表情、表演、影像、叙事等的夸张,逃避对个体主体的关注和对现实的精雕细刻、默识体验型的关注。他们奉行娱乐至上,不关心娱乐的社会伦理价值,作为一种文化姿态的反讽搞笑,成为他们的重要话语手段,他们是以反讽、颠覆、搞笑、娱乐化的方式从边缘借助商业的力量向中心和大众社会突进。
从类型的角度看,当下中小成本喜剧电影属于“青春片”范畴或者说是喜剧电影与青春片的类型混杂或文化杂交。“青春片”要求有足够时尚的外观表现以吸引青年观众。所以,那些夸张的嬉笑打闹或者如《失恋33天》中那样的语言时尚,就具有强烈的时尚外观和时尚消费的意味。影片往往以亮丽刺激、符合青年人审美形态特点的外观代偿性地满足青年人的本能需要。就此而言,喜剧电影的表演性就更多地带有时尚性和文化姿态性。
当然,这一代人也在长大成人,小成本喜剧电影表达的青年文化性也在发生某些耐人寻味的变异。以近期红极一时的《失恋33天》来看,这部影片颇为浪漫而小资,整体风格温柔“小清新”。剧中人注重优雅、精致、舒适的生活格调。在黄小仙们喃喃自语般的絮叨中,影片也不再耽于喧闹打斗,嬉笑怒骂的无厘头。《失恋33天》的喜剧格调的变异也许喻示着,小成本喜剧电影的主创和主要受众暨80后、90后一代在长大成人,他们正从边缘逐渐步入社会,他们渴望“我的青春我做主”,但又不得不面对着物质主义的“裸婚时代”,就像《裸婚时代》中的刘易阳们那样,他们也准备当“父亲”了。于是他们不再在社会的边缘嬉笑颠覆,而是渴望物质、安全、理想兼具的有质量的生活。一言以蔽之,他们正在与社会进行磨合,准备整装进入这个世俗庸常的社会。
注释:
①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200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②赵卫防《固守和北进——对新世纪以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美学互动的思考》,丁亚平等主编《跨文化语境的中国电影——当代电影艺术回顾与展望》,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
③王宏图语,转引自张渝《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消费——作为绘画主题词的青春》,《中国艺术》2003年第2期。
④[美]斯蒂芬尼·扎切莱克《青春喜剧片》,《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年2期。
⑤颜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5页。
⑥详情参见笔者《抒情的诗意、解构的意向与感性主体性的崛起——试论第六代导演的“现代性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顽主一族的市民形象在银幕上的崛起,涉及社会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g)问题。世俗化与超越性相对,是一种关注现实生活的取向,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西方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世俗化趋向与中世纪贵族社会的瓦解相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形成,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不再以出身而是以金钱作为衡量人的社会身份和成功的尺度。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俗化进程,也是对长期以来以出身和成份来衡量人的地位的官本位、政治本位文化的反动。所以顽主一族形象在银幕上出现的文化意义在于,以一种嘲讽解构的姿态告别政治意识形态,告别那种对于神圣、教条的盲目崇拜和非理性的狂热,而回到实在、感性、世俗的日常生活状态,回到一种尊重个体生存的实用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尊重法律的契约意识,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工作伦理精神”。
⑧详见陈旭光《中年写作:文化转型年代的思与诗》,《大家》1997年第4期。
标签:喜剧片论文; 失恋33天论文; 青春片论文; 疯狂的石头论文; 电影类型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青春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