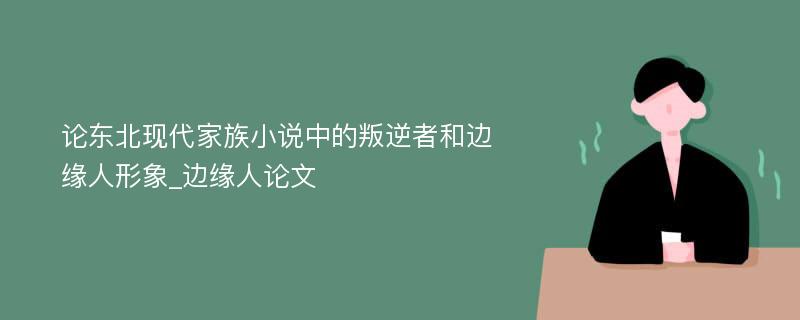
论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中的叛逆者与边缘人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叛逆者论文,形象论文,家族论文,边缘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叛逆者和边缘人是最能突出体现作家创作意旨的人物形象。析理和解读这两类人物群体,是探求东北现代家族小说要义的关键所在。
自巴金始,中国新文学家庭小说都在重复着一个基本命题:革命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终结性消解。在革命的冲击下,传统封建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家族内部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由观念上对旧家庭的反叛走向行动上对旧的秩序与伦理的破坏与颠覆,企图用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来救赎古老的家庭和社会。五四以来家族母题小说的这种叛逆与救赎的深度模式深深地影响了东北作家的创作。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中创作得最成功的形象不是那些意志坚定的彻底的反封建的战士,而是在传统家庭伦理的与现代家庭理想之间徘徊的怀揣救赎思想的叛逆知识分子。《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绿色的谷》中的林小彪、《平沙》中的白今虚、《麦》中的陈穆等无疑是这类文化新人的代表。五四以后东北作家主体意识觉醒,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与西方现代思想的渗透下,青春力量扩张,主观意志高扬,情感的骚动与人性的弱点种种复杂的感受交织在他们的思想性格与心理情感中,自然也反映在他们笔下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中。这些东北青年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和民族灾难面前,面对旧家族的不可逆转的衰败表现出了一种对封建家庭制度的叛逆和对精神家园的拯救相交织的复杂的人性特征。
旧有的家庭和家族的伦理的合法性陷入窘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它提出质疑的恰是这些来自旧家庭内部的叛逆与救赎的文化新人。在这些年轻一代的身上,表现出非常相似的思想性格,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来自于他们超强的思想观念在旧的家族中得不到认同,因为对旧有的家族的叛逆和格格不入而产生无路可走的彷徨,激情的呐喊难以得到回应。他们狂热、敏感,都有比较突出的自我本位立场。这群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性格不仅带有家族、时代的印痕,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在人的意识觉醒后对自身主体精神人格的自发显示。《平沙》中的白今虚,少年起就清高自赏,寡言自守,“一半是鲠直,一半是傲岸”。寄住马府后,目睹了马府的淫乱和污秽,不堪生活激变的打击离家出走,他“开始有意的白热”,也“开始有意的灰颓”;他曾投身于学生运动的“狂潮”,但“潮退时”,他“虽是没被吞入,也没被吐出,却陷入了错迷的泥沼里,永久不拔。他简直不再深信他至今所深信下来的一切了。他感到不堪拯救的绝望和绝情”。他当了一名小吏,“足足有两年之久,在醇酒妇人里埋葬了他的灵魂和智慧”。调“京城”后,他一度对都市生活感到新奇、欢欣,但他随即感受到这新奇的一切,“无非是土和砂”,“他在这涂着鲜艳的颜料的土和砂里,发现不出他的期待着的新的灵魂和智慧”,他转而滥看杂书,想在老、佛、波德莱尔、法兰士、尼采、屠格涅夫等中寻觅灵魂的归宿,但结果更陷入“大昏迷、大疑惑”中,他“感到有灵魂在转地疗养的必要”,便重回故乡。然而此时故乡已人事全非,马公馆里死的死、疯的疯、逃的逃。古丁笔下的白今虚无法与颓败混乱的家庭为伍,在目睹了这旧家庭的崩溃后,置身于这般颓落中无法心宁,只得再度离家远行,孤寂地独步。在白今虚的身上体现着一种典型的来自旧家庭的文化新人面临的“沉没”和“自救”并存的孤独的心态。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这些青年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崇拜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卢梭和康德的学说,反对封建专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他们的家族思想性格中融入了现代意味,有理想的家庭模式,所以他们对旧有的家庭秩序和生存秩序都充满了反叛的精神,在潜意识中总是希望在自己这一代身上实现救赎的理想。《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是在日军侵略的动乱之下,在呈现出山雨欲来的危机时刻,丁家出现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既是一个热情的青年,又从他父亲遗传了富豪公子的感伤。他在南方受教育,远离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加入了思想激进的文学社团,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他从南中国带回了新知识和人道主义,于是由他的心灵之灯,照亮了科尔沁旗大草原的一角黑暗。浮现在丁宁眼前的千万农民黝黑的泪脸、深宅大院里淫逸得厌倦、备感虚无的男女,使他对旧家族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他亲眼目睹了草原上“畸形的、缺陷的、病态的”社会人生,他“在想着,这样,就是这样才应该怎样去救护呢,救护这可爱的人生啊,让生命纵情地跳跃啊”;他感慨于贫与富都处于病态之中,“多余的劳动,把人折伤了,而在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无事可作的懒散,却在蠢然的浑身生了触角似的,患着极度的神经衰弱了。”他非常同情雇农的遭遇,并下定决心致力于改善雇农不幸的生活处境,他充满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亚历山大的坯子”,雄心勃勃地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此时的丁宁是作为具有几百年创业历史的大家族的叛逆者形象出现的,与充满原始资本积累血腥气的祖辈相比,他已经成为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新人”形象。生存作为第一要义,一直是丁氏家族恪守的人生哲学。丁氏家族以此为精神动力贪婪地攫取财富,而到了末代男儿丁宁这一代,又企图通过改善农民的生存问题实现“新人”的理想和抱负。他在反省自己带有祖先强悍粗鄙的本性以后,主动向农民作了让步并再一次离开家乡,把希望寄托在农民之子、反抗的英雄大山身上。在他的心目中,大山无异于草原精神的化身。这里的草原作为丁宁的精神家园已经超越了祖辈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而成为农民具有反抗苦难意识的心灵圣地。
《绿色的谷》中的小彪显然是“喜欢涉猎各种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而受到“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新观念影响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这位拥有大片土地的少东家,从小丧父,虽然是地主的儿子,可母亲却是下坎小户人家石海廷的女儿。父亲死后,母亲“简直就是老石家的一条驴”,在舅父石德海的唆使下,她实际上是被卖给了住洋行的买办钱如龙。有钱太太家的生活,愈合了心灵上的创伤,她的性格被严重扭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她挨打受骂,每天受到钱如龙鞭笞的时候,便“缅想起昔日少女的纯洁的生活,暗自啜泣”。同母亲一起生活过的小彪自然看得一清二楚,从小就滋长出对这种生活的厌恶情感。他认为,“人生是个大骗局,历史也是个大骗局,他骗你,你骗我,我骗你……互相欺骗,互相作假”。从外面的世界读书回来之后,开始大胆地追求个性的独立与解放,追求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他蔑视祖辈留下的殷厚遗产,认为那不是属于自己的;他抛弃封建门第观念,追求美好的爱情。小彪对小莲的爱是真诚的,是这位淳朴的农家姑娘使“那些生长在都市中的女人,被脂粉抹平了脸的女人,一个一个地从他的记忆的网罗跌落下去”。但在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里,他们的爱情之花是难以开放的。对于管家霍凤与姑姑相爱而不能结合,他深知这是“缺陷的制度”所使然。“他几乎想击碎所有旧的堡垒”和“缺陷的制度”,也为自己的宅第高唱过挽歌:“没落是你的出路。”作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小彪知道姑姑林淑贞要以高价出卖河套地的时候,极力反对。这对自家不无好处,可他表示:“这种好处我不想要,我们得为大伙着想。”他望着眼前“懒惫的土蛇似的柳条边,曲折如羊肠的寇河的支流,枯萎的大片草甸”,也“宛如嗅着那草的干枯的香气,使他幻想春天的山谷的美丽”。他对下坎佃户充满同情,对劳动人民依恋,以至于最后发出“我的土地也并不是我的,我想把它们全部送给你们”的誓言。他也寂寞、空虚、苦闷,也曾经信奉人生只不过“随便玩玩”的哲学,但狼沟佃户、绿林英杰和家乡沃土又给他一个极大的滋养和润泽,他看到了封建买办、乡间恶痞那“自私、贪婪、欺诈、没落”的鬼脸,真正感到了农民才是真正的土地的主人,终于将田地分给佃户,把祖辈的产业“一把灰扬出去”,成为“给自己的宅第唱挽歌的歌手”。
在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中,“叛逆与救赎的文化新人类”人物形象的成功,关键得益于作家们对他们思想的复杂性的展示。作家们从这类知识分子精神与心理深层意蕴揭示他们思想的复杂性和弹性。丁宁在他父亲生意失败、家业倾摇的时候回来了,帮他父亲借了一笔钱,去大连做投机生意,自己便暂时接受了残破的家业。在这个时间,他不动声色地又更阴狠地平息了大山领导的农民退租运动,同时发生四次爱情纠葛:他本想与女婢春兄私奔,一齐到南方去求学。结果,因春兄被出卖遭强奸而幻灭了;他在一次出游中意外遇到村女水水,留下了一段情,为此几乎被大山枪毙;又为了给他父亲借钱,受了三十三婶的诱惑;此外,又扮演了托尔斯泰《复活》里的“南赫留道夫”:与服侍他的女婢灵子发生了关系。他离家之后,灵子肚子大了,被丁宁母亲发现,竟将灵子活活毒死,厉声地喊:“你这个不要脸的,……你生下的孩子算谁的,他的名字能上我家的祖先堂吗?”在丁宁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封建家族的叛逆者,五四新文化熏染下的旧家庭的救赎者,却又是一个地道的软弱的旧家族的同道中人。他一方面痛恨游手淫逸的父亲,同时又顺从父亲的荒谬意愿;他一方面怨恨母亲的残虐,同时又没有制止的勇气;他一方面怀抱人道主义的理想,同时又是玩弄女性的伧父;他一方面敬佩大山,想引为同志,可是在现实冲突中,他又成为大山凶恶的敌人。
透过丁宁这个人物,可以看出纠缠在旧家庭的叛逆者和救赎者身上的道与魔、灵和欲、理和情、爱与恨等等诸方面的冲突。这些叛逆者来源于旧家庭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他们无法彻底摆脱与传统家庭及其伦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叛的激进与情感的眷恋同时存在于每一个叛逆者身上。物质上对旧家的依赖与情感上的眷恋,既昭示出他们与封建家庭的无法割断的血缘联系,又预示了他们走出旧的阴影,摆脱传统重负的艰难。作为旧家庭的一部分,他们在抨击它的落后、保守的同时,在情感深处存有维护家族的一份责任,他们未必对旧家庭的灭亡拍手称快,而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哀婉的叹息。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情怀为知识分子的叛逆行为埋下了软弱和妥协的种子。同时,“英雄式的纨绔子弟”尽管接受的新学说,让他们时刻要反对任何的压迫和奴役,提倡平等、自由和解放,但人们常常忽略了这些“英雄式的纨绔子弟”也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他们在大家庭中都具有一种少主人的身份,这给他们带来的是有形的、无形的各种优越感,在他们身上总能找到一种旧有权力的残留和变形。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救赎是有阶级局限性的。
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对传统家庭中女性悲惨命运的关注和焦虑。在五四个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在现实与历史中悲惨的生存处境引起了人们的同情,作家们关注更多的是女性作为人的独立个性与价值。在传统家庭中,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正常的人性被残忍地扭曲,她们成为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家庭中的没有自我的边缘人。东北现代家族小说鲜明地凸显出边缘人形象,其中《绿色的谷》中的林淑贞和《北归》中的杨小蝶,就是两个塑造得比较成功的被旧家族和封建宗法压抑和扭曲的边缘人形象。
山丁在《绿色的谷》中塑造了一个受宗法纲常奴化的、被封建礼教压扁了的女性形象林淑贞。作为狼沟大地主林家的掌门人,林淑贞对这个地主家族充满忠诚和责任感,这个“生命力旺盛的执拗于生的女人”,一面成天坐在那把祖父常年坐的雕花红椅上看守家业,维护林家的门风,另一方面用封建思想和道德精心培养和规范林家的独苗小彪,望其成才以使林家产业得以维持和发展。宗法血统观念在她的身上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家族财产的继承问题上,她不相信除林家后代小彪之外的任何人。所以当她知道小彪与佣户于七爷的孙女小莲相爱之后,当即警告小彪不要受小莲的诱惑。自私、狭隘的家族观念已折磨得她不相信一切外姓之人。至于她本人,首先就是宗法社会封建纲常的牺牲品,林淑贞守门望寡的生命状态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的正常情欲被无情地残害。这时几代忠实奴仆的后裔霍凤,不仅是她操持家业的得力助手,而且也是填补她空虚精神世界的最佳人选,这个对礼教愚守着的女人惧于“门第”和“名望”而不敢公开恋情。事实上这个已被封建伦理和门第观念魔了心智的女人也并非与霍凤真心相爱,两个人的结合,并不能抹平阶级上的差异。她从思想深处并没把霍凤看成是自家人,因而“没把林家的产业分给霍凤丝毫”,“霍凤在林家只不过相同一头强大的名誉雄蜂”。这个被封建伦理奴化了的女性对自己与霍凤的感情也自认不轨而向菩萨赎罪,而且在她死后继续用封建律条“虐杀”了霍凤。作为狼沟大地主林家的守业人,林淑贞终没能守住林家的产业,而是在凄苦的精神生活中,被家族兄弟所杀。林淑贞既是封建家庭制度的牺牲品,又是封建纲常与伦理的维护者和帮凶,林淑贞可怜又可悲的凄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残酷压榨和扭曲。作者在悲叹这个在家族斗争中生命被压扁、灵魂被扭曲的女人的同时,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既戕害女性肉体生命又虐杀她们精神生命的吃人本质。
小松在他的长篇家族小说《北归》中塑造的杨小蝶的女性形象,以人性堕落、精神轰毁和心灵涅槃这种“绝望的体验”,将生存在旧家族中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推向了极致。曹港工业强人杨经业的女儿杨小蝶是一个正充当着学生领袖、热心社会活动且有伟大企图的女青年,忽然受了父亲的唆使,嫁给一个青年工程师。事实上她的父亲是利用自己女儿的婚姻来获得一个青年工程师的支持,从而促使自己在曹港的工业中获得地位,完成一个压迫多数人的阴谋。因此杨小蝶的下嫁在当时曾受痛烈的攻击。从一开始为了父家的责任就对这个婚姻有所承受而嫁给刘振邦的杨小蝶却莫名其妙成了妾,她开始痛恨自己的丈夫,她闹自杀,孤独和寂寞侵蚀着她。在一场大工潮之后,她因怀念父家,又忧虑着父亲的矿山,气愤地放走刘振邦回了娘家。然而,事实上这场工潮正是她的父亲杨经业亲手阴谋策划的,旨在驱逐越来越威胁他事业的杨小蝶的丈夫刘振邦。父家的阴谋瞒着她,杨小蝶面对无视自己的存在、轻视自己的幸福的父家,再一次被一种高渺的孤独感深深包围。杨小蝶又开始仇恨着家庭,感到父亲、哥哥和所有的亲属都欺骗了自己,她大声狂笑,泪影浮在自己的眼睛上。这位既“追求黄金,也追求幸福”的大小姐,在父家和夫家双双受到打击和欺骗之后,心态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她的报复行动病态地表现在她与自己的侄子大光的乱伦行为上。她的所为不只是报复刘振邦对自己的爱情,同时又要报复父家,那就是对杨经业遗产的焦虑与窥视。杨小蝶对黄金的追求在工潮之夜刘振邦败走麦城、其与刘振邦坚决分离的行动中可窥一斑。正如刘振邦后来所言:“也怪她太糊涂,怎么会猜想到我离开曹港就不会再找到阔事情,怎么会见到我离开她爸爸就不能有什么发展。”杨小蝶对金钱的看重,也是促使她同大光的不耻行为的发生。杨经业将自己的财产与事业寄托在杨家的第三代人身上,而杨家“两股”就这么一个大光。她把大光笼络在自己的怀中,无非是看重了大光对杨家遗产的继承权。为此,她的报复越来越病态,越来越疯狂,居然唆使杨家的仆人老唐奸污了自己的情敌和财产的有力争夺者——同样与大光通奸的、大光的婶娘、自己的弟媳妇紫姗。杨小蝶为了报复父家对自己的不公,又帮助刘振邦在曹港的工业上重新获得地位。然而,当刘振邦再一次无视杨小蝶的感情而放弃曹港的事业时,杨小蝶对婚姻彻底绝望。在父亲杨经业死后,因为对杨家的背叛杨小蝶几乎未得到多少遗产,万念俱灰的杨小蝶沉沦在豪赌之中,一夜输了十几万元的巨款而却无人为她偿还。曹港因遭受了战争与暴乱的洗劫,她的父家与夫家均在一夜间土崩瓦解,杨小蝶“沦为几块钱也可以让人开开心的妓女”。在严重肺病中苟延残喘的杨小蝶,最终在曹港的幽灵、曾经是自己丈夫面前的一只狗的梁伟的暴力欺凌中屈辱死去。
杨小蝶令人心悸的悲惨命运昭示了家族伦理的最大的弊端之一,便是对男女的两重标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只有单方面的责任与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父亲、丈夫只知道自己的利益而没有一点为父为夫的责任,他们的自私给妻子和女儿带来的是无穷的精神痛苦与凄惨的生活际遇。家庭和家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男性为本位,女性成为满足男性欲望和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无论是对杨经业来说,还是对刘振帮来说,在这个属于男性的家族世界中,杨小蝶作为一名女性无疑是处于边缘人的角色,不管她如何反抗和抵制,她在家庭中没有任何地位,然而家庭却对她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女性来说,家庭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她们一生都要受到家庭的影响,在属于父亲的家中,她扮演的是听话的乖女儿角色;成人之后,遵从父命,走进丈夫家中,为人妻,同样在家庭中她必须服从,“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这便从经济与人格两方面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可见妇女解放的最大障碍就是腐朽的家庭制度,杨小蝶病态的报复行为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对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地位的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