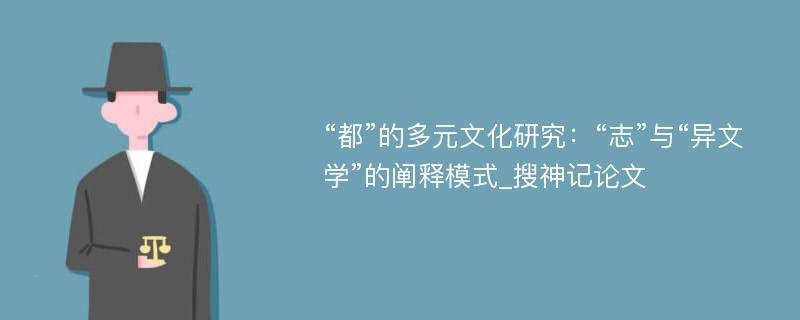
“蛊”的多元文化研究——志怪文学的解读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有许多神秘文化的说法,时至今日还未得到科学而彻底的研究,“蛊”是其中之一。当代研究“蛊”的论著不少,都说它是一种巫术,完全认可古书所说的“蛊”和它的危害。有的并用现代医学、心理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给那些危害来做“科学性”的证明。所谓某种巫术可能是实有的,而所说的那种非理性的效果只能是骗人的。既承认是巫术,又相信它的效果,就没有科学的立场和观点,便是自我矛盾的二元论。
笔者认为那种培养“蛊”以损人利己的巫术是没有的,它们是志怪文学的艺术产物,是智巧性的骗人故事,是汉语多元文化的类型,包含着历史、医药卫生、语文、文学、迷信等因素。我们应当用科学的立场和观点,用新的方法做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而不应被“蛊”牵着鼻子走,完全相信那些奇异的内容。
一、“蛊”的历史解读
要揭破蛊的神秘和迷信,先需要对比早期的平实说法。蛊的神秘化基本是从晋代开始的,在以前,“蛊”字有多种含义,都是指实有的事物,并无神秘性。
“蛊”的本义是吃谷物的螟蛾。《左传·昭公元年》:“谷之飞亦为蛊。”但谷并不能飞。杜预注:“谷久积则变为飞虫,名曰蛊。”[1](2025页)《论衡·商虫》:“谷虫曰蛊,蛊若蛾矣。粟米饐热生蛊。”[2](931页)可见,所谓蛊,就是由“螟”而“蛾”。先吃稻株等的心部,后来吃谷粒等。“蛾”就是螟变态发育的成虫。
“蛊”,也指有害的热毒气。螟蛾生于夏季炎热之时,因此,把夏季的热毒也叫蛊。《史记·夏本纪》:“(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3](184页)《史记·正义》:“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曰‘初伏’……。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按,狗,阳畜也。以狗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3](184页)是说开始设立“伏”这个祭祀节日,在祠中祭祀,又在郭城的四门杀狗,即涂狗血作“血衅”。
“蛊”,也是其他某些害虫的统名。《周礼·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凡殴蛊,则令之,比之。”郑氏注:“毒蛊,虫物而害人者。”[1](888页)令,命令;比,组织群众,都是公开性的。《周礼·秋官·剪氏》:“剪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郑氏注:“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虫鱼亦是也。”[1](889页),所谓“虫鱼”,即蠹鱼,俗名吃书虫。庶氏所除的是使人致病的害虫,剪氏所除的是损害器物的害虫,统称为“蛊”。“以攻说禬之”、“以攻禜之”,是说在特称为禬、禜的祭祀中,宣读对害虫数说罪状而攻击驱逐的词令,韩愈《祭鳄鱼文》、柳宗元《骂尸虫文》、《宥蝮蛇文》、《逐毕方文》等,应就是由此仿写。实质性的措施是用有芳香味的草来熏,统名叫嘉草,具体的一种叫莽草。
“蛊”,也是病名。《素问·玉机真脏论》:“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4]症状或病因是“冤热”,与夏季的热毒叫蛊相承。
“蛊”,也用为动词:迷惑。中热毒之气的中暑是昏迷,引申而指思想情感的迷惑。《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生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又,“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把“内热”与“惑蛊”并提。又,“‘何谓疾?’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曰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1](1781页)筑室于她的宫旁,为她跳《万》舞,就是要她受迷惑。《哀公二十六年》:“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1](2182页)
汉代把埋木偶人使某人得病的巫术叫“巫蛊”。蛊,指受害昏迷。
这种种蛊都是实有的,其文化要素有:1.对客观的暑热、螟蛾危害的认识。2.科学的防御方法是用芳香性的草熏。3.非科学的防御方法是用狗血禁忌和下诅咒性的驱逐令。4.埋木偶巫术用“蛊”称名,即巫术与“蛊”有了瓜葛。后世对1、3、4这三项因素都继承而又变易,再增加繁饰因素,于是产生了许多神秘和迷信的说法。
神秘和迷信说法是从晋代开始的。共有四条志怪说法。《搜神记》卷十二有三条:“余外妇姊夫蒋士,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食我蛊者,乃张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按,“去”字之误)。今世攻蛊,多用蘘荷根,往往验。蘘荷或谓嘉草。”“潘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皆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荥阳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皆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5](157-158页)《搜神后记》卷二有一条:“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饮食,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丈余,便欲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6]
这些说法最大的改变在于蛊是为了伤害别人而专门饲养的。它可以变成狗、猪、蛇、蜈蚣,可以隐形在食物中。但是,对最关键的一点即蛊的本体是什么,却没有说明。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有许多繁衍,总的特点是越说越神秘可怕,越说越有分歧而互相矛盾。有关文献,一般研究蛊的论著都有引录,本文只在后面分析具体事项时,引及相关的局部。
二、医药卫生事理的解读
古代无降温设施,清凉饮料又少,对夏季的热毒特别敬畏。《吕氏春秋·仲夏纪》描写五月的气候:“其日丙丁……其味苦,其臭焦。”是说火神发威,人口干舌燥,吃什么都似味苦,空气像焦灼了。又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是说白昼达到最长之后转为渐短,黑夜则渐长。有的作物已成熟,有的正在成长。是害虫繁殖、活跃时期,有的夏令疾病还会使人死亡。同文还说人们在夏季要调节生活方式:“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止声色,无或静。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大致是说:清心寡欲,减少房事,清淡饮食,节制活动。国家也有相对的措施:禁止砍伐树木烧炭。城门日夜不闭,集市贸易不征税。对在押重犯,暂缓刑罚,增加饮食。不是紧急的劳役暂缓。而这些都是以调节阴阳二气使其和顺的哲学理论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一种指导思想,至于具体事项,未必有充分的合理性。端阳节就由此而来,此不详及。
所以,早期“蛊毒”的文化内涵正是对夏令热毒和医药卫生认识,后来的志怪说法虽把它变说为种种神奇怪异,但仍然有这种本原的影迹可寻。说益虫要在五月五日开始培育,实际就是对早期把热毒叫“蛊”的遮掩性说法。等于说:蛊就是热毒,以五月五日为甚。
《搜神记》:“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5](158页)《夷坚志》补志卷二十三《黄谷蛊毒》:“(蛊)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8](1761页)《乾州厅志》卷七:“苗妇能巫蛊杀人,……必密设一坛,以小瓦罐注水,养细虾数枚,或置暗室床下土中,或置山僻径石下。人得其瓦罐焚之,放蛊之人亦必死矣。”[9]近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十:“大约其用蛊,恒在冷茶冷汤中。”[10](493页)近人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闻有一蛊妇设坛在家,……烧温水为神沐浴,不意为小儿所见。翌日,妇上山工作,小儿仿效之,烧沸水为神偶沐浴,将蛊烫死。中有一偶即为蛊妇自己之魂所附。妇在山上工作,即已自觉,返家换衣后,即气绝身死。”[11]这几则都是说蛊怕高热,分明是承早期把热毒气叫蛊而来的异变。从“同性相斥”设计志怪情节,类似的“同性相斥”神秘文化个体又如:说人逢本命年必有灾;婚俗有同属相必相克的忌讳。甚至说,长于什么武器的人必死于持这种武器的敌人。“以毒攻毒”式的众多巫术都是此类。
飞蛊会发光。鲍照《苦热行》:“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文选》李善注:“行晖,行旅之光辉也。”实误,行旅的光辉是什么特别的光辉呢?它怎么能使人病呢?杨慎《丹铅录》:“南中畜蛊之家,蛊昏夜飞出饮水,光如曳彗。”黄节据此认为“李注非”。[12]《续禄劝县志》:“(云南禄劝县)土俗畜蛊,或鼠蛙之类,夜放晓收。其出入有金光。”[10](487页)清东轩主人辑《述异记》:“偶坐晚堂,见空中有流光如帚,似彗星之状。问之胥吏,云此名‘飞蛊’。乃蛇蛊也。”[10](488页)这又是另一种假中含真,透漏出把热毒气叫蛊的本源。因为热、火、光,是同一事理。
近人王世祯《中国民俗风情》:“篾片蛊的害人是将竹篾一片,长约四五寸,悄悄地把它放在路上,行人过之,篾跳上脚腿,痛得很厉害。久而久之,篾片又跳入膝盖去,由是脚小如鹤膝,其人不出四五年,便要一命呜呼了。石头蛊的害人是将石头一块,放在路上,结茅为记,但不要给他人知道。行人过之,石跳上人身或肚内,初则硬实,三四个月后,更能够行动、鸣啼,人渐大便秘结而瘦弱,又能飞入两手两脚,不出三四年,其人必死。泥鳅蛊的害人是煮泥鳅给人吃,食罢,肚内似有泥鳅三五个在走动,有时冲上喉头,有时走下肛门。如不知治,必死无疑。”[13]这种说法极为离奇古怪,绝对不是真实的,它的附会途径完全出人意料。所谓石头蛊是从牛黄、狗宝、淋石等“结石”生发的。《本草纲目·淋石》:“(藏器曰)此是患石淋人尿中出者,正如小石,收之为用。(时珍曰)此是淫欲之人,精气郁结,阴或煎熬,遂成坚质。”而“淫欲”就是《左传·昭公元年》:“近女室,生疾如蛊。”“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借此把结石与“蛊”附会在一起。动物和人体内的结石,也是一种“臌”或“痼”病,暗中谐音成“蛊”。泥鳅谐音“疑遒”:你应当对这个说法大加怀疑。这是一层。泥鳅也是鱼,谐音成“愚”:这种说法是在愚弄你呀,你相信了的话,就愚蠢太甚呀。所谓“篾片蛊”,是谐音“蔑、骗”。蔑:没有(此事),我是说假骗你呀。所谓篾片、石头“跳”到人身上,是谐音“调笑”的“调”:是开玩笑的话。所谓“结茅为记”,其中是谐音“冒”,指本是胡说乱说。这样解释岂不也是离奇古怪,有什么依据呢?依据就是志怪文学的规律。例如著名的“青蚨还钱”,有谁能证明青蚨是什么虫呢?它一名“鱼伯”,正是“愚百”或“愚伯”的谐音,你信了它,就是百倍的愚蠢,就是笨伯。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如果对神秘文化没有实质的研究,不知它的“趣假性”,自然会以为我的解释岂不是也离奇古怪。
三、“蛊”的语言文字解读
《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说“蛊”是会意字。皿,代表装谷物的器皿。虫,是其中的螟蛾。从“谷”再把“蛊”读成同音。这些都是合事理而平实的,但辞书还无如此简明的解释。
我国神秘趣味文化的一大特色,一种拿手好戏,就是利用语言文字手段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无作有、有作无,从而形成大背事理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形成莫名其妙的怪异性。志怪故事如此,“蛊”的志怪故事自然也如此,限于篇幅,仅辨析十一种具体情况。
(一)《左传·昭公元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曰蛊。”这个意思《国语·晋语八》是:“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三国吴国韦昭注:“皿,器也。为蛊作器而受也。”已经把“皿”解释成饲养蛊虫的器皿,可见当时已有这种志怪说法。南朝梁顾野王《舆地志》:“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食饮中,人不觉也。其家绝灭者,则飞游妄走,中之则毙。”[14]还都没有怎样饲养的说法。《隋书·地理志下》:“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相自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之以杀人。”[15]《本草纲目·蛊虫》:“造蛊者,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为蛊。故字从虫,从皿。皿,器也。”“(时珍曰)蛊毒不一,皆是变乱元气,多因饮食行之”[17](2371页)
这是虽神秘却无任何事理性的谎言。虫各有自己的食谱,不是凡比它弱小的都吃。虱能吃蛇吗?蛇可以吃许多种虫,但在一年内,只吃包括虱、蜥蜴、蜘蛛、蜣螂等99只虫,岂不饿死?无毒蛇即令吃许多毒虫,也不会变得有毒。毒蛇吃许多其他毒虫,也不会增加毒液。但谎言也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见缝插针的投机取巧。虫,繁体作蟲。所以“蛊”字本来作“蠱”。从“三虫”生发,从而傅会出百虫在皿中自相残啖,最后存活的自然最凶恶,就是蛊的说法。“蛊毒不一,皆是变乱元气”的解释也不确。虫各有各的元气,自相残杀而食,无所谓把其他动物的元气与自己的混杂。即令混杂,为什么就成为吃人的蛊呢?人吃许多动物,只是吸收营养,并不变乱元气。按那样解释,人岂不是都成了蛊?
《说文》:“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此释并不全面,疏忽了积谷生虫和热毒等本义。“腹中虫”也无文献根据。段注力辨此话非字面之义,而指由外到内的冲击祸害。“中、虫,皆读去声。《广韵》、《集韵》皆曰:虫,直众切。虫食物也。亦作蚛。腹中虫者,谓腹内虫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自内而蚀,故曰虫。此与虫部‘腹中长虫’、‘腹中短虫’读异。”[16]是说:虫是动词,义为“蚀”。
(二)秦德公时用涂狗血禁忌。对于神灵,是以三牲为祭;热毒是伤害性的,不是敬祀,而是祈禁它的危害。敬的形式,禁的内容。“狗”是谐音为“苟”,指热毒伤人为“苟”。热与狗没有关系,但经过“苟”的事理中介,有了“热——苟——狗”的联系。把“苟”的事理隐蔽,就是“热——狗”的志怪性联系。《搜神记》:“潘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蛊有怪物……或为狗豕。”神异的“狗”,传示的实际是“热——苟”的事理。
梁陶宏景《神农本草经》:“近城市人以空罂塞口,纳粪中,积年得汁,甚黑而苦,名曰黄龙汤。治温病垂死者,皆瘥。”[17](2939页)温病就是热病。《本草纲目》言黄龙汤治“蛊毒百毒”承此。而《述异记》“中斯(按,即蛊)毒者,唯自投粪窖中,稍或可解”便是趣假说法。按,“黄龙”谐音“黄弄”:是黄色的大便弄成的。《本草纲目·狗》:“俗又讳之以龙,称狗有乌龙、白马之号。”仿“乌龙”而故意把“黄龙”别解成指黄狗。黄龙治蛊,实际是说“黄狗治蛊”,仍然是“热——狗”的假事理。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猪亦可放(指用猪变蛊),狗则不能。故蛊妇怕狗,不吃狗肉。[11]”其实也是从同性相斥而趣说的。
(三)《黄谷蛊毒》等说:蛊吃人五脏。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不一。这种附会的机缘是《周礼·剪氏》“剪氏掌除蠹物”的郑氏注:“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虫鱼亦是也。”其中的“穿食人器物”本是说蠹鱼这种蛊虫打洞蛀蚀人的器物。“食”通“蚀”。“人”是“器物”的定语。好事者卖弄聪明,把“穿”字移到后面,变成“食人器物而穿”,“食人器物”意思变成蛊虫吃人的五脏,“穿”成为指再“穿透出来”的“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不一”。
(四)《搜神记》说中蛊毒的症状是“吐血几死”。唐《朝野佥载》:“江岭之间有飞蛊,……中人即为痢,便血。”[18](1685页)中暑会有恶心、吐泻。把“吐泻”谐音成“吐血”,或把“泻”换成复说的“便泻”,再谐音成“便血”。
(五)《新唐书·方技·甑立言》:“诊曰:‘腹有蛊,误食头发而然。’令饵雄黄一剂,少选,吐一蛇如拇,无目,烧之有发气,乃愈。”[19]《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尝中蛊……夜又梦吐大蚓为一肘(按,肘是印度量词,一肘是横列二十四指宽的长度)。”[20]
治疗吞下头发就应当使头发吐出。变说成:头发在腹内变成如蛇的蛊,打出来的蛊就是蛇或蚯蚓。其实是从人吐出蛔虫来附会的,而这又是从《后汉书·华佗传》仿来的。“佗闻其呻吟,驱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醋,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见佗北壁县此蛇辈约以十数。”[21]所说的“蛇”不是字面意思,而是从蛇的俗名“长虫”,指很长的虫,即蛔虫。《说文》:“蛇:虫也。从虫而长。”但“长虫”作专名才是蛇,作一般说法是长的虫。《后汉书·华佗传》使用了语文的歧义手段,把一般的说法故意别解成专名,来誉说华佗的医术。这是方技书的说法。
(六)唐刘恂《岭表异录》卷二:“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胪胀成蛊。”[22]《夷坚志》三志壬卷第二《聂伯茂钱鸽》:“临川聂伯茂,……病腹下气蛊,病块如覆盆。积日不差,仅年余而卒。”又同书丙志第八《顶山回客》:“忽得蛊病,水浮肤革间。……问之曰:‘病几何时矣?此乃水肿,吾有药能疗。’……应手水流,溢于塌下,宿肿即消。”[8](434页)这些故事中的“蛊”实际是“臌”字的谐音,指体有肿块或浮肿鼓起。用“蛊”字是受了神秘的“蛊”字的影响。但对病的原因和症状没有被人放蛊暗害的说法。
(七)《夷坚志》丁志卷一《挑气法》:“从事郎陈遹力为德庆府理官,鞠一巫师狱。巫善挑气。其始与人有仇隙,欲加害,则中夜扣门呼之,俟其在内答应,语言相闻,乃以气挑过。是人腹痛肚渐胀,日久,腹皮薄如纸,窥见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结,药不可治。狱未成而死……。此妖术盖有数种。或咒人使腹中生鳖者。或削树皮咒之,候树复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8](543页),“挑气”的意思不易明白。从具体情况分析,是如下的曲折:过——迈——卖——粜——挑。过,是把气吹过去。得传染病,方言也叫“过病”。把“过”换为同义的“迈”,又换为同音的“卖”,又换为口语同义的“粜”,又换为同音的“挑”。这种多次曲折转换的表述,唐代专门叫“三折语”。呼名而答应便得病,又是利用神秘文化的名字崇拜。从受气得病来说,如中医所言,“郁气得鼓胀病”,即又是“鼓、蛊”的谐音。而“使人腹中生鳖者”,“鳖”实际是“憋”的谐音作假。削树皮为蛊,又是“皮、痞”的谐音作假。憋、鼓、痞,同指腹内肿块。
(八)前引《乾州厅志》说苗妇“养细虾数枚”来制造蛊。腹中结块而不外显的病,中医叫“瘕”。谐音假说为用虾制蛊。
(九)敦煌文献伯二六三七《出蛊毒方》:“豆豉七粒,黄龙一分,乌龙肝一分。右件药物细研为末,都为一服,空腹下。”神秘文化给豆类赋予许多的药效都是虚假的。如《五行书》:“正月朔旦及十五日,以赤小豆二七枚、麻子七枚,投井中,辟瘟疫甚效。又正月七日,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吞七颗,女吞二七枚,竟年无病。”[17](1510页)实际是以“豆”谐音“斗”:和病魔相斗。《三遂平妖传》说有“点豆成兵”的妖术,同一机杼。宋姚宽《西溪丛语》:“如中毒者,先以白矾末令尝,不觉味苦,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23]检验是否中毒,不腥就是无豆腥气。神秘的设计是:“斗”性(腥、性谐音)都用在与蛊斗争上了,所以不觉豆腥气,即意味着中毒。特说赤小豆、黑豆、绿豆,是再作神秘。敦煌文献中的“乌龙肝”就是狗肝,而“肝”谐音“干”,指旱,又与热毒一致。
(十)《搜神记》说:“累世为蛊,以此致富。”不言怎样致富。《隋书·地理志》言:“死则其财产移入蛊主之家。”又不说怎样移入。《黄谷蛊毒》:“(被害者)人魂为虫祟所拘,不能托化,翻受驱役于蛊家,如虎使伥然。”《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桃生蛊毒》:“相传人死,阴役于其家。”[24]《汀州府志》:“死后魂灵为之力作,坐是致富。”[10](482页)原来是被害死的人的魂灵给施蛊者干活,使得他富裕。但是,这个解释绝对说不通。所以还必须探究真正的傅会原由。把《左传》“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节缩为“淫生蛊”,却别解成:淫由于蛊而生。把“淫”换为谐音的“银”,成为银生于蛊,即蛊产生银子。这就是神秘莫测的养蛊致富。
蛊的一种叫“金蚕”。《本草纲目·金蚕》:“陈藏器云:故锦灰疗食锦虫蛊毒。注云:虫屈曲如指环,食故绯帛锦,如蚕之食桑叶也。今考之,此虫即金蚕也。”[17](2371页)说的就是蛀虫。但它不是只吃锦,布、毛毡、木头也吃。所以吃锦是遮掩说法,是“持金”的谐音,指进财而富。进财即“进产”,谐音为“金蚕”。全是玩弄文字游戏。蛀虫也是高温时为盛的,仍然透漏出“蛊”的本源。
《铁围山丛谈》:“金蚕始于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状如蚕,金色,日食蜀锦四寸。南人畜之,取其粪置饮食以毒人,人即死也。蚕得所欲,日置他财,使人富贵。然遣之极难,水火兵刃所不能加害。必倍其所致金银锦物,置蚕于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蚕随以往,谓之嫁金蚕。”[25]它既然使人富贵,为什么又要送走它?《汀州府志》:“大凡蓄蛊之家,久必为祸,须以银物伴送密封,或置道旁,谓之嫁金蚕。”[10](482页)然而,既知道久必为祸,还要倒贴一倍嫁它,又为什么养它?应是“假金蚕”的谐音谜底。实际是隐约告诉人:所谓金蚕蛊等等说法都是虚假骗人的。这与前面所解释的“泥鳅”、“篾片蛊”等是一致的。
袁枚《子不语》卷十四《蛊》:“云南人家家畜蛊。蛊能粪金银以获利。食男子者粪金,食女子者粪银。此云南总兵华封为余言之。”蛊在外吃人,回家排粪为金,只能是袁枚的巧思。他利用民“梦见粪主进财”的说法(这是因为“粪”谐音“丰”,指钱多了)。又利用道教把侍奉神仙的童男童女叫“金童玉女”,而说“食男子者粪金,食女子者粪银”。
(十一)《粤东笔记》:“粤东之贾往赘西粤土州之妇人,寡者曰‘鬼妻’,人弗取也。贾欲归则必与要约。三年返,则其妇下三年之蛊;五年,则下五年之蛊。谓之定年药。愆期,则蛊发膨胀而死;如期返,其妇以药解之,辄得无恙。……以蛊留人,人亦以蛊而留。”[10](485页)《滇南新语》所言相同,但成了蜀地的情况,显然是变换地点的抄袭:“蜀中多畜蛊……又山中摆夷,剥全牛,能咒其皮如芥子。货客入山,不戒,或为夷女所悦,当货毕言归,则私投饮食以食客,女约来期。如约至,乃得解;逾期,则蛊作腹裂,皮出如新剥者。更闻元郡江(按,无‘元郡江’地名。‘郡’字当衍,元江在云南省)外,以木易腿;索财既足,始复其胫。否则,木脱夔立矣(按,用‘夔一足’的典故)。其害亚于蛊。安能得此辈而尽律以大辟。边荒妖毒,庶其息乎。遗孽为害之说,余殊不敢信。”[10](487页)
汉人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商,与妇女情爱,回归时约期再来而未。好事者做趣假之谈,利用了“贾(gu指商人)约”、“辜约”与“蛊药”,“负约”、“妇约”与“妇药”等的谐音(药指以蛊为毒药)。至于把牛皮用咒语变为芥子大的毒药,却是“牛皮”与“扭脾”的谐音。指扭转他的心性,让他回来。“脾”是“脾性”的简说。说他若转心即变心不回来,“蛊药”就发作,实际就是说他“辜约”了而已。而对客商索财不足,就用木头换他的腿,由于未交代具体情况,难以考虑神秘化的途径。但木腿与木偶仍然有关联。《滇南新语》的作者说他要把用蛊的人处以死刑,是相信实有那样的蛊,但这是假话。又说他“殊不敢信”所说的蛊,这才是真话。他正是要从编造的离奇古怪的蛊来让人醒悟:蛊是编造的趣味故事。
四、“蛊”的文学解读
从整体来说,志怪的蛊就是对实有的热毒的蛊的特种文学说法,有如“哈哈镜”中的人像,有真、假、怪的特点。真,是客观的实体,即反映热毒,以它为题材。假,是手段。怪,是艺术目的或主题,也就是志怪的另名“齐谐”的“谐”:诙谐、智趣。我们应当准确把握这些特色。不知这些,就把它既看成巫术,又看成医学档案,相信并再次宣传确实有巫术可以培育蛊虫来损人利己。因此,前文所说的那些从字的形音义生发的趣假,实际也还是文学手段。
《搜神记》故事中的儿媳不知家中养蛊而把蛊蛇烫死,“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这是“恶有恶报”的文学主题,志怪小说中多见。蛊家妻女被蛊淫,包含两层事理。浅层也是恶有恶报。深层是《左传》“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的断章取义,仅截取“淫内蛊惑”而作生发。最初当是骂蛊家妻女乱辈分而淫,后来变为与蛊虫为淫。
志怪作品有一种笔法:设置疑兵。即有意提供与主旨事理无关的内容,干扰读者的正确思路,如前面说到的,本只是用“豆”谐音“斗”,却说成黑豆、绿豆、赤小豆。
志怪小说的“怪”不是目的,“怪”与“谐”的统一才是目的,即要有智趣性。《夷坚志》补志卷二三《黄谷蛊毒》:“(蛊)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远者一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遐恤亲戚宗党,必施之。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或无外人至,则推本家一人承之。……(养蛊家)有五色线、杯珓及小木棋子,两面书‘五逆五顺’四字。……所谓顺逆棋子,降蛊之时所用以卜也。得顺者客当之,逆者家当之。”[8](1761页)原来是说让百虫残杀留一个,变为迎接雌雄两个来家交配。但这雌雄两个又是从何而来的什么虫呢?什么虫交配的淫液有毒呢?此毒的正常用处是什么?都是没有丝毫寓含的。先说当日无客来,便对本家人用蛊,后说用卜决定对客还是对本家人用蛊。先说蛊数月或一年交配一次,后说淫液当日有效。如此又怎能经常害人?都是自相矛盾。如儿子结婚分居,来客是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已婚的儿女,也向他们投毒?如无客来,对本家人用蛊不外是对这些人投毒,他们会服从吗?这些说法够奇怪了,但是不负载意义,为怪而怪,没有文学性。可以说是志怪作品中的败笔,这可与前面说的文学性对比。
《太平广记》:“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由是成疾。……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绐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18](1676页)这也是杯弓蛇影类型。中医叫气臌,并未吐虾蟆而骗说吐了,即心病还得心来医。此例充分说明所有吐出某种动物的说法,都是子虚乌有。这是以蛊的同样题材,却达到说明没有蛊的独特主题,也可以对比而领会此类作品的文学性。
五、“蛊”的迷信解读
这指的是与本原的热毒没有关系,也无其他积极寓含,纯粹是借神秘的蛊来宣传迷信的内容。《搜神后记》的昙游道人,念咒就能使隐藏的长丈余双蜈蚣蛊虫显形而逃走,并饱食蛊虫曾在内的饭食而安然无恙。就是宣扬宗教咒语的法力。
《夷坚志》丁志卷一《治挑生法》:“与药服之,食顷,吐积肉一块。剖开,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鸡形,头尾嘴翅悉肖似。”[8](541页)中蛊毒使腹内有积肉不化,治疗使吐出来。把膜包的积肉剖开,其中有已成形的小鸡,离奇之至。这是对下面一种说法的移植:迷信说吃肉而杀生的一种报应,是吃什么就在腹内变为什么,它也要害你的命。《黄谷蛊毒》所说:“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鱼鳔之类,乃是恶物。”从吐鱼变为吐鱼鳔。再《夷坚志》丁志卷一《治挑生法》:“识者云:‘此中挑生毒也。’……果然,……泻出生葱数茎,根须皆具。肿即消。”是掐头留尾的说法,隐蔽了吃葱的原因。是宣传不吃荤的泛化,因葱也是荤菜。
本文研究的结论是:神秘化的蛊都是虚假的,是对热毒、痼、臌、瘕、痞、症、郁、憋等症状的趣味说法。神秘化的蛊是志怪小说的产物。志怪者,齐谐也。谐,即隐曲、诙谐、趣巧、奥秘。手段有:泛化、异化、双关、歧解、张冠李戴、断章取义、拆字、谐音等等。众多的说法组成蛊的网络体系(它的底层是不神秘的早期的蛊和相关内容)。简单地说,它们是骗人的;深刻地说,是特种诙谐趣味文学。
西方的四月一日是愚人节,又叫万愚节。人们以各种方式做愚弄人的游戏,即说假话开玩笑。蛊的以及其他的许多志怪故事,就是我们祖先千多年前愚弄人的文字游戏。西方愚弄人的游戏即时而过,我国的志怪小说,许多却是文学名篇。那些荒诞的说法,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与读者作玩捉迷藏的斗智。可惜一些研究者不知奥妙,被蛊牵着鼻子走,既使文学价值不得彰显,又促助迷信宣传。这是研究的空白和失误,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如此。这倒如俗语所说“张公吃酒李公醉”、“当事者清,旁观者迷”。
著名民俗学家马连良先生在《倮族的招魂与放蛊》一文中说:“如放蛊人之说,西南苗夷区中,皆有此说,但我历年居苗夷区,何未之见,仅闻某某人中蛊因而昏狂,或残废死亡。”[10](495页)这是难得的如实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