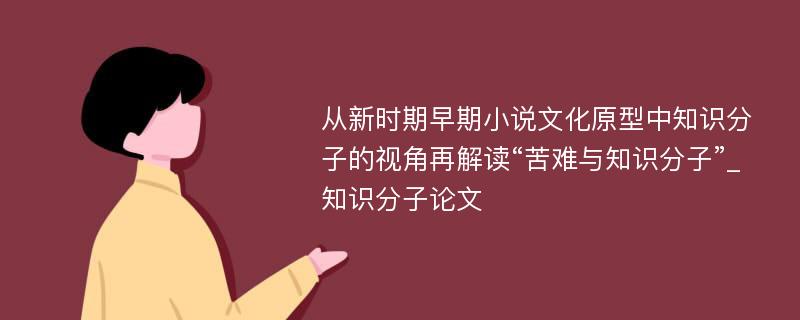
“苦难与知识分子”的再解读——“新时期”初期“文革”小说文化原型的知识分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原型论文,新时期论文,文革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建国后的30年历史中,“知识分子”一直是个辛酸的话题。“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烙 印”这一概念,将知识分子几无例外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原罪”标志,可叹的是知识 者自身也往往怀着赎罪心理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一局面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 结束。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代表执政党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和工人阶级一样只是分工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这一 政策的转变,带动了全社会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重新认识和估价,长期处于贱民地位 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获得了表达和宣泄的空前契机,对自身意义与归属的寻求也 成为他们对文革历史进行反思的一个伴生主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50年代沉入社会 底层的王蒙、张贤亮、丛维熙等一批右派作家的作品显示出独步一时的思想力度和情感 强度。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文学最早从知识分子视角所展开的叙事。
所谓“视角”即叙事者在故事讲述中所站的位置,它对故事的讲述、意义的产生起着 一个中心调节的作用,所以叙述学者布斯说,视角的选择,“是一个道德选择,而不只 是决定故事的技巧角度”。[1](P135)建国初期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作品难以被视 为知识分子视角,只能说是知识分子题材。而“新时期”初这批右派作家的反思小说才 是当代文学知识分子视角的开端。如今,重读80年代这些反思题材作品,不仅可以寻找 “知识分子视角”的“原初”形态,还可以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情感模式和文化原型的发 掘,发现一个民族的苦难在当时是如何被表现出来,并深深感动了众多读者的;同时也 会发现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知识分子与历史的互动,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主体” 局限下艰涩地实现的。
一、忠诚信念与权力话语
“新时期”文学是以《班主任》、《伤痕》等一批“伤痕文学”为其先导的,但很快 ,随着大量右派被平反,一批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重返文坛,形成了从知识分子角度 批判和反思“文革”、“反右”等历史的“反思文学”。在新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作品 揭露自身“缺陷”、“伤疤”而能获得上下一致好评的,而右派作家的反思小说却没有 遭遇这样的厄运。究其原因,应该说和这些作品所基于的叙事模式密切相关。这些作品 ,往往从“党”、“人民”、“祖国”等价值理念中获取思想资源,所有的苦难倾诉、 社会批判都是以对党、人民、祖国的价值皈依为前提。当然这种情形在不同的作家作品 那里有不同的侧重和差异,但其结构模式和主要功能是相同的。
王蒙兼有干部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他的作品大多表达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对党、对信 仰的执着无悔和忠诚信念,表现了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执着情怀。一方面,作者 对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精神扭曲与异化的揭示是深刻的。如《布礼》的主人公钟亦 诚因一首小诗获罪,在不断上纲上线的群众批判和领导教育的强大攻势下,自己也对自 己的“罪恶用心”感到厌恶,外在的批判慢慢变成自我内化的罪感。所以,在“文革” 中,不管是被红卫兵用皮带、链条毒打,还是惩罚性的劳动改造,他都以感激的心态接 受和顺从,真诚地以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灵魂,以赎罪的狂热去拼命劳动和感谢党的挽 救。就连外在的气质容貌也因长期的罪感民谦卑的表情和诚惶诚恐的语调,当年那个单 纯热情、迷恋诗歌的钟亦诚早已无影无踪。但在总体叙事上,作者把人物的身份定位为 革命机器的螺丝钉,所以那些饱受肉体磨难和精神侮辱、有过消沉与迷惘的主人公们, 往往把冤屈当作考验,把苦难当作修炼,始终不放弃神圣的信念和对这一信念的忠诚。 作者还把这一信念给予一般化,使得主人公在平反之后满怀感激的如下话语,显得真切 感人:“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 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 这海填平。”这种宗教般的虔诚使得加在人物身心上的一切苦难和屈辱蒙上了圣洁和崇 高的光环,在回溯荒谬历史的同时,也建构了知识分子苦难而光荣的历史形象,从而为 受害者在新的政治时期重新定位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在丛维熙的作品中,忠诚与信念的依托则是“祖国”。其代表作《雪落黄河静无声》 ,便是表达这一信念的典型文本。主人公范汉儒从一个知识者被打成右派成为一个“鸡 倌儿”(养鸡),流放劳改20多年,但他始终乐观、正直,甚至没有怨言和痛苦。在饥荒 年代,他以一颗单纯、诚实的心维护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宁可煮菜帮子吃,也不动农场 一个鸡蛋,连从老鼠洞里掏出的四个鸡蛋也如数交公。而劳改农场场长“黑妖期”则把 自家的十个鸡蛋送给右派范汉儒,说“我没给孩子,没给老婆,给你拿来是看你还有中 国人的骨头:将来政策松动一点,你还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这个日常的感人细节配 上不无做作的解说(通过人物语言),显示了作者刻意把政治受害者转换成社会精英来歌 颂和赞美的叙事意图,它们的潜在逻辑是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寄托在一批民族之魂身上, 随着那段“非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结束,被错误地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受到国 家的重视和社会的亲睐。这里,爱国的主题又自然转换为权力话语,使知识分子历史形 象的重塑和现实社会地位的再造获得极大的有效性。正如有评论者所深刻指出的:“有 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 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对党保持忠诚,对革命事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通过这种重述 ,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例如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使拨乱反正后重返现 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2](P10-11)
相应地,创作主体的这种忠诚信念也直接左右了一些作品的情节设计和意象营造。如 《杂色》中,流放新疆农村的音乐家曹千里尽管似老马般饱受践踏和蹂躏,在面对雪山 、草地和蓝天时却突然间产生了奇妙的内心变化:为自己不是蜘蛛、蚂蚁、老鼠而是一 个人,一个有幸来到20世纪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前面的叙事显然难以归结为一个堂堂 正正的人)而感谢生活,进而把自己幻化成骑着龙种骏马、飞奔向前的骑手而放声歌唱 。这种主观理念的强行介入显然是叙事者的意图暴力,它与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正常心理 逻辑难以统一。《灵与肉》中的许灵均也有同样的情绪转化:劳教结束后因无家可归留 在农场放马,这原本凄凉、孤寂的生活,却被描写成充满诗意的美妙体验:“他骑在马 上,拿着长鞭,迎着雨头风,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在马群周围奔驰,呵斥和指挥离 群的马儿。于是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 和风、和雨、和集合起来的蚊蚋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雄壮美丽的 大自然对漂泊心灵的抚慰又很快放大为热爱祖国的宏大主题,因而“他感到了满足:生 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上得不到的东西。”这样的转化 不仅过滤掉了苦涩的正常心理体验,而且还令人不觉地回避了现实政治的残酷性。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蒙等作家对民族磨难的体验与反思是真挚而深沉的 ,但在整个时代的集体主义信念和历史线性进步的精神氛围中,作家们仍然难以把个体 的生存经验和理性思考提升到独立的个体意识,他们依然要把知识分子的思考自觉或不 自觉地依附于国家意识形态,因此知识分子尽管受磨难但却仍然强调他们忠诚与无悔的 信念。这看来并不是虚伪的,却并非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错觉。
二、母与子的叙事模式
忠诚无悔的表层叙事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学模式,其逻辑前提是把个人与执政党的 关系设定为母子般的伦理关系。如《布礼》中的凌雪所言:“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 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消了,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大震动,然后你会更好 地改造自己……”所以不仅钟亦诚们的痛苦、屈辱应该无怨无悔,而且对“母亲”也不 应在任何角度和层次上予以怀疑。虽然,这是人物的心理独白,不能完全等同创作者的 思想情感,但从作品的倾向性来看,作家对笔下人物是持认同姿态的。我们没有理由怀 疑作者情感的真诚,但这种缺乏理性反思的情感真诚不仅无益于整体的自身肌体更新[3 ](P80),而且离知识分子标榜的思想先锋和批判职能更是相差甚远。如果说钟亦诚们年 轻时的选择包含着年轻人的激情和时代的必然,那么他们以后的思想则一直停留在年轻 时代,而没有与年龄、经验一起成长,理性的独立人格始终没有出现,“膜拜的过程便 是放弃自己思想的过程”。[4](P70)
“母与子”的结构模式在张贤亮笔下有所不同,他更多的是把自然、劳动者、人民这 些更容易为知识分子接受和认同的集体概念,作为化解政治带来的身心创伤的良药。《 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中的底层劳动者,都是受难中的知识分子的接纳者与拯救 者,他们以母亲般的胸怀与纯厚无私抚慰着这些政治罹难者的疲惫肌体和创伤心灵。《 灵与肉》中有这样一个叙事上的详略之别,即在叙述主人公许灵均被父亲抛弃和母亲病 死的“旧社会”经历时,包括细节在内的“描写”直观而具体;转入“新社会”的叙事 时,便只剩下——是“党”、“新社会”收留、培养了他,并成为他的再造父母——一 笔带过的抽象叙述。这种详略之别体现了作者的叙事困境,但也呈现了这样的内在逻辑 :“血缘父亲”与“象征父亲”具有相同的结构,并在鲜明的对比中形成了一种隐喻关 系。这与《布礼》中的“母与子”情感模式是完全一致的。“人民”在这里也似乎是具 体的、活生生的个人,然而无论是勤劳、乐观的李秀芝,美丽、纯情的马缨花,憨厚、 内向的海喜喜,善良、热心的郭扁子、满口脏话但质朴仁厚的谢队长等,都是在劳动者 高贵、知识者卑下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即把以土地和劳动为生活方式的农 民和以思考和智力为生活方式的知识者在体力劳动中进行对照,以显出劳动者的质朴、 勤劳、达观等品质和知识分子的柔弱、无力、卑下等劣质。在这样的道德对比中,就把 造成农民贫困、粗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原因轻轻放过了,这使得 这些作品虽不乏动人之处,但仍脱不出苦难倾诉和忠诚告白的模式,是知识分子自怜自 恋而又自虐式的潜意识流露。同时,作品中表达的对“土地”、“人民”、“祖国”的 情感认同,以及对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发自内心的欢欣,在批判反右和文革对 知识者的打击和迫害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认同了用来贬低、打击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和 道德偏见,即拿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认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 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5]在这一过程中 ,这种为扼杀知识分子思想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点,也会被知识分子内化为自身的一种 受虐的心理需要。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就反复表达改造后的欢欣,显示出如帕斯捷尔纳 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所指出的一匹马是如何被驯服的真相。[6](P576)帕迪说:“一 个被剥夺了自由思考的心智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的”。[7](P52)相应地,知识分子精神自 主性的缺失正与专制主义的通行互为因果。
在《雪》中,母与子的情感模式更带有压迫性的封建话语色彩。范汉儒在“我承受的 灾难再大,也不能做一个黄河的不肖子孙”的信念支撑下,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没有沉 沦,而且这种祖国至上的信念还深入到他的情感生活。他选择爱人的标准就是:“别的 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于祖国,它对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她不能有一次不忠。” 所以经历无数磨难和近20年的等待,并为了爱情放而弃回城的范汉儒,在即将结婚之际 ,得知爱人陶滢滢当年被划为右派时曾试图逃离国境被抓回的“污点”后,竟残忍地离 开了她,放弃了这份苦难中得之不易的情感。他提供的理由是:“一个炎黄儿女最大的 贞操,莫过于对祖国的忠诚。”作者虽然一直正面地描写着这个人物,但却无意识间泄 露了忠诚理念与封建意识的血缘关系。毫无疑问,这种有着强烈的封建话语色彩的忠贞 理念,已经成为当事者有悖常理与人性的准宗教,进而也使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范汉儒心 仪的从来就不是平等意义上的真正爱情。
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文革”叙事中“子不嫌母丑”式的情感认同 模式,使得写作者不无炫耀地沉溺于自我的苦难倾诉,表现出一种美化苦难的畸变心态 ,因而也就排除了对民族灾难和人民困苦进行更深层次思索的可能性。
三、文化原型与政治规训
知识分子苦难叙事模式的另一潜层内涵则是“家与狗”的民间道德,其逻辑演绎就是 主与奴、施恩与报恩、主宰与服从。显然,母子从属关系已不只是伦理情感的层次,而 是传统中国社会政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土壤。其实,古人早有质疑儒家的专制等级秩序 的异言,《后汉书·孔融传》提到孔融的悖逆之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 ,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又言“若遭饥馑, 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8]孔融并非真的对父母无情无义,而是借此表达对等级专 制的封建社会结构的不满。所以作为一个奴性文化传统的怀疑者,孔融受到呼唤平等和 独立人格的鲁迅的大力推崇。鲁迅曾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说过,汉末的孔府,很 出了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样没落。[9](P40)鲁迅所指的奇人之中,首屈一指 的是孔融。鲁迅本人更是直接表达西方现代平等伦理观,以期待和呼唤平等的人格和民 主的社会。五四时期,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追随者大都是以个人的觉醒成长作为 民族强大的基础和前提,抨击以子女对父母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政治结构,并 以家庭伦理观念的变革作为新的社会政治理念的象喻,反对一切压迫性的政治观念和社 会观念。但这种文化原型和伦理情感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延续,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意识 深处依然有着深深的烙印。
这当然与知识分子的现实社会定位不无关系。知识者的价值往往搭载于其他阶级、阶 层之中,或者说以归属于某种社会力量而显示自身的价值。“知识分子总是渴望奉献, 而其奉献对象就是某种意识形态。所以几乎所有的现代知识分子都在寻找他们可以为之 奉献的意识形态”。[10](P47)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往往以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为自 己的价值依托和归属,如五四时期的平民思想、劳工神圣,30年代的大众观念,40年代 的人民至上,等等。闻一多为纪念五四26周年撰写的文章《人民的世纪》中大胆地质问 :“叫人民献出一切,缩紧腰带,拼了老命,捍卫了国家,自己却一无所得,这难道叫 人民的世纪吗?”[11](P26)这里,“人民”和“国家”显然是分离甚至对立的,当时的 “人民”提法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批判动机和效果。但后来社会的巨大变迁,不仅给人们 带来了“站起来了”的新生感和自豪感,也带来了对来自传统士大夫和民间的那种“父 子”、“母子”文化的潜在继承和意识形态改造。这使得业已经过“现代”洗礼的知识 分子,在对“进步”、“先进”的追求中,不自觉地丧失了本应有的主体性。这一文化 隐喻的转换过程,其实也是规训和自我规训的实现过程。
母与子的情感认同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普遍状况。这既是中国士大夫文 化的传统积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极力塑造的结果。可在当时,这又是那个历史转折时 期知识分子在一个乐观的历史前景的设定上,自觉、主动地与国家意识形态呼应一致的 体现。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最初几年,上述几个整体性概念,成为知识分子在政治磨 难和精神规训中所能寻找到的合法有效的政治批判资源,对它们的理想化的理解与信仰 也是对文革极端荒谬的政治面貌的映照,只不过,在发挥这种批判功用的同时,也陷入 了批判对象自身的逻辑陷阱之中。
收稿日期:2004-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