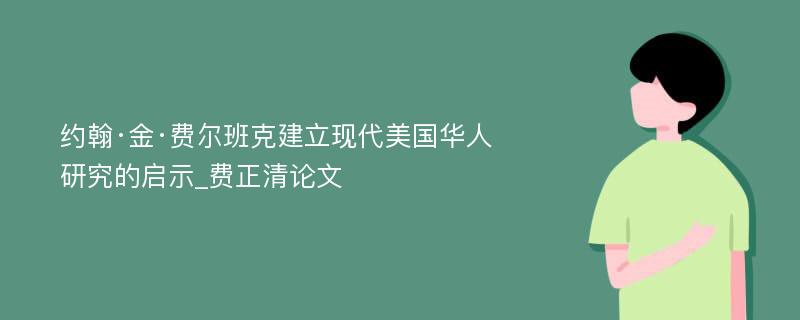
费正清创建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中论文,国学论文,启示论文,费正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二战前的一门不显眼的学科,发展为今日的一门显学,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费正清在创建美国中国学过程中所阐述的学术思想,对现今学术界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传统与困境:早期的美国中国研究
自19世纪末起,以法、荷、德为主的西方学者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入手, 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将兰克( Leopoldvon Ranke)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和中国的考据学巧妙地结合起来, 形成了汉学研究体系。20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聘请一些欧洲的著名汉学家如劳费尔(K.B.Laufer)、夏德(F.Hirth )和伯希和(PaulPeliot)等到美国讲学,所以美国早期中国研究受欧洲影响很大。他们翻译和整理了大量的中国经典文献,为后继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者提供了一条捷径;他们从语言学和社会学切入中国问题,所涉及的课题带有跨学科的性质,为日后中国研究中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树立了典范和积累了经验。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精神,终于在70年代以后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时候显示出能量和效力。
但是,美国早期汉学家基本上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课题过于专门化,在短期内很难看到社会价值。而且,他们漠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甚至鄙视对中国现实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研究中国1796 年以后的事件,
算不上历史学,只能算是新闻工作(注:Theodore H.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New York:Harper & Row,1978,pp.49—51.)。
由于美国早期的汉学界只跟在欧洲的后面亦步亦趋,结果是美国的中国学得不到发展,研究水平在一定时期内也不可能有所提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不足50人,没有一个专业的学会,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没有相互间的交流,更没有学者间研究课题上的合作。
学术研究的低迷,也影响了美国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对远东的政策。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的远东政策都无法取得最后的成功,这与美国在东亚和中国的学术研究上力量薄弱是有关系的。费正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发出警告:“这个国家(美国)面临着在亚洲摊牌的局面,处于全然无知之中的美国人必须系统地提出一个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民主政治需要建立在人民理解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我们在亚洲政策方面的无知和惨败可能是我们民主政治的终结。”(注:费正清:《远东危机和美国的教育》,《美国远东评论》第11卷(1941年6月)。)
他很明确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与国家的需要相吻合,外交政策也需要学术研究来探明方向,制定正确的远东政策的前提是对远东和中国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把这种信息传达给美国的公众。(注:费正清:《远东研究和美国教育的贡献》,《学校生活》第27辑(1940年11月)。)这正是费正清与美国传统汉学之间的分水岭。
二、美国中国学的功能:教育公众和影响政策
费正清认为,“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这便是他创建中国学的宗旨。
在教育美国公众方面。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是代表作。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他任驻华大使特别助理期间,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期望很高。费正清却发现国民政府“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的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但那时美国了解中国的人实在太少了。在费正清离开中国的那段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全力扶持蒋介石政权。1945年10月费正清再度以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身份来华时,目睹了战后国民党腐败的愈演愈烈和上层阶级对国民党的离心离德,因而对美国所实行的对华政策深感忧虑。他指出,美国在中国面临着两难选择:“革命将危及我们的自由主义的利益,然而反动更是现时就破坏这种利益……我们似乎宁要反动的种种罪恶,而不要革命的种种未知的危险”,但“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革命,那么我们终将发现自己将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注: Fairbank:"1946:Our Chance in China",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1946.)可悲的是,美国政府只依照自己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国,根本不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为了使公众了解中国的变化,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什么问题,费正清致力于《美国与中国》的写作。
此书于1948年首版,至1989年已出了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它不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详实,中心是让读者明白国民党为什么必将失去中国。这正符合美国公众的需要。因此该书甫一出版,费正清名声大噪。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方面起过更大的作用和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尼克松总统在为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作准备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参考书。费正清这本书和其他一些著作,许多论者往往以学术性不强予以贬斥。但费正清却认为:“根据我的经验,‘拾人牙慧’的历史学家影响更持久些。这样的学者说话、写作旁征博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正是使我们名垂千古的秘诀。”(注:柯文、戈德曼:《纪念费正清》,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在以研究影响政策方面,他大胆地提出的独特见解,是建立在对中国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证明其很多看法是正确的。
二战刚结束,他就从中国的政治现状出发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要不要做好迟早同中国共产主义妥协的准备?在中国,有哪些机会能使条件令人满意?在危机时代,中共会不会同俄国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清醒地和客观地估计我们的机会,必须懂得,极端的回答虽然来得痛快,却是于事无补的。 ”(注:《费正清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他不同意西方分析家轻率地将中共称为“莫斯科的傀儡和工具”,认为中共“20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对付中国的环境,历尽艰辛,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计划。华北不等于东欧。”“我们必须把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看作是民族自决问题,而不是外来侵略问题”(注:Fairbank:"1946:Our Chance in China".)。
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费正清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但他并没有因这种冲击而改变初衷,相反,他认为,“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丢失中国’的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注:《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在相对沉寂了十年以后,1966年他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将自己的新思考公布于世。他赞同知名中国学家鲍大可(Daok Barnett)所提出的改变“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主张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认为,“孤立北京只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遏制的目的也仅仅在于遏制,而不是进行恐吓,制造混乱,更不是进行挑衅”。他还主张采取迂回的方式逐步改善对华关系,允许和吸收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甚至联合国,为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打开方便之门(注:Fairbank,"New Thinking about China",Atlantic Monthly,June,1966.)。
美国的右翼政客把费正清看作是“共产党的辩护士”,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台湾当局则多次掀起了对费正清批判的浪潮。其实,此时费正清也受到中国共产党颇多微辞,当费正清在美国接受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出席一次又一次的听证会的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展了对费正清的批判,指责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正在变本加厉地歪曲中国近代史”(注:参见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5页。)。
费正清处于四面受指责的境地,但正是这种境况,证明了他不是哪一种政治力量的吹鼓手。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走向有幸都被他言中,也为费正清的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了一个注解,即学术不是简单地为某种政治力量寻找合理的理论依据,而是站在学者独立的立场上,阐述和破解社会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向,对政治的发展起引导的作用。费正清创建美国中国学的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美国中国学的架构:以历史学为主干的综合研究
美国中国学是一门以历史研究为主干,结合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
把历史学作为主干,部分原因是费正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情感归宿在历史学。他认为,“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历史没有充分的知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因为中国是一个与西方差异极大的社会,要了解它的特殊性,只有从中国的历史出发。许多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是从西方的理念出发的。对此,费正清批评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的头脑简单到何等的地步。”“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好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注: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11页。)
费正清一贯坚持从中国的历史出发来研究中国。他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兴起在本世纪初的“蓝皮书史学”。 英国马士(H. B.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直到今天还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几乎都是根据西方的档案资料来研究中国的。他们的著作确切地说,应称为西方对华关系史,而不是中国的外交史。费正清则开创了以中国档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风,1932年,费正清第一次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他是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之一。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所引用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档案。他不鼓励他的学生将时间都花在语言学习上,他曾说过:“汉学家就像是语言的仆人,甚至是奴隶,但历史学家的问题是要将语言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注: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为此,他与他的助手邓嗣禹、刘广京、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等合作,编成了《近代中国:1898至1937年中文著述指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等一批书籍,要学生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的资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原始资料,对研究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98—399页。)。
费正清钟情于历史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具有最大的涵盖性和最少理论束缚。
由于费正清只提出模式而很少涉及理论。中国的一些学者批评他“浮浅”。其实,不从理论出发来观察历史,正是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精髓。美国史学界流派众多,实证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费正清在很大的程度上继承了这一史学的传统,他不愿在中国研究中建立一般的理论,很少在宇宙观的思索中花费时间,在进行最一般的概括时,也尽量避免使用确定的、严密的概念化的语言,甚至对抽象的理论表示了厌恶。正是他的这种治学态度,使他的中国研究没有因为观念形态的约束,以及理论先导的影响而变得裹足不前,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观察中国。
美国对中国研究是一个区域性的研究课题。区域研究的目的,在于集中各门社会科学对一个单一的地理区域进行综合的研究,它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是一门把各种学科的学者汇集在一起的新学科(注:参见费正清:《全方位研究中国:区域性研究和我们的远东问题》,《哈佛校友会会刊》第49卷第9期。)。 历史学给中国问题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它较少理论束缚的特性又给予了学者们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自由想象的空间,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扩大了中国学的范畴,使中国研究延及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赋予美国现代中国学蓬勃生机。
二战后虽然哈佛的资金来源大幅增加,但对经费竞争依然十分激烈。只有哈佛—燕京学社支助过中国文学和人道传统的研究,但对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却很少有人感兴趣。在费正清、赖肖尔的努力下,哈佛大学的部分学者组成了“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专业委员会”。它通过讲座、讨论和特定的合作项目,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使教授们汇聚到一起。在该委员会的协调和组织下,中国研究逐步发展成为包括对中国的人口、社会流动、思想潮流、文化演变、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科举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众多课题进行研究的学科。费正清在促进确立哈佛的这一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区域研究的模式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学术企业家”:学术领袖的作用
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称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注:柯文、戈德曼:《纪念费正清》,第112页。),这是一种赞誉。作为一个学术界的领袖, 费正清除了必须具有非凡的学识外,还具有整合各学术流派、开拓新的研究课题、为学术研究争取经费以及扶持研究后备力量的能力。
整合各学术流派需要大度和宽容,摒弃门派之见。费正清创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使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但他并没有孤守一隅,而是争取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其他著名学府的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在5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分为两个派系,一派是以哈佛为中心,以费正清为核心;另一派是以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为中心,以研究太平天国的戴德华(George Taylor)为核心。费正清感到, 这种学派之争,已处于非理性的感情化状态,“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学者之间的合作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障碍……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已不可能不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对中国的事变感兴趣的学者,对此既有理性的也有感情上的体验”。因此,费正清认为,“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尽可能中立、可行的基础上,恢复我们的团结。”(注:邓鹏:《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0页。)他联合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Martin C.Wilbur)等学者, 请福特基金会资助,筹备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国问题讨论会,并主动与戴德华进行联络,作出和解的姿态。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在 1960年8月召开了现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由戴德华出任会长。这个联合委员会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政治倾向上的差异而造成学术领域里的敌对状态,促进了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费正清还不断为开发新课题作出努力。为调整中国研究领域传统汉学占主导地位的基础结构,他在50年代就提出了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问题进行研究,倡导成立了中国思想研究会,并将该研究会学者关于儒家思想、儒教国家制度和行为的论文汇编成《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一书(注: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242页。)。 他支持史华慈等人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研究,他所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开了系统研究中国革命的先河,史华慈和布兰特(Conrad Brandt )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崛起》、《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这两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他认为,传教士问题是一个被忽视的课题,为此积极推动这方面的研究,他对诸如《明代人名词典》这样的研究项目也倾注了极大的兴趣。他提倡给研究项目以广阔的变动范围,认为传统的研究给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知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学问是不扎实的(注: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252页。)。这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的提出, 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开辟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的道路。有的评论者认为,费正清的学术研究只集中在他的早期,这是一种偏见。应该说,作为一个学术领袖,费正清在本人的学术取得相当的成就后,逐渐从文献研究中走出,转向了构筑有关中国的综合研究的大厦。他“总是做初步的勘探工作,发现矿石,建立采矿公司,而把采掘的工作留给他的学生”(注: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201页。)。
费正清在创建美国中国学过程中发挥了“学术企业家”和学术领袖的重要作用。学术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如何处理好政府部门、基金会和学术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三者之间,费正清可以说是长袖善舞。据统计,自1958年到1970年期间,费正清争取到私人基金会和政府部门所提供的资金达4000多万美元。对此不少学者有看法,认为费正清等人的学术研究与政府过分紧密的拥抱是一种危险。而费正清的观点是,学问应当为国家的行为提供信息,大学的责任应该是对那些将同时满足学术和政府及社会需要的当代问题进行基础研究。他认为“有价值的成就是个人十分聪慧而又注重实际的一种平衡。他不是仅仅提出一个伟大的思想,而是还要有所实施。”(注:丹尼·谢罗克:《与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一次谈话》,《哈佛杂志》1979年第 4期。)没有迹象表明,费正清的学术观点受到政府的支配。美国的基金制度,对美国的学术研究是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的,费正清和他的中国研究正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
费正清的学术观点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至少可以给我们仍处于低迷徘徊状态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以一种启示:学术研究只有从纯学术的圈子中解脱出来,发挥其本身的功能,为解决现实问题进行基础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学术研究又不能只是简单地融入社会,还必须保持其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本身的功能。这是学术研究的责任,也是学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