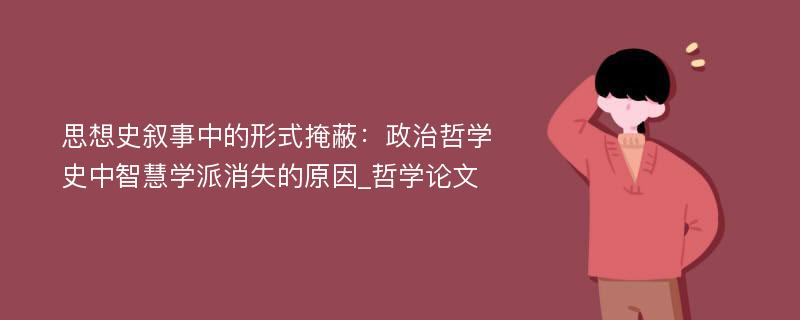
思想史叙事中的范式性遮蔽——智者学派何以在政治哲学史中消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范式论文,学派论文,智者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希腊城邦政治哲学史的既有建构范式
论及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历史,很多学者都认为古希腊城邦社会实现从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奠基者是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城邦晚期思想家,而智者学派在这一转向中的作用似乎不值一提①。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学者中,美国学者萨拜因(George H.Sabine)也许可以算作是一个典型。一是因为,萨拜因在自己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中明确地罗列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剪裁”思想史的理由;二是因为,他的这本书作为美国经典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很受推崇,前后好几版,历时数十年,印数甚巨,流传广泛,甚至还被译成很多种文字,影响所及,远远超出英语世界。以至于当代思想史研究大家施特劳斯(L.Strauss)也以编写一本能取代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的教科书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②。
那么,萨拜因在思想史叙事中推崇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城邦晚期思想家、贬低智者学派的理由何在呢?从《西方政治学说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两条:一是对智者学派以诡辩术见长颇有微词,认为智者学派注重的辩论术算不上是什么政治上的“爱智”。萨拜因就此评论道:“就诡辩学派而论,他们根本不讲什么哲学,他们讲授的是富裕的学生们愿意付学费的知识。”③因此在萨拜因看来,智者们在这方面严格说来算不上思想家。二是认为,即便智者学派有些人文主义关怀,但也没有踩到政治哲学的“点子”上。因为这些人文关怀没有指向“追求变化中的不变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这个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而是指向了“任何人愿意相信的任何事物都是真实的”这个似乎荒谬的、“白费气力”的怀疑论④,因而偏离了政治哲学的主要的任务。
由此看来,萨拜因所谓的政治哲学,其主要任务就在于探明社会公共领域中变化与多样背后的“不变”与“统一”,就在于在这个确定性的基础之上为人类的应然政治生活提供一个不可置疑的、能“知善恶”的坐标。不难理解,在这样一种理解范式面前,智者学派带有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色彩的人文思想的确显得有点“不入流”,它们在萨拜因的思想史叙事中消失也就的确不难理解了。
然而,今天的人们大概已经很难毫无保留地认同萨拜因这样一个有关政治哲学的取舍标准了。对古希腊政治思想颇有研究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巴克(E.Barker)就很明确地主张,凡是涉及到人文和人伦的思想探讨都应归入政治哲学范畴,而不必考虑其目标指向,因为“人与国家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根本不可能纯粹地讨论个人的伦理,任何关于人类行为的哲学都必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哲学”⑤。
更重要的问题似乎还不在这里。萨拜因的这个认知范式实际上还决定了他对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城邦晚期思想家政治哲学的解读眼光,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推动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在萨拜因看来,希腊城邦晚期三大政治思想家在对公共生活进行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继续沿着业已为自然哲学所开辟的老路线——追求变化中的不变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⑥前进的倾向。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最突出的思想贡献便体现在这个方面。
但是,今天人们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三位思想家的发掘似乎进入了更深的层次。英国当代思想大家奥克肖特(M.Oakeshott)认为,城邦晚期三大思想家对政治哲学的最大贡献其实并不在于他们对确定性、本源性和一元性知识的追求,他们的最大思想贡献实际上在于对城邦既有主流知识体系的怀疑与颠覆。在他看来,政治哲学最大的特点正好不是对于确定性知识的追求,而是对于社会公共领域中的确定性知识的质疑与颠覆⑦。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也反复强调,人们先前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解读一直有误。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对于政治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杰出历史贡献不在其他地方,而在这位思想家于彻底的思想怀疑与自觉的行为节制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⑧。施特劳斯所提出的“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去”的口号,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的。很自然,这种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不同的苏格拉底学派,也展示出苏格拉底学派对于政治哲学的形成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贡献。
用这种新的眼光来打量希腊城邦从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我们便会觉得萨拜因建构政治学说史的框架带有着一个已经逝去时代的厚重印记。在那个时代中,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使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化,是要揭示出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那个“不变”,是想为政治学说与政治实践寻找一个确定的、不可怀疑的基础。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政治学说史发掘出希腊城邦晚期三大思想家,放大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思想,并把他们看成是这些方面的代表人物当然是不奇怪的。然而斗转星移,在经历了对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反思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今天,人们认识世界、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范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切对于确定性知识的寻求,对于建立在一元论基础上的终极根源的追索,不仅不再具有先前那样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人们对复杂大系统有越来越清醒认识的情况下,被认为是人类认识史所走进的一个误区。在这样一个重大认识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智者学派的政治哲学地位的重新审视,与前人在不同的范式基础上进行一场新的对话。
当然,在展开这一对话前,我们还是要先对智者学派的政治思想全貌作一简单的扫描,从而为重新认定智者学派在政治哲学发展历史中的地位提供一个基础。
二、智者学派的政治哲学架构:个体主义、怀疑论与相对主义
智者学派用来与既存的客观主义本体论自然哲学相抗衡的基础,是它对于个体感知的强调。从个体感知出发,它形成了自己的个体主义、怀疑论与相对主义立场,并在这样一种立场上,智者学派形成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人类公共生活的理论框架。
首先,智者学派从强调人们的个体性感知出发,颠覆古希腊自然哲学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政治至善主义的独断倾向。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大多坚持自然与社会的同一性,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建立在“数”基础上的正义理念,还是赫拉克利特建基于“火”之上的贤人统治合理性,都在本质上体现出用“一”来统摄“多”的基础主义思维模式。应该承认,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⑨,也反映了人类出于自身发展和社会治理需要而对确定性知识产生的依赖。但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对于“一”的过度关注,往往总是通向对于一元整体和一统真理的强调,忽略对于差异性存在的注意。而在政治上,这样的关注与追求也隐含着政治理性主义和政治至善主义的独断倾向。毕达哥拉斯已经有了将社会乌托邦化的萌芽,而深受其影响的柏拉图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王”与理想国家的理论体系。尽管柏拉图的哲学王与理想国思想在古希腊并没有得到在实践中全面展开的机会,但现当代一些国家的历史却全面演绎了这种思想可能包含的恐怖内涵。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当代一些思想家断然反对这种带有浓厚理性主义、独断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奥克肖特指出,人们“如果已知绝对确定性和普遍适用的原理或公理,任何政治建议可参照它们决定其优点,论证性的政治论说就有可能出现”⑩。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一元的、确定的真理统治下,一个基础主义的时代就离我们很近了。在这个时代中,一切差异与变化会被真理统一起来,真正的创造性都会受到排斥。
很显然,智者学派“不打算去穷究事物的第一因。他们开始立足于经验之上,并试图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积累大量的知识,然后再从中引出某些结论”(11)。在今天来看,智者学派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从这种以“一”统摄“多”的认知范式中突围出来,从根本上否定这样一种难免会走向定于一尊的理性主义逻辑结构。我们看到,普罗泰哥拉从感知主体出发,强调了事物的相对性,注意到了事物用途的多样性,以及人的判断尺度的多元性。他在回答苏格拉底关于“好”是否有利的问题时说,“我们知道许多东西——肉、酒、药物和许多别的事物,有的对人有害,有的对人有利;有的对人既无利也无害”(12)。一句话,对事物进行判断的尺度总是因人而异的。
智者学派在谈及认识和评判社会政治生活的标准时,更多地将人们的主体感知作为判断尺度。普罗泰哥拉有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3)的说法,肯定了个人主体感知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将个人的主体感知、见解和体验看作是真实的存在,是权衡利弊、真假的标准(14)。这种对于个体感知的强调很明显地与爱奥尼亚学派的“理念论”划清了界限,从而不再去苦苦追求万物归一的那个本源。正是从个体的感知出发,以普罗泰哥拉为代表的智者学派拓展出了一个向多元、差异和主体性建构开放的空间。
其次,智者学派从对个体感知的强调出发,进一步以个体主义中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去对抗和颠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整体主义。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更多地受城邦社会主流生活的影响,因而带有整体主义色彩的话,那么智者学派则强调了一种个体主义的政治观,更多地关注建立在个体感知基础之上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城邦对于政治生活的划一安排,反对以善的名义,以多数人的名义实行思想和行为的一统。
智者学派通过对于个体感知的强调,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张扬,突出了自己对于既成的客观一元本体论自然哲学的颠覆与叛逆,并对于早期带有拟人化和超人化特点的希腊神学和神话提出了质疑。以至于泰勒斯所谓的“神就是宇宙的心灵或理智”(15),到了普罗泰哥拉那里,则变成了“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16)。这种对于神的实在性和神圣性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落实到政治领域,也就使得政治生活的合理性不再依附于、外在于人自身的超自然对象身上,不管这种超自然的对象是采取神的形式,还是采取理念或者客观精神这种形式。这样一来,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整体主义取向实际上也就被掏空了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一种建立在个体感知和人的主体性、多样性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便大体上有了自己的一个轮廓。
最后,智者学派还从个人感知的主观性、相对性出发,以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于以追求本源性、确定性为特征的既存自然哲学和后来的政治哲学进行了解构。我们知道,古希腊自然哲学和萨拜因理解下的苏格拉底学派的政治哲学虽然在对象的指向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方法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相似之处便是热衷于对事物的本源和确定性知识的追求。也正是这种对于事物本源和确定性知识的追求体现出了这种哲学内在的本质主义和理性主义。
智学学派中有些人严厉地拒斥这种本质主义哲学。他们从不可知论,从个人感知的主观性、相对性出发,进而得出了“一切皆为虚妄”的结论。这方面,高尔吉亚也许可以算是一个代表。他在《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中提出自己的三个原则,“第一个是(除了人们的自觉之外)无物存在;第二个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第三个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17)。高尔吉亚的“三原则”在这里解构的实际上是当时主流社会认知范式所赖以确立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基础,是一切以确定性面貌出现的事物。他所谓的“在每个职业上和每个年龄上,我们每个人都对每一件事有自己的美德”(18)的看法已经使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相对主义论者,已经非常接近当代思想家费耶阿本德“什么都行”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智者学派从感知、从经验、从主体出发所走向的相对论、怀疑论观点,不仅使得依赖于绝对本源与绝对知识之上的一统真理观、一统价值观成为不可能,而且也撼动了当时作为希腊城邦社会基础的整体主义以及与整体主义相应的等级制度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智者学派的尝试的确收到了如思想家罗素所言的,一种哲学是另一种哲学的解毒剂的功效。著名思想家卡西尔(E.Cassirer)在这方面也画龙点睛地指出:“智者们的哲学以及他们本人精神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他们那令人惊异的多面性。他们心平气和地对待每一件事。他们以一种新的精神突破了由传统的概念,一般的偏见和社会习俗所形成的障碍。”(19)而哈维洛克则明确指出,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精神直接表现在反抗苏格拉底学派的智者学派传统中(20)。
当然,如何看待和评价智者学派所倡言的相对主义,这恐怕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每一种看法实际上取决于认识与评价主体本身的价值偏好。而且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智者学派的个体主义转向也未必就一定能解决希腊城邦社会面临的危机。但是,我们如果从思想史发展的意义上来看,智者学派的确创造性地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开拓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它颠覆了既有的主流认知框架,颠覆了一元真理观的基础,成就了政治哲学史上极有意义的认知范式转变,为人类最终走出整体主义困局迈出了可贵的尝试步伐。因此,将政治的基础构筑于人的感觉、需要、欲求的基础之上,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它都是对于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维进行平衡的有效手段。这对于经历了20世纪政治理性主义风云肆虐的我们来说,恐怕会有着特别的感受。
三、遮蔽与去蔽:认知范式间的对话与转换
英国思想家柯费尔德(G.Kerferd)曾就早期智者学派的政治思想探索在政治哲学史上受到不合情理的遮蔽,得不到后人承认一事,谈过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事情的原因似乎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因为智者学派本身流传下来的著作十分稀少;另一个是因为柏拉图充分发挥自身天赋对智者学派极尽攻击之能事(21)。这样的解释诚然有一定道理,然而细究起来似乎也有说不大通的地方。智者学派目前的传世作品固然不是很多,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并不比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们所留下的作品更少。为什么这些自然哲学家们的思想没有受到遮蔽,而智者学派的思想却受到遮蔽呢?至于智者学派受到其论敌柏拉图等人的恶意攻击,似乎也不能作为生活在现当代的后人们不承认智者学派学术地位的充分理由。今天的政治哲学史毕竟是由后人而不是由柏拉图他们在编写。
因此在我们看来,智者学派的政治哲学思想受到忽略甚至无视的原因,恐怕与特定时代政治哲学史编撰者的认知范式,或者说与柯林伍德意义上的“绝对预设”,与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不无关系。正是政治哲学史的编撰者所特有的理性主义认知范式、理性主义的绝对预设和集体无意识,决定了他们的眼光,决定了他们对史料的剪裁,决定了他们通过剪裁所力图展示出来的理性主义“意义世界”,决定了“近现代对希腊政治思想史的书写,与对希腊政治的书写一样,完全是按照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希望的那样在书写”,也决定了“智者们只有在所谓的古典主义影响受到最大削弱的地方才会受到关注”(22)。
国内学者马德普先生曾指出,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中有着一种历时弥久、影响至深的“大理性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古代强调自然理性,中世纪强调上帝理性,而近代强调人的理性”(23)。虽然马先生这样的划分线条似乎粗糙了一些,但个中揭示的道理却极为深刻。正是这样一个大理性传统构筑的认知范式长期左右着人们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社会政治、看待思想理论的眼光与方法,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偏执,一种追根求“源”、万宗归一的形上偏执。
在政治思想史上,柏拉图也许可以算是在西方世界确立这种理性主义认知范式的第一人。他在综合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对于世界万物本源探索,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抽象本质追求和巴门尼德对于感性和理性区分的基础上,在继承苏格拉底对概念本质的探求和对绝对善的强调的前提下,构建起了一个以“理念”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认知范式。在这个认知范式中,理解与把握这种超然于现象世界、作为万物本源、决定着万物发展的理念便成为一切知识中的核心知识,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去揭示这隐藏在万物背后的本真之源,去把握这事关世界与人类命运的真理认识,去提供一个现实政治可以去依之施工的可靠蓝图。而哲学家的理性也就成为开启这理想世界之门的不二法门。
柏拉图极度张扬理性主义的认知范式的影响虽然由于希腊城邦世界的湮没而一度缩小,但它却从来没有被真正摧垮。相反,这个认知范式于一千多年后在科学全面进军的大背景下获得了报复性的疯长,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联起手来开始向人文世界全面进军。近现代人文学科的探索为获得自身存在合法性而加速向科学主义认知形式靠拢,向往着在人文领域建立类似于牛顿力学式的精确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哲学立志于发现社会与政治生活借以立足的原点,进而通过“中性”观察揭示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力求精确地描绘出人类社会与政治生活未来发展的前景,力求获得没有争议的政治生活指导原则和行为依据,也就成为了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霍布斯抱着成为政治学领域牛顿的目标进行他的“利维坦”研究,自然法学派对于确定的人性的努力发掘,斯宾诺莎对伦理学的几何化处理,孔多塞通过“人类进步史表”对普适规律的追寻,功利主义者们对可量度的幸福感的热衷,历史决定论者身上所体现的对历史必然规律性的追求,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于“价值祛除”的向往,都充分地体现出理性主义认知范式对确定性知识、普适规律的渴望,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与模仿。不难理解,诞生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的政治哲学史研究,会很自然地带有“理性主义的传统”(24),会很自然地“发现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中,在理性的人们中间存在着对于客观的善,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这种善的手段,以及关于彼此冲突又相互促进的政治家的艺术和公民权利方面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25)。我们从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中看到的“编织”主线,正是思想家对于所谓的客观本源本体、确定性知识的基础、事物发展内在原则、社会秩序不变规律的探索与“发现”的努力。因此,萨拜因将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所持有的认知范式的局限。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背景的认知范式的出现有着它自己在那个时代的合理性,也有着一种所谓的“不可避免性”。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市场经济与多元时代的充分展开,人们对复杂大系统发展中的开放、不可精确预测与操控特点的知晓,人类建立自己完美社会实践的灾难性后果的一再重演,已经对人文学科中理性主义的认知范式有了一种清算性的反省。哈耶克对于滥用理性与科学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揭示,波普尔对于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一元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伯林从多元价值角度出发对于理性主义的一元独断的声讨,奥克肖特有关怀疑主义政治合理性的阐述,大体上完成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的建构。这样一种新的认知范式的问世,不可能不引发政治哲学史的地震。而后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以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更加激进的态度,对以崇尚普遍规律、普世价值为标志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和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知识话语霸权,不承认有客观的真理和普遍的价值追求,以多元与差异、倒错与间断这类话语消解人们对于元叙事方式的执着,他们反对以技术思维作为政治思维的认识原则,解构一切超验标准和神圣性,完成了对西方近现代主流思想文化的根本颠覆。他们中间的激进分子如费耶阿本德更是接受了一种知识观上的无政府主义,接受了一种哲学上的相对主义。
当然,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有着复杂多样成分的思潮,其中突出的极端倾向也不无负面的影响。但它所完成的认知范式上的转换却是无法否认的。在新的认知范式以及这种范式带来的新的意义世界中,我们对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哲学发展过程的观察,便不能不形成一幅新的画面:智者学派在思考社会与政治事务时所坚持的主体性、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思想都有了更大的意义阐释空间(26)。他们用主观感知去抗衡一元本体和唯理主义;用相对主义去怀疑理性专断和确定性知识;用约定建构去反对神圣与绝对原则;“教人向对他们有权威的东西去运用思想”(27);用政治平等说“与直到那时为止依然盛行于希腊人之中的神秘主义、精英主义的政府观”相抗衡(28)。智者学派的这些思想在新的认知范式中,显然不只应该被算作是政治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其历史地位与理论意义也远远超过柏拉图理念论对于政治哲学发展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有着什么样的正当理由,可以把希腊城邦世界出现的从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起点与智者学派隔离开来呢!
这样说来,把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城邦晚期思想确定为希腊政治哲学转向的实现者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道理呢?这恐怕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加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如何来理解苏格拉底等对于政治哲学发展的贡献。如果我们把苏格拉底仅仅看成是通向柏拉图理性主义政治学的阶梯,那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今天的新认知范式中便很难成为实现这种转向的思想家。如果我们突出苏格拉底等对确定性知识的怀疑主义的态度(“我知道自己不知道”),突出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对雅典政治实践与理论的颠覆性批判,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与智者学派一起完成了政治哲学转向的思想家。而且,也只有在作了这样的一种区分之后,我们对斯特劳斯有关“回到苏格拉底”,“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呼吁,恐怕才会有较为确切的把握。
如果说,政治哲学的最大发展是政治认知范式的转换,那么不同认知范式间的对话正是我们消除遮蔽,形成新的视角的必经之路。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时代同样也有我们自己难以逾越的“遮蔽”。
注释:
①持有这一看法的人很普遍,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现代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专家萨拜因以及美国当代思想大家施特劳斯都持有这一立场。西塞罗认为“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并且迫使它对人生和礼俗以及善恶之物进行研究的人”(参见[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21页)。萨拜因更是明确地反对把智者学派看成古希腊政治哲学形成过程的参与者。而施特劳斯等人编的《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则把修昔底德这位史学家而不是智者学派纳入到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之中。
②参见[美]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8-1049页。
③[美]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南木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页。
④[美]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0-51页。
⑤[英]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⑥[美]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1页。
⑦M· Oakeshott.Religion,Politics and the Moral Life.Editor,Timothy Fuller.New Hav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119-155.
⑧这里的思想可参见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24页)以及甘阳为该书中文版所写的导言。甘阳指出,苏格拉底开创古典政治哲学的起点,“就是为了克制‘哲学’的走火入魔,以维护政治社会的稳定”。参见该书第60页。
⑨基础主义思维是通过抽象来把握特殊背后的普遍,个别背后的一般。这就摆脱了在人类文明滥觞时期普遍对事物进行直观把握的局限。关于这一观点,可以参考黑格尔对泰勒斯命题的精彩论析。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鳞、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6-187页。
⑩[英]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11)[德]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贺仁鳞校,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12)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3页。
(13)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8页。
(1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智者学派所反对的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标准,而对个体理性他们并不排斥。相反,普罗泰哥拉认为要想成为有教养的人应该在少年时就开始学习。联系到大多数智者都以教师为业,我们可以认为智者们对于作为个体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是有着肯定态度的。
(15)苗力田:《古希腊哲学》,第22页。
(1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
(17)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
(18)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4页。
(19)[德]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66页。
(20)参见E.Havelock.The Liberal Temper in Greek Politics,London:Jonathan Cape,1957,pp.17-18.
(21)[英]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等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l页。
(22)E.Havelock.The Liberal Temper in Greek Politics,London:Jonathan Cape,1957.pp.17-18.
(23)马德普:《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24)这里所说的理性主义传统内容,我们可以在冈内尔(J.Gunnell)的著述中得到启示。他指出,“带有传统观点的思想牢牢地控制了政治理论史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传统分类中的经典著作(至少包括下列人物的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马克思)……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个传统始于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参见[美]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王小山译,岳鳞章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25)这里引用的是卡特林(G.Catlin)在其所著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中的话,转引自唐士奇:《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6页。
(26)针对理性主义价值一元论的独断,伯林认为,“始终存在着一种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说,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智者学派的普罗泰哥拉、安提丰和克里蒂亚斯,认为包含着价值判断的信念和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制度,并不取决于对客观不变的自然事实的发现,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意见,后者是可变的,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英]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页)。无独有偶,常士闫先生在其研究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所揭示的权力与知识的密切关系,与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强权就是真理”的观点不谋而合。参见常士闫:《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27)[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9页。
(28)[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标签:哲学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范式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思想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自然哲学论文; 古希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