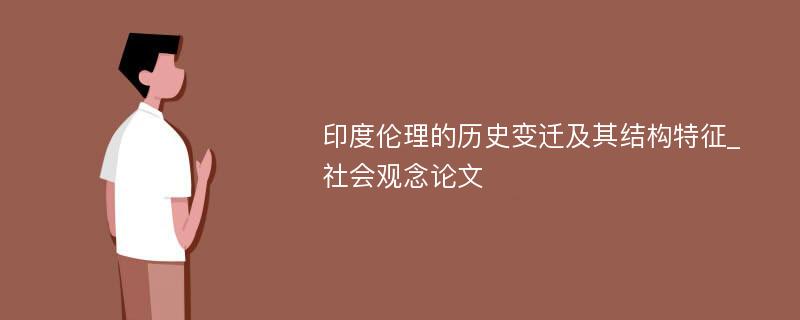
印度伦理的历史性变迁与结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历史性论文,伦理论文,特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508(2014)04-0092-08 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认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我国学者欧东明认为,该宣言只是提出了分别出自基督教传统和儒家传统的有关“道德金律”的表述,严重忽视了印度传统,他专门特别地强调了印度的非暴力主义。①其实,早在1984年,C.克劳福德(Crawford)在《印度伦理思想的发展》中以深入的观察为依据得出结论说,印度人的思想为确立全球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②世界著名小说家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其题目来源于惠特曼的同题诗篇《印度之行》。在惠特曼看来,印度是灵魂的归宿;在福斯特看来,印度是“人类永恒的家”。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从印度伦理观的历史发展脉络,就印度民族和印度国家伦理观的结构构成和内容演变特征,作一粗浅的梳理,以冀为全球伦理的构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印度伦理的日益现代性 印度民族和国家的伦理观将古代中世纪的宗教化、近现代的圣雄化和当代的法制化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现代性发展特征。 (一)古代中世纪的宗教化 尽管“印度人没有纪事的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事实的历史”,③但是,印度古代时期的宗教典籍却非常丰富。 印度最古老的文献资料是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的最原始文献《吠陀》(veda)。它出现在印度原始社会瓦解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公元前1500年—前900年),即著名的吠陀时期。那时,印度人的伦理观念主要体现最早的隶属于吠陀本集的《梨俱吠陀》。在阶级社会诞生后,印度人的伦理观念主要体现在《吠陀》的最后一部分,即公元前10世纪—前5世纪之间的《奥义书》中。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婆罗门教僧侣根据《吠陀》与《奥义书》的基本思想,以及传统习惯惯例,创立了一系列关于人生行为规范的法经(Dharma sūtra)和法论(Dharma sāstra),即《摩奴法典》(Manu-smrti),构成印度最古老的伦理观念的基本内容,影响持续数千年,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印度教教徒的伦理观念。 公元前600年—前500年,印度诞生了其他各种宗教派别,如佛教、耆那教等。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进入了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盛世。仅就佛教而言,经过了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三个阶段,到公元9世纪左右,佛教有了大批的重要的经书。耆那教的重要经书是《谛义证得经》,顺世论的重要经书是摩陀婆的《摄一切见论》。 到了11世纪,来自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三次入侵印度次大陆,并建立了印度封建社会时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莫卧儿帝国。在中世纪宗教一统天下,世界上基督教世界、儒家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三足鼎立,穆斯林世界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组成。莫卧儿帝国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进入强盛时期,各种宗教思想在印度共存共荣,宗教辩论成为国家大事。因此,“印度古代的伦理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印度的宗教哲学之中”,④古代印度人的伦理观念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印度是世界宗教和人种博物馆,多元性非常突出,但是,直至今日印度教仍然是印度的主体宗教。印度民族众多,但没有一个民族的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而信仰印度教的人数却占全国总人数的82%还多。可以说,“印度教所代表的文化,就是印度民族精神普适性的依托”。⑤因此,下文在分析印度民族和印度国家伦理观的时候,主要是依据印度教教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否认其他宗教伦理观的存在和影响。 (二)近现代印度民族伦理观的圣雄倾向 进入近代,印度次大陆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以理性和人性为特点的西方文明携带着坚船利炮闯入印度次大陆,对次大陆人民的伦理观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英国殖民者在次大陆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分成英国直接统治区和间接统治区——500个土邦王公的统治区。在这种情形下,印度的伦理观进一步复杂化,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分化。另一方面,在英殖民者未进入南亚次大陆之前,古印度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单元的分散、不统一,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对印度长达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将四分五裂的印度连结成为一体,印度人的整体意识、一体化意识开始形成。 在这种既分裂又一体化的撕扯过程中,最终有一个人把整个次大陆的民众团结了起来,那就是圣雄甘地。“甘地主义作为印度农民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中介’”,⑥把历代不关心政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吸引到民族主义运动中来,印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伦理观进入生成阶段。依靠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道路,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正式建国,真正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印度民族精神和民族伦理观开始形成。甘地的思想代表了次大陆民众的心声,也符合次大陆历史发展和伦理发展的潮流。甘地的一言一行充分代表了近代时期印度人民崇拜向往、并且愿意追随的理想。 就印度的伦理观而言,与古代的宗教化相比,近代的甘地化表明印度的伦理观从神化过渡到人化。印度民众赋予甘地以圣雄的称号,“圣雄”来源于梵语的敬语“mahatman”,意思是“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ed),接近于神人的凡人。与古代的宗教相比,甘地的思想代表的是印度民族的思想,而非部落社会群体的思想,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和集中代表。时至今日,印度学者告诉笔者,作为研究印度的中国学者,必须了解的人就是甘地,必须读的书就是甘地的著作。可以说,甘地的思想与宗教思想一样是现代印度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当代印度国家伦理观的法制化 独立后,印度的伦理观由人化转变为法制化,由古代宗教教义的约束到近代圣雄的感化最后发展到法律的制约。既非神,也非人,而是法。在现代社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前现代国家,宗教就是最高法律,它规制着整个社会和人民的道德生活。社会和个人的伦理完全来源于宗教文本。但在现代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伦理完全来源于宪法。当然,印度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到宪法的伦理。但是,印度宪法的起草者B.R.安贝德卡尔博士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明确谈到了“宪法的道德准则”就是“把宪法的形式至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制民众服从这些形式的权威,但伴之以言论自由的习惯”。⑦他还说:“宪法的道德准则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宪法的道德准则必须要培育。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人民还没有学会它。印度的民主不能只是印度土壤的上等肥料,如果是那样,那根本就是不民主的。”⑧由此可见,印度的建国之父们充分意识到印度需要培育一种新的伦理观,即“宪法的伦理观”,它应该是更加具有包容性,在性质上应该是世俗的、民主的。所以,独立后印度的伦理观以宪法的伦理观为主导和主体,印度的宪法决定着印度将来伦理观的发展方向。 二、印度伦理的渐进系统性 印度伦理观将古代中世纪偏重人与社会、近现代偏重人、社会与政治和当代将政治经济与社会和人综合在一起,呈现出日益完善的系统性特征。 (一)古代中世纪以人和社会为重心的伦理观 吠陀的第一部《梨俱吠陀》中的不少赞歌表述了古代印度人的一些伦理观念。一方面是日常的伦理观念,如要求人们友好、互助、诚实等,另一方面是种姓制观念。《梨俱吠陀》中的一首赞歌在谈到“原人”(purusa)时说:“婆罗门是他(原人)的嘴,他的双臂成为刹帝利,他的两腿是吠舍,他的两足生出首陀罗。”⑨意思是各个种姓都是“原人”身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种姓的不平等是符合自然秩序及人的需要的,是一种和谐的现象。恰如泰戈尔所言“印度人强调个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对于他们来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伟大的事实”。⑩而在德国思想家韦伯看来,固守职业“在印度被提升为一种根本的宗教义务,且为有力的宗教性约束所强化”。(11)这是固守职业的经济伦理。 《奥义书》进一步加强了种姓分工的伦理思想,把遵守种姓义务看作美德,把违背种姓义务看作大逆不道。此外,它还提出一系列在印度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宗教哲学理论,如善恶因果、轮回解脱、梵我同一等,还强调苦行、做瑜伽以及履行宗教义务等都是善,是达到解脱或梵我同一的重要步骤。(12) 《摩奴法典》首先明确了业报轮回。“(人死后)凡有喜德的诸魂,取得神性;受忧德支配的,取得人性;沉溺于暗德的沦为畜牲:这是主要的三种轮回。”(13)其次,为种姓制社会具体规定了一套人生的基本生活历程或要求,即“四行期”:梵行期、家居期、林居期、遁世期。但是,只有前三种姓才有资格按此生活,首陀罗和贱民则无权过此生活。这套人生行为规范展示了种姓制成型后印度社会伦理观念的基本内容。它虽从吠陀奥义书时期开始逐渐产生,但影响却持续数千年,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印度教教徒的伦理观念。再次,《摩奴法典》还强调了正义。“保护人民的国王,被势均力敌的、优势的或劣势的敌人挑衅时,不可回避战斗;要记取武士种姓的义务。”(14)尽管《摩诃婆罗多》不允许侵犯少数人的权利,视人如视己。(15)最后,《摩奴法典》还规定尊敬师长,师为上。“相传父亲为嘎尔荷波蒂亚火(家居者之火),母亲为达克那火(南火),师父则为阿诃瓦尼耶火(烧供火),这个三火更重要。”(16)一个人“由于尊敬母亲而得下界,由于尊敬父亲而得空界;由于服从师长而得梵的天界”。《摩奴法典》还规定:“教师通过传授启示的典籍,给予学生以不论大小的好处时,人们应该知道,出于他施予圣道的恩惠,本法典将他看做是精神上的父亲”;“无论是否有教师的命令,学生都应该热心从事学习。设法使可敬的师长满意”;“答复老师的命令,或和他谈话时,或卧,或坐、或食,或从远处或从旁视,都不应该”;“诽谤老师,死后变驴;诬蔑老师(则死后)变狗”。(17) 上述伦理思想带来的后果恰如韦伯所说:“一个全心冥思生命及其种种过往的人,对于政治—社会事态的一时的情势是不会有什么兴趣瞧上一眼的。”(18)古代印度的伦理思想几乎都是关于人与自然的论调,严重忽视政治和社会。 (二)近现代印度以人、社会和政治为重心的伦理观 到了近代,从甘地的思想可以看出,印度民族追随和向往的伦理观是以人为根本,延伸到社会,表现为政治。 在人的伦理观方面,甘地首先强调道德是一切的基础,神就是伦理和道德。他说:“有一件事在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就是相信道德为一切事物的基础,真理为一切道德的本质。”为什么要敬神呢?甘地明确表示:“对我来说,神就是真理和爱。神就是伦理和道德。神是无畏,神是光明和生命的源泉……神就是良知。”(19)甘地要求“坚持真理运动的参加者所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充分体现在他为真理学院规定的十一项誓言中,分别是:非暴力、忠诚、贡洁、节欲、不偷盗、不贪占或忍受清贫、参加劳动、自产、无畏、容忍和敬神。这十一项誓言除了继承《摩奴法典》规定了德行的十大特征,(20)外,增加了“自产”。其次,甘地特别强调自我克制。他认为,文明的真正含义不是增加欲望,而是慎重而自愿地限制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提高服务性能。他说:“幸福生活的秘密就在于自我克制。自我克制就是生命,而纵情享乐则是死亡……为了服务而产生的自我克制有一种说不出的欢乐。任何人都不可能夺走这种欢乐,因为这种甘露是出自人的内部,并且维持着生命。没有这种欢乐,人就不可能长寿;即使长寿,也没有价值。”(21)最后,甘地指出,实现道德、追求真理和爱的途径是自我牺牲的苦行。甘地说:“我要在印度大胆地提倡古代的自我牺牲的原则。”“一个人应当从容地为家庭牺牲自己,一个家庭应当从容地为自己的村庄作出牺牲,一个村庄应当从容地为自己的地区作出牺牲,一个地区应当从容地为自己的省份作出牺牲,一个省份应当从容地为自己的国家作出牺牲,一个国家应当从容地为全人类作出牺牲。”“追求真理务必引入苦行反省和自我磨难,有时甚至至死,不存在丝毫的自我利益。”他又写道:“真理是不通过折磨对方,而是通过折磨自己来达到的。”(22) 在社会伦理观方面,甘地强调爱是生命的法则,是人类社会的凝聚力。他说:“假若爱不是生命的法则,那么生命就不可能在死亡之中永存着。生命就是不断地战胜死亡。如果人与野兽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话,那就是人逐渐地认识到爱的法则,并且把它实际应用到自己个人的生活之中。世界上的一切圣者,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实践我们人类行为的这个最高法则的活生生的典范。”他还说:“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在构成我们地球的无数原子之间没有一种凝聚力的话,那么地球就会变成碎片,我们也不能再生存下去。正像无意识的事物中间有一种凝聚力一样,在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中也肯定有一种凝聚力量,这种生物之间的凝聚力的名称就是‘爱’。我们可以在父子之间,兄妹之间,朋友之间看到这种爱。”(23)甘地还将爱的法则应用到整个自然界,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价值。众所周知,甘地有一句名言:“地球可以满足人的需求,但却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他指出,“在一个非暴力的社会,我们一定不能向这个地球索求任何东西,那是最卑微的或最低贱的人类所不配拥有的”。(24) 在政治伦理观方面,甘地主张村社自治,取消政治、权力和国家。他说:“我怀着极大的恐惧看着国家权力的扩大,因为国家权力在扩大的同时明显有利于将剥削降低到最低程度,但却毁坏了个体,从而对人类造成了最大的伤害,因为个体才是一切进步的根源。”(25)“我的自治的意思是:印度政府由印度人民所同意,并由成年人口的最大多数所确定。在这个自治的社会中,选举的条件是无私、无我、无取得权力和地位。”(26)尽管如此,甘地把关于人和社会的伦理观应用到现实生活,却是最终表现在他深深厌恶的政治和权力方面。正如B.帕勒克所言,“坚持真理运动(Satya-graha)是一场非暴力的革命,但这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改变关系,关系的改变最后是以权力的和平转移完成的”(27)。显而易见,甘地将自我牺牲的苦行作为民众非暴力抵抗的同义词,其政治意义是十分明确的。 政治作为最终的表现结果,还体现在甘地独特的经济伦理观上。而他的伦理观同样也是他关于人和社会的伦理观的应用。甘地强调经济正义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甘地认为,经济正义是社会正义在经济和道德领域的结合,其中心是强调体力劳动,反对不劳而获。(28)“平均分配的真正涵义是如何满足每个人的各种天然欲望,而不是别的……实现这个目标(平均分配)的第一步骤是必须改变个人的生活……他必须把个人的欲望减低到最低的程度……在个人方面实行自制。”他又说:“如果印度要成为世界所羡慕的一种独立生活的典范,所有的清道夫、医生、律师、教员、商人以及其他人都必须在诚实地工作了一天之后获得同样的工资。他倡导的“共同繁荣的社会是力图争取建立在真理和非暴力基础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将没有种姓或信仰的差别,没有剥削的机会,并且使个人和集体都有广阔发展的前景”。而且,甘地常常把他的共同繁荣理想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此甘地的社会主义常常被称为“在人道社会主义范畴中的共同繁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29)为了实现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甘地提出的方式是自产(面包劳动)和委托制(Trusteeship)。“面包劳动”就是一个人为了养活自己必须从事一些必要的体力劳动。事实上,甘地是把劳动作为防止和根除社会不平等的一种重要的方法。除了面包劳动,委托制也是用非暴力的方法达到经济平等。(30) (三)当代印度系统综合性的伦理观 当代印度国家的伦理观深受甘地、泰戈尔、尼赫鲁和安姆贝德卡的思想影响,(31)是众位思想家各种理念和思想交锋融合与折衷的产物。贱民出身、后来皈依佛教的安姆贝德卡是印度宪法的构建之父。不相信宗教的尼赫鲁亲自起早了印度宪法的前言。与激烈地批判西方的大工业的甘地不同,尼赫鲁是现代大工业的追随者。尼赫鲁的经济思想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促进生产增加消费、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社会目标。但是,尼赫鲁早在1939年就指出:“我们一定不可忘记,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具有个人品德及作为基础的达摩这一概念。”“无论如何,利润动机应服从于社会目标。”“我们的经济计划必须建立在人类前进的基础上而不是为了金钱而牺牲人。”“计划不仅从经济学的观点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角度考虑,而且包括文化、道德价值及人的生活方面。”(32)因此可以看出,在“道德是一切的基础”这一点上,尼赫鲁的伦理观与甘地的伦理观没有根本的差别。印度的宪法正是这些建国之父们共同伦理观的产物。 从根本上说,印度宪法是人民起草的,为人民服务的。因为印度的宪法之父们支持和保留了印度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普遍存在的伦理观,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印度的Preamble部分,基本权利部分和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印度宪法前言指出,要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共和国”,并保证公民获得以下所有权利:(1)正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2)自由:自由的思想、表达、信仰、信念和崇拜;(3)平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并促进所有人的地位平等和机会平等;(4)友爱:保证个人的尊严以及国家的统一和完整。这些权力是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奠基石。基本权利部分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歧视宗教、种族、种姓、性别或出生地;公共就业机会平等;废除不可接触制;废除各种称号,除了军队或学术称号,国家不授予任何称号,印度公民也不能接受任何外国授予的称号。所以,基本权利一方面保证法律和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禁止现实中的不可接触,以实现一个人人平等的伦理社会。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目的是努力创造一个公正合理的道德社会。 印度宪法所体现的伦理观不仅与每一位印度公民的权利有关,还与每一位印度公民的义务相关,这些公民不分性别、阶级、种姓和宗教等。印度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的伦理观也存在着代际的差距,但是,印度宪法字里行间所强调的基本义务却是所有公民在最低程度上可以接受的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印度宪法规定印度人民有义务坚持“珍惜和保护我们多元文化的丰富遗产;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包括森林、湖泊、河流、野生动物,并同情所有活着的动物,促进印度不同宗教、语言、地区或部门中所有人民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的兄弟般的友爱精神;放弃那些伤害妇女自尊的做法”。(33) 最重要的是,印度宪法所体现的伦理观是一套相对不变的价值观,符合一个国家伦理观发展演变的缓慢性特征。印度宪法在66年前制定,直到现在仍然发挥同等的作用。因为印度宪法是一份不断被修改的文件,能够容纳各种社会变化。印度宪法的修改历程亦能充分体现印度社会伦理观的转变。 三、印度伦理的多元性 印度伦理观将古代中世纪的多元共存、近现代的东西方交融和当代的多元统一聚合在一起,呈现出根深蒂固的多元性特征。 (一)古代中世纪印度伦理观念的多元性 印度学者沙尔玛认为:“迄今为止,印度教仍自认为是一个宽容的宗教,大体上这种好战倾向是持续受到抑制的。印度教乐于培养这种宽容的名声,有时甚至坚持宽容不仅是它的特色之一,而且还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34)事实上,早在婆罗门教居主导地位的时期,不少印度人信奉着其他宗教。如公元前6世纪—5世纪,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等教派诞生。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 与婆罗门教认为不平等是一种和谐的观念不同,佛教的基本的原则有三条: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强调众生平等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最大区别。其次,与婆罗门教强调个人自身的修行不同,后期佛教思想中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慈悲利他”的观念,当然,早期与婆罗门教一样偏重自利。与婆罗门教倡导的人生四阶段不同,佛教强调“克己”,即佛教理论中直接论及较多的“三学”——戒、定、慧。 与佛教不同,耆那教不承认吠陀的权威,在印度属于“非正统派”。二者的伦理观念存在不少差别。耆那教在伦理观念上有高的道德标准和低的道德标准。低的道德标准表现在其关于戒律等的要求中,如要求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淫、不执著世间事物等。高的道德标准是要求灭“漏”。“漏”指身、语、意的行为产生的业的物质流入人的“命我”(灵魂),从而形成束缚,使其不得解脱。因此,必须灭漏,才能解脱。《谛义证得经》中提到了控制漏的方法,包括谨慎、克服痛苦、善行等。(35)与婆罗门教相同,耆那教自产生以来,一直十分强调苦行。顺势论更是非主流的教派。与佛教一样,顺世论也反对种姓制的不平等,但与佛教的克己和慈悲利他不同,顺世论反对压抑人的正当欲望,肯定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要求。 总之,从古代印度各种宗教思想哲学来看,它们在伦理观念上有着不少相同或接近的成分,如“大多数宗教哲学派别都主张要抑制人自己的欲望,不少派别十分强调人们的出世生活”。(36)但它们也存在着各种差异如平等观、禁欲观和出世观等,充分体现了古代印度伦理观念的多元性。中世纪伊斯兰教进入南亚次大陆,更加丰富和彰显了印度宗教伦理观念的多元性。 (二)近现代印度伦理观的兼容并蓄性 甘地伦理观的来源是多样的。如上所述,甘地为真理学院制定了十一项誓言,其中五条来源于印度传统伦理观中所宣扬的五种基本美德——戒杀(非暴力)、忠诚、不盗、不贪、禁欲。所以,甘地的伦理观首先来自于印度传统的哲学思想,其次来自于西方的哲学思想。西方有三本书对甘地具有重大的影响,两本是H.梭罗的《文明不服从的义务》(1847)和《精湛的论述》,第三本是托尔斯泰的《神国与你同在》(1893)。甘地说,这些书彻底征服了他,尤其是从第三本书中他第一次发现了“非暴力”和“爱”的真谛。(37)此外,甘地的伦理观也受到西方基督教苦行主义的影响。他说,《新约》中关于宁愿让自己受苦也要容忍暴力的教义(“谁打你的右头,也将左头转过去让他打;谁扒去你的外套,让他也拿走你的大氅。”)“直接触动了我的心。”(38)他认为耶稣基督、丹尼尔和苏格拉底是“消极抵抗或灵魂力量的最纯粹形式”,因为他们能以自我磨难和献身来追随真理。甘地的伦理观最后来源于他自己的创新性。甘地以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在印度历史中找到了文明三要素:耕地的犁、手纺车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甘地伦理观的来源多样性既是印度教包容性的体现,也充分证明近代印度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伦理观具有东西方兼容并蓄的特点,是多元统一的。 古代印度伦理观的多元性基本上是内发性的,均起源于印度次大陆,后来伊斯兰教进入次大陆,但仍然属于东方的宗教伦理观念,它们是多元的,但它们是相容的。比如,近代穆斯林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赛义德·艾哈迈德主张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组成一个国家。他说:“印度教徒兄弟和穆斯林共同呼吸印度的空气,共饮恒河和朱木纳河圣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实际上属于一个民族。”他指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印度的两只眼睛,他们应当在心灵上合而为一并采取一致行动,反之就将会同归于尽。 然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进入次大陆后,印度民族思想观念的多样性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正如著名小说《印度之行》的末尾,阿济兹说:“只有当英国人被赶出印度时,只有到友谊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上时,我们才可能成为朋友。”(39)无疑,英国的殖民统治扼杀了文明间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一位直接担任穆斯林神学中心阿里加学院院长的英国人伯克竭力使赛义德·艾哈迈德相信,与以国大党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同道对穆斯林不利,相反支持殖民当局才合乎他们的利益。所以,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艾哈迈德经常发表言论,认为国大党所追求实现的民主政府,对穆斯林的利益是很不利的。他表示,穆斯林只占印度人口的1/4,在国大党所期望的民主制度下,印度教徒将完全压倒伊斯兰教徒。这种想法也为多数穆斯林领袖所共有,并一直影响着他们的意见和行动。1898年艾哈迈德去世后,经过其后继者广泛宣传,在穆斯林政策演进的诸阶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激起他们要求指定的议会议员人选,要求有利定额的分区选举,最后要求成立巴基斯坦。西方学者韦尔弗雷德·坎特威尔·史密斯在他的《现代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中对此有着精辟的见解:“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那追求着一个国度的并不是一种领土上、经济上或语言上的共同体,更严格地说,甚至也不是一种民族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宗教的共同体。就‘源头’而言,那种在印度建立—个伊斯兰教国家的运动,并不是国家去追求伊斯兰教品格的过程,而是伊斯兰教去追求—个国家的过程。”(40)由此可见,近代印度宗教伦理观念的多元性在政治的影响下,最终以次大陆两个政治实体的出现而告终。 (三)当代印度伦理观的综合性 随着印度的独立,尼赫鲁思想居主导地位,直到1991年印度大张旗鼓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经济改革开始。但是,根据印度宪法,尼赫鲁等建国之父们为国家制定的方针大策仍然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仍然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共和国”,所以独立后印度的伦理观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它首先激发的是一种“大印度”的理想和目标。它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统一体,是一个领土完整和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第二,印度不仅是独立的、完整的,而且要走到世界的前列。(41)这一思想在印度独立初期对于克服传统上小国寡民、一盘散沙、我行我素的思想意识和凝聚民心、树立民族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也为维护印度的统一和民族向心力的形成确立了理论根基。印度宪法充分保证了国家的多元性,规定,印度要建成一个世俗的国家,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 印度第一任总理、杰出的政治家尼赫鲁在他晚年将自己的实践哲学归结为全面的“综合哲学”,并提倡“整体的人生观”,这也恰恰是当代印度作为现代国家的伦理观特点。记者卡兰吉亚问尼赫鲁:“您所说的一切有关我们的遗产及其发展问题,提出了要用一种全面的‘综合哲学’来取代那种‘对抗的原则’。我这样理解,对吗?”他回答说:“对,就是一种综合哲学。”尼赫鲁没有就此做系统、详细的论述,我国南亚问题研究专家朱明忠先生通过对尼赫鲁的谈话,认为尼赫鲁的“综合哲学”包含着两层涵义:其一,从本质上看,“综合哲学”是力求在两种对立或冲突的因素中,建立起某种桥梁或联系的纽带,使它们的关系协调起来,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其二,从方法论上看,“综合哲学”竭力避免暴力的手段,力求用和平、合作、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在解释这一点时,尼赫鲁说:“在不否认或拒绝阶级矛盾的同时,我们想用一种和平的、合作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以缓和逐步增长的社会冲突,力争说服人们不要用打倒或消灭的方法相威胁。甘地可能还不知道,我和你所理解的这个阶级斗争的方面。但是,他的解决方法对于我们的时代,特别是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合适。”(42) 通过印度宪法,我们发现,当代印度的伦理观综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甘地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包容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是一种综合性的哲学思想,是多元统一的。 总之,通过上文对印度伦理观的历史变迁和结构特征来看,笔者认为印度全球伦理观的构建提供了三条根本原则:多元性意味的友爱与共存;综合性意味的宽容与包容;民主性意味的非暴力。就像甘地对民主的前提的解释:一要有非暴力作为原则,二要有人民自己的意志。(43)印度是“灵魂的归宿”,印度是“人类永恒的家”,上述那些深深烙在印度民族和印度国家血液里的伦理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同样应当成为全球伦理的血源。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ajiv Rangan博士的一些启发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注释: ①欧东明:“全球伦理视野中的印度宗教传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0页。 ②[加]J.奥康奈尔:“评克劳福德的《印度伦理思想的发展》”,初晓译、周庆琪校,《哲学译丛》,1984年第6期,第80页。 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④姚卫群:“印度古代宗教哲学中的伦理观念”,《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81页。 ⑤熊坤新、严庆、王兴玉:“印度民族精神及其成因”,《国际资料信息》,2006年第12期,第32页。 ⑥王立新:“印度农民政治文化变迁和现代民族运动的兴起”,《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第73页。 ⑦B.R.Amedkar,Constituent Assembly of India Debates(Proceedings),Volume VII,Nov.4,1948,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vol7p1.html. ⑧B.R.Ambedkar,Constituent Assembly of India Debates(Proceedings),Volume VII,Nov.4,1948,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vol7p1.html. ⑨S.Radhakrishnan,C.A.Moore,A Source Book in Indian Pilosophy,Bomb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19-20,转引自姚卫群:“印度古代宗教哲学中的伦理观念”,《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81页。 ⑩[印]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6页。 (11)[德]韦伯:《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12)S.Radhakrishnan,The Principal Upanisad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53,pp.796-797,pp.809-811,pp.829-846,转引自姚卫群:“印度古代宗教哲学中的伦理观念”,《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82页。 (13)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摩奴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 (14)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摩奴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15)[印]凯塞·库玛·查克拉巴提:“从比较的观点看印度伦理”,《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2页。 (16)蒋忠新译:《摩奴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17)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摩奴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2、58、59、60、7页。 (18)[德]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9)朱明忠:“论甘地的道德伦理思想”,《南亚研究》,1988年第3期,第49页。 (20)张力:“论甘地思想中的苦行主义因素”,《南亚研究季刊》,1988年第4期,第43页。 (21)朱明忠:“论甘地的道德伦理思想”,《南亚研究》,1988年第3期,第55页。 (22)张力:“论甘地思想中的苦行主义因素”,《南亚研究季刊》,1988年第4期,第43-46页。 (23)朱明忠:“论甘地的道德伦理思想”,《南亚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24)Bhikhu Parekh,Gandhi: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8. (25)Bhikhu Parekh,Gandhi: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8. (26)彭树智:“甘地的印度自治思想及其国家观”,《史学集刊》,1989年第1期,第61页。 (27)Bhikhu Parekh,Gandhi: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64. (28)彭树智:“甘地的农村经济思想及其道德观”,《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第5页。 (29)黄心川:“甘地哲学和社会思想述评”,《南亚研究》,1985年第1期,第10-11页。 (30)彭树智:“甘地的农村经济思想及其道德观”,《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第6页。 (31)参阅Ananya Vajpeyi ed.,Righteous republic: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Ind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 (32)文富德:“略论尼赫鲁的经济思想”,《南亚研究季刊》,1989年第4期,第39-45页。 (33)Government of India,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2007,http://lawmin.nic.in/coi/coiason29july08.pdf. (34)[印]沙尔玛著:《印度教》,张志强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35)姚卫群:《印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0-244页。 (36)姚卫群:“印度古代宗教哲学中的伦理观念”,《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D4年第5期,第86页。 (37)参阅Bhikhu Parekh, Gandhi: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8)张力:“论甘地思想中的苦行主义因素”,《南亚研究季刊》,1988年第4期,第45页。 (39)[英]E.M.福斯特:《印度之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 (40)W.C Smith,Islam in Modern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p.75-77. (41)薛克翘:“印度独立后思想文化的发展特点”,《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第50页。 (42)朱明忠:“尼赫鲁的哲学观”,《南亚研究》,1998年第1期,第30-31页。 (43)彭树智:“甘地的印度自治思想及其国家观”,《史学集刊》,1989年第1期,第62页。标签:社会观念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甘地论文; 摩奴法典论文; 奥义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印度之行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