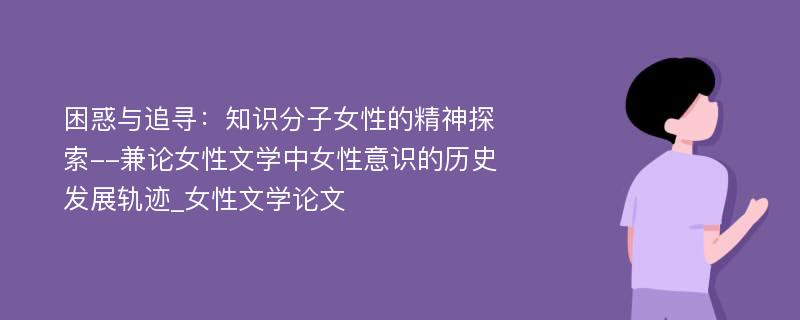
困惑与寻求: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兼谈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历史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轨迹论文,困惑论文,意识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坛上,曾涌现出一大批以切身体会来描写女性经验的女作家,她们以女性特有的心理感受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了一部部别开生面的作品。现当代人物画廊中,更摇曳着活跃异常、多姿多彩、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男性作家塑造的。而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往往把对女性的描写作为对整个现实世界反映的一个方面,通过这一内容,力求更全面、深入地表现客观现实的真实面貌;后者则不同,她们在其中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热忱和心血,把它视为世界的重心、现实的中心来描写和表现,倾诉了他们对人生、宇宙的全部感受、体验和思考。在这一类作品中,你也许会感到某种偏执甚至有时是乖戾,但你不能不为她们真诚的激情所感动、所征服,你将更真切地体味到女性的情绪和脉搏、人生的况味和真谛。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本文将以现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时期——“五四”(及其后续)时期和新时期,以这两个时期中一些描写知识女性卓有成效的女作家为代表,来探索小说作品中知识女性精神跋涉的轨迹。同时,通过对知识女性精神历程的把握,尝试从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看女性意识的演进。
1
中国妇女在那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不仅同许多男人一样遭受着政权、族权、神权的压榨,而且还要经受被压榨的男人的压榨,这种双重的生理的、心理的奴役,使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坍了旧中国闭关锁国的障壁,外来思潮的渗入与自身气候的成熟,使中国这块板结已久的干涸土地发生了大面积的骚动,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那样一场巨大的裂变,反封建、呼吁民主与科学和社会改革的呼声,使经历了漫长的夫权社会、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意识,也在此被震醒了。于是有了女性的期待、不满、向往与愤怒,有了女性的欢笑、哭泣、撞击与破坏……新思潮、新文化给沉闷的旧中国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唤起了一代青年的觉醒,其中,年轻的知识女性的觉醒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知识有如智慧之树的果子,拨开了她们心灵上厚厚的蒙昧尘埃,使她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以及自身的处境,探求这个奇妙世界并力图改变这世界的意识觉醒了,“夏娃”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伊甸园。不满于现实继而不安于现实便是女性们主体意识觉醒后的最初心态——这是精神探索的开始,也是被动而沉寂的女性生态的结束。“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是从两个方面开始的:一是对所处非人地位的经济的、物质的反抗,这是女性文学的最初收获;一是对被压抑的个性的精神扩张,集中体现在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讴歌上。于是,在“五四”时期,在“女人无史”之后的“有史”的开端,知识女性结束了被注释、被命名的悲哀历史,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有了形形色色的理想抉择与追求的方式,出现了沅君式的、庐隐式的、丁玲式的追求。探索与寻求一种合适而合理的生命方式成了精神之旅的第一层。作家们借各自笔下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女性形象宣示着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索,但同时又在不得结果的苦闷中彷徨、叹息,而这种彷徨、叹息更加显示着探索的扩展与深化,于是,这一切都否定着旧有的生活模式设计,而新的(不成熟的)生活图景开始在其作品中展现。
“五四”时期知识女性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是觉醒的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在沅君笔下,最先表现为“性爱”与“母爱”的冲突。
在中国,“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首先是对“专制”而言。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慈母》、《误点》里的女主人公在实现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意识外在的和内在的重重阻力,其外在阻力具体化为母亲对儿女婚姻的干涉,构成“性爱”与“母爱”的对峙与冲突。“唯有正当沅君女士的时代,那是一个母亲的爱和情人的爱相冲突的时代。”(注: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这是一种时代的冲突,必然化为这批刚刚飞出鸟笼在寻路的青年女子灵魂中的苦苦搏斗。
《误点 》中的女主人公清楚地意识到两种爱的冲突, 深切感受到在两种爱中选择的痛苦与矛盾。女子对于母亲的爱恋和天然的依赖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意识。母爱象征伟大、无私、高尚、圣洁。母女之爱除了血缘的关系,还有中国民族文化和亲情伦理意识的积淀。要冲破“母爱”而就“性爱”,对于新旧交替时期因袭着旧观念重担的知识女性来说,在心理上必然造成沉重的压力。她们在向旧势力冲决的时候,没有顾忌外界的阻力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勇于去完成“爱的使命”的“旅行”,却在“母爱”的心理障碍上顿足进而徘徊起来。
那个时代“母爱”的背后隐藏着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阴影。母亲对于子女婚姻恋爱的干涉,甚至仅仅“劝诫”,也都是事实上的统治中国数千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物化表现。“母爱”在客观上成了封建势力的精神化身。
从沅君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出,知识女性在求得解放的途中,不仅要迎战来自社会封建传统观念和势力的阻力,还要战胜自身传统心理的内在阻力,这是又一种冲突,这种冲突看起来不那么激烈但却更加持久,因而使她们求得解放的道路显得更加艰难。在母爱与性爱的交战中,知识女性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毕竟还是前进了。《旅行》中的女主人公是冲出了家庭,在外求学的青年学生,她携同恋人一起以“完成爱的使命”的旅行,向封建礼教发起了勇敢的挑战!在《旅行》中,已看不到“母爱对性爱”的直接钳制力。知识女性冲出家庭的勇敢精神是“个性精神”和“自我意识”得以强化的表现。
沅君式的知识女性们似乎不存在“价值追问”“理想选择”这样的心态,她们多半只拥有一个极明确、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要完成“爱的使命”,爱情成为这些知识女性们自身生命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殉爱的使命”在她们看来是“天下最光荣的事”,她们明确地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沅君以她颇具特色的艺术之笔展示出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那种坦白直率的描写和细腻深入的心理剖析比比皆是,它们深刻地揭示了女主人公们这种心理特征,“大胆无畏的写出一般女性不敢写的女性的毫无隐饰的恋爱心理”。(注:王哲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然而,作为刚刚从旧社会脱身出来的“新女性”,她们终究又摆脱不了母爱与旧的道德观所带来的负罪感。所以,浑身洋溢着叛逆精神的“我”即使有勇气和所爱的人一起去旅行,却又不住地自责自己的行为给母亲带来的痛苦。她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她们的灵魂却在不断徘徊,最后她们在极度的痛苦中选择了一条“牺牲生命来殉爱”的道路。沅君为她的知识女性们安排了一条近乎悲壮的道路,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实际上却是逃避——逃避现世、逃避压力、逃避来自于心灵的苦苦挣扎的苦痛。她们最终一无所获,既没有找到爱情的幸福,也没有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下的贤淑女子,沅君式的女性在结束生命的同时也结束了精神的继续探索。
沅君没能给她的女主人公们指出一条实在的出路,但她的作品已经展示了新女性的存在与不断成长,在冲破了“母爱”及在“母爱”这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掩盖的丑恶的封建家庭关系之网以后,知识女性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庐隐笔下,她们对爱情、人生发生了更为深沉的思考。觉醒了的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在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身上突出表现为个人理想与现实人生的冲突。冲突的过程加重了知识女性与社会的膈膜感,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并未得到社会应有的承认与尊重,在这种来自外界的压力下,她们蜷曲在“自我”情感的狭小空间,苦闷、彷徨起来,又不甘走回头路,结果陷入“游戏人生”又被“人间游戏”的悲哀之中,这是庐隐为我们塑造的“五四”时期的“时代儿”的旅历。她笔下的亚侠(《或人的悲哀》)、丽石(《丽石的日记》)、露沙(《海滨故人》)等,都是这种命运。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靠着“个性主义”武器,冲破家庭的桎梏固然不易,走出家庭,要进一步冲破社会上虚伪与丑恶织成的罗网更加不易。这是冯沅君笔下的知识女性在心理上没有估计到而为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遇到的现实。知识女性的希望之火被惨痛的教训灭为灰烬,她们“个人”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的一个个被否定,说明她们面前依旧存在着使她们的愿望与要求不被承认和尊重的强大的社会阻力,这在她们的心理上造成无形的重压,使之难以喘息,因而她们的苦闷、抑郁和伤感则是必然的了。“或人”们的悲哀,不仅在于国衰民赢,倍受欺凌;也不仅在于“眼睛所视,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的种种罪恶”;而且更在于青春的“性的苦闷”。亚侠接二连三陷入感情的漩涡中,欲拔不能,然而抢着“钓”她的“渔夫”却没有一个她心目中那天边、那海上飘来的红帆王子。她不甘被人玩弄,用“游戏人间”的玩世不恭与人周旋,内心却痛苦异常。人生的究竟“求不到答案”;“想放纵性欲”又不甘堕落,终于只有怀着“悲凄之感”,愤然跳湖。丽石的忧郁,从表面上看,是因好友沅青有了恋人而疏远了她,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条件反射:为什么她就遇不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如意郎君?然而受新思想洗礼的丽石,当然不愿听任“媒妁之言”的撮合,但自己又难将心事对人宣示,内心交杂着失落感和自卑感,只好“抑郁而死”。
理想与现实的悲剧性冲突,在露沙身上鲜明再现为“智情不调和”的矛盾。由于她幼时饱受冷刻环境的熏染,养成孤僻倔强的性格。她聪明、敏感、心思极深,仿佛已识破了“世界的谜”,但她又多愁善感,“极富于感情”。当她看到伙伴们“先后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的时候,她自己也陷入了与有妇之夫梓青相恋的感情漩涡。她一面告诫别人:“自爱还来不及说得着爱人家吗?”“何必求人了解?自己有时也不了解自己呢?”主张精神生活,一面又为“知情交战,苦苦不休”,感叹“人世的谜始终打不破”,而不得不自认:“至于平时故为旷达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呻吟,到这种关头,自然要为情所胜了……”,最后,她虽然携同恋人“逍遥海滨精庐”,也只不过是消极遁世之举,终究逃不脱悲剧命运。尽管在庐隐笔下显露出了理想在现实面前退缩的软弱性,但庐隐式的知识女性较之沅君笔下的知识女性还是前进了一步,她们已经从“爱情至上”的虚幻王国中走了出来,认识到“爱情也是靠不住的。”这虽然带有一些极端色彩,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促使她们从情感世界中抬起头来,看看这个广袤的世界,思索一些爱情之外的个人价值。但思想的局限仍然使她们不知去向。如果说沅君式的女性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中终于淹没于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中的话,那么庐隐式的女性们则在新的目标确定上感到无可医治的困惑,于是只有“一味放荡着,——好象没有目的地的船,在海洋中飘泊……”(《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们曾经试图走出“或人的悲哀”,结束灵魂漂泊状态,这种努力在1931年的《何处是归程》中仍隐约可见。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庐隐的心中仍是一片茫然。庐隐一直试图为她笔下的知识女性们确定一个目的地,但却一直没有做到。最后,这些人生路上无目的地可寻的人们,终于被磨掉了身上所有的锐气,在灵魂的极度疲惫中消失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种比沅君稍深一层的认识以及最后的幻灭,都是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庐隐也是一个在人生旅途上屡遭坎坷的苦苦的探索者。因而,那种浓厚的自叙传色彩,那种忧郁感伤的情调都构成了庐隐作品的鲜明艺术特色。
从沅君、庐隐的创作可以看出,女性意识最初的觉醒反映出女性意识对现实的理想化和主观化,使女性意识只限于表层的外在的觉醒上,而深层的传统意识没有根本性的触动。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仅处于历史的第一级台阶。但不管怎样,她们为新女性求得个性的解放,追求人的自身价值,对纯真爱情的大胆追求,发出了可贵的第一声,显示了中国的女性“并不是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鲁迅语)
人们不会忘记丁玲1928年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一篇充分地表现个性主义和新女性叛逆精神的杰作。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通过莎菲对追求“灵肉”一致爱情的失望而发出“叛逆的绝叫”,把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从中国古老的传统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向束缚女性思想发展的一切陈规旧矩作了大胆的挑战。如果说沅君、庐隐作品的女主人公的美学追求主旋律还是为寻找男人是无可非议的,那么丁玲的创作则不是以此所能概括得了的。人性觉醒,出路何在?丁玲以其睿智的思想和艺术彩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经历过“五四”潮流的冲击特别是个性解放思想熏陶的莎菲,挣脱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开始“人”的觉醒,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她要求合理的人的生活。但莎菲又和“五四”以来仅仅以个人的恋爱婚姻自由为奋斗目标的某些青年男女不同,她比她们走得更远,比她们要求得更多,虽然她还不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但她仍然追求得十分执著。这样,她就不可避免地和社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她也就必然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反叛情绪。可是,由于那一代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实际生活环境与思想现实所限,她还不可能找到反抗黑暗社会的正确道路。单凭个人力量,不可能和强大的社会相抗衡;而孤傲倔强的性格,又决定了她决不向黑暗势力妥协。这就使她陷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苦痛之中,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无以渲泄的精神苦闷。从莎菲身上,我们看到,她已不同于大多数青年知识女性仍把目光局限于争取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和单纯寻求知识的小圈子里,而是追求更远大的目标,虽然这目标并不明确,是模糊的、朦胧的、渺茫的。莎菲可以理智地处理自己的感情却又不知在爱情之外生命的出路何在,所以她的精神探索以到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消耗生命而告结束。在莎菲之后,丁玲的探索仍在继续。《一九三○年春上海》(一)中的美琳已经认识到“……她理想只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但是现在不然了。她们还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丁玲在这些女性身上都寄寓了一种非常真诚的希望。丁玲笔下的知识女性们似乎都坚信,在精神的漂泊之后必有一个理想的归宿在前面,尽管还不清楚这归宿是什么,尽管要获得需要付出艰苦与代价,但她们仍然坚信着。丁玲小说中女主人公,尤其是那些知识女性,美丽多情,孤傲倔强。在爱情上表现出女士的主动性和优越感。在她笔下,那些女人,比起男子来,更加勇敢、更加坚韧。丁玲发现并肯定了女性的独特价值和优势。她激扬了女性的灵魂,表现为一种女性中心意识。这些在丁玲作品的艺术表现上也都可以得到生动的展示。
沅君式的女性也好,庐隐式的、丁玲式的女性也好,她们既然做了“铁屋子”里面率先觉醒的女性,就必然地去寻求冲出这压抑环境的办法。但是怎样“打破铁屋子”以及冲出这“铁屋”之后又该怎么办,却一直是她们心中纠缠不清的问题。探索是不可避免的,但探索过程中的困惑、迷茫也是不可避免的。二、三十年代的这些女作家们,虽然她们无法为自己找到生命的真正出路,虽然她们对于女性意识的探索还只是处于第一级台阶,但她们开创了以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审视、表现自我生存世界的崭新历史,让中国女性一向最为隐秘的主观内心世界,得到了最客观的呈现。她们把审美的专注目光从传统的外在世界转向女性的内心情绪世界,从而使中国女性无限隐秘的精神内海,第一次毫无顾忌地、赤裸裸地奔突到了小说作品中,为读者展示出了一个全新的女性心理波动的情绪系列。在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里,女性的情绪世界已经不似传统小说那样,只是一角的位置,也不只是为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才采取的一种艺术手段,而是膨胀流贯到全篇。作者重笔挥洒的已经不是人物的活动史,而是“心史”。当然,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提供的女性心理情绪系列,往往只是处在一种“纯感觉”的状态——即还没有达到理性分析的心理观照活动,还未步入思想的阶段。但不管怎样说,以沅君、庐隐、丁玲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给文坛辐射了许多新热。
“五四”已经成为历史,“五四”时期的知识女性也作为这巨册史书中辉煌的一页被时间之手轻轻翻过,但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仍在继续,因为只要存在肉体的囚禁,心灵的困顿,存在对自由的追寻,这种探索就不会停止。
2
“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在新潮流的冲击下,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但随后的中国半个世纪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使“女性文学”未能沿着前人指引的路标走下去。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女性文学呈现出将个人意识融入集体意识、女性解放汇入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的趋势,而建国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中,个体意识更是作为一种异端而被排斥和批判,女性意识被冷落也是很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冰川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女性文学”直到70年代末才再度出现并逐步崛起。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个性意识又成为社会瞩目之点,女性意识也重新复苏。历史便从这里重新起步了。如果说20年代“女性文学”的崛起,表现了知识女性从觉醒到苦闷困惑的精神状态的话,那么,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最终远远地超越20年代的“女性文学”,表现了一种成熟和发展。
新时期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觉醒不需从经济物质开始,而一下子楔入精神领域。固然,女性意识的第一声喘息,与“五四”时期女性意识指向一致,但它毕竟是在历史的辅垫下重新起步的。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抗衡和挑战,还是对女性内部的审视和反思,都使新时期的女性意识在恢复“五四”精神的同时又超越了历史。女性意识的恢复和超越顺从了历史开拓的两条线索继续展开:一是对外部世界的剖析和观照;一是对女性自身的内部审视和认同。内部和外部的探索达到一定程度并交融互渗后,便使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达到了成熟和发展。
新时期女性文学向外探索,首先是从爱情问题开始的,尤其是以大量关于知识女性爱情婚姻的作品作为主导。表面上这似乎仅是对几十年、特别是对十年动乱中人性中最闪光的部分——“爱情”的被约束和扼杀的反叛。究其实,却仍是向传统的封建观念的挑战。与“五四”不同的是,“五四”是以包办婚姻的家庭为反叛的目标,而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则是从对无爱婚姻的弃绝和对爱的婚姻的追求起步的。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问世之初,在中国大地上引起轩然大波。在80年代初,在“人”的问题为主潮的背景下,男女主人公违背“常规”的爱情方式对于旧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冲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小说写了两代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和憧憬。母亲为了一份不能实现的爱而生活在精神的折磨中,女儿因为没有爱而不谈婚嫁。作者发自内心地感叹:“如果我们能够互相等待,而不糊里糊涂地结婚,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哟!”虽然这类感叹在无望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但对爱情的呼唤与追求,使这篇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一经复苏,便具有高屋建瓴之势,在社会上引起哗然。在爱什么和怎么爱的具体展开中,我们看到了张洁苦心经营的当代知识女性的人格构想。无疑,张洁不同于“五四”女作家之处,是她对女性的思考,开始就从女性本体出发,而不是在女性之外。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张洁采用了清醒的女性意识指导之下的全新视点——女性审美视点。它体现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更体现出她们作为人类一半的女性的自觉。这一视点以女性的自审意识为基础,用自觉的女性眼光,以女性的立场和姿态,描写女性的生活,揭示其生存的困境,展示其奋斗的风采。
这一时期,王安忆、张抗抗也无不吟唱着真善美的歌。王安忆雯雯系列小说中纯情似水的雯雯之爱,是一幅透明的画,一首无声的歌,是至高无尚的爱,无边无际的爱。而《北极光》中芩芩所憧憬的象闪电、象火焰般绚丽的“爱情”;宗璞用大提琴营造的知识女性华彩辉煌的“弦上的梦”(《弦上的梦》)……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正是这样在它一展新姿之时便提出了最基本的实际上是恢复和获得女性的最起码的人的权利的要求。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萌生、觉醒,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追寻理想爱情,而是放开眼界,发出“女人不是月亮”的抗争,明显转向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追寻。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经获得人身的独立解放,她们最先生出了一种希冀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生存价值的强烈愿望。因此,这个时期的小说,一方面表现了她们为自身价值的实现,独立人格的确立,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不甘退却,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另一方面描写了奋斗途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事业与生活相矛盾所带来的烦恼和痛苦。这就使新时期女性文学呈现出比其他任何时期的更高层次,也更充满艰难困苦的图景。
当代知识女性从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为展示自身的价值,参与到社会竞争的激烈挑战中,知识女性凭其卓著的才智和特有的灵性不仅可以和男子在同一片天空下平等竞争,而且很多知识女性已远远走在一般男性前面,她们再也不会做个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小女子了,再不用依附男人过活了。然而妇女的彻底解放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知识女性在现实面前遇到的除了艰难的社会生活竞争之外,更有一连串的情感烦恼和精神痛苦。
还是张洁,如果说,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她是试图营造一个爱的天国的话,那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这种浪漫主义开始淡化。在《方舟》中,张洁对女性的角色困境有了更加深切的体察。《方舟》用女性在生活和事业间的矛盾表现了现实生活的严酷和冷峻。也正如小说卷头语所揭示的:“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社会对女性的观念认识聚着厚重的传统观念的雾障,这股雾障随时可以压迫事业女性。荆华这位思想、学识都直压须眉的知识女性,不得不过着清贫而又孤独的生活;柳泉在专注于工作时却陷入男女间的桃色纠葛中以及梁倩面对繁杂的工作倾其全心而被讥笑、嘲弄的苦楚,都构成了事业女性在生活中的灰暗色调。尽管现实并不全同于《方舟》所展示的,但女性在事业中的艰难选择确实反映了社会意识的文明层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用职业等外在形式来衡量,而是以观念意识的认识程度来确定的。当着整个社会意识尚在变革之时,对女性的社会认同也不会奢求先行得到进化;当着女性意识先于整个社会意识的文明之时,便衍生出女性意识与整个社会意识的错位,事业与生活矛盾的痛苦。女性若要战胜这些现实、雾障和痼疾,必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作者借梁倩、荆华、柳泉之口无拘无束、痛快淋漓地渲泄了对世俗社会的怨愤、对世俗男人的鄙夷甚至诅咒。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唯一和最大要求是“贤妻良母”,而当觉醒的女性试图摆脱男权文化对自身身份的限定时,她们和男权中心文化的冲突就产生了,她们自身的角色困境也产生了。张洁的女人们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女性除了贤妻良母的角色,不能有其他社会角色?张洁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当女性想要寻找自身的多重定位时,有那么大阻力和困扰?这种阻力和困扰来自哪里?正是在这些不断出现的困惑驱动下,张洁的笔触一改当初的抒情与理想化,逐步走向冷峻乃至某种程度的冷酷。
张辛欣是另一个从创作伊始便自觉立足于女性的视野,从女性的视角去描写生活、刻画人物形象的女作家。其诸多作品均执著于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表现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苦恼和抗争,其女性意识的流露自觉而强烈。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最后的停泊地》等小说中对女性生存困境和感情困境作了深入的思考。在《在同一地平线上》,张辛欣思考的是既然男性和女性已处在同一地平线上,即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社会问题和生存问题,那为什么对女性却又有别一样要求呢?——如同样都要挣钱养家,同样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那为什么男性对家务可以不管不顾,而女性非得照顾家庭,甚至在必要时为男性牺牲自己的工作、事业呢?这公平不公平?而造成这不公平的又是什么?与张洁一样,张辛欣也陷入了困惑。
在《最后的停泊地》和《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张辛欣坦诚地正视了女性之作为女性的特质,及女性的真正的感情需求。张辛欣一再承认,在感情上,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更纤细、敏感、细腻,她们更时时渴望着找到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可是问题在于,一些优秀的女性往往错过了另一半,找不到最后的停泊地。一方面,残酷的社会生存境况使每一个人包括女人不得不努力成为优秀者和强者;另一方面,当女人优秀起来后,她很可能就面临着独自漂泊、无所皈依的情感现状,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由于张辛欣的作品多半是产生于冷静的思索之后,是某种观念的思想的结果,因此或多或少地带有“图解”即“主题先行”的意味,这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略受影响,但这些并不能削弱她作为“中国女权主义文学”(让我们姑且在此提出这样一种不够确切的概念)在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的身份。
应该说,新时期女性文学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还是不完全等同的。但是从作品中所流露的女性的情感焦虑,却使我们看到新时期女性文学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认同之处,即传统的女人的角色与现代人生之间的冲突在女性心理上造成的不平衡及其压抑感。当然,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显而易见。早期女性文学更富于“五四”时期“凤凰涅槃”的浪漫色彩,寻求在激烈与彻底的反叛中获得再生。这种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女性与环境以及与外在于女性欲望的角色规范之间的张力,因而表现得犹如江河直下,一泻千里。新时期女性文学则更多带有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点上的种种困惑,因而更多地表现为女性自身内在的矛盾冲突,甚至形成她们精神上的危机感。一方面她们要冲出传统的角色规范,以前辈女性难以达到的姿态立足于社会;而当她们终于得到那成功得令人晕眩的一刻,茫然回顾,周围却是一片失去生机的寂寞沙地。
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第9页。 )女性文学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剖析,认识到要想保持女性的独立和自强,并不能寄托于社会“女士第一”的绅士精神,而应来自社会深层意识的彻底觉醒和成熟,也来自女性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女性意识觉醒和成熟的根本,在于女性本体意识的认知程度。于是,女性意识在对外部探索之后转向了对内在世界的审视与反思。
如果说“五四”知识女性一直在为灵魂的自由寻找归宿又因不得归宿而到处漂泊的话,那么新时期的知识女性则是从抗拒与理想相悖的归宿而开始,别无选择地再一次踏上了精神之旅。之所以说她们拒绝接受与她们理想不符的归宿,是因为新时期女性们第一个想要远离的就是给人温暖与享乐的“家”。当然,她们心目中的“家”代表了她们所向往的两性和谐组建——互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没有矛盾的家庭。但是她们也明白,这种两性完全的结合,由于存在着两性世界的隔阂与对立,由于人仍然没有实现彻底的解放,还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在她们笔下有许多“无家可归”的知识女性,钟雨、荆华、柳泉、梁倩即是。她们或是不能与所爱的人共建家庭;或是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与她组成家庭的爱人,只有孤独一生、漂泊一生。但是这些女性们却不甘心在灵魂的孤独无依中流浪终生。因此,她们拼命地完善自己,以求为自己营造一个精神的归宿。“妇女,要争得真正的解放还需要从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她自有治疗悲哀的法儿,那就是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认识——对人类、对社会、对朋友,你是有用的。”(注:张洁《方舟》。)这种女性自身价值的自信,无疑会增强女性的自尊或自强意识,从而生发出一种向上的勇气和信心。黄蓓佳的《请与我同行》、《这一瞬间辉煌灿烂》、程乃珊的《女儿经》、张蔓菱的《唱着来唱着去》都体现出女性因自审而不断发挥自身价值和面对生活重压的信心。在剖析和自责中认识女性内在的尊严和价值,进而从女性自身的价值里寻求与外部世界相抗衡与合作的勇气,建设一种新女性的尊严和人格。用女性的价值和尊严,以女性的自我认同与整个社会的认同相统一,并最终使女性人格的价值全面实现。陆星儿的《啊,青岛》写了因家庭的错位生成了榕榕与丈夫的隔膜,在经过自身的努力以后,榕榕终于弥补了夫妻感情的裂痕,在人格尊严平等的位置上,保持了家庭的平衡。从中可以看到女性已经彻底摆脱掉对男性的依附,显示了“哪怕失去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也要保持自己尊严”的决心和操守,显示了女性战胜生活和拥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在陆星儿及其同代人一直试图为女性们寻找一个最佳的生活方式以解决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冲突之后,陈染、陈洁、嵇伟、张欣等后新时期占据文坛的新一代女作家的目标却是为知识女性们孤独迷惘的精神寻找一个理想的休憩地。她们笔下的知识女性比之张洁与张辛欣的知识女性少了许多传统的负累。她们洒脱、自由,可以率性而行,有充分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身处广州经济特区,张欣较早感受到走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脉搏。《绝非偶然》中的何丽英是一位被称为“白领丽人”的职业女性,大学毕业被发配到外贸公司当打杂的,她毅然辞职进了私营广告公司,一切靠自己奋斗,被老板炒鱿鱼之后依然独立地寻找出路,张欣不仅写出了都市职业女性的艰辛和她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而且写出了她们不屈不挠地独立奋斗的精神,还写出她们在爱情婚姻中恪守独立自主的人格尊严。何丽英注重夫妇之间相互信任和尊重,面对丈夫的婚外恋,虽痛苦,但决不纠缠,而让丈夫自己去选择。张欣以敏锐的直觉感受到了,处于谋生奔波和竞争中的现代女性,不断发展着、强调着个性独立,似乎越来越少那种古典式的充满诗意的相互依附的忘我痴情了。唯其如此,她们方拥有完全不依赖于男子的包括精神在内的真正独立。她们那种独立奋斗的女性精神,以及面对生活创痛、精神压力时的冷静承受,比之于80年代张洁、张辛欣笔下追寻自我价值的女性那种背负事业和家庭的十字架的沉重,显然是一种新质。它意味着女性开始走向真正的独立,真正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参与竞争,实现女性自我价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然,这一实现过程仍将是相当漫长的。
从张洁笔下的钟雨、梁倩、柳泉、荆华到张辛欣笔下的“她”、到张欣笔下的何丽英,这是知识女性形象塑造中的一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困扰着当代妇女的许多具体的矛盾和问题。这是一群永远在寻找精神家园的知识女性,她们有着深重的精神痛苦,但是在痛苦的外壳包裹下却有着不死的追求和渴望。正是这种追求和渴望使女性意识经历了对社会的外部探索和剖析、对内在的审视和反思之后,使女性意识在漫长的探索道路上终于趋于成熟。正如刘西鸿在《月亮摇晃着前进》里借若愚之口表明的:“她是女人,她可以做妻子,可以生养孩子,可以烹饪,可以编结,可以裁剪,但在她能前进的时候她理应前进,她首先要前进。”“钱、财、丈夫都是身外之物,不是自己的。只有事业,自己的事业,才和自己同在。”这里对女性自我的认识,可谓是冷静、客观的。在承认女性天赋之责的前提下,并不轻松地意识到女性应该先争取到独立和自强。这种对现实的冷静分析,透露出新一代女性的洒脱。作品中所充溢的女性自我意识,女性的自尊和自强不是偏激的外在索取,而是冷静的内在自信。
综上所谈,新时期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充分体现了新的发展时期的时代特点。它既有继承“五四”反封建传统意识的历史深度,又有千年因袭观念中挣扎的困窘,更有超越“五四”向着更为成熟的自由而美丽的女性天地飞翔的趋势。女性意识发展的最高指向也即是人的最高指向: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女性的痛苦、希望和理想绝不是由女性自身可以孤立完成的,她将需要全社会的辅助和努力。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尽管在前行途中会有停顿、会遭到挫折,但最终她们必将跋涉下去,去追寻作为人的自由存在的境界。
这便是关于人的精神历程的故事,这便是女性意识发展的过程,这些故事是由饱经苦难的女人们完成的。但是人类的精神发展永远不会走向完结,一条小路被荒草淹没了,那么旁边一定会有另一条小路悄悄地伸展出来。
寻求没有完结,痛苦也没有完结。一切仍在继续之中。愿整个人类不断文明进化,愿有着“人类心灵美好一半”的女性意识文明成熟!
标签:女性文学论文; 女性意识论文; 丁玲论文; 庐隐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爱情论文; 张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