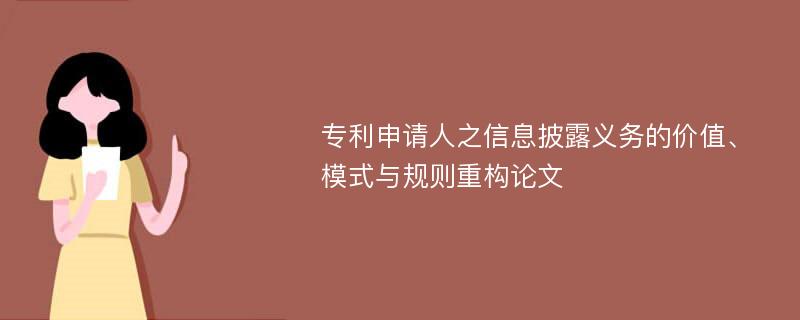
专利申请人之信息披露义务的价值、模式与规则重构
杨德桥
(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10)
摘要: 信息披露义务的科学构建和恰当履行,有助于降低审查信息的搜索成本,有助于提升专利申请和审查的质量,有助于建立诚信的专利运行体系。信息披露义务的立法模式有强法律责任、弱法律责任和无法律责任三种。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属无法律责任模式,这导致我国专利信息披露义务的虚置化。应当从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应为披露的内容、披露的时间和方式等方面重构我国专利信息披露制度,同时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
关键词: 专利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法律责任模式;信息披露规则
随着专利申请量的急剧增加,近年来我国专利行政机关的审查任务愈发繁重,审查员用于个案的审查时间日益缩短,难以保证审查结论的质量。提高专利授权质量,防范问题专利的产生,进行有效的专利审查是最为关键的一环[1]。专利审查的基础是进行现有技术等关联信息的获取。审查员只有掌握了专利审查所必须的信息资料,才有可能形成高质量的审查结论。信息不足是导致专利不当授权的重要原因[2]。理想的做法是建立一整套机制保证审查员能够获得所有与授权条件有关的现有技术文献[3]。在现有的专利审查实践中,专利审查员获取审查所必须的信息资料,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作为最了解与专利有关信息的发明人、申请人或专利代理人,却未能在提供专利审查信息资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专利法虽然规定了专利申请人负有提供审查所需的信息资料的义务,但是由于没有规定义务不履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加之该义务可能和申请人渴望获取专利权的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潜在冲突,在专利审查实践中该义务呈现出虚置化的状态,未能发挥出应有效用。参酌国外法例的可资经验,重置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明确该义务的法律约束力,对于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若再考虑时间跨度,我们以文献数量与时间跨度之比来说明问题,则显得更为直观与合理。宋至明中叶跨度六百余年,总计30部左右。其中宋代近320年,十余部(彭忠德言“12种”);元代近百年,共7部;明中前期190年左右,十余部;晚明跨度八十余年[注]③本文所言“晚明”,指嘉靖三十九年(1560)至崇祯十七年(1644),计84年。,三十余部。据此笔者统计,晚明时期官箴书的“生产”速度约为:宋至明中叶平均速度的6.5倍、宋代的8.5倍、元代的4.5倍、明中前期的5.5倍。当然,这些具体数字绝非科学与客观,在此只是为了更加直观地表明,晚明官箴书的数量发生了骤增。
1确立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的价值考量
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专利申请人应当将其所知悉的、对判断其申请的可专利性有重要影响的信息资料完整地提供给专利行政机关,供专利行政机关在审查申请的可专利性时作为参考。专利申请人是知悉与发明有关信息资料的主体之一。专利审查所需信息资料在由审查员检索获得的同时,规定专利申请人负有相应的信息提供义务,对于节约信息搜索成本、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建立诚信的专利运行体系均具有重要价值。
1.1 有助于降低审查信息的搜索成本
可专利性审查的中心任务,就是将专利申请书中披露的信息与审查员所检索到的相关技术信息进行审核比对,以确定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创造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是否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对象,说明书对发明创造的公开是否充分,等等。审查员所掌握的对比信息的充足性,常常从实质上影响着审查结论的可靠性。为了提高专利审查的质量,专利审查员必须要花费相当的时间进行对比信息的检索,专利行政机关要花费巨额的费用建立和维系检索数据库。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分析,美国专利商标局为每项专利申请进行现有技术的检索平均花费约5 000~7 000美元[4]。这些费用最终会以专利申请费的形式转嫁给申请人承担,或者由公共财政予以填充。专利审查员通过检索所获取的对比信息中的相当一部分,往往已经掌握在申请人或发明人手中。在现代专利申请的主体结构中,职务发明创造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职务发明创造也占据了77%以上的高比重[5]。职务发明创造不同于基于个体兴趣的非职务发明创造,往往都是系统化科学研究的结果。职务发明人一般占有与发明创造相关的大量现有技术资料,最了解与发明创造有关的信息资讯,对于其发明创造的优势和缺点也最为熟悉。职务发明创造人完全具备将专利审查所需要的信息资料提供给专利行政机关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发明人或申请人缺乏将相关技术资料,尤其是那些不利于其申请可专利性成就的技术资料,提供给专利行政机关的内在动力。因为这样做往往意味着降低其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概率,不符合其垄断发明创造技术市场的期待和利益。如果将向专利行政机关披露与专利申请有关信息规定为专利申请人一项法定义务并设定相应的法律效果,无疑将会敦促专利申请人向专利行政机关积极披露相关的信息资料,从而有助于减轻审查员的信息检索负担。同时,由于专利申请人或发明人在专利申请时已经掌握了与发明创造可专利性有关的信息资料,设定其向专利行政机关提供这些信息资料的义务也不会增加其经济负担。而且在发明人原本就掌握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要求审查员独立地去搜索这些信息,显然是一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6]。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没有增加申请人的经济负担,并相应地减轻了专利审查员的信息检索成本,故从总体上来讲有助于降低专利审查信息的发现成本,并最终降低专利制度的运行成本,减轻专利申请人的经济负担。
1.2 有助于提升专利申请和审查的质量
专利审查的质量通过专利审查结论的可靠性来体现,也就是说,无论最终做出的是驳回决定还是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其结论都能够经得起辩驳和检验,符合专利法所规定的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在司法程序中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专利审查结论的可靠性由专利审查过程的严密性来保障。专利审查过程的严密性,一方面依赖于专利审查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专利审查员所能够获取的审查信息的充足性。虽然审查员可以通过专利局的数据库进行审查信息的检索,获取在先专利和科技期刊方面的信息资料,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与在案专利申请有关的信息资料通过专利局数据库无法获得的情况。例如非正式出版物、未纳入电子数据库的出版物、产品说明书等审查员不易接触的资料所记载的现有技术,还包括那些不属于现有技术但是对专利性审查有重要价值的信息,例如国外同族专利申请的结论、与该专利申请有关的诉讼信息等。所以有相当存量的非专利技术信息审查员难以在现有数据库中寻找,往往只能仰赖申请人的提供[2]。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申请人和审查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审查员所能获得的相关信息越广泛,审查结论越具有可靠性。在美国专利法看来,设立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力争授权有效的专利[7]。也就是说,力争做到符合授权条件的一律授权,不符合授权条件的一律驳回,努力维护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两方面的利益,精准地实现专利法确立的价值目标。
申请人对专利行政机关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为多数国家专利法所肯认。但是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是否需要承担以及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不同国家专利法的规定又存在重大的不同。法律责任一般被理解为违反法律义务所承担的不利后果,体现了国家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或法律秩序[17]。法律责任是法律义务得以实在化的手段。根据法律责任的不同,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可以区分为如下3种不同的立法模式。
1.3 有助于建立诚信的专利运行体系
构成“不正当行为”,除了信息足够重要之外,还必须存在欺骗专利行政机关的意图[22]。这是因为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行为”并不是一项纯客观观察,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也不存在一个必须完成的固定量值,所述信息对申请人来说必须是“已知的”才会产生披露义务。专利申请人并没有确定性的义务要去进行现有技术的检索,去寻找并找到与可专利性实质相关的信息。不过,“一个人不应当为了避免对信息或现有技术的实际知晓而假扮无知,或者忽视很多对可能存在重要信息或现有技术的警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就构成了‘本应知晓’的因素[23]。”“基于未尽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如果该重要信息属于申请人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则可据此推定其具有欺骗意图[24]。”故意是一种主观心态,颇不易观察,故如何证明存在欺骗专利行政机关的故意常常成为这一要件判断的难点。在以“不正当行为”作为抗辩事由时,被控侵权人往往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申请人具备欺诈故意[18]。因为能够证明有意欺骗的确凿证据很少见,所以美国法院一般都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推断意图的存在。但信息的重要性程度特别高的时候,这种推断尤其合适。这遵循重要性与意图这两项基本因素之间的(适当的)方向关系。所遗漏或虚假陈述的信息越重要,证明存在不正当行为所需的意图要素的标准越低,反之亦然。“在成立不正当行为的判断中,申请人虚假陈述或隐瞒的信息越重要,就需要越少的证据来证明意图的存在[25]。”但是,推断意图的证据还必须符合“清楚且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如果对不正当行为的指控是建立在申请人未向专利局披露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的,则“必须采用清楚且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该申请人决定故意隐瞒已知重要对比文件[26]。”此外,“仅仅存在足够的证据,并且根据这些证据可以合理地作出该推断仍是不够的,这个推断还必须是根据这些证据可以得到的最合理的唯一推断,才能满足清楚且具说服力的标准[27]。”在既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间接证据可以支持的情况下,不能作出有关意图的推论[13]410。如果申请人由于过失,甚至是重大过失,未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不足以径直认定存在欺诈专利局的故意。CAFC在一则案件的全席判决中指出:“‘重大过失’被用来指代多种行为类型。然而,只有对全部情况都加以考虑后才能对特定行为进行定义。我们的观点是,将特定行为认定为‘重大过失’的本身并不能推定存在欺骗故意;必须要结合所有证据,包括证明存在诚信的证据,对涉案行为进行审查后显示具有足够的归责性,才能认定存在故意欺骗意图[28]。”在美国专利法上,不正当行为被视为是一个法律问题,因此通常应当由法官做出判定。当然,法官也可以授权陪审团听取与“不正当行为”中的信息重要性和欺诈意图相关的证据,并提出建议;或者,经当事人协议一致,将不正当行为事宜交由陪审团做出判定[29]。一旦“不正当行为”被认定,申请人将会面临严厉的处罚措施。根据不正当行为原则,如果申请人故意提供虚假的实质性事实,或者隐匿实质性信息,那么其所获得的专利将被判定为无执行力[30]。
2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的立法模式
为专利申请人设定信息披露义务之所以有助于实现专利法的价值目标,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对专利权人来说,承担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助于增加所获专利权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专利申请人在专利申请的过程中,为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会尽可能向专利行政机关披露与可专利性审查有关的信息资料,专利审查员做出专利授权时所考虑过的信息资料比专利申请人不承担该义务时要更加充分,也就说此时的专利授权是在更为严格甄别的基础上做出的,自然其可靠性也就会相应提升;同时,由申请人提交给专利局的这些信息资料由于在专利审查的过程中已经被官方正式考虑过,在专利授权之后,这些信息资料被其他人用作现有技术以无效该专利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故,在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存在的条件下,专利授权的稳定性更高,也就更有利于专利权人利益的维护。其次,对社会公众来说,由于申请人负担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向专利行政机关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其故意进行误导性陈述或重大疏忽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从而有助于避免其披露错误的或者不准确的信息,保证专利授权的质量和专利信息的品质,最终有助于社会公众对现有技术之自由使用的公共利益[8]374。从信息披露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果来看,该制度更重要的作用可能还在于其能有效阻止不符合授权条件的专利申请的提出,从而能够在源头上控制专利申请本身的质量。有国外学者对上千件专利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专利审查员很少依据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做出缩小专利权范围或驳回专利申请的意见,审查员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检索结果做出驳回决定[9]。也就是说,该制度在帮助专利审查员做出驳回决定上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所以有学者据此认为我国不但不应当强化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最好在未来的专利法修改中明确废止该制度[3]。该义务存在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它的威慑作用,它有助于打消那些妄图通过欺诈等不正当行为就明知可专利性存在问题的发明创造提出专利申请的念头,从而在源头上提升了专利申请的质量。
我国专利法也建立了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了申请人负有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规定在专利法的第36条。该条第一款规定,发明专利的申请人在请求进行实质审查的时候,需要提交申请日前形成与其发明有关的参考资料;第二款规定,如果该发明专利申请也在国外提出过,那么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国外专利局的检索资料和审查意见,若申请人未能按照要求提供,其申请将被视为撤回。可见,我国专利法为两类不同情况的信息披露要求,规定了各自不同的法律后果。对一般专利申请的信息披露要求,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对于已经在国外申请的同族专利申请,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专利法释义,《专利法》第36条的立法目的在于,敦促申请人提供其所掌握的信息资料,减轻专利局的工作负担,提高专利审查的效率和质量[38]。《专利法实施细则》对专利法中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作出了相对更为细化的规定,具体体现为对说明书应当包含内容的说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7条第1款第2项规定,说明书应当包含“背景技术”的内容,“背景技术”应当“写明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和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有可能的,并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就是对现有技术披露的要求。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文件如果不符合“细则”第17条的规定,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44条的规定,其申请视为撤回;但是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3条的规定,却不属于驳回申请的事由。《专利审查指南2010》未规定对申请人现有技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的审查方法,反而规定审查员“不必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据”,如果申请人不同意审查员的意见,由申请人决定“是否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39]”。这意味着在专利审查实践中,审查员并不会对申请人现有技术披露情况进行重点审查,更不会据此作出对申请人不利的决定。在我国的专利审查过程中,审查员主要还是依赖自己的力量来搜集现有技术情报并据此作出审查决定。
所谓弱法律责任模式是指,申请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可以成为专利行政机关驳回专利申请的理由,但是一旦获得授权,不得以在专利申请过程中违反披露义务为由对专利权不予执行或宣告专利权无效。弱法律责任模式下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强法律责任模式下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对于违反信息披露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则明显要轻于强法律责任模式。弱法律责任模式的代表为日本专利法和德国专利法。《日本专利法》第36条第4款第2项规定:“如果发明是文献公开的发明,欲获得专利者必须说明其在专利申请之时已经知晓的文献公开发明所刊登的刊物的名称以及其他与文献公开发明有关的信息的出处[31]。”也就是说,根据日本专利法的规定,如果专利申请人在专利申请之时知晓与其申请有关的表现为出版物形式的现有技术,则应当向日本特许厅做出说明,指明文献的出处,虽然无需提交文献的复印件[1]。《日本专利法》第48条之7规定:“审查官认为专利申请不符合第36条第4款第2项规定的要件的,要向专利申请人发出通知说明此事,指定一定期间,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意见书。”也就是说,如果日本特许厅发现申请人未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则有权利要求申请人就此作出解释说明或进行补正。《日本专利法》第49条第5款规定,“根据前条(第48条之7)规定发出通知时,专利申请所做的说明书的补正或提交的意见书仍然不满足第36条第4款第2项规定的要件的”,“审查官就该专利申请,必须做出拒绝授予专利的审查决定。”也就是说,在日本专利法上,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属于驳回专利申请的法定事由之一。《日本专利法》第123条集中规定了可得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的事由,但是该条并未将违反第36条第4款第2项所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列入,说明在日本专利法上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获得的专利权的效力不受影响。就日本专利法对信息披露义务的立法理由,日本学者田村善之论证到:“在提交专利申请时,如果存在申请人知晓的文献公知发明,应(在说明书中)记载该出版发行物的名称及相关信息的出处。为了实现审查的高效率,《专利法》要求(申请人)承担先行技术的开示义务(2002年修改)。在该义务规定的违反问题上,尽管申请人会收到审查官违反该规定的事先通知(《专利法》第48条之7)或成为拒绝审查之理由(即事前通知后的补正、被要求改善而未改善的,《专利法》第49条第5项),但由于在审查终结后诱发纠纷发生将违背专利制度之宗旨,所以该情况被排除在异议申请理由和无效理由之外[32]。”虽然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获得的专利权不容否认,但是并不意味着不诚信的申请人就此可以高枕无忧。根据《日本专利法》第197条关于“专利欺诈罪”的规定,如果申请人系通过故意隐瞒现有技术或者递交虚伪材料而获得专利授权,则要受到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的刑事处分。专利欺诈罪侵犯的是国家法益,因此在日本该罪是非亲告罪。只不过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罪名的案例非常稀少[33]。所以,在日本专利法上,对于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主要制裁手段还是在专利审查阶段的驳回专利申请制度。
2.1 强法律责任模式
申请人应为披露的内容受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条件的限制。首先,从主观上来说,申请人只负有披露其所知悉信息的义务,而不包括那些不为其所掌握的信息,无论这些信息对该专利申请来讲有多么重要的价值。信息披露义务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给申请人设定一项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检索义务,而是要申请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事——不隐瞒、不虚构。因为信息披露义务是为所有类型的申请人设定的,无论他们是严谨的科学技术专家,还是嬉戏的发明爱好者,虽然他们未必都有能力进行现有技术的检索,但是他们都应该是诚实信用的专利申请人。遵照科学原则行事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秉持诚信原则行事则不应当有例外。当然,在判断一项信息是否已经为申请人所知悉的时候,往往还要采取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方法,借助于该信息本身的重要性、申请人自身的客观条件和申请所处的环境来综合决定。在专利审查和司法实践中,“应当知悉”往往就是“知悉”的代名词。为了避免申请人陷于不利境地,借鉴美国专利法的规定,在认定申请人“应当知悉”时,应当采取“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一较高的证明标准。其次,从客观上来讲,申请人应当披露的只是那些足以影响可专利性判断的重要信息,而不包括那些只与申请有所关联的泛泛信息。所谓“重要信息”指的是那些构成专利权无效初步证据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未必最终能够无效掉该专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构成“重要信息”的主要是那些专利申请的负面信息,一般不包括积极证成专利权的信息。从信息的范围上来讲,以现有技术信息为主,但是不局限于现有技术信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Critikon一案中,确立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必须要向USPTO披露的内容不只限于现有技术,还包括申请人已知的对可专利性有重要作用的全部信息[43]。CAFC之后曾多次重申这一原则:披露义务远不止USPTO《专利法实施细则》中所规定的范围,而是应当延伸至“在决定申请是否具有可专利性时任何理性审查员认为的重要信息[44]。”不属于现有技术的信息范围仍然十分宽泛,通常包括非在先技术的文章,竞争对手先前的专利申请,在发明者专利申请日前的产品许诺销售,被省略的测试结果,与本专利申请相关的专利申请的诉讼程序,可专利性所依赖的实验详细信息,描述在先技术的笔记,以及在相关的专利申请中,其他审查员所做出的驳回专利申请优先日期的不利裁定,等等[29]。总之,只要足以影响专利申请的可专利性判断,就属于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范畴,而不仅仅包括现有技术信息。所以,在美国专利法上该义务被称为信息披露义务,而不是像有些国家专利法那样称之为现有技术披露义务。
由于知识产权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获取知识产权的欲望也就前所未有地被调动起来。于是在知识产权获取的过程中,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蠢蠢欲动。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外源驱动”现象[10],更是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Williamson[11]认为,所谓“机会主义行为”是指,行为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实施的偷懒、欺骗、误导等有悖诚信的行为。从法律上来讲,机会主义行为是指,行为人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损害制度价值和制度目标的行为。知识产权领域内所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破坏诚实信用原则、推高知识产权交易成本、知识财富逆向流动和导致司法工具化等危害[12]。在我国专利实践中所存在的各种形式“非正常申请”行为,就是典型的知识产权机会主义行为。2017年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新修订的《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扩充、明确了非正常申请行为的种类,并加大了打击力度。为了规范知识产权获取行为,打击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维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声誉和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我国2013年修订《商标法》时增加了“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2015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新增了“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这说明,业界普遍认可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内的基本法律原则。信息披露制度是专利领域内落实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制度设计。根据各国对信息披露制度的内容设计,该制度并不要求专利申请人向专利行政机关披露与专利申请有关的所有信息,而是要求申请人披露其所掌握的与可专利性有关的重要信息,其核心是不得存在故意遗漏或虚假陈述,也就是说不得存在误导专利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专利申请人违反向USPTO(美国专利商标局——笔者注)进行披露的义务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不正当行为抗辩。提出该抗辩的一方还必须证明,隐瞒重要信息(或提供不实信息)的意图是要欺骗USPTO。重要性和意图是构成不正当行为的独立元素,具有重要性不代表着就存在意图[13]409-410。”所以,信息披露义务的真正目的不是要给申请人规定提供信息资料的具体义务范围,因为它仅仅要求申请人提供其所知悉的信息资料,在申请人客观上不掌握相关信息资料的条件下,该义务实际上处于不存在的状态;而是要求申请人在从事专利申请行为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不得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提出明知不符合可专利性条件的专利申请。要求申请人披露与专利申请有关的信息,符合社会公众对于申请人的道德预期[3]。信息披露制度为不诚信的专利申请行为规定了较为严重的法律后果,有助于从根本上防范问题专利的产生,建立诚实信用的专利运行体系。在我国专利实践中,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对专利体系所造成的损害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地纷纷出台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应对。如,2013年河北省出台地方指导意见,规范专利申请行为,遏制和防范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14],甚至有专利代理机构因为代理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受到了行政处罚[15]。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国当前所存在的大量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主要还是由于政府对于专利制度运行的过度干预所造成的。减少政府对专利制度运行的行政干预,回复专利制度的市场经济本色,让市场在专利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防范问题专利的根本出路[16]。
2.2 弱法律责任模式
第3步:在软件Matlab 2012b中通过编程求得该预测方法的相对误差,并且与BP神经网络直接预测法的相对误差进行对比分析。
德国专利法关于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大体和日本专利法相当。《德国专利法》第34条第7款规定:“应专利局的要求,申请人应当在说明(该法本条第3款)中完整、真实地描述就其所知的现有技术[34]。”与美国专利法、日本专利法不同的是,根据德国专利法的规定,申请人只有在专利局提出披露现有技术的要求的条件下才负有相应的义务,并不承担抽象意义上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德国专利法》第42条第1款的规定,未披露现有技术的缺陷,在形式审查阶段可以不予以考虑。也就是说,现有技术披露义务不是形式审查阶段的主要关注对象。根据该法第44条的规定,在实质审查阶段,审查员应当对专利申请是否符合第34条规定的现有技术披露要求进行审查。该法第45条进一步规定,经审查专利申请不符合第34条规定的现有技术披露要求的,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补正缺陷。如果申请人未能在审查员指定的限期内补正现有技术披露上的缺陷,根据该法第48条的规定,此时应当驳回专利申请。也就是说,在德国专利法上,违反现有技术披露义务构成专利驳回的法定事由之一。《德国专利法》第21条和第22条封闭性地规定了专利撤销和宣告无效的情形,并未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确定为撤销或无效的事由。专利法列举的撤销和无效理由是穷尽的,基于其他理由提出的撤销或无效请求无法获得支持,专利不会因其他理由而遭废除。尤其仅与授权程序相关的瑕疵,不在考虑之列[35]736-737。“只要证实,基于实体法的理由,一项专利(以其授权版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授权或者是非法侵占的,则出现异议和无效宣告而撤销[35]733。”信息披露义务规定在《德国专利法》第三章“专利审查程序”之中,被视为授权程序事项,而不是实体性的授权条件,故不作为废除专利权的事由。这也就是说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获得的专利权能够确定地发生法律效力。当然,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获得专利权虽然不可据此撤销或宣告无效,但并不意味着不产生其他法律责任。《德国专利法》第124条规定:“在专利局、专利法院或者联邦最高法院的程序中,当事人应当真实、完整地陈述事实。”如果申请人在专利申请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则需要根据其他法律的规定承担公法上的责任,但是并不会据此影响专利权本身的法律效力。
2.3 无法律责任模式
所谓无法律责任模式是指,专利法没有为申请人设定信息披露义务,或者虽然设定有信息披露义务但是没有规定义务不履行之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在无法律责任模式下,申请人的信息披露负担是最轻的,甚至他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向专利行政机关披露相关信息。《欧洲专利公约》和我国专利法即属于这一种模式。欧洲专利局设立有专门的信息检索部门,专司欧洲专利申请的检索事宜,负责出具欧洲专利检索报告。《欧洲专利公约》第92条规定:“欧洲专利局应当根据本公约《实施细则》,基于每件欧洲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在适当考虑其说明书和附图后,对每件欧洲专利申请作出欧洲专利检索报告,并予以公布[36]。”《欧洲专利公约(2000年)实施细则》第二章“欧洲专利检索”以7个条文的篇幅,对欧洲专利检索报告的内容、扩展的欧洲检索报告、不完全检索、发明缺乏单一性时的检索报告和检索报告的送达等内容作出了专门规范。由于欧洲专利局具有专门的检索部门和规范的工作程序,所以欧洲专利局进行专利审查时主要依靠该局检索部门的检索报告进行,并不要求申请人提供与专利申请有关的现有技术信息。欧洲专利申请人即使掌握了与其专利申请之可专利性相关的现有技术信息,也完全可以保持沉默[8]364。欧洲专利局的规定看似对专利申请人更为友好,但是这种友好是有代价的。欧洲专利局专设信息检索部门,虽然可以提高信息检索的质量,但是也相应地提升了制度运行的成本。这种成本最终以申请费的形式间接地转嫁到申请人的身上。据有关学者统计,欧洲专利申请的申请费用平均为美国的3倍[37]。
刚好我这时喝了一口茶,听他讲完,差点儿轮到我笑喷。幸好我还算清醒考虑当着女生的面笑喷不雅,硬生生地将茶水咽了下去。哪曾想这一咽却咽出了问题,不知怎么,口腔中的那一颗假牙竟然脱落,连同茶水也一并咽了下去。
3申请人信息披露规则的重构
正如前文所述,规定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对专利制度良性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专利法虽然规定了信息披露义务,但是没有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致使该制度成为无牙的老虎,制度目的无法真正有效实现,甚至形同虚设[40]。美国专利法为信息披露义务设定了可以产生不正当行为抗辩的严重法律后果。由于缺乏比较法上的支持,美国专利法的规定在国内也遭受了一些批评[41]。但是,不正当行为抗辩的存在却是保证申请人“按规矩做事”的必要方法[13]404。诚如一位美国专利法学者所言:“支持保留不正当行为抗辩的最有力的实际理由就是,除非对保留信息处以严厉处罚,专利律师及其客户将不会有动力协助USPTO对专利申请进行彻底审查并且只核准有效的权利要求[42]。”笔者建议参酌美国、日本等国家专利法的规定,对我国专利法上信息披露制度进行重构,核心就是要赋予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的法律约束力。
3.1 披露义务的主体
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首先是专利申请人,他应当向专利行政机关披露所知悉的相关信息。但是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不应当局限于专利申请人,因为设定该义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协助专利行政机关提高审查质量,只授予那些真正有效的专利,事关重要的公共利益,因此与专利申请人存在关联关系的、知悉相关信息的人,都应该通过申请人诚信地向专利行政机关披露相关信息。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除了申请人之外,本申请的所有发明人、代理人以及其他实质性参与到申请过程中人,都负有向专利行政机关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7]。只不过其他人的披露义务只能通过申请人向专利行政机关来履行,不具有独立于申请人的单独法律地位。在申请人并非发明人,或者申请人系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受让专利申请权的情况下,将发明人或转让人规定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此时往往申请人并不掌握相关信息,发明人或转让人恰恰是重要信息的知情人。如果是申请人之外人的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致使申请人的申请被驳回或者专利权被判定不可执行,则申请人有权根据合同法等其他法律的规定追究其他人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3.2 应为披露的内容
所谓强法律责任模式是指,申请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时,如果专利授权决定尚未作出,专利行政机关可以据此驳回其专利申请,如果专利授权决定已经做出,则可以作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不可执行的正当事由。可以看出,在强法律责任模式下,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后果是严重的,该立法模式对专利申请人的心理约束力是巨大的。美国是强法律责任模式的代表。根据美国专利法实施细则37 CFR 1.56(a)条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情况不但是美国专利商标局做出专利授权决定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还是法院在专利诉讼程序中判定专利权效力和执行力的重要考量因素,其影响力贯穿该专利的整个生命周期[7]。在美国专利法上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被称之为“不正当行为”。1945年,美国最高法院根据衡平法上的“不洁之手”原则创立了专利法上的“不正当行为”理论,允许被控侵权人将专利申请中的“不正当行为”作为侵权抗辩事由[18]。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从而构成不正当行为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要件,其一是信息的重要性,其二是存在欺骗专利行政机关的故意。所谓“信息的重要性”是指,专利申请人未能向USPTO披露的信息或者向USPTO披露的错误信息,足以影响USPTO对涉案专利申请可专利性的判断。申请人未披露或错误披露的重要信息一般有3种情形,分别是:(1)未能向USPTO披露该申请人已知的关于可专利性的重要信息;(2)向USPTO提交的关于可专利性的重要信息是虚假的;(3)向USPTO作出的关于可专利性的重要确定性陈述是虚假的。因此,不正当行为可以是基于专利申请人的疏忽,也可以是基于其故意。在何为重要信息的判断上,存在着USPTO的行政标准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的司法标准这两种判断方法。USPTO的行政标准认为,在如下两种情况下成立重要信息:其一,该信息本身或者与其他信息的结合,构成涉案专利之权利请求不具有可专利性的表面证据;其二,在申请人反驳专利局做出的不可专利性意见或主张成就可专利性时,该信息否认申请人所采取的立场或者与其不一致[19]。但是,如果一项信息仅仅是已经提交给USPTO的其他信息的累加(未加入新的或不同的内容),则不认为该信息是重要信息[20]。类似地,如果USPTO的审查员独立地发现了申请人未披露的已知信息,该信息也不会被视为重要信息。CAFC曾经在一则案件中判决到,当一篇对比文件出现在审查员面前时,不管该对比文件是审查员检索得来的还是申请人披露的,均不应当认为向审查员隐瞒了该文件[21]。CAFC的司法标准认为,在判断一项信息的重要性时,应当看“合情合理的审查员”是否认为该信息对于可专利性的判断是“重要的”。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则该信息就是重要的。虽然该信息并不一定是具有无效性的,若审查员已经知晓该信息,则会导致该专利申请之权利要求不会被核准。在这种情况下,要宣告这些权利要求无效,被隐瞒的现有技术虽然并不充分相关,但是对可专利性已充分关键,并形成了判决不正当行为的基础[13]405。
“C语言程序设计”实验课中,笔者采用了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具体操作:让同学们在课下按照实验任务,利用微课平台提供的学习资料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微课中留下的问题作业。在课堂上,学生进行一节课实践测验,然后在老师的引导下,以小组为单位的方式汇报完成情况并展示实验成果。
3.3 披露的时间和方式
设定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专利审查和授权的质量,因此信息披露的时间原则上应为申请人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时间[40]。在专利申请提出时和形式审查阶段,由于尚未开始对申请人是否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实质性授权条件进行审查,所以此时申请人是否提供旨在用于实质审查的相关信息,均不影响专利审查程序的推进。而且由于形式审查阶段只审查申请文件在形式上是否完善,对是否符合授权条件的实质性信息不审查,所以即使此时申请人提供了相关信息,一般也不会纳入审查员考虑的范围。况且,并不是所有的发明专利申请均会进入实质审查阶段,所以在此阶段要求提供用于实质审查的相关信息,对于最终未能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专利申请来讲无疑是加重了申请人的负担。信息披露义务中所披露的信息,以现有技术为主,不作为授予专利权的积极条件,也不会和其他专利申请形成抵触,不存在时间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无需严格限定在申请日完成。由于申请人披露的相关信息可能会对专利的实质审查形成影响,为了让审查员能够全面高效地完成专利实质审查,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一般应当在实质审查请求提出时一次性完成,除非相关信息在实质审查请求时尚未被申请人所掌握。对于那些在实质审查开始之后申请人才掌握的相关信息,只要专利授权尚未最终完成,哪怕是在已经发出了授权通知书之后的时间,申请人仍然可以随时提供相关信息[7],但是申请人不得存在有悖于诚信的故意拖延。申请人信息披露的方式应当遵循专利申请中的书面原则,以正式书面文件的方式向专利局提出。至于是需要提供相关信息的全部内容,还是只需要指出信息的出处,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审查员获取相关信息的难易程度来确定。如果相关信息通过专利局的数据库可以方便地检索获取,则申请人只需要披露该信息的具体出处即可以,此类信息一般表现为在先专利申请和科技期刊。如果相关信息不为专利局所掌握且不易于为专利局所获取,则申请人应当披露该信息的整体内容,一般通过提供相关材料的复印件来实现,以便于提高审查效率。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材料,等同于申请人对于不利于其专利申请的自认,因此一般在证据形式上不必进行严格的限定,可以申请人自便的形式向专利局提供。
3.4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可能引发的法律责任,是信息披露制度的核心。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多数国家的专利法都规定了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所不同的主要是违反该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内容。我国专利法第36条规定了两种形式的信息披露义务。该条第一款规定了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是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第二款规定了国外同族专利申请的信息披露义务,为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如果没有根据专利行政机关的要求披露国外专利局的检索资料和审查结果,将视为撤回。由于国外同族专利申请毕竟是专利申请中的少数,所以可以认为第36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信息披露要求才是我国专利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的主体。法律责任是法律义务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由于第36条第1款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缺乏相应的责任条款,所以我国专利法上一般信息披露义务其实就是一种倡导性的规定。因为单方审查程序缺乏对抗性系统的通常优点,所以专利制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利申请人向专利局履行诚实和诚信的义务。然而,申请人由隐匿现有技术或提供虚假事实以免影响其获得专利权的强烈动机,因此申请人善意履行诚信义务会大打折扣[45]223。无论出于尽可能获得专利授权还是节约专利申请成本的考虑,在缺乏相应责任机制的情况下专利申请人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动力主动披露相关信息,所以信息披露制度在我国专利法上基本没有受到重视,在专利实践中也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为了使信息披露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落到实处,有必要对我国专利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进行重构,根本的改造手段就是为专利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披露义务规定明确的法律后果。我国有学者持与笔者相同的立场,“为保障该义务的充分实施,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制度是非常重要的[1]。”
(196)平叉苔 Metzgeria conjugata Lindb. 刘胜祥等(1999);彭丹等(2002);杨志平(2006);马俊改(2006);项俊等(2006);李粉霞等(2011);余夏君等(2018)
在信息披露义务法律责任的设计上,比较法上亦无统一的成例可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制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制度是完美的,对一国具体专利制度的评价,必须从该国的现实国情和专利制度的整体出发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我国专利制度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干预色彩浓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运作。由于政府“外源驱动”的刺激,在我国专利制度的运行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市场行为,各种形式的“非正常申请行为” 即为著例。“非正常申请行为”说到底就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投机行为。信息披露义务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要求申请人向专利局提供多少信息,而是要求申请人诚信地进行专利行为,这与我国从制度层面规制“非正常申请行为”的时代需求不谋而合。专利法上的诚信具有超越申请人、专利行政机关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等当事方的重要意义[46]。在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善,专利申请人机会主义行为高企的现实条件下,实施更为严厉的信息披露制度无疑是符合我国现实条件的。笔者认为,在信息披露义务之法律责任的设计上,美国专利法的规定颇具借鉴价值。也就是为信息披露义务设定授权前和授权后双重的法律责任。在专利授权之前,如果申请人未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则应当作为专利局驳回申请的法定事由;在专利授权之后,如果发现申请人在专利申请的过程中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则应当判定该专利权不可执行。之所以不认定专利权无效,乃是因为无效事由均属于不符合专利授权的实质性条件,信息披露义务只是申请人负担的程序性义务,与专利无效事由在性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信息披露义务之违反,与其说是申请人未能披露重要信息,毋宁说是申请人存在欺骗专利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所以对申请人主观状态的考察乃是认定信息披露责任成就的关键所在。美国专利法专家谢科特和托马斯在详细研究美国专利法上不正当行为之后不忘告诫我们:“还有最后一点需要记住。美国专利法没有对申请人附加任何义务要求申请人进行现有技术检索。因此,一个人不会因为没有检索到现有技术参考资料而被认定有不公平行为。专利申请人的唯一义务是引用那些他或她已经知道的那些现有技术。而搜索所有相关现有技术是USPTO以及法院上对方当事人的任务。不公平行为原则想要惩罚的是欺骗行为,不是懒惰或者疏忽行为[45]228。”
参考文献:
[1]梁志文.论专利申请人之现有技术披露义务[J].法律科学,2012(1):130-138.
[2]袁晓东,刘珍兰.美国专利申请人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对专利质量的影响[J].情报杂志,2011(6):14-19.
[3]崔国斌.专利申请人现有技术披露义务研究[J].法学家,2017(2):96-112.
[4]LEMLEY M A. Rational ignorance at the patent office[J].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1, 95(4): 1495-1532.
[5]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统计年报2017[R/OL]. (2018-09-28)[2018-10-03]. http://www.sipo.gov.cn/docs/201809281619458
42782.pdf.
[6]KUHN J M. Information overload at the U. 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reframing the duty of disclosure in Patent Law as a search and filter problem[J]. Yale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2011, 13 (1): 89-140.
[7]张大海,曲丹.简述美国专利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5(5):87-91.
[8]梁志文.论专利公开[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9]COTROPIA C A, LEMLEY M A, SAMPAT B. Do applicant patent citations matter ? [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4):844-854.
[10]王楚鸿.专利技术的“可用性”缺陷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6(11):200-202.
[11]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51.
[12]刘强.机会主义行为规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完善[J].知识产权,2013(5):64-69.
[13]穆勒.专利法:第3版[M].沈超,李华,吴晓辉,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4]本刊编辑部.河北出台地方指导意见,遏制防范非正常专利申请[J].中国专利与商标,2013(4):108.
[15]知识产权报特约评论员.诚信提交专利申请,切实维护正常秩序[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8-01-25(1).
[16]徐棣枫,邱奎霖.专利资助政策与专利制度运行:中国实践与反思[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74-78.
[17]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332.
[18]刘文琦.解读美国专利法“不正当行为”理论的适用[J].电子知识产权,2010(5):53-57.
[19]USPTO.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appendix r patent rules[EB/OL]. (2018-01-10)[2018-10-06].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index.html.
[20]CAFC. Star Scientific, Inc. v. R. J. Reynolds Tobacco Co.[EB/OL]. (2011-08-26)[2018-10-08]. http://www.cafc.uscourts.gov/content/star-scientific-inc-v-rj-reynolds-tobacco-co.
[21]CAFC. Molins PLC v. Textron, Inc.[EB/OL]. (2011-06-20)[2018-10-08]. https://openjurist.org/48/f3d/1172.
[22]STEVAUX K N. Inequitable conduct claims in the 21st century: combating the plague[J].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05, 20(1):147-172.
[23]CAFC. FMC Corp. v. Hennessy Indus., Inc.[EB/OL]. (2012-10-22)[2018-10-08]. https://openjurist.org/836/f2d/521.
[24]陈雨.美国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
[25]CAFC. Honeywell Int’l, Inc. v. Universal Avionics Sys. Corp.[EB/OL]. (2007-06-03)[2018-10-09]. http://www.cafc.uscourts.gov/content/honeywell-international-v-universal-avionics-systems-corp.
[26]CAFC. Nilssen v. Osram Sylvania, Inc. [EB/OL]. (2007-10-10)[2018-10-09]. http://www.cafc.uscourts.gov/content/nilssen-v-osram-sylvania.
[27]CAFC. McKesson Information Solutions, Inc. v. Bridge Medical, Inc.[EB/OL]. (2007-05-18)[2018-10-10]. http://www.cafc.uscourts.gov/content/mckesson-information-solutions-v-bridge-medical.
[28]CAFC. Kingsdown Med. Consultants, Ltd. v. Hollister, Inc. [EB/OL]. (1999-08-25)[2018-10-10].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2/81/978/2420856/.
[29]海冰.美国专利法中的不正当行为问题[J].电子知识产权,2009(4):79-81.
[30]GOLDMAN R J. Evolution of the inequitable conduct defense in patent litigation[J]. Harwar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1993, 7(1):37-100.
[31]日本国会.日本专利法[M].杜颖,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3.
[32]田村善之.日本知识产权法[M].周超,李雨峰,李希同,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207.
[33]青山纮一.日本专利法概论[M].聂宁乐,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51.
[34]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外国专利法选译(中)[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882.
[35]克拉瑟.专利法:德国专利和实用新型法、欧洲和国际专利法[M].单晓光,张韬略,于馨淼,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36]哈康,帕根贝格.简明欧洲专利法[M].何怀文,刘国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0.
[37]DINWOODIE G B, HENNESSEY W O, PERLMUTTER 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atent law[M]. Newark: Lexis Nexis Publishing, 2002:718.
[38]安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9.
[39]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指南2010[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41.
[40]丁宇峰.专利质量的法律控制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6.
[41]MACK K. Reforming inequitable conduct to improve patent quality:cleansing unclean hands[J].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06, 21(1):147-176.
[42]JANICKE P M. Do we really need so many mental and emotional states in united states patent law?[J]. Tex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ournal, 2000, 8(3):279-298.
[43]CAFC. Critikon, Inc. v. Becton Dickinson Vascular, Inc. [EB/OL]. (2018-07-28)[2018-10-12]. http://www.lddoc.cn/p-445408.html.
[44]CAFC. Akron Polymer Container Corp. v. Exxel Container, Inc. [EB/OL]. (2010-11-08)[2018-10-12]. http://www.cafc.uscourts.gov/search/node/Container.
[45]谢科特,托马斯.专利法原理[M].余仲儒,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46]崔航.不正当行为原则的发展历程与启示[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8(1):36-44.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Model and Rules of Patent Applicant ’s Oblig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Yang Deqi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and proper performanc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 will be helpful to reduce the search cost of examination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tent application and examination, and to establish a credit patent operation system. There are three legislative model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strong legal liability, weak legal liability and no legal liability. China’s Patent Law is a non-legal liability model, which leads to the vacu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The pat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f our country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ubjec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 the content of disclosure, the time and mode of disclos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clear legal liability for the viol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 should be stipulated.
Key words :patent applica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 legal liability mod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ules
中图分类号: G3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 2019) 18-0154-10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18.020
收稿日期: 2018-10-06,修回日期: 2019-01-18
基金项目: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制造2025’视阈下内蒙古制造业知识产权战略构建与实施机制研究”(2016NDB091)
作者简介: 杨德桥(1979—),男,山东单县人,法学博士,博士后,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
标签:专利申请人论文; 信息披露义务论文; 法律责任模式论文; 信息披露规则论文; 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