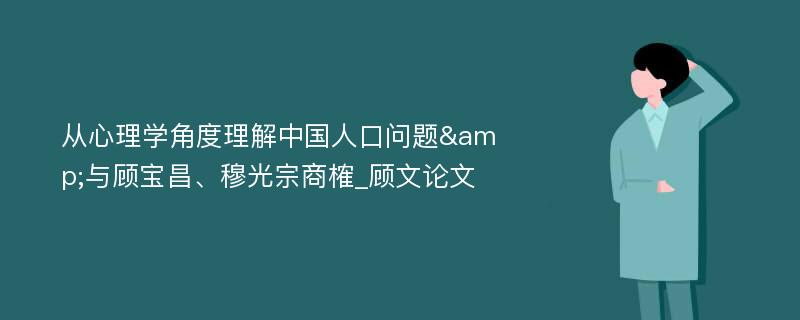
从心理学视角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兼与顾宝昌、穆光宗二位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位论文,视角论文,心理学论文,中国人口论文,穆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1994年第5期发表了由顾宝昌、 穆光宗两位撰写的题为《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论文后,得到了学者、领导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我们收到很多来稿和来信,也接到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打来的电话,就该文谈了自己的看法。文中所提观点十分重要,它关系到对中国计划生育如何认识的问题。为此本期发表由严梅福、石人炳合写的与之商榷的论文,以期对这一重要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内容摘要] 本文是对《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主要论点的再认识。以心理学原理为依据,提出计划生育的目的是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但转变观念有赖于改变行为,而改变生育行为又只有在行政、经济等控制措施的“强化”下才能实现。文章认为全国低生育率掩盖了农村的较高生育率;人们生育观念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中国未来人口战略因此只应修正和补充,而不能根本改变。
顾宝昌、穆光宗两位先生在《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以下简称顾文), 十分负责地思考了过去二十多年和未来的中国人口问题,表现了人口学者应有的高度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他们文章中的许多论点都涉及到了对我国既往人口政策的分析评价和对未来,特别是世纪之交人口发展的战略思考,其讨论的命题之重大,所表述观点影响之深广,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从心理学的角度,就顾文中一些观点提出看法。
1 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什么?
诚如顾文所述,经过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的人口控制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不仅在1971—1990年期间少生了22142万人〔1〕,而且, 最令人信服的莫过于是我们终于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以世界上任何国家还不曾有过的速度迎来了低生育率,将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了2.0这一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2〕。可是,当我们从心理学理论的视角出发来审视这一成就的合理性以及后续工作的时候,我们与顾文的观点之间又存在着明显分歧。
顾文认为,生育率虽然降了下来,但是,由于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把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放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把少生强调到了就是一切的地步,似乎计划生育就是抓人口计划,只要完成了人口计划,就万事大吉,而所谓的人口计划又归结为生几个孩子。这样,就造成漏报,导致统计失真,直接危及对国情的认识和决策;生育选择空间缩小,人们千方百计选择男婴,出生性别比因之升高;地方上形成短期化的政府行为,过分倚重行政手段的运用而忽视如何有效运用经济手段和文化措施;只注意减少过剩人口的增量(节流),忽视减少过剩人口的存量与流量(开源),即只注意如何少生,忽视合理开发利用现有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源等诸多问题。结果,导致了人口政策实施中的偏颇,甚至严重偏离了政策的基本要求。很显然,顾文认为计划生育由于只抓人口数量控制,将少生视为计划生育的全部内容,以致最终使计划生育背离了自身的目的与宗旨。因此,顾文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并就此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计划生育的宗旨决不仅限于少生多少人,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人口条件、人口状态和人口环境。
我们不同意顾文认为计划生育由于只抓人口数量控制就背离了计划生育的宗旨与目的看法(原因在2 中解释)和对计划生育宗旨与目的的概括,试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后者给出我们的答案。人的生育观念在生育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生育活动的发端、维持、改变和终止,无不是在生育观念支配下实现的,这是人类与动物在生育活动上的根本差别,也是人类能够对自身繁衍实行有计划控制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认为计划生育的宗旨决不仅限于少生多少人上,也不仅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人口条件、人口状态和人口环境上,而是要通过计划生育的实施,使人民群众在人口再生产上形成计划生育观念,即计划生育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是在于转变绵延了几千年,已经深入到了个体的潜意识和集体的无意识(潜意识)之中的传统生育观念,代之以计划生育观念。我们相信,一旦社会群体都建立起了计划生育观念,那么,下降了的生育率的反弹,生育统计上的漏报、谎报,婴儿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人口素质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都将不复存在,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宽松、合理、有序的人口环境就会不期而然的到来。这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就计划生育的目的而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是主要的,环境是从属的,因为良好的人口环境最终是由具有计划生育观念的人创造的。
然而,计划生育观念的作用为什么如此重要,其内容是什么呢?生育心理的有关研究认为,计划生育观念是迄今为止最进步、最合理的生育观念,它不仅摒弃了封建主义的陈腐生育观念,而且也放弃了不顾社会发展进步,只求个人享乐与在封闭的状态中追求“自我实现”的抑制生育思想,它包涵下述内容:
(1)宽广的同类意识。计划生育观念的核心是集体主义精神,而同类意识又是集体主义的心理内涵,富有宽广的同类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是计划生育观念最突出的特点。所谓同类意识是指人将认识对象知觉为自己的同类,纳入各自的“同类”概念体系的一种心理现象。同类意识之所以是计划生育观念的主要特征,是因为国家、民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推动人们去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要动力,人们计划生育观念的形成是生育者对民族、人类的苦难寄以高度同情,对之感同身受,愿意使个人、家庭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结果。没有对民族、人类未来深切的忧患感和对其苦难与厄运的无限同情,就不会有生育者放弃个人家庭利益,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的行为。
(2)扩大的个体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指人对自己身体和心理活动的知觉。但又不止如此,一些与个体相关联的他人反映到个体头脑中也可以成为个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个体的属于“我的”的那一部分人发生的变化可以引起同他的躯体、精神受到刺激时相同感受。比如人会将亲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有的父母在失去子女后痛不欲生,恨不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子女的复生;无数先烈为了“我的”民族英勇捐躯。我们把自我意识的这种扩大化称为自我意识的外包涵性。具有计划生育观念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外包涵性明显扩大。而持有“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观念人们的自我意识的外包涵性十分狭小,实质上只包涵着自我。它像一层硬壳把生育者与民族、人类利益隔开,使他们不顾国家面临的“人口爆炸”全力生育;或者不管民族已进入“人口冬天”不愿生育。形成了计划生育观念的人,地区、民族乃至人类的利益都可以进入他的自我意识范围之中。生育者从民族发展来取舍自己的生育行为,对民族的兴盛,人类的未来给以极大关注,注入深厚情感。为在民族的兴旺发达中自己所作的生育努力感到慰藉,也为民族的人口困厄与危机中自己应负的责任感到羞惭与内疚。
显然,与传统生育观念内容有天渊之别的计划生育观念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生育观念。它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育的性质。较之于建立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而言,它属于治本的工作。但是,由于在我们这个素有多生多育传统,多育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既有几千年历史的积淀作用,又是农民生活中十分现实的问题的民族中要实现生育观念转变,无异是一场生育革命。正因为如此,转变生育观念才成为了计划生育的宗旨与目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才不可避免地成了“天下第一难事”。
2 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反思
此外,我们也不赞同顾文对以往计划生育工作中大力实行人口控制,严格遏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做法提出的类似反思性的意见。顾文认为,控制人口无疑是历史的抉择,是中华民族重续强国梦的必由之路。然而,问题在于我们长时间以来,搞的都是“少生就是一切”,单打一的数量控制。但今天看来,这样做不仅隐含一种类似于人口决定论的悲观而急躁的非理性,而且能带来使被行政强制力压下去的生育率出现反弹的“欲速则不达效应”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急骤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调,干群关系紧张等“顾此失彼效应”。文章因此提出,人口是不是控制得越紧越好这类问题尚需研究。
首先,我们认为当我们国家急待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而由于历史上人口政策的失误,它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有近9亿人的庞大基数, 每年以25‰以上的自然增长率,1600万以上的绝对数增长的人口时,把遏制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或者说把“少生就是一切”在一段时间里放到第一位是非常正确的;而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受到人口过快增长威胁和“少生就是一切”会带来一些负效应这“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政府果断有魄力的表现。试想,当我们面对着不能再增大了的人口基数与自然增长量,必须为先辈由于对人口发展规律的无知所犯的错误而采取非常措施,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而我们古老的民族又有着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多生多育传统的时候,把人口数量控制放到最突出的位置是正确的选择。
诚然,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来都是把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相提并重。但这主要是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结果而言,它并不排斥政策在执行中,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个方面有所侧重。在计划生育中抓主要矛盾,抓住并解决了主要矛盾,就可以为其它从属矛盾的解决创造条件,使之“迎刃而解”。少生能使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但也正是少生能使少年儿童的抚养比降低,比如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中老年系数为6.08,1990年升到了8.59,但与此同时,少年儿童系数却由1964年的42.35降到了29.62,〔3〕这又会有利于经济发展, 为解决加速到来的老龄化问题创造条件;少生可能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但是,也只有在少生的基础上,干部才能带领群众走上“少生快富”之路,最终密切干群关系;少生在一些地方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但只有在少生的条件下,比如在只有一个女孩的时候,像我国现在城市里一样,人们才会在不分性别的基础上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从而随着对女孩歧视的消除而最终消除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近期,我们调查了湖北省松滋等五个县(市),发现凡是曾经雷厉风行抓了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生育率降低比较快的县(市),并没有出现“顾此失彼”效应。比如松滋县1994年的人口出生率只有11.18‰, 同时,出生性别比近年都在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乡乡都办有敬老院,原来的“五保”老人和现在的一些孤寡老人都得到了妥善供养;计划生育已不再是“天下第一难事”,几乎没有发生因计划生育而造成的干群重大矛盾与冲突。相反,有个出生率、多胎生育率较高的县,干群关系的紧张确实达到了一定强度,出生性别比高达131,居全省之冠。 理论和现实给出的这些启示使我们觉得,需要对二十多年来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反思,那么,把控制人口数量当主要矛盾抓并没有错,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还有不少地方并没有把它当作主要矛盾,放到“压倒性”的位置来抓。
其次,从计划生育的目的与宗旨是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出发,只有严格实行生育控制,修正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多生多育行为,才能转变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最终形成计划生育观念。这也从心理科学的角度支持了我国前段计划生育中狠抓人口数量控制的作法。在心理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具有广泛影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思想、观念是内隐的东西,有如一个黑箱,其规律、特性都难以认识,因此,不愿妄言怎样对其实行改造和修正,不强调就观念本身去转变观念,而是注重人的行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能得到改变,那么,行为后面的思想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这一理论又确信,人的行为是可以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和改变的〔4〕。从行为心理学的理论看来,要在中国实行人口控制,遏止人口过快增长,迅速将人口出生率降低下来,减轻并最终甩掉压在我们民族身上的沉重的人口压力包袱;要转变支配人们多生多育的传统生育观念,实现计划生育的宗旨与目的,重要的不是“苦口婆心”地去做生育者的思想转变工作,不是把降低生育率的希望寄托在诸如“动之以情”的说服,“晓之以理”的教育上。而是主张倾注全力去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即用各种方法制止人们的多生、抢生等行为,激励人们的少生、优生行为。当社会人群的生育行为实现了由多生到少生的转变,并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得到巩固。那么,人们的生育观念就会得到转变。
我国人口控制实践证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并非虚妄之言。比如,1963年以前,在城乡基本上没有进行生育控制的时候,我国城镇人口的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都高于农村〔5〕;城乡群众的生育观念、 生育意愿差别不大,都倾向于多生、早生、生男孩。但实行计划生育后,由于城乡在政策上的差异,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人口生育行为的限制远比城市宽松,就使得农村和城镇人口不仅在生育行为上显出极大不同,农村在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上都大大高于城镇,而且,二者在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上也出现了明显差异。据对我国计划生育先进省吉林的调查,那里即使是去掉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让人们处在不控制生育的情况下,愿要一个孩子的妇女比例农村比城市也低得多,大体只相当于城市的17.8%,愿意生3个孩子以上的农村妇女竟占24%,高出城市3倍,而在生育的性别偏好上,30%的城市妇女对孩子性别没有选择,这一比例高于农村妇女2.2倍。〔6〕
人们的生育观念能够在抓少生的过程中,并且必须通过抓少生的过程才能转变,曾经看来是十分不可取的“少生就是一切”式的单一人口数量控制模式,最终导出的却是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计划生育宗旨与目的的实现。它说明勿须简单地反对单打一的人口数量控制,它其实是一条通向合理人口状态和良好人口环境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我们不同意顾文认为计划生育由于只抓人口数量控制,因而背离了计划生育的宗旨与目的的看法的原因之所在。
3 中国未来人口问题的战略思考
要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战略思考,首先必须明确,现阶段以及下世纪初期和中期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握低生育率到来后的一段相当长时期里,我国人口问题的诸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对此,顾文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人口问题也在转型,从突出的数量问题开始转向并发的综合问题,我国已被推入到了“泛人口问题”时期。中国面临着低生育率条件下人口问题如何综合治理的挑战,人口调控的时代,人口综合治理的时代到来了,而单一的人口控制时代已经渐渐地落下了帷幕。关于什么是综合治理,顾文指的是在控制总量的基础上提高素质、调整结构、合理分布,充分、有效、合理地开发现有的人口资源的“五位一体”的人口发展战略。
这表明,在顾文看来,随着低生育率的到来,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数量过多与增长太快同发展的矛盾转换成了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因此,再没有必要像已经和正在做的那样,大张旗鼓而又深入细致地去抓人口数量控制,手段也应当从行政控制转向综合治理,总之,是从总体战略上转型的时候了。
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前不久还在被大声疾呼,甚至出示黄牌警告的“非常严峻的人口形势”只在弹指一挥间就彻底消除了,因而可以不再那么紧张,可以稍事松口气,实行计划生育工作重心的大转移了吗?我们不以为然,在这方面应当牢记理论对政策误导所造成的难以挽回的影响和损失。
基于我们对计划生育的目的和宗旨不是从治标上创立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人口环境,而是从治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而改变生育观念又无须从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入手这一认识,和面对低育率虽然已经出现,但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远未完成,不少地方生育率还没有真正降下来,一些地方降下来后又随时可能出现反弹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轻言在人口政策上实现战略性转移,不啻是给具体工作部门正在下大力气进行的人口控制工作泼冷水。当低生育率初始出现的时候就急于进行战略转换是危险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首先,我们必须对已经到来的低生育率做具体分析。尽管1993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2.0,即使在排除一定的数据不实因素以后, 也还应当能处在更替水平(2.1)。但是, 我们切不可忽视我国生育率下降的不平衡性这一特点和这一特点所包涵的更深层的寓意。我国城市总和生育率虽然降到了1.33,比许多人口出现零或负增长的国家还要低。但农村却还在2.8,“老、少、边、穷”地区则还要高。所以, 可以认为,全国的低生育率掩盖着农村的比较高,一些地方还相当高的生育率。而我国人口控制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又都在农村。所以,当农村的人口控制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的时候,我们要实现全线战略转型,那就等于是在农村这个最长的线段上“开小口子”,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第二,人们的生育观念尚未发生根本转变,而这又是最重要的,它实际上是我们决定是否应当在战略上转型的关键。据报导,法国年轻已婚夫妇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愿要孩子;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子女;德国的二千二百万户人家中,有子女的只占49%,其中近半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7〕但是,在我国,即令是像上海这样人口出现负增长,总和生育率只有1.23(1993年),全年出生人口中第二胎及以上的比例仅为4.27%(1991年)的城市,据调查全市至少有56%的人希望生育二个以上的孩子。〔8〕至于生育目的,从对全国部分省区农村的调查看,“养老送终”、“传宗接代”仍是居于第1、2位。〔9〕这说明, 现在我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生育观念虽然已经开始有了可喜的变化,计划生育所倡导和期望的基本价值规范,诸如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优教等也在更广泛范围,更深的层次上被人们所接受。但是,离计划生育观念的彻底形成还有很大距离。如果我们在生育观念转变初露端倪的时候,就冒然放松控制生育数量这一修正多生行为以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继续转变的条件,那就是在为生育率的反弹提供思想基础。
第三,从心理学角度看,实行人口战略转变亦为时尚早。如前所述,人的生育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但怎样让改变了的生育行为保持下去而不出现反弹,又决定于“强化”,决定于强化的次数与“时程”安排。任何被修正了的行为要想得以保持,一定次数的“强化”是不可少的,“强化”作为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强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塑造或修正人的行为的主要手段,行为心理学就是藉助奖励与惩罚的强化手段来对人的行为进行定向控制和改造的。
从心理学强化理论看,我国已经降低了的出生率所以会不稳定,出现明显波动,甚至有所回升,在接近更替水平时呈徘徊之势,具有较强的反弹特性,不是因为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是一种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不是因为作用与反作用力,压力与反抗这样简单的力学作用关系的存在;也不是因为“极限法则”在人口控制中的作用,使得人口控制越是接近目标的极限,遭遇的困难就越多,努力与绩效就越不成正比,努力的效果出现递减趋势的结果,而是因为缺少强化或强化不足。也就是说,是因为在计划生育中,缺少有效的奖励与惩罚这两种强化手段和这两种手段不能得到科学的运用,难以在修正和塑造人们的生育行为上产生应有的效果所致。
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15—64 岁妇女平均生育数城市为1.87个,农村为2.44个,城市一胎已经普遍化,农村几乎家家都有了2个以上孩子。是什么原因使得城乡人口控制有如此巨大差别呢? 为什么城市计划生育容易推行而农村困难重重呢?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城乡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时,总是婉转地归因为城市人口文化素质高,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条件,不像农村一样存在着对男性劳动力的急切需求等,而不愿直言不讳地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城市有着比农村有力得多的保证人口控制得以顺利实行的行政和经济的奖罚这种强化手段。
在70与80年代,行政与经济奖罚这种强化手段对城市职工生育行为的制约作用是农村无法比拟的。城市职工违反计划生育,要罚款、扣发奖金、不调工资、降薪、直到开除公职,这种控制与惩罚是针对着职工的“生存点”进行的。只要想想,在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的年代,一个失去了“铁饭碗”的人,又要养活超生的人口会有多么困难,就不难理解这种惩罚所起的强化作用是不可抗拒的,因而,也就能懂得城市职工想多生而又不敢多生的道理了。据对北京市已领独生子女证妇女的调查,她们的期望子女数普遍是2个。而事实上, 城市当时的强化措施使职工面临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得与失的权衡,而是“生存”与“生殖”这样一个严酷的抉择。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是不会舍“生存”去求“生殖”的。所以,城市里确实是靠了有力的行政与经济的强化手段来抑制职工的生育行为的。
行政和经济的强化手段在农村从来没有达到城市的力度与效度。其原因是农民与城市职工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行政的强化措施对他们没有多大约束力,他们无工资、奖金可扣,无薪可降,也不怕被开除,只有几亩责任田和几间赖以栖身的住房,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决定了农村行政与经济强化的限度,总不能将超生者从他的责任田上撵走,这就是为什么即令是在计划生育进行得十分顺畅的年代里,农村人口控制也比城市难得多,出生率比城市高得多的原因。这一对比说明,农村被掩盖的较高的生育率与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是可以通过强化来降低和转变的。但是,它要求我们找到合适的强化手段与方式,并假以时日,继续把人口数量控制放在突出位置,反复施行强化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主张现在就实行人口战略转变,弱化或撤除“强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从二十多年来推行计划生育已使人们生育观念有了可喜的变化这一事实推断,再有略长于此的时间,继续不懈地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坚持使用强化手段修正人们的生育行为,城乡群众的生育观念将会发生根本转变。
责任编辑注:顾宝昌、穆光宗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6期6~14页。
收稿时间 199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