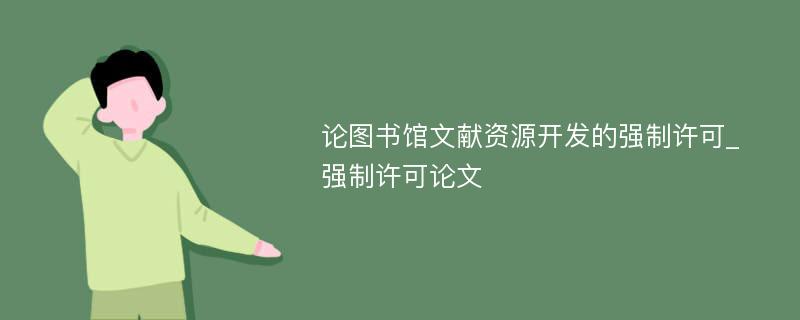
论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的强制许可使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开发论文,文献论文,图书馆论文,许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知识产权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我国图书馆界也开始着手研究知 识产权法对图书情报工作的影响,强制许可制度作为其中一项研究内容开始引起界内人士的 重视,但由于图书馆作为社会公众利益代言者之一,希望文献资源开发和传递能以低成本或 无成本进行,因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知识产权制度对图书情报工作的制约作用,这一点在 对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强制许可使用制度进行 认真研究。
1 强制许可使用制度概述
1.1 强制许可使用的概念
法律是协调社会各种利益的调节器,版权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版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予以认识,并加以平衡和协调。世界各国版权法在奉行对作者权利予以保护的同时,也注重 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国版权法以权利专有形式确认版权人对作品享有 权利的同时,又以版权限制制度对这种专有权加以合理约束,使社会公众能够利用作品。版 权限制制度主要包括: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公共秩序保留、经济权利穷竭、善 意使用、反向工程等。
所谓的强制许可,是指版权人在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授权他人以某种方式使用其作品时,作 品的使用者可以向本国版权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强制使用作品的申请,版权行政管理机关根据 申请颁发强制许可证,强制使用作品。它与合理使用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属“非自愿 许可”制度,后者属“自愿许可”制度。强制许可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对版权人专有权利的 限制,使社会公众得以利用作品,以促进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
1.2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待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的不同态度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的国家,它在1909年版权法中规定了这一制度[ 1]。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承认并采纳了这一制度,但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发展不平衡,导致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的规定也大相径庭。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国家更尊 重版权人利益,对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制定了严格的申请条件和繁琐的申请手续,并对允许使 用的方式进行严格限制。例如,美国版权法规定强制许可的适用范围为唱片许可、自动点唱 机许可、电缆广播许可和公共广播许可等四种形式[2],而且申请条件苛刻。强制许可证 在使用过程中也受到严格限制,若敢“越雷池一步”,强制许可证就会被收回。又如德国版 权法仅在第61条规定了“制作音响载体的强制许可证”。加拿大版权法有关强制许可制的规 定较为简单,其适用范围只有复制权和表演权[3]。
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往往以版权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 作为立法准则,鼓励社会对作品的使用,忽视版权人的经济权利。所以,发展中国家对强制 许可制度一般没有制定严格的申请条件和使用方式,适用的客体范围也较广,有的甚至覆盖 所有版权作品。个别国家甚至制定了与国际版权公约最低要求相冲突的强制许可制度。例如 ,菲律宾版权法规定,只要国家利益需要,政府即有权颁发复制教育、科学或文化领域作品 的强制许可证[4]。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这种与版权保护宗旨相违背的“强制”许可制 度持谴责态度。
1.3 我国立法机关对强制许可制度所持的态度
我国对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的立法有过激烈争论。1989年12月,由李鹏总理署名并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审议稿》中的第44条,规定了强制许可使用制 度,该条款规定:“作品发表三年后,如果著作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授权他人出版或以其他 方式传播,为了教育或科学研究的目的,经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可以强制出版或 者以其他方式传播,但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著作权使用费”。该条款的适 用范围和作品使用方式显然太宽,而且限制性条件也很少,这显然与版权保护的根本宗旨不 相符,特别是在社会版权意识淡薄的情况下,实施不受严格限制的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必然 会给版权维护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西方法学家也意识到“这项规定应用到西方图书上的范围 将太广”[5],因此,该条款在人大审议时未获通过,1991年颁布的《著作权法》删去了 该条款。尽管我国著作权法没有强制许可条款,不允许对国内版权作品进行强制许可使用, 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享有《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规定的优惠待遇,从理论 上讲可以颁发对外国版权作品强制使用的“强制许可证”。
2 国际版权公约中的强制许可使用制度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版权保护始终呈现出强化趋势,《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 约》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没有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落后 现状,使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政治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升,它们希望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外国版权作品,而发达国家作为版 权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品国,强化版权保护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极力反对削弱版权保 护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双方立场对立,矛盾尖锐。国际两公约中的强制许可使用制度 的确立,可以说是双方激烈论争、讨价还价的一个产物。
2.1 斯德哥尔摩会议
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伯尔尼联盟在布拉柴维尔召开非洲国家代表大会,非洲各国 代表强烈要求修改《伯尔尼公约》,提供特别许可权,使发展中国家为了教育和科学研究, 可以自由地使用国外版权作品。在1967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修订《伯尔尼公约》会议上,经 过激 烈争论,通过了《斯德哥尔摩议定书》,制订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其主要内容 是:
(1)缩短作品翻译权和复制权的保护期限。
(2)允许颁发不经版权人同意翻译其作品的非独占性的强制许可证。
(3)作品首次出版10年后,允许自由翻译。
(4)为教学、学习和研究目的翻译、复制外国作品时,可根据本国标准、以本国货币付给作 品报酬,此类出版物还可以向第三国出口。
该议定书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并拒绝在议定书上签字,西德政府原表示同意, 后又以遭到出版商协会强烈反对为由拒绝批准。到1970年,只有东德、罗马尼亚、乍得、塞 内加尔和巴基斯坦等5国批准该议定书。因没有得到多数国家的批准,使该议定书“流产” 。英国一位法学家评论这一事件时说:“作者和出版者看不到有任何理由为了帮助发展中国 家而让钱财从他们手里跑掉”[6]。
2.2 巴黎会议
为了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待强制许可使用国外版权作品问题上存在的分歧,197 1年7月5—2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主持下,于巴黎召开了修订《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国际会议。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允许发 展中国家颁发强制许可证,并将相关条款分别列入两公约的修订文本中,其主要内容为:
(1)允许颁发翻译出版国外版权作品的翻译权许可证。两公约其他成员国任何以印刷形式或 类似形式出版的作品,自出版起满3年后,其版权人没有授权将其译成本国文字出版,则任 何使用单位都可向本国的版权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将该作品译成本国文字出版的强制许可证。 如果译成的文字不是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上述3年期限可以缩短为1年。
(2)允许颁发复制出版外国版权作品的复制权许可证。两公约其他成员国的任何以印刷形式 或类似形式出版的作品,自出版后满5年(其中数学、自然科学或技术领域的作品自出版后满 3年,小说、诗歌、戏剧、音乐作品和以图书形式出版的美术作品自出版后满7年),仍没有 授权他人在本国发行,本国的任何使用单位或个人都可以向本国版权局申请复制出版外国作 品的非独占性强制许可证。
3 我国图书情报部门应用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正确分析和评价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的实际作用,是我国图书情报部门开发国外版权作品可 行性的关键所在。法学界部分人士认为,两个国际版权公约中的强制许可使用制度,是发展 中国家手中的“达摩克利斯剑”,它使版权所有者从拥有绝对的复制权和翻译权,降为只拥 有对复制权和翻译权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又使发展中国家以自己能负担的经济条件得到发 达国家的版权作品[7]。图书馆界的大多数人认为图书情报机构可以利用“强制许可证” 开发国外版权文献。肖希明认为:这两个公约规定的强制许可制度,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开 展资源共享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8]。冯锦生认为:凡是有条件进行翻译与出版工作的图 书馆及其他文献情报单位,均可利用上述有关规定,更好地去开发国外文献资源[9]。邵 葵认为:强制许可制度有利于文献信息的传播[10]。笔者认为: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对我国 大多数图书情报部门开发国外版权作品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国际两公约都对强 制许可证的颁发附加了如下一系列苛刻条件和复杂的申请程序。
(1)严格限制颁发强制许可证的客体和类型。可以颁发强制许可证的客体为外国版权作品中 的印刷出版物和为系统教学用的视听制品,艺术作品、雕塑和计算机程序,均不包括在内 。可颁发强制许可证的类型仅为翻译强制许可证和复制强制许可证,改编、表演等均不能颁 发强制许可证。
(2)作品的使用目的受到限制。翻译强制许可证只允许为教学和学术研究目的而颁发,复制 权强制许可证只允许为公众需要而成为系统教学目的而颁发,其中允许强制复制的“视听作 品”仅指以录音、录像形式复制国外专为教学准备和录制的视听资料,其他类型的录音、录 像制品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为教学需要)均不允许颁发强制许可证。
(3)允许强制翻译、复制外国版权作品的时间限制太长。就翻译权许可证而言,若翻译成中 文 出版,时间限制为作品出版后满1年,但申请者要再过9个月,方可获得强制许可证;就复制 权强制许可证而言,时间限制分别是作品出版后满3年、5年和7年,申请者要再过6个月才能 获得强制许可证。笔者认为信息如海鲜,越新鲜越值钱,翻译强制许可特别是复制强制许可 的时滞显然太长,图书馆如果利用上述手段开发国外文献信息,其价值将被大打折扣。
(4)申请程序繁琐,并以遭版权人拒绝授权作为申请前提。首先,申请人在申请强制许可证 时,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和国外版权人取得联系,要求对方授权其作品的翻译或复制使用,并 遭拒绝。如果无法找到国外版权人,也需加以证明。其次,申请人在向本国版权机关申请强 制许可证时,还要将副本寄给作品原出版者和作品出版国的版权中心备案,如无版权中心可 递交,则应将申请副本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版权情报中心。
英国《书商》杂志对上述规定曾评论说:“我们假设某一作品获得好评,引起发展中国家 的注意,出版业的起码逻辑告诉我们,翻译权所有人必然会受贿出售其作品,这不仅在经济 上有利可图,而且还要对译本出版、发行建立垄断控制,未必有哪个头脑清醒的出版商会坐 等和听任别人对他的权利实行强制性掠夺”。[11]由于遭版权人拒绝授权的可能性不大, 这使得图书馆获得强制许可证的机率大大降低。
(5)强制许可并非免费许可。过去曾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出版社误认为强制许可证“可以减免 版税形式用于教育和科研书籍的发放”,[12]其实,强制许可使用并非是“免费的午 餐”,利用该制度翻译出版或复制出版国外版权作品,仍需向版权人支付报酬,而且这项报 酬必须符合两国自由商谈版权转让时所支付的版税标准,所支付的货币必须是美元或德国马 克。所以,我国图书情报部门利用强制许可证开发国外文献,在开发费用上没有任何便宜可 占。
(6)强制许可证存在随时失效的可能性。图书馆利用强制许可制度,投入经费开发国外文献 ,在经济上也要冒一定的风险。根据两公约的规定,颁发强制许可证后,版权人又向他人发 出授权,许可其作品在我国使用,而且经授权翻译出版或复制出版的印刷品又与依强制许可 证印刷或出版的印刷品价格相当,强制许可证将立即失效。另外,两公约还特别在强制许可 有关条款中,承认版权人的收回权,即国外版权人一旦行使收回权,停止其作品在市场的发 行,则无论使用国是否承认收回权,均不得颁发强制许可证。我国著作权法虽未承认收回权 ,但我国作为两公约成员国之一,有义务遵守两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也是我国政府所持的态 度,《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1992年)第3条第3款明确规定:“如果《伯尔尼公约》和 《日内瓦公约》与中国国内法律、法规有不同之处,将适用国际公约。”
从上述限制性条件来看,我国图书情报部门所迫切需要开发的国外文献,要在出版后较长 的 时间才能强制翻译出版或复制出版,而且申请手续繁琐,还需使用美元或德国马克支付版税 ,这使得图书馆利用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变得十分困难。这一制度从表面上看给了我们一些“ 优惠”待遇,但实质上是对版权限制的限制,英国评论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 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影子。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五六个国家使用过这一制度。所以,我国图 书馆绝不能将开发国外版权文献的希望寄托在强制许可使用制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