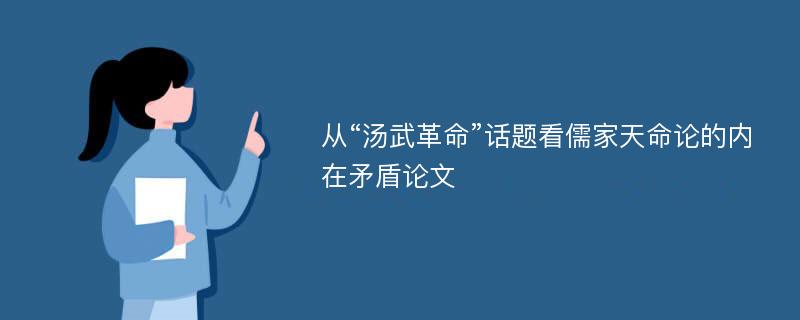
从“汤武革命”话题看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
杨永康
摘 要 汉代以来,“汤武革命”是受命还是放杀,一直是学者们议论的话题。苏轼、祝允明等人以“汤武放杀”说向主流的“汤武受命”论提出了挑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辩驳。“汤武革命”话题不断被拿出来争论,反映出儒家“君权天授”的纲常观念与“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关键词 汤武革命 ;天命论;内在矛盾
天命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出发点,它规定着皇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历来深受统治者的重视。从西周开始,统治阶层就逐渐形成了“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天命思想,到战国时发展成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儒家思想体系中还有一种观念被不断强化,这就是“君权天授”的纲常观念,即君权在儒家纲常伦理中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君权天授的纲常观念与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共同构筑了儒家天命论的基础,二者相互支持,互为依存。然而,历代学者对“汤武革命”的不同解读也反映出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一、汉初“汤武受命”之争与“逆取顺守”说的流行
兼并征伐是战国秦汉时代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学者大多认同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天命转移,因而邹衍五德相胜之说大为流行,汉初儒家学者极力鼓吹“汤武革命”,借以论证汉诛暴秦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所谓“汤武革命”,就是肯定汤武暴力革命是顺应天命人心的正义行为。儒家经典《孟子》有云:“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注] 《孟子·梁惠王下》卷二。 《易·革·彖辞》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尚书》之《汤誓》《仲虺之诰》《汤诰》《泰誓》《牧誓》《武成》诸篇均明确支持“汤武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在汉儒心目中,“汤武革命”与“尧舜禅让”一样,都是改朝换代的理想模式。然而,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一场关于“汤武革命”的争论,充分显现出儒家天命论的尴尬与困境: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注] 《史记·儒林列传》卷一二一。
如何评价汤武革命,黄老学说与儒家学说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以黄生为代表的黄老派认为,汤武以臣弑君,以下犯上,为放杀。以辕固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为受命。最终,景帝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平息了这次争论,但可以看出景帝从内心来讲还是偏向黄生的,作为君王谁也不愿意被人革命。这次争议围绕汤武是革命还是放杀展开,最后的结果是辕固生理屈辞穷,拿高皇帝来压人。虽然辕固生打着天下归心的旗号,支持汤武革命顺应天命,黄生的放杀论恰恰击中了革命论的要害,“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这种反问对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无疑是棘手的,甚至是难堪的。
任何儒者都无法无视黄生所提出的尖锐挑战,此后人们对汤武革命的看法趋向于“逆取顺守”之说。黄生与辕固生争论之前,陆贾谏高祖已有逆取顺守之说[注]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卷九十七,陆贾说高祖有云:“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文帝时,贾谊《新书》亦有言:“殷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隐其恶而扬其徳美,立其功烈而传之久远。”[注] 贾谊:《新书·立后议》卷十。 贾谊对汤武革命之看法就是较为典型的“逆取顺守”的看法,即承认汤武以臣放君、以下弑上,又表彰汤武为天下开利除害,立功烈于后世。可见,汉初学者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就存在着歧见。或受命,或放杀,或兼及两说。受此影响,汉以后很多人对汤武革命的正义性提出不同看法。魏晋至隋唐时期,逆取顺守之论成为人们的共识。西晋段灼论史时曾说:“昔汤、武之兴,亦逆取而顺守之耳。”[注] 《晋书·列传十八》卷四十八。 北朝时,长孙绍远也曾说过:“逮周武克殷,逆取顺守,专用干戈,事乖揖让。”[注] 《北史·列传十》卷二十二。 唐代官修《晋书》提及武王伐纣时说:“以三圣之知,伐独夫之纣,犹正其名教,曰逆取顺守。”[注] 《晋书·帝纪五》卷五。 唐太宗亦持同样看法。帝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无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注] 范祖禹:《唐鉴》卷三。 唐太宗显然从自己的角度解释汤武革命,以唐朝取天下的经验来看,改朝换代必然伴随着以下逆上,血流漂杵,太宗并不否认自己亦是以逆取天下。可见,认为汤武革命为“逆取顺守”的看法影响颇大。对唐太宗认为武王逆取天下,范祖禹并不认可,在评论这段对话时说:“太宗于是失言,《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异也。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所以为仁义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则无时而可也。”范氏虽然引用经典否定“逆取”之说,但没有从正面回答黄生的问题,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下页表4的数据显示:62%的学生能够将听到的故事复述下来;55%的学生能写出所听材料的摘要;仅有47%的学生可以根据所听语料前半部分推断出结尾;根据教材提供的语料,高达73%的学生能够参与到预设问题讨论中;59%的学生根据所听到的语料准备演讲,81%的学生能够适应POA听说教学模式提倡的小组合作学习;根据语料和不同的听说任务,79%的学生能够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
四是注重心理素质健康教育培训。针对监狱戒毒警察工作生活中面临的监管安全压力、执法安全压力等导致的心理问题,河南省司法厅联合高校举办由政工干部和基层业务骨干参加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引导政工干部把心理矫治的手段运用到干部思想政治工作中,引导基层一线警察掌握释放自我、缓解压力的手段和方法。各直属单位也把队伍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定期邀请社会心理咨询专家或利用单位内部心理咨询师对警察开展心理辅导、心理知识讲座、心理咨询、心理拓展、心理矫治等心理素质培训,使队伍掌握应对压力和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技巧,有效缓解工作生活压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逆取顺守”之说的出现与流行,反映了人们意识到革命说与放杀说各有其合理的一面,亦有其不通之处,力图融合二说。顺逆之际的矛盾尴尬,还是揭示了汤武革命在伦理上之困境,天命会转移到道德上存在重大瑕疵的君主身上吗?汤武的行为够得上圣人吗?这些问题必然会引发进一步的争论。
回到家,果果打开信封,读着信,忽然捂着嘴巴,默默地流泪。她仿佛想起她曾经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她仿佛想起了她曾经是世界五百强公司的著名建筑师,她仿佛想起了她为了更好的照看儿子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她仿佛想起了她带着高烧39.8度的儿子在繁华的街头冒雨打车却无人搭理,她仿佛想起了同样高烧39.8的她为了一分钟都不离开儿子而未及时治疗竟患了脑炎,最终失忆智力下降永远停在了16岁……忽而,她笑了,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慈祥而欣慰的笑。
二、苏轼的“武王非圣人”说及其反响
北宋苏轼“武王非圣人”之说的提出,再次把“汤武革命”的讨论推到前台,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汤武革命”的理论危机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苏东坡“武王非圣人”之说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注] 此段引文均出自苏轼:《东坡全集》卷一百五,《志林·十三条论古》。
南宋真德秀亦批评了苏东坡的观点。首先,认为武王取天下,非武王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文武皆圣人也,文王之时纣之恶未熟,故文王犹得以事之,至于武王之时,则纣之恶已极,杀比干,囚箕子,微子纣之庶兄也,抱祭器而归周,武王于此虽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岂武王之心哉”。其次,文王之事殷,武王之革命,均符合天道纲常。“但所处之时既异,故所行之道不同,文王所处乃君臣之常,武王所处乃君臣之变,常固正也,变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再次,孔子之所以对汤武革命略有不满是为了强调形势之不得已,替武王开脱。“然常道人皆可为,变则非圣人不可为。故圣人于汤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论乐则以武为未尽善,论泰伯之让天下,文王之事殷,皆称其为至德,伯夷则谓求仁而得仁,此非贬汤武也,盖惜其不幸而为此不获已之举也。然恐后世遂以汤武为非,故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言汤之变夏命,武王之变殷命,皆顺乎人心而应乎天命也。”最后,孔子为了防止后世乱臣贼子借汤武之名行篡逆之实,故对革命略有微辞。“故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顺天厥罪惟钧,《论语》微有不满之意者,恐后世乱臣贼子借汤武之名以窥伺神器也。《易》发革命之义者,恐后世乱君肆行于上,而无所惮也。圣人立言其为后世虑深矣,东坡乃谓汤武非圣人,盖但见一偏而不知圣人或抑或扬皆有微指也。”[注] 《西山文集》卷三十一,《问文王至德》。 真德秀的“常变”之论并没有超越朱熹“并行不悖”之说。其要旨在于对臣子强调伦理纲常,对君王则发明汤武革命之义,主张二者互补,但是同样回避了民生与君权发生冲突时,革命与纲常之间何以抉择,人们该如何自处的问题。
快到五十七岁时我才得到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的意思是: 书售出后可以收回成本。 《意大利印象》之前全都亏本,出书意味着破产。 不用说,那时我既没有“写作自由”,也没有“精神自由”,什么自由也没有。[3]429
再次,文王之道乃君臣两全之道,反对以兵取之、放杀之。“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改过,否则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在苏轼看来,“圣人出而天下归之”才是王者之道,既实现了有德者居之的理想,又维护了君臣之道两全的纲常道义。苏轼的论调很有一些现代民主色彩,未免过于理想化而显得有些迂腐,却也提出了不同于汤武暴力革命的天命转移之道。
矿区二叠系和古近系中火山岩均较发育。二叠系火山岩主要出现在早期,为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及熔岩。古近系古新统典中组火山岩在本区较发育,出露于矿区大部分地区,主要有气孔状安山岩、粗面岩、凝灰岩、火山角砾熔岩等。
其次,孟子表彰汤武革命,乱孔子家法,乃孔氏罪人。“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不惟孔子罪之,良史亦当罪之,周公亦罪之。孟子论汤武非符周、孔之意。
最后,武王不得已而封武庚,是为了缓解舆论上的压力。“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诛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盖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苏轼通过楚子南的故事,说明武庚之叛周,自有其道义上的责任与义务,并不值得谴责。更进一步揭示了武王不得已而封武庚是为了笼络人心,以减轻道义上之负罪感。
明代学者胡直以“公天下”的观点,支持“汤武革命”说,对苏东坡的看法进行了反驳。“故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克绥厥猷维后。又曰,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公天下之论也。故以殷之天下观天下,则武王之杀纣为非,以天下生民之命观天下,则武王之杀纣不为非也。所谓顺天而应人也。苏子非之,过也。”但另一方面,苏轼的看法引发了胡直的进一步思索,提出了“武王必不能释天下之归己”的观点,通过三点疑惑,间接揭示了太王、武王在臣道上存在缺憾。其一,武王不立箕子微子之疑。“予以为成汤放桀,夏之子孙无可托者,故汤自为之,若商尚有微、箕二子者在,箕子所陈《洪范》皇极之道,远绍执中,使箕子有天下,其锡福庶民岂下武王。武王既诛纣,释箕子囚,访闻其道,即尊而立之,继殷嗣可也。非独嗣殷也,盖箕子有敷锡庶民之道,使为南面宜也。武王素殷臣,率天下尊之,从而北面焉亦宜也。纵使箕子不欲有天下,则微子亦可王也,武王岂必自为之乎。武王必非如后世利天下者,然而计不出此何也。”箕子既为圣贤,武王何不尊之为王。由是观之,武王取天下难道没有私心吗?其二,武王置箕子于朝鲜之疑。“武王既不能释天下之归已,又不能强箕子以有天下,则延留箕子置之中国,天子师友而宾之,大小臣工师事之,又或分国而处之,使中国之民咸被敷锡生人之泽,则武王之心即尧心矣,然终置之朝鲜异域,使与中国眇然不相为,何其左也。”箕子既为圣贤,武王何不以之为师,置之中国,惠及百姓,反而将他放逐到异域,武王之心与尧心相差何其远矣。其三,武王篡商之疑。“周之先世太王生太伯及仲雍王季,斯时去武丁未远也。殷之泽方未艾,天下未有纣之暴,其天与人未厌殷也。其时季历虽有圣子如文王,而太王臣道也,恶得先有翦商之志,太伯又恶用逆,探其父之志,遂逃荆蛮以避之。谓其说诬,则孔子所谓三让天下又何以称焉。若太王果先有是志,武王终取天下而家之,则武王实成其先世簒窃之志,即《书》所谓弋殷命者是己,未为可也。”[注] 《衡庐精舍藏稿》卷十四,《疑论》。 太王已有翦商之志,武王成篡窃之实,则武王何以称天命。由此可知,虽然胡直支持汤武革命之说,但是更多的证据表明太王、武王不臣之志在先,武王无法合理解释自己取天下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使得胡直不得不对汤武革命的说法存疑。
本次研究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s) 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朱熹曾说:“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徳,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于此二者中须见得道并行而不悖处,乃善。”[注] 《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泰伯篇》。 朱熹认为孔子对泰伯、武王虽有扬抑,总体上都给予很高的褒扬,苏轼的说法有失公允。对于伦理纲常与革命的矛盾,朱熹采取回避与缓和的态度,认为泰伯奔吴,夷、齐不食周粟,乃坚守臣节之举,维护了君臣大义,其行为符合天地之常经,而汤武革命,除暴安民,天下归心,亦为古今之通义,二者并行不悖。朱熹对泰伯、夷、齐的褒扬,反映出黄生“汤武放杀”说、苏轼的“武王非圣人”之说对儒家伦理体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朱熹力图调和革命与纲常之间的冲突,采取了道并行不悖的说法,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因为在天为最大的伦理体系中,纲常伦理与革命对立显而易见。一方面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真理,另一方面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民本思想,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革命之际人们何以自处?
首先,孔子对周武王颇有微辞,只不过因为自己是殷的子孙、周的臣民,不便明说,但多次婉转地表达了怪罪之意。“昔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其可谓至徳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孔子表彰尧、舜,表彰周文王、伯夷、叔齐,就是怪罪周武王弑君之罪。
苏轼“武王非圣人”之说一出,就引起当时或后世学者的注意,他们纷纷发表议论,“汤武革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除洪迈等少数学者肯定苏轼的说法之外[注] 《容斋续笔》卷二《汤武之事》。 ,更多的学者对苏轼的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
三、祝允明的“汤武非圣人”说
明代学者祝允明进一步发挥苏轼的观点,提出了“汤武非圣人”的论断。祝允明在《罪知录》中首以“刺曰”立论“汤武非圣人”,次以“说曰”阐明理由,再次以“演曰”发挥自己的观点,最后以“系曰”汇集历代学者非议汤武革命的言论,论证有力,富于逻辑,可以称得上“汤武放杀”说之集大成者。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
首先,孔子并未称许汤武为圣人。“夫子《书》述誓诰武成,存其迹也,伯禽、秦穆亦存焉,安必尽圣乎。亦非以殷后姬臣而称存之。《书》圣贤言事皆录者,它日亦未始专称二君圣,二君固贤者过之者也。”祝氏认为孔子述《尚书》,其目的主要在保存史迹,并非专称汤武为圣人,汤武只不过比一般贤者略强而已。
其次,以德而论,汤武略贤于刘邦、李世民;以迹而论,实与王莽、朱温同列。“二君曷不圣,事不唐虞夏后类也。恶乎贤,贤于刘邦、李世民也。迹无殊尔,德贤之也。以迹则莽、温等尔。而刘、李且以贤过莽、温诸盗,况二君耶。如以功,则刘、李亦何歉于二君耶。”在祝氏看来,只有尧舜禹禅让,道德上没有瑕疵,可称圣人,余者非篡即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再次,孟子“诛一夫”之论背叛了孔子《春秋》之义。“孟轲言武王诛一夫纣,不为弑君。夫《春秋》无将,矧躬殪而攘之乎。无将、诛一夫,义不并立,轲果弗畔仲尼耶?”祝允明认为《春秋》大义在诛伐乱臣贼子,而孟子“诛一夫”之论却鼓励以下犯上,以臣弑君,完全背离了孔子之道。
最后,汤武吊伐并非出自公心,实乃为谋私利。“或以二君吊伐,亦大公耳。果若为公,癸辛既亡,胡不取文命之属,若武庚、微、箕辈为之乎。或又谓:微、箕虽贤,余固中人,固皆弗二君若也,弗己若也,不之立而自立,公也。又不然,癸辛之前,其君固尤弗二君若也,二君生是时,则固亦不放弑之矣。今也癸辛既亡,民吊罪伐已矣,余子犹其未亡之前,何不可立而存其世也,舍而自立,是本意不在吊与伐,果在吊伐,曷为以义举而不以义终之舆。反复参察,未知攸处。或又曰:此责二君过欲全也,吊伐既讫,使复继绝,固曰全善,然若秉公自立,恶亡善兴,民受其赐,倓然安之而无怨尤焉,亦可为已。夫是者固为之,即刘李之为也,今以二君同科刘李,少为过之固宜。病其作俑,乱天人大纲,翻以圣称,则恶可乎。”[注] 《祝子罪知录》卷一。 通过问答形式,揭示了汤武吊伐“以义举而不以义终”的虚伪性,进一步证明了汤武二君于德于功与刘邦、李世民并无太大的不同。
祝允明对“汤武革命”的贬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将汤、武与刘、李同列,与莽、温同论,认为汤武不配称圣人。指责孟子背叛孔子,认为孟子只是纵横者之流,连贤人也不配称。认为汤武吊伐,乱天人大纲。其言辞之激烈可谓离经叛道,祝氏对纲常伦理的绝对化走得比理学更远,其思想的保守性更为明显。“臣不得放弑乱君,子不得放弑顽父”,祝氏对“汤武革命”彻底的否定,一定程度反映了民本意识的没落和君主专制意识的加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祝氏从德、功、迹等方面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通过对比揭露了汤武革命的虚伪性,还是有所发明。
四、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
历代学者对“汤武革命”的不同评价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西周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天命观有其内在的缺陷。儒家传统天命观形成之际就包含着双重价值标准,一方面宣扬君权天授,君臣纲常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又标榜“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主义,鼓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命循环论。无论秦汉之际的五德循环之说还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论,都继承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汤武革命”成为天命转移之际的理想范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是,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缺陷也就此显现。在通常情况下,两种价值观念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天下为公”价值理念的实现依靠皇权“家天下”的政治模式来实现,而皇权政治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也需要“天下为公”的价值观来装饰。社会动荡或易代之际,“天下为公”与“纲常至上”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此时的人们如何抉择呢?传统的天命观显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革命”还是“放杀”之争也就随之而起。
黄生、苏轼对“汤武革命”的批判,使后世学者意识到儒家伦理体系之中存在着漏洞,并试图进行弥补,如朱熹的“并行不悖”之说、真德秀的“常变”之论,都在试图调和儒家天命循环论体系中潜伏的“君”、“民”二元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祝允明以“《春秋》无将”讨伐“诛一夫”,视孟子为孔子之罪人,将孔孟之道对立,充分反映了这种对立的尖锐性,同时也反映出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儒家伦理体系中传统的革命意识逐渐受到排挤,纲常意识逐渐被强化的趋势。正是基于这样的天命观,革命与忠君的情结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易代之际,新王指责旧君失德厉民,失去上天的护佑,其国当灭,标榜自己修德救民,获得上天的眷顾,应为天下主。另一方面,对于为旧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臣义士和不仕新朝的遗老遗少,舆论又不厌其烦地为之树碑立传。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有着共同的天命论作基础,它们各自都能从中寻找出自己的价值准则,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看似对立却为一体。
作者简介: 杨永康,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获得“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项目支持(项目编号:2016052001)。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7-0028-07
责任编辑: 王望
标签:汤武革命论文; 天命论论文; 内在矛盾论文;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