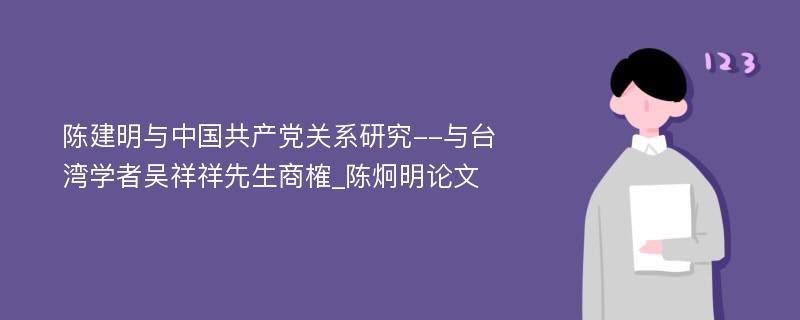
陈炯明与中共关系考——兼与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中共论文,学者论文,关系论文,陈炯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3)06-0045-07
从1918年经营闽西直至1923年败退惠州,陈炯明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与苏俄和中共都有过比较频繁的接触。因此,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即曾撰文认为陈炯明与苏俄乃至中共关系暖昧,并暗指苏俄与中共同1922年炮轰总统府事件(即“六一六”事件)亦有一定关系[1]。近年来,为陈炯明翻案者日众,但在这一问题上仍未见有学者较系统地指出吴氏的谬误。本文即拟根据笔者近10年来收集到的零星材料,作一考释,以求稍还历史以原貌。
一、漳州时期的陈炯明与苏俄
1918年至1920年间,陈炯明率粤军驻扎闽西漳州一带。这段时间,在其辖区内曾有宣传苏俄的刊物公开出版,而且苏俄曾经派人与陈炯明联络。因此,吴相湘在文中认定两点:“(1)陈炯明之公开歌颂俄共,早在五四运动以前。(2)民国九年初夏,俄共密使即达到陈处与陈密商。”[1](p.98)揆诸史实,从大体上看,这两点都是事实,但在细节上有些许出入。下面分头述之。
其一,宣传苏俄问题。
1919年夏,陈炯明所率粤军在闽西立足方稳,他即邀请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主持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梁冰弦等人赴漳州,共商大计。在梁冰弦等人的帮助下,是年底《闽星》杂志出版。从《闽星》所刊文章的内容看,该刊确实曾以很大篇幅介绍苏俄,并对苏俄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都有一些正面评价。然而,公开歌颂苏俄还不完全等同于完全认同苏俄。事实上,终陈炯明一生,他都没有服膺过阶级斗争学说,而这一点又正是列宁主义的精髓。据梁冰弦回忆,1919年当他初抵漳州时,曾与陈炯明有一次饭后长谈:
谈到社会主义运动,陈同意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小贫和大贫,没有显然的阶级,用不着斗争;中国向来一个皇帝独裁,实际是乡绅局董分裁;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似乎是世界共通的,实则将来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成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这是当时陈氏见解的重点。[2](pp.14-15)
征诸其它史料,海隅孤客(梁冰弦)的回忆录在言及他人提供的史实时,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份。不过,陈讲上述这段话时,梁毕竟在场,再考虑到他在香港写回忆录时并无为陈作伪的压力,因此便不能完全否定陈炯明在五四时期不愿完全学俄的真实性。实际上,我们也只有沿着这个思路,才能理解陈炯明晚年息影香港时,在一片“师俄”声中公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真实原因。
其二,会晤俄使问题。
1920年春,确实有苏俄代表来漳州晤陈。吴相湘先生根据《陈竞存先生年谱》与海隅孤客的回忆,猜测这个苏俄代表便是曾经帮助中共建党的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其实不然。
据陈炯明的朋友编订的《陈竞存先生年谱》记载,是年4月29日,“苏联政府密派路博将军到漳访问先生(指陈炯明——引者),愿设法资助先生完成革命大事业,先生以革命应赖自力,乃婉谢之,先生并有书致列宁”[3](p.25)。另据当事人梁冰弦的回忆,1920年苏俄代表赴漳州的原委如下:
住在天津策动组成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苏俄党人布罗威氏,通过闽南教育局职员冀籍姜某,进言陈老总(指陈炯明——引者),谓有列宁至友V氏(笔者现在已忘记其名字,只记得首音是V),将向亚洲诸国进行其推进革命任务,同时也为苏俄取得助力,方能挣破欧洲封锁难关。……老总对此作出乎意料的客气和坦率的表示,他说:“闽南,这中华民国的一个角落,刚巧由我在此看家,你们,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认为要干什么,只要商量过,最后经我同意,那便什么都不妨干去。比方这苏俄朋友,请他来先看看我们这里是否算得个地盘,这么个小局面是否算得有凭籍,一切谈谈也好。”[2](p.19)
在梁冰弦的回忆录中,还谈到了陈炯明等人要求苏俄帮助建立军事学校与军需工厂。如此,两段史料透露出两点不同:首先,年谱记载来访的是“路博将军”,而梁冰弦回忆的是一个姓V的“列宁至友”;其次,年谱记载陈炯明对苏俄的主动援助的意向采取了“婉谢”的态度,而梁冰弦回忆则认为陈炯明主动向苏俄代表要求获得援助。
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记载,1920年陈炯明也曾向他当面提出要求苏俄援助,两相印证,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年谱中所说陈炯明婉拒俄援,显系溢美之词。依照史料学的基本原则,亲身经历者的回忆一般要比道听途说者更接近实际,但这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铁律。就梁冰弦的回忆而言,由于时过境迁,他甚至忘记了来访俄使的真实姓名,以至吴相湘只能根据梁氏提供的俄使姓“V”这一线索,联想到另一姓“V”的苏俄代表维经斯基。而根据苏联后来公布的资料,这名曾经会晤陈炯明的苏俄使者,既不是年谱中所载“路博将军”,也不是吴相湘先生猜测的维经斯基,他的真实名字叫波达波夫,1919年即来中国活动,曾在上海、漳州和香港等地分别见过孙中山、陈炯明和国民党另一军事领袖李烈钧。1920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而梁冰弦听说他在回国途经远东时被仇家所害),不仅向苏俄领导人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还将他带回的陈炯明致列宁的信与李烈钧告苏俄人民书刊登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上。因此,陈炯明的这封信便成了揭开这一谜底的关键。
从现在见到的转译自俄文的《陈炯明致列宁的信》,可出看到,陈炯明对社会主义有颇多认同,如他写道,“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比较起来,李烈钧的《告苏俄人民书》倒更像一篇外交辞令。不过,陈炯明写信的深层动机可能还是争取俄援,在信的后面部分有一段写道:
我深信新的俄国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相信它对中国即将到来的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给予帮助和支持。在它的帮助下,中国人民,经过斗争和牺牲,将会更早地获得独立,摆脱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建立新中国。[4]
求援之心切,显而易见。经过波达波夫的推介,陈炯明给苏俄一些官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0年底,俄共西伯利亚局负责人威廉斯基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上也撰文认为:陈炯明是“苏维埃制度的追随者”,由陈领导的“真理社”则是“中国共产主义的组织”。[5]不过,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苏俄当局的高层人物对陈炯明发生兴趣的材料,不管是波达波夫,还是威廉斯基,在当时皆不具备能够在对华政策上拍板的权力。
总之,在1919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大变动之际,驻扎漳州的陈炯明也顺应了这个潮流,大力宣扬苏俄,这些甚至为漳州赢得了“闽南俄罗斯”的盛誉[6],苏俄也因此向他示好,使得双方一度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吴相湘先生所暗示的——陈炯明此时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因为即使是吴佩孚这种军阀,同样也曾因扩张实力的需要,同意在自己的辖区建立工会,并与苏俄有信使往还(注:如吴佩孚的高级幕僚白坚武就在1922年5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俄人霍德罗夫来保定谒吴公(指吴佩孚—引者),并以李守常(指李大钊—引者)之介绍同余作主义上之深谈,……与余订交,殷殷握别。”此后还记载了俄使数次访吴的经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一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况且,从相关材料看,陈炯明与苏俄接触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争取对方的物质援助。
二、孙陈分手前的陈炯明与中共
1920年8月,陈炯明率粤军回师东进,年底即占领广州。吴相湘先生认为:陈炯明在自己的地盘不仅默许陈独秀等人宣扬“过激主义”,而且他自己也信奉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过激主义”。吴的直接证据主要有二:
第一,1920年2月,在广州出版的《民觉》杂志曾经刊载陈炯明的一段话,对国会议员有所批评:
人类以互助而为生存,以努力而图进化,既无庸人自扰之人事,又何需法律政治以理其纠纷?法律政治起于人类之自扰自缚,其价值亦为中国山医命卜耳。人智日进,其末日当在不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政客者且将随之而受末日之处分。然当此人类社会尚在自扰自缚时代,欧美政治家或为世俗所目存,唯吾国则如彼政治家者实所罕见,所谓政客者则为世所诟病,政客寄生于各界,国会议员占其一部分,议员中不无自好之士,然一入盗跖之门,群以盗跖目之,无足怪也。[1](p.100)
第二,1921年秋,陈炯明曾在广州公开赞扬工会,反对私有制:
现在广东的工会已陆续成立,但是组织上还要注意!原社会所以发生一种恐怖的现象,此其恶根皆由于现在经济社会制度尚许各个人有私有的特权,因此而人类遂生出自私自利的念头。此种自私自利的念头,根本上可以动摇社会的秩序,结果使人类彼此相争相夺,若不将此项制度设法调剂,人类痛苦,实无可救药。[1](p.102)
从第一件证据看,应该承认陈炯明的思想中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的苗头,这可能与他受梁冰弦等人的影响有关。但是,陈炯明的主要目的还是砥励议员端正品行,而这也确实是当时议员,包括那些南下支持孙中山的所谓“非常国会”议员的一个紧迫问题。据孙的亲信吴铁城事后回忆,在这些南下议员中,“高瞻远瞩且能侃侃而谈,富有正义感而能守正不阿的,意气虽消沉却能洁身自好,综共不过五六十人,约居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数不堪承教”[7]。陈炯明在通篇中并未强调要在当下废除议会这类国家机器,这一点便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有了质的不同。至于第二件证据,可以看出陈炯明当时具有“私有为万恶之源”的思想,不过,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思想。连臭名昭著的安福系政客王揖唐都可以高谈“民生主义”[8],陈炯明的这种思想也就算不上非常出格了。
应该承认,从漳州回到广州的陈炯明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但与孙中山身边的许多亲信,如戴季陶、邵力子、沈玄庐等人一样,陈炯明虽认同财产公有,但仍无只言片语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仅这一点,便与中共的理念绝然不同。不过,也应该承认的是,正是在陈炯明的庇护之下,中共在广东的早期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据《陈竞存先生年谱》记载,曾经有人向陈炯明告密:他所聘来的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但陈炯明只是“一笑置之”。从笔者看到的资料看,那些告密者的说辞并非空穴来风。初到广东时,陈独秀说话还比较谨慎,对于广州青年,只是希望他们“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两个月后,即开始大谈特谈社会主义,而且明白无误地告诉广州青年:“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10]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非但如此,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成立,其经过不仅颇为顺利,而且称得上大张旗鼓。据当时的报纸记载:
本月十四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假座东园开成立大会,并举行马克思纪念会,互助总社亦加入一并举行。是日团员、社员、来宾赴会者,共有三千余人。……是晚该团所组织之青年剧社亦于是晚七时开演《碧海磷香》,专揭破资本制度之下遗产毒害,并开影俄罗斯大革命画片以娱来宾。是晚来宾约三千余人,……[1]
白天开会有3000人,晚上看戏又是3000人,联想到半年前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开会时的东躲西藏,中共早期成员在广州的活动空间之大,在全国范围内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若无实际掌控广东的陈炯明之庇护与允许,这种盛况的出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陈炯明对中共活动的宽容态度,当然也会引起中共成员的好感。高语罕,1920年入团的中共早期成员,于1921年10月间作为安徽代表赴广州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当年11月7日他见到刚从广西前线回到广州的陈炯明,后来他记下了这段观感:
晚间古政务厅长(即古应芬——引者)、邓参谋长(即邓铿——引者)、孙市长(即孙科——引者)请在财务厅公宴。因为今天陈竞存先生凯旋,在座者有中上层军官全体,政界、学界、绅界、商界、工界以及各省教育会代表,共计二百余人。饮酒高歌,人人皆有一种愉快的样子,而陈竞存先生一言未发,大有“凯歌高唱几人回”的痛定思痛的心思!陈竞存先生,我不把他当作一个武人,也并不把他当作一个政治家,只把他当作一个我们人道主义的“保护者”!他没有嗜好,不要钱,生活无异于常人,这是他的私德高洁的地方;他终日孜孜不倦的服务,这是他公德过人的地方;当那不得志的时候,能屈己以下人,委身于朱庆澜的亲军统领,后来卒由此一成一旅之众,崛起漳州,一战胜桂,这是他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忍小愤以就大谋的地方;当那军事方殷、需财孔亟的时候,毅然拒绝一千多万的赌饷,这是他伟大人格的表现!以此数端衡诸全国将帅而无愧色者,陈竞存而外还有谁!陈竞存而外还有谁![12]
不难看出,这种赞美之词,事实上已远远超过好感的范围,而称得上崇敬了。
综上所述,1920年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直到1922年与孙中山分手,这段时间他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是颇为融洽的。虽然仍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时在思想上已认同中共的理念,但中共在广东的发展也确实得益于陈炯明的庇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正因为此,1922年4月,当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所提6点反对理由的第4点即是:“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13]对陈炯明实力的看重,溢于言表。
三、孙陈分手后的陈炯明与中共
1922年6月16日,粤军炮轰越秀山总统府。这是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也是陈炯明与中共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发生之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曾赴惠州与陈炯明会晤,至于这次会晤的详情仍是待解之谜,但在吴相湘先生笔下,二陈会晤却与孙陈分裂有某种连带关系。譬如,吴氏《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一文在介绍1922年5月陈独秀曾赴惠州谒陈炯明一事后,即警示道:“震惊中外的陈军炮击广州孙大总统府事变即在是年六月十六日发生”[1](p.107),似乎陈独秀的惠州之行暗藏某种交易。
二陈会晤确有其事,因为陈演生的年谱、梁冰弦的回忆和陈公博的回忆皆曾提及。但对陈独秀此行的动机,则说法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此行是劝陈炯明加入中共,这也是吴相湘先生认为二陈会晤含有阴谋的主要理由。据梁冰弦回忆,陈炯明亲信陈秋霖一日访晤陈炯明,意外地在门外听见陈独秀与陈炯明之间的谈话:
(陈秋霖)步至邻室,知竞存那边有客正剧谈,止于邻室,谛听移时,那边只一宾一主,复辩出语音为陈独秀,姑且听听说甚么。原来这说客滔滔汩汩演说一大通,乃劝竞存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发展。竞存则兜着大圈子,本其平日口吻,纵谈“各取所需”和“各取所值”这二大原则,暗示他正怀疑马克斯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法则。独秀又说要干不能徒恃军队,广大的工人群众负很大的任务。竞存更示反对,他说现阶段中国劳动运动只宜作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以后将不可收拾。独秀抹了一鼻子灰,怏怏而退。[2](p.39)
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抵惠州只是礼节性拜访。据当时的中共广东地方组织负责人陈公博回忆,陈独秀是由陈公博和陈秋霖陪同而去的,但陈公博不愿见陈炯明,所以当陈独秀与陈炯明晤谈时,陈公博与陈秋霖正在惠州城内游玩,只是在回广州后,才谈到联陈或联孙的问题。陈公博后来写道:
仲甫先生在回沪之前一日,约我在宣讲所谈话,我记得是下午,学生已经放学,……他说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我们应知有所适从。论道理是应当联孙,论力量是当联陈,问我有甚么意见。仲甫先生到底是刺探我的,还是真要问我主张,我至今不敢判断,但我正色对仲甫说,我们暂时不说道理和力量,孙先生到底是中国一个人,陈炯明纵然了不起,也只是广东一个人,何去何从,先生当知所择。仲甫先生听了我的话,默然一回,说我们看罢。(注:陈公博:《我与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广州:1981年内部出版,第103页。)
陈炯明与陈独秀的这次重要会面,在梁冰弦那里,属于听人所言,故可信度不高,起码在时间上便不可信,因为梁氏回忆录所记时间是在炮轰总统府事件之后,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在陈炯明公开反对孙中山后,根本不可能再去违背共产国际的意志而与陈炯明长谈,所以梁所说的陈独秀劝陈炯明加入中共一说,不太可信。而吴相湘以此暗指陈炯明与中共之间的某种交易,更是别有用心的先入之见。陈公博是二陈会晤的当事人,故比梁冰弦的回忆更为可信,但考虑到陈公博当时也未亲临二陈会晤的现场,后来在国民党内他又须借重孙中山的大名,故他对陈独秀的那番话也可能有事后为自己洗涮的成份,不可尽信。
在新的资料出现之前,陈独秀与陈炯明在惠州会晤的详情还只能存疑。不过,根据笔者现在掌握的材料,在1922年6月的炮轰总统府事件发生后,也确实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可以大致反映中共与陈炯明之间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其一,尽管1922年6月16日炮轰总统府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很快采取联孙反陈的态度,从而与苏俄的对华政策保持了一致,但这中间不是没有犹豫。
据张国焘回忆,事件发生之际,陈独秀立即向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表示: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为此还处分了同情陈炯明的广东党组织领导人(包括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14]。但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可能主要还是在于苏俄的压力。事实上,1922年6月,中国政局发生突变之际,苏俄的选择,早已不是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而是在孙中山与吴佩孚之间。如前所述,若苏俄方面对陈炯明还有丝毫兴趣,便不会在波达波夫自漳州回国之后,不给渴望俄援的陈任何表示。毕竟,以陈炯明在全国的影响力,是不能望孙中山或吴佩孚之项背的。(注:上海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在1922年底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11月4日的投票结果是:孙文(第二名)、吴佩孚(第四名)、陈炯明(第十名);11月11日的投票结果是:孙文(第一名)、吴佩孚(第五名)、陈炯明(第十二名)。这个结果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外国人对三人的定位。详见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也正是在苏俄的影响之下,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22年发表宣言,明确指责英国“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15]。言下之意,陈炯明成了英国人的走狗。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这也是中共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对陈炯明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
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22年6月15日,也就是陈炯明的军队炮轰总统府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中一段却暗含着对孙中山的批评,该文件写道:
又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其实这办法之内容也决不是解决时局的办法。在第三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上,联省自治自然是没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但是我们所认为不违背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是由民主派执政的自治省联合起来,组织联省政府,来讨平非民主的军阀政府,……决不是依照现状的各省联合——联省自治政府和北京政府脱离就算完事,因为这乃是联督自治不是联省自治;更不是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几个封建式的军阀就可以冒称联省自治的,……[16]
从表面上看,对联省自治的质疑即意味着对陈炯明的质疑,因为陈炯明作为当时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过,后面特意对联合皖系的卢永祥与奉系的张作霖不以为然,则显然不是,或者起码不是专门针对陈炯明的,因为揆诸史实,当时正热衷于与卢永祥、张作霖组成反直三角同盟的人,不是陈炯明,而是孙中山。因此,在实质上,这段话所表明的内涵还是各打五十大板,在孙陈之间不偏不倚,而这显然与苏俄袒孙弃陈的态度有一定差距。
其二,不管苏俄和中共对自己采取何种态度,陈炯明很少或从未公开抨击苏俄与中共,即使中共宣布与自己决裂,陈炯明也未对中共采取报复行动。
1922年6月23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曾致电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告诉他自己“经历着陈炯明——一个多亏有文(指孙中山——引者)方有其一切之人,造成之严峻危机”;[17]是年8月,在致苏俄代表越飞的信中,孙中山再次强调:“陈炯明是一个坏人”,并声称:“人们能够理解一个在基本政策问题上脱离其政治领袖的政治追随者。但是,当这样一种脱离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它就打击了全部政治生活的根基。”[18]值得注意的是,在给苏俄方面的两封信中,孙中山都格外强调陈炯明之错在于以下犯上。这种解释颇让人意外,因为:第一,作为一个革命性政党,俄共并没有严格的类似于东方人的尊卑观念,所以在他们看来,以下犯上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第二,孙中山自己也是造反起家,若严格按照不许以下犯上的逻辑,孙自己的反清义举同样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不过,孙单从陈的政治道德,而不从政治思想和行为的角度离间苏俄与陈炯明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证了陈炯明在广州期间并没有不利于苏俄和中共的言行。否则,在这个方面做文章,应该更能引起苏俄对陈的反感。
另外,据当时广东党组织的成员梁复然的回忆:“陈炯明叛变后,抱怨共产党没有与他合作,于是转而成为憎恨广东党组织。他下令禁止进步书刊发行,连一向在昌兴街丁卜蚊帐店代售《响导》的发行机关也被禁闭,搬走文件书籍,只准卖蚊帐。”不过,就在同一篇回忆录中,梁复然也承认:像“群报”、“宣传员讲习所”、“注音字母教导团”这类组织,是中共主动提出停办的[19]。而且,综合现在所有的相关资料,都没有发现陈炯明及其部下在炮轰总统府事件之后武力镇压中共的证据。连梁复然在20世纪60年代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广东党组织只是转入“半公开半秘密活动”,没有完全转入地下。
非但如此,在1923年陈炯明还数次召见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身份的彭湃,表示对农会活动的支持。不管是别有用心,还是惺惺作态,陈炯明从败退惠州直至1924年2月,一直支持彭湃领导的惠州农民运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中间,对于手下压制农会的要求,陈炯明也曾数次予以干预。而且,据彭湃事后回忆,陈炯明还曾向他流露过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欣赏,主张“化私为公”,反对“抢私为公”,仍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思想[20]。
总之,在孙中山与陈炯明正式分手后,为了适应苏俄既定的联孙政策,中共立即与陈炯明划清了界限,为此不惜处分了广东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但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与曾给予自己极大支持的陈炯明决裂,中共还是表示出短暂的犹豫,而且,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在炮轰总统府事件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与陈炯明仍有往来,但双方也没有像孙中山与陈炯明那样势同水火,一方面陈炯明未对中共采取报复措施,另一方面仍容许中共地方组织在自己的地盘开展农民运动。
四、余论
综上所述,从经营漳州到败退惠州,陈炯明与中共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一个合作——决裂的复杂过程。在1922年6月炮轰总统府事件发生之前,双方通过合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益处,但这种合作也是以陈炯明企图获得苏俄援助为前提的。在炮轰总统府事件发生之后,尽管中共中央的态度一度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了联孙弃陈的态度。这中间,苏俄的取舍自然是一个关键因素,但也不能完全忽视陈炯明与中共之间在政治思想上的差异。总观陈炯明的一生,从早年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到晚年大谈基尔特社会主义,应该承认其思想中包括一定的社会主义成份。但从来没有证据能够说明陈炯明曾经认同中共的理念——马克思主义,相反,在其晚年手订的《中国致公党修订政纲意见书》中,表现出与中共理念的直接冲突。如谈到经济建设时,陈炯明强调:
经济建设,须有全国性计划,以谋发展之平衡与配合之妥善,惟计划之订定,必须依照民主方式。在计划规定之下,人民须有充分经济企业之自由,除保护劳工及防止法律独占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本党认为经济民主应以此为起点。[21]
“人民须有充分经济企业之自由”,仅这一点,不仅表明陈炯明对待当时正在流行的“计划经济”思潮的不以为然,也足以表明其思想与中共理念之间的巨大差距。吴相湘先生一味地将陈炯明与中共装进同一只篮子里,完全无视这种差距的存在,如果不是学术上的无意疏忽,那就只能是政治上的别有用心了。(谨以此文纪念新近去世的老友、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双璧先生。)
收稿日期:2003-03-25
标签:陈炯明论文; 陈公博论文; 孙中山论文; 陈独秀论文; 1920年论文; 台湾总统府论文; 中国漳州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吴佩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