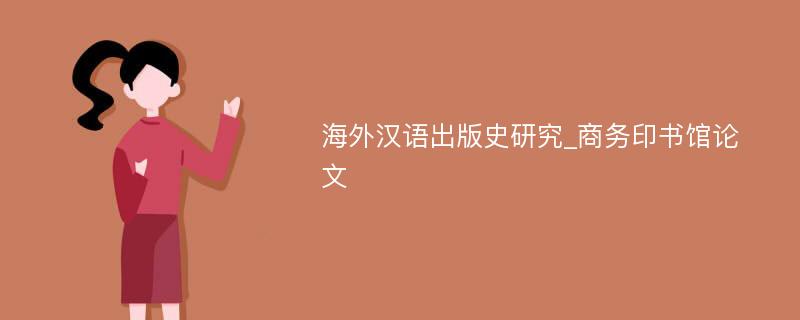
海外中国出版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版史是对出版历史进行总结归纳的学科。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国度,中国具有悠久的出版历史。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一直是海内外的学术热点之一。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是指域外人士用英、日等文种出版的研究著述。由于外文的语种很多,本文主要介绍以英文为主的撰述,兼及其他语种。
从1925年美国出版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著作至今,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已经有了八十余年的历史。根据这八十年来的研究情况,我们可以将它分为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阶段。
一、海外早期的中国出版史研究
海外早期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刷史方面。
较早对中国印刷史进行研究的是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847年,他发表在Journal Asiatique上的“Documents sur I‘art d’imprimer a I' aide de planches au bois,de planches au Pierre et de types mobiles”一文,对中国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物的发现,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造纸和印刷术西传的兴趣,由此也引发了西方对中国印刷术研究的高潮。①但真正集大成的,则是美国的卡特(T.F.Carter),他是最早系统地对中国印刷史进行研究的学者。作为一个美籍学者,卡特对中国的印刷术怀有浓厚的兴趣。而哥伦比亚大学又是美国大学中最早设置中国文化教席的名校之一。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时任中国文化系主任的卡特(T.F.Carter)的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该书利用大量中、朝、日、阿拉伯文等史料,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叙述,是海外最早对中国印刷史进行研究的著作。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中国印刷术的背景”,介绍造纸的发明、印章的使用、石碑拓本、佛教对印刷术的促进等;第二编是“中国的雕版印刷”,介绍雕版印刷发明的经过、最早的雕版书、宋元时代的雕版印刷等;第三编“雕版印刷西传的进程”,介绍雕版印刷术向国外具体的传播过程;第四编是“活字印刷”,就中国的活字印刷、朝鲜的活字印刷、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与中国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卡特的这一著作,后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加以增补,在1953年重新出版。后又经美国富路德(L.C.Goodrich)增订,在1955年出版。卡特的著作在1925年出版后,就由中国人刘麟生采用文言,翻译成《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世界名著丛书》中于1928年出版。由于翻译该书时,删削了部分内容,加上一些注文没有译出,向达曾重新翻译该书数章,刊载于《图书馆学季刊》上②。195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吴泽炎重新翻译的译本,并定名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该书除对部分字句做了改动外,还以译者按的形式补充了一些材料。
1930年,日本东京的三秀舍出版了中山久四郎著的《世界印刷通史》。该书的第二编是“支那篇、朝鲜篇”。“支那篇”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过程作了介绍。又分两篇。第一篇“支那印刷史前记”,介绍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背景及其过程;第二篇“支那印刷史本纪”,从隋唐时代印刷术开始应用起,一直写到当时的民国,对历代有代表性的印本、印书机构、印书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介绍。
1931年,日本东亚研究会出版了长泽规矩也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该书共十篇,记录了当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的新旧书店情况,对了解当时的图书出版和发行情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94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吴光清(Kuang-tsing Wu)先生以Scholarship,Book Production and Librariesin China,618-1644(《初唐至明末的中国学术、图书出版及图书馆发展史》,未公开出版)为题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芝加哥大学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该文对初唐至明末的公私藏书、印刷出版、以及目录校勘等学术活动进行了研究,涉及初唐至明末这一阶段的出版史研究。
这一时期,海外不少学者发表了一些零散的论文,对中国印刷史进行了研究。如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曾撰写了《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一文,介绍了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传入西方的过程。该文曾由张阳麟翻译后,发表在1926年7月的《学衡》第五十五期上。日本藤田丰八博士撰写了《中国印刷起源》一文,认为“印刷之术,滥觞于印度之佛像印刷,流传以入于中国,而其术大成,此似为不可争之事实也。”③该文虽从佛像印刷入手研究印刷术的起源问题,但由此得出印刷术起源于印度的结论,却缺少说服力。此文由杨维新翻译,刊登在1932年3月的《图书馆学季刊》第六卷第二期上。日本长泽规矩也的《宋元刊本刻工名录初稿》,将130种宋元书中的刻工按笔画进行了编排,对了解当时的刻书情况具有一定的价值。该文由邓衍林译录,刊登于1934年9月的《图书馆学季刊》第八卷第三期上。美国恒慕义(Arthur W.Hummel)撰写的《中国活字印刷术之检讨》,介绍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中国人墨守雕版印刷术的主要原因。该文由刘修业翻译,刊登于1948年6月的《图书季刊》新第九卷第—二期上。
至于没有译成中文的外文论文则更多了。如Lionel Giles1929年在British Museum Quarterly上发表的“Early Chinese Printing”、Kwang-tsing Wu(吴光清)在1942年、1950年的Harvard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的“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Chinese Printing under Four Alien Dynasties,916-1368”;在1952年的Library Quarterly上发表的“The Development of typography in Chin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等文,便是其中的代表。
总的看来,早期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在对中国印刷术的研究上用力甚多,尤其是侧重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西传等进行研究。
二、海外中期的中国出版史研究
海外中期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以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先生的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中文通译名《书于竹帛》)的出版为开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海外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视角更为宽广。这一时期,在中国印刷史研究领域,关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并在出版管理、传教士在华出版等其他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6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存训先生的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对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700年前后中国书籍的发展历史做了全面的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2004年,该书出版了最新的英文版。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的底稿是作者的博士论文The Pre-printing Record of China: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和图书》。该书的英文本出版后,立即在东方和西方世界引起轰动。除不断重印外,还被译成了中、日、韩等其他文字。尤其是中文版,有了四个不同的版本。1975年,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的《中国古代书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郑如斯教授增补的《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96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以《书于竹帛》为名,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2002年,上海的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以《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题,出版了该书的第四次增订本。2004年,该书被选入“世纪文库”,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书店再次印行。
1985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存训先生的另一部重要著作:Paper and Printing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ume 5,《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对中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过程、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研究的最高水准。该书原是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中的第三十二章。该书前三部分论述纸的发明与发展,后六部分论述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向世界各国的传播过程,及其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该书同样有多个中文本。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北京的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祖慰教授的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199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拓、汪刘次昕的译本《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造纸与印刷》。2004年,该书的中文原稿本由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编订、增加了新材料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为名出版了最新的中文本。
1981年,苏联莫斯科出版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Терентъев Катанский)著的《西夏书籍业》,以黑城发现的西夏图书为研究对象,分“西夏书籍的制作技术”、“黑城所出注明年月的西夏书籍和写本”、“西夏书籍的装帧艺术”、“写本书”、“印本书”、“11-13世纪的西夏文献—黑城遗书”、“书籍与人”等7章,对西夏书籍的制作、装帧、书籍的生产者等作了介绍。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曾供职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从事西夏学的研究。该书已经被认为是西夏书籍史领域的经典著作。200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克孝、景永时译的中文本。
1983年,伦敦的Wynkyn de Worde Society和纽约的Fredetic C.Beil共同出版了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的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中世纪中国的印刷和出版》)一书。该书对纸的发明、印刷术的起源及其原理、印刷术的发明过程、雕版印刷的优势、活字印刷技术的研制、早期的图书出版与图书销售、有代表性的印本等做了介绍。
来华传教士推动了中国出版的发展,他们在华的出版活动也是值得关注的焦点。1977年,Adrian Arthur Bennett所著的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这是最早系统研究傅兰雅的著作。傅兰雅(John Fryer)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华期间曾参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工作,并创办了《格致汇编》等刊物。该书对了解晚清传教士在华的出版活动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何凯立(Herbert Hoi-Lap Ho)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A study of their programs operations and trends,对1912-1949年间在华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做了研究。该论文1988年由香港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出版。该书从当时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出发,对民国时期传教士的角色和活动、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的历史及其组织、出版物的内容及其特色等作了探讨。2004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建明、王再兴翻译的中文本,并将题目定为《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
中国政府对出版业的管理这一课题,也有人开始涉及。Lee-Hsia Hsu Ting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1900-1949,对晚清后期和民国时期政府对新闻出版业的管理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该文1974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专门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进行研究的著作。
1970年,Florence Chien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1897-1949,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及对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1972年,法国的戴仁(Jean-Pierre Dr è ge)以商务印书馆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1897-1949(《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该论文1978年由法国高等汉学研究院出版。全书共四章,考察了商务印书馆诞生与成长、兴盛与衰落的过程,在国际上具有极大的影响。该书由李桐实翻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内部印行,2000年公开出版。
1978年,新西兰籍华人叶宋曼瑛又选择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她的博士学位论文——From Qing Reform to Twentieth-century Publisher: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 1867-1959(《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共十章,对张元济一生的思想与事业进行了系统研究。其评价客观而公允,代表了海外对张元济的评价。198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论文的英文本。199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人凤与邹振环合译的繁体中文本。
日本学者大庭修所著的《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就中国书籍输入日本及其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做了阐述。该书由戚印平、王勇、王宝平翻译,1998年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芝加哥大学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在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4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译书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威尔斯利学院魏爱莲(Ellen Widmer)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96年第36卷上发表的“The Huan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A Study in Seventeenth-century Publishing”(《杭州与苏州的还读斋:17世纪的出版业研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在Late Imperial China上发表的“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Fujian”(《中华帝国晚期的商业出版:福建四堡的邹氏与马氏家族刻书》)等,也具有较大的影响。
此外,1968年,Sidney Fosdick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Chinese Book Publishing During the Sung Dynasty,960-1279”(《宋代的中国图书出版》)、潘铭燊(Poon Ming-sun)1979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960-1279”(《宋代图书印刷史》);马庭理(Edward Martinique)的“Chinese Traditional Bookbinding”(《中国传统书籍的装订术》,San Francisco 1983)、米乐(Constance R.Miller)的Technical and Cultural Prerequisites fo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the West(《中西印刷发明的技术和文化先决条件》,San Francisco 1983)、卢秀菊(Shaw Lu Shiow-jyu)的 The Imperial Printing of Early Ch'ing China,1644-1805(《清初殿版书籍考(1644-1805》,San Francisco 1983)、艾思任(Soren Edgren)编的Chinese Rare Book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美国收藏的中国善本书》,New York,1984)等书,也都涉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近期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
2000年以后,西方的中国出版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如“文化权利”、“公共领域”等概念,对中国出版史进行研究,强调中国出版史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关联,及其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二是对个案研究特别重视,通过分析个案,使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
近期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以美国学者最为活跃。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贾晋珠(Lucille Chia)的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印书牟利: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选择福建建阳作为地区个案进行研究,探讨了这一地区的书籍出版在宋元明时期的发展。尤其是对这一地区书籍贸易情况的研究,对更好地评价和了解坊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周启荣(Kai-Wing Chow)的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现代化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利》,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以明代中国的出版为切入口,用文化权利、公共领域等概念,对明代中国的出版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全书从书籍生产成本和书价探讨起,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书价比西欧的便宜,士大夫普遍能买得起书。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书籍出版在明代的地位、科举考试与出版的商业化等问题。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的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古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对引起近代中国革命性变革的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过程进行了研究。该书在辨析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印刷资本主义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对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的历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全书以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例,对印刷技术引起的新式出版业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分析。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周启荣(Kai-wing Chow)合编的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图书文化》,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是一部研究晚明至清的中国出版史的论文集。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晚明至清的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了探讨,涉及传统雕版的优势、晚明时期新阅读群体的构建、晚清畅销型商业出版物、明清时期小说市场、清代的非汉文出版等多个主题。
这一时期,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也为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贡献了力量。
英国剑桥大学约瑟夫·麦克德莫特(Joseph McDermott)的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国书的社会史:晚期中华帝国的图书和文人文化》,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是最新出版的研究中国图书史的著作。该书主要探讨1000-1800年间中国图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对图书的销售和市场结构等进行了探讨。
德国海德堡大学鲁道夫.G.瓦格纳(RudOlf G.Wagner)近年来也对晚清的中国出版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采用公共空间理论对美查及其申报馆的出版业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的《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文稿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申报馆早期的书籍出版(1872-1875)》(中文稿载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文章,对申报馆的出版事业及其贡献作了新的阐述。
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所著的《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2000年,增补本2004年),对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历史及其与日本的交流进行了探讨。该书着重对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情况进行了分析,对这一影响早期商务印书馆发展的关键性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合资,是双方之间的一次自愿合作。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海外出版史研究,已经侧重从社会史、经济史等角度来进行,标志着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化。
纵观海外八十余年的中国出版史研究,我们发现,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已经从早期的中国印刷史研究,转向探讨中国出版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等多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借助文化权利、公共领域等一些概念,重新构架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将继续成为海外的主流。可以预料,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将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5JA87005)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
②刘麟生翻译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出版时间,不同书上的介绍各不相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未列出出版时间,无从查考。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收录的《五十年来新闻出版印刷书刊目录》著录该书出版于1938年。钱存训先生编的《中国印刷史简目》(载《装订源流与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著录该书出版1928年。方厚枢先生的《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后所附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也著录该书出版于1928年。由于本人未找到原译本,暂认为出版于1928年。
③转引自: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编.中国印刷史资料汇编.第二辑.内部资料.1986,323。
标签:商务印书馆论文; 北京印刷论文; 文化论文; 芝加哥大学论文; 读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印刷术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