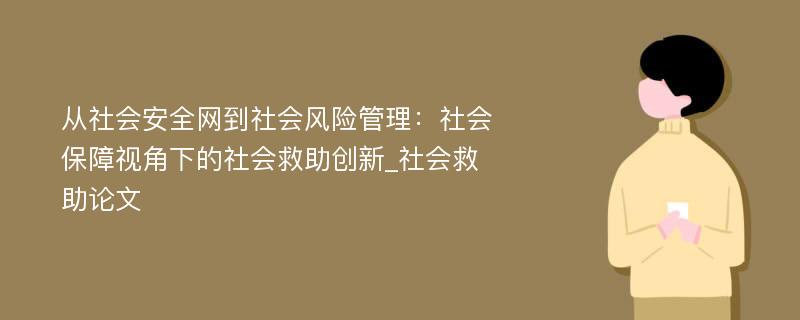
从社会安全网到社会风险管理:社会保护视野中社会救助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安全网论文,风险管理论文,视野论文,社会救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118-10 在经济生活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在帮助并提升民众防范与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更有利于财富创造上的重要性日渐凸现。20世纪伟大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曾经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归结为市场机制和社会保护制度建设的双重反向运动,即市场化的推进摧毁了传统社会中家庭与社群对成员的保护功能,将民众推入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由此激发出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国家与社会以各种方式为民众提供了风险防范的新制度。[1]在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各国民众更多地曝露在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也无法预见的风险之中,发展与完善社会保护体系已经变成了一项全球性任务。[2]这一点对于身处剧烈制度变迁的转型国家来说更为显著,对中国也是如此。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下,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前均拥有特定类型的社会安全网,也能为民众提供一定的生计保障,尽管保障水平普遍较低。转型国家的经验显示,在市场转型的初期,原有的社会安全网会出现破洞,相当一部分在旧体制下享有一定社会保护的社会群体,遭遇到生活水平突降的厄运,变成新的弱势群体。[3]与此同时,剧烈的制度变迁过程,尤其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社会风险,造就新的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4]例如,在中国,城市贫困的升级就被视为转型时期的一个全新问题。[5] 因此,如何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重新编织一张严密的社会安全网,使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增强其可行能力,以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乃是转型国家社会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事实上,中欧的一些转型国家很好地迎接了这一挑战,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重建了社会保护体系,从而实现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奇迹,其中一些国家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6] 以人口和经济规模来计,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转型国家。从1978年至1998年这一期间,市场力量的释放是中国社会经济大转型的主线。正是借助于市场力量的释放,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大批从未经受过真正市场经济洗礼的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社会风险中。[7]在全球化时代的市场转型过程,中国的制度选择必须在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和社会保护体系建设之间保持平衡。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市场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市场转型和经济增长不再单兵突进,社会发展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政府的发展战略也逐渐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元模式转变为推进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8]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社会保护体系建设的力度日益加强,成为中国社会事业发展的中心。 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是社会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政策或福利国家的国际文献中,相比较于普惠福利(universal transfers)和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社会救助普遍遭到相对忽视甚至质疑[9],这体现了一种贬斥剩余主义、弘扬普惠主义的学术传统。依照这种传统思维,社会救助的运行基于选择性原则,仅仅将社会保护以拾遗补缺的方式提供给经过官僚体系挑选的人,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社会保护的普惠性,另一方面也在受益者那里造成了社会羞辱(social stigma)。[10]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救助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全球性福利国家的瘦身和转型,导致慷慨的普惠主义福利国家受到质疑,而社会救助基于选择性原则将有限的国家福利资源配置给真正有所需要的人群,反而成为福利国家改革的新时尚。另一方面,社会救助在全新的社会保护理念中实现了华丽变身,从仅具有保护性的社会安全网转变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利器。新理念的出现意味着社会救助的治理体系和政策工具正在发生着转变,并且日益被纳入到积极社会政策或发展型福利国家的变革大思路之中。 一、社会保护的新理念:超越社会保障 “社会保护”一词最早出现在波兰尼的著作中。随着波兰尼的思想在全球左翼学人中愈加受到重视,“社会保护”在20世纪末的国际学术界日渐流行。“社会保护”已经日渐取代了人们过去常用的“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一词,用来指称防范社会风险的所有举措。[11]“社会保障”一词不再成为一种泛称,乃是因为这一辞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用法。在美国或论及美国时,这一辞藻被用来特指“社会安全税”(Social Security Tax)支撑的社会保险项目,而且在英文中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其主要功能是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12]在很多其他国家或不论及美国时,“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一词改为小写,泛指一系列社会政策项目,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普惠型福利给付、医疗保障以及各种帮助民众渡过难关的现金型和实物性给付。[13]在中国,“社会保障”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保障”指的是“社会保险”,即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主管的五个社会保险项目,而广义的“社会保障”则泛指一切保障民众防范社会风险的措施,包括社会保险,也包括社会救助,还包括其他一些措施。实际上,国际文献中常用的“社会保护”,基本上等同于中文中“广义的社会保障”。既然如此,在中文中放弃累赘的“广义的社会保障”概念,代之以“社会保护”这一简洁的词汇,更有利于国际沟通。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绝大多数国际文献中,“社会保护”所包含的内容远比“社会保障”在内涵上更多,在外延上更广。依照亚洲开发银行2001年给出的一个界定,“社会保护”意指所有旨在帮助人们减少贫困与脆弱性的政策与项目,至少包含五大组成部分: 1.劳动力市场政策与项目:旨在促进就业与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行; 2.社会保险项目:旨在为人们减缓因失业、疾病、残疾、工伤和老年所带来的风险; 3.社会救助与其他福利项目:旨在为缺乏足够生活支持的最弱势群体提供援助; 4.小微金融与社区发展项目:旨在通过社区帮助人们应对风险及减少脆弱性(因此,这类项目亦可称“社区型项目”),例如小微贷款、小微保险(社区保险)等; 5.儿童保护项目:通过普惠型现金或实物给付(免费领取的婴儿乳制品和其他婴儿用品等),为儿童抚养提供普遍性支持,并为特别困难的家庭以及针对具有特殊情况的儿童提供额外特殊性支持。[14] 在这里,第一项和第四项,也就是“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区发展项目”,均不属于传统所谓的“社会保障”范畴。这种概念本身就传递了两种理念,即社会保护不仅为民众提供消极的保护,而且还实施积极的干预,以帮助民众更好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之中。这种超越了“社会保障”旧传统的“社会保护”新概念在相当一部分文献中得到了采纳。[15] 世界银行倾向于把社会保护视为公共部门协助个人、家庭和社区更好管理风险并着重对贫困人群提供支持的各种公共干预措施。世界银行的新社会保护概念有如下几个特点: 1.社会保护是跳板而不仅仅是安全网。公共干预的目标是帮助贫困者跳出贫困,而不是跌入贫困陷阱。这一点对于很多女性贫困者来说尤为重要:新社会保护的重点在于帮助她们摆脱那些阻碍其获得生产性资源的种种社会限制。 2.社会保护是投资而不是成本。公共干预的宗旨是帮助贫困者提升其未来的生产性能力。 3.社会保护注重治本更甚于治标。公共干预的手段是减轻贫困者的风险规避意识,以鼓励其从事风险较大但回报也较高的工作。 4.社会保护注重现实可行性。正式的社会保护项目只对1/4的世界人口是可及的。在很多国家,试图通过公共扶持来消除贫困已经超出了政府的财政能力。[16] 在“社会保护”流行之前,与“社会保障”一词同样流行的是“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一词。在有些社会政策文献中,“社会安全网”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泛指一切能够帮助人们应对苦难和风险、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既包括政府出面组织的各种公共社会保护计划,也包括各种民间的、社区性的社会保护项目。[17]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安全网”实际上等同于“社会保护”。在公共社会保护计划中,最重要者莫过于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计划。社会保险的受益人范围相对比较广,而社会救助则仅仅面向贫困人群。[18]然而,很多国际社会政策文献采用一种狭义的社会安全网概念,即面向贫困人群的、作为最后手段的社会保护措施,在很大程度等同于社会救助。世界银行的出版物基本上就是在“社会救助”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安全网”这一辞藻。[19]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概念,在正式表述时基本上限于公共部门所采取的措施。但在另外的文献或另外的上下文中,社会保护不仅包括由国家出资并且亲自组织服务递送的公共项目,而且也包括许多由市场组织、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网络甚至家庭所提供的民间项目。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在2001年发布的报告《社会保障:新共识》中提出,“社会保护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收入保障和使受保人享受医疗和基本社会服务。它涉及各种不同的参与者,如家庭和当地互助网络、民间团体机构、企业和商业市场、政府和社会保障机构以及国际社会。”[20]自2000年以来,世界银行就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强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相融合的大社会保护概念。 二、超越剩余主义:社会救助在社会保护中的新定位 “社会保护”一词的流行,绝非如一个新的时髦辞藻代替陈旧词汇这样简单。实际上,这也是全球性福利国家转型中社会政策理念和治理模式变革的一种体现。与此同时,社会救助也在福利国家大转型的进程中有了新的定位。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简要回顾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 福利国家的发展起源于19世纪末期。在此之前,在社会保护领域中占据主导性的理念和思路是所谓的“济贫法传统”(the Poor Law tradition)。1597年,伊丽莎白王朝统治下的英国议会通过了《济贫法》(The Poor Law),从而正式建立了公共财政支持下的贫困救助体系,并且确立了一整套行政框架。基本上,“济贫法传统”乃是把公共救助的对象限定在“老弱病残”,也就是完全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生存的社会成员。[21]然而,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终结了济贫法传统,不仅仅是社会边缘群体,全体公民(甚至包括享有合法居住权的外国人)均有权成为国家福利的受益者。简言之,在福利国家中,享有社会保护成为每一个公民的社会权利。[22] 大体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经历了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同步高速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从而在经济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制度建设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这一期间,构建社会保护体系的过程,也就是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国家通过推动各种公共福利项目主导了社会保护的各项职能,而民间和市场力量在社会保护中的作用自然受到忽视。不仅如此,福利国家建设的主流是重视“普惠主义”(universalism),即致力于让所有民众均能享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保护。这一点在西欧和北欧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国家尤为明显。[23] 在具体措施上,社会保险和普惠福利更具有普惠性,从而受到更多青睐。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一般以人人参保、人人受益为特征。普惠福利,既包括全民公费医疗这样的非现金性福利给付,也包括所谓的“普惠型收入转移”(universal income transfers),即政府通过税收筹资并向某些人群发放的现金型福利给付,例如在很多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家庭津贴、儿童津贴、基本养老金等,几乎是人人(也就是所有纳税人)均可获得。相对来说,社会救助因为其受益对象具有所谓的“选择性”而遭到贬抑。社会救助的受益者也容易被视为整个社会的依附者,多多少少遭受某种歧视,从而形成所谓的“社会排斥”现象。[24]长期以来,社会救助在社会保护体系中处于次等地位。社会救助甚至一度被视为古老无用的济贫法传统的残留物,必将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成熟而消亡。[25] 社会救助的次等地位在比较社会政策文献中有着充分的反映。在国际社会政策文献中,有很多种对福利体制或者社会保护模式进行分类的方法,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种就是剩余型(residual model)与制度型(institutional model)的两分法。这种分类方法首先由美国社会政策学者维兰斯基(Harold Wilensky)和莱博尔(Charles Lebeaux)提出[26],后来由英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开山者蒂特姆斯(Richard Titmuss)发扬光大,提出福利模式的经典性三分法,即剩余型、工业成就—绩效型和制度性再分配型。“剩余型模式”(又译“补缺型模式”),就是指福利提供主要由民众的工作单位(市场)、家庭和社会支持网络来承担,而国家仅仅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工业成就—绩效型模式”,就是指福利提供主要依赖于就业;而“制度性再分配型模式”,意指国家根据既定的游戏规则(制度),明确赋予国民享有社会福利或者社会保护的权利,而不考虑民众是否有能力或者有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这些福利或者社会保护。所有采用这一三分法的文献,均把剩余型福利模式视为济贫法传统的现代延续,乃是社会保护体系有欠发达的表现,而社会救助则是这一落后模式的主要支柱。在这些学者(尤其是蒂特姆斯)看来,社会保护体系的现代化意味着从剩余型模式向制度性再分配型模式的转型,也意味着社会保险和普惠型福利最终应该取代社会救助成为社会保护的主要措施。用蒂特姆斯自己的话来说:制度性再分配型模式使“福利在一个社会中成为一种主要的统合制度,它在市场之外,基于需要的原则,(为民众)提供普惠性的服务”。[27] 1990年,丹麦学者古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on)出版了后来享誉士林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在此书中,他重新表述了蒂特姆斯的三分法,把发达国家的福利体制分为三类,即:(1)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模式,盛行于英国、美国和大洋洲;(2)法团主义模式或社会市场模式,盛行于西欧地区,以德国为典型代表;(3)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盛行于北欧地区。在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中,福利项目的类型组合特征如下:大量的家计调查型社会救助项目、一定数量的普惠型收入转移项目和一定数量的社会保险项目。在法团主义模式中,社会保险居主导地位,而社会救助和普惠型收入转移项目扮演补充性角色。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中,普惠型收入转移项目发挥主导作用,而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具有补充性。[28]艾斯平—安德森本人明显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青睐有加。 可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加剧,西方各国的福利国家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所谓“福利国家紧缩”成为全球性的风潮,许多国家削减了众多公共福利项目[29];另一方面,社会保护的制度结构也不再以国家大包大揽为特征,保障社会福利和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在国家、市场、社会(包括家庭、社区和非营利性组织)之间发生了程度与种类不同的转移,从而出现了从“福利国家”走向“福利社会”的趋势。[30] 福利国家的大转型激发了种种学术思潮的兴起。很多学人把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福利国家的建设对立起来,认定后者会给前者带来负担。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ederick von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为代表的一代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上下文中一般称“保守主义”)思想家对于福利国家所引发的福利陷阱深重、官僚父爱主义、公民责任感削弱、市场遭受侵蚀等问题,展开了激烈批判。1974年,美国著名公共经济学家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以非常专业性的方法论证了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如何不利于经济发展。[31]1984年,美国著名保守主义学者穆雷(Charles Murray)出书,严厉抨击美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导致相当一批福利受益者游手好闲,对政府产生严重依赖,不仅自身跌入贫困陷阱,而且还极大地损害了生产性经济。[32]从保守主义角度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卡托研究所出版的《福利的终结》一书名噪一时。[33]他们主张缩小福利国家,即重拾为主流社会政策文献所不齿的“剩余型模式”,让政府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而把推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责任留给个人、家庭、社区、非营利组织和市场。 总的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许多国家,家计调查型福利的发展一度快于其他社会福利给付,这说明社会保护的发展趋势是重新重视具有选择性的社会救助体系。[34]在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福利国家本身发生大的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大规模失业的出现导致对社会救助需求的激增,社会救助的开支出现了一定增长。[35]传统上,社会救助在联邦制的发达国家一向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但自20世纪后期以来,联邦政府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而社会救助体系的地方特色依然有所保留。[36]此外,学术界的研究也发现,普惠主义福利模式并未像传统的社会政策学术界所认为的那样在高支出和高再分配之间产生强的正相关。[37]尽管这样的研究发现并不能自动证明社会救助必定能产生良好的再分配效果,但至少对矫正社会政策学界对于剩余主义模式的偏见有一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社会救助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但无论在何种类型的福利体制之中,社会救助在社会政策支出中的比重依然是最小的,因为社会保险和普惠福利的开支一般都占较大比重。因此,西方发达福利国家的施政重心,并非向加强社会救助的方向发生急剧改变,而是向“收入调查型福利的漂移”。[38]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世界银行为全力提升社会救助在社会保护体系中的地位付出了不懈努力。[39]尤其是,社会安全网成为世界银行减贫战略的一个重要要件,也是世界银行指导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实施经济调整的辅助性社会措施之一。[40]由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努力,社会救助不仅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护体系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新的制度与治理模式。根据学者的研究,从目标定位到服务递送,社会救助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可分为:(1)纯现金给付型,包括面向贫困家庭的一般性社会救助、儿童与家庭津贴、社会养老金(专门针对贫困与伤残老年人的补充性养老金,不同于社会养老保险金或国民年金)等;(2)收入转型附加型,即在现金救助给付之外附加一些条件,包括就业保障计划或长期公共项目、人类发展救助(即附带有提升教育和卫生水平的现金社会救助项目)、资产保护与积累型救助、各种实物性救助项目;(3)整合型脱贫减贫项目。[41] 三、从消极保护主义到积极干预主义:社会救助治理模式的创新 社会救助在社会保护体系中有了新的定位,这也导致社会救助的理念及其政策工具和治理模式都发生了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其理念从社会安全网转变为社会风险管理。 “社会风险管理”的概念和理念是由世界银行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其主导的全球性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框架,其核心观点如下: 1.风险的无处不在:所有个人、家庭及其所在的社区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有自然风险(生老病死、灾害意外等),也有人为风险(待业失业、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全球化的一个后果就是风险的相互关联性增强,从而导致经济与社会震动的扩散范围和幅度增大,在此过程中,贫困人群应对风险的脆弱性放大。 2.弱势群体风险管理工具的缺失:面对这些风险,缺乏资产和其他禀赋的弱势群体自然会利用一些自我保护机制,如好年景时进行资产积累、寻求收入来源多元化、建立家庭或社区非正式风险分摊网络等。但是,这些机制既不稳固,也不经济,而且往往会在糟糕年景中有损贫困家庭在人力资本中的投资。而且,社会风险常常呈现相互叠加、自我强化的态势,因此弱势群体管理社会风险的能力尤为脆弱。弱势群体所缺乏的是社会风险管理工具的可及性。[42] 3.社会风险管理的公共干预至关重要:社会风险管理有三种策略,即防范、缓解、应对,可采用基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种机制或管理工具,其中社会包括家庭、社区和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43]社会风险管理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44] 4.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多元性:面对任何特定的弱势人群,社会风险管理的框架必定包含着多种策略与多种机制的组合,即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均无法独揽,也不可偏废。 世界银行的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在传统社会政策学者那里是遭到贬斥的,认为其要害是强调个人责任的优先性,看重市场机制的重要意义,将集体行动或国家义务的重要性放在次要位置。[45]一向与世界银行不大咬弦的国际劳工组织断定,风险规避是人的本性,社会政策应该把安全和保障赋以更高的价值。与世界银行强调公共部门协助民众(尤其是弱势人群)管理社会风险的取向有所不同,国际劳工组织强调的是人人享有社会保障。[46]2009年,国际劳工组织联合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社会保护地板”(social protection floor)的概念[47],并于次年设立专门的顾问机构,与联合国开发署等已有机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社会保护地板”的铺设,其中社会救助体系的强化是其重要内容。[48]“社会保护地板”理念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致力于落实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以确保所有人在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达致适当的生活标准。[49]与世界银行强调积极应对风险相比较,世界劳工组织的取向偏重消极防范风险。 其实,在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左右派之间的重叠共识相当丰富,而左右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辞之争。于是,颇有一些社会政策学者试图调和世界银行和世界劳工组织的两派思路,提出了诸如“适应性社会保护”(adaptive social protection)和“风险调整型社会保护地板”(risk-adjusted social protection floor)等中庸型新概念。[50]这些新概念或新理念的提出都涉及社会救助的治理变革,即强调社会救助不仅仅是救助,而且要帮助受益者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更具有适应性,对于社会风险更具有针对性。 总体来说,在发达国家中,尽管各国政府的施政理念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将社会救助治理模式的改革纳入“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也着力推动这一治理创新。所谓“积极社会政策”,是指一种全新的政策理念,即将各种社会项目的重心,从保障民众免受风险转向其能力建设,并且以更好的方式利用其能力。[51]将积极社会政策作为施政主轴的福利国家,自然被称为“积极福利国家”,而那些将过去的消极社会政策转变为积极社会政策的改革举措,被称为“社会激活政策”(social activation policy)或“社会激活项目”(social activation programmes)。[52]福利国家的这一改革取向,最终目标是召集并塑造“积极的公民”(the active citizenship),强化公民的责任感,通过积极参与和选择[53],将“消极的社会”改造为“积极的社会”。[54] 积极社会政策的理念其实并非全新。在此概念提出之前,有关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和工作福利(workfare)的研究和实践早已行之有年,前者的宗旨是将劳动政策的重心从失业保护转为就业促进[55],而后者的取向是将社会福利政策从收入支持的提供转为工作能力的培养。[56]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将原来两个略有不同但颇多重叠的研究与政策领域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社会激活的努力不再限于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和就业政策,而是从就业政策扩展到儿童政策、弱势人群政策、老年人政策等。在此过程中,社会救助也发生从消极保护主义向积极干预主义的转型。消极保护主义型社会救助的最大弊病就是政府只是一味地扶持、救助,从而让福利领取者产生福利依赖,使得社会救助政策变成了社会陷阱,而积极干预主义型社会救助将施政重心放在福利陷阱的填平。[57]社会救助体系的施政取向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同针对特定人群的诸项社会政策变革有机地融合在一起。[58] 就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而言,其施政重点对象一向是失业救助或社会救助的受益者,而不是失业保险给付领取者,因为后者一般有一定的时限,而且其宗旨就是为了保证失业者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与其学历、能力、志趣相匹配的新工作。但失业救助或社会救助则没有时限,在拥有失业保险的福利体制中,失业救助的受益者往往都是长期失业者,很多人正在或已经对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丧失了积极性。因此,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具体措施包括: 1.提升公立劳动服务机构对福利领取者的接触频率; 2.严格福利申领资质标准,加强给付惩戒力度,促使福利领取人进入工作; 3.设定参与劳动力市场项目的义务[59]; 4.在就业促进的公共服务中引入“准市场”机制,并在干预政策与制度安排上加强协调,以提高社会救助领取人返回劳动力市场的效力。[60] 就儿童与家庭政策而言,原来的消极社会政策只是政府提供现金和实物给付,无论是以普惠型福利还是社会救助的方式,而积极社会政策的重心放在为儿童及其抚养人(尤其是单亲母亲)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使他们成年后能有效地参与职场、融入社会。具体而言,积极儿童与家庭政策包括: 1.投资于儿童,通过各种童年干预项目,确保儿童不受社会排斥,不为福利依赖所影响; 2.促进母亲就业,通过税务优惠等措施,促使母亲实现一定的经济独立; 3.协调家庭与工作责任,包括培育托儿服务以及家庭亲和型职场。 就弱势人群而言,原来的消极社会政策只是政府加以扶持,而积极社会政策强调扫除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即采取更有效的社会救助措施,不仅要确保他们享有一定的生活标准,而且还要鼓励他们摆脱福利依赖,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和工作之中。具体而言,积极的弱势人群政策包括: 1.完善从福利到工作的改革议程,促使从单亲母亲到伤残人士全面提升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2.改善职场福利,促使福利领取者提高参加工作的意愿; 3.推进政策间的协调,降低福利领取者脱离劳动力市场的激励。 就老年人而言,原来的消极社会政策是通过社会养老保险和普惠型国民基本养老金以及一些拾遗补缺型养老救助(主要是通过得到补贴的养老服务),为所有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然而,随着老龄化,尤其是随着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老龄政策的重心在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中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即一方面促使老年人继续参与工作、融入社会,另一方面提升老龄脱贫和老年服务的效率。具体措施包括: 1.减少提前退休计划,增多延后退休计划,从雇主和雇员两方面为延长雇佣年限提供更强的经济激励,尤其是防止雇主因偏见而采取老龄员工下岗或解雇措施,避免让老年人陷入贫困[61]; 2.养老金计划的多样化,即一方面改变原养老金的领取资格(例如提高退休年龄等),另一方面为即将退休者和已经退休者提供各种多元化的选择,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例如在职业培训上发挥积极作用、参与社会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业务、提供咨询等); 3.鼓励各种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的发展,从而为低收入的、脆弱的老年人提供更有效的社会服务,包括居家型、社区型和居住型的老年看护; 4.老龄社会服务的社会救助采取补需方的模式,即通过发放老年服务代金券的方式,让老年人及其监护人有更多的消费选择。[62] 由此可以看出,在积极社会政策的新框架中,所有种类的社会救助项目都开始融入了参与社会、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新内容,促使受益者摆脱福利领取者的消极境况,使他们成为积极的公民。 四、结语 社会保护的制度建设,对于市场力量逐步释放的转型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传统的社会政策学术界,社会保护制度建设的重心在于由国家为民众提供保护,以防范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覆盖全体民众的普惠型福利成为社会保护的首选,其次是覆盖所有工作人群的社会保险。相对来说,由于其目标定位必须依据选择性原则对受益人群进行筛选,其功能在于拾遗补缺,其后果常常造成羞辱效应和社会排斥,社会救助受到社会政策学术界的忽略和贬斥。 然而,福利国家的转型提上了全球性社会政策的议事日程。社会保护的取向发生了深刻转变,从消极的收入保障转变为积极的能力发展。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将行之已久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工作福利政策整合起来,强调社会保护的功能必须超越收入保障,为所有受益者提升自己参与劳动力市场并进一步融入社会的能力,并且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些能力开辟广阔的空间。正是在福利国家从消极保护主义向积极干预主义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护体系中有了新的定位,其制度建设和治理变革也应时而兴。社会救助项目,无论其目标定位人群是长期失业者、抚养儿童的家庭、弱势人群还是老年人,都纳入了能力建设的积极内容,以帮助受益者摆脱福利依赖性,并从福利陷阱中跳跃出来。 在全球性福利国家转型的浪潮中,世界银行长期推动的社会安全网旧措施被社会风险管理的新框架所取代。与之不同,国际劳工组织大力推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护地板”的铺设,但也同时注重将社会保护体系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完善结合起来。毫无疑问,社会政策的终极追求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或者说在推进社会发展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完美的协调。世界银行和世界劳工组织所代表的两大社会政策取向,以及众多学者就这两个取向的争论或在这两个取向之间进行的调和,都体现了对社会政策终极追求的不同探索。标签:社会救助论文; 社会政策论文; 社会风险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创新理念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世界银行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