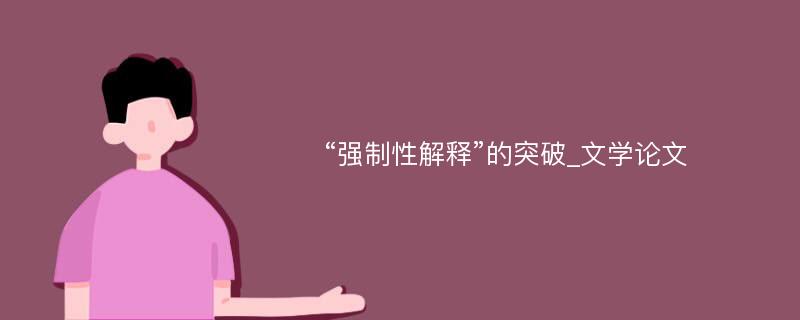
“强制阐释”的突破之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6)06-0067-08 哈罗德·布鲁姆宣称:“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①。何出此言?在他看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等大行其道的“憎恨学派”均偏离了“审美阅读”对文学的情感性、想象性和心灵性的体悟,而更多地关注文学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问题,以至于当今的文学研究者大都转变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②。的确,自1960年代以来,文学阅读已经普遍地“向外转”,越来越功利化,越来越“理论化”,越来越“去审美化”。国内学者张江用术语“强制阐释”恰当地概括了这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去审美化阅读模式”。他所谓的“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在他看来,强制阐释的首要特征就是“场外征用”,即“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③。显然,相比而言,布鲁姆对去审美化阅读模式的批判比较情绪化,张江对之的剖析则更具学理性。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对这种去审美化阅读模式进行剖析和批判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文化批评”,文学阅读能否突破重围,重扬“审美”的旗帜?针对强制阐释的盲点和漏洞,应当采取哪些有效的策略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 一、“强制阐释”:理论时期的阅读模式 如卡勒所言,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指望从中找到符合某种理论模式的对“关于什么”的问题的解答:“是关于恋母情结矛盾冲突的”(心理分析),“是关于遏制颠覆力量的”(新历史主义),“是关于性别关系不对称的”(女权主义),“是关于文本自我解构本质的”(解构主义),“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阻碍的”(后殖民主义),“是关于异性恋根源的”(同性恋研究)④。“理论先行”已经成为文学阅读的“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文学作品被任意切割,被当作对某种“理论”十分生硬地转述和注解,“理论”已经使文学阅读变得极其简单化和模式化。瓦伦丁·卡宁汉在《理论之后的阅读》中指出,理论化阅读正在消解着文学,消解着文本,将它们简化为一套套理论程式或一个个理论模型,“理论在单一化、使文本单一化、使读者单一化。理论邀请你像一个女人、一个解构主义者、一个新历史主义者、一个后殖民主义者,或德里达派、或拉康派、或福柯派那样去阅读。”⑤很明显,这种用先在的理论模式去套弄和切割文学作品的阅读方法正是张江所概括的“强制阐释”,而“强制阐释”与种种理论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强制阐释”正是在“理论时期”建构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典型的阅读模式。为什么会这样呢? “理论时期”的时间段大约为1960年代至1990年代,在此期间,涌现了一批重量级的理论家,如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尔迪厄、埃莱娜·西苏、朱迪斯·巴特勒、格林布莱特、伊格尔顿、詹姆逊、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出现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风行一时的批评流派。概而言之,这些理论家和批评流派的“理论”都带有极强的社会功利指向。这是因为理论的兴盛与战后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和“反文化运动”有直接的关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⑥。在这个大背景下,文化和文学理论无不具有功利性和政治性,如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的运作,等等。 正如安东尼·伊斯特霍普所总结的,文学阅读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机制”⑦。《美学的复仇》一书的编者米歇尔·克拉克也认为,后现代的理论批评已经习惯于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术语而不是传统美学术语,来解读文学和艺术作品,促使文学研究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开放,总体上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甚至文学本身的重要性⑧。理论的兴盛已经引发了一场“反美学”的浪潮,开启了一种“去审美化阅读模式”,“强制阐释”由此应运而生。 正因为如此,卡勒承认道,“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⑨。希利斯·米勒才危言耸听地说,“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⑩。李欧梵将这些理论操演了一遍之后也感叹道,“文学艺术本身,是任何理论无法完全攻破的,否则我就只谈理论,不研究文学了”(11)。总之,“理论”无关乎文学,文学阅读和批评回避文学本身,而转向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领域,这就是“去审美化阅读模式”或“强制阐释”的病灶所在。因此,“面对文学本身”当是重构文学审美阅读主导地位的必然选择。 二、重建文学观念:文学是审美的人学 王元骧指出,“文学观念”是整个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我们思考文学问题的理论前提,也是我们开展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思想依据”(12)。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理论”为了实现其向外转、政治化和去审美化的目的,其重要策略便是打着“反本质主义”的旗号,解构一切传统的文学观念,并建构了自己的“建构论文学观”。“建构论文学观”主要包括三层内涵:第一,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文学”定义。在他们看来,文学没有真正内在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是历史化、地方化和语境化的不断流变的概念。第二,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文学价值判断标准。特定时代中的特定人群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确认文学经典,但这种价值判断决非“绝对真理”,因为“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13)。第三,文学研究需要向外转,并政治化。既然不存在文学本质或文学本身,那么,值得研究的就不再是文学的内部特性,而是建构它们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即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领域,“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体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而加以把握”(14)。总之,后现代理论家们关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文学”,而是“是什么建构着文学”,其目的就是废弃文学概念,否定文学本身,从而为自己走向文学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提供合法性证明。 在解构传统文学观念的过程中,这些后现代理论家和批评流派着力打击的乃是“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直至20世纪上半叶,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遵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将文学定位为“人学”,确立人的尊严,坚持人性价值,崇尚对永恒真理、普遍人性和美的高尚沉思,优秀的文学作品被视为审美和伦理的最高成就。这种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认为,“研究文学会使你成为更好的人,会发展你的想象力,因此可以想象性地进入他人的经验,进而学会尊重真理和所有价值正义。”(15)但是,后现代理论指出,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至少存在四大问题:其一,他们对文学经典的选择受制于自己的偏好,局限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的作品。其二,他们总是按照单一的影响和风格传承来思考经典,“这是一种排他性的、父权制的思想结构”。其三,“人文主义学说主要从形式美学的评价立场来接近对象,忽视了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16)其四,他们没有注意到,文学价值的评定实际上会受到特定社会中特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操控。可以看出,后现代理论颠覆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的策略主要是“建构论文学观”,他们对文学本身的审美的、人性的和伦理的价值并无兴趣,更不想加以深入地研究。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后现代的种种大文化理论采取建构论的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政治学的路径,试图解构人文主义文学观,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呢?正如奥斯汀·哈灵顿所说,“社会理论把艺术品的价值归因于社会机制、社会惯例、社会感知和社会权力等语境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但我们主张,社会理论不能从社会事实推出艺术品的价值,社会理论本身不能产生艺术品的审美判断。”(17)在我看来,建构论文学观对人文主义文学观的攻击打的只是一场避实就虚的外围战,“文学本身的审美的、人性的和伦理的价值”毫无损伤,并蕴涵着永久的魅力。相反,建构论文学观要把文学阅读引向文学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领域,这跟我们过去将文学视为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反映又有多大实质上的差异呢?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理论的倒退,是要让我们重走文学认识论和文学工具论的老路。 我认为,拨开后现代文学理论设置的重重迷障,“什么是文学”依然是一个真问题,答曰:文学是审美的人学。我们似乎已经忘却了那些最基本的文学常识:首先,文学是审美的。审美不是认识,审美判断是情感判断而不是逻辑判断,文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语言性、情感性、体验性、形象性、虚构性、想象性乃是文学最根本的属性。其次,文学是人写的和写人的。“作者之死”乃是某些后现代理论家炮制出来的一个弥天大谎,必将成为文论史上的一桩“丑闻”。文学的价值恰恰来自于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对特殊生存情境的感受,对历史、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然后以一种个人化的话语方式塑造出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文学的本体不是社会历史,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人生最终实在和根本的、有关个体心灵和生命的“情本体”(18)。“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19)人心、人性、人情,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再次,文学是具有伦理价值的。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钱谷融强调:“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20)总之,“审美”、“人”、“伦理”是文学的三大核心要素,重启文学审美阅读必须以此为突破口。 三、始于“审美判断”:审美阅读策略之一 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应当是理论在先,还是审美在先?应当是作为规定判断力的逻辑判断在先,还是作为反思判断力的情感判断在先?这是区分“强制阐释”与“审美阅读”的一个焦点问题,不能不明辨之。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判断力”区分为“规定判断力”和“反思判断力”,如果普遍的建构性的规则、原理、规律预先被给予,我们把特殊事物归于其下,使事物获得明确的规定而被认识,这就是规定判断力。如果只有特殊的事物预先被给予,我们为了对之有一个统一性的把握,必须为之找到普遍的范导性的规则、原理、规律,这就是反思判断力。规定判断力是“从普遍出发归摄特殊”,其先天原理是“合规律性”;反思判断力是“从特殊出发寻求普遍”,其先天原理是“合目的性”。规定判断力是以知性为主导的逻辑判断、认识判断,反思判断力中的“审美的反思判断力”是以想象力为主导的审美判断、情感判断。现在,我们用康德的这些基本原理来区分“强制阐释”和“审美阅读”就会变得很清晰。显然,强制阐释用现成的普遍的理论框架来套弄和切割特殊的文学作品,应用的是规定判断力,是以知性为主导的逻辑判断、认识判断,文学作品因此而成为认识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通道,指向客观外部世界。相反,审美阅读则从特殊的文学作品、独特的阅读感受出发,应用的是审美的反思判断力,是以想象力为主导的审美判断、情感判断,文学本身的审美的、人性的和伦理的价值才是鉴赏的核心,指向主观心灵世界。之所以说强制阐释是一种与审美无关,与文学本身无关的文学阅读模式,道理也就在这里。而但凡强调审美阅读的人,其主张无不符合“审美的反思判断力”的基本原则,孙绍振便如是说:“我们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以人的价值观念、审美的价值观念、人的情感的价值观念、人的自由、个性、想象的特殊逻辑为指导。”(21)因此,从审美判断、情感判断出发,而不是从逻辑判断、认识判断出发,这应当作为审美阅读的“第一原理”定下来。 遵循“从审美判断、情感判断出发”这个第一原理,我认为审美阅读要重点把握好以下两个环节: 第一,重视文学阅读的情感体验。康德指出,“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象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22)。这句话深刻地揭示出审美的情感特性和人学特性。童庆炳由此认为,“‘审美’,最简明的概括,就是‘情感的评价’”(23)。“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知音》),文学审美阅读最初获得的便是丰富的情感体验。清人袁枚说得非常精彩,“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24)面对理论先行的阅读现状,苏珊·桑塔格指出,“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25)瓦伦丁·卡宁汉提出了“动情阅读”(touching reading)的对策,主张用身体、情感和心灵全方位地融入文本(26)。希利斯·米勒同样强调文学阅读的体验性与参与性,“阅读就应是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情感、想象,在词语的基础上,在自己内心再次创造那个世界。这将是一种狂热、狂喜,甚至狂欢,康德称之为‘癫狂’。”(27) 第二,重视审美意象或文学形象的品赏。高尔基谈论文学阅读体会时说:“当我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驴皮记》里,读到描写银行家举行盛宴和二十来个人同时讲话因而造成一片喧声的篇章时,我简直惊愕万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仿佛现在还听见。然而主要之点在于,我不仅听见,而且也看见谁在怎样讲话,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微笑和姿势,虽然巴尔扎克并没有描写出这位银行家的客人们的脸孔和体态。”(28)文学营造的意象或形象世界能够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所以,朱光潜强调,“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29)。在阅读中品赏意象时,主要运用的是审美想象力,审美想象力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透过语言来构造人物和景物的画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构造“审美理念”这样的高级意象。由于没有确定的逻辑概念完全适合审美理念的高级意象,所以,这些意象便能够引发更多的意象,“它向内心展示了那些有亲缘关系的表象的一个看不到边的领域的远景”(30),臻至司空图所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佳境,给人带来极大的审美自由感和愉悦感。 四、关注“文学的质量”:审美阅读策略之二 彼得·威德森将近现代以来生成的、人文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文学观念称为“大写的文学”(Literature),将后现代以来生成的、反人文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文学观念称为“小写的文学”(literature)。前者以文学经典为标准,崇尚文学价值,重视文学的质量;后者抹平了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甚至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忽视文学的质量,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政治功能。具体而言,威德森指出,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一浪接一浪的理论动摇了“大写的文学”,并改变了理论批评,其策略主要有两点:一是将“大写的文学”观念历史化、政治化,二是挑战作者主权、“文本自身”、内在“含义”和本质主义的“解释”等概念(31)。在他们看来,文学价值与作者的独创性、文学文本的质量无关,只是依赖于特定社会的话语—权力和机制/机构的设定;而“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32)。 对此,我们不禁要产生疑问,后现代理论对“文学经典”和“文学价值”的解构到底具有多大的合理性呢?一时一地构造出来的文学经典或许可以认为是话语—权力建构的骗局,但是,那些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可以无限阅读的文学经典难道不正说明它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和伦理价值吗?刘象愚认为:“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所谓丰富性,是指经典应该包含关于人类社会、文化、人生、自然、宇宙中那些重大的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与观念的对话和争论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完善,参与人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积有益于人类生活。”(33)哈罗德·布鲁姆也指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在于它的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种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34)。可见,“把价值问题简化为权力与视角问题会落入相对论的陷阱”(35),文学经典或文学价值与意识形态之间不能画等号,因为它们具有超越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内在的判断标准,那就是文学本身的审美的、人性的和伦理的价值。 威利·皮尔在《经典构成:意识形态还是审美质量?》一文中有针对性地论证了“文学的质量独立于政治立场”的观点。通过对亚瑟·布鲁克的长篇叙事诗《罗梅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史》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题材相同的作品的比较,皮尔发现,尽管布鲁克作品的叙事立场与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封建意识形态完全一致,而莎士比亚剧作所弘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之格格不入,但是,后者反而成了文学经典。使莎士比亚剧作成为经典的真正原因是“文本因素”。首先,莎剧的语言更加复杂并富有创新性,其风格和语域更加丰富多变,映射着多重含义。其次,莎剧中增加了许多人物,增强了公共场景与私人场景、高等人物与低等人物、严肃与幽默之间的张力。再次,莎剧的叙事线条更加复杂,故事时间从布鲁克叙事诗中的九个月压缩为几天之内,从而深化和加强了观众的情感投入。更重要的是,莎剧的主题完全不像布鲁克叙事诗的封建道德说教,而赞扬了这对恋人的优秀品质,及其追求爱情、幸福、自由的虔诚和执着。由此证明,文学经典和文学价值并非一时一地的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而主要来自于文本自身的审美质量(36)。 当然,皮尔得出“文学的质量独立于政治立场”的结论有点走极端了,因为好的文学与好的政治在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方面,在价值论和本体论层面尚有可以融通之处,但是,皮尔指出,文学文本自身的审美质量是构成文学经典和文学价值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它启示我们,审美阅读一定要关注“文学的质量”。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是关注作品的艺术价值,二是关注作品的人学价值。 品鉴作品的艺术价值,最重要的就是要评估作品的审美独创性和典范性。康德说,美的艺术是只有作为天才的作品才是可能的,因为天才的作品不是根据预设的规则创作出来的,而具有独创性;但这种独创又不是胡闹,天才的作品同时又必须是典范,可以被别人用来模仿,并用作艺术评判的准则。关于独创性,我们要看作品是否开辟出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意境、新的语言、新的风格、新的文体、新的方法、新的技巧,但对这些创新层面的判断,必须以文学自身的美学传统和内在的发展逻辑为参照系,正如布鲁姆所说,一个作者的独创性就在于不断突破前辈大师们的艺术模式,在与既有模式的“竞争”中创立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关于典范性,指的是那些公认的文学经典所具备的具有示范功能的审美规范性,但是,这种典范性的获取与其独创性又是密切相关的,如左拉评论福楼拜时所说:“《包法利夫人》一出现,就形成了整个一种文学进展。近代小说的公式,散乱在巴尔扎克的巨著中,似乎经过收缩,清清楚楚表达在一本四百页的书里。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包法利夫人》的清澈与完美,让这部小说变成同类的标准、确而无疑的典范。”(37) 利维斯指出,伟大的文学家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也具有重大的意义(38)。文学是审美的人学,它以“语言”这种极具穿透力的媒介来表达人对生存的感受、对生命的体悟、对现实的超越、对伦理的抉择,乃是“以心铸心,以心传心,以心感心,以心应心”的“心学”(39)。品鉴作品的人学价值,首先要把握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独特的性格、命运和灵魂,其次要深入到作者本人的独特的情怀、个性和良心,最后触及到时代的心理、国民的魂灵乃至普遍的人性。总之,伟大的文学不仅具有审美的独创性和典范性,其最高目的还应当是使人类的道德获得提升,灵魂得到净化,人性走向完美。 五、重提“审美溶解”:审美阅读策略之三 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进入“后理论”时代,去审美化的强制阐释阅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遭到了质疑和抵抗,出现了一些重新思考审美问题的著作,但大家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不可能再回到前理论时代了”(40)。在这些反思性的美学著作中,一些人强调了审美经验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还有一些人试图重新调配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41)。无论如何,理论时期的强制阐释模式依然辐射出强大的影响力,原因在于这种阅读方式具有鲜明的自我反思性、政治批判性、社会实践性和公共参与性。当今,“文化政治”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化、政治化的阅读方法能够有效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会在底层阅读、边缘阅读、性别阅读、族裔阅读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文化批判功能。然而,既然不想重复强制阐释的去审美化之弊,那么,这就给理论之后的审美阅读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审美地读解或表达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 其实,对这一问题的探寻在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那里已经积淀了一批丰厚的遗产。由于在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一再受挫,卢卡奇、葛兰西始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便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当作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佳途径,其中,文学艺术成为抵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领域。文学艺术何以能够担此重任呢?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好的文学艺术具有审美自主性,建构了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象世界,并具有内在的真理内容和价值判断,因而能够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祛蔽和批判。阿多诺等人的美学观在近年来兴起的“新审美主义”思潮中又重新获得了认同。由约翰·若津和西蒙·马尔帕斯提出的“新审美主义”既反对以康德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审美观念,又对去审美化的意识形态批评不满,而主张“在艺术或文学的具体特性研究方面开辟一个批评空间,极大地改善审美批评在当代文化中的潜力和地位”(42)。他们在阿多诺的批评理论中获得启示,但是,究竟如何在审美阅读与理论化、政治化阅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新审美主义仍然是语焉不详的。 在我看来,阿多诺、马尔库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好,约翰·若津和西蒙·马尔帕斯的“新审美主义”也罢,其实都预设了审美与意识形态、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二元对立,过于强调二者之间的“对抗”而不是“融通”的一面。后来的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倒是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之处下了一番工夫,但只是侧重于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共生”关系。其根本的理论缺陷就是将“审美”等同于“文学形式”,而忽略了文学的情感的、人性的和伦理的价值。究其原因,在他们的观念里,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我们所强调的文学是审美的人学,文学是心学。所以,我认为,只有在“文学是审美的人学”这一根本的文学观念上来立论,才能有效地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审美阅读与理论化、政治化阅读之间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是审美的人学”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它不同于追求形式美、纯粹美,脱离现实生活,超越意识形态,摒弃道德意识的各种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念,因为它强调“人”在文学中的核心地位,而“人”又必然牵连着整体的社会生活。其次,它区别于一味地强调外在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批评,将文学阅读等同于社会科学阅读的种种认识论的文学观念,因为它是以审美为本位的。综而论之,“文学是审美的人学”坚守文学的“审美”、“人”、“伦理”三大核心内涵,在这种文学观的烛照之下,外在的现实生活、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必须以“溶解”的方式有机地融入文学的审美世界、意象世界、人的情感世界,而化身为诗性的现实生活、诗性的社会历史、诗性的意识形态。童庆炳指出:“应该看到,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溶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都溶解于其中,综合于其中。因此,文学艺术撷取现实的审美因素,不但不排斥非审美因素,相反,总是把非审美因素的认识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甚至自然属性交融到审美因素中去。这样,文学艺术所撷取的审美因素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凝聚政治、道德、认识等各种因素。”(43)我认为,童庆炳的“审美溶解说”虽然提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但是,对解决理论之后变得非常尖锐的审美与意识形态、审美阅读与理论化政治化阅读之间的矛盾依然有效。“审美溶解说”启示我们,文学世界首先应该是审美的世界、诗情画意的世界,其“内在的”现实生活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已经被审美化、诗意化、情感化、价值化了,从而区别于“外在的”现实生活、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我们阅读的重点显然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进一步而言,即使是对审美化、诗意化、情感化、价值化的“内在的”现实生活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读解也还应当以人心、人性、人情为落脚点,正如另一位学者所说:“任何涉及社会现实或史实的文学作品,假如它的表现成功的话,永远不在于它的反映了社会现实或史实,而是它成功地掌握了受到如此社会现实或史实考验之中的人性的真实和光辉。”(44)可见,只有坚守“文学是审美的人学”的文学观念,以“审美溶解”为阅读策略,我们才能走出审美与意识形态、审美阅读与理论化、政治化阅读之二元对立的困局,才能走出意识形态批评的认识论误区,才能克服强制阐释的去审美化之弊。 注释: ①②[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第412页。 ③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④⑨[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第4页。 ⑤Valentine Cunningham,Reading After Theory.Blackwell,2002,pp.123-124. ⑥[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页。 ⑦Antony Easthope,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1,p.127. ⑧Michal P.Clark(ed.),Revenge of the Aesthet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5. ⑩[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11)李欧梵:《世纪末的反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12)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13)(14)[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第207页。 (15)Antony Easthope,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1,p.9. (16)(17)[英]奥斯汀·哈灵顿:《艺术与社会理论》,周计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第4页。 (18)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5页。 (19)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20)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21)孙绍振:《审美阅读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22)(30)[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第160页。 (23)童庆炳:《文学审美论的自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24)(清)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65页。 (25)[关]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6)Valentine Cunningham,Reading After Theory.Blackwell,2002,p.147. (27)[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28)[苏]高尔基:《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3页。 (2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31)Peter Widdowson,Literature.Routledge,1999,p.92. (32)[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3)刘象愚:《经典的解构与重建》,《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34)[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5)[英]奥斯汀·哈灵顿:《艺术与社会理论》,周计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36)Willie van Peer(ed),The Quality of Literature.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8,pp.17-29. (37)[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译者序言第5页。 (38)[英]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页。 (39)柯庆明:《文学美综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40)[英]拉曼·基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41)Jane Elliott and Derek Attridge(eds),Theory After 'Theory'.Routledge,2011,p.249. (42)John J.Joughin and Simon Malpas(eds),The New Aestheticis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3. (43)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44)柯庆明:《文学美综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标签:文学论文; 判断力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情感模式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读书论文; 人性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艺术与审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