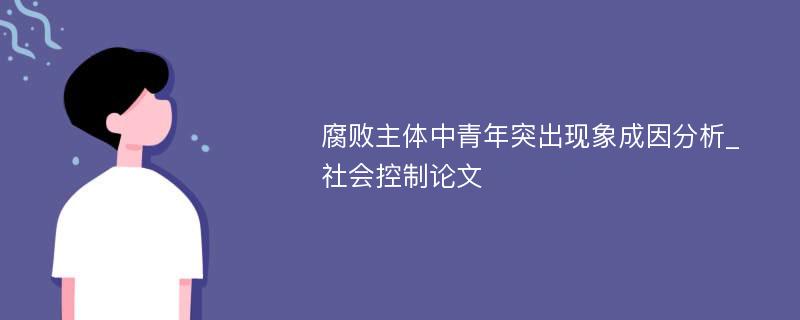
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现象的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青年论文,腐败论文,主体论文,现象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腐败主体的“59岁现象”到“39岁现象”,再到“26岁现象”,三种腐败主体先后继起,表明腐败已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年龄层次,各个年龄群体中已不存在没有腐败的清洁之域。腐败主体中的青年群,既具有所有腐败分子的共性,又带有其年龄群的自身特征。
一、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主导价值观的改变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变迁为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提供了理论藉口和时代机会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主的全方位改革正在逐步走向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有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发生分化变迁,各年龄人群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极大变化。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社会现象就深深地烙上了时代背景的痕印。
1、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由权力为主向金钱和财富为主,为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理论藉口。中国几千年一直奉行“官本位”,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是以权力大小为主来进行衡量。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分层主要就是以行政级别来进行区分。彼时社会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以权力的大小来占有、享用和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社会生活中过分突出政治和宣扬强烈的禁欲主义,并且又因为实行比较严格的论资排辈等制度,以及物质不太丰富等现实原因的限制,使腐败难以进行。而进入转型期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进,经济原则在社会得以确立并逐渐占主导地位,便从各方面冲击原有的价值标准和取向,使之转向以金钱和财富为主的价值评判,并成为人们衡量成功标准主要尺度。腐败的青年主体在其思想深处,采用的价值标准与取向便是金钱至上。
2、前喻文化向并喻文化过渡并迅速转向后喻文化,为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提供了权力前提和时代机会。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最先提出。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主要表现为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即“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及人类文化的大发展,尤其是划时代的科技发明或创造,都会带来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化。而这三种文化的传承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类文化的激烈演进,即主要由发现和发明而引发。我国由农业文明进入短暂的工业文明,并又跟随历史的车轮进入现代文明。文化形态由前喻文化向并喻文化过渡并迅速转向后喻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当今,老年人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局势受到强烈冲击,年轻人跃上历史的前台,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逐渐占据人类发展的主角,在诸多社会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掌握更多的重要权力。凡此种种,为那些主体存在缺陷的青年进行腐败提供了权力前提和时代机会。
二、现行干部政策中过分强调年龄限制等局限,为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埋下了祸根
现行干部政策中比较严格规定了在相应级别的政府机构中,必须配备相应年龄的年轻人作为领导干部,这就为一些年轻人拥有较好的职位和较大的职权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同时,在我国目前干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个主要局限,就是干部选拔制度上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对干部的选拔都有一个标准,其中既有软条件,也有硬指标。但软条件如思想品德素质、革命意识、政治觉悟方面等都不是很容易操作,而硬指标如年龄、产值、政绩等很容易量化。尤其是在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的观念下,过分强调年龄限制,甚至搞“一刀切”,刻意追求“年轻化”。同时也忽略了我党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干部选拔和评判机制和标准,没有坚持德才兼备,只强调才能或者年龄方面,却将品德和政治素质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这一点却埋下了腐败的祸根:那些意志薄弱、自制力差的政治素质低、道德水准差的年轻人更容易走入腐败的泥淖。
三、社会控制机制的不足与缺陷,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这个社会问题的滋生和蔓延
腐败行为的危险性决定着腐败主体的腐败动机强烈程度和行为取向。如果腐败危险性低而腐败收益大,对腐败惩处弹性过大、各种处罚规则不严密,使腐败者在说情风、人情风的荫庇下逃脱法律的制裁,或者以腐败的方式打击另外的腐败行为,导致腐败的“安全系数”过大而“危险系数”过小,不仅不能使腐败行为有所收敛,相反却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腐败的动机并将付诸于腐败的实际行动。因此,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既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结果,也是社会控制机制在青年群中疏于防范和其本身缺陷的产物。
1、社会控制机制存在的不足及缺陷,不能有效防范腐败主体中青年群的凸现。现行社会控制机制存在诸多不足及缺陷,其三种主要控制手段——组织控制、道德控制和法律控制相互之间功能不和谐,各主要控制手段内部次因素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未能对先于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之前的“59岁现象”和“39岁现象”进行有效治理,从而使青年群中一部分掌握公共权力者产生侥幸心理,步入了腐败的泥淖地。同时,加之现行社会控制机制的不足及缺陷,对既有腐败现象处理和惩罚较为宽松,也是导致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重要原因。
就组织控制来看,在腐败的处理上,它存在三个比较明显的缺陷。一是大量以党的文件、行政文件来预防腐败,监督机构过分政治化,倾向于行政建制,未能赋予其社会性和法律性的独立地位。二是办理腐败案件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干扰性过大,不能使腐败问题依法得到及时处理。相反,在客观上促使腐败分子醉心于编织社会关系网,营造腐败群体,以求最大利益和最大的安全系数。三是惩处腐败上,一方面是以党纪政纪处分,甚至以“异地为官”等方式代替法律来惩治腐败,基本起不到惩治腐败的作用。腐败的收益大大高于腐败的成本,这种现实的存在使那些“前腐后继者”往往有极大的内在驱动力,投入腐败者的行列。
道德控制功能的充分发挥以组织控制或法律控制的有效发挥为前提。但当前在一部分人中仍存在一种心理趋势,期望通过强调道德控制,或者强调道德控制配合组织控制,试图以此作为防御腐败进攻和腐蚀的盾牌,以道德良心的谴责代替法律制裁和组织惩罚,从而将腐败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程度和范围内。结果是贻误制度建设的时机,降低了腐败成本,从而使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未能在道德控制下有所收敛,相反利用多重的道德标准为腐败寻求借口,满足心理失衡的慰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助长了腐败的蔓延。腐败的青年主体一般说来思想品德素质和职业道德意识较差,道德控制功能的弱化,从良心谴责上减轻了他们贪污腐败所带来的耻辱感、沉重感,于是在众多的诱惑下难以自持,不知不觉地踏入腐败的雷区。
现实生活中的法制控制仍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与社会控制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须将法律控制置于其核心地位的要求相矛盾。因而导致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基于利益关系、互惠的交换关系以及不可预测的人情关系的组织控制,对腐败惩处弹性过大、各种处罚规则不严密,使腐败者在组织控制的荫庇下逃脱法律控制的制裁,形成了以腐败的方式打击另外的腐败行为,结果是旧的腐败行为还没有得到有效惩处,却又出现了新的更为严重的腐败行径的不良后果。同时,法律控制本身存在制度建设滞后的局限,一方面是立法滞后,另一方面是法律制定过程中的应急性、阶段性强,缺少超前意识。法律控制常常尾随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对腐败问题解决的滞后性,大大降低了反腐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实施法律法规所需人员的素质、法律控制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了法律的软弱,甚至是司法腐败。法律的软弱,是对腐败的无奈和纵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成为了腐败的帮凶或者本身就成为腐败的主体。
2、社会控制机制疏于对腐败主体中的青年群的防范。我国一直以来,曾经存在的腐败主体也多为中年或老年,青年只是占很少的比例,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倾向不具有普遍性。因此社会控制机制重点在于防范和惩处老年和中年的腐败主体,未将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对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社会问题疏于防范。随着社会分化和变迁,青年跃上历史的舞台。同时,腐败范围、腐败对象及腐败主体等在各方面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腐败主体中青年腐败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已具有社会问题的属性。但社会控制机制并未对以往的控制方式和行为进行与时俱进的改进,仍然疏于对腐败主体中青年群进行防范和控制,使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社会问题的生存拥有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因此,社会控制机制的不足与缺陷,以及对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社会现象疏于防范,导致不能及时将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社会问题消除在其萌芽状态,而在一定程度上却纵容了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社会问题的滋生和蔓延。
四、腐败青年主体自身的主要缺陷是造成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决定性因素
事物发生变化,内因起主导作用。腐败的青年主体,其自身的主要缺陷是致使其腐败的决定性因素。
1、青年群体本身的局限性,使腐败进攻青年的可能性增大。年轻人由于其生理特性及人生经历短、阅世未深和社会经验少等导致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年轻人血气方刚,勇于突破陈规陋习,富有大胆革新和创造精神,但他们又桀骜不驯,喜欢过着不受拘束的生活,工作上也不愿有所羁绊,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试图摆脱各种纪律的约束和相应机构的监督。同时,长期的学校生活,使他们的人生经历较为单一,他们拥有的主要是书本上的知识,缺乏对实际生活的了解和社会生活的磨炼;他们未受过革命的洗礼,思想上比较幼稚,加之社会整体道德氛围和环境较差,导致他们的公共道德意识、职业意识以及法律意识等都相对较差。这就是导致他们腐败的最为关键的思想因素。
2、失去监督和制约的腐败青年主体在当今社会已经拥有更多的腐败机会,成为腐败主体中青年群凸现的社会问题的诱发因素。具有腐败的机会是腐败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想腐败,腐败主体必须占据一定的社会职位以及拥有相关的职权、信息和资源等。职权越大、社会地位越高,其拥有的腐败机会就越多。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越往上层社会流动,其拥有的职权就可能越大、拥有的信息和资源等就越多,其拥有的腐败机会就越多。进入现代社会,向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主要依赖于教育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同时,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落实及深入发展,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的现实,年轻人这个年龄段的主体享用着时代和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最有可能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他们是这些战略和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和最大受益者。
通过对腐败青年主体的分析可知,他们一般具有较高学历或职称、较强的业务能力或素质,即他们具备较多的人力资本,较年轻人总体水平为高,尤其是大案的主体,一般都是大学文化程度及其以上。因此,在逐渐转向由人力资本决定社会流动的社会,他们可以流向更好的社会阶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具实权的职位。也就是说,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腐败机会。但是,他们的高人力资本,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人力资本。因为这种人力资本只关涉其科学技术水平和职业能力或素质,却很少或根本不涉及其思想品德素质和职业道德意识。另外,许多领导以放手让年轻人大胆地干、大胆地闯,不干预其工作,当成自己识贤重才的标志,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使这些人拥有了失去制约和监督的实权、大权,致使其腐败的机会无限地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又诱使了其腐败动机的强化。
3、腐败的青年主体具备强烈的腐败动机,驱动着主体有缺陷的青年进行腐败活动。腐败的青年主体的腐败动机既有自己内在欲望激发的因素,亦有外在的社会现实的教唆的作用,是内有动力外有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在动力的腐败动机。首先,年轻人正处于成家立业和发展各种爱好兴趣的关键时期,各方面都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尤其是在暴富群体奢靡生活的示范作用引起的攀比心理、暴富阶层丰富的经济收入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导致官员的相对剥夺感等情况下,更容易使这些追求时尚生活、以会过“现代”生活标明自己“思想解放”的年轻人群体追求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有限的收入与庞大支出的矛盾,便依靠非制度化的方式,即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受贿等腐败手段来加以解决。其次,以越轨的方式满足对成功的渴望。年轻人有着更强烈的成就动机。当其所处的职位和相应的职权不能满足社会对其成功的渴望,年轻化的腐败主体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承认的成功目标,即拥有大量的金钱和财富,在正当途径不可能达成其目标的情况下,采用了社会不承认的违法的手段去实现。再次,他们想趁着自己年轻,积极购买政治人身保险,进行政治投资,建立政治经济安全网。于是想方设法多捞票子,垒起再上仕途“台阶”的物质基础;以打破“规矩”开拓工作局面去搏得领导赏识,走领导“捷径”,从而试图得到提拔重用。酿成的后果不是陶醉于灯红酒绿之中,就是醉心于编织社会关系网,或者就是破坏已有制度的约束力、丧失自己、单位甚至是社会发展的机遇。
外在压力的腐败动机。腐败的青年主体的外在压力首先来自自己的同辈群体,因为一个人社会地位及成功程度的主要比较对象是其所在的同辈群体。人人渴望成功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志是财富的多寡而不再主要是权力的大小。于是,以权力谋取钱财的念头不由而生。其次则来自自己的家人及其亲朋。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庭、家族至上的传统里生存的中国人,有时很难摆脱家庭、家族编织的压力网络,尤其是由家庭或家族的经济力量或全部资源资助而成为官员的年轻人,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家庭或家族谋取钱财或其他利益被认为理所应当,否则便很难在家庭或家族中立足。再次来自社会。受“光环作用”的影响,社会对那些已经业有所成、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之辈,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期望,企盼他们更快更多地功成名就,在众多领域尽快地开花结果。而受能力、精力及素质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很难达到社会期盼的高度。但是,为了保住社会曾经给予他们的光环和桂冠,他们不惜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幸的后果往往是导致了“旱地拔葱”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