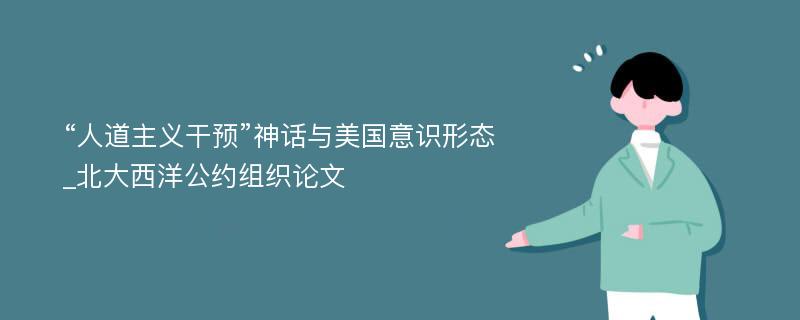
“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人道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人道干涉”论在西方被炒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大有取代以联合国宪章 为基础的现行国际关系准则之势。以“人道干涉”为核心的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对非西方 国家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造成了极大威胁,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其实, 所谓的“人道干涉”并无人道可言,只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冷战后全新的国际政治结 构下,为确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所散布的神话,是为美国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 新干涉主义树立法理依据所做的舆论准备。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索新干涉主义的意 识形态根源,并根据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干涉政策中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利益和 国家实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前景做一简要分析。
一、“人道干涉”的由来
“人道干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指导原则之一由来以 久,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最初全面推出“人权外交”的卡特政府,企图以此在 美苏全球争霸中,为失去势头的美国重新夺取道德高地,然而当时美国还受多方制衡, 在“人权”和“人道干涉”问题上尚不具备冷战后取得的为所欲为的主宰地位,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这一双刃剑的掣肘,结果导致外交挫折,“人权外交”难以为继。
“人道干涉”论再次兴起是在冷战结束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美国沿 用多年的反苏遏制战略已不复适用,亟需寻求新的全球战略;尤其是美国过去干涉别国 内政时一直使用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保卫自由世界”等口实已不再有效,需要 新的替代物。在随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中,一股被称为“道德政治论”的思潮鼓吹 抓住美国独霸世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对全世界进行“道德征伐”(moral crusa de),根据美国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世界,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对美国认定的所谓“ 无赖国家”(rogue states)的内政进行干涉,这就是所谓的“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 义主张向全世界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包括人权、民主和资本主义,其核心部分是以“捍 卫人权”自命的“人道干涉”,即美国有权对发生“人道灾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 干涉,包括除掉它所认定的违反人权的政府[1]。“人道灾难”是一个非常含糊而又宽 泛的观念,以此作为美国在全世界进行军事干涉的理由虽然可以给美国极大的主动权, 却也可能因此过度增加美国的干涉负担,或者会让美国因为对真正的人道灾难袖手旁观 而陷入道义困境。因此,尽管美国朝野不少思想库、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人道干 涉”的研究和宣传注入了极大的热忱①(注:有意思的是,“人道干涉”论在美国自由 派(包括威尔逊自由派和冷战自由派)和保守派(主要为新保守派阵营中都获得了广泛的 支持。自由派的布鲁金斯学会和《外交事务》杂志,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世界 事务》、《国家利益》等杂志在这场讨论中都很活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美国和 平研究所和半官方的全国民主基金会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例如前者早在1992年就组织 有关“人道干涉”的讨论会,并出版了题为“人道干涉问题上的三种观点”的研究报告 (U.S.Peace Institute,Three Views on the Issu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而且还带动了相当一批国际组织积极响应②(注:例如,早在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 就通过了第688号决议,宣布伊拉克政府对其国内的库尔德族和什叶派穆斯林的迫害已 经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为美英等国派兵进入伊北部进行武装干涉开了绿灯。 这是联合国首次把一国的内部局势定性为国际威胁,从而为国际干涉提供了法理根据。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还宣称:“我们显然见到公众态度正在也许是无法抗拒 地转向一种理念,即以道义的名义对被压迫者实行保护应当超越边界和法律文件。”[1 ]联合国提倡的“人道干涉”与美国略有不同,主张干涉必须经由联合国批准、执行, 而不能由美国独断独行。可是现实中真正能够决定并实施干涉的是美国而不是联合国, 因此联合国对“人道干涉”的赞同只能起到为美国干涉提供合法依据的作用。),美国 政府在正式表态中对它还是持审慎态度,强调美国的卷入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是“ 促进美国安全利益的有用工具”,因而美国的干涉应当是“有选择的”[2]。后来的事 态发展表明,美国官方对“人道干涉”作低调处理有助于它在波黑、卢旺达和其他许多 地区发生的人道灾难面前逃避道义责任。
美国及其盟国对“人道干涉”的宣传造势在科索沃战争前后达到了高潮。1999年4月22 日,正当美国和北约对南联盟狂轰滥炸期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芝加哥发表的讲话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后来被称为布莱尔主义的“国际共同体主义”,成为“人道干涉”论 的正式宣言。被布莱尔的“国际共同体主义”系统化了的“人道干涉”论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的内容:其一,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而且也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的现实,世界已 经变成一个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国际共同体”。其二,任何国家的内部事 务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和人民,而其他国家和人民自然有权进行干预。因此, 关于主权和国界的传统观念和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原则都必须加以修正。人道灾难尤其是 种族屠杀不复被视为内部事务;而当对内压迫产生出巨大难民潮对邻国造成冲击时,就 应以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论处,由联合国或者当联合国无法行动时由西方 国家出面进行国际干涉。其三,现存的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主要为联合国及其安理 会)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加以改革,建立“人道的国际新秩序”,使“人道 干涉”不再同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秩序冲突而享有法统的正当性。其四,西方国家进 行“人道干涉”是出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考虑:它所带来的和平、稳定和秩序有利 于企图维持现状的西方国家,而它所促进的“自由、法治、人权和公开社会”的价值观 既满足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又有助于它们的国家利益,因为“我们价值观的传 布使我们更加安全”[3]。
一个体现西方全球战略新观念的重大主张不是由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总统来宣布,而是 由一个美国的伙伴代言,这里自有其奥妙。美国官方对“人道干涉”的态度一向谨慎, 即使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亟需利用它去煽动公众的支持时,在高层正式表态中也从不对它 作一般性的原则论述,更避免做出广泛的承诺。这倒不是美国不存这样的居心,而是它 另藏玄机:除了如前所述担心把伪善的调子唱得太高会束缚自己,使自己陷于被动之外 ,美国还担心公开号召修改以至废除主权原则会大大削弱现存国际秩序,风险太大,搞 得不好反而会损害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再说如果由美国官方出面提倡“人权高于主权” 的观点,将使美国本国颇成问题的人权纪录受到国际监管,这是从不容忍本国主权受到 半点外来限制(如国际组织或国际公约)的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一 方面利用美国和西方在理论、传媒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及其对本国乃至世界舆论近乎垄断 的影响,在全世界做好“人道干涉”有理、合法的舆论准备,从而当美国需要利用“人 道干涉”为由进行干涉时可以师出有名;另一方面政府却故意不把话说死,为自己留下 充分的转圜余地,以握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权。说白了,美国既想拥有以“人道” 为由进行干涉的权力,又不想承担因充当“人道卫士”而引起的义务,因此故意态度暧 昧。
美国这一策略在科索沃战争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民间享有较高信任度的“自由” 媒体和舆论领袖同政府配合默契,对公众进行大剂量、高强度的“信息轰炸”和舆论引 导,成功地营造了美国举国上下从自由派到保守派同仇敌忾支持“人道干涉”的共识, 开创了自越战以来美国新闻舆论界主动配合政府进行涉外战争宣传的先例,这也是美国 外交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当然,单是民间舆论还不够,还缺乏权威性,所以美国 很乐意由布莱尔来填补这一空白,让他以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的身份 ,在美国发布新干涉主义的宣言,为“人道干涉”论抹上一层非官方的官方色彩(对美 国而言),也为北约轰炸加上一圈道义光环。这样,搞得好,布莱尔的“国际共同体主 义”讲话将可媲美半个世纪前温斯顿·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成为划时代的宣言;搞得 不好,美国尽可不必为一个英国人的言论负责。
布莱尔的“人道干涉”论是为北约侵略南联盟制造舆论的,而北约的侵略战争又为西 方大肆宣扬的“人道干涉”论提供了一个最明白无误的注脚,可以帮助人们弄明白西方 所谓的“人道干涉”实际上是什么货色。科索沃战争能不能算作“人道干涉”?如果不 能,那么“人道干涉”究竟是否存在,抑或只是西方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制造的 神话?让我们通过案例分析来寻找答案。
二、人道是假、干涉是真
根据西方的定义,“人道干涉”的目的是制止人道灾难,而人道灾难则是指平民因天 灾而大量丧生、流离失所,或因战争或种族清洗等人祸遭受大规模屠杀、迫害和驱逐。 按照这个定义,人道灾难在科索沃不是发生在北约干涉之前,而是发生在北约干涉之后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官方宣传和新闻媒体为了给北约的侵略提供口实,不惜歪曲事实, 谎报军情,故意把北约干涉前在科索沃发生的一场有限的种族冲突和因此引发的小规模 、低烈度的平叛内战夸大成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吹嘘北约的轰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为“制止种族屠杀”而进行的战争。事实究竟如何?
科索沃是南联盟的一个省,其200万居民的90%以上为阿尔巴尼亚族,其余为塞尔维亚 族。1995年,数千从克罗第亚逃亡的塞族难民进入科索沃定居,引起阿族的不满和对塞 族人的骚扰、迫害,甚至有小股恐怖分子攻击塞族村落,犯下烧杀劫掠等暴行。南联盟 警察部队依法清剿匪徒,而阿族分裂主义分子则在西方的唆使、支持下,公然打出科索 沃解放军的旗号发动叛乱③(注:1997年,阿尔巴尼亚因经济原因发生动乱,美国趁机 煽动叛乱并对阿政府施压阻挠其恢复秩序,导致阿政府危机和全国无政府状态。美国及 其西欧盟国趁乱通过阿—科边境向科索沃解放军运送先进武器装备,在阿为其招募兵员 并对叛乱分子进行游击战和恐怖活动训练。见《纽约时报》1998年7月11日报道。)。以 后在科索沃发生的,就是一场规模和伤亡都极其有限的平叛内战,其间双方都犯有在种 族冲突中常见的仇杀和虐待无辜平民的暴行④(注:根据战争爆发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的一份实地调查称,违反人权的行为,包括绑架、谋杀和任意拘押等,在科索沃,塞、 阿双方都时有发生。调查组发现的证据包括一处理有14具阿族受害人尸体的坟坑和两处 共埋有40具塞族受害人尸体的坟坑。见《纽约时报》1999年4月2日报道。)。这些暴行 的数量和范围都不大,而且并非一个种族对另一种族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施暴,远 不能同西方大肆渲染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相提并论。根据普遍接受的估计, 科索沃双方在北约轰炸前被杀害的平民人数不过两千,难民人数约十万。美国著名政论 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指出,把这类种族冲突称为“种族屠杀”是对真正种族 屠杀受害人的侮辱;假如这也算“种族屠杀”,那么世界上种族屠杀比比皆是,例如哥 伦比亚内战每年都造成更多的伤亡和难民,然而正是自称对科索沃的“种族屠杀”无法 忍受的美国,一直在大力支持哥政府军对主要为印第安人的游击队进行的“种族屠杀” ,使哥成为西半球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4]。
北约的轰炸导致南联盟军警强化对科索沃阿族叛乱的镇压,也增加了对阿族平民的驱 逐和暴行。北约的侵略使南联盟的国家安全以至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而科索沃阿族在轰 炸期间配合北约制造骚乱并为北约空袭提供情报和地面信号也已构成叛国罪行。任何国 家在处于紧急状态下对叛乱活动都会采取一些极端措施,而且阿族为北约轰炸指点目标 也激起塞族义愤,引起一些自发的报复行动。然而即使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在科索沃也 没有发生过西方媒体宣扬的“种族屠杀”。同美国当年在朝鲜的“老根里惨案”和在越 南的“美莱村惨案”中集体屠杀平民的暴行相比,南联盟军警的行为要克制得多、温和 得多。北约占领科索沃后动用大量人力寻找臆想中的“万人坑”和“强奸营”,结果一 无所获⑤(注:北约入侵科索沃后,战争罪行的国际调查人员在科索沃到处挖掘,一共 发现二千多具尸体,其中阿族占多数,还包括部分死于北约轰炸的受害者。见路透社20 00年5月14日电讯。)。北约占领一年后,北约扶持下的科索沃阿族法庭审讯了第一宗“ 种族屠杀”案,被告被控在战争期间杀害一名并指使他人杀害另一名阿族平民。将一个 一共只涉及两起死亡的案件作为“种族屠杀”起诉,不啻对“种族屠杀”和国际法的嘲 弄,在国际上传为笑柄⑥(注:路透社2000年5月15日电讯。)。按照这样的标准,纽约 三名种族主义警察把一个完全无辜的黑人当成枪靶子射了41枪的谋杀案,就更应当以种 族屠杀论处,然而在美国这三名凶手却获无罪开释,得以逍遥法外。
在科索沃,北约的狂轰滥炸使外逃难民从原来的十数万激增至约百万,用联合国大学 一份研究报告的话来说,就是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洪水”[5]。美国的精密炸 弹还屡屡击中难民车队,使上千阿族人死在他们的“解放者”手中。尤为恶劣的是,美 国和北约的“人道之师”还在轰炸中使用了国际禁用的、专门用于增加对平民杀伤力的 集束炸弹和贫铀弹,造成大量妇女儿童的伤亡和环境的放射性污染。北约的轰炸共使万 余人丧生,更多的人伤残,伤亡数倍于轰炸前的“人道灾难”。北约的轰炸和占领给科 索沃带来了什么呢?是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是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是有加 无已的种族仇恨和人人自危的无政府状态。在北约占领军的纵容下,阿族暴徒有恃无恐 、变本加厉地对塞族进行种族迫害,塞族平民被杀害、妇女遭强暴、住房被烧毁的事件 时有发生。据统计,在北约占领的一年中,共发生了4500多起袭击塞族平民的事件,有 800多人遭杀害⑦(注: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000年5月29日专电。)。更有甚者,北约占 领军尤其是美军也加入了迫害塞族平民的行列,对其随意搜查住所,无端拘捕关押,极 尽恐吓骚扰之能事,使大量塞族平民无法忍受而逃离家乡,形成新的难民潮。
北约的轰炸不仅是科索沃人道灾难的真正开始,而且还把人道灾难带给了塞尔维亚。 北约在塞尔维亚特地选择民用目标狂轰滥炸,轰炸居民区、医院、学校、露天市场、公 共汽车、客运列车等以增加伤亡,轰炸桥梁、铁路、公路、发电厂、变电站等基础设施 以切断国计民生,轰炸炼油厂、化肥厂、制药厂等以造成毒物外泄、破坏生态,轰炸广 播电台、电视台和其他通讯枢纽以对南人民封锁事实真相。轰炸使100万人无家可归,5 0万人失业,200万人失去生计[6],使人民的生活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在停炸后相当长 的一段时期内都无法摆脱。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实质是把南联盟全体人民作为人质,以屠 杀无辜、摧毁家园为手段要胁南政府屈从于美国的霸权,这也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径,或 准确地说,是美国国家恐怖主义的生动表演。
美国及其盟国对科索沃的干涉既无人道灾难存在于前,反有人道灾难尾随于后,于“ 人道干涉”不只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应该称作“反人道干涉”才名 副其实。实际上人道救援从来都不是美国决定是否对外国进行干涉的主要考虑。在20世 纪几场真正能称得上种族灭绝的人道灾难中,美国都是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30年代 ,当纳粹德国开始在欧洲消灭犹太人时,美国拒绝接受犹太难民;70年代,在红色高棉 屠杀了上百万柬埔寨平民后,美国仍支持保留它在联合国的席位;90年代,在联合国已 明确获知卢旺达将有种族屠杀发生后,美国阻挠、拖延增派联合国维和部队去制止,致 使80万平民在屠杀中丧生⑧(注:见美联社1998年12月15日电和路透社2000年4月14日电 。1999年底发表的一份联合国调查报告和最新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都证实了这一指 控,见路透社2001年8月22日电。),而这还仅仅是美国见死不救、阻碍或拖延联合国维 和行动一贯做法的冰山一角。反之,美国干涉造成的人道灾难倒不在少数,如美国在19 54年颠覆危地马拉的合法民选政府后导致的军人独裁和内乱使20万人丧生;又如美国在 1965年支持苏哈托在印尼发动军事政变,屠杀了50万政治反对派;再如美国在海湾战争 后对伊拉克实行的经济封锁,在截至1996年的5年内已使50万儿童因生活条件恶化和缺 乏医药而夭折,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还称这个代价是值得的[7]。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
克林顿一再强调科索沃战争是“为价值而战”,是为了制止“种族灭绝”的“人道干 涉”;而美国在近二十年里也一直以世界的“人权卫生”自居,声称人权是西方价值观 的核心。不错,西方是有重视人权的传统,马克思曾把美国的独立宣言称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人权宣言”[8](p.256)。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西方价值观崇尚的人权首先是 至高无上的白人的人权,而“非我族类”的所谓“劣等民族”却得不到平等的权利。历 史上美国政府就曾对北美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在截至19世纪末的近三百年中, 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遭到美国联邦军队和白人移民的驱赶屠杀,人口从约1000万骤降至 24万⑨(注:见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99,microsoft Corporation,(multim edia edition)及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official Web site(www.census.gov) .),几近灭绝;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和修改法律,使美国白人可以“ 合法”地、步步进逼地将原来属于印第安人的美国境内土地抢夺殆尽;更令人发指的是 ,迟至193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印第安重组法”,授权政府把生活在少量印第安保 留地上的、还保持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印第安家庭拆散,用暴力把儿童从他们的父母手 中夺走,送往数千英里以外的寄宿学校强行洗脑,以消除印第安文化的一切“邪恶影响 ”,甚至连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交谈都要加以残酷体罚。屠杀人民—掠夺土地—消灭文 化,世界上的种族灭绝,没有比这更彻底的了。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特征。我们今天聆听美国高谈阔论“人权”和“人道干涉”时,不妨把这 段历史重温一下,权当一个小小的备注。
当然,美国海外干涉有时也会产生人道救援的附带效果,例如美国在“二战”中最终 参加对德作战,对击溃纳粹、解救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起到很大作用;又如它对波黑内战 的干涉,尽管耽误了三年,未能及时防止25万平民遭屠杀和200多万难民的流离失所, 但它毕竟还是促成了停战与维和的成功。然而美国在这些事件中最初坐视人道灾难的蔓 延而无动于衷的事实说明,人道因素在其是否进行干涉的决策中的分量是无足轻重的。 美国尽可大肆标榜这些干涉的人道性质,但实质上人道因素在这些案例中只是搭了其他 决策动机的便车而已,并不是美国干涉的主要或原发性动机。如果真正出于人道目的的 人道干涉并不存在,那么美国海外干涉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三、美国海外干涉动机之谜
美国海外干涉的动机无外乎两大类:一是国家利益;二是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包括战 略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等等。战略利益系指有利于改善和加强美国的战略态势, 如使国际力量对比朝对美国有利的方向转化,或增强美国对战略要地和战略资源的控制 ;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维持美国主张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的威信;经济利益包括对海外 投资和商品市场及其他经济资源和产权的占有和保护等等。意识形态是指美国信奉的社 会政治价值观,包括人权、民主和资本主义等。美国海外干涉的动机往往是多重的,可 以包括多种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可是在对美国海外干涉历史仔细考察之下,可 以发现其中不少案例是既无法用国家利益动机也无法用通常理解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的。
还是以科索沃为例。为了向美国公众兜售他干涉科索沃的决定,克林顿宣称那是为了 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他罗列了一大堆理由,几乎涵盖了上面提到的所有因 素,但却少有能够成立的论据。他将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同当年的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 ,声称南在科索沃的“侵略”如果不加制止就会蔓延开来,威胁欧洲稳定和世界和平, 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然而克林顿忘记了科索沃自从1918年南斯拉夫建国以来 就是它的一个省,他也没解释一个国家怎么能够侵略它自己。何况南联盟的国家实力同 希特勒德国有天壤之别,根本不具备对欧洲稳定和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能力。即使几年 前在波黑发生的远比科索沃严重的战乱也并未颠覆欧洲稳定,更遑论祸及世界和平与美 国繁荣。克林顿还声称在南联盟拒绝接受美国和北约以武力威胁后如不兑现使用武力, 则美国和北约的威信将大打折扣。但这实在是一种拙劣的诡辩,它掩盖了美国从一开始 就没有理由威胁使用武力的前提。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强国在任何情况下都 可以找到干涉别国的理由了——只要先用武力胁迫对方接受一些不可能的条件,然后再 出兵“捍卫”自己的威信。顺便说一下,对北约轰炸的动机,一些观察家们特别钟爱一 种“战略利益”的解释,即北约急于摆平南斯拉夫是出自东扩的需要。但是只要看一眼 欧洲地图便能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因为它无法解释急于东扩的北约,何以将位于南斯 拉夫以东且迫切要求加入北约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拒之门外,却要对南斯拉夫加以武 力威逼。
克林顿自然少不了用维护西方价值观念为轰炸辩护。他讲的西方价值观念首先是指人 权或人道,关于这点前面已经有过分析评论。他的另一层意思是向南联盟输出民主,这 可以从他本人以及其他美国及盟国的军政要员反复把米洛舍维奇称作“暴君”、“独裁 者”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宣言中看出。可是克林顿们不可能不知道在南斯拉夫早已存在 民主政治,包括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总统、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示威游行和集会,等等。 且不说北约轰炸的实际效果使反对派和独立媒体因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而受到钳制,单是 向南输出民主的说法原本就讲不通,因为南斯拉夫不需要西方把它已经有了的东西强加 给它。不仅如此,克林顿们对于向南输出民主何以同维护西方价值观念挂钩的解释也牵 强附会。布莱尔引用约翰·肯尼迪的话说“自由是不可分的,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受奴役 ,谁能自由?”然而他们却忘了,在美国黑人受奴役的两个世纪里,即使近在咫尺的美 国的白人不也照样活得自由自在、心安理得吗?就算是南斯拉夫没有民主,又怎么会影 响到远在天涯的美国及其价值观呢?伪善之辞,莫此为甚。这使人想起过去英国曾以贩 毒为由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曾几何时,美国又以禁毒为名对巴拿马发动侵略战争。只 要强权在手,反正都是它的理。如果美国对科索沃的干涉既不能用国家利益、也无法用 通常理解的意识形态解释,那么它的真实动机究竟何在?这成了美国海外干涉动机的一 个难解之谜。
问题的答案在于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独特成分,即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 ism)。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对人类世界抱有的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信念体系,它的核心 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总和,但内容却更为丰富也更为实际,包括对人和社会的解释和评 价,引导价值判断的规范理论和作为奋斗目标的理想境界,以及把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 纲领和宣传纲领。通常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其美国版本就是上面提 过的人权、民主和资本主义。但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分支——以美国 特殊论为内容的民族意识形态,它由美国优越感和使命感组成。美国人历来认为美国式 文明,从价值观念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远比其他民族优越,堪为世 界楷模,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从这种优越感又派生出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认为美利 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负有天赋使命,向全世界传布美国文明,按照 美国模式改造世界。这两条信念不仅使美国的对外关系必然具有扩张主义性质,而且还 使这种扩张主义具备了顺应天意、理直气壮的道德正当性。从当年美国在“神授天命” (Manifest Destiny)的旗帜下屠杀的印第安人、扩张领土,直到今天在“人道干涉”的 口号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就都是这种优越感和使命感一脉相承的表现。
让外国政府听命于美国是按照美国理念改造世界的关键所在,是美国民族优越感和使 命感的具体体现,也是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不成文的目标。美国杰出的历史学 家和外交评论家阿瑟·施莱辛格曾对美国外交政策做过一针见血的总结:“美国政策的 功能就在于根据其他国家对我们规则的恭顺程度将它们划分好坏。”[9](pp.5~8)美国 前总统里根更为爽快,在1985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 叛乱的支持到何时为止时,他曾直言不讳地宣布:“直到他们(指尼加拉瓜政府)叫大爷 (say uncle)为止”。时任副总统的布什事后解释说,“叫大爷”的意思就是尼加拉瓜 建立同我们(即美国)类似的政府和社会[10](p.669)。有不服的就打,打到“叫大爷” 为止。里根使用的黑社会语言一语道破了美国干涉的天机。米洛舍维奇先是在波黑战争 问题上得罪了美国,继而又拒绝美国肢解南联盟的朗布伊埃协议,当然就只能落得令美 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下场。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复杂的信念和理论体系简化 成通俗易懂、便于掌握的口号和教条,成为帮助人们理解世事、指引人们行动的指南。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美国民族意识形态极端发展,为美国外交政策定下的实际 操作指南。掌握了这一条,许多既不能用政治意识形态又不能用国家利益解释的美国外 交决策之谜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四、美国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民族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是既联系又区别的概念,它们作为外交政策 目标既有一致也有矛盾。让一个外国政府听命于自己、按美国的意图处理内政、外交, 既能满足美国的民族优越感和使命感,又能扩张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还能为美国带来 实际利益,这当然是一举数得的好事。但是事情不都是那么尽如人意的。当美国面对一 个不听命于它的民主政府,或一个亲美的军事独裁政权时,它的民族意识形态同政治意 识形态就发生了冲突,而这种冲突的结果几乎肯定是颠覆独立的民主政府、支持亲美的 独裁政权,因为对于美国来说,臣服美国比民主人权重要,何况亲美政权有助于美国国 家利益的可能性也较高(但不是绝对如此)。这两种情形在冷战期间美国外交中均不乏其 例,譬如美国曾用直接入侵或秘密颠覆的手段推翻了一系列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主合法政 府,其中有伊朗的摩萨台(1953)、危地马拉的阿本斯(1954)、刚果的卢蒙巴(1961)、秘 鲁的古拉特(1964)、多米尼加的波切(1965)、希腊的帕潘德里欧(1967)、智利的阿连德 (1973)、尼加拉瓜的奥特加(1984—1990),等等。另一方面,美国还豢养和支持了不胜 枚举的右翼军人独裁政权,其中多数曾犯下最残暴的反人道罪行。
美国外交决策是对多种动机权衡取舍的结果。这些动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权衡 取舍的决策机制也十分微妙,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说,当这些动机之 间发生冲突时,根本国家利益具有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权⑩(注:这方面最有说 服力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中和解。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反美的国家之一,而 且当时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文革”极左影响之下,远比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更令美 国深恶痛绝,可是美国仍然选择联华制苏,这说明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考量可以超越任 何障碍。);在不涉及根本利益时,民族意识形态往往超越其他因素成为决策的操作指 南。同时,民族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以及非根本国家利益等诸因素,在影响政策上的力 量对比并非静态,而是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的改变而改变的。当国家实力相 对较弱时,意识形态的分量会相对少一些,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就会占较大的比重;当国 家实力上升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就会提升。当年美国还不是世界强国,就很少管别国的 事,尤其是意识形态的事。美国第六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独立日演说中 针对美国人的世界使命感告诫他的同胞:“美国不该到海外去寻歼妖魔。她为一切民族 的自由独立衷心祝福,却只是本国自由独立的斗士和捍卫者。对于一般人的事业她只能 表示声援,或以自己的表率作用给予支持。她深知一旦卷入为外国的事业而战,即使是 为外国的独立事业而战,就会陷入打着自由旗号、盗用自由名义、实际上却因利害冲突 和阴谋诡计或因个人私欲、妒嫉和野心而起的各种战争而无法自拔。她所奉行的政策的 座右铭就会不知不觉地从自由变为暴力……她则可能成为世界的独裁者。”[11](p.80) 对照美国对科索沃的干涉,人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然而,曾几何时,美国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过去的谦虚谨慎似乎成了多余,就 连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付出惨重代价学到的教训,也在90年代海湾战争的凯歌声中 被淡忘了。以意识形态扩张为核心的新干涉主义正在抬头,道德征伐的鼓吹者打起“新 里根主义”的旗号,就近两个世纪来一直被美国外交奉为圭臬的警句——“美国不该到 海外去寻歼妖魔”,针锋相对地发问:“为什么不?……在1823年(原文如此——笔者) 可能很明智的主张到了今天就不再适用。当年孤立弱小的美国面对的是欧洲列强的巨人 们,而今天的巨人正是美国……正因为当今世界秩序的和平安全如此倚重美国,洁身自 好和靠表率去领导世界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怯懦和迂腐。”[12](pp.18~33)不难预料, 只要美国的实力在世界上保持压倒优势,在今后几十年里,主张对外意识形态扩张的道 德征伐论和“人道干涉”论在美国国内就会有很大的市场,美国外交政策也将不可避免 地受其影响而带上新干涉主义的色彩。
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制约的情况下,对美国新干涉主义的限制只能主要依靠其国内的反 对舆论。美国公众对以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根本利益和重大利益为目的的海外干涉的 支持是坚定的,即使代价再高也在所不惜;但是公众对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海外干涉的 支持就完全不同,是有条件的、脆弱的和难以持久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是既没有坚实利 益基础也没有明确判断标准的情绪、愿望和主观意志。美国公众在顺境中被轻易激起的 理想主义扩张狂热,在海外干涉遭遇挫折、失败或招致沉重经济负担甚至生命损失时会 很快颓丧、退缩,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转向孤立主义。近年来美国经济出 现持续稳定的繁荣,增加了美国公众对海外干涉经济负担的承受力和容忍度;加上美国 采取让盟国甚至联合国分担干涉开支的做法,降低了本国的干涉成本。同时,美国在最 近几次海外军事干涉中都采用以空中打击为主的方式,大大减少了本国人员的伤亡,这 样就避免了因代价过高而反对干涉的公众舆论。这些都是削弱美国国内对新干涉主义制 约的因素,而且从目前形势来看,这些因素都还将持续一段时期,甚至还有增强的趋势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新干涉主义还将横行一时。可是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不可能永远上 升;美国干涉的国家不会都象伊拉克或南斯拉夫那样易于征服,而且战火一起也不会总 是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让美国占尽优势;国际社会尤其是非西方国家也不会永远一 盘散沙、任人宰割。只要美国一意横行下去,它的第二个越南不会很远了。
标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神话论文; 科索沃战争论文; 南联盟论文;
